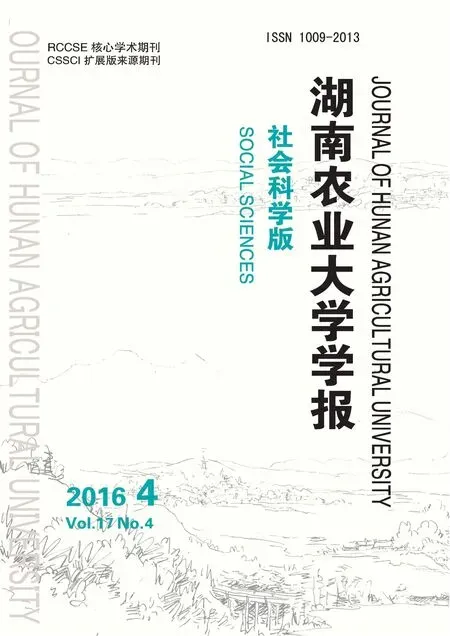农村消费型贫困的发生机理与治理策略
——以鄂东S镇农民建房为例
郑晓园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农村消费型贫困的发生机理与治理策略
——以鄂东S镇农民建房为例
郑晓园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鄂东S镇农民建房消费现象显示:随着收入型贫困的减缓,因消费超出支出而导致的消费型贫困日益显现,农村贫困的性质和形态正发生深刻变化。城市消费主义的示范与扩张、半熟人社会村庄分化的消费转型以及婚姻市场化下农民家庭再生产的消费导向,构成了消费型贫困的发生机理。消费型贫困具有较强的社会结构因素,单纯依靠农民自身难以得到有效根治,应强化地方政府主导功能,节制无序的建房消费竞争,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加强包括文化价值在内的新农村建设,以加强对消费型贫困的治理。
农村;消费型贫困;发生机理;治理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学界普遍从收入角度界定贫困,认为贫困是一种收入不足带来的经济困境[1-2]。围绕贫困成因,经典贫困理论形成了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两大派别[3]。结构主义将贫困归因于外在结构,认为制度设置、政策安排、群体利益争夺等社会力造成的不平等是贫困产生的根源,市场供求关系波动导致失业等经济力产生的贫困也具有不可抗拒性。文化主义[4]将贫困归因于某种亚文化(例如贫困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例如人口素质、知识贫困或人力资本缺乏),其中,贫困文化理论认为穷人对贫困产生适应性的规范和价值观,包括屈从感、缺乏计划和自我控制等,进而限制他们抓住机会增加收入。而在具体的经验研究领域,过去 20年农村贫困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性贫困问题上[5]。而关于区域性收入困境的原因探析主要围绕要素缺乏展开,包括自然条件制约[6]、经济区位的劣势[7]以及人口问题[8-9],认为这些要素的缺乏导致了农民的低收入困境。
无论是经典贫困理论还是贫困经验研究都将贫困视为一种收入困境,收入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尤其是贫困理论体系日益完善,对于贫困治理政策和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然而,收入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忽视或掩盖了贫困的变迁与多元性,贫困被简化为收入问题;其二,贫困经验研究在经典贫困理论的框架下展开,但是对于贫困现象的解释停留在表层,并且对于贫困产生的深层机理缺乏解释力;其三,贫困与贫困治理的关系也被简单化,治理贫困指向单一地提高收入,造成了一定的方向误导。
就当前中国农村而言,贫困的性质和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城乡关系的系列转变带来了市场的开放与收入机会的增多,使得农村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弱化,农民通过城乡流动的打工经济进行劳动力要素有效配置,从而实现了收入水平的提升。然而,农民在摆脱收入型贫困[10]的同时,又陷入一种更加显著的消费型贫困,突出表现为建房潮流、人情异化与赌博盛行。在城市化和市场化背景下,乡村社会和农民生活逐渐被消费所主导,农民家庭逐渐陷入支出困境,农民的贫困表达不再是“收入不足”,而是“消费太大”。与农民收入问题引发的高度关注不同,因消费所引发的贫困问题并未引起足够关注。与城市消费相比,农村消费一直被认为是不足的[11],政府也一度出台“刺激农民消费”[12]的相关政策。事实上,消费越来越构成农村贫困的新诱因,农村贫困的发生机理正在改变。
随着贫困类型的变迁,贫困研究视角面临从收入型贫困到消费型贫困的转换。收入型贫困一般通过“贫困线”进行衡量,贫困线指特定时空条件下维持人们基本生存所必须消费的最低费用[13]。本研究中消费型贫困是指处于“最低收入”之上的消费超出收入的经济困境,并且无法通过收入进行指标化。打工经济提升了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但是后者增长的速度远远超出前者。以建房消费为例,农民消费行为呈现非理性面向,既超出实际消费需求,又超出自身收入水平和收入能力,既是超高消费,也是超前消费。消费型贫困是一个社会事实,它的深层含义是消费的失控。理解消费型贫困的关键在于消费的超出为何失控。笔者拟以鄂东S镇农民建房消费现象为例,厘清作为社会事实的消费型贫困的发生机理,并探讨相应的治理之策。
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经验材料来自于鄂东Q县S镇的田野调查。笔者及所在团队一行20人分成三组,在S镇先后进行为期10天与25天的驻村调查,调查涵盖7个典型村庄。在了解村庄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全面情况之后,围绕着建房消费、农民贫困、地方政府扶贫问题展开调查,并对农民家计模式、收支结构、建房消费进行了数量统计。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数据来源为Q县门户网站统计资料。
二、消费型贫困的个案分析
Q县是国家级贫困县,S镇地处低山丘陵,土地资源较为稀缺,人均6分、户均3亩,以双季稻为主要种植作物,山林资源开发价值不大。在普遍依赖农业收入的20世纪80年代,S镇是区域性贫困的典型代表:人地关系紧张,农业形态单一,人均收入低下,仅仅达到国家的贫困县标准即150元/年,农民抗风险能力缺乏。由于土地稀少、农业收入不足,S镇农民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离土离乡外出务工,形成年轻人外出务工、老年人在家种田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Q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高达60%。打工经济极大增加了农民的家庭收入,显著减缓了收入型贫困的发生。其一,农民家庭收入结构发生转型,收入来源多元化,并且对农业的依赖性降低,务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例不断提升。由于务工收入主要以货币收入形式呈现,打工经济对农民家庭的直接影响是可支配性收入显著增加。目前,当地一般家庭的年收入水平为3~5万,其中务工收入占比90%以上;其二,打工经济打破了传统小农经济的低水平均衡。农民家庭劳动力要素得以有效配置,高价值劳动力(年轻人)与市场结合,低价值劳动力(老年人)与土地结合,农民家庭收入实现了最大化。然而,收入型贫困的减缓,并没有将农民从贫困状态中解放出来。农民在摆脱收入型贫困的同时,又陷入了另外一种消费型贫困。
打工经济在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开启了农民的建房消费之旅。S镇花村4组共计42户,除了6户在县城和乡镇买房,其余农户全部在村建房。除了特别偏远的高山地区,当地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修建起了高大漂亮的楼房。S镇出现两次明显的建房现象:第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打工先富起来的农民率先建起两层楼房,村庄中的砖瓦平房逐渐消失;新一轮建房从 2008年开始至今,农民普遍修建三四层(五层的也很多)钢混式楼房替代原来的两层预制板式楼房。第一次建房是农民收入水平提升之后消费水平提升的自然体现,是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正常需求,而在新一轮建房大潮中,消费已经越来越与收入和需求脱钩。其一,建房消费规格高,远远超出当地农民的收入水平。修建一栋三四层连体式楼房成本至少需要30万,有的甚至高达四五十万,对于3~5万年收入水平的农民家庭而言,意味着要耗尽6~10年的所有积蓄,无疑产生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其二,建房消费超出农民的实际需求,新建楼房利用率极低,浪费极大。农民一般只装修下面1~2层居住,并且实际居住的只有 1~2间,上面的楼层通常被空出来堆放杂物或者作为隔热层,还有大量新建楼房因农民外出务工而直接闲置。这些楼房确实改善了农民的居住条件,但远远超出了实际需求。用农民自己的话说,“房子大了,就是(用来)装空气,装灰尘”。其三,建房消费动力强,而且趋于失控。农民新一轮建房来得集中而又猛烈,建房消费对农民而言成为必须实现的刚性需求。建房规格越来越高,从两层到三层、四层、五层,楼层不断攀升;建房周期短,房屋更新加快;房屋样式也不断翻新,由“在外面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引领,村庄建房“时尚”涌现。如花村刘某在 2000年时建了一栋二层楼房,2010年 “跟风”又建了一套四层楼房,建房周期不过十年,这种例子不在少数。
建房的巨大消费开支将很多农民家庭卷入贫困之中,S镇的徐镇长说,“农民一辈子就是为了建房,为了建房陷入长期贫困。”当地很少有农民能一次性拿出30万建房,农民建房的基本模式是“打工+负债”。一方面集全家之力,一边赚钱一边消费,在打工积蓄只有几万元时就开始谋划建房,一层一层地修建,并且是先建毛坯房的框架再慢慢装修,这样到完成建房往往需要5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另一方面负债消费,为了缓和资金压力,向亲戚、朋友借钱建房和赊欠建筑材料在当地极为常见,这就意味着农民在建房完成后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还债过程。对农民而言,建房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建房带来的巨大消费压力被分散在这个过程之中,并作用于家庭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农民不仅超高消费而且超前消费,造成了家庭的阶段性贫困。
贫困并非简单的经济问题,其对社会的影响广泛而又深入。首先,对于农民而言,消费形塑了新的家庭经济学。巨大的建房消费不仅将农民家庭卷入阶段性的经济困境,还挤压了教育、投资等发展性家庭支出的空间,而且降低了家庭的积累性,压缩了家庭的弹性空间,农民家庭因意外事件陷入绝对贫困的风险增强;其次,对于村庄而言,建房消费竞争产生了恶劣影响,不仅不利于有序的村庄规划和良好的居住秩序,还可能加剧村庄社会分化。不仅普通农民成为贫困群体的可能性增强,绝对贫困群体边缘化程度也大大提升,村庄社会结构的紧张加剧。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消费型贫困暗含了转型期村庄社会和农民生活的价值危机,村庄不仅不再是“低消费、高福利”[14]的场域,反而是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器。
三、消费型贫困的发生机理
S镇农民建房消费现象显示,农村消费型贫困的发生学表现为一个过程:从消费的增长到消费的超出再到消费的失控。消费型贫困的产生以消费的增长为前提。农村消费的增长客观前提在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长期以来,农民“储蓄”、“节俭”的形象深入人心。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S镇农民普遍处于“低消费”状态,农民生活很少与市场发生关联,本地消费市场发育程度很低。农民不需要消费,也抑制消费,这是与传统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和低收入水平相适应的。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农民逐渐摆脱收入型贫困,可支配收入显著增加,消费能力也随之增强。收入约束弱化,虽然为消费的增长提供了空间,但是收入增长并不会自动产生消费的增长,更不会导致消费的超出和消费的失控。由消费超出和消费失控形成的消费型贫困,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经验显示,城市消费主义的扩张是农村消费型贫困的诱导性因素,半熟人村庄社会分化的消费转型构成消费型贫困发生的社会土壤,婚姻市场化下农民家庭再生产的消费导向是其重要推动力。
1.城市消费主义的示范与扩张
农村消费型贫困的发生直接源于城市消费主义的扩张。消费型贫困意味着农民经历了“低消费”向“高消费”,“抑制消费”向“消费主导”的转变。S镇经验显示,农村消费的凸显,导火索在于城市的消费示范效应,其首先作用于打工先富的农民。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打工先富的部分农民率先在村庄中建起楼房。一位在 1998年建房的中年农民回忆:我 1990年到广东打工,工厂里干净整齐,回家了看到老房子就不顺眼,又脏又破。后来攒了2万块,就想盖楼房,让家里人住得好一点。打工经济不仅增加了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也改变了农民的消费观念。较早摆脱收入型贫困的农民便出现了消费需求升级,他们逐渐接受城市“卫生”、“舒适”的消费观念,并将务工收入转化为建房消费行为。以收入增长为基础,以需求升级为目标,以建房消费为内容,农民生活的消费面向增强,农村消费逐渐凸显。在初始阶段,农民建房不过是打工经济的自然结果,消费的增长与收入的增长保持同步,建房消费与否对于农民而言是可以选择的,村庄建房呈现自发秩序。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建房的中年农民是当地农村消费的开启者,那么,新时期农村消费的主体即新生代青年农民则主导了新一轮建房消费。正是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城市消费主义由“示范”变为“扩张”:城市消费主义经由年轻人更加普遍深入地进入村庄社会和农民生活。与早期外出务工农民不同,S镇年轻务工农民普遍欠缺务农经历和村庄生活经验,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更加城市化,城市消费标准对于他们而言是内化的。与早期外出务工农民相同的是,很多年轻务工农民无法在城市获得体面生活的就业和收入,因而他们仍然对村庄生活保持预期,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返回村庄生活。在城市消费主义与村庄生活预期的共同作用下,在农村修建一套不落后于城市生活标准的房子成为年轻人的刚性需求,因为后者构成年轻人生活尤其是婚姻生活的起点。对于年轻人而言,房子不仅要“卫生”、“舒适”,还要“有档次”、“有品味”,村庄建房标准也因此被不断推高。城市消费主义形塑了年轻人的高消费预期,并诱导了两个后果,一是“预期”代替“需求”成为建房的出发点,这就为消费的超出提供了动力;二是高标准建房需求经由年轻人引入村庄社会,并且不断扩张,为消费型贫困的发生找到了社会土壤。
2.半熟人村庄社会分化的消费转型
城市消费主义的扩张只是诱导性因素,村庄以消费为标准进行分化,吸纳并转化城市消费主义,是消费型贫困发生的社会土壤。
伴随着收入型贫困的减缓,乡村社会逐渐展开建房消费竞争。打工先富的农民在村庄中率先建房,成为了村民口中“有本事”、“有面子”的人。建房消费作为收入水平提升和消费能力增强的展示,引发村庄社会评价向其靠拢。因而,先富农民通过建房展示自己消费能力获得村庄较高的社会地位,没有建房的农民在村庄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卢晖临[15]指出,在平均主义心态作用下,富人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建房,而普通农民为了保住社会地位建房,由此开启了村庄社会地位竞争。王德福[16]认为,华北农民节衣缩食建房是为了在以建房为内容、以小亲族为范围的面子竞争中获胜。确实,在村庄社会中,农民普遍存在“平均”和“比较”心理,对自身所处社会地位比较敏感。“你建了我也要建”,“不能被你比下去”,这是农民卷入建房消费的社会心理基础。事实上,S镇90年代中后期的农民建房自发性较强,而超出收入水平建房和消费型贫困则集中发生于新一轮建房消费潮流之中。建房从一种自发的“展示”转型为一种虚假的“表演”,建房消费的“符号性”凸显。如果说 90年代中后期率先建房的农民展示了自己的消费能力,那么,建房在后来已经与农民的实际消费能力脱节。那么,这种并不能作为消费能力与收入水平表征的建房消费,如何与面子或者社会地位关联?
其一,“半熟人社会”[17]为表演性消费发育和表演性消费与村庄地位关联提供了可能性。在 90年代的农民建房中,建房消费作为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的标准是有效的。一方面,建房消费的表演性还没有凸显,因此保持了消费与收入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村庄在当时本质上仍然属于熟人社会,村民之间彼此熟悉,熟人社会中经济社会分化也自然是清晰的。而在新一轮建房潮流发生之时,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村庄社会呈现半熟人化状态,村民之间不再是知根知底,尤其是在收入层面呈现隐性化状态。简而言之,在半熟人社会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打肿脸充胖子”、与实际不符的认知偏差现象难以避免。半熟人社会中的面子竞争更加依托外显性消费来展示,外显性消费与实际收入的一致性判定失效,通过超出收入的外显性消费表演获得他人肯定性社会评价和自我地位的提升在半熟人社会中获得空间。所以,农民建房的楼层和规格不断攀高,这种超出自身收入水平和能力的外显性消费直接指向较高的村庄社会评价。
其二,外显性的住房消费成为一般性社会识别机制。房子在村庄社会中演变为一种符号,不再是“富裕”的象征,而是“一般性”要求。如果说先富农民建房提升了自己村庄社会地位,那么,普通农民卷入建房,则更多地是为了获得一般性社会地位,表现为“随大流”和拒绝边缘化。房子构成基本的社会识别机制,“建房的不一定有钱,但是没有建房的肯定没有本事”,没有建房的农民在村庄社会中被首先识别出来,他们“抬不起头”,产生强烈的边缘感。普通农民因为拒绝边缘化而卷入建房消费,实际是通过建房获得作为一般性村庄社会成员的资格。房子对农民而言成为一种社会价值的载体,并构成村庄社会地位的识别机制。
3.农村婚姻市场强化了建房消费导向
村庄以建房消费为内容进行分化和展开竞争,使得嵌入村庄社会的农民家庭陷入消费压力。同时由于农村婚姻市场的变化,农民的家庭再生产也越来越卷入建房消费的压力之中。调查表明:当地农民的基本人生任务是帮儿子娶媳妇,但近年来娶媳妇越来越与建房联系在一起,建房消费成为农民家庭再生产的启动成本。“娶媳妇”和“建房消费”之间并非直接关联,建房作为婚姻门槛的机制在于:
其一,年轻人在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高标准的消费预期,这种高消费预期构成年轻人婚姻生活的起点,并通过代际传导机制将消费压力扩散到整个家庭之中。S镇年轻人对住房有高标准需求,但是由于他们自身收入有限,其中老年父母自然被卷入中间,进而使整个家庭浸润在消费压力之中。与华北农民建房的代际剥削现象不同,在S镇,建房属于两代人共同完成的任务,因消费带来的贫困状态也是整个家庭所共同承受的。
其二,婚姻市场化打破了传统婚姻圈,形成了女性婚姻市场,以住房为主要内容的婚姻要价不断攀升。调查中发现,由于女性资源外流,当地中老年父母普遍担心儿子娶不到媳妇,S镇的一些偏远村庄例如白村甚至形成了光棍村。在S镇,女性因为在婚姻缔结中占据主动地位,高标准的住房条件越来越成为她们的要求:最好是进城买房,其次是集镇买房或建房,最低也要在村建房。由于一般村民难以承担进城买房的艰巨任务,在村建房成为普遍的婚姻消费项目。
其三,在流动背景下,婚姻市场信息不对称加剧,建房成为婚姻识别机制。正如上面所言,在村庄社会,有房子不一定富裕,但是没有房子肯定被认为是“落后”。没有建房的农民在村庄社会中被首先识别出来,不仅在村庄社会分层中处于边缘位置,更会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导致家庭再生产难以完成。当地农民普遍存在的“婚姻焦虑”,进一步强化了以建房消费为标准的村庄社会分化,农民为了让儿子娶上媳妇而加入到这场越演越烈的建房消费潮流。因而,在婚姻市场化作用下,农民的家庭再生产越来越为建房消费所主导,许多农民为了建房举家外出务工以顺利进行家庭再生产,并且甘愿忍受阶段性贫困状态。
综上可见,城市消费主义的扩张、村庄的消费分化以及农民家庭再生产的消费导向,成为消费型贫困的发生机理。而且三者交互作用、不断强化,使得消费本身很可能由价值实现载体转变为价值本身。在农民看来,建房消费是为了获得村庄社会地位和完成人生任务,后者分别与农民的社会性价值与本体性价值[18]挂钩,具有目标的合理性,而这种目标的合理性极容易掩盖实践的消极性。而一旦建房消费本身获得价值,高标准消费就会不断进入农民的生活,超出收入水平和能力的建房消费越来越变得难以调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消费型贫困在农民身上很可能表现为一种“积极的贫困”,这种贫困虽然会产生压力感知,却不会遭遇主动拒绝。因而,农民以建房消费为价值载体,是消费型贫困不可抗拒的深层机理。
四、消费型贫困的治理策略
农村贫困问题对于社会稳定影响广泛而又深入,贫困治理也一度成为政府重点工作。长期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贫困治理聚焦于收入型贫困,并着眼于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收入型贫困由于可以量化为政绩并且带来大量扶贫资源输入,一直是地方政府贫困治理的重点。Q县政府的贫困治理主要从80年代中期的发展集体经济(村办企业、集体果园)、“一村一品”(种植山药、土豆等经济作物),到 90年代中期推动药材产业,再到后税费时期培育新型农业主体和鼓励农民创业,主要围绕着改变传统农业、提升产业层次展开;与此同时,不断注入扶贫项目进行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Q县 30年贫困治理在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另外,打工经济释放了多余的农业劳动力,使劳动力资源得以更加优化地配置,家庭收入实现了最大化。在收入型贫困缓解的同时,以建房消费为内容的消费型贫困日益凸显。而与对收入型贫困治理的热情不同,政府对以建房消费为主的消费型贫困缺乏重视,没有意识到收入的增长并不能自动消除贫困以及消费型贫困治理的紧要性。新时期的贫困治理急需转型。地方政府必须认识到消费型贫困的社会后果,并且担当起治理消费型贫困的责任主体,因为消费型贫困具有较强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光靠农民自身不仅难以摆脱这种贫困,还可能导致消费型贫困越演越烈。基于消费型贫困的发生机理,贫困治理的战略方向应该是强化地方政府角色,遏制无序建房,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加强包括文化价值在内的新农村建设,从而有效防止消费型贫困的发生。
其一,遏制无序建房。地方政府需要抑制诱致消费型贫困的载体,净化社会风气。不同地区消费型贫困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S镇消费型贫困的表现形式是建房消费,长期以来,当地政府对农民建房放任自流,村庄缺乏规划,农民建房选址自由。地方性宅基地政策也形同虚设,在宅基地面积、高度上缺乏限制性规定,宅基地指标也不加以控制。而缺乏干预的农民建房被城市消费主义、村庄社会竞争以及农民婚姻压力所支配,最后产生了消费型贫困以及其他一系列社会后果。基于此,地方政府需要通过相关宅基地政策、政府管控和村庄规划遏制无序的建房消费竞争,节制过度消费。政府干预对于治理消费型贫困非常重要,有利于瓦解农民的超前消费,遏制无序的消费竞争。
其二,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在净化社会风气之外,价值重建需要展开,地方政府应当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消费型贫困的深层原因不被处理,价值问题不被涉及,就不能阻止消费型贫困以其他形式发生。当然,并非是要鼓励农民回到传统的“低消费”状态——适当增长的消费对于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而是要反对“消费的超出”和“消费的失控”,反对农民生活被消费所主导,引导农民建设合理的消费秩序。在这个方面,尤其需要警惕城市消费主义的扩张,避免刺激农民消费、鼓励农民进城的政策对于农民消费的强化和影响。
最后,加强包括文化价值在内的新农村建设。调研发现,新农村建设对于加强村庄建设、减缓消费型贫困具有积极意义。S镇由政府和村庄统一规划在吴村进行“幸福新村”建设,以解决高山移民安置和困难群体住房的问题,对减缓消费型贫困有启发作用。村内住房规格(大小、高度、布局、风格)一致,都是占地80㎡、单层或者双层的小屋小院,另外集中开辟空地给住户养鸡、种菜,还修建了一个文化广场供村民休闲娱乐。新村建设在在当地村民中获得很高的评价,一是造价低,一套房屋总成本只有十多万,二是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房子不大不小足够居住,房前屋后设计合理,还有公共活动场所。作为一项贫困治理实践,新村建设不仅节制了农民自发的建房消费竞争,避免了因建房消费带来的贫困,而且满足了农民实际的居住需求,提升了农民的村庄生活福利。
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消费型贫困的兴起,正在深刻影响村庄社会和农民生活。在现实中,消费型贫困容易被村庄的表面繁荣和农民的积极热情所掩盖,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正好迎合了“刺激消费”的政策倾向。而事实上,村庄社会和农民生活在消费的浸润下暗含了价值危机和社会危机,村庄乱象丛生,主体性缺失。鉴于中国农民仍将长期依托于村庄而生活,有必要节制无序的建房消费竞争,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加强包括文化价值在内的村庄建设,重塑村庄的“低消费、高福利”,以抵御日益显著的消费入侵,以及伴随而来的消费型贫困。在这个意义上,消费型贫困的治理,关系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以及中国农民生活的未来。
[1] Townsend P.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 and Living Standard[M]. London:Allen Lane and Penguin Books,1979:38-39.
[2]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5-38.
[3] 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J].社会学研究,2002(3):49-63.
[4] 沈红.边缘地带的小农——中国贫困的微观解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86.
[5] 关信平.社会政策与反贫困行动[C]]//李培林.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729.
[6] 朱玲.中国扶贫理论和政策研究评论[J].管理世界,1992(4):190-197.
[7] 何承金,赵学董.论我国的贫困状况与发展农业区域经济[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1):47-53.
[8] 屈锡华.扶贫经济开发与中国贫困地区人口发展的整体素质[J].中国人口科学,1994(2) :24-30.
[9] 穆光宗.论人口素质和脱贫致富的关系[J].农村经济与社会,1992(4):44-54.
[10] 王德文,蔡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消除贫困[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3):46-69.
[11] 安毅,张青.扩大农村消费的总体思路与政策建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8):53-57.
[12] 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组.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EB-OL].新华网:http://www. farmer.com.cn/ywzt/ wyhwj/yl/201502/t20150205_1011781_3.htm.
[13] 唐平.中国农村贫困标准和贫困状况的初步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1994(6).
[14] 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50-56.
[15] 卢晖临.集体化与农民平均主义心态的形成——关于房屋的故事[J].社会学研究,2006(6):147-245.
[16] 王德福.做人之道——熟人社会里的自我实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7]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9.
[18] 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J].开放时代,2008(3):51-58.
责任编辑:曾凡盛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consumption-poverty and its governance countermeasures: Set the building boom of S town in east Hubei as an example
ZHENG Xiaoyuan
(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China Governanc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Peasants’ building boom in S town of east Hubei reveals that the nature and type of rural poverty is greatly changing,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income-poverty has been slowed while consumption-poverty springs up. The expansion of urban consumerism, the differentiation on consumption in village society, the consumption orientation of peasants’ family reproduc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 constitute the mechanism of consumption-poverty. As consumption-poverty has strong social structural factors, the peasants cannot break away from poverty by themselves. It is the local government that should reign the poverty governance,control the disorder of consumption competition, guide a correct view of consumption and village construction including value reconstruction.
countryside; consumption-poverty; formation mechanism; governance countermeasures
C912.82
A
1009-2013(2016)04-0042-07
10.13331/j.cnki.jhau(ss).2016.04.007
2016-06-10
华中科技大学资助项目(0118404053)
郑晓园(1989—),女,湖北随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