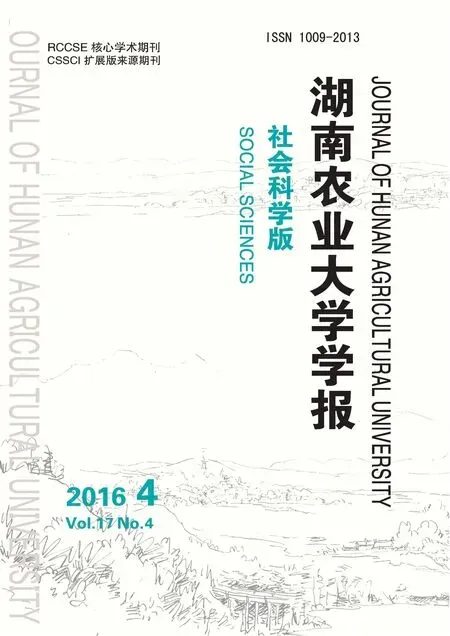乡村社会日常人际传播及其社会功能
费爱华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8)
乡村社会日常人际传播及其社会功能
费爱华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8)
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传播主要有“招呼”、“聊天”、“闲话”和“骂街”四种类型。日常人际传播是乡村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形成和运行的纽带,是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方式,也是村民形成社区心理认同的基础,具有一定的社会关联功能。日常人际传播明确了传播者在村庄里的地位和角色,有助于乡村社会规范的形成和乡村社区秩序的维护,发挥了一定的舆论监督作用,具有一定的秩序建构功能。另外,面对“拥挤”的乡村社会,日常传播也有利于妒忌和怨恨等不良情绪排泄,化解乡村纠纷,发挥安全阀功能。
乡村社会;人际传播;社会功能
转型期中国乡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中青年外出打工人数增多,乡村社会老龄化和空心化,而大众传媒的普及导致外来文化渗透、宗族观念弱化、乡土人情逐渐淡薄等等。尽管如此,因稳定地缘关系的存在,中国乡村社会仍是一个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相互间仍旧保持着较强的依赖性和互动性,人际交往频繁。与城市社区具有发达的大众传播相比,乡村社会沟通交流主要是通过人际传播进行。因此,对乡村人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乡土社会的理解,丰富人际传播学的理论研究。
在乡村社会中,人际传播主要有“招呼”、“聊天”、“闲话”和“骂街”等四种类型。“招呼”是相互认识的人之间为表达礼貌而进行的一种简短的人际传播形式。在乡村,打招呼是约定俗成的礼貌行为,“同一个街坊的男女在街上或田里碰到时应该打招呼”[1],其主要内容是问候,即通常所谓的“寒暄”,是人们在社交时出于礼貌的需要,以客套的方式表达意义、联络情感的语言形式。“聊天”是在关系相对较为密切的人之间进行的内容更为广泛、时间更长的人际传播。相互关系较为熟悉的人,“招呼”可能是一场马拉松“聊天”的开始。聊天“是一次游戏,好比打网球一样,球越久不落地才越好。”[2]“闲话”则是关系很近的人之间表达对村里或周遭熟悉的亲戚、朋友、邻居、干部等的不满,并对其进行负面评价的一种人际传播。“闲话”与“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聊天”主要涉及村庄“外面”的一些事,即使谈到村庄内部事务也通常是对事不对人,与个体村民关系不大,不涉及对个人的评价,不会引起纠纷,所以是“无关痛痒”的;而“闲话”所涉及的则是村庄内部、传播者身边的人与事,往往涉及个人隐私,特别是对与谈话双方都相互熟悉、关系较为密切的个人的负面评价上。“骂街”则是通过咒骂别人表达愤怒的一种特殊的人际传播。在整个过程中,骂者就像舞台表演一样,站在村庄的公共区域,或像讨伐者一样站在冒犯者(很多情况下是怀疑对象)的家门口,诉说自己如何吃亏、如何被冒犯,并用各种各样的脏话去咒骂冒犯自己的人。
学者有关乡村人际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乡村社会人际传播的总体性研究,如传播主体、传播信息、传播机制等[3]、人际传播中信息交换[4]、人际传播的变迁[5]等;其二是乡村政治活动中的人际传播,比如选举中的候选人面向选民的人际传播[6]、村民政治参与中的人际传播[7]、上访中的人际传播[8]、乡村治理活动中的人际传播[9]等;其三是有关“闲话”的研究,如闲话的意义和权力[10]、闲话的属性[11],闲话的变迁及功能异化[12]等等。上述研究对乡村人际传播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缺少对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人际传播整体性、系统性的分析,而仅仅局限于“闲话”一种形式,对日常人际传播的功能还缺少更深入的研究。笔者拟透过社会学视角对乡村社会中主要人际传播的社会功能进行探讨。
一、关系发展与社区认同的社会关联功能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村民累世聚居、互动频繁,形成了村落的共同文化,构成了村民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而随着工业化发展导致农民大规模流动,当代村庄社区相对传统村庄而言正逐步走向“陌生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逐渐疏离,村庄向心力弱化,乡村社会似乎真正进入到一堆互不相干的“马铃薯”状态。“疏离”的乡村社会不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不利于村庄公共事务的开展,更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推动。因此,推动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促进村民对社区的认同、提升乡村社区的“社会关联”[13]是十分必要的。
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传播有助于提升乡村社区的“社会关联”。一方面,人际传播有助于增进村民之间的关联,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人际传播有助于增进村民与乡村社区的关联,提升其对社区的认同。就人际传播增进村民之间的关系发展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人际传播是建立和维系人际关系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是通过传播得以形成、维持和改变的。关系的基本单位不是某个人,也不是某两个人,而是相互间的互动[14]。招呼和聊天是与别人建立关系的第一步。招呼是友好的表示,其问候语不具有针对性,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从情感表现上看通常是不经意的,其功能主要与点头、握手或拱手之类的身体语言接近[15]。相互之间打招呼说明两者的关系是友好的,至少不是矛盾和冲突的。大量空闲时间是聊天的基础条件。在中国乡村,生产力不发达,生活节奏不快,每年乡村有大量“农闲”时间,所以对生活其中的人们来说,长时间的聊天是一种本能。正如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所说,“与盎格鲁撒克逊经常表现出的阴郁独处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人最主要的享乐就是同别人聊天,无论老朋友或者陌生人都差不多。”[16]聊天可以提供一个揭开话题的过程,并可以逐步深入,为将来的关系发展做好铺垫,也可以增加现有关系的范围。
(2)人际传播是促进人际关系的手段。“熟悉是从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17]建立和维持感情的办法之一,就是经常打招呼和聊天。招呼、聊天是人们相互熟悉和深入了解的重要途径,招呼中对非亲属关系使用拟亲属称谓,往往更能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18]。凡是能够主动热情与别人打招呼,或者积极回应的村民,往往都能获得村民们正面的评价。这样的人往往性格开朗,能和他人友好相处,因而广受欢迎,他们在村中也格外有人缘。与之相反,不喜欢用拟亲称呼叫人、不积极打招呼、不擅长聊天的村民,往往性格孤僻呆板,和其他村民的关系自然就较为疏远,也较难与别人结为亲密关系。在闲聊过程中,双方既不必劳神费心,又不会因观点不合而陡起纠纷,正是“融洽关系的好玩意,几乎可以说是人人爱讲,个个爱听的”[19]。参与“闲话”的双方或多方往往彼此关系密切、信任度较高。陌生人、关系一般的人之间很难产生“闲话”,只有面对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人们才可能讲出对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他人进行道德评价的闲话,因为闲话一旦传播出去,会产生一定的人际关系风险。
(3)人际传播还可以缓和、修复双方曾经的矛盾关系。两个村民一旦发生矛盾,时过境迁以后,其中一人可以通过试探性主动打招呼、聊天来改善双方关系。哪怕对方不理,只要坚持留下这个沟通的管道,就会重新维系两人的关系。尤其是打招呼通过拟亲缘的称呼拉近双方的距离,即使双方有些小矛盾或者未公开的龃龉、甚至内心的妒忌和怨恨,也可以维持表面上的和谐。
另外,人际传播是获得外部信息、了解外部世界的基本形式,是人们相互交流的原始方式。乡村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传播为村民之间互相交流信息、促进村民和乡村社区的情感联系提供了机会,有助于提升村民对农村社区的认同。
(1)满足了人们对信息获取的需求。著名作家叶圣陶介绍民国时期的聊天时曾说,“有的讲昨天的赌局,……有的讲自己的食谱,……有的讲本镇新闻,……有的讲些异闻奇事”[20]。虽然时过境迁,但现在村民们一起聊天的内容大同小异,小到工作家庭生活琐事、花边消息,中到村庄事务、地方新闻,大到国家政策、各级政治人物、公众人物、国际新闻等等。为了满足归属的需求,人们通过招呼、聊天和闲话等日常传播活动增进彼此的了解、分享了各自独特信息、促进谈话双方的关系,不断确立、维护自己与村庄的联系。“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21]人际传播可以满足村民的信息需求,增加村民对乡村社区的心理归属感。
(2)人际传播可以促进村民和社区之间的情感联系。聊天和闲话可以给村庄和个人带来轻松娱乐的情感享受[22],使分享者体验到愉悦情绪、感受并增强彼此的亲密关系[23]。辛勤劳动之后,放松肌肉和神经的紧张是一种生理需要。因为受文化水平影响,大多数村民没有听收音机、看电视、读报纸的习惯,聊天就成为大家消磨时光、交流信息、娱乐享受的主要手段。特别是一些娱乐性闲话能带给村民情感上的愉悦和放松,从他们的开怀大笑中,可以感受到村庄中户外聚谈的吸引力。“工做完了,男子们也不常留在家里……。茶馆、烟铺、甚至街头巷口,是男子们找感情上安慰的消遣场所。在那些地方,大家有说有笑,热热闹闹的。”[20]人际传播中的骂街对事件的双方当事人来说是一件不快的事,但对其他村民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娱乐活动。“骂街”有两种类型,一是“独骂”,“骂街”过程只有骂者一人唱独角戏,没有明确的被骂对象,通常是因自己财产受损、被盗,却没有明确的证据指认嫌疑人,骂者只好通过“骂街”来泄愤并对对方给予警告。二是“对骂”,即有两个对立方参与的骂街,通常起因于双方(如邻里、兄弟等)之间的利益情感纠纷积累的宿怨,以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为导火索,从小小的争执、说理开始,最终演变成情绪性的相互谩骂。“那万籁俱寂的乡村,女人的骂街声也就成为死寂的乡土社会里的狂欢乐曲,没有她们的声音,生活就像是死水一潭。”[24]在百无聊赖之际,村民们以事不关己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来欣赏骂街舞台剧,骂街过程中“观众”会被一些话语逗笑,事后骂街中的趣事、隐私也将成为人们长期津津乐道的聊天素材。
(3)人际传播为乡村公共空间的形成和村民的公共参与打下基础,促进了村民的社区认同。乡村公共空间是指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在其中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场所,以及在这些场所中产生的一些制度化的组织和活动形式[25]。人们在巷头巷尾、店旁树下自由地聚集招呼、聊天甚至闲话,交流彼此的感受,传播各种消息,发表各自看法,增进了彼此的理解和信任,也逐渐培育了意见领袖,形成了乡村公共空间的原始形式。人际传播也为村民对社区公共事件的参与创造了条件,在聊天和闲话中初步拟定公共议题的方向,讨论乡村公共活动和公共仪式举办的初步方案,就某些公共问题坦率发表各自意见等等。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村民们可以组织正式集会,就重要的公共议题进行公开讨论,最终形成对人们行为具有一定约束力的社会意见。“地域共同体形成的动力机制是居民自主参与住区公共议题的决策过程,并通过参与过程产生对地域空间的认同”[26]。村民通过人际传播有意无意地参与了村庄事务,在参与中加深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从而增进与乡村的社会关联。
二、规范生成与舆论监督的秩序建构功能
在中国,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国家治理的难点,传统中国“皇权不下乡”,“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27]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通过行政体系将权力渗透到乡村,但成本巨大且容易导致乡村社会主体性的丧失,社会整体利益严重受损。改革开放后,国家正式权力逐步撤出乡村,乡村治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正朝着村庄自治、多元治理、间接治理和依据法律的契约治理方向发展[28]。尽管已经朝着根据法律的契约治理方向发展,但依靠共识规范达成的乡村社会内生秩序依然具有补充的作用,在乡村治理中有迫切的需求,是多元治理的一部分[29]。秩序建构主要依靠社会性共识规范的达成和规范生成后的执行来完成。规范是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形成的行为和准则,是社区共同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规范形成后则通过村民的心理内化和外部舆论的社会压力对村民行为形成约束,从而减少社会摩擦,维护社会秩序,实现乡村“善治”。
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传播具有一定的秩序建构功能。首先,人际传播可以明确各自在村庄里的地位和角色,建构有层次、有秩序的乡村社会网络。打招呼是“以语言去建立社会地位而让对方明白的一种过程”[30],体现了一定的权力关系。主动积极打招呼的人往往地位相对较低,他们通过主动、热情的方式来表达对对方的尊敬。“每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出则悌’,逢着年长的人都得恭敬,顺服于这种权力。”[12]偶尔一个地位较高的人也会主动打招呼,这时地位较低的对方就会觉得被“给面子”而受宠若惊,并以双倍的热情给予回报。另外“拟亲属称谓”承袭了其所带有的尊卑长幼之别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社会分层功能[31]。
聊天同样具有一定的社会分层、固化秩序的功能。“男人从不参加女人的聚会,女人也不允许参加男人的聚会。”[1]聊天通常发生在角色或地位相差无几的人之间,性别、年龄、角色特征、社会地位差距较大的人很难坐下来进行长时间的聊天。因为聊天是一次双向交流的信息沟通,在交流中信息被去隐私化和公开化,这种交流要求双方消除社会距离,保持平等地位。聊天常常形成若干个圈子,圈子内的人具有一定的平等和互利性,依靠一种长期自然形成的信用关系加以维系[32]。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层次的聊天圈子,圈子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乡村精英聊天的圈子普通村民进入是不受欢迎的,普通村民聊天的圈子乡村精英也不屑加入。
闲话则有利于参与者维持自己在群体网络中的地位[33]。闲话是人们为寻求摆脱孤立状态、试图加入到某一社会关系网络或强化其网络地位而出现的一种人际传播。如果个人希望发掘、创造或维持他在某个群体之中的地位和角色,那么,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之中的其他人的原始信息(如家庭背景、婚姻状态、嗜好品性、年龄体质等)、这些人之间现存的或潜在的关系(亲近还是疏远、友好还是敌对),以及这个网络内在的权力结构(谁是领袖、谁是仆从、谁是局内人、谁是局外人)及其发挥作用的各种非正式“游戏规则”的信息等等,都变得至关重要[34]。这些信息正是以闲话的形式在村民们之间进行传播,村民们通过闲话不断制造和传递与自己相互联系的、有关人和事的各类信息,以确认、改善自身在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中的存在和地位。
其次,人际传播可以传输村庄一致遵从的价值观,维持村庄秩序。招呼和聊天是建立乡村共同体的基本纽带。打招呼在乡村社会是普遍现象和日常行为举动,内含村庄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也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系。招呼中的称谓(“叫人”)是一种秩序建立的仪式,它强调在乡村社会应该尊敬长辈。招呼、聊天的信息看似平淡无奇,但这些信息经过日积月累,在每个村民中不断充实的人际传播中形成村庄共有的信息知识库,每个村民既积累他人的经历记录,也在他人的头脑中被积累记载,最终形成村庄地方性知识。闲话则通过一再重申价值和支撑该价值的道德原则来维持一个村庄的秩序。很多娱乐性闲话也能发挥寓教于乐的功能,对一些不符合村庄秩序的人和事通过一些调侃的闲话,可以为其他村民提供反面教材。在闲话的分享过程中,对照自己和他人面对同样事情的反应,可以比较彼此在重要的信念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使分享者体验到愉悦情绪,感受并增强彼此的亲密关系,帮助确立群体规范,使群体对其成员的控制力增强。
其三,人际传播特别是闲话与骂街还发挥着舆论压力作用。闲话发挥了村庄“舆论”功能,确保对村里那些不遵从村庄价值观、交往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个人形成“非正式的惩罚”[35]。如果村庄中个别村民行为违背了社会伦常、当地习俗、村规民约等,或者对其他个人、集体的利益造成损害,大家就会背后议论他,这时闲话实际上形成了舆论压力,因为村庄有脸面的人通常都“怕别人说闲话”,这就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一些精英村民的不合情、不合理行为。闲话之所以具有社会效力,形成集体压力,就在于其背后所隐藏的村庄公共性。如果谁做事方式触犯了村庄规范,并让村庄丢脸,大家就可以唾弃他,并用闲话议论。闲话的实质就在于其所具备的评判性,而其效力与合法性都来源于村庄的公共性[33]。
骂街则是比闲话更公开、更严厉的、面向村庄强势人物的一种舆论监督方式。一些村民如果觉得乡村精英的一些做法伤害了他们个人或公共利益,面对面地交涉和论理无法奏效,而闲话的舆论监督由于过于温和难以产生效果时,他们就会采取骂街的形式给予对方以公开的压力,同时也唤起其他人的注意,“煽起全村性制裁的一种行动”,形成群体压力。作为一种有效的“弱者的武器”,骂街既可以“以恶抗恶”的方式来出出闷气,也可以此唤起公众的关注和支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村强权人物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侵占”,是一种对付强权和暴力的一种扭曲的、变形的舆论压力。
三、心理调适与纠纷消解的安全阀功能
日本学者寺田浩明曾指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犹如“载满客的电车”。“满客电车模型”这一理论在现实仍有一定的解释力[36]。“电车”意味着有限资源被限制在某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而“满客”则说明希图占据资源的人数众多,所以平均下来每个个体所能获得的资源则相对紧张。一个人占据的资源过多,其他人能获取的资源必然减少。因此,身处村庄的村民犹如电车的乘客,特别关注细节和其他个人的一举一动,对他人所占据的资源都会十分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会被村民们放大、扭曲,从而为乡村社会的各类纠纷、冲突埋下了伏笔。
纠纷产生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人的“气”或“气性”。“气也许正是理解传统中国人求取安宁与直面冲突的一个重要枢纽。”[37]“气”是人们在村庄生活中,未能达到期待的“常识性正义平衡感觉”时,针对相关人和事所生发的一种激烈情感[38]。无论是传统乡村社会还是现代乡村社会,“气”都在中国人生活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在拥挤的乡村社会,“气”主要体现为妒忌和怨恨两种情绪。妒忌是一种对地位相近的别人与本人获取资源对比形成落差的心理失调行为,怨恨则是认为受到直接的伤害和挫折而滋生的一种情绪,妒忌、怨恨情绪累积可能会因为某个导火索的出现而爆发严重的冲突。乡村社会的人际传播特别是闲话和骂街有利于妒忌和怨恨等“气”的排泄,在“拥挤”乡村社会发挥着积极的安全阀功能。
科塞的安全阀理论指出,任何一个社会的运行都会在社会主体间产生不满情绪,这些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时,需要安全阀“充当发泄敌对情绪的出口”,从而使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免于受到毁灭性的影响[39]。如果没有安全阀,累积的不满情绪有可能超过社会系统的耐压能力,会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的崩溃和瓦解。穷人中流行的某些政治笑话是为了嘲讽富人,被统治阶层中流行的某些政治戏剧是为了嘲讽统治者,政治笑话与讽刺就是一种安全阀,排泄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不满情绪。通过释放被封闭的敌对情绪,安全阀可以发挥维护系统稳定的作用。一个社会系统越僵化,越不允许人们公开、直接地表达不满情绪,就越需要“安全阀”制度[40]。相对于城市社区而言,乡村是一个沉闷僵化的社区,尤其需要积极发挥安全阀的功能。
村民们的日常闲话具有释放怨气的功能。由于村民们在平时互动中比较注重“人情”与“面子”等问题,一些对别人内心的不满和妒忌乃至怨恨当面难以表达,往往只有通过背后的闲话渠道发泄出来。通过在信得过的人面前说别人的闲话,贬低被说者的人格和地位,平衡内心的“紧张感”和挫折感,也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从而使得妒忌情绪和怨恨情绪得到安全纾解。“散布流言可以使传播者觉得自己在群体中变得更加强大,更有影响力,也更受欢迎,从而获得归属于群体中心的优越感,”[34]使自己在一个群体内的社会地位、权力和威望得到提升,从而改变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
骂街则更多地排泄了怨恨情绪,有利于冲突的消解。骂街可以及时泄愤,防止矛盾累积。一个村民在和另一个村民交往过程中屡屡吃亏,由于脸面的问题一直忍耐,这时的一场骂街可以让吃亏方冲破脸面的束缚,主动将双方的矛盾公之于众,在村民们面前讨个说法,接受舆论的评议,获取舆论的支持。“骂街”的台词通常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简短的事实。骂街者首先会气愤地诉说自己受到委屈的经过和事实,指责对方的不是之处,解释骂街的缘由和来龙去脉,以取得周围村民们的同情和理解。二是骂词,包括贬损类、诅咒类骂词。贬损类的骂词是将对方贬为“猪”“狗”、“蛇蝎”类的低等动物,或将平常视为隐私和禁忌的东西如人的生殖器官、排泄物、性生活等等公开化。诅咒类詈语则是诅咒对方丧失生命,如“不得好死”、“断子绝孙”等等。三就是威胁语言。骂街人通过威胁语言显示力量,用暴力语言显示说话人具有实施暴力的能力,谋求自己在身份、力量、地位上的平衡[41]。威胁语的功能类似于鲁迅笔下的“精神胜利法”,可称为“语言胜利法”。虽然骂街表面上激化了矛盾,但实际上也是解决矛盾的开端,使矛盾的解决具有积极的趋势。正因为将矛盾公开化,利益受损方在情理上获得舆论支持,在心理上取得一定的平衡,同时借助大家的舆论压力,限制了强势者对自己利益的进一步剥夺,避免了矛盾进一步升级。另外,骂街也是张扬个性、调节心理的一种另类途径。不平则鸣,一个人生活幸福,心境就会平静,泼妇骂街大抵也只是因为生活的不如意。骂街时是什么话难听骂什么,什么话最能伤人骂什么,什么话骂出来最能出恶气骂什么。通过大骂一场“糊涂”街,把心中积郁的气放出来,不仅心里舒畅和轻松多了,也多少找回一点面子,让人知道我也不是随便让人欺负的,从而找回一种心理平衡[42]。
闲话尤其是骂街尽管属于一种“失范”行为,但它们像“安全阀”一样可以使村民们相互之间积累的不满情绪不断排泄出去,短期来看可能影响了双方的关系,但长久来看则有利于社区的稳定。闲话过程中,说闲话的和被说闲话的两人关系是扭曲的,骂街的时候,骂街双方的亲属、邻里关系更是被打破。不过,闲话和骂街过程中这种正常关系的扭曲和颠覆不具有长期性和永久性,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地缘或亲缘关系把双方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被临时打破的关系在后来的往来过程中会逐步得到修复。可见,闲话和骂街这类日常生活中的失范和冲突具有自我排解和修复的能力,保证了乡土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事实上,乡村社会对闲话和骂街都持一种肯定和宽容的态度,这是自治社会的一种本能,因为它们一方面可以制约着强权者,另一方面为弱势群体提供一个纾解怨气的通道。
乡村社会日常传播既有社会关联、秩序规范和安全阀的正面功能,同样也有一定的负面功能,尤其是闲话与骂街,可能会导致当事人关系紧张、退化乃至恶化甚至会出现人身伤害事件。乡村产生冲突的第一个重要原因主要是邻里间的沟通问题[43],在很多乡村纠纷中,由于这种信息获得方式可以使得纠纷当事人在事件间建立起更多、更复杂的关联,所以闲话传播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在有些纠纷中决定了整个纠纷的展走向[36]。由闲话、骂街导致的恶性的暴力事件会留下冷漠、仇恨,被说闲话的人如果承受能力较弱会因“人言可畏”而“以死明志”,同样,骂街失败的一方觉得丢面子气不过“自杀”等等。这些都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1]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28.
[2] 特里·K·甘布尔,迈尔克·甘布尔.有效传播[M].熊婷婷,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83-184.
[3] 李红艳,谢咏才,谭英.构建中国乡村传播学的基本思路——传播学本土化的一种探索[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86-89.
[4] 周云,彭光芒.人际传播中的信息交换与利益实现[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8-20.
[5] 李红艳,左停.乡村传播意义下的农村发展[J].新闻界,2007(6):38-40.
[6] 骆正林.候选人在村民选举中的信息传播[J].新疆社会科学,2009(1):96-100.
[7] 杨善华,柳莉.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J].中国社会科学,2005(3):117-125.
[8] 郑欣.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9] 吴毅.小镇喧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0] 薛亚利.村庄里的闲话:意义、功能和权力[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11] 冯广圣.一种特殊的人际传播:闲话传播[J].国际新闻界,2012(4):30-33.
[12] 王会.闲话的变迁及其功能异化:一个理解村庄社会性质的维度[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2011(1):36-41.
[13] 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
[14] 斯蒂芬·李特约翰、凯伦·福斯.人类传播理论[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226.
[15] 郭攀.问候语说略[J].语言文字应用,2003(1):110-115.
[16] 亚瑟·史密斯.中国人气质[M].张梦阳,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122.
[17]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9.
[18] 满蕾.从电视剧《乡村爱情》看东北方言的称谓语特点[J].现代语文,2009(3):113-114.
[19] 易中天.闲话中国人[M].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364.
[20] 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262.
[21] 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3.
[22] 薛亚利.村庄里的闲话:意义、功能和权力[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165.
[23] Stirling R B.Som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perative in gossip[J].Social Forces,1956(34):262-267.
[24] 吴治平.变态人格下的“乡骂”[J].农家女,2009(5):36-37.
[25] 费爱华.乡村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探析[J].学海,2011(5):97-102.
[26] 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J].社会学研究,2007(4):138-164.
[27]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110.
[28] 吴理财.乡镇改革与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构建[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1):30-34.
[29] 王义宝,李宁.社会资本视角下新型农村社会治理秩序困境和能力创新[J].思想战线,2016(1):141-146.
[30]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8.
[31] 黄涛.村落拟亲属称谓制的社会功能[J].社会科学研究,2003(6):107-110.
[32] 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19-200.
[33] 桂华.论村庄社会交往的变化:从闲话谈起[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5):44-48.
[34] 李智.谣言、流言和传说[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2):115-119.
[35] 朱晓阳.罪过与惩罚[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99.
[36] 李显波.讲的什么理:乡民纠纷行为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06:127.
[37] 应星.“气”与抗争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6.
[38] 陈柏峰,郭俊霞.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206.
[39] 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6.
[40] 毕天云.社会冲突的双重功能[J].思想战线,2001(2):110-113.
[41] 陈开举.英汉骂语的文化心理分析[J].江汉论坛,2008(7):126-129.
[42] 吴治平.变态人格下的“乡骂”[J].农家女,2009(5):36-37.
[43] 赵树凯.乡村关系:在控制中脱节——10省(区)20乡镇调查[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2-9.
责任编辑:曾凡盛
Study on the dail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rural society and its social function
FEI Aihua
(Nan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210018, China)
The dail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rural society, which includes "greeting", "chat", "gossip" and "street-cursing", has social relevance, regulatory and safety valve function. The dail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the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and the psychological identity of the villagers. It helps to clarify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he villagers, to construct the rural social network, to establish the rural community order, and to carry out the supervision of public opinion. In addition, it is conducive to the excretion of envy, hate and other negative emotions, and the resolution of rural disputes in the "crowded" rural society.
rural societ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ocial function
C912.82;G206
A
1009-2013(2016)04-0035-07
10.13331/j.cnki.jhau(ss).2016.04.006
2016-06-05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09YJC860016)
费爱华(1966—),男,江苏泰州人,社会学博士,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南京大学融合传播实验室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