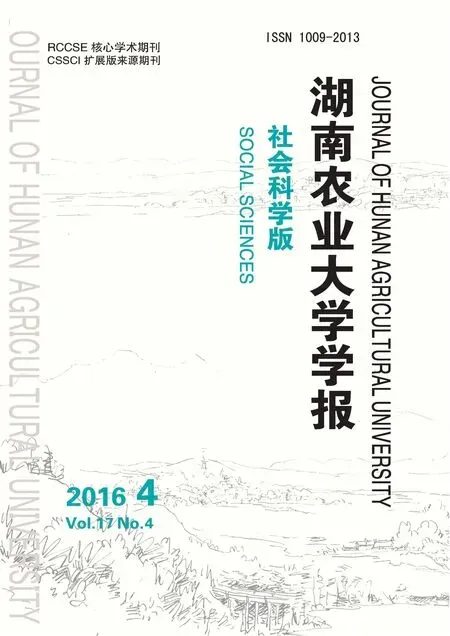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杨昌彪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重庆 401120)
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杨昌彪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重庆 401120)
中国现行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一直围绕强化政府义务来建构,存在着公众参与主体范围模糊不清、参与权利内容缺失及参与主体法律责任缺位的问题,致使公众参与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政府公信力不断下降。立法应摒弃以单纯强调政府义务的立法理念,明确界定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权利主体、具体内涵和法律责任,实现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有序化和有效化的制度价值。
环境群体性事件;公法权利;公众参与;缺陷;环境行政决策
一、问题的提出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就开始出现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由于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和地方政府环境公共决策的形式化、简单化、粗暴化等因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数量日增,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数量每年递增25%[1]。近年,茂名水污染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常州毒地事更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些事件既暴露了地方政府处理环境纠纷及其群体性事件的简单和粗暴,也反应了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形式化和群体性事件扩大化的特征①。法学界就公众走上街头与政府抗争的根源和解决冲突的对策展开了探讨。王锡锌主张放弃传统的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专家理性决策模式而建立协商式的公众参与模式,开启了国内公众参与协商回应式理论研究的先河,也成为目前学界的通说。他主张通过公众参与协商治理模式的建立,增强政府行政过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2]。朱谦则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归因于社会公众个体利益表达的非理性,而主张建立组织化的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机制,即代表制[3]。栗燕杰将公众参与的功能定位为行政决策澄清事实、预防化解纠纷,是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必要辅助条件。[4]杜健勋将协商式参与模式进一步深化,提出效仿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构建“参与回应”式治理模式。他认为在当今风险社会下,之所以大规模爆发环境群体性事件是由于政府解决环境问题的动力和压力不足所以,必须进行法权配置,强化政府义务,通过官员问责,实现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消减和社会的有序安定[5]。目前,学界普遍认同在强化政府义务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积极回应来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并且将其落实到整个环境行政决策过程中。事实上,自 2003年《环境影响评价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一直贯彻这一立法理念,但通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政府,目的是为了政府的有效治理和风险防控,既公众参与程序的不断完善是为了增强政府行政和决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降低公众对政府决策的抵触心理[2]。杜健勋提出的参与回应型治理模式也是为了规避群体性事件而引发的政府治理危机。朱谦直接以个体非理性为由,反对个体参与行政决策的过程。综上,可以较为明显地解释为何公众参与制度实施了这么久,而公众却在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求助无门而不得不通过暴力围堵政府大门、集体散步等非体制内方式寻求救济。可以认为中国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中过度强化政府义务而尚未完全确立公众参与权致使因环境纠纷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中国对司法权利保障和公法权力规制研究较多,但对行政公法权利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对于公法权利的著述凤毛麟角。环境法学视野下的公众参与权作为公法权利在中国立法上没有完全建立,学界研究较少。由于缺乏基础理论研究,同时因为中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使得公众的参与权在受到侵害时,既得不到法律的救济,也得不到理论的声援。在 2014年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十多家环保组织作出《中国江河的“最后”报告》中提到:自《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公众参与条例》实施以来,水电开发依照法律和条例应该召开专家咨询会、公共听证会等,但听证会不仅召开次数非常有限,而且公众参与的渠道和机会总是形式大于内容。这使得希望通过公众参与来强化政府决策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愿望落空,而且政府的公信力不断降低。而受环境行政决策影响的公众,可能未被邀请参与行政决策,丧失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他们不得不通过“将事情闹大”引起社会关注,给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妥协,而通常政府迫于社会压力最终做出让步。这就是目前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突发和解决的最普遍模式。将权力关进笼子,必须先将权利放出笼子[6]。笔者认为,在构建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时,应以环境行政参与权的理论构造为核心,兼顾政府义务和公众权利两个维度,对现有制度进行解构并予以重塑。
二、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理据
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从法理上论首先必须回应三个问题:第一、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权的属性问题,即其在权利体系中该权利属于何种性质的权利;第二、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权的功能问题,即讨论该权利创设的必要性;第三、具体的权利类型构造问题,即在回应前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探究具体的权利内容。下文围绕上述三个问题展开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现行制度的检讨,并提出完善的路径和方案。
1.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权的属性界定
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权是公众参与权在环境行政领域的具体表现,其本质属于公法权利,从其所属的法律部门看,主要涉及公法部门法,譬如宪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从权利诉求看,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权主要是公众通过行政参与能够影响政府行政决策,理应属于公法权利。宪法及行政法学界对公众参与的研究由来已久,可以从公众参与权以及公法权利的产生及发展探究该权利的法律属性。在国外法学界影响较广的是雪莉·阿恩斯坦的公众参与梯度模式理论,她认为公众参与应该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型是假参与,包括操纵、训导;第二种类型是表面层次的参与,包括告知、咨询;第三种类型是高层次表面参与,主要是展示;第四种类型是深度参与,包括合作、授权、公众控制,而这一梯度的排列标准是公众参与的权利大小。公众控制是公众在参与行政决策时获得管理的权利,是公众参与权利中最高形式[7]。公众参与八种梯度理论实质上是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权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尤其是第四种类型:合作、授权及公众控制模式,实质上是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权扩大与政府行政权缩小的过程。中国现行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类型还不够明确,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经常在四种类型中徘徊。
但是雪莉没有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公法权利,更没有阐释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权。现代意义上的公法权利概念的建立,普遍认为始于卡尔·弗里德希·冯格贝尔,后经比勒尔的系统阐释而最终确立。所谓公法权利是指私人个体根据公法规范所享有的、针对国家公权力机关的权利,公法权利主要是参政权②。耶里内克曾根据公民在国家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对公法权利的类型进行了划分,正式提出了公法权利中的公众参与权。耶里内克认为公民在与国家关系中具有四种法律地位,一是被动地位,二是消极地位,三是积极地位,四是参与地位。与雪莉提出的公众参与四种类型具有相似性。在这四种法律地位中,被动地位导致个体对国家的服从义务,不能够支持个体的公法权利,另外三种法律地位则支持公民的公法权利,其中消极地位支持公民的自由权,积极地位支持公民的受益权,参与地位则支持公民的参与权[7]23。作为一种基础性公法权利,参与权所代表的是个体作为国家的一个成员参与国家意志形成的地位。耶里内克采纳了卢梭的公意理论来对参与地位进行阐述。国家的意志作为一种公意,其本质是个体意志的整合,因此国家需赋予公民参与国家意志形成的能力,具体而言,国家法律应当规定,哪些人在何种具体的条件下能参与国家意志的形成。日本现代著名宪法学家芦部信喜继承耶里内克关于公法权利三种法律地位的理论,将公法权利划分为自由权、受益权和参政权[7]61-62。参与地位的确立前提是立法确认完善的公众参与权。在不同的公法领域,参与权的具体形式是不同的。如在宪法领域,典型的参与权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环境行政领域中,公众的环境行政决策参与权是公法权利的具体化。
2. 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权的功能
公法理论从法学理论上界定了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权的公法权利属性,但是具体的权利内容需要以功能主义为目标,即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权的内容要在公法权利的框架下进行立法确认,同时又要以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的功能为目标。公法权利具备行政主体塑造功能,使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的地位逐渐走向平衡。同时公法权利具有价值秩序建构和监督行政权力的功能,表现在:预防行政权的滥用;抵抗行政权违法行使;促进行政权合法、适当运行;促使违法、不当的行政权得以纠正等[7]38-40。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权属于公法权利,具备公法权利的上述功能,另外,基于环境行政领域的特殊性,公众参与环境行政权利具有维护生态环境和实现环境法治的特殊功能。有学者就认为环境问题上的政府失灵所导致政府环境行政决策权滥用和环境公众参与权利保障缺失是造成环境法治轮径的症结所在[8]。环境权利缺失与“政府失灵”的关系,在前文关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缘由分析已经论述,通过构建环境行政领域的公众参与权,可以克服政府决策过程中的独断和缺位,进而实现环境法治。
3.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权的类型构造
如上文所述,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权属于公法权利,且具有立法确认的必要性,应对其具体权利的类型构造进行理论分析,为立法确认提供支持。公法权利理论认为权利由基础性权利和功能性权利构成,所谓基础性权利即有权请求政府作为或不作为;功能性权利是基础性权利的法律保障,即当基础性权利遭受损害或损害威胁时,权利主体享有的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9]对于环境行政公众参与权的构造而言,同样可以区分为基础性权利和功能性权利。环境行政公众参与权包含基础性参与权和功能性的参与请求权。此外,作为一种公法权利,环境行政参与权的确认,除了作为公众环境行政参与制度建构的基本要素之外,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破除过去“官尊民卑”的陈旧观念,彰显人民在环境行政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确立公众与行政权之间对等的法律关系[9]260。人民享有公法上权利的规范根源,立基于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也是宪法保障人权的必然结果。
三、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的缺陷
现行中国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制度是以规定政府义务为主的单一结构,这一特点在《环境保护法》修改之前尤其突出。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只原则性地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既没有规定公众的环境行政参与权,也没有规定政府保障公众参与的义务。第一次在环境立法中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对于公众的环境行政参与权也只字不提。《环境影响评价法》在第5条宣示性地规定了“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并没有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权利,只是表明国家对于公众参与的一种鼓励态度而已。该法规定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规划应该听取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除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以上内容主要在强调政府听取意见的义务。环保部2015年7月颁布实施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也只是对公众参与程序的细化而已,而非公众环境行政参与权利的细化。该办法全文二十条,除去立法目的、适用范围、溯及力及生效时间的规定,剩余十六条规定中有九条在强调环保主管部门的义务,有三条为环保主管部门相关工作的一般指引,明确公众权利的只有两条③,其余两条规定了公众义务。《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属于环保部的部门规章,法律效力位阶低,适用范围较窄,无法有效规制政府其他部门涉及环境的行政决策活动,更无法保障公众参与的权利。
《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中虽然也规定了公众参与的内容,但也以强调政府的义务为核心。如《行政许可法》要求设定行政许可时,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在实施行政许可时,对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④。《行政许可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公众享有行政参与的权利。在这一点上,《行政许可法》与《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公众参与制度的结构是一致的⑤。
中国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主要以政府保障参与义务为核心进行建构,忽视了对公众环境行政参与权的确认和保护,是一种一维结构的公众参与制度,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缺陷:
一是参与主体范围模糊不清。法的指引功能要求法律通过明确界定权利与义务的范围,指引社会公众做出理性的行为。上文释明,中国现行立法未完全确认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权,究竟参与的主体是谁?立法尚未做出明确回应,而是在不断规定政府保障公众参与的义务。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与市场类似,存在失灵的恶性循环,在政府做出环境行政决策时,如果政府怠于履行义务,公众会因缺乏法定环境行政决策参与权而无法启动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有关程序。此时,会产生两种法律后果:后果之一是公众参与的程序性权利受到损害,即政府在未履行保障公众参与法定义务时,环境决策未出现环境公益减损的情况下,公众的程序性参与权受到政府权力的侵蚀;后果之二是公众参与的程序性权利受损同时公众利益及环境公益受损,即因政府违法决策,发生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事件。
二是参与的权利内容缺失。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权应当包括基础性的参与权和功能性的参与请求权。其中基础性的参与权应当包括实体性参与权和程序性参与权,前者保证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后者保证参与的有序性。功能性的参与请求权属于救济性质,是前面两项权利的保障。现行立法并未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实体性权利。中国法律法规主要强调政府义务,对于公众参与权利的具体内容只有零星规定,公众没有完整的基础性参与权利和功能性权利,致使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无法实现有效及有序的制度价值,且公众无法通过功能性参与请求权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只能寻求私力救济⑥,而且这种私力救济的主体通常是一个受害群体,而不是个体。勒庞提出理性的个人会受到社会群体思维的诱导而丧失独立思考,群体的表现是低智商、情绪化的。公众要求对环境行政决策的参与本身是合法且应当的,但公众的情绪化和无序性需要法律进行规制和引导。现行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程序不够完善,公众“救济无门”,只会选择更加激进的、情绪化的方式维护因政府环境行政决策失误而损失的利益,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的爆发。
三是参与主体的法律责任缺位。行政法学通说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共同构成了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环境行政决策的参与主体应包含作出环境行政决策的政府和相对人。环境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法律责任承担主体应包括这两个主体。中国现行立法并非没有规定两者的法律责任,但是不够完善,尤其是关于政府回应公众参与的法律责任不够明确。譬如环境保护法第五章专门规定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但是全文未提在公众参与过程中政府如何回应公众的意见。第六章关于法律责任中也未对没有回应公众意见的政府决策行为予以规制。立法中和实践中,政府回应都未受到法律的规制,使得公众参与决策流于形式,无法实现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的有效价值。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应当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政府对公众参与提供保障的同时,应该对公众主张参与权利做出积极回应,实现该制度的价值。如前文所述,公众参与并不是要求由公众对环境政策做出独断,而是在决策过程中公众充分参与,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利益诉求,政府对此做出评估和考量,无论决策结果如何,都应当对公众做出积极回应,并且负责对公众的质疑予以解答,舒缓公众的对立情绪。但是,现行立法对于公众参与的程度和有效性缺乏详细的规定,使得实践中公众参与流于形式,政府对公众的质疑或是搪塞或是置之不理,最终诱发环境群体性事件。
四、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的完善
克服现行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三大缺陷的关键是确认和完善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权,这也是耶里内克及雪莉关于公众参与理论的基石。首先,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权的权利主体界定一直以来在实务界争论不休,即公众的范围究竟如何界定。立法必须予以明确“利害关系人”的范围,进而对公众参与权利人的范围做出明确回应,否则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将会陷入真正利害关系人可能无法参与决策的混乱局面,最终使公众参与成为假参与或者表面参与。其次,为实现对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法律指引,立法必须对公众参与权的内涵进行立法确认。通过对公众参与实体性权利的立法确认,使得公众可以在政府怠于履行政府义务时,有权主动启动参与机制;通过对公众参与程序性权利的立法确认,使得政府在环境决策的启动、实施全过程都符合法定程序的规定;通过对功能性参与请求权的立法确认,保障公众在基础性参与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威胁时,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方式得到法律的救济。最后,立法应明确各参与主体的法律责任,规范公众参与行为和政府怠于回应公众的失灵行为,为实现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有序化和有效化提供强制性法律依据。
1.确定公众参与的主体范围
立法必须明确公众作为主体参与决策的范围,为公众提供明确的指引。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主体应该包括公民、企业和相关组织,不应做过多的限制。根据奥尔胡斯公约,公众指一个或数个自然人或法人以及其依照国家法律成立的协会、组织或团体。环境行政决策所涉及的“所涉公众”也就是指正在受或可能受环境决策影响,或于环境决策中具有利益的组织或个人。也包括未具有直接利益诉求,但为贯彻公约目的,宣传环境保护并符合本国法律任何相关要求的非政府组织(NG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⑦。现行环境行政决策制度在设定公众参与的主体范围时,主要强调“利害关系”,即要求参与的主体与环境行政决策的结果又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一点和奥尔胡思公约中关于“直接利益”的规定有相似之处,但是现行环境行政决策制度并没有效仿奥尔胡思公约的扩张性规定,对“直接利益”做出扩张性解释,即并未将不具有直接利益的非政府组织纳入参与主体的范围。在中国,环保组织在监督政府环境行政决策、维护环境公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立法已经确认了环保组织及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法律地位,突破了传统诉讼法关于“利害关系”的规定。在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中,应该对“利害关系”做扩张解释,扩大参与主体的范围⑧。
在具体的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设计中,如何识别应该参与的“公众”是一个难题。参与公众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参与的效果。由于信息不充分,环境行政部门无法从广大公众中准确选择参与主体,倘若政府强行指定参与公众,不但有悖公众参与的目的,甚至会适得其反,引来更大责难。为降低信息成本,可以在参与活动进行之前,通过网络、电视、公告等渠道广泛发布信息,征集参与的公众。在政府详细公开信息的前提下,公众个人对于自身是否受影响和受多大影响最为了解,具有信息优势。因此,对于有意愿参与的公众实行登记,并要求登记人员列举其认为可能受到的影响,并提出初步证明,从而识别出可能受影响的公众,保障其参与的权利。若参与人数较多则可由其推选出代表。对于有意愿参与的环保组织原则上应该同意,若参与的环保组织过多,可由其推选出代表性组织参加。
2. 确定公众参与的具体内容
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权利包含基础性参与权和功能性的参与请求权。立法规定基础性权利可以为公众提供指引,明确公众享有的法定参与权利的详细内容。而功能性的参与请求权的规定是为了克服政府回应机制缺失的缺陷,即当政府怠于行使法定义务损害公众的基础性参与权时,能够及时寻求法律的救济。基础性的环境行政参与权并非一项单一的权利,而是包含多项子权利的权利束,如公众参与启动权、获取信息权、参与意见表达权等。如前所述,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过程乃是公众与政府、企业互动的过程,公众在此过程中的行为包括参加行政活动、发表意见、获得反馈、参与决定等行为。为了使得每一个参与行为都具有规范基础,保障各行为的有序、有效进行,应该根据各类行为设定相应的权利。环境行政公众参与活动中公众参与行为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一是参加行政活动,二是表达意见,三是获得回应,四是参与决策。由于公众的参与行为乃是前后相继的连续性行为,因此环境行政参与权各子权利的赋予应该保持连续性,前后衔接,覆盖到环境行政参与的全过程,构成一个完整的权利体系。
基于基础性权利产生的参与请求权需要与基础性权利相对应。如果可以直接通过立法确认参与请求权最好,如若不行,公众参与权本身即可以推导出参与请求权。环境行政参与请求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诉权。诉权本质上是一种向法院请求法律救济的请求权,属于广义上的公法请求权范围。此处的公众参与环境决策请求权是一种实体法上的权利,可以不通过诉讼而直接向行政机关行使。当环境行政机关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公民便无需通过法院寻求救济。当环境行政机关没有履行相关的义务时,法律可以赋予公民诉权,通过司法渠道进行救济。
3. 明确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主体责任
公众群体情绪化和政府失灵是客观存在的,必须通过明确法律责任进行规制。克服公众参与无序化和政府回应机制缺位的最好手段是制定严格的法律责任。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包括公众权利和政府义务两个维度,因而法律责任也应该涵盖公众违法责任和政府违法责任两个维度。公众参与的无序化需要立法规定,当公众违法行使其参与权时,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政府回应机制缺位也应当追究政府责任。导致公众参与无序化的原因不只是公众违法参与,实践中群体事件的发生多是由于公众参与权尚未建立,公众无法通过法定途径寻求救济,所以法律责任的确定应着重放在规政府责任上。其立法可以参照2015年颁布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将领导责任及党政同责作为规制的原则。对在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中,未回应公众意见或者消极回应而做出决策的政府及党委负责人、直接责任人进行党纪和法律的双重规制,并作为政绩考核之一,实行终身追责。
注释:
① 学者调研后总结出公众参与环境公共决策的几个阶段:1.对政府决策行为不知情;2.猜疑并且评议企业项目建设;3.因发现或怀疑环境污染损害事实而向政府部门了解情况;4.希望政府重新审查或查处污染企业;5.被企业和政府忽视后的集体散步或围堵政府部门;6.媒体曝光后群体性事件发酵而引发大规模冲突;7.政府维稳,担心事态扩大化而妥协,公众要求可能得到满足。参见汪劲《环保法治三十年》第53页。
② 公法权利理论在我国台湾地区已较为发达,如台湾地区学者李建良教授所编写的行政法教材《行政法基本十讲》已将公法权利作为专章进行论述。公法权利在大陆地区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关论著不断推出,如徐以祥:《行政法学视野下的公法权利问题研究》等。
③《环境公众参与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电话、信函、传真、网络等方式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这属于基础性参与权中的程序性权利。第十二条规定: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有权向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举报。”本条宽泛的规定了公众对“环保主管部门不履行职责”的举报权利,可以理解为是功能性参与请求权的原则性规定。
④ 如《行政许可法》第十九条规定:“起草法律草案、法规草案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草案,拟设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设定该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该条强调了起草单位负有听取公众意见的义务,但却明确规定公众享有参与权。类似规定还可见该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
⑤ 此种以强调政府义务为核心的公众参与制度或许也不仅限于《环境影响评价法》和《行政许可法》,在其他法律制度中同样出现,这或许与我国长期以来强调政府主导的传统有关。
⑥ 私力救济可界定为: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者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实现权力,解决纠纷。私立救济具有非程序性,主要实现途径是依靠私力,此处的“力”包括对权利救济有影响力的一切手段——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目前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多数是由于公众在法定制度内无法实现权利诉求,只能寻求私力救济,毫无程序可循,致使群体性事件从一开始发生就必然决定了其破坏性和不可预测性。参见徐昕《论私力救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 在《奥尔胡斯公约》第二条第5款规定了所涉公众的范围,对环境行政参与权的主体范围的确定提供了参照。
⑧ 关于社会组织等参与环境保护的正当性及可行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强调“社会组织的非政府性决定了其不受政府行政权力的支配,是与政府、企业并列的‘第三部门’‘,能够更加中立和理性的对待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也能够更加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行政执法。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决定了其不以谋取利润为目标,而是注重将自身财产用于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积极地改善生态环境。”详见本书第47页。
[1] 汪劲.环保法治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9.
[2] 王锡锌.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一个理念和制度分析的框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
[3] 朱谦.个体公众参与的非理性——公众环境利益表达组织化[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34-35.
[4] 栗燕杰.行政决策法治化探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128.
[5] 杜健勋.邻避运动中的法权配置与风险治理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4):110-114.
[6] 郭道辉.把权力关进笼子先要把权利放出笼子[EB/OL]. (2014-12-26)[2016-3-19]http://www.21ccom.net/articles/ china/ggzl/20141226118142.html.
[7] 徐以祥.行政法学视野下的公法权利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3-184.
[8] 谢海波.论我国环境法治实现之路径选择——一正当行政程序为中心[J].法学论坛,2014(3):112.
[9] 李建良.行政法基本十讲[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259-260.
责任编辑:黄燕妮
The defects of the system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and perfect path
YANG Changbiao
(Economic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China's curr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system has been around for strengthening administrative government obligations to construc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absenc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main range of vague, lack of participating right and legal liability. As a result, public participation rights cannot achieve effective relief, environmental group events occur frequently an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fall. Legislation should simply focus on the government to abandon the ideas of legislation obligations to clarify the subject of rights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power of the executive, the specific content and legal responsibility to realize the value system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system of orderly and effective.
NIMBY conflict; public law rights;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defects;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D922.6
A
1009-2013(2016)04-0076-07
10.13331/j.cnki.jhau(ss).2016.04.012
2016-04-29
司法部资助项目 (14SFB20043);2015年西南政法大学资助项目(XZYJS2015200)。
杨昌彪(1989—),男,河北张家口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法学。
——评《大学内部治理中的学生参与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