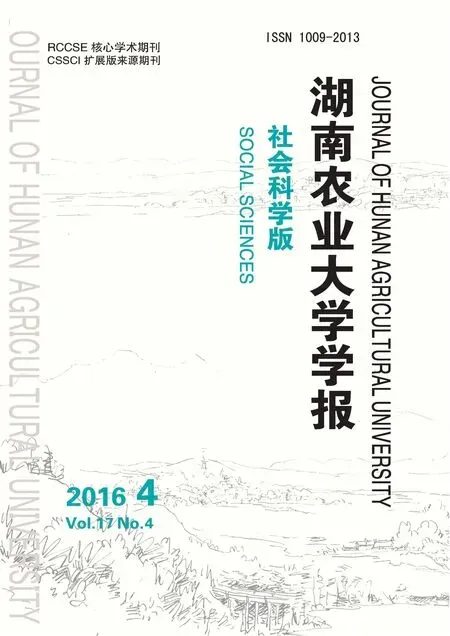农村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困难及其对策
尹振国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 401120)
农村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困难及其对策
尹振国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 401120)
农村职务犯罪主要是指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其法律适用存在诸多难题,如“农村基层组织”及其“人员”的认定、公务与集体事务的区分、公共财产和集体财产混同,不同性质的违法数额能否相加、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能否成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不明确,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机构不统一等。在对立法和司法解释上的疑难问题加以归纳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界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范畴、正确区分公务和集体自制事物、区别侵占公共财产或集体财产的行为性质、明确不同性质的违法数额不能累加、明确渎职犯罪主体不包括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等对策。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村干部;职务犯罪;村民委员会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俗称“村干部”)职务犯罪是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包括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的犯罪行为。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报告显示,中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0.32%,农村居民6.74亿。中国农村约有58.9万个村委会,有98%以上实现了直接选举。以每个村委会有5名村干部计,就有近300万名村干部。“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基层是整个国家政权体系的基础,如果农村基层政权发生大面积的贪腐,那么国家政权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能否遏制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才是对反腐败的真正考验。由于农村工作十分复杂,在司法实践中,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行为的性质认定存在较大的分歧。现有的研究多采围绕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现象、原因、对策展开,关于法律适用问题的研究大多未结合司法实践,不够深入。基于此,笔者拟围绕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经济发达地区的审判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防治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对策。
一、农村职务犯罪
在国家乡镇政权权力“悬浮”于乡村、支农强农富农惠农资源下乡的大背景下,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日益高发、易发,在经济发达地区,此类问题更为突出,危害更为严重。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村干部为主体的“小官巨腐”案件日益凸显。
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权力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法律法规授予的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的权力,按照现有法律、法规,村委会享有的行政管理权力几乎囊括了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能。法律法规授予村委会的权力由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来行使。另一部分是村民委员会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享有的自治权力,这些自治权力同样由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享有。在现有的体制下,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拥有政府代理人和村民代理人的双重身份,而他们可以轻易游离于国家权力(体制内)和村民权利(体制外)的监督,从而容易导致其“滥用委托权力来谋取私人利益”。村干部权力过大,缺少制约和监督,是导致贪腐的主要原因[1]。村干部贪腐已成为城镇化趋势下的突出问题,村干部贪腐,凸显乡村治理之困。如果对村干部贪腐问题不重视,村干部有“胥吏化”的危险[2],乡镇政权有被架空的危险。如果村干部再与农村宗族势力、宗教势力、黑恶势力勾结、联合,就会对乡村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从近年来各地发生的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来看,村干部职务犯罪多发生在征地补偿款、拆迁补偿款、赈灾救济款、扶贫款、惠农业补贴、低保、粮食补贴、住房补贴等款项的报批、分配、发放环节。村干部常见的作案手段:以权谋私,私分国家对集体土地的补偿、惠农补助及项目资金;损公肥私,违规处置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和其他公共财物;滥用职权,在工程建设项目承包和经营活动中谋取利益;弄虚作假,骗取国家各种支农、惠农资金;违规操作,挪用公共款物;吃拿卡要,索贿受贿等等。随着城镇化的飞速发展,城市近郊的农村土地升值,村干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土地爷”,近年发生的大案基本上与土地有关。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群众感受最深、痛恨最深,村干部腐败是不折不扣的“群众身边的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要切实解决好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提升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201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坚决查处发生在农民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2016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加大对农民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监督审查力度,重点查处侵犯农民群众权益的问题”。“中央一号文件”释放了强烈的信号——向“农民身边的腐败”亮剑。从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为期两年的集中惩治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
治理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腐、防止其“胥吏化”的根本之策是大幅压缩村民委员会的行政权力,加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实现村干部权力有限化、明确化、法定化、规范化。在目前乡村社会国家权力缺位的情况下,国家刑罚权要“补位”,刑法必须对日益严重的村干部腐败问题予以积极回应[3]。
二、农村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难点解析
通过梳理、分析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例可以发现,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立法和司法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公检法之间对案件的定性和管辖问题也存在着较大分歧,严重影响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打击,这些问题亟待解决①。
1.“农村基层组织”及其“人员”界定模糊
“农村基层组织”一般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现行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立法解释中的“村民委员会等农村基层组织”,这里的“等”是等外,是列举未尽,表明农村基层组织是类似于村民委员会级别的组织;另一种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将“农村基层干部”分为两类,一是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和基层站所负责人,二是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村民委员会成员,这表明“农村基层组织”还包括乡镇一级政权组织。究竟哪一种符合刑法的规定呢不清楚。
农村党团组织、农村村民自治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组织的职能并非泾渭分明,而是重叠和交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身份、职位、工作任务也存在重叠和交叉的情况(有的村干部身兼数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会计、村经济合作社社长等),将哪些组织的人员确认为“农村基层组织的人员”也难以确定。
此外,对于大学生村官是否是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也界定不清[4]。刑法第九十三条将国家工作人员划分为纯国家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大学生村官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列入公务员序列;也不是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因为农村基层组织不是国有单位,而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5];不属于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因为农村基层组织不属于事业单位,更不是公司、企业;那么他们是否能类分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呢?法律并未予以明确。
2. 公务及集体自治事务界分不清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以下简称“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立法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七种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②。这里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被称为“准国家工作人员”,属法律拟制,与“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纯国家工作人员”相对,而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以上七种行政管理工作之时才能成为“准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只有当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政府从事以上七种公务之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才分别适用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的规定[6]。而当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集体事务(农村党务、团务工作、农村自治事务、集体经济经营事务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可能分别适用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规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不同的职务便利,由不同的司法机关管辖,构成不同的犯罪,配置不同的刑量,适用不同的减刑、假释规定。因此,对公务和集体事务进行区分是案件定性和管辖的关键。由于农村基层工作事务异常繁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会拥有多重身份,在履行职务时公务和集体事务集于一身,互相交织,他们从事的事务哪些是公务,哪些是集体事务,界限十分模糊,导致定罪困难。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立法解释采用列举加兜底的方式对“行政管理工作”即“公务”进行了规定,“但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的范围如何则不无疑问,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和分歧的来源。
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范围。行政机关主要是从事行政管理事务的,虽然不排除其他国家机关也有行政管理实务[7]。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也可能协助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工作,但不是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立法解释所指称的“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是指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国家行政机关从事行政管理工作。那么,基层组织人员协助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从事工作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如何处理?
公务与农村集体事务交织情形下行为性质的把握。公务与农村集体事务交织、混同问题在农村基层组织利用、依靠“土”政策在国有土地上建房过程中较为突出,审判实践中争议较大,不同法院定性各异,亟待统一。当前,政府为推进农村住房制度改革而建设农民公寓房,政府在立项后,将相关农村集体土地的性质通过法定程序转为国有,并在房屋建设中给予相应补贴,建设资金由村集体向银行贷款解决,具体的工程建设事宜主要由村集体负责,房屋分配由村提出方案、镇政府确认。从政府角度看,这是政府工程,土地也为国有土地,带有公务性质。镇政府作为项目建设主体,在国有土地上建设农民公寓,是人民政府经营和管理国有土地的一种形式,村基层组织因受人民政府的委托,协助人民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而代为履行了部分的资金筹集、工程建设管理、工程款拨付及房屋分配等权力,行为人的行为应认定为协助政府履行公务。从村集体角度看,建造资金、费用开支、施工管理等均由村集体负责,住房也是出售给村民,属于村自治范围内事务的内容。当前争议的焦点是当村务与公务两者交织在一起时,对行为人的行为是按照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还是按照村自治范围内事务认定更为妥当?或者说,对于政府指导或主导,但农村基层组织自主实施的工程建设项目,是否可以认定是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包干型”征地拆迁中非法占有征地补偿费的行为的定性。“包干型”征地拆迁方式是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实行以行政村为单位包干、核拨,村委会按有关规定落实到户兑现。政府对下拨给村的补偿款,实行多不退、少不补的原则。此种征地拆迁方式引发下面两个问题:一是“包干型”征地拆迁中发放土地补偿费是属于公务还是村务?二是村集体提留前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土地补偿费的行为是贪污还是职务侵占?
3.公共财产和集体财产不明确
在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财物与挪用钱款案件中,财物的性质决定着被告人行为的定性。如果行为人非法占有的是公共财物,挪用的是公款,则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若行为人非法占有的是集体财物,挪用的是集体资金,则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由于基层组织财物管理混乱,没有按照“专款专账、专款专用”的要求进行管理,公共财产和集体财产经常混同在一起,甚至公共财产、集体财产与私人财产混同在一起,无法分辨,行为人非法占有或者挪用这些财产,构成犯罪时如何定罪?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公共财产和集体财产混同但各自数量明确时,如何处理行为人非法占有或者挪用的财物?
4.不同性质的违法数额能否累加无明确规制
犯罪数额是决定定罪量刑的主要因素。如果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既利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的职务之便又利用从事集体事务的职务之便,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所收受或索取的财物均达不到成立犯罪的数额要求,但合并计算可达到某一具体犯罪数额标准的情况下,是否对行为人进行犯罪追诉?如何定罪?同样的情况可能也会发生在非法占有、挪用财物犯罪中:贪污、挪用的公共财物的数额与侵占、挪用集体财物的数额均达不到成立犯罪的数额要求,但合并计算却可达到成立某一具体犯罪数额标准。对不同性质的违法数额能否累加无明确规制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扰。
5.农村职务犯罪中的渎职罪难以认定
刑法第九章将各类渎职罪的主体确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法渎职罪的立法解释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该立法解释是对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纯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扩展。而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立法解释却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七种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准国家工作人员)[8,9]。也就是说,立法解释并没有将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列为渎职罪的主体。在司法实践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权上的便利或者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如何定性处理存在困难。
6.职务犯罪案件管辖的机构不统一
从司法程序角度来讲,案件性质决定案件管辖,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犯罪的,由检察机关侦查;涉嫌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挪用资金等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侦查。纪委在查办农村基层组织中党员的违纪行为时,对涉嫌犯罪的人员以及线索也是根据其所涉嫌的罪名移交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办理。法院在查明事实后虽有权变更起诉罪名,但由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不统一,各办案机关对法律的理解、案件事实的把握和认定不同,会影响犯罪证据的收集,检察机关对法院判决变更指控罪名的抗诉较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案件管辖问题异议较多。管辖问题客观上造成人民群众举报难、告状难。虽然法律规定了案件线索、材料移送制度,但是由于流转环节多,增加了泄密的可能,对举报人、告状人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三、农村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困难的破解
1.合理界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范畴
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立法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七种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可见,立法解释将“农村基层组织”理解为村民委员会一级的基层组织,不包括乡镇一级的政权机关。
一般而言,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农村党团组织人员,即党支部(党总支)、共青团支部成员等;第二类是农村村民自治组织成员,包括村民委员会及下属的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与计划生育等委员会的成员、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村会计、村出纳、村文书、村小组组长等;第三类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村经济合作社、村互助合作社、村经济联合社中的成员;第四类是农民自发组建的组织中的成员,如农村治安联防队、农会、农民协会、农民互助合作组等组织中的成员等。
村党支部书记、委员、村委会主任、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村财务人员、村文书、村民小组长等人员,因在农村基层组织中担任某种职务,或多或少负有组织、领导、沟通、协调等职责,存在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可能性,在一般认识上应被认为是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具备被认定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可能性。将上述人员实施的贪污、收受或索取贿赂、挪用行为纳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职务犯罪的主体范围属扩张性解释,符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语义范围,并不违反刑法罪刑法定原则。换言之,无论是经选举、任命、指派、提名、批准、聘用等而在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中担任职务的任何人员,无论是长期或者临时,计酬或者不计酬,都属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
大学生村官是国家选派到农村中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很显然不属于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也不属于国家机关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因为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不是国有单位,也不是非国有社会团体。大学生村官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如果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可以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
2. 正确区分公务和集体自治事务
由于政府行政管理工作包罗万象,而成文法无法囊括所有的政府行政行为,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立法解释中的“政府行政管理工作”不限于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行政管理工作。根据行政法定原则——一切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与法规的规范,行政行为“符合法律与法规的规范”并不是指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形式完全符合法律、法规,而是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精神和法律的正当程序[10]。行政管理活动必须遵守行政合法性原则,即有法律法规依据并遵守法定程序。对于从事不属于政府行政管理权属范围内的工作,不能认定为“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党组织从事党务工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收受或索取贿赂,构成犯罪的,定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只是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政府才是行政管理的主体,政府也是行政管理责任的最终承担者。“作为法律上的主体,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其要有意思表示能力,且能独立地作出,非依附性是主体的基本要求……社会组织和个人成为社会主体的关键是独立性。[11]” 由于法律、法规没有授予村民委员会独立行使行政权的权力,其不能成为行政主体。
在现行刑法规定中,未明确在受委托组织中从事公务人员的法律地位。立法解释将此类人员作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最高人民检察院第5号指导案例(陈某、林某、李甲滥用职权案)认为村委会系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政职权的组织进而将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列入渎职犯罪的主体是不妥的,因为立法解释已经将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列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刑法明确性原则不仅要求刑法条文明确,而且要求刑法概念的外延分类明确。既然立法解释已经将协助政府从事七种行政管理工作时的村基层组织人员划定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就没有必要再将其纳入“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否则,既扩大了立法解释的内涵(超出七种行政管理工作的范围),又导致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在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能否构成渎职罪没有明确的结论。如果根据刑法解释得不出唯一的结论,或者模棱两可,或者左右摇摆,那么必然会陷入“不可知论”,那么这种刑法解释必然是错误的。否则,就会随意给人定罪或者宣告无罪,破坏刑法保障人权的机能。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受委托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不能列入纯国家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可以在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中增加一类国家工作人员即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可解决这一难题。
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间的把握。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绝大多数是临时的、有时间限制的。既然是“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协助行为是从行为,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才是主行为,从行为依附于主行为。也就是说,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时间段是依附于政府行政管理时间段的。政府行政管理行为的结束就意味着协助政府行政管理行为的结束。换言之,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是有时间限制的,不可能成为永久性的工作。那么,一旦超出这个时间段,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应定性为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挪用资金等,不可能构成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
公务与农村集体事务交织情形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处理具体案件时,难以区分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是利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职务便利,还是利用管理村集体事务的职务便利的,一般应当认定为利用管理村集体事务的职务便利,因为他们本身毕竟是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而并非政府公务人员。
“包干型”征地拆迁中非法占有征地补偿费的行为定性。浙江省《关于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犯罪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发放到村,村集体尚未提留前,村基层组织人员对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侵吞、挪用行为,应认定为贪污罪或者挪用公款罪。据此,有意见认为在村集体提留前村委会委员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便利,采用将集体土地虚报为个人土地冒领土地补偿款的行为应按照贪污罪定罪处罚。从形式上看,以贪污定性是符合上述规定的,但具体到“包干型”分配土地补偿费用的方式而言,认定非法占有的钱款属于集体财产更符合实际情况。镇政府核拨的作物补偿款在由村集体支付村民的作物赔偿款后还有数额不小的结余款项,行为人的行为并未直接影响到村民的利益;又因采取的是“多不退、少不补”的包干处理方式,行为人的行为也未直接侵害国家利益。对于结余款项可视为村集体提留资金。结合《解答》中第三条规定:土地征用补偿费发放到村,村集体按照规定提留后,村基层组织人员侵吞、挪用应当发放给农户的资金,以贪污罪或者挪用公款罪认定;侵吞、挪用村集体提留资金的,以职务侵占罪或者挪用资金罪认定。故从资金性质角度看,非法占有的资金属于集体资金,非法占有的行为应按照职务侵占而不是贪污定性。
3.区别侵占公共财产或集体财产行为性质
由于农村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混乱,实践中土地补偿金、房屋拆迁补偿金、搬迁安置费与村内自有资金相混淆的情况较为常见,因而存在着定性难的问题。对此,首先应确定行为人系利用何种职务便利实施的侵占、挪用行为,如果分别利用了不同的职务便利侵占、挪用公共财物的,则应当分别定罪,实行数罪并罚,对此并无疑问。如果利用一种职务便利侵占、挪用财物构成犯罪,而利用其他职务便利侵占、挪用财物尚未构成犯罪,则以构成犯罪的罪名定罪量刑,对此亦无争议。如果不能具体确定行为人利用何种职务便利实施侵占行为的,应当根据刑法中有利被告人原则,就低认定,择一轻罪定罪处刑。村基层组织人员采取虚报土地属、人口数等手段侵吞土地征用补偿费的行为,应认定为贪污罪。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发放到村,村集体尚未提留前,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对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实施的侵吞、挪用行为,应定性为贪污罪或挪用公款罪。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发放到村,村集体按规定提留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侵吞、挪用应当发放给农民的资金,以贪污罪或者挪用公款罪认定,侵吞、挪用村集体提留的资金,以职务侵占罪或者挪用资金罪认定。
由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量刑重于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对涉案资金权属的界定直接影响量刑,所以在定罪时也可以通过客观证据反推行为人的主观意图,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分析。有证据证实行为人主观意图明确指向土地补偿费用等资金的,侵吞、挪用的资金在土地征用补偿费用数额内的,以贪污、挪用公款罪认定;超过的部分认定为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行为人主观意图指向土地补偿费用等资金的,以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罪认定;超过村集体资金、属于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部分,以贪污罪或挪用公款罪认定。
如果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挪用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数额与侵占、挪用集体资金的数额均未达到构罪标准,但总额达到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构罪标准的,以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认定。
4.明确不同性质的违法数额不能累加
对职务犯罪来说,犯罪数额是成立犯罪的主要条件,犯罪数额体现着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因此,犯罪数额不仅是追诉犯罪的标准,而且是犯罪构成的要素之一。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唯一依据,如果某一行为不具备犯罪成立的全部要件,则不可能构成犯罪。不同性质的数额均未达成成立犯罪的程度,那么均不能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那么不同行为均不构成犯罪,即使将不同性质的数额相加也不构成犯罪。如浙江省《关于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犯罪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第 4条规定:“贪污、挪用土地征用补偿费的数额与侵占、挪用集体资金的数额均未达到构罪标准,但总额达到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构罪标准的,以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认定。”
5.明确渎职犯罪主体不包括农村基层组织人员
刑法规定渎职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进行了扩张解释,增加了三类人员——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显然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能否将其归入第三类,即“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的人员。由于村主任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既不是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又非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因此,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不能成为渎职罪的主体。虽然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立法解释所列举的救灾、抢险、防汛等六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行为客观上是存在,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按现有法律,还不能对其认定为渎职罪,为此需完善刑法。
6.统一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受贿、挪用资金等归检察机关管辖,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挪用资金等由公安机关管辖。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分散管辖带来的举报难、告状难、侦查难等问题,建议统一由检察院管辖,如此就可解决难题。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本质上属于腐败犯罪。而对于腐败犯罪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侦查主体一元化”,即由一个专门的机关进行管辖,有的是检察机关、有的是专门的反贪部门如香港的廉政公署,中国的二元化模式显然不符合国际“侦查主体一元化”的潮流。而且,多头执法容易导致推诿扯皮、力量分散、效率低下、司法成本高等问题。也可以将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视为刑法拟制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从而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划归检察机关统一行使[12]。
注释:
① 根据我国刑法典,我国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进行规制的主要罪名是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刑法第228条)、挪用特定款物罪(刑法第273条)、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法第342条)、非法采矿罪、破坏性采矿罪(刑法第343条)、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刑法第 345条)、贪污罪、职务侵占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等等。
② 七种行政管理工作是指:(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代征、代缴税款;(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1] 赵东平.村官职务犯罪的权力透视[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4):97-101.
[2] 薛恒.清代对胥吏的管理及其失控原因[J].东南文化,2003(7):66-69.
[3] 吴杰.村官职务犯罪刑法规制的基本原则[J].法律适用,2015(7):60-64.
[4] 熊永军,王东方.大学生村官职务犯罪的困境与对策——以王某贪污救济款为例[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坛),2012(5):141-145.
[5] 欧少亭.新编现代汉语词典[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2:991.
[6] 赵秉志,时延安.略论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立法解释[N].法制日报,2000-05-28(3).
[7] 张兆松.论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刑法地位[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4):110-117.
[8]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7.
[9] 李景月.行政管理学[M].甘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3.
[10] 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3.
[11] 张树义.行政主体研究[J].中国法学,2000(2):79-85.
[12] 徐宏.“村官”职务犯罪职能管辖的困局与出路[J].中国检察官,2010(9):59-61.
责任编辑:黄燕妮
The legal dilemma and breach of occupational crimes relating to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YIN Zhenguo
(School of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Village cadres corruption has been a serious problem under the rural-urbanization in China. This problem has highlighted village government difficult position. The penal law must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village cadres corruption.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of occupational crimes relating to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For instanc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person", official and collective affairs, confusion of public property and collective property. On the basis of the summary of problems about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ome detailed solution is proposed to perfect the legislation.
person in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village cadre; duty crime; villagers' committee
D924
A
1009-2013(2016)04-0063-07
10.13331/j.cnki.jhau(ss).2016.04.010
2016-05-27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调研重点资助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13BFX048)
尹振国(1981—),男,湖北汉川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法治研究。
———公务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