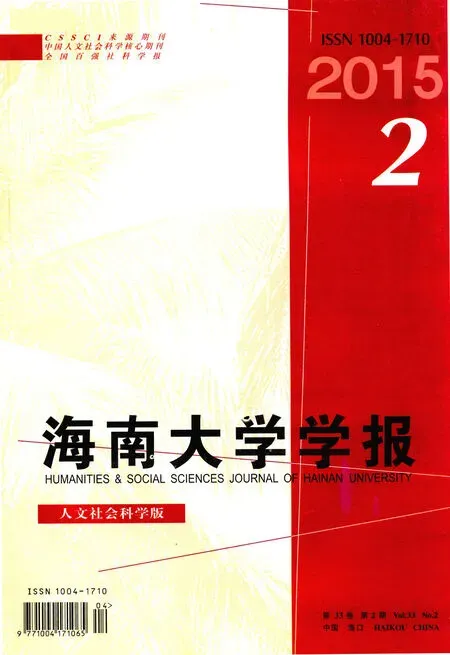从叙事学角度看拉封丹寓言的艺术特征
王 佳,丁 杨(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从叙事学角度看拉封丹寓言的艺术特征
王佳,丁杨
(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运用20世纪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提出的叙事理论,分析拉封丹寓言中的“时距”和“语态”等叙事策略,并探究它们对寓言产生的价值。一方面,寓言叙述中不同的“时距”使得寓言的叙述节奏不断变换,拓展了寓言故事的内容,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也丰富了寓意;另一方面,拉封丹寓言中独特的叙事“语态”建立了不同于作者和读者的直接对话渠道,它强化了叙述者的身份,从而进一步发挥了其情节编撰以及与叙述对象沟通等功能。拉封丹的作者身份与叙述者身份的互动,使读者不必将寓意与作者本人的哲学立场建立必然联系,从而让读者获得更广阔的哲学思想空间,使寓意生成更具开放性。
[关键词]寓言;拉封丹;叙事学
法国17世纪著名寓言家让·德·拉封丹在所创作的《寓言集》中独特创作技巧使原本枯燥的寓言故事变得丰富,使功能性文本获得了较高的美学价值,从而成为法国家喻户晓的寓言经典,在数百年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寓言的文本形式和寓言本身的功能价值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本文将用20世纪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在《辞格III》中所提出的叙事学理论来探究这种可能性。
热奈特提出的叙述研究方法是完全不同于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关于修辞性叙述的研究理论,该理论强调以文本为中心,同时关注叙述方法和叙述行为,叙述方法体现作家的创作风格,而叙述行为的明确有助于挖掘深层的文本意义。热奈特将叙事方法分为五个类别:时序( ordre)、时距( durée)、时频( fréquence)、语式( mode)以及语态( voix)。不同叙述策略的组合形成了作家各异的叙事风格。和长篇小说不同,寓言的篇幅比较短小、干练,能体现寓言家个人特色的叙事方法通常是“叙述时间”和“语态”。拉封丹就是能在短小篇幅中体现精湛技艺的寓言家。多变的“时距”和“语态”形成了拉式寓言的独特叙事艺术。
一、“时距”的自由
“时距”也被称为“叙事节奏”。热奈特认为,叙述故事的速度是无法精确测量的。文本不同于电影或音乐,可以直观地判断出一个所谓的正常速度,叙述的速度取决于文字,而只能获得一个相对速度,所以测定叙述时长和叙述故事发生时长的关系具有一定难度。热奈特参考了让·里卡杜的观点,将叙述运动分为概述( sommaire)、省略( ellipse)、停顿( pause)、场景( scène)四类①热奈特根据叙事文本时间( TR)和故事时间( TH)的关系将叙述运动分为:概述( TR<TH),省略( TR =0,TH = n),停顿( TR = n,TH =0),场景( TR = TH)。。这一分类方式有助于人们理解作者在叙述中的选择:概述的叙述时距远小于故事时距,是作者线条式纪录故事内容的方式,而这也是传统寓言创作的基本模型,寓言的鼻祖伊索笔下的寓言故事就大多以概述为主,例如,在寓言《狗和牛皮》中,故事讲述部分只有两句话:“一群恶狗看见有几张牛皮泡在河里,但是可望而不可及,他们便决定把河水喝干。但直到狗已经被河水撑破了肚皮,牛皮还飘在离他们很远的水里。”[1]这种简明的叙事风格是功能性文本的一大特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叙述,并以直接的方式析出寓意。这一方法在寓言创作中较为常见,“概述”在拉封丹寓言中仍是重要的叙述方式,不过,拉封丹并不满足于“概述”这种缺少感情色彩、略显沉闷的叙述方法,在大部分寓言故事中,拉封丹都会适时地利用“省略”、“停顿”等方法来改变“叙事文本时间”,进而改变叙述的节奏。需要指出的是,在寓言叙述中,“省略”和“停顿”都是相对而言的,是文本中的“话语”( récit)和功能“故事”( histoire)的原型比对得出的,这里的原型是读者经验中寓言故事的原型,“无论话语层次怎么表达,读者总是依据生活经验来构建独立于话语的故事”[2]20,以此为基础,笔者便有了判断叙述节奏变化的准绳。
“省略”是叙述中时常会出现的一种叙述方式。在小说中,“省略”的使用频率会比较高,但在寓言中,本身就简洁的文本如果“省略”不当就会脱离寓言的轨道,从而导致寓意的偏差。拉封丹在文本中一般“省略”的是故事的结局,在不影响读者完好地理解故事梗概的前提下,这种开放性的结尾会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并留出想象空间。如: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中,好逸恶劳的知了在寒冬向蚂蚁求助,遭到拒绝,知了此后的遭遇并没有在文本中提及,拉封丹选择用蚂蚁的一句话结束:“歌唱?我太满意啦。你呀,现在跳舞吧!”[3]4应该说知了最后食不果腹的结局是该篇寓言的重点之一,但拉封丹没有直接提及它,而用蚂蚁耐人寻味的回答来结束全文,知了的求食未果之后下场如何,问题的答案留给读者思考,结局的“省略”并未削弱寓意的实现,反而更好地警示那些想不劳而获的人们。在《驮神像的驴子》一文中,自以为被人膜拜的驴子并不知道在它面前膜拜的人们所敬仰的并不是它,而是它背上的神像,直到有人指出:“人家拜的不是你,是神像”[3]160,故事到此为止,并没有续写“驴子”对嘲讽的回应或者遭遇的下场,虽然这一结尾让故事略显突兀,但仔细思考,“驴子”的“沉默”衬托了其思想的匮乏,“驴子”回应的缺席反而增强了作者的讽刺力度,获得了令人更为捧腹的效果。适时的“省略”把节约的叙述空间留给读者,让读者更好地根据自身的经验和感悟体会属于自己的寓意。
故事叙述节奏的变化还体现在“停顿”的使用上,“停顿”常常是通过对环境和心理的描写来达到烘托的效果。“停顿”的叙事文本时间无限大于故事时间,当“概述”和“省略”确保文本的简洁时,“停顿”会在一定程度上令文本有拖沓之嫌。而作者在寓言中对“停顿”的使用十分大胆,他的“停顿”不但数量多,而且都出现得恰到好处。寓言《城里的老鼠和乡下的老鼠》讲述的是:虽然城里的老鼠能享受城里的美味,但是却要时刻警觉,提心吊胆地生活,而乡下老鼠的食物虽不甚丰盛,但却能吃得安稳、踏实。在该寓言中,如果以“概述”的方式记录故事,在第一段叙述完“城里的老鼠”请客与“乡下的老鼠”“共享吃剩的鹀雀”之后应该可以由第四段衔接:“就在那饭厅门口,他们听到了一声响”,但作者对“晚宴”的描写足足占据两段,“在土耳其的地毯上,……这真是惬意的盛宴”[3]16。这两段描述性内容放慢了叙述节奏,却让读者产生了身临其境之感,“晚宴”氛围的渲染也为后来“晚宴被打扰和破坏”埋下了伏笔,让人体会到强烈的落差感,感受的一“起”一“落”,“对这种提心吊胆的享受再美也不渴望”的体会显得更加深刻。这里的“停顿”不仅没有破坏叙述的流畅性,还提升了文本的艺术价值。在《老人和驴子》中,准备投敌的驴子“在那儿蹭蹭擦擦又满地打滚,在那儿蹦蹦跳跳又唱歌吃草”[3]183,这一处驴子的滑稽表演看似无关故事主干情节,却让后来“主人走了而驴不走”的发生显得十分自然。这一描写还增添了文本的趣味性,让读者对“驴子”所象征的那一类人感到可笑。
除了善用“停顿”,拉封丹寓言叙事的另一重大突破,是对“场景”的大量使用。“场景”可以认为是文本中戏剧性的演绎,是将舞台搬到书面上,而其中对话体就是热奈特所认为的“等时叙述”的文本形式。“等时叙述”的价值在于还原故事的原貌,给读者真实感。对话体在寓言中的表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将寓言置于对话内容中,在下一层的叙述中展现,这一模式在中国先秦寓言中出现较多,比如在庄子寓言里,很多寓言都是通过庄子本人之口,或者是文中人物间的交流来道出。另一种对话体则是让寓言故事中的主人公来实现,用“场景”增加寓言的真实感。在拉氏寓言中,“场景”更像是舞台表演,表现力和戏剧性都被强化,《寓言集》中有主人公对话的寓言所占比例较大。热奈特认为,在传统叙事领域,“概述”和“场景”常常是相对立的,用轴线条叙述的常常不是故事重点,而以“场景”表现的一般都是故事矛盾的焦点所在。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强化寓言故事中的矛盾,从而暗示出寓言所蕴含的哲理。拉封丹寓言中的动物们都是善于运用语言的精灵,在《寓言集》中,以你来我往的对话推动情节发展、展现矛盾焦点的故事很多,如,寓言《狼和小羊》[3]18中的对话就展现了拉封丹舞台设计精彩的一面。强者与弱者的对话首先展现了二者截然不同的性格,其次,通过“狼”的话语,道出了强者惯用的“强盗逻辑”,而“羊”的一再示弱将故事情节不断向前推进,“狼”吃“羊”的结局就变得顺理成章。这则寓言中,三分之二的篇幅为对话,“概述”部分相对较短。这样的设计非但没有削弱寓意的力度,反而使得读者对故事的理解更加容易,体会更加真切。寓言《两位医生》一共十行,前七行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并给出了寓意“庸医误人”,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文本,而是通过最后二人的话语进行了一番调侃:“一个说‘我早就料到他的死亡。’一个说:‘信了我,他还在世上。’”[3]156这两句话并没有在功能文本中显得多余,它增强了文本的趣味感,拓展了读者的思考空间。由此可见,拉封丹叙述中“场景”的运用让寓言显得更有立体感,更加生动。
对“时距”的灵活使用就如同不断变化的音乐节拍,让文本显得鲜活、立体,拉封丹像音乐家一样,在如此短小的故事中,通过对“概述”、“省略”、“停顿”和“场景”叙事手法的来回转换给读者演奏出一首首动听的小曲,让读者不会在阅读中感到乏味,并在轻松愉快中领悟寓意。
二、“语态”的变化
“语态”( voix)在叙事学中也被称为“叙事视角”,该术语以及热奈特提出的另一叙事概念“语式”( mode)都是借用语法中的术语,“语态”一词是语法中为了分析文本的“施动者”和“受动者”,而在叙事学中是分析叙述主体和叙述对象的问题。传统寓言叙述一般采用“全知视角”,“叙述者”较少参与文本。总体上看,在《寓言集》中,拉封丹沿袭了全知叙述视角的叙述传统,但具体到语篇中,作者并不满足于仅仅在故事外“俯视”,以第一人称身份介入叙述的情况时常出现,不仅强调寓言由“我”引出,还不时将“我”对于故事的思考和盘托出。“可以说,在可信度上,全知模式给叙述者提供了大于任何其他叙述模式的活动空间,叙述者既可以选择享受以常规惯例为基础的绝对可信性(这是任何第一人称叙述者都无法达到的),又可以为了某种目的,将自己从上帝般的权威位置下降到人物或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位置上(这是其他第三人称叙述者难以办到的)。”[2]235拉封丹很好地把握了全知叙述中的这种相对优势,十分娴熟地运用变化的视角,常常给人以出其不意的感受。
按照热奈特叙事层次和叙事人称进行分类,笔者把寓言的叙事模型归为外故事叙事层—异故事叙述者( Extra-hétérodiégétique)②根据在不同叙述层次所产生的叙述行为,热奈特将叙述者的地位界定为四类:外故事叙事层-异故事叙述者( extra-hétérodiégétique),外故事叙事层-同故事叙述者( extra-homodiégétique),内故事叙事层-异故事叙叙者( intra-hétérodiégétique),内故事叙事层-同故事叙述者( intra-homodiégétique)。,可以认为这是寓言的常态,但并不是所有寓言都遵循这一规律,寓言故事也可以是以作者本人亲身经历的事件为叙述内容,或者是由故事内某一人物通过第二层叙述道出的故事的同故事叙述者( homodiégétique)或内故事叙事层( intradiégétique)的情况。这一现象在东方寓言中出现较多,苏东坡笔下的寓言常常是发生在叙述者身上的事情;而庄子的寓言多是通过与人的对话道出,这些叙事方法反映出东方寓言欲烘托寓意的客观性的特点。而拉封丹寓言基本沿袭了古希腊时期的寓言创作传统,动物寓言居多,故事的主人公都以第三人称出现,虽然叙述者位于所叙述故事外层,但叙述者得以经常参与到叙述过程中,比如,在寓言《猫和老耗子》的开头,“我读过某些作家写的寓言”[3]93,而在寓言《大山分娩》的结尾“我每想到它的时候,便想起有一位作家”[3]153,甚至还有和“叙述对象”的直接沟通“不论你怎样努力,也总是无法改变”[3]66。叙述者的多次出现虽然无法让人们将其身份界定为同故事叙述者,但是叙述者身份的强化对于寓言却意义重大。热奈特认为叙述者参与或不参与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问题,“不参与”较容易界定,而“参与”的情况常常需要细分,把握其度,热奈特所划分的五类叙述者的功能让人们更为清晰地看到了《寓言集》中叙事者“参与”的技巧性。
第一个和第二个功能分别是讲述故事和设计、编排故事结构的功能。作者借叙述者之口设计和讲述故事,这也是叙述者最为基本的功能。《寓言集》中的叙述者所设计故事的特征笔者前面已经谈论过,而拉封丹似乎不仅仅需要一个个巧妙编织的故事,还时常强化叙述者在寓言中的存在性,如在寓言《酒鬼和老婆》中,叙述者开篇就说:“每个人的缺点时时会暴露,羞辱和害怕没法使之消除。关于这一点,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我讲的一切,都有例子支持。”[3]78强调是“我”设计和讲述了这则寓言故事是拉封丹常用的方法之一,它给人一种“叙述者就是圣人、智者”的感觉,意图增强读者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它不同于善于以第三人称将故事以客观真理的方式呈现的传统寓言,这种将道德训诫溶于富有趣味性故事的寓言,强调叙述者的地位不仅能增强阅读者的兴趣,还可以调动阅读者的情绪。第三个功能是与叙述对象的沟通。拉封丹寓言中叙述者的强化,使得沟通都是以最为直接的方式进行。叙述者是善于沟通的“智者”,时刻让叙述对象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强调文本的交流性与沟通性。在寓言《掉在井里的占星家》中,这种在叙述者和叙述对象之间的交流让人感觉到自然、真切,“不用引申,这意外事本身,对多数的人,可以作为教训。我们生活于世的人们中,很少有谁不喜欢听一种论点……”[3]53。而在《狮子和蚊子》中,叙述者邀请大家一同来总结寓意:“这件事能给我们什么教训?”[3]47这种对话式的沟通方式有书信体作品的特征,读者不会感到是“道德卫士”在说教。此外,“情感”功能和热奈特提到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拉氏寓言中主要体现在叙述者主观感受的介入。首先是通过叙述者的旁白,强调其对某一类人或事物的好恶,在《农夫、狗和狐狸》中,“狼和狐狸全都是非常可怕的邻居……”[3]437其次,叙述者常常还对整个寓言故事表达出明确的情感倾向,并以第一人称给读者忠告,在《出售智慧的狂人》中提到:“别走近狂人身旁而跟他距离不远,我不能给你一句更加明智的忠言。”[3]353在叙述中,是应该保持中立、客观,还是彰显其倾向性是寓言家自己的选择,拉封丹属于后者,从不对“主观感受”加以隐藏,在不同的语篇中体现叙述者的立场情感,让寓言更具生命力。
三、作者的“实”与“虚”
“从叙述文本出发,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所叙述的故事内容,还可以了解叙述的行为。”[4]拉封丹的寓言为谁而写,或者说寓言的“叙述对象”是谁?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文本之中。从多次用到的“致辞”来看,作品的叙述行为至少存在两个层次,寓言故事的叙述者不论是否以“第一人称”介入文本,都不等于撰写其“致辞”的人,可以认为“致辞者”的表述实际上是作者本人的声音,它位于高于故事叙述者的叙述层。拉封丹的“致辞”属于热奈特在的《广义文本之导论》中提出了“副文本”。热奈特认为“副文本”有丰富和延长文本的功能,并将之比喻为“门槛”、“前厅”,是通达正文必不可少的途径。在拉封丹的《寓言集》中开篇就明确提到:“致太子殿下”。看起来,整部作品是为太子而创作,使作品有了庄严的色彩。不过,在单独的语篇中,也有为某些权贵度身定做的寓言,作者时常也会更为明确地将寓言献给不同身份的叙述对象。在《磨坊主附子和驴子》开头就提到,“致德·莫克洛瓦先生”[3]66,在《多情的狮子》中,叙述对象是“德·塞维涅小姐”[3]97,而在《寓言之力》中,则用了“恭呈德·巴里雍先生”[3]271来表现寓言创作的初衷。拉封丹的叙述对象可以是王储,是公爵,也可以是宫廷里听其吟诵的贵族们。必须承认,受到宫廷贵族支助的文人在创作上多少会体现出“献媚”的一面,不过,叙述对象的确立并不是为了排斥其他的读者群体,叙述对象的明晰化能让读者更好地定位寓言,并归化寓意。从另一方面看,叙述对象和读者的明显分离使得读者也不再被安排坐在规定的“读者席”上,受教于作者,而是站在有一定距离感的位置来观察并思考,这一变化给了读者更多的自由,对寓意的接受不是被动的、受强制的,而是主动的、有选择性的,这也与整部《寓言集》“寓教于乐”的创作风格不谋而合。
寓言故事中叙述者的思考是否和“致辞”发起人的立场具有一致性?寓意常常是站在哲学高度上的思考,拉封丹是哲学家吗?在批评家香佛尔看来,拉封丹从来不把自己当成是哲学家,甚至害怕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觉。通过归纳,不难发现在不同寓言文本中的寓意所隐射的哲学思想相互之间会有共鸣,也存在差异。而如果将这些哲理性的“寓意”和拉封丹本人的实际生活态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更多明显的不同。由此可见,与“致辞”体现作者真实身份相比,在寓言内部所展示的是一个虚构的、预设立场的“叙述者”。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还原出一个完全不同于作者本人的“隐含作者”,在韦恩·布斯看来,“隐含作者”是作者在文本中所展示的“第二自我”。在《寓言集》中,拉封丹是对能体现不同哲学思想和主张的寓意的展示者,而不是捍卫者,批评界一般可以将其寓意总结为伽森狄主义、伊壁鸠鲁主义以及蒙田学派这三个哲学流派的思想体现。因此,通过每一篇寓言所各自还原出的“隐含作者”的观点并不能汇聚成一个统一的属于拉封丹本人的立场,在这一点上,他区别于很多自身是哲学家,并希望让寓言成为所代表的哲学思想载体的寓言家。拉封丹并未向读者“推销”哲理,而是让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在文集中形成复调共鸣。用热奈特的话说,拉封丹实际上是在“假想叙述者的立场和思考角度”。而从读者的体验角度来看,“寓意”本身是否是作者的思想直接体现并不是阅读的关键,能感受到代表各种不同思想的“寓意”相互交织才更令人着迷!
从总体上看,作者通过在文中的第一人称“虚”、“实”相辅的展现方式,让作品既体现清晰的创作意图,又不会轻易地被固定的思想倾向所束缚;作者既显形又隐匿于文本中。《寓言集》的创作在彰显目的性和功能性的同时,成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辩难场。
热奈特在20世纪提出的叙事理论为更好地进行文本解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而用该理论研究寓言这一功能型文本具有特殊意义。数百年来,为何拉封丹的《寓言集》能成为寓言史上的经典,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拉封丹不愿意让故事沦为寓意的奴隶,拒绝缺少美学价值的单调叙述,要让寓言读者体会到只有小说中才具备的多变叙述方法;而另一方面,拉封丹从不陷入某个哲学阵营,把寓言固化为某个哲学流派或思想的表层话语,他选择了不固定的“叙述者”身份,让观点与思想相互碰撞、相互辩难。巧妙的叙述手法还让“文本—寓意”的单一指向发生了改变,读者寓意习得的思路被打开,寓意的获得不再被烙上“道德训诫”之名,文本的价值也就不再随时间的流逝消散。叙事理论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拉式寓言的魅力所在,也向人们解释了拉封丹为何能在文学大师辈出的法国文坛占得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伊索.伊索寓言[M].李长山,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 63.
[2]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拉封丹.拉封丹寓言全集[M].钱春绮,黄果炘,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4]GENETTE Gérard.Figure III[M].Paris: Seuil,1972: 73.
[责任编辑:吴晓珉]
O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La Fontaine’s Fables from the Angle of Narratology
WANG Jia,DING Ya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Adopting the narrative theory of Gérard Genette,the critic in the 20th century,this paper analyses such narrative strategies as“durée”and“voix”in the fables of La Fontaine and delves into their values to the fable.On the one hand,different“durées”,in the narration of the fables,make the narrative rhythm continually change,extending the contents of fable stories,enhancing the readability of the text and enriching their implied meanings.On the other hand,the distinctive narrative“voix”in La Fontaine’s fables establishes a kind of direct dialogue channel different from the author and the reader,which strengthens the narrator's identity,thus further exerting his functions of plot compi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narrative objects.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uthorship of La Fontaine and his identity as a narrator makes it unnecessary for the readers to establish an inevitable connection between morals and the philosophical standpoint of the author himself,which helps the readers acquire a wider space for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makes the generation of morals more open.
Key words:fable; La Fontaine; narratology
[中图分类号]I 1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6) 02-0105-05
[收稿日期]2016-01-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5YJC752034)
[作者简介]王佳( 1981-),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法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