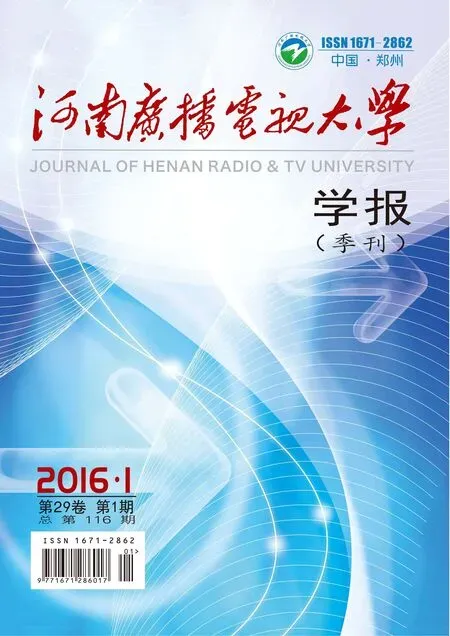《人面桃花》叙事空白研究
安忆萱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人面桃花》叙事空白研究
安忆萱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110034)
《人面桃花》作为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江南三部曲”的先声,以叙事空白的艺术技巧建构起革命与乌托邦交织的历史想象。在绣阁到民间的叙事断裂中,给予读者巨大的阐释空间。同时,格非又试图对读者的阐释进行规囿,以“伴随文本”揭示小说的叙事隐秘,以反抗传统的先锋精神为根底,实现了叙事空白技巧的进步,表现出对于文学高地的坚守以及面对中西文学艺术冲突时的犹疑。
《人面桃花》;格非;叙事空白
沉寂十年之久的格非于2004年推出长篇小说《人面桃花》,而后的十年,格非以“江南三部曲”获得了当代文坛的肯定。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阎晶明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细腻的叙事”“循环如春秋的结构”,给予了格非作品最高的文学殊荣。《人面桃花》作为“江南三部曲”的先声,以20世纪初的中国为背景,建构起革命与乌托邦交织的历史想象。作为具有先锋性质的长篇小说,格非在作品中始终坚持着后现代叙事策略,依赖内在的统一与感觉的和谐,打破故事的完整结构,制造文本裂缝,留下大量叙事空白。
涂年根在《策略性叙事空白研究》中指出:“叙事空白是故事时间大于0,文本篇幅等于0的叙事现象。”[1]叙事空白是作者基于种种原因的有意为之,如顺应主题压力、遮蔽负面影响,凸显事件意义等。叙事空白的出现使得文学作品成为“断臂的维纳斯”,以“不写”达到“隐而愈显”的美学效果。《人面桃花》中叙事空白的出现一方面凸显了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主题,另一方面也使文学回归了艺术之美。
一、绣阁到民间的叙事断裂
《人面桃花》以主人公陆秀米的成长经历为线索,通过其懵懂、躁动、蜕变、成熟、凋零的思想转变,勾勒出知识分子由蒙昧、开化、转型、革命到失败的悲剧命运。全书共分四章,章章如迷雾般铺散开来。第一章“六指”,旨在叙述秀米的绣阁故事,以秀米的生理困惑为开端,巧妙暗示出“变化”的意味。同时,作者不失时机地将张季元带入绣阁生活,并为张季元设置了多情男人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作为多情男人的张季元,始终以秀米的母亲芸儿为遮挡,倾心秀米,然而这一身份对秀米的影响仅仅局限于情感的萌动。而张季元的知识分子身份对秀米的革命历程则影响颇深。作为秀米的革命导师,张季元推动了秀米的成长,促成了秀米知识分子新身份的形成。需要指出的是,张季元的日记在这里作为被遮蔽的文本直到秀米走出绣阁才得到揭露,因此张季元的二重身份在秀米的绣阁生活中仅仅起到暗示作用。处于绣阁的秀米始终是混沌而朦胧的,如何消解生活中的困惑,是否能够踏上革命之路始终是未知的。第一章以张季元的死做结,似乎暗含了秀米接替张季元革命理想的必然命运。值得注意的是,秀米的知识分子道路在这里处于禁锢在绣阁的初始阶段。
“花家舍”作为秀米脱离家庭氤氲的转折点,以其沆瀣匪气与桃源梦境的极端矛盾冲击着秀米原有的价值理念。尽管第二章的叙事时间已是三年后,却并未因时间的久远与上文发生断裂。第二章的花家舍故事很大程度上源于第一章所铺垫的秀米与张季元潜在的情感纠葛。在“花家舍”以匪首们的欲望展开叙述时,秀米也因着匪首们的明争暗斗而走上知识分子的开化阶段。作为与秀米的成长息息相关的提点人韩六,格非似乎有着自己的犹疑。一方面,格非肯定着韩六对秀米人生道路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却又对韩六进行了叙事上的遮蔽——韩六从何而来?韩六的金蝉从何而来?韩六去向何处?当秀米问及韩六身世之时,韩六默然,而后道:“我的事,以后再慢慢说与你听罢。”[2]然而文本此后再未提及。韩六的来去被蒙上了与其身份设定(尼姑)相符合的虚妄之意。在这里叙事出现了空白点。如果说韩六身上的空白姑且可以认为是作者的无心之失,第二章“花家舍”与第三章“小东西”之间明显乃至突兀的空白却绝非如此。当秀米再次出现在普济之时,已经被新的身份“校长”所取代。“秀米”渐渐退居幕后,“校长”浮出水面,甚至完全解构了少女的存在痕迹,校长忧戚而悲哀,恍惚而冰冷。由“秀米”到“校长”的转变不仅是少女到革命者的蜕变,也是被启蒙的知识分子到知识分子启蒙者的重大身份更替。然而对于这一关键的蜕变阶段的叙述在小说中是缺失的:“校长”这一身份如何获得?如何形成?花家舍故事与“校长”归来之间的时间距离是显而易见的,这一距离包含了什么?更大的叙事空白由此而成。第四章禁语则承袭上文情节,自然流畅,而小说结尾秀米将死之时所见景象,又提示了关于父亲的叙事空白的存在。在叙事空白点之外,绣阁到民间的断裂指向知识分子成长过程中蜕变阶段的缺失。
二、阐释的自由与规囿
波兰著名美学家罗曼·英加登在文本研究中将文本分成若干层面,指出了结构中存在的空白点(叙事空白),并要求读者以自身的经验与想象对其进行填补。叙事空白的出现“呼唤”着读者与作者合作,共同完成作品,实现作者与读者隐性的互动交流。格非在《人面桃花》中蓄意为之,将主人公由绣阁到民间的转型阶段遮蔽,隐去了知识分子成长道路中蜕变的关键一环,将最重要的叙事交给读者,实现了文本建构的多元化。在花家舍的大火中,秀米实现了少女的成长,而后“校长的身影从黑漆漆的屏风后面闪了出来”[2],看似突兀的叙事断裂中,不难发现作者为这段缺失的过程其实明确交代了时间和地点——两年,日本,由此读者便可在时空的圈定中展开想象。两年的时间中秀米经历了两种转变:由女人而为“母亲”,由被动的跟随者到主动的领导者。前者的变化由“小东西”这一角色进行支撑,秀米的母性是否始终是隐藏的?秀米对待小东西的态度有何变化?当母亲这一新身份形成时,秀米与此前有何异同?“母亲”给予读者的想象无疑是巨大的。如果说前者是身体上的变化,后者则更多指向精神的升华。从绣阁到花家舍,秀米的行为始终是被动于母亲或匪首们的诱导与控制中。当秀米回归普济,已然成为主动的引导者。在日本期间,秀米经历了怎样的启蒙或冲击,便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叙事空白激发着读者的阐释空间,使读者在阅读中实现秀米形象的完善,作家即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3]以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换取最珍贵的文本反馈。
然而,格非在创作过程中又试图对读者的想象进行规囿,对某些叙事空白进行自问自答式的补充,以“伴随文本”打破时空顺序,在当下的叙事谜题中插入未来的叙事谜底。伴随文本一方面扩大了文本间性,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叙事空白的及时消解,减少了文本的模糊性。在民国革命故事之外,格非以冷静的全知视角对文本进行了重构。在这里,伴随文本主要指对历史风物、人物、事件的注解,如对历史遗迹皂龙寺的叙说,对昙花一现的人物薛举人、龙庆棠、小驴子等的生平说明,对主要人物老虎、喜鹊等的介绍,对事件的揭秘等。格非以理性的语言适时插入伴随文本,对这些风物、人物、事件的阐释不仅推进着秀米的革命进程,也隐约拆解着文本中的叙事空白。如对小驴子的介绍:“1905年策动花家舍土匪起义成功,并于翌年初春率部攻打梅城,历时二十七天,而告失败,受伤被捕。”[2]由此推知,秀米在花家舍大火后的遭遇以及东渡日本的起因。再如,对于秀米制止母亲埋葬金针地一事,众说纷纭,而真正的原因在紧随其后的伴随文本中得到了揭示:“张季元原先葬在普济村西的一大片金针地里……除了张季元的棺木外,人们还意外地发现了另外三只大木箱,撬开木箱后,里面装着的竟然全部都是枪支”[2],给予了事件确定答案。对读者阐释的规囿尽管削减了读者的创造性阅读空间,却使文本更加充实清晰,体现着格非自身对叙事的选择。
三、先锋精神的策略表征
传统叙事以“时间的连续性”和“事件前后的因果逻辑关系”为支点,走过了百年文学史。在传统文学话语场的权力关系中,作者始终被置于权力的顶层,以理性而紧密的叙事策略主导着读者的接受过程。于是,以“聆听者”出现的读者便在交流的巨大沟壑前望而却步,失去了文学创作的自主参与权。格非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以反抗传统的先锋精神制造着叙事的颠覆,打破了完整与统一的叙事成规。“他的叙事把整个存在推入疑难重重的境地,生存的历史在回忆中猝然断离,而生存的现实或者丧失了历史的依据,或者由于与历史重复而变得根本不可靠。”[4]借由高超的叙事技巧,格非实现了文本对读者的完全开放,作者与读者由主动/被动、传递/聆听的二元对立转化为协调合作的同盟。
叙事空白是格非惯用的叙事策略之一。从最初的先锋实验作品《迷舟》《褐色鸟群》《青黄》到《欲望的旗帜》,再到《人面桃花》,叙事空白始终以“不在”强调着对“在场”的关注。然而,即便是叙事手段,格非对“叙事空白”的运用也并非一成不变。《欲望的旗帜》作为格非在先锋实验阶段后,直接介入现实与人性问题的长篇小说,围绕贾兰坡教授的离奇死亡展开叙述。与《人面桃花》相同的是,作者始终执拗于知识分子叙事,借助空白策略完成文本建构。然而,这两部仅仅相隔四年的作品,在对叙事空白的处理上却表现了不同的选择。对于前者,格非将文本的缝隙聚焦于对贾兰坡之死的叙述,以内容的空白召唤读者想象。而后者,则由内容跨之结构,即绣阁到民间的结构断裂。格非引领着读者由“寻找”而为“发现”。“寻找”即是以探求空白谜题的欲望为动力,推动情节发展;“发现”却是直接呈现未解之谜,使读者在面对巨大叙事空白之余,茫然无措。另外,两部小说也出现了由线性到网状,由纵向到横向的空白策略演变。《欲望的旗帜》以空白(贾兰坡死亡之谜)为线索,自始而终,随着线性的时间流动阐释欲望主题,简洁明晰。《人面桃花》却对行云流水的故事进行截断,将大故事中错综复杂的小故事抽离,插入多个空白点,交织错落。更为重要的是,格非一改往昔空缺的直白,在《人面桃花》中将空白变得暧昧难解。不同于《欲望的旗帜》中始终提示的贾兰坡死亡原因的空白,作者对于《人面桃花》中设置的空白进行了有意忽视,将叙事空白束之高阁,阐释的重任则完全交付读者。格非在《小说叙事学研究》中指出,“优秀的作家应设法创造出自己的读者,而不是相反”。[5]格非在创作中虚设着高质量的读者,即“第二自我”,以叙事空白策略的转变对读者提出更高的阅读要求。这不仅仅是作家的自信,更是对读者的自信。
四、文学高地的坚守与犹疑
格非借由明清小说的修复与转换,运用后现代叙事手法,向传统致敬,获得了“江南三部曲”的巨大成功。《人面桃花》作为其中最具中国风格、历史神韵的小说,彰显着格非对于文学高地的坚守。在当下的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的边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声色犬马的利益诱惑中,作家对于文学创作深感力不从心。文学的清高年代一去不返,世俗乃至庸俗的文学大行其道,甚至纯文学写作而今保有的孤芳自赏之态也遭遇了无情的碾压。文学对市场的谄媚化倾向愈加明显,文学自身的泡沫化样态也愈演愈烈。在越来越多的作家实施文本染色的今天,格非作为特立独行的作家之一,可贵地保持了文学创作的本心。在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致谢词中,格非提及当下文学的娱乐化趋势时指出,“文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矫正力量……(文学)也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人心”[6]。在《人面桃花》的创作中,格非践行着他的文学信仰,以对现实的有力关注,挖掘人性本真,道出了知识分子成长道路中的尴尬与困境,以故事本身与叙事技巧的双重魅力打破了以声色换取文学市场的潜规则。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作为先锋小说的扛鼎作家之一,格非所接受的文学资源更多始于西方,尤其是对于叙事空白在内的叙事技巧的运用,可谓娴熟。西方理论与文学经典的确带给了中国文学无法企及的感召与帮助,正是在对浩如烟海的西方理论的转换与运用中,我们开辟了本国文学的新规范,实现了文学“质”的飞跃。但是,一味秉持西方理论,唯西方文学马首是瞻,难道不会导致对中国文学特色的遗忘么?答案是肯定的。中国文学自《诗经》始,渊源千年,自有其独特魅力所在,如若一味偏于西方,忘却本国艺术精华,实为文学本质精神的丧失。格非在《人面桃花》的创作中,兼具中国传统文学韵味与西方技巧追求,但对中国传统技法的应用却是浅尝辄止。在西方文学的视野中,中国文学作为“他者”存在,又常常为西方的他者所忽视,如何化解此种尴尬境地引人忧思。在对未来中国文学的瞩目中,我们期望能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作品,开拓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以中国特色对西方文化霸权与市场文学进行去魅,实现中西方文学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以“中国”文学的身份迈向世界文学,靠近世界文学,走进世界文学。
[1]涂年根.策略性叙事空白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5,(3).
[2]格非.人面桃花[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3]杨帆.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言语“空白”论[J].前沿,2004,(7).
[4]陈晓明.空缺与重复:格非的叙事策略[J].当代作家评论,1992,(5).
[5]格非.小说叙事学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6]格非.致谢词[EB/OL].凤凰文化http://culture.ifeng. com/a/20150930/44763203_0.shtml,2015-09-30.
I207.4
A
1671-2862(2016)01-0041-03
2015-10-21
安忆萱,河北保定人,辽宁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