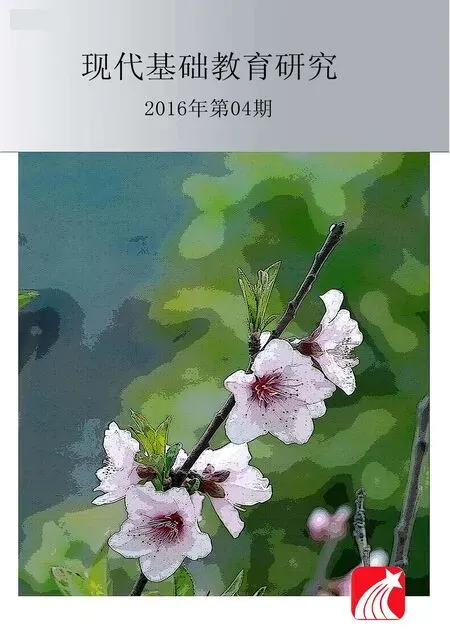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前期探索分析与后续研究建议
李志厚,黎 珍,邹颖慧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前期探索分析与后续研究建议
李志厚,黎 珍,邹颖慧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文章以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时间维度与世界、中国、地方的空间维度,作为梳理中小学综合素质评价研究文献的出发点和立场,分析了近十年来国内关于中小学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的基本状况,发现其研究成果具有“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评价指标的具体化、评价方式的质性与量性结合化、评价结果呈现多样化”等特点;但还需要进行“明确培养目标、加强评价理论对研究的指导、突出基本核心素养在评价中的权重、恰当运用评价技术、有效运作评价机制”等方面的探索。文章尝试从“评价体系的思想基础、评价内容的构建、评价主体的组合、评价方式的选择和评价结果的应用”等方面,提出构建地方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思路。
中小学生综合素质;素质教育;综合素质评价;学业评价
黎 珍,湖南岳阳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邹颖慧,湖南桂阳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综合素质评价是现代教育领域研究的一个难点, 从学者们对综合素质概念的不同诠释便能知晓。笔者认为,对综合素质评价进行研究首先要了解它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社会背景。在此前提下,再在评述我国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的基础上反思其中的问题, 并且借鉴国外高校录取时所采用的综合评定成果,来完善我国综合素质评价理论及实践。
一、综合素质研究背景分析的应然思路
要深入研究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应该追本溯源以了解其发展历程,分析当下现状,并展望未来以应对新的挑战与机遇。与此同时,还要从世界格局出发,结合我国发展现状和地方特色来进一步确定研究的起点和立场。
1.传承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
(1)中国综合素质评价的历史源远流长
谈及对学生学习与发展的评价,可以追溯到古代《礼记·学记》中“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力而不返,谓之大成。”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根据目标进行每两年一次的综合素质评价。战国时期的大商人白圭将自己成功的经营谋略概括为“智、勇、仁、强”四个方面,并以此选拔自己的学生。“智”是指智力过人,通达权变;“勇”是指知进退、善决断;“仁”是指知取予之道;“强”是指具有坚韧顽强、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这也充分体现了他心中人才该具备的素质。[1]三国时期的智者、军事家诸葛亮在《将苑》一书中,从人的“志向”“应变力”“见识”“胆略”“人品”“德性”“诚信”等方面观察与评判人才,即“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究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这七个方面总结出其用人之道。[2]随着时代的变更,科举制度的兴起和发展导致了升学与出仕为主的评价目的。曾国藩在选择人才时从人的“精、气、神”几方面综合考虑,并且强调全才应德才兼备,“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陶行知的人才观体现在“国无游民,民无废才,群需可济,个性可舒”。新中国成立以后,高考仍然强调以升学为主的培养目标。在意识到应试培养目标的弊端后,1985年我国提出了素质教育改革。正是素质教育的推动,让综合素质评价逐渐成为了教育研究的一个重点。
(2)目前中国各地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研究方兴未艾
自教育部2002年底颁布《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起,综合素质评价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有十余年。尽管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存在较多未达成共识的方面,如理论上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内涵界定存在不确定性或不一致性;基础教育目标设置不够清晰、准确;教育目标、课程、教学和评价的一致性与连贯性不足;评价研究的理念或指导思想过于强调西方以测量学业成绩为主的教育目标分类或以SOLO理论为依据的考试方式科学性,从而忽略对学生整体素质发展的思想基础和相关理论的研究等。理论上的不清晰和政策上的不完善导致了综合素质评价在实践中出现流于形式、各说各话的现象。不仅这些问题亟待解决,而且《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颁布标志着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正式与高考挂钩,成为学生升学的“重要参考”[3],因此各地各学校深入开展了综合素质评价的相关研究。
(3)面向未来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构建势在必行
有了移动互联网的瞬息万变与资源整合,未来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必定有所改变。而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教育在今天培养的人要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才能显示其真正成效。因此,教育必须面向未来,即教育不仅要满足当前社会对人才的需要,而且要致力于培养未来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这就要求我们不仅以历史的和当下的视角来把握人才培养和教育测评,更需要以前瞻的、长远的战略思维来计划我国现代教育的改革。我们要在把握世界和我国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探索未来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素质的需求,并且要前瞻性地转变人才培养观念,勇于探索更好的人才培养模式。只有面向未来的教育和有预见性的人才培养,才能使我们当前的教育更好地为中国未来的腾飞做出贡献,并实现我国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前瞻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就更需要面向未来的人才评价体系的支撑。
2.世界格局,中国国情,地方特色
(1)互联网引领的世界呼唤对综合素质人才的培养
互联网主导的世界是一个高速增长、传播和迅速变化的世界,是一个动态、整体、互补和平衡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世界。在多样化、动态变化、复杂而不确定的21世纪,一个国家的发展力和竞争力不仅取决于有知识、有活力、有能力的劳动群体,还取决于是否能够为劳动群体提供学习和更新知识及技能的机会,使他们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综观各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有以下一些共性特点:一是教育目标综合化,注意培养全面多样发展的人;二是重视基础学力的提高;三是强调全球化意识的培养;四是注重道德观和价值观教育;五是强调学生个性发展。[4]如英国的中小学课程改革重心在于培养学生交流、数的处理、信息技术、共同操作、改进学习和解决问题六项基本技能以及在自我、人际关系、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价值观;日本强调培养学生参与社会和国际意识、独立思考和学习能力、掌握本质的基本内容和个性发展的环境、鼓励学校特色和标新立异。这表明为顺应世界发展的趋势,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不仅强调学生们的学术素质、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硬实力,而且非常看重学生们的软实力,如自我、人际关系和国际意识等等。这意味着未来世界需要综合素质更高的人才来促进世界发展。
(2)文明中国的复兴取决于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
当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整体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我们应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来深刻思考这些发展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同时需不懈探索教育应当如何改革和创新,才能更好地促进时代发展。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独立任务的完成。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2010年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的富强。但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面临着社会公平、环境污染、人口、社会公共秩序等多种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难题,我国需要依靠更高的文明水平。这意味着我国需要培养具备“遵守公共秩序、具有诚信品质、能够面向世界”等综合素质的公民。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将处在从“富强中国”迈向“文明中国”的过渡阶段。[5]富强中国与文明中国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富强中国需要培养大量的人力资源,而文明中国旨在培养有教养的国民。文明中国要求我们看重并培养中小学学生的综合素质,这也意味着推进综合素质评价的势在必行。
(3)地方特色本土文化传承与创新决定综合素养评价的研究重心
除了考虑世界格局和我国国情,我们还要思考由于地域差异所导致的学生素质培养的不同,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的侧重点也应随之变化。例如,自古以来,广东就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要窗口。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广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求真务实的岭南文化。因此,广东在教育目标、课程与评价改革中,就应当尊重其文化特征,在保证人的基本素质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对那些“应用型”知识、技能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予以更多的关注。比如“信息技术”“通用技术”“综合实践活动”这类课程,以及诸如数学课中的“统计”、理科各门课中的“实验”,政治课中的“经济”“法律”,语文和外语课中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等等。[6]广东特色意味着广东中小学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构建具有必要性和独特性。
二、我国中小学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的现状分析
时代的发展与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需求,推动着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的深入与完善。那么,当前中小学的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现状如何?仍存在哪些局限?这是本文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构建理想的中小学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前提。
1.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小有所成
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期刊论文中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为主题进行检索,检索到文献4148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716篇;在中国知网(CNKI)硕博学位论文中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为主题进行检索,显示有3281篇 ;在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读秀学术检索中以含有“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为书名进行检索,检索到专著约120部。基于文献整理,笔者认为目前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现状研究可基本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评价主体上逐步发展成多元主体评价,如教师评价、 同伴评价、 自我评价、 家长评价和社区评价等,个别地方还设置专门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多元主体评价不仅减轻了班主任的负担,而且也增加了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二是在评价内容上,从过去简单的“德智体美劳”逐步细化成具体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并随着时代对公民素养培养的需求而不断更新。如2015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试行)》中将从品德发展与公民素养、修习课程与学业成绩、身心健康与艺术素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等方面对学生进行评价。[7]具体化的指标更便于学校操作。
三是在评价方式上,从以往的学业成绩评分或评等级等量性评价,发展到逐步结合档案袋评价、典型行为评价等质性评价方式,让评价结果呈现得更加全面和客观。
四是在评价结果的呈现和使用上方式多元,对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经常采用几种方式来呈现:一是百分制,用0~100分来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二是评语,教师对学生进行质性评价;三是等级,直接给出等级,或以百分数转换为等级。[8]
2.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研究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
经过多年综合素质评价改革,我国中小学综合素质评价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主要表现为:实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各地的评价方案和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在中高考招生中得到初步的应用;有力地推动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有效实施;相关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尽管如此,综合素质评价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中小学教育目的或培养目标的进一步澄清、加强评价理论对评价实践的指导、突出核心素养在评价中的权重、恰当地运用评价技术、有效地运作评价机制等方面。
(1)对教育目的或培养目标的进一步澄清
《教育法》规定,我国义务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德、智、体等诸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培养目标是否能与我国的基础教育接轨,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与启示。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其著作《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提出了目标管理的“黄金法则”,即SMART原则。该原则指出,目标必须具有明确性(Specific)、可测性(Measurable)、可达性(Attainable)、相关性(Relevant)、时效性(Time-based)。
所谓明确性就是要用具体的、针对性强的语言清楚地说明要达成的行为标准。这样目标才能够上传下达给相关人员。《教育法》中所提及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目标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概念。不同的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不同的理解,如不明确说明,这一目标在传递和执行中便可能产生偏差。
所谓可测性就是指目标应该是明确的,而不是模糊的。《教育法》中提及要将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那么达到什么水平才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呢?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理想、道德、文化和纪律呢?这些都是不清楚的。根据目标的衡量标准,应该使标准制定者与评价考核者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清晰的、可测量的标尺,避免在目标设置中使用概念模糊、无法衡量的描述。不难发现,在教育目标如何改进可测性这方面,我们仍有一段路要走。
所谓可达性,即目标要能够被执行人所接受,并且能完成。因此在目标设置的过程中要坚持员工参与、上下左右沟通,使拟定的工作目标在组织及个人之间达成一致。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之评价客体的价值主体,既可以是学生本人、家长、教师、学校、组织、政府、社会等中的一个,也可以是更多甚至全部。现实生活中,综合素质的价值主体会以符合自己需要的准则,对培养目标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对综合素质进行不同界定。[14]那么在实施综合素质评价时,极有可能由于社会价值的多元合成性,而使得综合素质评价的相关评价主体没有达成一致。因此,这样的教育目标的可实现程度有待提高。
所谓目标的相关性是指实现此目标与其他目标的关联情况。如果实现了这个目标,但跟其他目标或其他方面完全不相关,或者相关度很低,那这个目标即使被达到了,意义也不大。我们的教育目标是否具有相关性呢?其余课程、教学以及评价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是否起到了引领或导向的作用呢?这些问题都有待思考。
所谓目标的时效性就是指目标是有时间效果限制的。如果目标设置具有时间限制,那么我们就会根据工作任务的权重、学习的轻重缓急,拟定完成目标项目的时间要求,定期检查项目的完成进度,及时掌握项目的进展情况,以方便对相关人员进行及时的工作指导,以及根据工作计划的异常情况及时地调整工作计划。在实际操作中,我国义务教育并没有在时间上进行明确规划,例如什么时候进行评价,不同时段的评价涉及什么内容,等等。这导致许多学校容易忽略评价目的和过程,而只在提交综合素质评价报告之前给学生一个片面且简单的评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制定的义务教育阶段培养目标还是比较模糊的。由于综合素质评价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且评价时我们是根据培养目标来确定学生是否合格,那么培养目标的模糊性也就给综合素质评价的贯彻和实施带来了困难。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上述“SMART法则”,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培养目标进行反思和改进,从而使综合素质评价更容易操作,实施更富有成效。
(2)加强评价理论对评价研究的指导
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性评价制度,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人们改变传统的评价思想,树立“立足过程,促进发展”的新的评价理念。因此,在实施综合素质评价之前,执行者和相关人员都要对其理论基础进行充分了解。笔者查阅“中国知网”中关于综合素质评价的文献得出,大部分学者认为综合素质评价理论来自于多元智能理论、全面发展理论以及权力制衡理论等。但笔者认为这些理论并不足以增进我们对综合素质评价本质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所制定的综合素质评价方案并不是直接来源于这些理论基础,而只是用相关的理论对综合素质评价进行解释。因而出现综合素质评价的内涵模糊、指标缺乏明确性等问题,从而阻碍了其上传下达和有效实施。
在《第五十六号教室的奇迹》一书中,美国小学教师雷夫将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六阶段”理论创造性地引入班级管理,并以此来引导学生的人格成长。在此书第二章,雷夫详细阐述了这套理论的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我不想惹麻烦——靠惩罚起作用;第二阶段,我想要奖赏——靠贿赂起作用;第三阶段,我想取悦于某个人——靠魅力起作用;第四阶段,我要遵守规则——靠自律起作用;第五阶段,我能体贴人——靠仁爱之心起作用;第六阶段,我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并奉行不悖——靠境界起作用。在这一案例中,我们明白雷夫的班级管理原则从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中生长出来。那么反思我国的综合素质评价与其理论基础的关系,我们却发现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可以完全诠释我国的综合素质评价。例如,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将智能分为语言、逻辑数学、空间、肢体动作、音乐、人际、内省以及自然探索等智能,而我国综合素质评价的指标几乎与这些智能的内涵与维度没有多大关系,而只是用多元智能理论的某个观点对综合素质评价进行解释。其主要是对学生的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等六个方面进行评价。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多元智能理论并不是综合素质评价的理论基础,几乎没有理论可以涵盖整个综合素质评价的内涵,因此我国综合素质评价的理论基础有所欠缺,亟待改进与创新。
(3)突出核心基本素养在评价中的权重
从以往的研究中可知,不同的研究者界定综合素质的内涵是不一致的。但是大部分学者都基本把综合素质理解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各方面素质的组合”。2014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将评价内容具体化为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五方面;[10]上海市从品德发展与公民素养、修习课程与学业成绩、身心健康与艺术素养和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四个方面来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观察以上对综合素质的阐释,不难发现,不同地方教育部门对中小学综合素质的内涵界定和核心素质并没有达成共识,甚至遗漏了自古以来我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志向、意志、群育等核心素质。中小学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指该阶段核心的、基本的、可影响的、可评定的、对其终身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整体素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提倡“尚志”思想,体现在对志向、志气和意志的推崇,如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墨子的“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只有远大的志向和坚强的意志,才能激发人的学习动力,发展人的智力,促进人的成长。[11]同时,中小学生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群体交往素质也不可忽视。荀子说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群体交往素质强调能妥善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拥有更好地沟通和协作的技能、群体观念、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等。当今科技发展迅速,学科之间的不断交叉和融合需要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因此中小学生交往与合作素养的研究,应突出这个方面。
在教育学领域中,人的发展领域可分为社会、智力、身体、情感等领域,所以应使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成为有志、有德、有智、有为和有福之人,由此确定以精神、人品、智能、行为和情感等综合素质发展领域,并为其未来设计稳定完整的评价奠定基础。
(4)恰当运用评价技术
恰当有效的综合素质评价对相关的评价技术要求较高,最突出的就是测量、评定及计分技术。我国现有综合素质评价仍然以等级评价为主,这是因为等级评价便于教师操作。但在使用等级评价的过程中,仍存在等级维度划分、指标确定、评级规定是否合理、评价标准各个等级分配的比例如何确定、评价结果是否能反映出学生之间的素质差异等争议。这意味着单一的定量评价往往省略了评价过程中丰富多样的评价信息,难以真正把握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状况和过程。此外,目前评价的主体主要是班主任。由于评价主体的个人经验、对学生情况的了解程度等不同,因而容易导致评价结果的主观性大、随意性强,这就会间接影响评价的信度和效度。相比我国,国外一些国家的学生评价技术研究已经比较先进和完善,可以借鉴。如美国大学评估学生“整体素质”的总得分也叫作美国大学录取竞争指数,其评价公式为“综合素质总分=就读的高中(0~4分)+课程难度(0~21分)+年级排名(-1~3分)+平均成绩(0~16分)+SAT成绩(6~25分)+全国荣誉学者(0~3分)+申请论文(-3~5分)+推荐信(-2~4分)+课外活动(-5~30分)+种族多元化(-3~5分)+体育活动(8~40分)+超级录取(40分)+体育教练点名( 5~10分)+家住远处(3分)+父母因素(5~8分)+多元化(3~5分)”。[12]从公式中可知学生自身、教师、家长、学习管理人员以及招生委员会都可以是评价主体,并且对评价内容、评分标准以及分数比重都界定清晰。其次,现有的综合素质评价电子平台仍存在“信息冗余与有效信息不足并存、单位数据的价值密度低、信息管理系统中价值推理算法本身的科学性有待商榷、参差不齐的系统平台增大了师生的工作量,各方面的负担较为繁重”[13]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5)有效运作评价机制
2014年底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其中强调要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建立公示、检查、申诉与复议、诚信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实践中这些制度往往流于形式,仍有不少造假的现象。这是因为造假的代价低,即惩罚追责的规定不够具体和完备,惩罚力度小。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与高利害的升学考试的良好挂钩,不仅有赖于监督机制的完善和彻底执行,还需要形成诚信的文化和合理严谨的评价制度。美国在大学招生时并没有设置独立的机制来核查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更多依赖于人们的法制意识和诚信文化,但是对造假的惩罚是相当厉害的,这就使得学生和教师在提供申请资料时不敢弄虚作假,否则后果很严重。我国应当在加强惩罚力度的同时,对广大学生、教职员工甚至全社会进行诚信教育,要真正理解综合素质评价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是真实记录学生学习和成长过程,给学生提供认识自己、改进和超越自己的重要依据。
三、地方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探索建议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思想基础
荀况在《荀子·大略》中指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其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综合素质评价方案的提出与建构同样也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把握提出综合素质评价的理论基础,有助于更深层次了解综合素质评价的合理性,进而有效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不足,推动其顺利发展。笔者提倡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式来建构中小学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
所谓“中学为体”是确定“评什么”的问题。战国时期白圭以“智”“勇”“仁”“强”的标准选拔人才,充分体现了其心中人才该具备的综合素质;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则从人的“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总结出取人之道;清代军事家、政治家曾国藩对于人才的选拔和评价注重三方面素质:志趣、朴实廉介、多条理。
由此可见,虽然三位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各自选取人才的视角都不尽相同,但对于人才综合素质的看法却何其相似,都强调志向、品德、智慧以及修为等素养。因此在建构综合素质评价维度和指标的过程中,笔者建议以中华传统人才观所强调的“志、德、智、为”素质以及现代中国人所追求的“幸福感”为“体”,旨在为我国培养能够传承历史、面向未来的有志、有德、有智、有为、有福的“五有之人”。
所谓“西学为用”便是解决“怎么评”的问题。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在其著作《智力的结构》中提出多元智能理论[14]:“人的智力由七种紧密相关但又相互独立的智力组成。”[15]多元智能理论的评价特征是以帮助被评价者为目的,以“智能公正”为评价手段,旨在为评价者提供有关智能强项和弱项的信息,并提出继续前进的方向建议。同时其认为评价的功能在于促进学生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评价的重心是学生综合素质与个体差异性的和谐发展;评价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以主体身份参与评价过程,在评价过程中不断认识自我,自我教育能力不断提高。[16]这些特征与观点反映到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上,也就是提倡多元化的评价标准、多样化的评价内容、多元化的评价主体、多样化的评价方法。因此,多元智能理论倡导的评价思想为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并指明了改革方向。
2.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综合素质评价内容的理想建构
所谓“洋为中用”,即借鉴全世界各地所进行的综合素质评价方案,来为我国中小学综合素质评价改革保驾护航。
就英国和美国的评价内容而言,其在评价内容的选择上坚持两项基本原则。首先而且非常重要的原则是可行性原则。正如英国所确定的评价内容和指标,我们所选取的评价内容也要能够在日常教学中便于学生和教师收集,能反映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特点,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还要坚持弹性原则。如在美国的综合素质评价中,其认为学生是一个整体,学生的发展应该是全面而且具有个性的。同时,学生个性和喜好的不同会导致外在表现和选择的实践活动的不一样。因此美国采用模糊评价的方式,尤其是会采取学生自评的方式来考察学生个性化的综合素质。[12]作为适应急速变化的中国,我们也急需创新性人才。这就需要淘汰或改革以往“把所有学生都培养成同一个模样”的培养和评价方式。因此我们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在界定评价内容、保证基本素质的同时,也要为培养不同学生的不同优势而具备弹性。
所谓“古为今用”,就是保留我国几千年历史所形成的人才观并据此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比如,我国传统上历来重视对学生志向、雄心、抱负、理想的培养,有立志、明志、远志、达志的教育传统,这是人发展的核心因素之一;是学生进取心、内驱力和毅力恒心的源泉;也是他们具备勇气、胆识、意志的基础。因此,作为综合素质的评价,应该把学生培养为有志之人,将其纳入中小学的教育目标;还有我国历来注重培养孩子智勇双全、德艺双馨、身心健全等均衡的品质,有重视人品、道德、仁爱、善良、诚实、友爱、助人为乐等品行的教育传统;有注重发展学生博识广闻、深谋远虑,培养孩子韬略和智慧的丰富资源;也有大量健体强身、锻炼筋骨、尚武习艺等经验,更有倡导孩子要在学业、工作、事业上有所作为,要为国家、家乡、人类、天下多做贡献的殷切期望,还有注重培养孩子生存能力、生活技能而训练他们的一技之长、多艺防身、随机应变、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本领的文化。所以把学生培养成有德、有智、健康、有为之人,也应该成为中小学阶段的教育目的。而围绕这些教育目的或培养目标所确立的中小学生综合评价的维度、精选评价的指标,设计评价的权重,可以作为评价体系研制的指导原则。
3.以师为主,以他为辅——综合素质评价主体的理想组合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因此笔者认为,在实施时应确定多元的评价主体并进行明确的分工。但是各评价主体之间并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相互合作协商,形成一个整体来成功地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此过程中,笔者提出以下原则:一是共同体原则。内伏曾将评价主体分为四类:“内部业余评价者、外部业余评价者、内部专业评价者、外部专业评价者。”[17]在综合素质评价中,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地利用资源,让“教师——内部专业评价者、家长——外部业余评价者、社会用人单位——外部专业评价者、校长和学校管理人员——内部业余评价者”形成一个评价共同体,来为综合素质评价服务。二是主导与主体原则。由于评价工作牵涉到不同的利益主体,他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会就某一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们在确定评价共同体以后,需要对不同的主体进行角色定位以及任务分配,以此形成一个“以师为主,以他为辅”的评价共同体。
所谓“以师为主”,即在学生充分发挥自主意识的基础之上,教师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做出正确评价,以起到主导的作用。而“以他为辅”,即家长和社会用人单位作为外部评价者,积极关注学生的成长,在学校以外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的顺利实施提供外部保障。校长和学校管理人员扮演督促者的角色,监督综合素质评价方案的运行,确保综合素质评价方案在全校正常开展。校外专家和高校研究人员应该相互合作,成立专门的“智囊团队”,一方面从理论上不断完善综合素质评价方案;另一方面,在实践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在参考外国先进做法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最终达到综合素质评价方案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致性。
4.持经达变,主干与分支对应——综合素质评价方式的理想选择
基于英美等发达国家综合素质评价的成功实例,我们可以总结出他们在实施综合素质评价中基本都遵循了公平公正原则、可操作原则以及具有区分度的原则;在评价工具的研制上,都遵循或坚守信度、效度、接纳度、影响度、实施成本等好的标准。因此,所谓“持经”便是在进行综合素质评价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实施细则具有客观性、公平性。依据教育评价原理,在制定评价标准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下,为使评价工作简单易行,在制定实施细则时还要坚持可操作性原则。由于评价标准最忌讳的是“一刀切”,因而在坚持“持经”的基础上,评价标准需要将不同水平的学生区分开来,即“达变”。学校教育在确立使每位学生达标的基础上,肩负着培养精英人才的任务,而且国家的长远发展离不开这些人的贡献。所以在确定评价等级时,应既能将不同素质的学生进行分类, 又能将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进行分层,这才是一个好的评价取向或方式。这样才能根据学生自身的素质特点及智能水平进行针对性的培养,以最终实现中国梦。
5.超越定势,追求成效——评价结果的恰当应用
由于我国目前仍然没有充分利用评价结果来指导教育实践,许多校长、教师、家长和学生都不太看重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却十分看重学生的学业考试成绩。因此在评价结果的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大误区,即专注于学业成效测试的分析而忽视非学业评价结果的反馈。笔者认为,综合素质评价不仅应包含学业水平测试和分析,更要超越学业评价而关注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将评价结果应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为高校招生或用人单位选拔人才提供参考信息,即体现学业水平的衡量和学历程度的评判;二是用来作为促进学生素质全面而又个性发展的标杆,即体现超越学业评价的整体素质发展程度评估。
目前,我国教育界已经开始探讨将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纳入高校招生,希望改变整个社会只看重学生分数的氛围,为培养创新性人才和培养可持续发展的人才而尽心尽力。但是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一考定终身”的局面。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从两个方面着手来打开局面:第一,通过法律保障,即进一步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使综合素质评价真正成为既能反映学生的真实发展情况,又能够使高校客观公正招生的参考制度;第二,深入研究教育评价理论,积极转变和更新原有的教育评价范式。力求从清晰合理的评价目标、适当的定量和定性结合的评价方式、内容与步骤一致的评价机制、较高的信度效度、兼顾公平合理与正面影响的评价原则、可行性和实效性俱佳的评价工具等方面来研制该评价系统。如此,综合素质评价才能真正超越学业评价,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可持续发展。
[1] 张莉红.“智勇仁强”——刘鸿生商战谋略[J].文史杂志,1997,(2):28-30.
[2] 刘卉,赵恒平.古代人才考核对我们的启示[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2): 199-201.
[3] 朱哲.综合素质评价的“怪圈”如何破解[J].人民教育,2014,(19):19.
[4] 潘光文,吉标.当前各国基础教育目标变革的特点与趋势[J].教育探索,2005,(3):23.
[5] 傅国涌.直面转型时代,中国能否走通“东亚道路”?[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6] 高凌飚.关于建设广东特色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的思考[J].广东教育(综合版),2014,(Z1):64.
[7]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Z].沪教委基〔2015〕30号.
[8] 黄志红.新课程背景下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与构想[J].课程·教材·教法,2006,(11):21.
[9] 张增远.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践的反思与对策[J]. 考试研究, 2008,(4): 16-35.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Z].教基二[2014]11号.
[11] 骆郁廷.中国古代的尚志思想及其现实价值[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3):278.
[12] 洪志忠.美国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对我国的启示[J].当代教育科学,2010,(24): 17-19.
[13] 李金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技术实现[J].考试研究,2015,(4):15.
[14] 孙庆均,杨明月.多元智能理论实践课程[J].武汉:武汉出版社,2007:12,54.
[15] 乔淑霞.浅谈发展性学生评价[J].教育探索,2010,(12):33.
[16] 邹羚.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综合实训课程评价体系的研究[J].计算机时代,2011,(1).
[17] 苏启敏. 谁来评价学校:由专业团体到共同体[J]. 中国教育学刊, 2011, (12): 58-61.
Preliminary Analysis and Following Exploration Suggestions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o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I Zhihou, LI Zhen, ZOU Yinghui
(Educatioonal Science Colleg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Based on the time dimensions of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nd the spatial dimensions of the world, China and local, this essay aims to analyze literature researches of last 10 years to explore the basic situation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hich reflects some characteristics: diversifying evaluation subjects, specifying evaluation index,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s, and diversifying evaluation results. However, further clear training objectives are needed; guidance towards research of evaluation theor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core literacy’s importance in the evaluation are supposed to be highlighted; the appropriate use of evaluation techniques and the effective functioning of evaluation mechanism are still needed to explore. On the basis of what has been mentioned above, the essay tries to construct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program 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in local, which includes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content, selec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evaluation subject and evaluation methods,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evaluation resul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quality education,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evaluation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本文系2015年广东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素质评价与实施研究”(立项编号:2015JJKGYJ028)的阶段成果之一。
李志厚,广东南海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