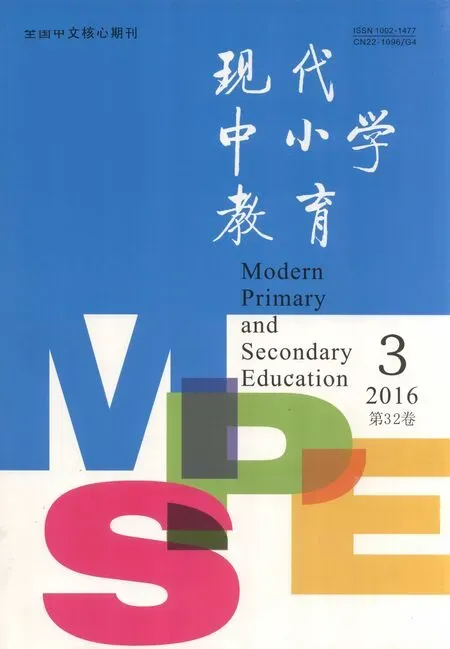对当前“语用热”的三点反思
杨 帆
(灌南高级中学,江苏 连云港 222500)
语文视角
对当前“语用热”的三点反思
杨帆
(灌南高级中学,江苏 连云港 222500)
[摘要]语言文字运用研究现已成为中小学语文教师的研究热点。但不少教师对 “语用”的理解存在偏差。其实重视语用,并不能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因为表达能力的提升主要靠思想、情感的充沛和多读多写多练。文本教学不能只偏重于语言文字形式的学习,因为文本的内容和形式言意一体,不可分割。对语言形式的零碎模仿,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传统和规律,因为提高语文教学效益的根本途径是熟读、精思、博览。
[关键词]语言文字;文本内容;语言形式
当前,语文教学中正在悄然升起一股“语用”研究热。很多教师认为,语文教学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语文教学是“言—意—言”的过程,应该“用课文来学语文,学语言文字的运用”。我觉得这种过分强调“语用”的观点有失偏颇,可能造成不少教师对语文教学理解上的混乱。
一、重视语用,能不能提高表达能力
不少教师认为,长期以来语文教学是一种“理解型”教学,以理解文本内容、思想、情感为主,很少涉及文本的言语表达方式,直接导致了学生表达能力低下。而倡导“语用型”教学,将教学重点移至对言语表达方式的分析、研究、借鉴、仿写和读写结合上来,便能促进学生语文基本技能中最核心的能力——表达能力的提升,真的是这样吗?
表达能力的提高究竟依靠什么?千百年来许多文人大家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曹丕首先提出了“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的写作规律,苏辙也说:“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上枢密韩太尉书》)他认为“文者气之所形”,这里的“气”其实就是指人的学识、眼界、胸怀等,他以孟子和司马迁两人的文章为例,说明“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上枢密韩太尉书》)就是说,孟子和司马迁的写作能力不是学来的,是因为“气”厚而自成一家,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能写好文章。刘勰认为文章由“情”而生:“情动而辞发”(《文心雕龙·知音》)“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文心雕龙·情采》)他认为写文章必须以“情、志”为本,如果语言表达不能与情、志配合,则不可能写出好的文章。
现代作家也反对一味地学习表达方式。鲁迅先生就说过:“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先生认为写作没有秘诀:“做医生的有秘方,做厨子的有秘法,开点心铺子的有秘传,……但是,作文却好像偏偏并无秘诀,假使有,每个作家一定是传给子孙的了,然而祖传的作家很少见。……”(《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致赖少麒信》)
由此可见,提高表达能力的途径其实就是两个:一是要有情感和思想,“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文心雕龙·情采》),只有情感和思想充足了,才能有表达的动机和欲望,写出来的文章才能感情真挚,语言优美;反之无病呻吟、言之无物则永远写不好文章。二是要多读、多看、多练。就像古人说的“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二),只有反复多读,使得“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其义皆若出于吾之心”,才能更好地体悟作品的情感和思想,并反过来体悟表达方式的特殊意义和运用规律。在多读、积累的基础上再多练,这样语言表达能力提升就能根茂实遂。如果把提升表达能力的希望寄托在表达方式的学习上,这显然是走反了道路。
二、文本教学,该不该偏重语言运用
文本言语表达方式的学习真的比文本内容的学习更重要吗?语文教学应该立足语言,这显然是对的。但有学者指出,语言在本质上不是“工具”,而是人的精神经验本体。语言作为一种“音义结合”的象征符号体系,与它所象征的精神内涵不可分离,所以语言在人的生活世界中体现为一个言意整体,意成于言,言即为意,言生于意,意即为言,言意一体,不可分割。[1]也就是说,语文教学中,语言所承载的认知、思想、情感等与语言表达方式紧密相融,离开了认知、思想、情感等因素,就谈不上语言运用;语言运用牢牢建立在相应的知识、认知和思维能力基础之上,所以并不能把“语言表达技能”独立出来专门培养。非要把二者区分开来的话,也是知识、思想内容决定语言表达形式,而不是相反;知识、认知、思想是语文能力的决定性因素,语言表达只是次要的附带因素。
以著名散文《我与地坛》为例,文中有一段:“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这里的句式表达很特殊,“剥蚀了……琉璃,淡褪了……朱红,坍圮了……高墙,散落了……雕栏”,貌似病句,然而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恰恰是紧紧服务于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的。只有用这种特定方式,才能表现出是地坛“主动地”褪去了琉璃、朱红等光彩,从而含蓄地写出了地坛对我的惺惺相惜和独特厚爱;在我心中,地坛就是等着我残废,为了接纳我、安慰我而存在的;特殊的句式写出了我对地坛的无比感激、亲近,写出了我与地坛之间的宿命关系。这种特定的表达方式和要表达的特定情感紧密相融,如果离开了史铁生这种特定的心理和情感,就不会存在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当然学习这种表达方式也就毫无意义。所以思想内容和语言表达紧密相依,要表达什么样的思想和情感,就会寻找与之相配的语言方式;随着思想、情感等的变化,语言表达方式必须随之而变化。所以脱离文本,脱离所要表达的特定情境、特定思想和情感,孤立地学习某种语言表达方式没有价值,这无异于舍本逐末。
三、零碎模仿,是不是符合语文教学规律
语文教学是一种选文型教学,不同选文之间的语言运用方式并无逻辑联系,那么如此零碎地对不同选文的言语形式进行学习、研究、模仿,符合语文教学规律吗?答案不言自明。
语文教学规律是什么,这可能见仁见智,但向传统语文教育学习,注重引导学生熟读、精思、博览,我想此种做法大家可能都不会反对。“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读得熟则不待解说便能自晓其义,更关键的是熟读才会逐渐形成语感,而语感是由习得语文知识向形成语文能力转变的关键,没有语感,语文学习永远事倍功半。在熟读的基础上,再辅以精思,所谓“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熟读、精思的同时,再广泛涉猎,博览群书,“观千剑则晓剑,读千赋则善赋”,通过博览,学生的视野不断开阔,语感不断增强,就能使学生达到言语理解和言语语用的高度自觉。当代的李希贵校长也认为“阅读比上语文课更有用”,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广泛阅读是语文教学的生命,比一味分析、讲授有效得多。他甚至曾极端地把每周六节语文课留四节用于阅读,只留两节用于课文教学,结果学生考得很好。所以古人虽然没有开设专门的写作课程,但在大量经典文本内容的诵读、体悟、积累中,言语表达的学习、体悟早已潜移默化,故下笔就能引经据典,洋洋洒洒。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文本知识、思想的学习和语言技能的学习其实是一个整体,思想就是语言,思想的形成就是语言的形成,思想的积累自然促进了言语表达的积累,正是丰厚的知识储备,思想储备形成了丰厚的言语储备。
而现在语文教学中,学生阅读、积累太少,长期以来,语文教学一直专注于文本的分析、讲授,课后则要求学生进行大量的题海训练,没有引导学生熟读、精思、博览,但我们并未认识到其中的弊端,认为失误在于只分析了文本内容,却没有分析文本的语言表达方式,所以现在要把着力点放在学习言语形式,这其实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参 考 文 献]
[1] 李山林.“语言”教育的歧路和“文化”教育的回归[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2):160-161.
[责任编辑:黄晓娜]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477(2016)03-0043-02
[中图分类号]G623.2
[作者简介]杨帆(1973-),男,江苏灌南人,中学高级教师,副校长,江苏省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展评一等奖,江苏省教科研先进个人,连云港市“港城名师”。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研室第11期课题(2015JK11-L125)。
[收稿日期]2015-11-15
[DOI]10.16165/j.cnki.22-1096/g4.2016.03.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