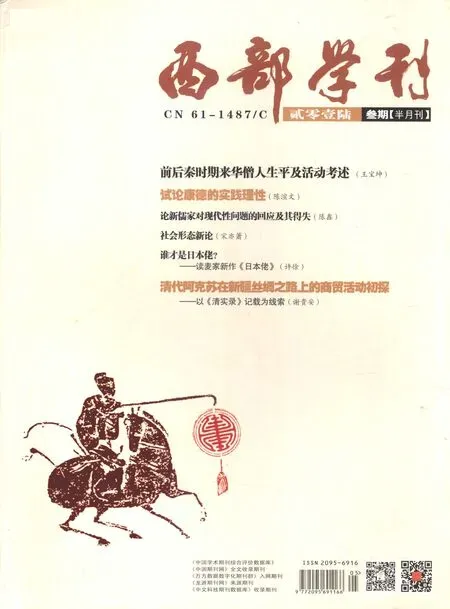前后秦时期来华僧人生平及活动考述
王宝坤
前后秦时期来华僧人生平及活动考述
王宝坤
前后秦时期的佛教发展是汉传佛教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个时期从古印度、西域地区、经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来了很多僧人,他们在汉地受到政府和僧尼道俗的礼遇,翻译、讲解佛教大小乘经论,指导汉地僧众进行禅修,特别是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等人,业绩辉煌,促进了汉地三论宗、成实宗、律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和禅宗等宗派的形成和佛教义学的繁荣,培养了大批僧界人才,极大地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佛教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前后秦时期;来华僧人;佛经翻译;讲解和禅修
前后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南北分裂、社会动乱的一个时期,南方东晋王朝偏安一隅,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各少数民族政权走马灯一样此伏彼起。但是,即便在这样动荡的社会格局中,很多少数民族政权非常重视国家文化建设,石赵王朝、苻秦王朝、姚秦王朝等最为突出。他们不仅仅重视学习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更注重学习从印度传进来的佛教文化。特别是二秦时期,从印度、西域诸国来了很多在佛教方面修养很高的僧人,他们都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在汉地僧尼道俗的配合下,他们翻译、讲解佛教经论,指导僧众禅修,培养了大批僧界人才,极大地推进了汉地佛教的发展和繁荣,也使他们传播佛法、普度众生的愿望得到了实现。本文试图以《晋书》《高僧传》《出三藏记集》等典籍为依据,将前后秦时期来华僧人群体的生平和业绩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综述其生平活动,阐释其在当代丝路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一
前秦定都于长安,公元378年,苻坚发兵襄阳,迎请佛教大师道安和海内名士习凿齿入住长安,道安早年师承佛图澄,在动乱的年代中,辗转华北、中原,在襄阳十几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僧团,在当时国内有很大的影响,道安入住长安五级寺,传播佛教,使长安形成了良好的佛教文化氛围。加之,苻坚倾心佛教,大臣赵正等崇仰佛教,促成了前秦时期长安佛教的兴盛。当时,有多位来自印度和西域地区的僧人,在长安翻译、讲解佛教经论。
僧伽跋澄 此云众现,罽宾(其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克什米尔)人,早年历寻名师,备习三藏,博览众典,特善数经,闇诵《阿毗昙毗婆沙》,贯其妙旨。于公元381年来到长安,被誉为“法匠”,苻坚秘书郎赵正,崇仰佛法,与在长安的释道安一起,请跋澄翻译《阿毗昙毗婆沙》,跋澄口诵经本,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授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授为汉语经本,于383年译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讫。
跋澄又齎《婆须蜜》梵本自随,第二年,赵正又请译出,跋澄乃与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三人共执梵本,秦沙门佛念宣译,慧嵩笔授,安公、法和共同校订。二经流传汉地。
跋澄戒德整峻,虚靖离俗。关中僧众则而象之。后不知所终。
佛图罗刹 不知何国人,德业纯粹,该览经典,久游中土,善闲汉语,他所宣译梵文,为当时所推崇。
昙摩难提 此云法喜,兜佉勒(也有译作吐火罗,地理位置相当于今阿富汗)人,龆年离俗,聪慧夙成,研讽经典,以专精致业。遍阅三藏,善《增一阿含经》。博识洽闻,靡所不综,国内远近,咸共推服。曾遍历诸国,后冒流沙东入汉地,于前秦建元中(365—384年)到达长安。难提学业既优,苻坚深见礼接。当时汉地还没有翻译四部阿含经,苻坚大臣武威太守赵正,欲请出经,值慕容冲反叛,关中大乱,赵正慕法情深,忘身为道,乃请安公等于长安城中,集义学僧,请难提译出《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还译出《毗昙心》、《三法度》等,计一百六卷。佛念传译,慧嵩笔授。自夏迄秋,绵涉两载。文字方具。后来,姚苌侵逼关中,社会动荡,难提辞还西域,不知所终。
僧伽提婆 此言众天,或云提和,本姓瞿昙氏,罽宾人,学通三藏,善《阿毗昙心》,洞其纤旨。常诵《三法度论》,以为是入道之府。为人俊朗有深鉴,仪止温恭,务在诲人。前秦建元中到达长安。宣流法化。在长安期间,曾与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共同译出《婆须蜜》二《阿含》《毗昙》《三法度》《广说》等百余万言佛典。因为慕容氏作乱,长安纷扰,所译佛典未善详悉,义旨句味,往往不尽,加之道安法师圆寂,未及改正定稿。提婆与沙门法和一同来到洛阳,不断研习讲解这些经典,四五年间,提婆汉语能力不断成熟,发现先前所翻译佛典,多有乖失,又与法和重译《阿毗昙》《广说》等众经。及后秦姚兴当政,大崇佛法,法和又返回长安,而提婆南下江南,被慧远请入庐山,以晋太元年间(376—396年),再译出《阿毗昙》《三法度》等。隆安元年(397年)来游京师建康,与江南名士、贵族、官僚交游,江南众僧聚集,请讲《阿毗昙》。后来东亭侯瑯瑘王珣集江南义学沙门慧持等四十余人,请提婆重译《中阿含经》,罽宾沙门僧伽罗叉执梵本,提婆翻为晋言。后在江南译出众经百余万言。历游华戎,备览风俗,其道化声誉,莫不闻焉。后不知所终。
僧伽罗叉 无传,罽宾沙门。未到过长安。在江南曾参与僧伽提婆翻译《中阿含经》。
昙摩耶舍 此云法明,罽宾人。少而好学,年十四为弗若多罗所知,该览经律,明悟出群。陶思八禅,游心七觉。当时人们将他比作浮头婆驮。晋隆安(397—401年)初达广州(昙摩耶舍应当是沿海上丝绸之路而来),住白沙寺,善诵《毗婆沙律》,人称之为“大毗婆沙”,时年已八十五岁,徒众85人。时有清信女张普明,咨受佛法,耶舍为说《佛生缘起》,并为译出《差摩经》一卷。
至义熙(405—418年)中,来到长安,时姚兴崇佛,深敬礼异,会有天竺沙门昙摩掘多来入关中,同气相求,宛然若旧,因共译《舍利弗阿毗昙》。后秦弘始九年(407年)初书梵书,至十六年(414年)翻译方竟,计二十二卷。太子姚泓亲管理味,沙门道标作序。
耶舍后游江南,大弘禅法,弟子众多。至宋元嘉(424—453年)中,辞还西域,不知所终。
竺法度 有传,昙摩耶舍弟子,在广州、交州一带传播小乘佛教,弟子多为尼众。
二
后秦也定都于长安,秦主姚兴崇仰佛教。公元382年,前秦王苻坚听从道安等人建议,派大将军吕光带兵去西域龟兹国迎请高僧鸠摩罗什,等吕光回转到凉州时,苻坚王朝已覆灭。吕光军队无所归属,驻扎凉州,鸠摩罗什也因而困于此地,前后达十七年。公元401年,姚兴派兵将罗什请到长安,从而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译经传法活动,随后,国内僧尼道俗纷纷慕名前来,而天竺、西域地区也不断有僧人闻名而来归投罗什问学,姚兴也早已令各关口守军对学士、求道者来往,不拘常规。学人、僧人来往不受任何限制。姚兴又设立僧官制度,以国家的名义给予给养,从而使得长安僧人云集,仅鸠摩罗什译场就有参与译事的常住僧人三五千人,形成了一个以罗什为中心的庞大僧团,僧团的形成也使得长安的佛教义学、禅学都得到了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僧才,培养出了一大批能够开坛说法的讲经法主。而罗什僧团在北方翻译佛经的同时,南方以庐山慧远为中心也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僧团,也有翻译佛经、讲经说法、问难修学等重要法事活动。南北两个僧团还有频繁的交往,国内的、海外来的僧人南来北往,当时的来华僧人除罗什外,还有几位。
弗若多罗 其汉语义是功德华,来自罽宾。少年时代就出家了,以持戒、有节操而得到当世的称扬,因勤奋诵读而备通三藏。以《十诵律》一部最为专精,成为当世宗师,有人认为他已经获得解脱的圣者果位。后秦弘始年间,振锡入关,秦主姚兴待之以上宾之礼。印度佛教的传统首先是以戒律精研著称,罗什也认为他持戒有法、堪为戒范而深感敬佩。对汉地而言,佛教经藏虽然翻译了很多,而律藏经典还未传扬开来,众僧听闻多罗对律部经典特别专精,都很渴慕获得律藏的经典的传译。在众僧的请求之下,在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中长安义学僧数百人,于长安中寺,设立译场,由多罗诵出《十诵律》的梵文经本,罗什主持翻译为汉语,翻译到全部经本的三分之二时,多罗得病去世。后来,又一为精通律藏的僧人昙摩流支来到汉地,才使这一译事得以完成。
昙摩流支 汉语意义为法乐,西域人,弃家入道,偏以律藏驰名。以弘始七年(公元405年)秋,达自关中。当初,弗若多罗诵出《十诵》,未竟而亡。长安众僧深感悲痛,而当时汉地佛教界高僧都有同感,庐山慧远也非常关注长安的佛经翻译事业,听说流支也精于毗尼,希望得到更详尽的律部典籍,就写信通好,表达愿望。说言:
佛教之兴,先行上国,自分流以来,四百余年,至于沙门德式,所阙尤多。顷西域道士弗若多罗,是罽宾人,甚讽《十诵》梵本。有罗什法师,通才博见,为之传译。《十诵》之中,文始过半,多罗早丧,中途而寝,不得究竟大业,慨恨良深。传闻仁者齎此经自随,甚欣所遇,冥运之来,岂人事而已耶。想弘道为物,感时而动,叩之有人,必情无所吝。若能为律学之徒,毕此经本,开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无上之津。参怀胜业者,日月弥朗。此则慧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愿垂怀,不乖往意一二。悉诸道人所具。[1]62
昙摩流支得到慧远的书信,又受到秦主姚兴的敦请,于是,就与罗什共译《十诵》,由于两位大师的共同努力,全部经文很快就翻译完了。他们二人又研详考核,条制审定,而罗什还是觉得译文过烦,没有达到尽善尽美。但是,不久,罗什也迁化了,还未来得及删改定稿。当时,流支住长安大寺,慧观欲请下京师,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当更行无律教处。”[1]62于是游化余方,不知所终,或云终于凉土。未详。
卑摩罗叉 意译为无垢眼,罽宾人。沈靖有志力,出家以后,按照佛教戒律的要求学习佛法,以苦修、保持节操为要务。后来学有所成,来到龟兹国,弘扬律藏,西域地区的学者、可能还有汉地的僧众,都到这里向他学习律学。这个时候,也是鸠摩罗什学习时期,约二十岁上下,罗什也向他学习律学。这样相处过二十余年,师徒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龟兹国被吕光军队攻破,罗什被掳走,卑摩罗叉也离开了龟兹,远走他方。又过了近二十余年后,听说罗什被迎请到长安翻译佛经,就感到很欣慰,想着也应当让汉地众生得到佛法律部,于是仗锡流沙,冒险东入。以后秦弘始八年(公元406年)达自关中,罗什以师礼敬待,罗叉以远遇欣然。后来罗叉一直留在长安,直到罗什迁化。罗叉最后整理了《十诵律》汉译本,为罗什的遗憾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卑摩罗叉又到江陵,在辛寺夏坐,开讲《十诵》,既通汉语,又善领纳,佛法无为妙理,被阐发于当世。长于研究佛理的僧众被吸引来了,而善于学习戒律的僧众也大大地增多了,律部典籍得到了大力弘扬,罗叉对汉地佛教的贡献也在于此。后来,道场寺的慧观法师又将罗叉所讲戒律内容概括总结为二卷本的经本,流传于江南,僧尼披习,竞相传写。当时还形成了几句谚语:卑罗鄙语,慧观才录,都人缮写。纸贵如玉。罗叉善于修德、养闲,弃喧离俗,还回到寿春石涧寺,七十七岁而卒。因为他眼睛发青,被誉称为青眼律师。
佛陀耶舍 意译觉明,罽宾人,婆罗门种族。十三岁随师出家,年十五,诵经日得二三万言,所住寺院,似乎常让他在外面作守卫,结果影响了他的诵读经典的学业。当地有一罗汉看重其聪敏,常常把乞来的食物与耶舍共用。到了十九岁,诵大小乘经达到数百万言,然而他性度简傲,颇以知见自处,说很少有人能胜任给自己来做老师,因为这样的大话,所以不能得到众僧的尊重。他威仪很美,常常谈笑风生,和他相处的人就忘掉了自己内心原来的隔阂,这样使他能够很好地和人相处。但是,他的年龄快到受戒的时间了,没有人敢于给他当受戒师,没有人来登戒坛,所以眼看快要三十岁了,还是一个沙弥身份。后来,就跟着自己的舅舅学习五明诸论,世间法术,多所练习,年二十七,才受具戒。他一直坚持以读诵为务,手不释牒。每端坐思惟经义,不觉虚过于时。他如此专精学习佛法。
后来,到了沙勒国,国王不悆,请三千僧会集一处,耶舍也被列为其中之一,当时太子达摩弗多,意为法子,看见耶舍容服端雅,问所从来,还问一些法理问题,耶舍对答清彻流利,辩才无碍,太子悦之,仍请留宫内供养,待遇隆厚。罗什当时还是一个十余岁的少年,比耶舍后到,还跟着耶舍学习,对耶舍非常敬重。耶舍与罗什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师徒之情。后来,罗什随着母亲回龟兹,耶舍非常欣赏罗什的学习领悟能力,还曾请求他留下来。沙勒国王薨后,太子即位,当时前秦王苻坚遣吕光西伐龟兹,龟兹王告急于沙勒国,向国王求救,沙勒王自率兵赴救援,使耶舍留辅太子,委以后事。救军未至,而龟兹王已败,国王回来后,就给耶舍说罗什被吕光军队掳走了,耶舍就感叹说:“我与罗什相遇虽久,未尽怀抱,其忽羁虏,相见何期。”[1]66在沙勒国又停留了十余年,就来到龟兹,由于他的传扬,龟兹国的佛教又开始兴盛起来。
当时罗什在姑藏,还曾给耶舍写信,想请老师来姑臧,从这里可以看出,可能罗什在凉州期间某些时候相对自由一些。耶舍接到罗什派人送来的书信,知道了罗什在凉州的一些情况,也打算准备一些干粮离开龟兹,去寻罗什,龟兹国人劝请挽留了耶舍。后来,耶舍还是来到了凉州,但是,罗什这时已被接到长安了。耶舍听说姚兴逼着罗什接受歌女,以好心办坏事,破坏罗什的道行,就感叹说:“罗什如好绵,何可使入荆棘林中。”罗什听说耶舍到达了凉州,立即劝姚兴迎请,当时,姚兴并没有听进去罗什的建议。后来,姚兴请罗什翻译更多的经典,罗什就说:“夫弘宣法教,宜令文义圆通,贫道虽诵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达幽致,今在姑臧,愿下诏征之,一言三祥,然后著笔,使微言不坠,取信千载也。”[1]67姚兴理解了罗什说话的意思,就派遣使者带着很重的礼品去迎请。耶舍对于重礼不予接受,就对使者笑着说:“圣上的旨意既然下来了,就应当前去效劳;但是,国王陛下似乎对待出家人过分厚道了,也不讲佛教的道理了,就像对待罗什那样,以歌女之类的待遇来威逼的话,我就不敢去了。”使者回来之后,就把这些话汇报给了姚兴,姚兴感叹其慎重,又派使者前去讲明意愿,以后再不会那样对待高僧了。这样,佛陀耶舍才来到长安。姚兴亲自出城远迎,在逍遥园别立新省,按照佛教的规矩进行四事如法供养,但耶舍并不贪著这些供养,也没有接受。每天吃饭的时间到了,耶舍会把供养来的食物分给那些身边的人,自己日中一食而已,生活很简朴,完全按照佛陀制定的戒条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当时,罗什正在翻译《十住经》,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疑难很多,以至于让罗什犹犹豫豫,无法动笔;耶舍来了之后,师徒二人已阔别三、四十年,相见非常高兴,相互配合非常默契,对经义共同讨论,逐步将一些疑难繁杂的深层义理问题阐解清楚,并宣译为汉语,译场僧众三千多人,都感到所翻译的文字非常恰当地表达了经本原义,使得这部经典得以顺利翻译。
耶舍这位高僧长相很特别,须发赤色,又对印度佛教五百罗汉所造之《大毗婆沙论》非常专精,常给人讲说这部大论,因此,大家都叫他“赤髭毗婆沙”。他还是罗什的师辈,因此又被称为“大毗婆沙”。因为姚兴及其他王室成员都来供养耶舍,衣钵卧具堆满了三间房子,而耶舍对此并没有多少兴趣。姚兴就把这些供养品变卖成资金,在城南建设一座新的寺院,送给耶舍。耶舍精通律部,诵出《昙摩德律》,司隶校尉姚爽祈请他翻译出来,姚兴却怀疑他诵出的这部经典会不会有错误呢。他就想测试一下耶舍记忆能力。就派人找来了羌族祖先传下来的治病药方古经,大约五万字。给耶舍两天的时间,请他读诵完毕,于是请他背诵,结果一字不差。大众都佩服他的超强记忆力。然后在弘始十二年翻译出《四分律》,总计四十四卷,还翻译出《长阿含经》等,当时是来自于凉州的沙门佛念宣译为汉语,道含笔受。到了弘始十五年解座,姚兴供养耶舍布绢万匹,耶舍分毫不取,道含、佛念及五百高僧皆得姚兴重儭施。耶舍后辞还外国,至罽宾得《虚空藏经》一卷,寄给商人,带回汉地,传于凉州僧众,后不知所终。
耶舍传译《四分律》,所以,此文将耶舍归入戒律僧;但耶舍还翻译《长阿含经》等。
昙摩掘多 无传,天竺僧人,曾在长安与昙摩耶舍共同翻译《舍利弗阿毗昙》二十二卷,道标作序。
佛陀跋陀罗 意译觉贤,本姓释氏,迦维罗卫人,甘露饭王之苗裔。祖父达摩提婆,意译法天,曾在北天竺经商,因而居住在这里。觉贤幼年父母先后双亡,被从祖父鸠婆利领养在自己家里,后出家度为沙弥。年十七时,与同学数人,俱以习诵为业,众人皆用一个月的时间才能背诵,而觉贤一天之内就完成了。他们的老师感叹说:“贤一日,敌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之后,修业精勤,博学群经,多所通达。觉贤年少时就以禅、律驰名,常与同学僧伽达多,共游罽宾,同处多年,达多虽敬伏觉贤的才能和智慧,但不能知道觉贤修持的境界。后来,因为觉贤已通过禅定的修持,达到解脱的果位,并常示现一些神变,才知道觉贤是位圣人,得到了不还果的果位。
觉贤常常想到各地游历去弘扬禅法,也看看各地风俗。正好这时有一位汉地的沙门智严西行求法来到罽宾地区,看到了当地佛教传播的盛况,僧众清胜,戒律精研,就非常感慨,想起自己故乡的道友、法侣不仅痛心,说:“我的那些道友们,都有宏大的志愿和求法修道的雄心,但是遇不到真正明白禅法的过来人,怎么才能学习禅法而达到开悟呢。”他在罽宾听人说:“有个叫佛陀跋陀的出家僧人,出生于天竺那呵利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学,他在童年就出家了,通解经论,少年时受业于大禅师佛大先。”早先的时候也生活在罽宾,还给智严说:“可以振维僧徒,宣受禅法者,唯有佛陀跋陀是这样一位堪当大任的人啊。”智严遂要请苦至,觉贤悲悯汉地僧人的求道真心而同意前往汉地。于是向当地众僧告别,带上干粮,向汉地进发。徒步走了三年,绵历寒暑,东度葱岭,途径六个国家,国主们都为他不畏艰辛、弘传佛法的精神所感动,纷纷提供路费和粮食等物品,使他能够顺利抵达汉地。觉贤走的路线与其他僧人不太一样,僧传中记载,他来到交趾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广东、广西一带,所以,他的行走线路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觉贤随后乘船绕着汉地的海岸线而行进,就到达了当时青州的东莱郡,可能是现在青岛地区,他上岸后,听当地的僧人说,有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现在长安,他就很高兴前往去和罗什会面。罗什深知印度佛教的博大精深,得知觉贤精通禅法,大为高兴。就在一起讨论法相等实修实证的问题,很快就把一些深层次的义理阐释清楚了,相互之间都受到道法的启迪。但是,觉贤与罗什所修学的思路、法系可能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有《长安城内齐公寺萨婆多部佛大跋陀罗师宗相承略传》一部著作的目录,从目录看,觉贤法脉,几近于后世菩提达摩所传之印度禅宗法系,但这里僧祐是按戒律师师相授的传承撰集的,因为僧祐撰集的著作早已散佚,法脉很难说清楚。其目录如“阿难罗汉第一”、“末田地罗汉第二”、“舍那婆斯罗汉第三”、“优婆崛多罗汉第四”等,只能说明戒的传承。
所以觉贤曾问过罗什:“君所出,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尔,何必能称美谈。”“不出人意”,是什么含义,可能不好确定;觉贤也博通三藏,他实际上后来到了江南,也是走了罗什以翻译佛经为主的路子,这也许是汉地众生的福缘吧。但这时,觉贤似乎不大认同罗什传译经典的做法,或许他想劝说罗什走禅观、实际修证的路子,而罗什当时年事已高,何况法务繁忙,很难去离群索居、修习禅法了。后来,罗什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经文有疑义的地方,也经常与觉贤讨论,共同确定经义。
当时,秦国太子姚泓,很想听觉贤讲解佛法,于是约请包括罗什在内的大批僧人,聚集在东宫,请觉贤讲法。佛教讲经、讲法有一整套制度,而且有印度的规矩,也有汉地的规矩,也有不同法系、法脉的要求。但是各类讲经活动都少不了道场上的互相问难,或者辩论。所以,在觉贤讲法法会上,罗什就开始与觉贤辩难,来回往复不知多少个回合了。
罗什问:法云何空。
答曰:众微成色,色无自性,故虽色常空。
又问:既以极微破色空,复云何破微。
答曰:群师或破析一微,我意不尔。
又问:微是常耶。
答曰:以一微故众微空,以众微故一微空。
当时,有一位曾经从天竺国求法回国的僧人宝云在给觉贤当翻译,他给大家翻译出这些对话后,大家很难理解其中意义。道俗听众都推断说,觉贤可能认为“微尘是常”吧。
过了几天,长安的义学僧们聚集在一起又请觉贤给予解释,觉贤说:
夫法不自生,缘会故生。缘一微故有众微,微无自性,则为空矣。宁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
以上的这些对话辩难,是当时僧人们的记录,大体的辩论内容就是围绕这些话题展开的。
秦主姚兴以全国之力,长时间地供养三千僧人,这些僧人每天都为翻译佛经、传写经本、接待来宾、往来问学、相互讨论、处理各类法务事务,忙忙碌碌的。但是,唯有觉贤在自己的僧房修习禅观,与大众不一样。有一天,他给弟子说:“我昨天在修习禅法的时候,看见我的家乡那里,有五艘船出海,要来汉地啊。”结果,他的弟子中个别人以为自己的老师修行很好,有很大的神通,就在其他僧人前夸赞,而那些年长的僧人,特别是道安僧团的弟子们,就认为这有点“显异惑众”,似乎与佛陀制定的戒律不太相符。而且,觉贤在长安的这一段时间,汉地喜欢修学禅观的僧尼道俗,闻风而来;但是修学禅法,各人根机不同,修学的发心、方式也不尽相同,一些浅薄的、或者根基不合适的人,往往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一个弟子,因修了一点点观行,就说自己得道了阿那含的果位,觉贤还未来得及去指导他的修行,这个传言就开始风行起来,结果引起大众的批评,有的僧众还认为这可能带来杀身之祸;一时流言四起,很多僧徒因没有领悟佛法甚深的妙义,没有修道的理论指导,从而引起恐慌,禅众僧徒一半天内就离散而去。而觉贤本人并不在意,但是,在长安其他僧众中间,也引起一些思想的波动,所以,为了维护长安僧众的秩序,也为了译场的稳定,当时的僧正僧略、僧人道恒就去对觉贤协商说:“根据佛经的记载,佛陀尚不随便说自己所得的修持之法;而和尚你怎能随便说一些虚妄的事情呢,最早说有五艘船从家乡出发,这本来就是没办法验证的事情;又有一些学禅观的门徒相互狂惑,互争是非,这样对于僧团的秩序、对于佛所制定的有关戒律都不相应,都有违背的地方。为了僧团的大局,你还是离开长安吧,不要再留在这里了。”觉贤说:“我身若水上的浮萍,去留不成问题;但是,我所要弘传的禅观修持方法,还没有得到大力推广,没有普度众生,这是我的遗憾。”
觉贤于是决定离开,有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愿意跟随觉贤,他们神色从容,没有表现出不满或者愤怒的样子。而长安那些了解禅观的僧众感到非常惋惜,有一千多人都来相送。
可能当时姚兴对此事还未了解清楚,等知道这样的事情之后,就对道恒说:“觉贤大沙门,是得道高僧,来游长安,准备弘扬佛陀遗教,他所学的禅法还未来得及传播,怎么能请他离开呢。再说了,不能因为个别人一句话的错误,而使广大众僧失去这样一位导师,这太让人惋惜了。”于是下敕派人前去追回。使者很快就赶上了觉贤的僧众,说明了姚兴皇帝的旨意,觉贤说:“我真诚地接受了皇帝陛下的恩旨,但是,我的去意已确定,不能遵从皇命了。”带领僧众日夜进发,南下庐山。
后来,庐山慧远法师还专门写信给秦主姚兴和关中僧众,派弟子昙邕送来关中,来化解这里发生的事情。觉贤到了江南,在庐山慧远及僧团僧众的祈请之下,觉贤翻译了禅数多部经典,还与法业、慧观等人首次翻译《华严经》六十卷,与法显等人翻译《僧祇律》,还翻译出《观佛三昧海》、《泥洹》及《修行方便论》等,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以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卒,享年七十有一岁。
从觉贤的年龄看,他在长安时期大约五十岁上下,要比罗什小十六七岁,所以,罗什说自己年老,也是常理;慧远法师可能后来专门过问此事,了解到这事情是“过由门人”,并没有明显记载说觉贤与罗什有什么不和或者矛盾。僧略、道恒乃是为了僧团大局,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行。汉地僧众对于禅观初来,没有义理的基础,出现这样的“走火入魔”现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与觉贤所传禅观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件事情,可以看做佛教史上长安盛事传奇之中的一段变奏。
关于长安翻译禅法的僧人,其实还有鸠摩罗什。僧睿在《关中出禅经序》中说自己在罗什初到长安的当月“予即以其月二十六日从受禅法”,罗什后来翻译禅法经典,是“寻蒙抄撰众家禅要,得此三卷,初四十三偈,是鸠摩罗罗陀法师所造,后二十偈,是马鸣菩萨之所造也。其中五门,是婆须蜜、僧伽罗叉、沤波崛、僧伽斯那、勒比丘、马鸣、罗陀禅要之中抄集之所出也。”所以,可见,罗什所传禅法经典不一定是按法系所传,而是从禅法中抄出可能适合于汉地僧众的修法而汇编出来的。
另外一个是昙无谶,虽然他与前后秦王朝没有关系,但他可能在后秦末期抵达凉州,先后翻译佛经多部。所以,也列在此处。
昙无谶 本中天竺人,早年曾学小乘,后随师学习《涅槃经》,专学大乘。先到龟兹,后进到姑藏,河西王沮渠蒙逊据凉土称王,素奉佛法,欲请谶翻译佛经,谶又学习三年汉语,才开始翻译《涅槃经》,沙门慧嵩、道朗深相推重。慧嵩任笔受,更请译《大集》《大云》《悲华》《地持》《优婆塞戒》《金光明》《海龙王》《菩萨戒本》等六十余万言。433年,昙无谶被蒙逊所害,时年49岁。昙无谶所译《涅槃经》为汉地首译,影响极大。
三
当然,前后秦时期业绩最为辉煌、影响最大的是鸠摩罗什法师。
鸠摩罗什 此云童寿,天竺人。这里要说明的是,罗什生于西域龟兹国,其父来自于天竺,其母为龟兹国王妹妹,按传统意义上来讲,罗什属于天竺人,但也是龟兹国人。其家族在天竺家世国相,其祖父达多,倜傥不群,名重于国。父鸠摩炎,聪明有懿节,在将要继承相位时,辞避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其放弃相位、荣华富贵,甚为仰慕。亲自出郊迎接,并请为国师。王妹年方二十,识悟明敏,体有赤黡,法生智子。诸国往聘,并不肯行。及见摩炎,心欲当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怀上罗什。罗什在胎中时,其母自觉神悟超解,有倍常日,并常到雀离大寺听闻佛法。罗什出生后不久,其母欲出家。后来,经丈夫同意,其母带着七岁的罗什一同出家。
罗什从师受经,日诵千偈。九岁时从名师槃头达多(罽宾王之从弟)学习小乘经典,受学《杂藏》《中》《长阿含》等,凡四百万言。在与外道论师的辩论中获胜。年十二,其母带他回到龟兹国,还到过沙勒国,诵《阿毗昙》,对《十门》《修智》诸品备达其妙义。还博览《四围陀》典及五明诸论,阴阳历算,尽得其妙。为性率达,不历小检。后遇莎车王子、参军王子兄弟二人,兄为须利耶跋摩,弟字须耶利苏摩,苏摩才伎绝伦,专以大乘为化,其兄及诸学者,皆共师之。罗什听其讲《阿耨达经》,明白阴界诸入皆空无相之理,遂改学大乘言:“吾昔学小乘,如人不识金,以鍮石为妙。”受诵《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等经论。至年二十,受戒于王宫,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后来,罗什母亲要去天竺,对龟兹王说“汝国寻衰,吾其去矣。”对罗什说:“方等深教,应大阐真丹,传之东土,唯尔之力。但于自身无利,其可如何。”罗什回答说:“大士之道,利彼忘躯。若必使大化流传,能洗悟矇俗,虽复身当炉镬,苦而无恨。”其母往天竺,进登二果。而罗什住新寺,披读《放光经》,广诵大乘经论,洞其秘奥。此时,罗什还以大乘之理使其小乘师槃头达多回向大乘,传为佳话。
罗什道流西域,名被东川,前秦王苻坚欣慕高名,即遣使求之。382年,苻坚派遣骁骑将军吕光等人率兵七万,西伐龟兹及乌耆诸国。苻坚对吕光说:“夫帝王应天而治,以予爱苍生为本,岂贪其他而伐之乎,正以怀道之人故也。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这段话道出了千里奔袭、出兵龟兹的真实目的。吕光随后远征龟兹,掳罗什而还,因苻坚败亡而驻军凉州,后自称王。鸠摩罗什也困于此,前后达十七年之久。401年,后秦主姚兴派兵迎请罗什到长安,在《晋书》姚兴传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姚)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睿、道坦、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罗什执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余卷。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般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①
其实,罗什在龟兹国发大愿要到汉地弘扬大乘,并没有设想要以怎样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在困于吕光军队期间十七年间无所宣化,所以,到长安后,正是“众缘和合”,由姚兴设立译场,以鸠摩罗什为译主,组织僧人进行佛典翻译,从401年至413年,据《开元释教录》考订,共译出佛经74部,384卷。其所译经目《高僧传》初步提到“屡请什于长安大寺讲说新经,续出《小品》《金刚波若》《十住》《法华》《维摩》《思益》《首楞严》《持世》《佛藏》《菩萨藏》《遗教》《菩提无行》《呵欲》《自在王》《因缘观》《小无量寿》《新贤劫》《禅经》《禅法要》《禅要解》《弥勒成佛》《弥勒下生》《十诵律》《十诵戒本》《菩萨戒本》《释论》《成实》《十住》《中》《百》《十二门论》,凡三百余卷。”[1]52
鸠摩罗什所译佛经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遗教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以及《大》《小品般若经》等,广为流传,一直是中国古代和现代僧侣阶层和广大佛教信众的必读典籍,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另外,除了像佛陀耶舍、佛陀跋陀罗、卑摩罗叉、弗若多罗、昙摩流支、昙摩掘多、昙摩耶舍等这些知名的僧人,从天竺、西域地区远道而来的外国僧人是很多的。罗什二十岁时在龟兹国王宫受戒之后,一直在西域地区多个国家讲经说法,诸多国王在讲经时“皆长跪座侧,令什践而登焉。”吕光军队掳走罗什,僧传没有记载罗什有没有随行僧侣,但根据罗什在西域地区的影响力,可以推断,一定有一些外国弟子舍命跟随,或者,在罗什被迎请到长安后,不远千里追踪而来,这虽然没有直接的资料依据,但这在情理之中。所以,罗什在感觉四大不适时,“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因为这些外国弟子可能对汉语不大通晓,或者谨守师教,规规矩矩,印度佛教传统戒律森严,师师相承,一丝一毫也不能紊乱,所以,除了做份内的事情以外,不与世务,这也可能是他们的姓名、活动、日常生活等被整个僧团“忽略不计”的原因,因而在僧传中几乎没有被提到。
佛陀跋陀罗其实也是一个僧团,与罗什僧团有很大的交叉。僧猛等人就追随佛陀跋陀罗学禅法。而姚兴在为罗什设立国立译场的同时,还为佛陀跋陀罗、卑摩罗叉、昙摩耶舍、昙摩掘多等另外设立译场翻译其它经典。如释道标《舍利弗阿毗昙序》中言:“惟秦天王(指姚兴)冲姿睿圣,冥根树于既往,实相结于皇极……会天竺沙门昙摩掘多、昙摩耶舍等义学来游,秦王既契宿心,相与辩明经理。起清言于名教之域,散众微于自无之境……于是诏令传译。”两位高僧在翻译时因“经趣微远”,而迟迟不能落笔,至弘始十六年,“经师渐闲秦语,令自宣译。”所以,僧肇给刘遗民的书信中曾谈及长安佛经翻译盛事时曾言:
什师于大寺出新至诸经,法藏渊旷,日有异闻。禅师于瓦官寺教习禅道,门徒数百,日夜匪懈,邕邕肃肃,致自欣乐,三藏法师于中寺出《律部》,本末精悉,若覩初制。毗婆沙法师于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毗昙》梵本,虽未及译,时问中事,发言新奇。贫道一生猥参嘉运,遇兹盛化,自恨不覩释迦泥洹之集,余复何恨。[1]250
什师即鸠摩罗什,禅师指佛陀跋陀罗,三藏法师指卑摩罗叉,毗婆沙法师指佛陀耶舍,这实际上是僧肇描述的长安佛教的盛事,当时是几个中心,当然,以鸠摩罗什的译场为最盛。
罗什僧团主要以佛经翻译为主,第一,罗什僧团获得了后秦王室、国家政府的倾力支持;第二,国主姚兴的亲自下诏确立国家僧官制度,僧正、悦众、僧录等官员由德高望重的僧人担任,国家按“侍中”等职务给予待遇,从而使僧团的活动与管理有了制度保障;第三,译场也有相应的翻译制度,有译主、宣译、辨义、笔受、参正、校正、传写等职务(由程序形成职务,后代发展更为完善)的分工,使翻译工作秩序井然;第三,僧团僧人来源于国外、国内的都有,往往以外国僧人作为译主、汉地僧人协助翻译的形式为普遍;第四,当时长安并非罗什一地译场,除长安大寺以外,还有中寺、石羊寺等其他寺院也同时开设佛经翻译场所,僧肇就曾经参加过长安不同的译场,如僧肇参加鸠摩罗什译场,翻译《百论》等佛典,还参加由姚兴亲自指定司隶校尉晋公姚爽任以法事、请罽宾沙门佛陀耶舍为译主的译场,在弘始十五年出《长阿含经》,僧肇为两个译场所翻译的佛典都作过序文。最后,鸠摩罗什僧团在中国佛教史上可能是人数最多、持续时间相对较长、翻译佛典又较多的几大译场之一,鸠摩罗什也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伟大的四位翻译家之一,其余三位是玄奘、义净和不空,也有史家认为,竺法护、真谛等也应作为大译经家。
结语
前后秦时期是一个战乱的时代,但是,从上文所罗列资料来看,很多来华僧人都能够从事佛经翻译、讲解的活动,有的还能够带领僧众进行禅修,培养出了大批汉地僧才,推进了中国古代佛教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繁荣。这些来华僧人所译经论大部分都被保存下来,特别是鸠摩罗什所译的经论如《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佛说维摩诘经》《阿弥陀经》《佛说遗教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典籍,一直在后世广泛流传,对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前后秦时期,几乎所有来华僧人都是沿着丝绸之路而来到汉地的,一路上他们传译佛教经论、弘扬佛法,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促进了中华民族与西域地区、印度地区以及中亚、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个别僧人最后又回到印度,也带回去了汉民族的文化,他们对古代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前后秦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各民族生活习俗、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差异,但是,佛教的传入和传播,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思想上、信仰上的交流和融合,弥合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种种隔阂和差异,加速了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和北方多民族融和的进程。
前后秦时期,来华僧人特别是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等人大量翻译佛教大乘典籍,促进了汉地佛教各宗派的形成,促进了汉地佛教义学的繁荣,推进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因佛教的传入,思想界开始整合了魏晋以来玄学的讨论热潮,在一个新的思想高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鼎立格局的形成。
总之,前后秦时期来华僧人的种种业绩,促进了汉地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良性的发展,也对中古时期思想界的整合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今天,我国政府提出发展“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涉及到很多的国家和地区,这是一项世界范围的宏大发展构想,这些地区恰恰是多种民族、多种宗教和不同文化类型的复杂区域,如何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而实现和平的、和谐的发展理念,就是摆在我们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所以,研究、借鉴和继承前后秦时期佛教文化传播、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一历史遗产,对我们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战略有多方面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晋书》卷一百十七,第2984页。
[1](梁)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
(责任编辑:杨立民)
B949
A
CN61-1487-(2016)03-0005-07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前、后秦佛教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2XZJ005)。
王宝坤,男,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谈谈徐兆寿长篇小说《鸠摩罗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