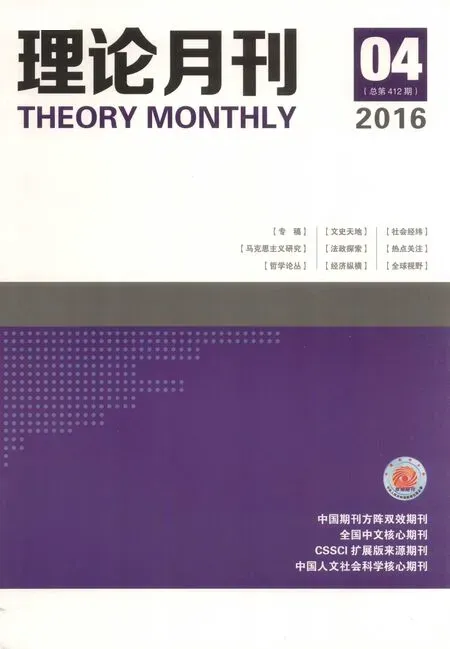美国经济法域外性问题的理论演变及评述
□刘艳娜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
美国经济法域外性问题的理论演变及评述
□刘艳娜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
[摘要]经济法的域外效力问题,如果法律本身没有规定,美国的传统做法是法院通过解释立法者的立法目的确定经济法是否具有域外效力。20世纪初期,对立法目的的解释建立在保守的地域性的主权概念基础上,其结果是经济法没有域外效力或者是美国经济法防御性地在适用于美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20世纪中期,美国法院对立法目的的解释在地域的基础上又考虑了实体主义因素,减少了一些经济法域外执行的情况。20世纪末期之后,美国放弃地域联系,实体主义开始在经济法的域外性问题上占据统治地位,积极对外推行美国的经济法的域外适用。对于经济法的域外适用,应该采用国际法的视角解释经济法的效力范围并将地域因素重新纳入解释的过程。
[关键词]经济法;域外性;法律解释;主权;实体主义方法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4.030
根据传统的国际私法,经济法由于自身的公法性质而不具有域外效力。自20世纪初起,美国在经济法域外效力问题上的立场从不承认本国经济法的域外适用,发展到主动在本国领土外适用美国经济法。这种变化突破了传统理论对经济法域外效力的否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美国解决经济法域外性问题的传统路径
人们从事跨越国界的经贸交往,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会牵涉到各国有关经济交往的私法性法律,比如合同法、海商法、票据法等私法性质的法律。同时,国家对经贸交往进行管制,所以还会涉及各国管制性的法律,比如税法、反垄断法、不正当竞争法、证券法、劳动法等公法性质的法律。在私法的背景下,美国通常会诉诸实体法以外的规则,尤其是法院所在地的冲突规则回答准据法的问题;在公法的背景下,美国法院的方法是面向内部的,它们会在实体法自身中寻求该实体法是否可以适用的答案。[1]也就是说,如果跨国经贸交往涉及到不同国家的私法,法院解决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的实体法适用?如果涉及到不同国家的公法,法院解决的问题是——本国的法律是否能够适用?
经济法是国家对经济交往进行管制的法律。从法院的视角来看,这种管制性法律能否在一国的领域范围外适用,一方面与诉讼的法院所在地的相关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与该法律对自身的适用范围的规定有关。
当法院地不承认外国经济法的域外效力时,即使经济法所属的国家规定了经济法的域外效力,该域外效力也不能实现。相反,如果法院地愿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外国经济法在本国的域外效力,则该经济法有适用的可能。比如,英国法院曾经在1921年的“拉利兄弟商号”案中主动适用西班牙的税法。
国内的法院能否将本国经济法适用于本国境外的经济行为呢?在美国,有关这个问题的最明显的证据是根据该法律自身对适用范围的界定。有些法律明确规定了自己的适用范围,比如1982年美国的《对外贸易反垄断改进法》(FTAIA)就明确规定了立法的效力问题,其第15条规定:“本条之下第1-7部分不适用于包含涉外因素的贸易和商业(不包括进口贸易和进口商业),除非(1)这样的行为具有直接的、实质的和合理的可预见效果......;(2)这样的效果使当事人可以根据第1-7部分提出请求。”[2]这种对本国经济法的域外效力的单方面规定,在本国法院是没有问题的,但外国对相关法律的域外效力的态度是不确定的。更常见的情况是,或者由于立法者的疏忽,或者由于立法者认为没有必要,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在很多法律当中立法者并没有对法律的适用范围作出声明。此时,美国法院就通过解释本国立法者的立法目的确定法律的可适用性。
2 属地主权基础上的经济法域外性问题
2.1否定经济法域外适用
20世纪早期,美国在经济法的域外适用问题上就延续了传统做法。以广为人知的美国香蕉公司诉美国联合水果公司案为例,香蕉公司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联合水果公司在美国境外的行为违反了美国的谢尔曼法,并且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个早期案件涉及到美国反垄断法能否适用于美国域外的垄断行为。霍姆斯法官在这个案件中没有转向冲突规则去寻求准据法,他的目光聚焦于谢尔曼法本身的可适用性。谢尔曼法并不包括专门强调其在跨境案件中的管辖范围的条款,因此霍姆斯法官通过解释谢尔曼法的立法目的确定了其适用范围。他首先指出了谢尔曼法的适用范围,认为美国的反垄断法并没有扩展到美国公司在中美州的反竞争行为。“有关一个行为是合法或者是违法的性质的通常的和最普遍的规则是,行为的性质必须完全由行为完成地国家的法律确定......对于另外一个管辖权来说,如果它刚好控制住了行为人,并根据自己的法律而不是行为人作出行为的地方的法律来对待行为人,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还会干涉另一个主权者的权力,同国家礼让相背离......”[3]可以看出,他认为义务的来源只能是行为地。霍姆斯进一步解释,“在疑难案件中,根据前面的考虑会导致把任何法律考虑为意图将其运作和效果限制在立法者有普遍合法的权力的地域范围内”。[4]根据这个解释,对于反垄断法是公法性质的经济法,立法者在立法时的意图是将其效力限制在立法者所属的主权权力的地域范围之内。因此,一个经济法范畴的公法的可适用性,取决于其立法者所属的主权权力的地域范围。只要经济法所调整的行为发生在经济法的立法者所属的主权地域之内,该经济法是可适用的;反之,则该经济法不可适用。所以,美国的谢尔曼法不能适用于美国公司在巴拿马从事的反竞争行为,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美国早期关于经济法域外适用的理论是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经济法的可适用性系于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又将立法者的立法目的限制在主权者调整其地域范围内的行为的绝对主权权力之上,从而得出结论——美国的经济法不具有域外效力。因此,法院所需要做的不是在相关的美国法律和外国法律之间进行选择,而仅仅是界定美国经济法的适用范围——美国的经济法能否适用于这个特定的行为。主权的地域因素在立法管辖权的分配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我们可以对这种做法做出几点评述:第一,这种关于经济法域外适用的理论属于法律解释方法。通过对相关国内法的立法目的进行解释,这种解释方法是面向国内法律体系和国内秩序的方法。第二,法院对本国立法者立法目的的解释带有一定的假设性,并且带有很大程度的自我约束。第三,这种理论也反映了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绝对主权理论。根据绝对主权理论,每一个国家都具有控制自己领土范围内的人、事、物和行为的权力,领土主权就是一种领土特权。每个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土特权也会去尊重别国的领土主权。对本国领土特权的维护也能解释法院在解释经济法时采取的自我约束立场,较少侵入别国主权作用的空间。
2.2防御性允许经济法域外适用
在香蕉案之后,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在1945年审理了美国诉美国铝业公司案。该公司是一家美国公司于1928年在加拿大成立的一个子公司,后来接管了美国铝业公司的财产。它和其他的几家欧洲公司用一个瑞士公司的形式创建了一个卡特尔,限制向美国出口铝,从而被指控违反了美国的谢尔曼法。在该案中,汉德法官采用了“效果原则”。根据该原则,如果外国公司的行为在美国有“效果”或者意图在美国产生这样的效果,美国谢尔曼法就可以适用于外国公司在外国的行为。谢尔曼法能够在美国之外适用于外国公司的原因就是卡特尔的联合效果影响了美国的相关利益。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防御性地将自己的经济管制性法律适用于本土之外,打破了香蕉案确立的原则,至此美国的反垄断法开始具有域外效力。
与香蕉案相同的是,该案也采用了解释议会的立法目的的方法解决谢尔曼法的域外适用问题。经过解释,甚至是意图在美国产生效果的行为也会被惩罚。汉德法官指出,“我们不能像解读一般文字那样解读这个法律当中的文字,而不去考虑国家能观察到的对它们行使权力的通常限制。这种限制通常与冲突法施加的限制相适应。我们不能责怪议会意图惩罚那些其行为没有在美国产生后果的人”。[5]这个解释的基础仍然是建立在主权的地域范围的基础上,因为这个解释要求外国公司的行为的效果以及意图产生的效果位于美国领土范围之内。因此,这个案件仍然取决于领土主权因素。但是与香蕉案不同的是,汉德法官不关心行为在哪个国家完成,而是关注行为的效果留在哪个国家。
与香蕉案相比,20世纪中叶出现的铝业公司案更多侵入别国主权。一旦行为所在的国家也主张对相关的行为行使立法管辖权,美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就会引起这些国家强烈的不满。
与香蕉案相比,我们可以对铝业公司案中的效果原则作出如下评述:第一,效果原则仍然是建立在属地主权的基础上,面对国内法律制度和国内法律秩序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第二,效果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防御性质。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对主张在本土之外发生对美国利益有影响的行为适用美国的反垄断法。这种做法与刑法中的“保护性管辖”有相似之处。第三,同香蕉案相比,效果原则的自我约束减弱了,在域外适用的问题上采用更加扩张性的政策。在铝业公司案之后,美国域外适用反垄断法的案件增加了。该原则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管制利益,但是没有同时顾及外国的管制利益和外国的管制性法律,所以不可避免地会与他国产生摩擦。它的出现与20世纪中叶绝对主权理论在美国日渐式微也有关系,美国在他国的主权利益面前不再小心翼翼,这是试探性的一步。第四,效果原则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之后陆续有国家效仿美国主张本国相关法律的域外适用,带来了经济法立法管辖权层面的冲突。
3 过渡时期经济法的域外性问题的解决
由于效果原则引发的其他国家的不满,美国逐步调整其经济法的域外适用理论,采用利益平衡方法。20世纪70年代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审理的“廷伯兰木材公司诉美洲银行”案是过渡时期的典型案例。该案涉及一家美国的木材公司在洪都拉斯吸收了当地的一家企业,但这家当地企业在洪都拉斯的债权人却在洪都拉斯提起了诉讼程序要求受偿。美国的木材公司只好向美国法院起诉,认为债权人的行为阻止了对美国木材的出口,属于限制竞争行为,并要求赔偿损失。
根据利益平衡方法,法院不仅必须确定美国对行使的特定的管制行为的利益对管制行为来说是充分的,还必须确定美国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竞争性利益相比也是充分的。在铝业公司案之后,Choy法官意识到虽然美国的法律覆盖到了一些超越美国边界的行为,但如果美国的利益太弱而外国限制的动机太强,那么很明显美国法律的域外适用就是不正当的。在此基础上,该案法官最终放弃了将美国反垄断法适用于该案。
但是根据什么来衡量美国的利益和外国的利益呢?该案法官认为不能去寻求国际法的根据,而是应该根据“礼让和公正”的概念来分析。根据《第二次对外关系法重述》第40节的规定——国家需要温和地考虑行使管辖权。该案的法官认为,在国际背景下的司法克制是一个礼让和公正的问题而不是国家权力的问题。[6]该案法院还提出了一系列引导管辖权分析的因素:与外国的法律和政策相互冲突的程度;国籍、忠诚、商业或公司的所在;任何一国的执行可以被期待获得一致的程度;与其他地方相比对美国的影响的重要性程度;明确影响美国商业的目的的程度;效果的可预见性等。
与效果原则相比,这是一个更合理的管辖原则,所以利益平衡方法也常被称为“合理管辖原则”。利益平衡方法既是美国对解释国内法方法的一个继承,同时也是对其他国家对效果原则反映的一个回应。利益平衡方法仍然承认如果行为的完成或者是行为的效果发生在美国境内,美国可以基于领土主权适用美国的反垄断法;同时美国在域外适用反垄断法时必须在考虑美国的利益的同时考虑相关外国的管制利益。因此,法院在管制特定经济活动的管辖权确立之后,必须评价和解释特定的因素,从而使管辖权的行使具有合理性。其中有一些因素是地域性的,比如国籍或公司的所在地、对美国影响的重要性程度、影响美国的商业的目的的程度等。而有些因素则包含实体分析的种子,比如与外国的法律和政策相互冲突的程度、获得一致性的程度、效果的可预见性等。这些实体性因素要求考虑到相关外国的法律、政策和管制利益,这种考虑在纯地域性的分析中是看不到的。
我们可以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法的域外适用理论进入过渡期之后,主权的地域性考量和相关的实体性考量均已经开始进入美国域外适用经济法的理论视野。但两种性质的考量因素在域外适用经济法的理论中的作用并不可同日而语。对外国法律、政策和利益的考量是为了确定美国的立法管辖权服务的,因此它是辅助性的。对美国经济法的政策和利益的考量仍然在经济法的域外适用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利益平衡方法统治的时期很短。1993年在最高法院审理的Hardford火灾案宣告了利益平衡方法的终结。该案的审理法院认为谢尔曼法能适用于外国行为意图产生并且确已在美国产生实质效果的情况。礼让能否导致法院在实践中减少行使立法管辖权呢?法院将礼让和外国的主权义务相结合,指出除非相关外国提出要求,否则立法管辖权的“真实冲突”就不存在。在相关外国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这种方法等于事先就关闭了对外国的法律、政策和主权利益的考量。对经济法域外适用的理论似乎又回到了地域性的主权概念的基础上。
4 实体主义基础上的经济法域外性问题
20世纪末期之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日益挑战建立在领土主权基础上的管制权力。荣格甚至曾经指出,调和主权的属地限制和跨国交易的自由流动具有不可能性。[7]但经济活动的国际性确实重塑了国际经济管制的过程和这个过程中各国国内法的角色。美国相关的经济法对此作出了快速反应,日益转向在实体主义基础上解决经济法的域外性问题。地域性的主权概念强调通过适用本国的经济法维护本国对跨国经济活动的管制利益,而实体主义基础强调,只要对跨国经济活动行使立法管辖权的国家的经济法与美国的法律足够相似,美国的利益就同样可以实现。
4.1实体主义基础的表现
在利益平衡方法中,可以看到实体主义的一系列要素,当这些对相关的竞争性的法律的实体内容的考虑仅仅是辅助性的。在真正的实体主义的考量中,需要对相关竞争性的法律的实体内容进行考量,为特定的案件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法律。对外国经济法的实体内容的考虑是一个核心因素,是第一位的。[8]
4.1.1允许当事人选择与美国法相似的外国经济法。在一些涉及到经济法适用的合同案件中,美国开始承认当事人选择其他国家的经济法的条款的效力。比如,在引起劳埃德保险市场崩溃的一系列案件中,美国投资者在投资协议中的法院选择条款和法律选择条款中都选择了英国。这些投资协议涉及到证券的部分原本都应该受美国证券法支配,但美国八个联邦上诉法院都承认了这些条款的效力。这意味着英国的证券法可以取代美国的证券法适用于美国投资者的协议。美国法院细致分析了英国证券法的内容,发现一个针对劳埃德的欺诈的请求在英国也是可诉的。美国证券法的经济政策可以通过适用英国证券法而得以实现。至此,经济法自动优于当事人选择的法律的定式被打破,美国法院在经济法的域外性问题上开始把目光从主权、地域等观念转向美国的政策能否得到实现。领土主权不再是决定性因素,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能否实现美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利益是决定性的。这与美国冲突法革命从关注地域联系到关注国家利益、政府利益的转变是一致的。[9]为了确定外国的经济法能否实现美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利益,对相关外国法与美国法律的实体内容的比较是尤其重要的。因此,这种实体主义方法能够筛选出与美国法相一致的外国经济法,赋予它们在美国的域外效力。证券法领域的做法在其他领域也有所体现。第九巡回法院处理的一个反垄断案件也考虑了外国反垄断法与美国法的相似性。
允许与美国相似的外国经济法在美国适用,等同于以一种变相的方式适用美国的经济法。不仅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实现了美国的利益,而且这种大度的态度还为外国投桃报李适用美国经济法提供了一种激励,并同时鼓励外国经济法向美国看齐。
4.1.2鼓励各国经济法的统一。要实现经济管制性法律的统一,必须首先检查各国法律的实体内容。在各国法律的实体内容差距比较大的领域,统一是不可能的。而在各国法律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地方,统一具有可能性。[10]美国有选择性地在一些与其他国家比较相似的经济管制法律领域鼓励统一。因为在这些领域鼓励统一引发的管制风险最小。比如,在跨国证券发行和交易领域,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就与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和国际证券组织委员会一起制定了国际会计标准。即使这种成功很有限,也是建立在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长期要求外国的证券发行人根据美国接受的会计原则提供资金陈述的基础上,这种长期的坚持事实上鼓励很多国家向美国的标准看齐,缩小了相关领域的法律差异。
4.1.3提供程序上的合作机制。经济活动的跨国性决定了一国在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查和进行执行的时候,可能会需要进入其他主权国家的领土范围。这时执行程序或者是调查程序就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才有可能完成。近来,美国开始在实体主义的基础上考虑提供程序合作的可能性。比如,在跨国破产领域,美国面对其他国家的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时,对于破产人位于美国境内的财产是转移给外国的破产程序还是根据美国的破产规则分配,美国会考虑外国破产程序下的分配规则与美国的分配规则是否在实体效果上具有一致性。美国签订的一些谅解备忘录也具有实体主义的导向。当美国的机构被外国请求合作发动调查或执行行动时,除非被调查的行为也违反了美国的管制法,美国的管制机构是不会提供合作的。这种程序层面的合作,也需要考察外国法律的管制目标与美国的管制目标是否一致,从而需要考察外国相关经济法的实体内容。程序上的合作机制也能潜在地推动外国法律向美国法律靠近,助力美国实体法律的输出。
4.2对实体主义基础的评述
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美国在经济法的域外性问题上已经彻底转向实体主义,地域性的主权概念日益被超越。对于这种转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第一,建立在实体主义基础上的经济法域外性问题仍然继承了美国面向国内法律秩序解释经济法域外效力的视角。外国的经济管制性法律能否在美国得到适用,取决于这些法律与美国法律的相似性,对美国经济管制目标的实现程度。美国始终无意为解决经济法的冲突寻找国际法上的支撑。第二,建立在实体主义基础上的方法不能做到对外国经济法的实体内容保持中立。无论是美国早期不承认经济法域外效力的立场,还是后来的效果原则和利益平衡方法,都没有对外国经济法的内容进行评价,因此它们都是实体中立的。而实体主义方法会对外国经济法的内容进行以美国国内法为标准的评价,那些与美国法律一致或相似的外国法被赋予在美国的域外效力,那些与美国法不相似的法律则被美国拒之门外。这实际上是在积极鼓励外国法向美国集中,与效果原则防御性的主张经济法的域外效力相比,这是更加主动地向外扩张美国法律和美国经济政策的方法。第三,建立在实体主义基础上的方法会导致美国法的过度适用。如前文所述,解决经济法域外性问题的通常思考路径是问:某经济法能否适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考虑案件与该国的领土联系来确定该案件是否是立法者的立法目的范围内的案件。但实体主义的方法问的问题是:外国的经济法与美国法律是否足够相似?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美国会拒绝适用外国的管制法,代之以美国的管制法。①在劳埃德案中,美国法院就采用了宽松的有关美国法域外适用的观点。第九和第十一巡回法院认为,如果拒绝当事人选择的管制法,后果就是对原告的诉讼请求适用美国的管制法。这种后果会导致联邦证券法的适用于所有这类交易,无论与美国的联系有多么少,会导致证券法的适用范围没有任何限制。作为一种反证,美国的管制法不应当在国际交易中随便适用,因此应当承认当事人选择的英国证券法的效力。但是在当事人选择的外国管制法与美国法不相似的情况下,美国还是会适用本国的管制法。此时,很可能美国与案件的领土联系很弱,美国的相关法律也得到了适用。实体主义方法忽略相关案件与美国的领土联系,从效果原则和利益平衡方法的视角来看,这种情况下美国法的适用是不合理的。第四,实体主义方法会导致各国管制跨国经济活动的权力失衡。传统方法在领土主权基础上分配跨国经济活动的立法管辖权,各国对跨国经济活动的管制权力取决于经济活动本身与特定地域之间的领土联系,因此各国的管制权力大致相当。而美国近年来的实体主义方法会导致美国在经济法冲突的解决上具有更大的话语权。而一些与美国的法律制度差别较大的国家对跨国经济的管制权力被明显弱化。
实体主义基础上解决经济法域外性问题的方法戴着美国经济管制价值目标的有色眼镜逐一评价外国的经济管制性法律,它不再满足于在美国境内克制地维护美国的管制利益,以一种更加富有侵略性的姿态积极向外部推行美国有关经济管制的法律、政策和价值取向。
5 反思与展望
与一百年前相比,美国解决经济法域外性问题的方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变化当中,有些东西保留下来,比如从美国的国内法律制度和国内法律秩序出发解决问题,较少关心国际法的影响;也有些东西被彻底抛弃,比如领土联系在确定立法管辖权上的重要作用。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美国所保留的东西和所抛弃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吗?
首先,解决经济法的域外性问题能否完全面向国内法律制度而将国际法置之度外呢?恐怕我们很难做出否定的回答。不同国家相重叠的立法管辖权主张在本质上就是国家主权权力的碰撞。如何协调主权权力之间的碰撞,无论如何都应该从国家间的立场出发,具有国际的视野。从一个国国内的法律秩序出发解决主权国家间权力的冲突是不合适的。在这一点上,欧洲国家的做法可以提供一些与美国相反的做法。比如,德国就是从国际法的框架内来解释法律管辖的范围。德国宪法第25条就明确在规范效力上将国际法置于国内法上。在德国看来,国际法为一国的立法范围创造了严格的、硬性的限制,在国际法的限制之外探讨规则意图适用的范围是不合适的。[11]在德国,多数意见认为以德国国内效果为基础的管辖权必须符合国际法。他们首先探讨了1927年国际常设法院对判决,认为该案的判决并没有对国家扩展其管辖权于领土外的人、财产、行为的效果施加一个普遍的限制,国际法在这方面给国家留下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只是在特定情况下,通过禁止性条款限制国家的管辖权。国际法到底能够为德国经济管制性法律的域外效力提供哪些有约束力的规范呢?早期的德国学者把目光投向互惠和礼让这样的软法规范,后来德国学者Rehbinder提出了一个国际法原则:禁止滥用权力。这个规则要求在疑难案件中应当以尽可能少的干预国际秩序的方式解释规则。如果德国经济法要域外适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交易与德国市场有一些联系;第二,该法适用不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后来,伴随着日益增长的域外管制行为,德国学者又提出了其它的国际法条款——主权平等原则、比例均衡原则、不干涉原则。尤其是不干涉原则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并在一些案件中认定德国联邦卡特尔办公室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在这里,笔者无意解释每个国际法规则的具体运用。本文只是想说明,在分析经济法的立法管辖权时,采用一种面向外部的视角,关注国际法的作用,能够阻止自私的、过度的管辖主张,尊重其他国家的平等的管制权力。与美国的方法相比,德国的作法更有利于让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管制共同体”实现组织化、有序化。
其次,解决经济法的域外性问题能否抛弃主权的地域性考量呢?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虽然我们不能将绝对的属地主权作为考虑经济法域外性问题的基础,但是在一个现实的以地域分割的政治世界,彻底抛弃地域联系的实体主义方法反映了霸权国家对他国主权的不尊重,我们需要将地域联系重新整合到经济法的域外性分析当中。在考虑地域联系时,必须站在国际法的立场上衡量,任何主张立法管辖权的国家,其管辖权是否具有公正性和合法性。在考虑公正性和合法性的时候,地域因素必须被纳入考虑的范围,虽然地域因素不必是全部的考虑因素。因为,在一个国家作为其中一员的全球社会,属地主权仍旧是表达每个成员利益的最合适的工具。
参考文献:
[1]William S.Dodge,“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in the Conflict of Laws”[J], Available at SSRN:HTTP:SSRN.com/abstract=1139102[2010-03-20].
[2]Peter Hay,Conflict of Laws:Cases and Materials (12th edition)[M],New York:Foundation Press, 2004,P735.
[3][4]American Banana Co.V.United Fruit Co.,213U. S.347(1909).
[5]William S. Dodge,”Extraterritoriality and Choice of Laws Theory:An Argument for Judicial Unilateralism”[J],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39(1998),P125.
[6]Hannah L.Buxbaum,”territory,territoriality and the Resolution of Jurisdictional Conflict”[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Vol 57 (2009),P646.
[7]Friedrich Juenger,Choice of law and multistate justice,[M],Bost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3,P21.
[8]Hannah L.Buxbaum,Conflict of Economic Laws: From Sovereignty to Substance[J],Vi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42,P957.
[9]Mathias Reimann,Savigny’s Triumph?Choice of Law in Contract Cases at the Close of Twentieth Century,Vi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 39,P584.
[10]Donald T. Trautman,The Role of Conflicts Thinking in Defi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ach of Ametican Regulatory Legislation,OHIO ST.L.J.Vol. 22,(1961),P591.
[11]Hannah L.Buxbaum,”territory,territoriality and the Resolution of Jurisdictional Conflict”[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Vol .57,(2009),P653.
责任编辑朱文婷
作者简介:刘艳娜(1977-),女,河北秦皇岛人,法学博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基金项目:燕山大学青年自主研究项目(15SKA004)。
[中图分类号]D912.2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6)04-016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