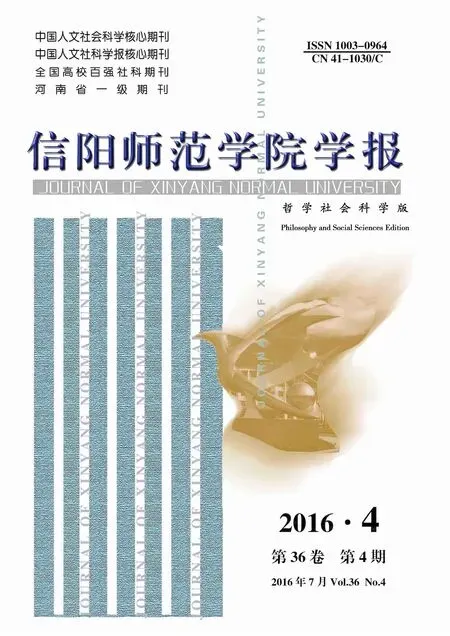论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趣味”
——以到中国旅行前的作品《杜子春》《奇遇》等为例
周 江
(信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论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趣味”
——以到中国旅行前的作品《杜子春》《奇遇》等为例
周江
(信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自幼钟爱中国古典文学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1921年到中国旅行前,创作了大量取材中国古代典籍的作品,并孕育出了他独具一格的“中国趣味”。“亲近中国古典”是芥川“中国趣味”形成的雏形,进而发展成了对“中国古典的回归”。他早期借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素材,凭借自己对于中国的憧憬与幻想,创作出了一系列如《杜子春》《奇遇》等作品。“中国趣味”不仅决定了芥川的艺术创作,而且影响着他的个人经历与人生选择。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中国趣味;《杜子春》;《奇遇》;中国旅行
芥川龙之介(1892—1927年)是日本大正时代的代表作家,在日本文学界享有“鬼才”之称。在其35年的短暂生涯中,作品高产且多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特别是其早期作品多取材于中国的古典文学。芥川用独到的创作手法对古典文学中的素材加以改编,完成了巧妙而又富有新意的再创造之作。例如在1921年其到中国旅行前创作的《杜子春》《奇遇》《秋山图》《酒虫》等作品,均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这些作品为我们描绘了芥川眼中的中国,也孕育出了他自身独具一格的“中国趣味”。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趣味”历来受中日两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在中国,对芥川“中国趣味”的研究以巴金的“批判说”为起点,经过几十年许多学者的褒贬不一的论争,后来“肯定说”占据主导地位。巴金曾以“空虚”“堕落”“几段不恭敬的话”等词语尖锐地批评芥川的作品和他的“中国趣味”[1]21-22。之后也有学者指摘芥川对于中国的关注只不过是市井庶民的生活片段,以及被列强蚕食的中国现状而已,取材中国的作品也缺乏一定的平衡性[2]。然而,后来随着对芥川作品的深入研究和探讨,“肯定说”便成为主流学说,如早期的鲁迅、夏丏尊等,之后的单援朝等学者皆持有此观点[3]。他们充分肯定了包括芥川的《中国游记》在内的取材于中国的作品所具有的现实性和透彻性。
在日本,对芥川的“中国趣味”的研究也褒贬不一。日本著名小说家宇野浩二、评论家川本三郎等都对芥川的“中国趣味”及作品进行了批判,说其内容空乏无聊[4]。而后以关口安义为代表的小说家,对芥川取材于中国的作品加以积极的评价。此外,村松梢风认为芥川是有代表性的“中国趣味家”。
由此可见,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趣味”及取材于中国的作品一直以来饱受争议,见仁见智,因此仍具有再次探讨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将以1921年芥川的中国旅行为界点,通过分析他到中国旅行前取材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来探究芥川的“中国趣味”的特点和发展变化,以及对其到中国旅行后取材中国的作品的影响。
一、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趣味”的雏形——“亲近中国古典”
提到“中国趣味”,不得不先谈谈日本人的“支那趣味”一词。“支那趣味”最早出现在1922(日本大正十一年)年日本当时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中国公论》的第1期名为“支那趣味的研究”的特设栏上,登载了小衫未醒的“唐土杂观”、佐藤功一的“我的支那趣味观”、伊藤忠太的“从住宅来看支那”、后藤朝太郎的“支那文人和文具”以及谷崎润一郎的“所谓‘支那趣味’”等5篇文章。特别是谷崎润一郎的“所谓‘支那趣味’”这一文章,首次明确提出“支那趣味”一词。由此“支那趣味”一词从大正时代开始郑重面世并渐渐流行起来。
“支那趣味”被定义为“以大正时代为中心的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异国趣味’”[5]21。自诞生以来,“支那趣味”逐渐被大正时代的文人墨客广泛使用。例如中国通的代表者之一后藤朝太郎曾说,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在家具、料理、旅行等方面选择“支那趣味”的风格。此外,有很多著名作家也频繁使用“支那趣味”一词,芥川龙之介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从意义上来看,“支那趣味”具有“中国人的趣味”“日本人的汉学的素养、文人的教养”及“对中国的人事物所散发出来的异国氛围的憧憬和热衷之意”[5]28-30这三层含义。大正时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和文人大体都会对中国这个日本文化源头的国度抱有一种情结。这种情结实际上主要是对汉诗文中的古典中国的亲近感和憧憬,即形成了所谓的“中国趣味”。
芥川龙之介自幼在具有浓厚的文学氛围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像大正时代其他大多数日本文人一样,他对中国的古典文学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中国古典文学文辞精深微奥、内容一波三折、手法浪漫夸张、意象宏大壮美,使得芥川沉醉其中、爱不释手。芥川不辞辛劳用假名注释诵读,有时虽然也会对汉文学作品有些误读,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广泛涉猎和浓厚兴趣。通过这些似懂非懂的奇妙而有趣的文字,芥川在心目中逐渐培养出了“对中国的人事物所散发出来的异国氛围的憧憬和热衷之意”,进而形成了一种“亲近中国古典”的“中国趣味”,为其自身的文学作品创作积累了源泉和艺术灵感。
渡边晴夫曾说:“芥川龙之介喜爱的中国古典,一个是历朝历代的诗歌,另一个是白话文小说、文言文小说及戏曲。”[6]芥川研读中国古典文学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在其随笔中提到的经典的作家作品就有不少,既包括《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长篇小说,也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中国著名诗人的诗歌,此外还有康白情、胡适、鲁迅等文人的现代诗。芥川在他1921年中国旅行前的随笔《爱读书籍印象》中,曾有过以下描述:
我儿童时代爱读的书籍首推《西游记》。此类书籍,如今我仍旧爱读。作为神魔小说,我认为这样的杰作在西洋一篇都找不到。就连班扬著名的《天路历程》,也无法同《西游记》相提并论。此外,《水浒传》也是我爱读的书籍之一。如今一样爱读。我曾将《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的名字全部背诵下来。我觉得即使在当时,《水浒传》和《西游记》也比押川春浪氏的冒险小说有趣得多。[7]683
由此可见,芥川对《西游记》《水浒传》等中国古典文学的喜爱,“亲近中国古典”的“中国趣味”也借此油然而生,在其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再例如在芥川半自传体的小说《大导寺信辅的半生》中,他对于自己的读书生活也曾有过以下叙述:
信辅从上小学时就开始喜欢看书了。让他对书产生兴趣的是在他父亲书箱底的帝国文库本《水浒传》。只有脑袋长得大的小学生在昏暗的灯光下把《水浒传》看了好几遍。这还不算,就是不看《水浒传》的时候,他心里也在想象着替天行道的大旗、景阳冈的猛虎、菜园子张青在房梁上挂着的人腿。是想象吗?可那种想象比现实更加现实。他还曾手提木剑在挂着晾干菜的后院里与一丈青扈三娘和花和尚鲁智深拼杀过。[8]511-512
沉浸在《水浒传》中各路英雄们的世界里的芥川,对于绿林好汉无拘无束、纵横天下的生活深深地向往,在他心里构筑了一个洒脱不羁、超越现实又充满英雄主义的中国形象。从而他的“亲近中国古典”的“中国趣味”也渐渐显现成形,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对中国的早期认知。正是这“亲近中国古典”的“中国趣味”在芥川的自身成长和艺术创作的道路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为其以后的文学经历增添了一抹浓厚的中国古典色彩。
二、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趣味”的发展——“中国古典的回归”
1.从《杜子春》来看“中国趣味”
正是由于芥川始终保有“亲近中国古典”的“中国趣味”,从未到过中国的他便借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素材,凭借自己对于中国的憧憬与幻想,创作出了大量的作品,包括《酒虫》(1916年)、《仙人》(1916年)、《黄粱梦》(1917年)、《尾生的信》(1920年)、《杜子春》(1920年)、《秋山图》(1921年)、《奇遇》(1921年)等等。通过这些作品,展现出芥川眼中那个神奇又艺术的中国。
日本学者关口安义说:“虽然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也很亲近于中国古典,但是芥川也不例外,他对经书、正史关注颇多,还对《游仙窟》《水浒传》《金瓶梅》等通俗小说也兴趣极深,并从中选取素材为自己创作所用。”[9]484中国学者张蕾也曾评价芥川:“中国旅行前这一时期集中撰写的作品——《杜子春》、《秋山图》、《南京的基督》等等,质量之高且数目之多。”[10]25由此可见,芥川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喜爱有加。
芥川取材中国古典的作品要么是把故事发生舞台建构在中国,要么是设在有中国人频繁活动的地方,且与中国古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构成“中国趣味”的典型表征。其中,《杜子春》是以唐代传奇《杜子春传》为蓝本改编的,也是巧借中国古典文学素材并融合芥川自身的创作灵感的经典之作,历来受中日学者的广泛关注。在《杜子春传》中出现的“唐都洛阳”“杜子春”“峨眉山”“铁冠子”等等这些典型的中国元素,在芥川的《杜子春》中也同样袭用:
时值大唐年间,京城洛阳西门下,有个年轻后生仰望长空,正自出神。那后生名叫杜子春,本是财主之子,如今家财荡尽,无以度日,景况堪怜。且说当年洛阳乃是繁华至极、天下无双的都城,街上车水马龙,络绎不绝。……老人笑着说道:“不错,我是神仙,叫铁冠子,住在峨眉山上。”……铁冠子任凭两鬓的白发在风中飘扬,放声高歌道:朝游北海木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人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11]767-772
从中可看出,芥川若不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入研读与吸收,怎会创作出具有典型“中国趣味”的《杜子春》这一作品。他不仅沿用了原著的部分中国古典元素,还巧妙借用吕洞宾所做的一首诗歌,加以编撰,使《杜子春》充满了浓郁的“中国趣味”。芥川将中国与传奇故事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表明在他的内心深处中国是一个古典气息浓厚的神秘国度。他通过作品来展现着自己独具一格的“中国趣味”——“中国古典的回归”。
2.从《奇遇》来看“中国趣味”
到中国旅行前,芥川的最后一部作品《奇遇》也是“中国趣味”的典范之作。《奇遇》是根据明代瞿佑所著的《剪灯新话》中的《渭塘奇遇记》改编而成的短篇小说。学术界一般认为芥川的《奇遇》是直接取材于《渭塘奇遇记》,对其改编的内容尚且不多。芥川在《奇遇》中也借用主人翁王生之口暗示了作品故事的出典:“最后,这件趣闻传到了钱塘文人瞿佑的耳朵里。于是,瞿佑据此写下了美丽的《渭塘奇遇记》。”[8]81可见芥川对原著作品的尊敬,对中国古典的亲近与喜爱。在《奇遇》中,亦可看出芥川的“中国趣味”:
某日,赵生到久违的王生家登门造访,王生拿出元稹体的会真诗三十韵,称其为昨夜新作之诗。在华丽斑斓的对偶句里,全诗不时流露出嗟叹之意。……壁下贴着四幅金花纸笺,题诗于上。诗体模仿苏东坡的四时词,而书法则师承的是赵松雪。那些诗我都一一记得,只是现在没有必要背诵出来罢了。…… 这就叫做“有美闺房秀,天人谪降来”吧。赵生微笑着,振振有词地吟诵起了刚才看见的那首会真诗的头两句。[8]76-79
由此便可看出,芥川在《奇遇》中娴熟地借鉴中国名家名作的技法,把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喜爱之意尽显其中,也将他的“中国趣味”——“中国古典的回归”充分地表现出来。他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熏陶,在作品中营造出了浓厚的中国古典意象,也以此增添了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
在漫长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中,中国的经典著作相继大量地传入日本。日本的知识分子用日语假名注释解读汉文经典,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理解中国并向中国学习。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一个充满着传奇与唯美的憧憬之地。日本文人通过对汉文经典的不断言说和改写,使中国的印记乃至近现代出现的“中国趣味”在日本文人的集体意识中代代相传、无处不在。即便是在大正时代,虽然西方近代文明以显著的优势席卷了整个日本,可是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文坛依然享有很高的地位。如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都有很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中国古典文学给自幼在其熏陶下长大的芥川龙之介等日本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中国作为唐宋诗人笔下的乐土、水浒豪杰和三国英雄的故乡、奇妙传说的舞台始终散发着古老而神秘的气息,承载着日本文人骚客的无限遐想。可以说,真正吸引大正时代的日本作家的是古典文学中的中国,甚至是幻想中的那个具有强烈古典美感的中国。也正是有此强烈的憧憬之意促使芥川到中国旅行。
三、由“中国趣味”衍生的中国旅行
1921年前后,随着“中国趣味”的流行开来,大正时代的文人墨客怀揣着对中国的幻想和憧憬,便相继来到了中国旅行,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中国趣味”的先觉者,谷崎进行了两次中国旅行,尤其是在1918年的第一次旅行后,谷崎创作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作品,如《苏州纪行》《秦淮夜》《中国旅行》《苏东坡》等小说、纪行、戏曲、随笔,给大正时代的文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中国趣味”的热浪。本就拥有强烈的“中国趣味”的芥川龙之介也受此热潮影响,“想到中国”的心愿便愈发浓烈。
芥川在大阪每日新闻社任职期间于1921年3月下旬至7月上旬到中国旅行。在这120余日里,他游历了上海、南京、九江、汉口、长沙、洛阳、北京、大同、天津等多地,可谓如愿以偿地完成了他 “想到中国”的梦想。
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后,芥川的所见所闻皆与他心中那个古典色彩浓郁的浪漫传奇的国度相距甚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加上连年内战,中国大地满目疮痍。残酷的现实使芥川心中的那个中国幻象受到了严重的扭曲,他的“中国趣味”也进而发生了变化。记录了芥川的中国旅行的游记——《中国游记》里有过这样一段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的描写:
一脚刚跨出码头,我们就被几十个黄包车夫团团围住。……本来,黄包车夫这个词,在我们日本人的印象里,倒绝不是脏兮兮的样子,不如说他们精力过人,劲头十足,令人产生一种返回到江户时代的心绪。可中国的黄包车夫,说他们是肮脏的代名词也不为过。且粗略地扫视过去,但见个个相貌怪丑。这么一群人前后左右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张张丑陋不堪的脑袋一齐向我们伸过来,且大声地喊叫着。一位刚刚上岸的日本妇女甚感恐惧。就拿我来说吧,当他们中的一人拉扯着我的外衣袖口时,我禁不住躲到了人高马大的琼斯君身后。[12]616
芥川被人力车夫的叫嚷和汗臭所包围时,他虽然对中国的向往和憧憬在转瞬之间就变成了厌恶和嘲弄,但芥川并没有完全改变自幼在他心中建立的具有古典美的中国幻象。他在旅途中时喜时忧,当他看到浪漫诗意的事物时,便会联想起汉文经典的描述,为自己的作品在中国得到现实的印证而感到欣慰和感动,然而当他看到肮脏庸俗的事物时,他又会用嘲讽贬低之词来宣泄自己对于现实中国的失望和无奈。进而也造成了他的“中国趣味”在中国古典和中国现实之间徘徊不定。由此可见,芥川的“中国趣味”不仅决定了他自身的艺术创作,也影响着他的个人经历与人生选择。
四、结语
在到中国旅行前,芥川龙之介眼中的中国是一个浪漫的艺术的国度。她的古典之美,无一不给芥川留下了诗情画意的深刻印象,也逐渐孕育出了他独具一格的 “中国趣味”。随着大正时代“中国趣味”的诞生和流行开来,自幼钟爱中国古典文学的芥川也融入其中,培育出了“中国趣味”的雏形——“亲近中国古典”。之后芥川的文笔更多地指向中国,取材中国的作品也比比皆是,芥川的“中国趣味”发展成了对“中国古典的回归”,而在芥川生涯中唯一一次的中国旅行也是由他的“中国趣味”衍生而来。“中国趣味”不仅决定了芥川的艺术创作,而且也与他的个人经历和人生选择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 関口安義.世界としての芥川龍之介[M].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7.
[2] 陳玫君.谷崎潤一郎と芥川龍之介による「支那」の表象―紀行文を中心に[J].広島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第二部,2003,(52):213-220.
[3] 单援朝.中国における芥川龍之介―同時代の視点から[J].崇城大学工学部研究報告,2001,(26):29-38.
[4] 井上洋子.芥川龍之介の中国旅行と《支那趣味》―谷崎潤一郎と芥川を軸として[J].千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0,(22):1-14.
[5] 西原大輔.谷崎潤一郎とオリエンタリズム―大正日本の中国幻想[M].东京:中央公論新社,2003.
[6] 渡邊晴夫.芥川龍之介の「支那」趣味について[J].国学院大学紀要,2007,(45):91-107.
[7] 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4卷)[M].揭侠,林少华,刘立善,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8] 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卷)[M].揭侠,林少华,刘立善,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9] 関口安義.芥川龍之介新論[M].东京:翰林書房,2012.
[10] 張蕾.芥川龍之介と中国―受容と変容の軌跡―[M].东京:国書刊行会,2007.
[11] 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1卷)[M].揭侠,林少华,刘立善,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12] 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3卷)[M].揭侠,林少华,刘立善,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韩大强)
收稿日期:2016-04-10
基金项目:2015年信阳师范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重点项目;2016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6-QN-233)
作者简介:周江(1991—),女,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6)04-012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