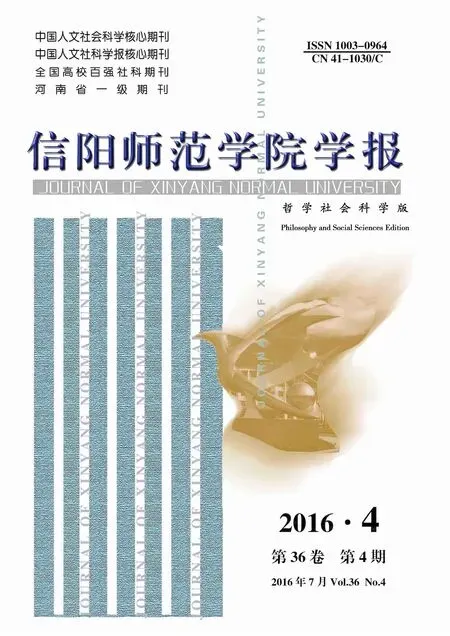劳动、时尚、情感:女性情谊的讲述方式
——以《万紫千红总是春》《街上流行红裙子》《闺蜜》为例
韩 煦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100871)
劳动、时尚、情感:女性情谊的讲述方式
——以《万紫千红总是春》《街上流行红裙子》《闺蜜》为例
韩煦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100871)
摘要:《万紫千红总是春》《街上流行红裙子》和《闺蜜》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和当下的三部书写女性情谊的电影。它们在讲述女性故事时所采用的相似而有区别的讲述方式,表达了左右女性之间微妙情感的主题,以及这种主题是如何与女性特质、时代情感及国家政治相互印证。
关键词:《万紫千红总是春》;《街上流行红裙子》;《闺蜜》;女性情谊 ;劳动 ;时尚;情感
2014年七夕强档,黄真真的《闺蜜》以不同于常见讲述“爱情故事”的情人节电影,来讲述女性之间情谊的故事。电影发行方公开强调:“《闺蜜》不是《致青春》,也不是《同桌的你》,更不是《小时代》,他们之间不存在同质化竞争。在这部电影中,观众可以看到只有闺蜜之间才会做的事,说的话。影片满满的尽是‘姐妹淘’和‘闺蜜情’。”[1]对于“闺蜜”或者说“姐妹情谊”的讲述,在近些年来的电影市场上是一个卖点,这是一个超越民族界限的世界性的热潮,如韩国的《阳光姐妹淘》《我的黑色小礼服》、日本的《NANA》《花与爱丽丝》、泰国的《亲爱的伽利略》、美国的《牛仔裤的夏天》等。这一类型电影带有显而易见的“小清新”色彩,故事的内容也集中于孤独美少女之间互取温暖、学会成长、学会爱等主题。因其书写的对象和其中的女性主义的立场,常被定位为“新女性主义”电影中的一个分支,“它以年轻女性为主要受众,讲述与女性生活密切相关的情感、工作、家庭、时尚、个人成长的故事”[2]。这里所提及的“年轻的女性群体”投射到当下的社会多是80后的独生子女。她们没有血缘意义下的姐妹和兄弟,在成长过程中闺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闺蜜”带给了她们的松散群体的整合感,这种具有“共同体”的集体形态的关系网络,对于这群年轻女性而言具有更丰富的内涵。这也恰是“闺蜜”而非“大哥/大姐”,这样的情感模式更多地存在于当下的大众文化之中,更能引发观影者的共鸣的原因。
对于女性情谊的书写是当代中国的文学史、电影史的常见主题,但书写的重心则随着时代发展有了不同程度的偏移,在女性情谊的基础之上讲述迥异而富有意味的故事。本文选取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和当下三个时间节点,分别以《万紫千红总是春》《街上流行红裙子》和《闺蜜》三部书写女性情谊的电影为分析对象,探究文本在讲述女性故事时所采用的相似而有区别的表达策略,辨析其中左右女性之间微妙情感的主题因素,以及这种主题是如何与女性特质、时代情感及国家政治相互印证,女性情谊所构造的女性共同体的嬗变,成为窥见其中偏移的结点。
一、电影文本与讲述年代
正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实际上,本文所选取的三部电影文本都具有类似的特征,即对当时社会特质的即刻映射,并非一种历史的书写,也没有史诗性的抱负,而是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从女性群体入手,在女性情谊的书写当中编织影片对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定位与想象。因此,影片所讲述的历史事件、时代背景成为关注的重点。
《万紫千红总是春》于1959年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制作,沈浮导演。影片中塑造了上海市吉祥里的一群女性群像:王彩凤、蔡桂贞、戴妈妈、陆阿凤、刘大妈、薛翠英、姚月仙等,讲述她们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当中响应号召,积极加入里弄生产组的故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蔡桂贞与大男子主义丈夫郑宝卿的龃龉和矛盾、王彩凤与恪守传统的婆婆刘大妈的斗智斗勇、陆阿凤与自我固有意识的对话和抗争等故事,展现了女性从“家庭”走到“工厂”的艰难。这种维度的呈现使得这部电影时常被标定为“妇女解放”电影。在1960年的《万紫千红总是春》座谈会中,给予了“反映1958年‘大跃进’以来我国城市街道生活所起的新的变化、新的面貌”[3]的高度评价。在当时针对电影的讨论、分析与评论中,妇女如何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与工人阶级家庭走出来,以及她们出走时所面对的迥异阻力等,是关注的重点。
《万紫千红总是春》是一部与当时社会运动几乎同步的电影,具有非常浓郁的现实意义,与其他描写“大跃进”运动电影不同的是,影片并没有讲述农村产粮、养猪、公社食堂、大炼钢铁等具有标志性的空间与事件,乡土中国并没有因为其典型而成为讲述的中心地域。影片将视野投向了作为中国现代性象征的上海,关注的是普通市民阶层当中的女性群体。在上海的城市属性当中,“摩登”遮蔽了它作为社会主义中国一分子的性质,而《万紫千红总是春》似乎在努力重塑城市形象,展示迥异于西方的、别样的现代上海。正如蔡翔所言,《万紫千红总是春》讲述了“一个上海里弄的家庭妇女如何在‘大跃进’运动中‘走出家庭’的故事”[4]。这部电影常常被视为“女性解放”电影的代表之作,即在“劳动”和“解放”的层面上获得诸多关注且是其彰显的内容,但在女性情谊的层面上则被忽视。本文即从这一被忽视的维度入手,去探究这种女性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并怎样在女性的个人成长、社会组织及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
《街上流行红裙子》由长春电影制片厂齐兴家导演,拍摄于1984年,改编自同年上映的同名戏剧。《街上流行红裙子》同样将视野投入上海,不同于《万紫千红总是春》集中描写上海里弄的家庭妇女,本片是写一群在工厂里做工的青年女工人:陶星儿、董晓勤、葛佳、阿香、小铃木等。固然这群女性由于其工人的“阶级”身份,天然地具有“劳动”的显性特征,影片也围绕陶星儿获得“劳模”展开,但有意味的是,在这部影片中,“劳动”并不会成为读者阅读电影/文本首要关注的层面,而“斩裙”作为一种“时尚”则成为最引人注目之处。该片被当时的影评人认为是自《庐山恋》之后,中国第二部涉及“时尚”的影片,并且在时尚层面走得更远。正如影片名所提示的,时装已不再作为电影的配饰,而成为书写的主体。虽然当时也有人指出,这部影片实与“名”不符,认为过于说教性的电影主旨与“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5]的片名相去甚远。
这种时尚元素的出现并非偶然,如果我们深入影片出现的具体历史境况之中,就会发现《街上流行红裙子》是在城市改革的背景下,讲述纺织厂女工的“新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20世纪50—70年代工业题材的延续,但“劳动”不再成为书写的主要对象,时代的变革也淡退为“已知”的背景。女性的爱美意识再次觉醒,对于“时尚”的定义也有了偏移:从50—70年代的“不爱红装爱武装”到此时的“街上流行红裙子”,对于女性共同体的塑造并未脱离“着装”的层面,而这种时尚并不是城市空间独立塑造的,而是在与乡下的对照当中自我完成。本文即自此角度出发,去探究时尚是如何塑造80年代的“新女性”,这种“新女性”与50—70年代新女性的异同,以及在追求时尚的共同目标下,女性情谊的罅隙与修复,其中隐含着的城市与乡村的权力关系也成为分析的重点。
《闺蜜》在2014年七夕情人节档上映,由一直关注女性问题的香港女导演黄真真拍摄,她的《女人那话儿》以纪录片的形式获得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作为具有明确的女性主义意识的导演,黄真真在拍摄当中将希汶、Kimmy和小美塑造成一个与男人进行不断“抗争”的“女人帮”共同体,而且在与男人的“斗智斗勇”之中,缝补、击破、牢固彼此的维系:帮助未婚夫出轨而失恋的希汶走出阴影,帮希汶促成与乔立的爱情,Kimmy与小美为了男人而相互“撕缠谩骂”。在这种情境下,女性情谊变得极其微妙、女性的地位也变得十分暧昧:在反男人的行动之中与男人达成了同盟。
与之类似,近些年中国电影市场涌现出大量描写闺蜜情的影片,即使并非全盘地将闺蜜情谊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但也将其作为重要的因素。例如《致青春》《一夜惊喜》《被偷走的那五年》《小时代》《同桌的你》等等。“以《小时代》系列、《闺蜜》为代表,开始探索更为细化的‘闺蜜情谊’”[2]。而且这类电影有着明确的观众定位:16—36岁的女性观影群体,述说多姿多彩的“闺中秘事”[1]。这一系列的女性共同体区别于之前的劳动共同体、时尚共同体,彼此之间的罅隙与龃龉更加复杂,矛盾的增长点也更加微妙,关键因素在于涉及了对情感,尤其是对爱情的书写,在此维度上,整部影片似乎在复制“天涯”“豆瓣”等的直播贴,“闺蜜”本身也成了极其暧昧的指称。而区别于男女的爱情之外,女性之间超越友谊尺度的同性之爱也成为“闺蜜”电影中构筑情节的另一思路。国家/政治等意识形态的表述在文本的叙事中褪色,几乎不再有标定时代变迁的特殊事件及节点,这些影片整体转向了“小时代”的叙述,不仅历史成了无物,而且现实(政治)也被刻意消隐,但也恰好构成了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不断扩展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同谋,成为“现实一种”。
总之,《万紫千红总是春》《街上流行红裙子》与《闺蜜》作为对姐妹/女性情谊的书写,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性,并且因之而呈现出不同的书写样态。女性如何结盟、女性情谊在何等维度上能够得以维系都与之密切相关。也是本文对这些影片分析的背景与切入点。
二、劳动、时尚、情感:作为女性共同体
共同体的概念通常是在与“社会”的辨析当中形成。滕尼斯强调“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我们这样认为)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6]67。这里便指出了“共同体”的独特性所在:既是私人的也是公共的。个人不会被完全地暴露在公共的视域当中,接受来自外界的监视,但也部分地享受着这种半公共性的组织所提供的物质便利与精神支持。同时,个人也不至于完全陷落在个体的窠臼而寸步难行,能够有足够的个体发展、压力释放等的自由。这种融合性揭示了“共同体”组织的复杂构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共同体成员的生活状态。滕尼斯在分析的过程中,将共同体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并且认为这三种形态是分离、发展后逐次形成的。其中,友谊构成了精神共同体形成的核心因素,友谊的产生源自职业和艺术的相似性,而且“这种纽带必须通过容易的和经常的联合”[6]67。在这三部影片当中,女性群体所构造的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属为“精神共同体”。但是这种友谊的基础在不同文本当中有着迥异的侧重,从而提示这种女性情谊的主要构造方式。劳动、时尚与情感三个要素成为《万紫千红总是春》《街上流行红裙子》《闺蜜》三部影片中女性共同体的旨要。
在《万紫千红总是春》中,女性之间联结的重要团体——“里弄生产组”,是以一种劳动的形式团结起来的“制度”组织。非常独特的是,这种组织包含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加工生产场所等多种形式,俨然农村合作社的变形——而这一点也暗合了“大跃进”当中对于“农村城市化、城市农村化”的要求。在这个共同体当中,中心人物是戴妈妈,她所做的工作也是将吉祥里的妇女们吸收到这个共同体当中,而这个共同体成立的目的显然不是私人情感的延伸,而是政治性的、生产性的:为支援边疆建设的志愿军缝制冬衣,同时也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女性从家庭的生活中解救出来,参与到社会性的生产当中,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女人的聚合带有妇女解放的性质,同时也对长久以来困扰文学界、思想界“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做出了回答。
里弄生产组“涉及女性解放的一个根本问题:如果没有制度的支持,妇女解放有无可能,或可能性在哪里”[4]。这种制度的支持基于劳动之上,走出家庭但也扎根于家庭。这是与之后的《街上流行红裙子》和《闺蜜》所不同的地方,它将视野投射到与女性密切相关的“家庭”问题之上,所涉及的女性也多为家庭妇女,而不是简单的青春少女们的爱情故事。所以影片的面向也更加丰富,内里的层次也更加复杂。例如影片中的郑宝卿与蔡桂贞夫妇之间的关系也是知识分子与家庭妇女之间的关系,郑宝卿被塑造成一个自私、封建的男子,他扮演着家长的角色,对妻子进行多重的管束,禁止她参与里弄生产组,认为是出去现眼,将蔡桂贞的生产与再生产局限在家的范围之内,避免她的社会性生产,甚至采取了闭门反锁等极端手段。摆脱这种依附的命运的唯一方式就是提供从家庭出走后女性的生存与活动空间,并能够使她在这个新的活动场域进行持续性的再生产。
影片当中非常具有意味的是戴妈妈位于居委会的办公室空间,这里成为生产组的集合地,也是众多女性的集结地。在成立大会上,镜头给了站在主席台上的戴妈妈长时间的特写,戴妈妈号召说:“这不是说,我们搞生产,家里的事儿就一点儿也不管了;也不是说,要参加就呼噜一下子都参加了,得要看条件,谁也不能勉强。姐妹们,努力吧!我们一定要自己解放自己。”而这也成为这群女性共同体组成的重要目的。她们借助的方式就是从家庭到社会的“劳动”。
在镜头面前,同样是劳动,在不同的空间呈现不同的样态。在密闭的家庭空间中,女性总在擦擦洗洗、缝缝补补,这种劳动的家庭性超越了公共性,在微观意义上,这种附属的角色,被自然而然地赋予女性。而在较为开放的生产组、居委会等空间,女性的劳动固然也是纺织、做饭、带孩子,但显而易见的是,个人被纳入集体当中,这些劳动不再是个体相对随意的行为,而是类似于工厂的组织化生活。里弄生产组的女性共同体所采取的方式,并非是争取社会性劳动与家庭劳动的平等地位,而是顺应这种预设去参与社会劳动。这大概也是这种女性解放运动的局限性所在,导致了女性的双重劳动,既要在生产组劳动,回家也依然要承担几乎全部的家务劳动。在生产组的社会劳动和解放自我的诉求,成为女性共同体形成并维持的动力,女性情谊在这种维度得到发生、拓展与加固。
“里弄生产组的建立,使得这一空间形态社会化,对于蔡桂贞等女性来说,便含有了摆脱自己命运的可能性。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的也是政治和经济的空间中,妇女的‘自信’才可能并不完全来自‘美’的支持”[4]。这种对于女性美的体认方式,在《万紫千红总是春》当中集中在女性的内在美、劳动美,是带着生产气息的健康美,外表、服饰则成为被遮蔽的面向——这种遮蔽既来自于“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主流舆论导向,同时也来自当时经济落后生产技术条件差的社会现实,这与《街上流行红裙子》对女性评价的标准迥异不同。
《街上流行红裙子》的讲述虽然集中于生产性的纺织工厂,这一组织制度固然提供了女性情谊发展的空间,但是“时尚”超越了“劳动”成为女性共同体的内核。《街上流行红裙子》对时尚的敏感度不仅仅是在以“红裙子”为首的时装上,影片的片头引入也是别具特色:一双手敲击着键盘,在当时最尖端、最科技、最时尚的电脑屏幕上,打出了“明年……将流行什么”,此时节奏不断加强的背景音乐也提示着一种“时代感”,由此引起了对“街上流行红裙子”的主题叙述。
在影片中,陶星儿评选劳模虽然占据了文本的大部分,但与此同时,有关女性之间别样竞争的侧面也悄然浮出,即对服装的重视、对时尚的热爱。影片所呈现的画面中,最夺目的红裙子是宽肩束腰装饰有蝴蝶结的红色过膝连衣裙,更重要的是,这裙子是美国料,是国内染不出来的。鲜艳的红色在此前普遍的黑白灰深蓝等冷色调中,十分引人注目;同时修身的剪裁将女性美好的身体曲线暴露无遗,一改之前宽松肥大的中山装和军装。实际上,作为关键物的红裙子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这件象征着商品/商业/消费的裙子出现在“劳模”陶星儿的身上,是值得玩味的。在参加服装展销会中,陶星儿跟日本记者谈道:“男女老幼穿灰黄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从服装的角度回答“上海的今天”的问题,其背后是非常有意味的,但在此,记者也提到了陶星儿自身着装上的“保守”性:白衬衫、蓝裤子。带着浓厚的20世纪50—70年代劳动人民的特色。
在50—70年代,女性的解放是伴随着“女性能顶半边天”的诉求出现的,社会劳动成为“娜拉”走出家庭之后的归宿——正如《万紫千红总是春》中所描述。“劳模”的形象分享着50—70年代遗留的构造:朴实、健美。所以,当陶星儿第一次穿上红裙子的时候,非常害羞,还将裙子进行了改造。她获得女性友谊的并非是她的劳模身份,而是她与其他女工分享对时尚的热爱,一起去公园斩裙,“展现的不仅是她们的身体,还是商品和商品的魅力”[7]。在影片的结尾,一大群女工身着各式各样的红裙子集体走出工厂时,给人造成了极其强烈的视觉冲击——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美学在崛起。影片的背景音乐“这就是生活”具有寓言意义地将时尚日常生活化,并且与此相关的景象是高大的楼房与工地,侧面展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上海新时代。“这部电影虽然也是以工人和工厂作为表现的对象,但城市,也即消费的城市的一面被真正凸显出来。影片中女主人公们在工服和裙子间的轮番变换,其实也就是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的切换”[7]。“洋不洋,中不中,衣服穿得紧绷绷”这是值班长对这些年轻女孩子们此时穿着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此时作为“新时期”的中国的社会特质。
《街上流行红裙子》所形成的女性的共同体比之《万紫千红总是春》和《闺蜜》更加复杂和别样,在这群城市青年女工当中,并非“工人阶级”或者“女性”就可以将她们简单而笼统地划归为一个群体。她们之间的龃龉与隔阂,在80年代整体的城市和乡村的意识当中,也有浓重的表现,存在于阿香与其他青年女工的关系之中。作为从乡下来的阿香,她的个体身份意识在异乡的境遇下更为凸显,在他者/自我的比对间也更为她深刻地感知[8],然而这种“乡下”的外来者身份带给阿香的则是自卑与困扰。在一群上海女工中,来自农村的阿香自然成了“他者”,在与时尚、繁荣、富有的上海的参照中,阿香自然地被标定为土气、凋敝、贫穷。尤其在这个女性共同体中,阿香的来历正如陶星儿的女劳模身份一般引人注目,一旦阿香有任何与共同体成员相异的行为与物品时,便会立即被冠以“乡下人”的称号进行区隔。这也是城乡结构差异在女性情谊中的投射,也在侧面显示了这个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的阶级/阶层特性,这种不稳固的因素的弥补,也是极其具有意味的。上海在与乡下的对比之中,其“时尚”的身份得以确立;然而在“上海/香港”的结构当中,上海似乎便成了时尚的他者,阿香便是利用这一点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中和,以趋近于整个共同体的“上海时尚性”——也即是某种纯一性。阿香谎称自己有一个在香港的表哥可以给大家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更时尚的物品,实际上是自己倒贴钱为她们购买。即便如此,阿香认为为了尊严是值得的。
在这些女性组成的群体中,无论是劳模、大学生还是乡下人,阶层的差异被对时尚的追逐所擦抹,合拢在相对纯一的时尚共同体中。她们之间的龃龉与矛盾也多是围绕着对时尚的攀比,而她们的团结也因对时尚的热爱与追逐而生。
在《万紫千红总是春》和《街上流行红裙子》当中,女性的情谊并不会受到男性的牵涉,展现的女性情谊在某种程度上是内向型的自足,是在同性群体内部的权利制衡,与外界沟通的是劳动与时尚。而在《闺蜜》当中,女性情谊发展的起落轨迹在与男性的关系当中,有着几乎同步的微妙嬗变。
在《闺蜜》当中,劳动作为情感的纽带已经不再发挥作用,时尚则更加日常生活化,不再具有单纯的审美作用,它比在《街上流行红裙子》中“联系”的作用更深一步,成了“阶层”的符号与划分——尽管这种区隔是自然而然并不被人所注意的。在《闺蜜》中,似乎是回到了最单纯却又最复杂的维度——情感。女性情谊不需要再借助组织与制度进行维系,“情感”拥有了“纽带”与“归宿”的双重身份。而这种情感所直接建构的共同体包含着爱情、友情、亲情以及其他别样情感的共融与杂糅。
影片的最开始就是Kimmy因为自己被男人甩而扬言跳楼,小美和希汶前来“劝阻”的故事,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三人友谊与男性之间绕不开的关系。接着,即将结婚的希汶却意外发现未婚夫林杰出轨,整个人陷入了神情恍惚的状态,此时Kimmy和小美担负起了照顾她的任务,做了很多无厘头的事情去鼓励她振作起来,并且Kimmy也略施小计为希汶与乔立牵线。总之,三个人的友谊因为男人的出走与进入而得到了牢固与深化。
然而到了Kimmy与小美之间,曾经发挥黏合作用的男人却引起了友谊的地震。落拓而有魅力的九天成了她俩追逐的对象,平日低调卑微的小美获得了九天的青睐,而万人迷Kimmy却在竞争中败北,引发了两人关系中位置的挪移,打破了曾经高低的平衡。而Kimmy明白九天并非安定之人,并不能给小美幸福,所以她采取了直接色诱九天的方式,让小美放弃,而小美却认为Kimmy看不得被超过。这大概是整部电影当中女性情谊破裂的高潮时期,实际上也是众多女性情谊当中的经典桥段,这里揭示出了存在于女性之间情谊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在Kimmy、小美、希汶的女性情谊当中,“分担”苦难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正如“我们也想分担你的难过”“他不配,因为你是最好的”“我们永远都在一起”,这是以悲情的画面营造温馨的、和谐的氛围,在共同对男人的敌对当中完成了友谊的深化与升华;她们同样也有内在于女性群体的狂欢,例如一起去奢侈品店血拼、一起参加《女人那话儿》拍摄中的疯闹、在餐厅中当众卸妆的玩笑、在KTV里的狂嚎……就这一点而言,女性情谊也在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当中得到了另一面的完善,女性既不是温柔的、贤惠的、文静的,也不是朴实的、健硕的、政治的,而是独立的、坚强的、时尚的,敢玩敢闹敢闯,同时也是非政治的或去政治的。这种对于女性之间结盟的讲述能够获得相当不错的票房,并被很多女生所喜爱,源于“感同身受”。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年轻的观影群体大多是独生子女,她们的成长伙伴不再是同一家庭中的血亲,而是同一小区的邻里或者同学等。这种交往比之兄弟姐妹之间的交往更具社会性,也正因如此,女性情谊的发展便包含了诸多的层面,亲情的成分融入到了友情之中,彼此之间分享甚至“独占”的情感也在这一代得到了更多的重视,继而女性共同体的核心构成就是裹挟着爱情、亲情、友情的“情感”组合。
不同于《万紫千红总是春》当中的“家庭妇女”、《街上流行红裙子》中的“工人阶级”,《闺蜜》里的女性有着“城市中产(上层)阶级”的身份,社会“劳动”与“时尚”已经自然化在女性的社会与个体生活之中,不再具有统摄全局的魅力,巨大的能指逐渐回归语词的本义。与此同时,曾经被遮蔽的细微“情感”在这一时期被再度发现,这种对于情感的追逐,似乎是在回归“友谊”的本义,即相互之间的情感需求,以此来对抗消费社会/物质社会的人际冷漠。然而恰恰是对于情感的回归,这种不能量化的联系纽带固然会使女性情谊比以往更加紧密,并且呈现出了兄弟/哥们儿的江湖属性,即女性之间的情谊不再局限于闺中,而是走出“绣花”“缝补”的幕布,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公共空间之中,与此相伴的也是女性生存与活动空间的变迁;但是这种感情倾向性的女性情谊,也潜伏着诸多的问题,即情感的复杂性,正因为对情感的投入更多,内里的层次也更丰富、内心也会更为细腻。同时,一般认为女性气质也更偏向于感性与细腻,使得在女性情谊当中任何一种行为都可能被细致地解析和无限放大,由于语言、动作、表情等在传达过程当中难免的信息缺失与偏向,解码会造成一定的曲解与误读,也就造成了女性情谊中的矛盾。
女性情谊所包含的不同面向在《万紫千红总是春》《街上流行红裙子》和《闺蜜》三部电影当中,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作为精神共同体的女性群体中的核心要素,与时代特色与旋律密切相关:50年代的“劳动”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同构关系,同时也与女性的解放运动联系紧密,女性共同体的构造在自我解放的目的中成为可能,而自我解放的途径则是参与社会劳动,从单纯的家务劳动当中解放出来,在这种诉求当中,女性被黏合在一起。80年代的“时尚”在“新时期”的同步当中,体现了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从“不爱红装爱武装”到“街上流行红裙子”,“红色”从革命的引喻转向了“时尚”,而“时尚”的另一层含义是现代,这种女性共同体的偏移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与时代同步的现代化。
三、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女性情谊如何可能
在《“姐妹情谊”如何可能?》之中,魏天真通过对女性作家、女性主义者之间脆弱“情谊”的分析,对姐妹情谊进行了怀疑,在“共在”的层面上提出了解决的可能思路,虽然她并不乐观。对此她尝试给出了答案:“因为某种深刻的相似或一致,人们(女性)之间才会彼此需要互相依存,而互相依存的人们之间也会出现对峙和恐惧,对峙和恐惧往往又产生于太过的相似或一致。”[9]或者说“要形成阵营及其力量,女性整体的同一性是必要的,而作为个体的人,又追求独特、独立和精神的丰富性”[9]。这似乎指出了女性情谊的悖论,即个体性与整体性之间的关系。但也正是从这样的龃龉之处入手,才有了解决女性情谊发展的可能性。
在《万紫千红总是春》中,戴妈妈是连接这群女性的中心,是这个女性共同体的“管理者”,她不断地发表演说与进行劝告,维护并扩大这一共同体:“大家很早就希望为社会主义建设献出一分力量,现在,这个希望可以开始实现了。我们要用集体力量安排好生活,安排好家务,根据各人的条件和志愿,参加生产,为社会主义加一块砖,添一块瓦。姐妹们,我们的力量是很大的,相信一定能对国家的建设做出贡献。”莫里斯·迈斯纳指出“大跃进没有具体的蓝图,它不是一个类似于五年计划的经济计划,而是一种乌托邦社会观的产物”[10]179-180。这种构造的乌托邦性质,在某种程度也展示了《万紫千红总是春》中女性共同体的某种想象性,虽然电影将其进行了政治寓言式的转移。在这段演说当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集体力量”的重要意义,固然闺蜜情谊本身就涉及两个及其以上的个人,而这也构成了一个“集体”,但是有意思的是,“集体”本身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所具有的独特意义。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集体在建构50年代女性情谊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即此时的女性情谊是通过集体进行抒写的。
在《街上流行红裙子》中,这群工厂女工的“共在”性在于她们对于时尚的追求,从白衬衣、蓝裤子的标准女工打扮转向了各式各样新潮的衣服,这个群体分享的信息集中在新的服装面料、新的服装款式,由此构成了集体性的时尚狂欢。游离在这个集体之外的是具有劳模身份的陶星儿、想要成为大学生的葛佳和乡下人阿香,只不过陶星儿的被排斥在于她对于时尚的迟缓态度与在工作上的积极态度,阿香是极力地跟随时尚甚至带领时尚却窘于她的出身,而葛佳是不屑于融入这个关注时尚的群体。她们三者的个人性成为她们的脱轨之处,同样也是在一起穿红裙子进行斩裙的过程中得到消弭与缝合——但是这种改造并没有消磨掉她们本身的个性。
《闺蜜》在现实意义上给予我们思考女性友谊的维度。在社会劳动、时尚已经完全日常化,女性获得了自足的经济收入与情感需求的时候,女性情谊如何避免在这些独立而个性的女性中夭折,成为一个世纪性的难题。社会化的女性,所面临的是更为复杂的女性情谊的困境,这群女性在青少年时期生活在集体之中,但同时随着社会变迁与教育思想的变革,对于“个性”有着更为强烈的追求,集体与个人之间的问题贯穿在成长的每一个时段,同样也存在于女性情谊的萌芽、发展、深化与完结的各个时段。单偶制的婚姻模式、女性社会性深度的不断挖掘等导致女性也参与到对配偶的竞争之中,所以形成的女性群体往往是规模较小的“闺蜜”,彼此分享秘密、共担苦难,并且同时一致对外地维护小团体的利益,维持作为集体的完整性与权威性;但同时,也要警惕内部的矛盾与不平衡,彼此之间也要保持相对的个体性与独立性,尤其在事业、爱情上。
因此,女性群体具有特殊性,她们既不像一个阶级,并没有在同样的工作和生存条件下与另一个阶级对立,也不像一个家族、民族或种族,使得她们能够获得安全感并且皈依[9]。她们由于自身身体的条件限制,天然地呈现出对于集体的需要,集体是汲取温暖、能量之源,也是释放压力、不满之处,同时这种女性的结盟也成为抵御与对抗其他群体的大本营,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也能发挥作用。但过度地依赖集体也会使得内部积攒冗余的能量,导致关系的失衡,这就需要女性从自身挖掘潜能——这种潜能基于女性个体的充分发展,即精神的、物质的自足,并且在小集体的发展当中能保持个性,或者说,这种个性能为固化的群体结构提供新鲜的信息,以维持女性共同体的不断发展与牢固。
总之,20世纪50年代的《万紫千红总是春》、80年代的《街上流行红裙子》与新世纪初的《闺蜜》同样将视野投向女性友谊的抒写,但因为时代的原因,文本重心发生了位移,女性共同体构造的核心因素呈现出了由劳动向时尚再向情感的偏转。在对这些迥异的女性共同体的分析中,左右女性之间微妙情感的主题与女性特质、时代情感及国家政治相互印证[11]。它揭示出了一种女性和解而成的“女性情谊”的可能之路,即在集体与个人之间寻找到平衡点,既能够在作为集体的女性同盟中友爱和睦,获取能量,同时也能够不被集体所束缚变成平庸人的复刻,发展出个体性的品质,成为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时代化的女性形象。
参考文献:
[1] 余殊.《闺蜜》:七夕“姐妹淘”[J].中国电影市场,2014,(8):6-7.
[2] 何晓诗,鲜佳.闺蜜电影:题材多元 定位精准[J].中国电影报,2014-07-18.
[3] 阳翰笙.《万紫千红总是春》座谈会[J].电影艺术,1960,(5):2-14+54.
[4] 蔡翔.《万紫千红总是春》:女性解放还是性别和解——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之四)[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2):55-58.
[5] 沈天水.慕“名”而来,失望而归——《街上流行红裙子》片名质疑[J].电影评介杂志,1985,(5):1.
[6][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 徐勇.20世纪80年代城市电影中的空间呈现和文化政治[J].当代电影,2014,(4):72-76.
[8] 李岩. 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教育伦理观探析——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对大学教师的启示[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6(1):80-83.
[9] 魏天真.“姐妹情谊”如何可能?[J].读书,2003,(6):88-92.
[10]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杜蒲,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
[11] 杨文臣. 生命意识与女性意识——论傅爱毛的小说创作[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5(1):102-106.
(责任编辑:金云波)
收稿日期:2016-04-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YY110)
作者简介:韩煦(1992—),女,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6)04-011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