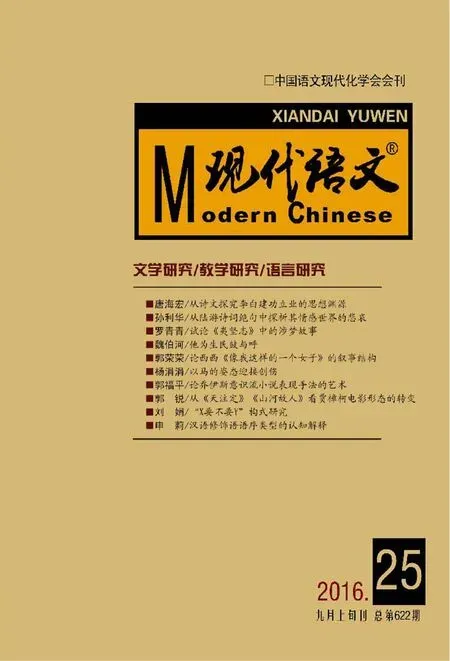风景与反省
——论苏童《黄雀记》
○候迎迎
风景与反省
——论苏童《黄雀记》
○候迎迎
在《黄雀记》中,苏童试图减少对风景人物的个人干预,用冷静的笔调描绘细节,呈现香椿树街上的日常生活画面,让人物呈现其生命自身的一种缺失。自然风景是苏童苦心经营的意象世界,不是以背景的形式出现在人物的视野中,而是人物存在于这一自然中,自然以客观的眼光来观看生活于其间人们的悲欢离合。人物无法摆脱自身所生活的那片土壤带来的桎梏,被困于“现实生活”这个巨大的阴影下,挣扎于其中,迷失了自我。苏童以不动声色的笔触,细细描绘日常生活细节的真实与残酷,同时也折射出的对现实和人性的关怀与反思。
黄雀记 香椿树街 风景 反省
2013年,苏童推出新作《黄雀记》。有人说苏童借助这本书重返香椿树街:也有人质疑苏童,三十年来始终被困于这条狭窄的香椿树街走不出来,到底有什么意义?苏童自己的解释是:“其实,这条街,我从未离开过。我描绘勾勒的这条香椿树街,最终不是某个南方地域的版图,是生活的气象,更是人与世界的集体线条。我想象的这条街不仅仅是一条物理意义上的街道,它的化学意义是至高无上的。我固守香椿树街,因为我相信,只要努力,可以把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搬到这条街上来。”[1](P125)在苏童三十年来的创作生涯中,他为读者奉献的关于南方生活图景的文字占其作品的一半以上,他致力于建构一个南方世界,但又不止于此。苏童的“野心”——把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搬到香椿树街上来,如何才能实现?他又是如何做的呢?
一、香椿树街的风景
张学昕多年来持续着对苏童作品的研究。他说:“其实,很早我就隐约地意识到,苏童最大的‘野心’,就是试图为我们重构一个独具精神意蕴地真正‘南方’。南方的意义,在这里可能会渐渐衍生成一种历史、文化和现实处境的符号化的表达,也可能是用文字‘敷衍’的南方种种人文、精神渊薮,体现着南方所特有的活力、趣味和冲动。与此同时,他更想要赋予南方以新的精神结构和生命形态,这些文本结构里,蕴藉着一种氛围、一种氤氲气息,一种精神和诉求,一种人性的想象镜像。”[2](P126)
南方的想象对苏童确实有股引人人胜的魔力。他的作品将一张张人事图画叠加在它所绘的那片景色之上,由此,二者连贯成无法区分开的整体。在《少年血》《城北地带》《黄雀记》等的“香椿树街系列”作品中,南方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南方阴郁的天空、炎热的阳光、阴柔的雨、香椿树街上古老残破的房子、浑浊肮脏的河流、简朴的善人桥、长满青苔的天井、废弃的码头、桥洞,堕落的茶馆,甚至是夜间出行的一只白猫,都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混合着文化、习俗和象征的氤氲,为读者的视网膜上的印象着上更深的墨色。
苏童笔下的南方小河,绝对不是静谧美好的象征,它不是一条清澈、湍急的河道,而是一条被工业垃圾肆意污染、漂浮着动物腐尸和拖着白色黏液的避孕套的肮脏河流,却仍是一条生命的河流。人在浑水中游泳、在粘稠的淤泥中打捞、也在泛着油光的河水中洗涤肉体和灵魂。这条河沉淀着香椿树街上生活的人们的集体记忆,同时也见证了个人记忆。《城北地带》中美丽的少女美琪在被红旗强暴后,不堪忍受流言蜚语,而跳入小河,成为一个带着水汽的绿色鬼魂,在香椿树街漂浮游荡;《黄雀记》中怀着身孕的仙女,在柳生被保润捅死后,被柳生家人指为幕后黑手,而被迫逃进肮脏的小河“洗一洗”。她们认为这条小河可以洗掉她们的不幸和灾难,但令人怀疑的是,香椿树街上的这条未命名的河,恐怕不能将人物从自身的罪孽中解救出来。在那里,人是河流的俘虏,而非主人。正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它亦慈悲亦残忍,流动着令人不安的双重性。那无名之流了然人们所有的秘密,见证了人们的过去,无论这记忆是明亮还是灰暗,人们都要背负它,并且珍惜它。
“所有的街道都不可能静止不动,它在时间中变化,甚至消失。就像我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生活的那条街道,它如今已经面目全非,几乎无法辨认,但我很高兴,它活在了我的小说里,活在了我的文字里,依然在呼吸,依然还在生长。”[3](P5)香椿树街不是作为一个固定的背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时间中变化、模糊、消失、更新乃至面目全非,这是一条成长变化着的街道,它反映时代的变迁,注视着这条街上人们的生活变化。
水塔在《黄雀记》中反复出现,在不同时期被装扮成不同的样子,承受人们对它的改造,但并不能达成人们本来对它的功能期望。最初柳生安排保润在水塔与仙女和解,却变成了强奸案的案发地;之后郑老板出资,水塔被改造成香火庙,却激化了群众与郑老板的矛盾;然后水塔短暂地变成保润的宿舍,结果保润捅死柳生而回到监狱;最后水塔成为仙女和婴儿的临时避难所,但结果却是仙女留下婴儿出走。水塔一直是客观的自然景物,它不能像人一样理性思考,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但它反映的是人的存在,承载的是人们面对欲望时的不同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同样经历变化的还有保润的家。保润蒙冤入狱后,父亲中风去世,母亲离开去了省城,祖父依旧住在疯人院,保润的家散了。祖父的破房间被马师傅装修成了“香椿树街历史上第一家精品时装店”,后来变成养生连锁药店。保润家的门也从一扇变成半扇,最后变成仅容一人通过的窄道。马师母说:“凡是要从实际出发,迎街门面多金贵,你给保润留这么大一扇门,他又没机会走,不是浪费吗”?[4](P136-137)家门的空间,由于商业需要被不断压缩,看似合情合理,但代表的却是正如保润的面子和生存空间,不断地被残酷的现实挤压。
无论是水塔的变迁,还是保润的家门不幸;无论是祖父引领的香椿树街居民的掘金运动,还是爱看热闹的香椿树街居民自发围观仙女的行为,总之,香椿树街上的风景,是苏童苦心经营的意象世界,每一个意象都有它的丰富意蕴,它们作为与南方城市共生的一部分,不是以背景的形式出现在人物的视野中,而是人物存在于这一自然风景之中,自然以无动于衷的眼光来静观生活于其间人们的悲欢离合。
二、反省的姿态
在苏童一系列关于少年题材的作品中,导致少年们悲剧结局的因素中“胆汁质”无疑占了很大比例。他们很容易被激怒,而一旦被激怒便很可能陷入可怕的暴怒之中,既而产生轻率鲁莽的行动,造成不可收拾的悲剧。舒农、小拐、红旗、达生、叙德、保润和柳生以及美琪、仙女们,他们既是对抗自身命运的反抗者,也是酿成自身和他人悲剧的同谋者,同时也是青春躁动不安的牺牲品。或许正是这如炽焰般的奔腾血液和强烈的生命力,让生活在阴柔的姑苏城畔的苏童迷恋不已,反复书写这些少年。
保润不同于小拐、达生这样的街头暴力少年,他是香椿树街上一个不起眼的少年,不喜欢动手,努力和人讲道理。但他的目光却透露出怀疑、否定、混淆一切的破坏力,被秋红形容为一卷绳子,毫不自知地表现出对他人的冒犯,表现出对粗鄙现实的不满和敌意。保润的目光可以用孤傲与愤怒这两个词语来表达。尤其是对仙女爱意的反差表现,明明喜欢她,却用绳子捆绑来伤害仙女,但保润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伤人伤己的行为,因为在他看来,绳子是自己向仙女炫耀、示威、超越自卑的唯一出路,人与绳子变成了无法分开的整体,丢失了绳子,人便不再完整。躁动不安的情感表现呈现出一种向两端撕扯的紧张状态,身体已经本能行动,脑子却一片迷茫。虽然保润没办法很好地表达自己,容易被他人误解,遭受不公平的对待,但愤怒成全了保润的生命表达,要求社会和他人公平地对待自己。保润的怒、仙女的怒、红脸婴孩的怒,成为一种生命的情绪性表达,血液里奔腾的怒,这既是生命的活力,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不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冷酷的现实生活处处是陷阱,一步错步步错,连悔改的机会都不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黄雀记》是继《少年血》《城北地带》之后呈现香椿树街人们日常生活面貌的其中一环,构成“把整个世界整个人类都搬到香椿树街上来”版图中的一块,而且这块版图也不断扩展延伸。作品中加入了如孝道问题、香椿树街居民庸俗贪财、井亭医院这个各色患者的大杂烩,包括代表情欲和金钱的郑老板和代表权利的康司令等社会现实,反映出时代转型期社会的特点。苏童细细描摹日常生活细节,慢慢铺展故事情节,叙述语调更加平和、宽容,于平和冲淡中暗藏冷酷的批判与讽刺。发生在保润、柳生、仙女之间的这场强奸案,以及十年后的重逢,揭示了命运的残酷。十年后,保润原谅了仙女,可他最终还是在暴怒的冲动下捅死了柳生,完成了复仇这一个看似他“应该”完成的仪式;柳生“夹紧尾巴”想要从物质生活层面补偿保润,可最终还是没有救赎出自己;仙女一直想要挣脱自己的命运,却迷失了方向。他们清算了别人的账,却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魂,被一条无形的命运之绳牵着走。
葛红兵以鲁迅等启蒙作家为参照,认为“苏童常常不能为自己笔下的人物的遭际提供一个社会性的解释,苏童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宿命的。”[5](P474)苏童就不是拯救者,更不是道德说教者,他没有站在道德角度,以启蒙者的姿态评判笔下人物的对与错。而是试图减少对风景人物的个人干预,站在这些东西之外,用冷静的笔调描绘细节,呈现记忆中复杂、丰富、富有意味的生活画面,观看并重新发现我们早已拥有却忽视的东西,让人物呈现其生命自身的一种缺失。人物无法摆脱自身所生活的那片土壤带来的桎梏,无法跳出自我去观看,只能徘徊在内在经验的心理表层,被困于“现实生活”这个巨大的阴影下,挣扎于其中,且迷失了自我。苏童不动声色的笔触下,细细描绘日常生活细节的真实与残酷,同时也折射出对现实和人性的关怀与反思。
至此我们才能明白,小说结尾怒婴安静地依偎在祖父怀里,其实是一种寓言式的姿态。苏童说:“忏悔与反省的姿态很美好,那是我所能想到的最恰当的面对过去的姿态。这个姿态,可以让一个民族安静地剖析自己的灵魂。这个姿态,还有可能带来一个奇迹,让我们最真切地眺望到未来,甚至与未来提前相遇。”[6](P126)可是,在这个姿态中,我们不禁担忧,丢了魂的祖父和还没有自我意识的婴儿,有没有忏悔和反省的能力?少年陷在粘稠的血液沼泽中躁动不安,忏悔的姿态在他们眼里只是柔弱的驯服,即使低头也只是暂时的妥协。那些需要忏悔和反省的人们,他们又在哪里?结尾中表现出的平静姿态或许只是苏童个人的一种美好愿望,以此来缓和这部作品带给我们精神上的逼仄之感。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安静缱绻孕育着雷电暴雨的撕裂,人生的残酷让人唏嘘无奈。生活充满了偶然,但一切偶然又有潜藏的因。暴躁的血液、危险的气息、无知的推演,把人步步紧逼到无路可退的死角。有时命运就是这般倔强、不可扭转,可同时也充满了力量。生活在香椿树街上的人,顽强地面对惨淡琐碎的日常生活。这就是藏污纳垢的香椿树街生生不息的奥秘。
三、结语
《黄雀记》是苏童送给自己的五十岁生日礼物——重返香椿树街,保持记忆,向过去致敬,然后重新出发。“重回”香椿树街,是对一种公共资源的重新建构,把现实隐藏在隐喻背后,用一种更加细腻的形式,来表现对日常现实生活持续的关注度和敏锐的现代感受力。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苏童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创造香椿树街这条“堕落”的南方街道的用意——以其忏悔和反省的姿态告诉我们如何与未来遇见。“放弃罪过往往需要我们对过去进行毫不妥协的审视并发现它其实是一份未曾被公布的记录,里面全是一些荒唐、不光彩的事。人类过去的一切,一代又一代,就像季节的缓慢更迭,形成了滋养我们未来的养料。我们就是以此生活。”[7](P671-672)
注释:
[1]苏童:《我写〈黄雀记〉》,鸭绿江(上半月版),2014年,第4期。
[2]张学昕:《苏童:重构“南方”的意义》,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
[3]傅小平:《苏童:充满敬意地书写“孤独”》,文学报,2013 年7月26日。
[4]苏童:《黄雀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5]汪政,何平编:《苏童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苏童:《我写〈黄雀记〉》,鸭绿江(上半月版),2014年,第4期。
[7]胡淑陈,冯樨译,[英]西蒙·沙玛著:《风景与记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候迎迎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