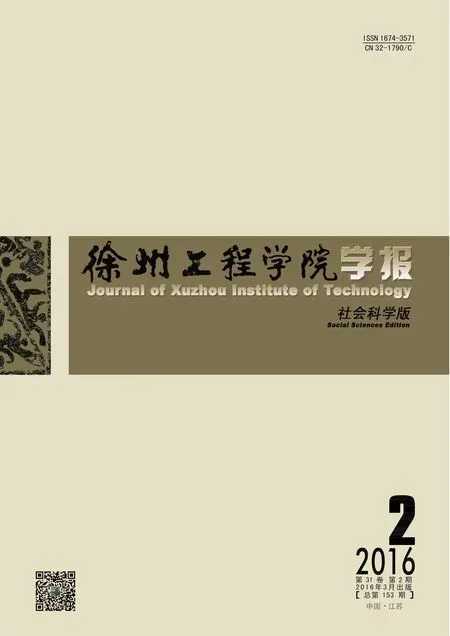论太虚大师对抗战与守戒的调适
韩焕忠
(苏州大学 宗教研究所,江苏 苏州 215123)
论太虚大师对抗战与守戒的调适
韩焕忠
(苏州大学 宗教研究所,江苏 苏州215123)
摘要:太虚大师从义理的角度对不杀生、不干政、不入军阵等佛教的基本戒律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以使其能适应僧尼参加抗日的实际需要。他依据《瑜伽菩萨戒本》等对不杀生戒进行了必要的调适,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活动中,表现出极高的政治热情。太虚大师从佛教重视慈悲的立场出发,调动了出家僧尼保卫民族、参加抗战的积极性,数十万出家僧尼在抗日战场上从事救伤、护理和掩埋阵亡将士尸骸的工作,将中国佛教的命运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民族的振兴中谋求自身的发展。
关键词:太虚;抗战;守戒;调适
古语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具体到每一个公民,因社会角色不同,其所尽责的方式方法自然就会有诸多的差异。佛教徒如何在国家振兴和民族繁荣中尽到责任,这是个非常重大的课题,一时不易阐明,我们不妨以太虚大师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如何引导广大僧众积极参加抗战、尽到救亡图存之责任,来看一看广大僧众是如何以佛教义理为依据而服务于国家振兴和民族发展的。
佛教的戒律应随时代因缘有所变化,是谓与时俱进,使佛教获得契理契机地发展,而不能泥古不化,拘执于教条。太虚大师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对佛教戒律进行的调适为此提供了充分的佐证。佛陀制戒,规定比丘不得杀生,不得结纳权贵参与政治,不得故往观看军事操练,不得无故出入军阵之中。如上诸事,若自作,若教他作,见作随喜,皆为犯戒,或失比丘或比丘尼身,或有大过错。这些戒条在出家僧尼的心目中可以说根深蒂固,对广大的佛教信众也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从而使佛教成为一种非暴力的和平宗教。然而进入1930年代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乃至最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将中华民族逼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也将广大中国僧众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存亡续绝的关键时刻,广大民众是迫切希望中国僧尼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之中来。一者,中国的僧尼数量庞大,将近有百万之众,若将他们调动起来,自然是一支非常可观的抗日力量;二者,近半数的中国人民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佛教的影响,如果僧尼参加到抗战的话,将使广大佛教信众或对佛教有好感的人们增强民族危机意识,从而激发出更加热烈的抗战积极性;三者,当时的佛教寺院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财富,僧尼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也可以加强抗日救亡运动的物资供应;四者,中国僧尼积极参加抗战救亡运动可以破除日本的侵略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他们的侵华战争辩护说:“中国已赤化或耶教化,佛教已被灭,日本为保护佛教及东方文化,向中国作神圣的战争,所以凡信佛的国民都应与日本站在一条战线上以对付中国。”[1]221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这套说辞是很恶毒的,它既可以激发佛教信众占半数的日本国民的参与侵华战争的热情,又可以在中国佛教信众与中国抗日民众之间制造猜忌和分裂,还可以使一些佛教国家对中日之间的战争持观望甚至亲日的态度。如果广大的中国僧尼参加到抗战中来,这些反动宣传就会不攻自破。
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的佛教界也有多方面的考虑。鸦片战争以来,外来宗教借助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中国大肆传播,造成佛教信众资源的严重流失,中国佛教界也与中国人民一道饱尝了外来侵略之苦;晚清以来,中国的危机日趋深重,人心思变,社会精英每讥佛教为“迷信”,僧尼为“寄生”,时不时地“占寺、提产、逐僧”,开展所谓的“庙产兴学运动”,在全民抗战的紧急关头,佛教界如果继续坚持闭门清修的话,无疑将授人以口实,以致在抗战胜利后的社会生活中将更加没有地位;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日本帝国主义虽以“保护佛教”作为侵略中国的藉口之一,但对交战区域的中国寺院和僧尼同样实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中国僧尼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面对这些兽性大发的侵略者,或出于本能,或激于义愤,即便是无人号召,无人组织,他们也会自发地采取一些抗日行为。
无论是从全国民众的殷切期望来讲,还是就佛教界自身的感受和考虑来说,中国广大僧尼都必然地要加入到抗战救亡的洪流之中。但战争是极端残酷的,僧尼参加抗战,即便不是直接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但不可否认会鼓励同胞去努力消灭敌人,会对我方的胜利和敌方的伤亡而欢呼雀跃,前者近于“教他杀”,后者则似“闻杀心喜”,都与佛教的基本戒律相违背。因此,必须从佛教义理的角度上对不杀生、不观操、不入军阵等佛教的基本戒律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使其能适应僧尼参加抗日的实际需要。太虚大师作为当时僧界的领袖人物,就对此进行了艰难而卓有成效的探索。
香港中文大学学愚教授的《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一书对当时佛教界如何调适戒律有很丰富的研究,本文则专门探讨当时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太虚大师的相关思想。此处所谓的抗战,并非单纯指通常意义上的抗日战争时期,而是泛指20世纪上半叶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反抗。
一、对抗日战争的看法
太虚大师站在佛教的立场上,认为极少数日本军阀忘恩负义,贪嗔痴慢恶性发展,不惜给中日人民造成极重的灾难,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正义的,因而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太虚大师对抗日战争的总看法,也是他对佛教的相关戒律进行义理调适的思想基础。
太虚大师非常珍惜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形成的深情厚谊,对极少数野心家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深感痛心。民国二十四年(1935)11月,他在《觉乎否乎可以觉矣》一文中不无动情地说,中日两国比邻而居,一衣带水,亲若兄弟,迭为师友,共同受到儒佛仁慈智慧的熏陶和滋养,相互间本来是可以在情感上“道义相孚,感应以诚”,在经济上“褒多益寡,胹合调济”以达到“和融靡阻”的。但是,他话锋一转,极为沉痛地指出,“乃因日本仿效欧美有一日之长,少数之野心者师其掠夺之惯技,竟视中国国民为刀俎上肉,一割而台湾,再割而高丽,近年侵及东北,四省沦亡,乃益进逼不已,时临以不测之威而骇慑全国民,逞兹可已而不已之强暴”[1]142。太虚大师以慈悲为怀,希望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家们能及早醒悟,不要将中国逼上绝路,“日本之少数野心者,若及今犹不猛然醒觉,系铃解铃,求日华民族感情之好转,犹自恣横行不已,则势必造成全中华民族对日本民族之仇视,力事报复,苟不能将中国人尽灭,则令日本永无宁日,而在人间亦不知更增加若干之杀机戾气”[1]144。太虚大师以哀悯之心,对那些发动侵华战争的少数野心家提出警告,衷心希望他们能适可而止,犹不失为一转圜之余地,但那些痴心妄想的军阀们已将中国视为送到嘴边上的肥肉,怎肯轻易放手?他们不断地制造事端,进行武装挑衅,最终在1937年7月发动了企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
太虚大师对少数日本军阀的忘恩负义极为痛心。在他看来,中国不仅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而且也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集大成者,日本所谓的古代文明,就是传承于中国的儒佛二教,因此中日两国有同洲同种同文之谊,可以说,中国在历史上是曾经有大恩德于日本的;近代以来,日本率先强盛起来,而中国也在进步之中,两国本应当携手同行,共同致力于建立国际新秩序,为人类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但是,“乃中国以毁弃本根袭取皮毛之错误,造成割据之内乱;日本专学会帝国主义侵掠以分裂蚕食中国为事,致演为现今日本生里求死、中国死里求生之死生相搏惨状!”[1]159对于这本不应该发生的人类悲剧,太虚大师的悲悯之情溢于言表。民国二十八年(1939)八月,他在昆明作《欢迎印度民族领袖尼赫鲁先生》一文,其中说到:“日本乃为中国赋以形,印度传以神,始脱其野蛮,得成为一文明民族。然甲午一战而胜后,其一部分操纵国权之军阀,发其野蛮本性,染于侵掠时习,窃得近代之科学绪余,立定征服中国之恶心,专造独吞东亚之恶业,因是造成近数年来中国被寇之滔天大祸。此其所为,不惟蹂躏荼毒中国全民族,及伤害全世界人类正义公道之情感,亦实将自颠覆其千三百年立国之基本,沦陷日本全民族于野蛮悲惨之境地!”[1]196-197因此,他希望曾经是日本之师保的中国和印度联起手来,对这个不肖子弟以重大教训。
在太虚大师看来,中国的抗战建国,就如同释迦牟尼佛的降魔救世。就佛教而言,佛必须降伏魔军,始可以成道救世,这与中华民族必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毫无二致。因此他说:“抗战建国,与降魔救世的宗旨,不但不相违,而且是极相顺的。……故中国抗战,乃是为除掉战争,止息战争,而起来抵抗于战争。故抗战的本质,是自卫的,和平的,为保卫全国人民及世界人类正义和平幸福而发动的。现在中国人,为外来侵略之恶势力的战争行动加害于中国,中国为国家民族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之为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1]171-172故而要显扬佛法,不但不能降低抗战精神,反而更应该促进抗战精神。因此,他坚信,在抗战中宣扬佛法,是能够促进抗战精神的,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他在《日伪亦觉悟否》一文中指出:“中国之抗战由日本弃和平解决方法而不用,突以武力进攻所迫成,其目的在求民族之独立与国家之自由平等,不达不止。此不惟理事昭然,而最近亦已在战场表现相当之抗战能力,确有达到胜利的把握。”[1]160就是说,太虚大师抗战必胜的预言不仅来自对正义的信仰,也来自中国军民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和坚韧毅力。
太虚大师还意识到,日本少数野心家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侵华战争,除了日本首先强盛起来之外,也是中国自身的原因所招致的一种恶果。他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月所作的《劝全国佛教青年组织护国团》一文中说:“国难的发生,根本是因于国内在位在野人众的失道悖德之所致。”[1]71他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在北碚三峡试验区演讲《新中国建设与新佛教》时也指出:“中国以五六十年来曾屡有良好的机缘,容许振作,固不应使现在有受痛苦之可能。但以前人思想错谬,虽早接触西洋文化,以无根本改进计划,唯认为购些军舰、大炮便足,致一误再误,现受恶果。”[1]1201这表明,太虚大师以宗教家特有的意志力,在全国抗日情绪日趋高昂的历史时期,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清醒状态和自省意识。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国难日亟,“外有强邻的陆海空军相威逼,更有其他的列强,用种种手段来压迫中国,使中华民族无复兴之日,且迫令走上灭亡的途径!”[1]124太虚大师号召佛教信众,特别是广大僧伽,应感念国恩,积极护国,他说:“国家对于吾人有保护教育恩,故吾人当献身国家而报之。人类固由父母为发生增上之因,然亦由社会互助而得存立,但是在社会矛盾紊乱之中,则吾人不能生存,故必有国家之组织,庶众生有所保障,社会得有秩序,而吾人始能于安宁中过生活。此无论信佛与否,皆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故吾人当有爱国之思想,而不容自外也。”[1]68为此,他从义理上对佛教的相关戒律进行了必要的调适,以便于广大僧尼更好地加入到抗日护国的行列之中。
二、对不杀生戒的调适
佛陀制戒,严禁佛教信众,特别是出家僧尼,不得杀害有情众生之生命。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不杀生的戒律立足于众生平等的佛教义理,体现了佛教慈悲为本的情怀,保证了僧尼不因杀生(特别是杀人)而受到国法的惩治,并将其视为佛教作为非暴力和平主义宗教的特质所在。但在一些大乘佛教的经典中,如《瑜伽菩萨戒本》等,则对不杀生的戒条在特殊情况下有所开许,这就为太虚大师在抗日救亡的时刻对佛教的不杀生戒进行义理调适提供了依据。
太虚大师常自谓“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在此《瑜伽菩萨戒本》中,就有对菩萨慈悲杀生的开许。如经文中说:“谓如菩萨见恶劫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或复欲害大德声闻、独觉、菩萨,或复欲造多无间业。见是事已,发心思惟:我若断彼恶众生命,堕那落迦,如其不断,无间业成,当受大苦,我宁杀彼堕那落迦,终不令其受无间苦。如是菩萨意乐思惟,于彼众生,或以善心或无记心,知此事已,为当来故深生惭愧,以怜愍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1]374太虚大师对此解释说:“大菩萨为利生故,毫不为自私自利,亦可权巧方便而开少分;然须地上菩萨智慧力强,善思决择,乃能正行。如有盗贼伤害有情,乃至声闻、菩萨、弒父、弒母、出佛身血,将造五无间业,菩萨见已起怜悯心,愿自堕那落迦——地狱——而不令彼无间业成。以大悲心,无瞋恚意而杀于彼,生多功德。”[1]374为了将杀害降到最低,菩萨出于慈悲,可以将施害者杀死,此处对菩萨慈悲杀生或一杀多生虽然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但毕竟开放了一条空隙。经文又说到菩萨见到官吏强暴、盗贼劫掠、僧伽或窣堵波物被侵夺等,都可以出于怜悯之心,依据自己的能力,采取暴力的手段,对这些恶行的主体或废黜,或夺取。太虚大师对此解释说:“如有君主、官吏以及恶霸、土豪暴虐无道,剥夺民财,妨害道路,掳掠行人,菩萨见已,痛念有情,吊民伐罪,孰曰不宜!或知彼是塔寺僧物,在家众物,夺为己有,姿意受用,菩萨方便,施以强力,取还原处,不名犯戒,反生功德。”[1]375这一点颇与中国固有的除暴安良之侠义精神相符合。对于这部《瑜伽菩萨戒本》,太虚大师不仅多次讲说,而且还将其作为他执掌的佛学院通用教材,鼓励弟子们进行深入研究,真切实践。
太虚大师认为,大乘佛教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运用到国际事务中,就是“和平为体,反侵略为用”,或者换言之,就是“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他以佛教寺院为例,“就佛教方面来说,最显而易见的是寺里面的佛像,寺门外两旁列着武装的金刚,前殿两旁有武装的四大天王,更后又有朝向正殿的武装的韦陀,这都是表示一种武力的防御,就是表示了能守的佛力。同时,前殿有向外坐的欢喜相的弥勒佛,后殿有向外坐的慈悲相的释迦佛,表出佛教设化救世的精神,更以佛法感化人类,攻去他的暴恶心,唤起他的同情心,也就是一种文化的进攻”[1]210-211。其言下之意,即便被视为佛门净土的寺院,都如此重视武装的守护,更何况处于强敌入侵中的国家!因此他主张,那些真正发心修学菩萨行的佛弟子,在山河破碎的关键时刻,应该现出威猛之相,“一切大乘佛菩萨,在密宗中,皆现起武装威猛金刚之相,以甚强威力,降伏烦恼,止息恶行,成就善行功德,摧折恶魔势力。一切佛菩萨,悲智为本而发金刚猛威之力,为大乘降魔之最高精神表现,亦即抗战之最高精神”[1]173。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不尽的烦恼,广大佛教信众与全体中国人民一道对之进行不屈不挠的武装抵抗,不过是大乘佛菩萨在降伏魔怨时所现的一种忿怒相罢了!
在太虚大师看来,日寇肆虐,国难当头,就是佛教戒律开许菩萨慈悲杀生或一杀夺生的特殊情况,因此,广大佛教青年应破除对守戒的顾虑,积极地参军入伍,运用各种手段去消灭来犯之敌,降伏魔怨。他说:“护国的工作,固然在国民各于其所处的地位所操的职业上,各尽其适宜的劳力;但从军终是护国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不惟建设现代国家必须有现代军事,就专为自卫而抵抗强暴的外寇侵压,现今有志护国的佛教青年,亦应有从军的需要!何况我们的佛教青年,原是遍在军、政、商、学、农、工各界的!”[1]74-75在家的佛教青年固应该加入到军队之中,去与来犯之敌作殊死的搏斗,以卫护国家免于沦亡,人们免于杀戮,即便是那些出家住寺的僧伽,其中很大一部分,也应去参加军队。“现今全国中数十万的寺僧,除开决志可为学僧、职僧、德僧的和老幼病废的以外,其余壮健的僧众,既不能为纯正的住持佛教僧宝,与其混在僧伽内污损佛门,倒不如全数去为国牺牲,从军抗暴,这实在是于教于国两俱有益的。至于能为学僧、职僧、德僧之住持僧宝的,那是自当专就其弘法利人的本务,以宣教、拯伤等工作,致其护国的劳力。”[1]76部分僧众参军打仗,固是在护国,继续住持僧宝者宣教、拯伤也是在护国。换句话说,在太虚大师看来,无论是参军还是继续为僧,都应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力卫护国家。
学愚教授在谈到宗教仪式具有鼓舞士气的作用时曾经说:“庄严而诚敬的宗教仪式给人一种神圣的力量,使人产生一种信仰般的信心,帮助克服一切人为的困难。作为精神和道德师表的出家僧众,他们的言行会对信仰尊敬他们的在家弟子产生深远的影响,乃至改变其生命。他们所主持的佛教仪式增强了军人的正义感,消除了他们心灵上的不安。当这些军人受到佛教仪式的洗礼,得到出家僧人的祈福,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也就不会或很少会在心灵上产生恐惧和行为上产生退缩。”[2]168
太虚大师作为当时广大佛教青年信众所崇敬的宗教领袖,他对不杀生戒的义理调适,对于那些走上抗日前线的佛教青年,特别是僧青年们来说,具有与此相同的宗教意义。
三、对不干政戒的调适
佛陀临灭,告诫弟子云:“不得参预世事,通致使命,呪术仙药,结好贵人,亲厚媟嫚,皆不应作。”[3]1110此即不准弟子结纳权贵,干犯国政。今天看来,大概是佛陀意识到,如果他的弟子们与某位权贵或某个王权结合得过于紧密的话,那么在宦海浮沉与王权更迭变幻无常的时刻,将会给他创立的教法带来灭顶之灾,而置身事外,就会使佛教获得超然于一切世俗利益之上的优越地位,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和殉葬品。在宗教超越于政治之上的古代印度固然如此,即便是在佛教必须依附于王权的古代中国,那些“不慕荣利,萧然世外”的高僧,还是深受帝王将相及广大佛教信众的尊崇,因此才有“爱僧不爱紫衣僧”的说法。但近代以来,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住持佛法的高僧大德如果继续逍遥方外、不问政治的话,佛教的利益就会成为任人宰割的俎上鱼肉。太虚大师顺应时代的发展,为了维护佛教的根本利益,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极高的政治热情。
太虚大师与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蒋介石关系非常密切,他将护持佛法及带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蒋介石的身上。1927年8月,蒋介石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受挫,被迫通电下野,回到老家浙江溪口,次月,他邀请太虚大师共游奉化雪窦寺,二人长谈竟夜,由此结交[4]130。太虚大师每以佛教领袖的身份,对蒋介石亦多所支持,如1936年蒋介石五十大寿,太虚大师即提议全国寺院举行庆祝法会,念诵《药师经》,以此功德,回向给蒋介石[4]225;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拘,太虚大师呼吁全国僧尼祈祷蒋介石平安[4]226。太虚大师将蒋介石视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继承人,号召全国的佛教信众支持和信任蒋介石的领导,对于巩固蒋氏的地位,亦有重大作用。太虚大师在新加坡撰文称扬蒋介石说:“蒋为第一流军事家,在庐山集训军官时的演说,早已预见到近三年抗战的情状,绝非日本现在的任何军人能企及。既有远见又有坚强意志,未发动抵抗则已,一发动后,自必抵抗到底,岂能被日本兵威所屈!且蒋在率领国民革命军奠都南京以后,虽几经退职,不旋踵即重起,已见他为全国唯一重心,离他不可。至二十一年后,他的刻苦耐劳,竭忠尽智,以为国为民服务,取得全民及海外华人之一致钦服。尤其‘七七’抗战之后,不唯成为中国国内军民大团结的最高领袖,且亦为国际所信仰的伟大人物。”[1]3401943年,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太虚大师在汉藏教理院发表演讲,认为这是一件特别值得庆贺的事情。他说:“中国近十几年来,无论军事、政治等,能有一个中心的力量,对外抗战,乃至使战事稳定,取得国际的同情等等,都是蒋主席努力奋斗的结果——所以国民革命军自北伐到现在,中华民国已有光明的前途。现在就任国府主席,不但是他个人实至名归的荣誉值得庆祝,也是全中国的独立自由乃至全人类的永久和平上值得庆祝的事。”[1]119也就是说,全国人民只要遵从蒋介石的领导,就能够实现抗战的最后胜利,使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我们认为,太虚大师对蒋介石的信任和厚望,实际上代表着当时广大中国人民对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富强的热烈渴望。而蒋介石在卫护佛教方面也确实曾给予过他极大的帮助。
虽然不能说太虚大师热衷于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政治活动方面确实是非常主动和积极的。如,抗日战争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太虚大师为此呼号奔走,他号召全国僧尼以各种方式参加到抗日运动中来,竭诚希望蒋介石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面对着国内军阀混战、国际世界大战的局面,他积极参加和平运动,为维护国内乃至世界的和平献计献策;为了反驳日本侵略者在东南亚各地的侵华宣传,他组织佛教南洋访问团,到各个佛教国家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蒙藏等边疆地区各民族皆信仰藏传佛教,他因此非常重视汉藏教理之间的融通,对发展蒙藏文化、巩固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加强边疆各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对于当时政府制定的各种有损佛教利益的法律法规及法令政策,他更是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方式寻求政治的解决,想方设法维护佛教的利益或者将佛教的损失降到可以承受的最低限度。也难怪佛教界内部会有些人讥讽他为“政治和尚”!太虚大师后来为自己辩解说:“世人又每以政僧讥余,然据孙中山先生之解释,政即众人之事,政治即管理众人之事,广义的管理众人之事,当无有过于菩萨僧者,亦唯‘菩萨僧’乃为真正的更无私事而专管理众人之事,故不同声闻僧少事少业少希望住,而剀切地表示须多事多业多希望住。余固未足为菩萨僧,然志愿所在则未尝一日忘学菩萨僧也;特患未能符政僧的名实,又何患世人之称为政僧?愿世之学菩萨学菩萨僧的佛徒,皆蹶然兴起,以共修此建设和平国际的菩萨大行!”[1]302-303也就是说,在太虚大师看来,热心政治活动,不仅不违背佛的戒律,反而正是大乘菩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普度众生的体现;他不仅不以作“政治和尚”为羞耻,反以之为荣,并且为自己未能真正符合“政治和尚”之盛名而不安。
太虚大师作为中国佛教界的光辉代表,在抗日爱国运动中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将振兴佛教与抗战救亡紧密结合起来,使佛教成为表述中华民族核心利益、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文化形态,在为国家和民族作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也为佛教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对不入军阵戒的调适
佛陀制戒,规定出家僧尼不得故往观看军事操练,不得无故出入军阵之中。盖军事操练及排兵布阵均是为了消灭敌人,出家僧尼故往观看或出入其中,可能会受到感染,产生乐杀之心,甚至予人以攻讦出家僧尼以策划杀人为事之口实,此类戒律也就因而具有了制止恶作、防护讥嫌的意味。太虚大师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自不能置身抗战之外,坐视国家和民族的沦亡,但作为佛教领袖,他又不愿所有的僧尼都上阵杀敌,他从大乘佛教重视慈悲的立场出发,认为僧尼可以接受救护训练,随军从事伤员救治、医疗看护、尸骸掩埋等工作,由此对佛教的相关戒律作出了适宜的调适。
民国二十六年(1937)冬,汉藏教理院学僧成立防护训练队,太虚大师作为创始院长发表训辞。他对队员们说:“佛法以佛菩萨之智悲为根本,以执金刚之威猛为方便。执金刚即为佛菩萨武装起来之变相。世有持诵金刚密法而于僧众受救护或防护等护国救民、护教救世之特训起疑沮者,正楞严所谓‘如说药人,真药现前反不能识,如来说为可怜悯’!盖根本失方便,则无以彰救人救世之用;方便本失根,则或丧失菩提善净之体。故在家佛子,虽可各随其职位以行事,而出家僧众之特组,则限于救护防护之训练。”[1]155-156在他看来,僧尼参加救护和防护的训练,是佛教的根本和方便的紧密结合,“国民与佛教徒之能刻苦耐劳与勤勇精进”,既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又关系着佛教的复兴,因此,他希望通过这次特训,能使广大僧众“矫正向来散漫放逸、怯弱萎缩之旧习,实现出整齐严肃劳苦勤勇之精神,本菩萨之智悲,去施行护教救世、护国救人之方便工作”,特别是作为他亲自教导的汉藏教理院学僧,“应比一般的禅林僧众,格外能吃苦、习劳、守规矩,并精勤学习众善功德,降伏止息一切恶魔害世害人之事”[1]156。也就是说,僧尼参与战场救护的特殊训练,本身就是大乘菩萨精神的体现,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犯戒的问题了。
民国二十八年(1939)八月,太虚大师出任云南僧众救护队总队长,他发表演讲,希望队员们既要站在国民的立场上去服务国家,又要站在佛教徒的立场上去宣扬佛教。他剀切地指出:“我们现在来训练组织成立云南省僧众救护队的初意,就是为的要使佛教徒能实际地从国民立场上去服务国家;同时,即是由佛教徒中主要分子的比丘僧众来负起宣扬佛教、振兴佛教、昌明佛教的责任。所谓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佛教道德精神,及勇猛无畏的服务精神,是要我们比丘僧去担任表现和发挥光大的。”[1]200他要求队员们,“能以大慈大悲的佛教立场,用勤劳刻苦、勇猛无畏的精神去做救护工作,使能超过其他救护队的工作,超过一般国民的服务精神;要用这样的服务精神去服务国家,显扬佛教。更进一层说,僧众救护队能够以这样的勤苦精神去到灾地难区救护被难军民,也就是完成了佛教的救世责任,达到了利人的目的”[1]202-203。这就意味着广大僧众出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阵之中,除了尽到僧众作为国民成员应尽的义务外,还具有体现佛教慈悲精神和完成救世责任的重大意义。
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紧逼,中国佛教的广大僧众中早就积聚了非常充沛的爱国主义情感,只是碍于戒律,缺少报国的路径而已。太虚大师将振兴佛教与报效祖国充分结合起来,对操练和上阵等戒律所作的义理调适,恰好打开了释放僧众爱国热情的阀门,并为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提振了精神和鼓舞了干劲。
五、结语
太虚大师在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利用佛教义理对相关戒律所作的调适,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佛教信众,特别是出家僧尼对参加抗战的诸多顾虑,调动了这部分人群保卫中华民族的积极性,数十万出家僧尼在抗日战场上从事救伤、护理和掩埋阵亡将士尸骸的工作,对于保证抗日战争的持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有些僧众还毅然从军,直接走上了消灭侵略者的战场,如抗战初期的人空法师及后期华西佛学院的学僧从军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太虚大师的影响。
人空法师可以说是由僧人而成长为抗日战士的典型。他曾就学于太虚大师创立并担任院长的武昌佛学院,毕业后北上巡礼五台山,在太原目睹了日军的狂轰滥炸和烧杀奸掠,行李被抢掠,并受诬为抗日间谍无辜入狱达半年之久,其间遭到无数次严刑拷打。侥幸获释后,他毅然在文殊菩萨前舍比丘戒,参加了聂荣臻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由于他骁勇能干,屡立战功,荣升为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队长、游击总队团长。这位原来的人空法师在一年之间,率部与敌军大战五十多次,收复三十多个县镇,有一次在庆功会上,他开怀畅谈:“我曾在武昌佛学院学过瑜伽菩萨学,有这样的一段:‘……菩萨见恶劫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我宁杀彼堕那落迦,终不令其受无间苦……如是菩萨……于彼众生,以善心或无记心……以怜悯心而断彼命……于菩萨戒无所违犯,多生功德。’日本就是大贼寇,造无间罪的,我们杀了他功德无量。”1940年夏,人空法师的游击队与八路军主力部队会师攻打汾阳,在激战中身负重伤,醒来后发觉自己躺在日占区的医院里。后来他设法逃离医院,又回到自己的寺院法空寺中[2]269。
华西佛学院的学僧也曾受到太虚大师的深刻影响。1945年1月该院的八名年轻僧人应征入伍,他们临行前公开发布了《华西佛学院学僧从军宣言》,其中就引用了太虚大师“佛必降魔,方能救世;僧应护国,乃可安禅”的教导和《瑜伽菩萨戒本》除恶安良的精神,坚持认为,僧众修行办道需要和平的国家提供一个安详的环境,需要人民来护法,如果国家亡了,人民都成了亡国奴,僧众就无以修行办道。因此,无论是从国家民族出发,还是为佛教自身考虑,僧青年都应成为消灭侵略者的生力军。他们愿意原谅那些认为僧人从军有违戒律的看法,但却主张对那些袖手旁观和冷嘲热讽者施以公理和国法的审判[2]264。
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高僧大德,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对佛教戒律所作的调适,使中国佛教成为民族利益的代表,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在时代的发展中实现了与时俱进。这段历史的公案告诉广大佛教信众,中国佛教必须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民族的振兴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努力使自家的行为规范与国家的利益相适应,才是佛教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太虚.太虚大师全书:第24卷:全32册[M].台北:善导寺,1960.
[2]学愚.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教[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
[3]遗教经[M]//大正藏第12册.鸠摩罗什,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
[4]印顺.太虚大师年谱[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朱春花)
On Master Tai Xu's Adjustment Between Resisting Against Japanese and Abiding by Precepts
HAN Huan-zhong
(Institute of Religion,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Jiangsu,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monks and nuns to resist against Japanese, Master Tai X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principles, made some necessary amendment to the Buddhist precepts such as ahimsa, noninterference, non-participation in the army etc.. He believed that the war launched by a handful of Japanese militarists would be doomed to failure and the Chinese people would obtain the final victory. Therefore, he showed great political enthusiasm in the resistance war and mobiliz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he monks and nuns engaging in rescue, nursing care and body burial. In this way, he intertwines the fate of Chinese Buddhism closely with the national destiny to seek for the religious development in the nation's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Tai Xu;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bide by precepts; adjustment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6)02-0070-07
作者简介:韩焕忠(1970- ),男,山东曹县人,苏州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佛教四书学”(13FZJ001)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