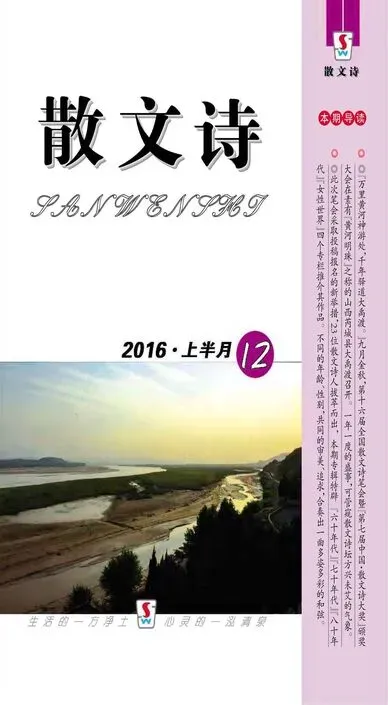海南物事
海南◎陈波来
海南物事
海南◎陈波来

写一颗饱受磨难的心,但只示以爱与感恩。
火山石
是石头。是石头一样的破碎,但不沉重,不着那般生硬的悲悯之色。
一样以大地为怀,一样在宽容与遗忘中不意间显山露水。但不是石头一样的沉重。
是石头。是最初各种粗粝与尖锐的事物在火中被销蚀、被幻化。
是鼓点,奔突于越来越高涨的熔流!是喊,是冲天的炽热的那一声喊!
——是那一声喊呐!终于没能喊破一个地老天荒。
因为只把自己喊得千疮百孔,所以破碎,所以轻如其命。
有什么戛然而止?有什么颓然而倾?
是石头落地。是一块千疮百孔的石头。
是石头。是石头中的少数。
啊多么像你!人中的少数。
山兰酒
海风不能全部吹到这里。
正好一粒刀耕火种的火星被撒向山林,那场火烧得铺天盖地。
穿青衣的黎家人信手在冷却的草木灰里点播下金黄的山兰稻种。随意的播种,但不计多少的收获更是充满喜悦。
对于呼啸于山野的黎家人,食物不只是白净的米粒,还有米粒化作的浊酒。
海风毕竟吹来,阳光热烈得如芒刺在背。
用不着再烧一把火,以及热火朝天的蒸馏,一如山兰稻在向阳的坡上自然秀实。
热带的海风与阳光使闷裹在芭蕉叶里的稻米很快发酵并酒液横流。
这是秋天,偶尔一叶枯黄拟将落向收割后的山坡的时节。
黎家人拉外乡人一起喝山兰酒,不用分碗而盛,满满一坛。
也不分你我,插上几根竹管轮番吮吸,满满一坛当当响的盛情和海量。
那外乡人,尝到高原故乡的糯米甜酒的味道,不胜酒力,在醉眼朦胧中认出似曾相似的亲人。
红木棉
我又一次向你仰望。又一次,你在冬天返回,就像冬天是你的故乡。
漫游者眼里有太长的夏天:持续的热度。早熟的果实与易碎的青春期。被白浪反复涂写的空旷的海岸线。
汹涌而又一成不变的绿色下面,是被捂住的根与譬喻、落叶与歌吹。
漫游者对陌地和季节的探问与求索,因倦怠而终至麻木。
是不是一点冷,短暂的、来自乡愁的那点冷,就可以唤你回来?
是怎样的冬天,无关冰天雪地的记忆,可以留住漫游者回家的心?
而你因此褪下最后一片矫饰的绿叶。
你以积攒的全部热情抟成一团团火焰状的花朵。
漫游者!你明亮地灼烧自己,以此找到安身的无处不在的枝头。
又一次,红木棉花开,就像返回冬天的一团团火焰。点燃我吧!让我也回家。
海螺
一座干净的城,因空空荡荡而显得干净。
连心的肉,牵扯的经与脉,有关生老病死的演绎,以及形单影只时缠绵的诗歌……
被三下五除二地剔除掉,干干净净。
干净得呈现不出过往的任何阴影与斑点,让人疑窦丛生,让人止步于空城而不敢有半步的冒进与深究。
空的城开始大声地说着那一片海。海在虚幻地响。
仿佛时间的置换与窃取也是虚幻。你摸不着那有过的荡漾和蓝。
仿佛最后,连虚幻都被干净地拿走。
有一天我老了,我会让一把海螺在身体里吹。
连一片落叶、一丝乡愁都不留下。因空空荡荡而显得干净。
沉香
天地撕裂处,好大一个伤口:不见血流成河,不闻痛苦之声八面起伏。
唯见山、石头、沙与土。
唯见块垒于胸,硌刺之于伤口。
唯见人。而人如蝼蚁。
唯有痛感,淅沥长在,因为有爱。
唯有大野芳菲,因为人世间,苦尽甘来,自有活色生香。
因此我们相爱,直到多年后那场玉石俱毁的焚烧。所有撕裂与伤痛都模糊了,我们留下的紧紧相拥的身影越来越清晰。
(陈波来本名陈波,1965年出生,海南省作协会员。现任海南大兴天泰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作品散见《诗刊》《星星》《散文诗》《诗潮》《世界日报》等国内外报刊,出版有诗集《碎:1985-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