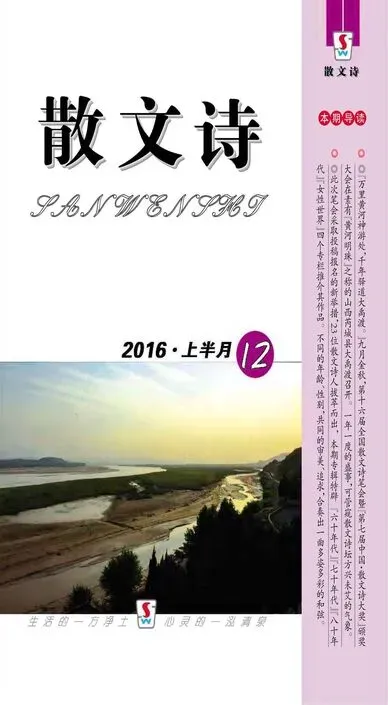蝴蝶
江苏◎张作梗
蝴蝶
江苏◎张作梗

在写作中,我力争谋求达到一种几何学般的精确。
蝴蝶
你询问我对蝴蝶的看法。语气轻柔像一封情书。
要是我是庄子就好了,或者,是一只蝴蝶也行。可惜我两者都不是。因此,我与蝴蝶永远隔着一双翅膀的距离。也就是说,无论我有怎样的看法,并不能改变它的方向、颜色、出行时间和它所要驾驭的风的多寡。
顶多,我依稀听见过它变成了一部悲情传说的主角。它一分为二,被压缩为爱情的标本。然而,多少年过去了,它依然在人世飞翔。与之交媾的死亡之梦,依然没有谁能解析。
有时,它变作一只尘土,飞舞在山野草径。它飞进眼里,磨损着我的眼球;粘在我的手上,像一粒老年斑;尔后,它飞离我的头发,远了,更远了,消逝在群山透明的呼吸中。
你询问我对蝴蝶的看法。在一只从书页掉落的蝴蝶标本上,我答非所问地写下如上文字——雨,在窗外下了一夜。
雪融
谁失去了谁?
万物有如从梦中走出,毛茸茸的,慢慢,恢复了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有关
一场雪的甜蜜之忆,当最后只剩下这一滩冰冷的水,整个冬天,我们行经其上的脚印,而今都流进了哪一类植株之中?
消融,究竟是一种绝望的渗透,还是一次彻底的遗忘?
大雨。驱车:沿途佳境空置
雨水在玻璃的连接处画出一条弹跳的虚线,仿佛雨水全是破碎的,全由破碎的云朵和原野构成。
你的到来不会比夜晚更迟。因为雨水是一个巨大的伪装,早已为你的出场做好铺垫。
此时,你若赴约,我就是你要兑现的诺言。你如果写一首悲情诗,我就是你倾诉的对象。而倘若你魔术般把雨水撑开,变成一把油纸伞,我就是你身边空缺的那个人。
挡风玻璃上,雨水分岔,向上飞跑。
雨刷器来来回回也擦不尽它们蝌蚪般浮游的头颅。
你的出现不会比一场暴雨更突兀。因为夜晚降临,万物模糊又温柔,
你的到来正好躬逢其盛,顺理成章。
此时,在雨中驰行,除了把玻璃连接处那条幻影般的虚线当成唯一的方向,我找不到更好的导航仪。
沿途佳境空置,雨影疏斜,夜色阑珊。
两个人的孤岛
飞翔的孤岛。沉沦的孤岛。我们用头颅赶路;腾出脚,去海水和云朵中嬉游。人世狂欢。我们用这铺天盖地的狂欢垒筑并加固我们的孤岛。我们在这狂欢上飘荡,克制又纵情。我们的孤岛是另外一本台历,翻一页,便是一次潮汐;翻一页,便是又一个节日。
以其绝缘体般的封闭,我们把我们敞开,朝向世界。应和日月星辰的律动,我们制造出新的生长和律动。我们拒斥又吸纳,孤单而浩瀚,无视风暴将我们的身体锻打为两截交缠扭动的闪电。
这人迹罕至之地。有多少片刻的消亡,便有多少漫长的沉醉。坐拥锦瑟,我从不吩咐和命令。我只负责享乐。
——爱是我们每日温习的功课和唯一要做的事。海水濯足,你的裙裾写满盛夏紫罗兰的日记。
海岸线一样绵长的孤岛。我们像一群候鸟,一次次穿过它——穿过时间的子午线。
睡眠深处的雨
雨,下了一夜。
闪电像是一只接触不良的灯管,隔一会儿亮一下。在万物慢慢收回它们警觉的影子前,我的睡眠比雨声还深。
“下雨∕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①引自博尔赫斯的诗歌《雨》;雨不是下在窗外,也没有下在别处。它下在我的心上、听觉上(死了的心和仍在尘世游荡的听觉);下在迷离之梦对这个世界的妥协或拒斥上。整夜,我的意识在泥泞中冒烟,雨水就要成为它的助燃剂。
一半的我还原为草本科目的水汽,氤氲在你的呼吸中;另外一半被阶上冷雨冲进排水沟,流到我遥远的肉身之外。
愈被遮蔽,窗外摇晃的路灯愈发显得突兀、狐疑。好似一只枯叶蝶,我栖歇在夜色巨大的枝条上,连风也不能辨识。——你的晚祷和早诵,串成绿色之雨的火车皮,梦境般掠过我睡眠的窗口。
雨,下了一夜。
(张作梗本名张海清,1964年出生,湖北作协会员,现居江苏扬州。作品散见《诗刊》《星星》《诗歌报》《扬子江》《诗选刊》等报刊,出版诗集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