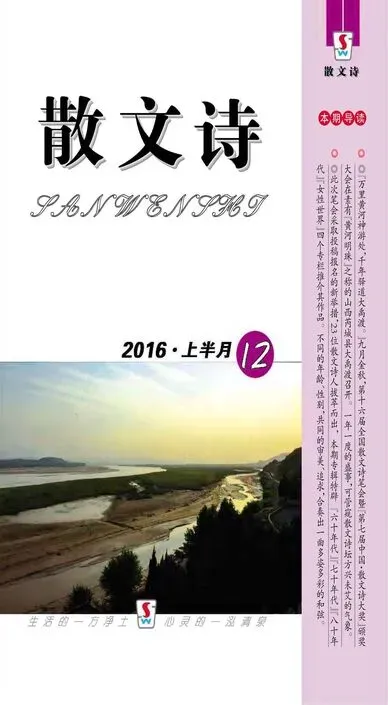喊羊,父亲喊出了自己的身体
福建◎张平
喊羊,父亲喊出了自己的身体
福建◎张平

沙粒也激荡风暴,纯净沙粒,结晶诗音。
喊
我们在阳光底下扯破嗓门,嗓门挨着草丛,挨着树叶,它们都像流云的金子。
再往深处喊,挨近一群羊,把嗓门贴在它们的眼睛。
暗合白色,它们眼睛流动的金子,是一曲诉说不尽的春风谣。
依旧波浪一般,翻滚。
父亲喊羊,喊出了自己的身体.
春风谣
一根挥鞭,停落的鸟儿没有飞走。它成了影子,在守望的高处。
摇晃,这是山冈的一次震动,高处的震动。生灵那么矮小,隐没草野,再隐没一次,我们是更小的生灵。
命运在驱赶我们,每一秒都在迁移。
每一秒也在跌落,看那些奔跑的羊群,抖落尘埃,又站起来了,匍匐春天的身影埋藏着我们的雷鸣。
羊儿脆弱如草
草,挺立山冈,山冈高了。羊儿呢?它抬头望月吗?它凝望多久了。
它的身体不再流动金子,模糊的眼神比风脆弱。比草脆弱。
低垂眼神,它静若一块石头,那么小的坚硬,被山冈隐没。
日落的辉煌,也是那丛草。
故事
父亲的故事藏于一封鸡毛信。
它赶着羊群,比夏天奔跑得还快。歇晌,他打开鸡毛信,又迅速揣入羊的身体。
这个季节的动作迅速如挥动的镰刀,仿佛歇晌季节的风暴。
羊群依旧飞奔,如石,石子滚着,溅起如火星的文字。
父亲的一封鸡毛信,也溅起火星。
在羊群的背后,父亲被甩得更远。
他追赶一封鸡毛信,他深藏的秘密,自己也打不开了。
牧羊人
羊儿在安静地嚼草,你的挥鞭却举得更高。在高处,你看那些浮云,更像是宿命中的羊群。
风将它们移动,好像它们总在赶往故乡。
故乡又在哪儿呢?在高处,你总是想将什么挂起。营帐幽暗,是那盏萤灯吗?
而你总是围拢不了一群羊,奔跑在高处,天空的栅栏溃散。
你举着挥鞭,是不是要将深处的孤独驱赶?
给羊的问候
哪一头羊都是父亲,它们都留下了孤草的影子。
在山冈的高处。它们都曾陷入山谷,一个人的暗穿透不了两岸群山。而高处的流云,像是奔跑的兄弟。
一切又那样缓慢,像父亲的纸烟,一粒火星映亮了模糊的面庞。而黄昏是迅速的,模糊的更加模糊。
埋在夕光中的面庞比羊群更无助。
哪一头羊都是父亲,父亲的前世是羊,后世是羊,今生是羊。羊,命运与栅栏,摆脱不了。
在暗屋,我们仔细辨认蹄印,因为太细小,没有什么痕迹。我们也看不清父亲,着急的夜晚,一根挥鞭在抽打自己。
怎么会这种情况呢?他愈不相信自己,抽打得愈加凶猛。
“好了,骨头会击碎的。”
我们埋进羊的无助,把自己的阴影立于山冈,替父亲将蹲伏的身体搬到高处。
山冈
高处流云,身体不胜寒。
他守望低处的山涧,绕来绕去,绕到心间。流水柔软,安放高处的身体。他要望低处的羊群,星光点点,在草丛中,它们埋没自己,他也埋没星光、身世、高处的炊烟。
再眺望一会儿,他也是凝固的石头,高处的石头,把沉默带到流云。
大地一声不吭已入,高处不胜寒。
羊齿草
夕光去追寻。大地柔软了那些影子。
而我怎样停顿,摸到大地的边缘,摸到低处的流响。低处,一丛羊齿草继续大面积铺开,当这些流响深入夜色。
深入了潦草的民间,这时,我也坐在黑暗的一侧,怀想,或是聆听。
我又怎么去辨认柔软的指针?
夕光只是一部分,它的追寻是另一部分。
我在其间,也大面积覆盖,又是多余的思想。可是时光无法摆脱。
羊齿草也有大海的艰涩。
下酒菜
一块羊骨头从没有坚硬,炉火也没有照亮理想的目标,木栅栏依然在修补,父亲,他举起酒杯,与抱起的斧头一样苍茫。
第几杯下肚了?去抓一束风作为下酒菜,风,比羊骨头更脆弱,一磕散乱四方。
我在拼一张木桌,把各自逃离的聚拢。听,父亲在追逐走散山冈的羊群,他累了,仰卧在高处。
四面悬崖就是为了抓住星光的明亮。父亲又把它当作灯盏,头顶辉煌,脚下黑暗。
斜风
你看到风歪斜的身体吗?它多么像顽皮的孩子,在泥泞的小路滑行。
对,春天来了。
这个顽皮的孩子把小手伸进我们的衣领,让我们再一次触动凉意,然而,枝条有了绒毛,一切都在回暖。
这双顽皮的小手是绒毛的继续。
时光倾斜的那一部分就要绽放。
这个顽皮的孩子垂下翅膀,因为种子使他承受了重量。因为梦。
我坐在锄头柄上歇晌已久
我坐在锄头柄上歇息已久。这倾斜的角度,天空高远,鸽哨一次次迷失。
我托着下巴,看父亲与水田。
涌动的不仅仅,是眼角的东西。
仿佛我要替羊群歇一歇,停落疲惫的翅膀。一切都短暂了,包括前一会儿涌动的鸽哨。我从未安慰过自己的灵魂。我坐在锄头柄上,并没有将日子的沧桑安顿。
夜空下
天空看上去什么也不存在,正因为如此,有人在努力安放。仿佛星星挪出的位置,安放了相似的灵魂。
下一刻,安放的灵魂,也会空出座椅。又有什么相似的补充。
仰望,草原终于空出了自己,身体缓慢的过程,找到了亲近的羊群。
蹄印跟踪火焰,天空看上去什么也没有回应。一个人不再辽阔,我们是迷乱的夷人。
草在安身立命。
(张平1968年出生,福建省作协会员,邵武市作协副主席。作品散见《诗选刊》《星星》《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散文选刊》《散文》《福建文学》《山东文学》等报刊,出版诗集《遥想》《在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