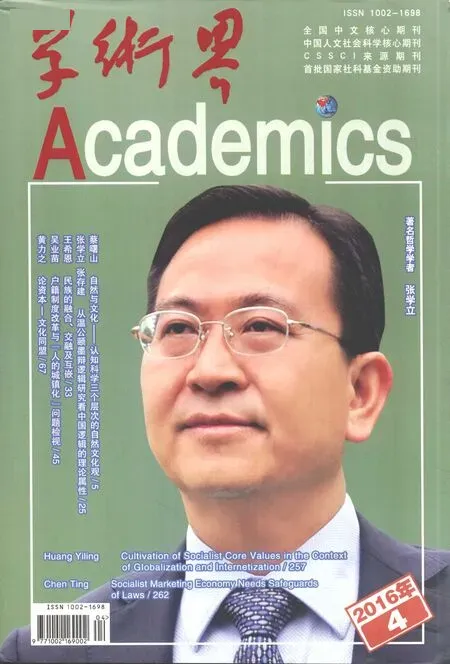《列子》的“化”:本体设定与具象过程〔*〕
○ 卞鲁晓
(1.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234;2.淮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列子》的“化”:本体设定与具象过程〔*〕
○卞鲁晓1,2
(1.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上海200234;2.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安徽淮北235000)
《列子》的“化”是由形而上抽象之根据向形而下之具象运化生成的哲学设定,是其解释宇宙现象、论人生形而上存在的核心概念。学界囿于《列子》文本问题,尚未对《列子》“化”展开深入研究。文章在两个层面多个维度展开对“化”的讨论。在形而上层面,《列子》以动态之“化”体现本体恒动的态势和作用机制,以“无”标识“化”的生化根据、以“气”为“无”至“有”的中介,是时间上超越一切无始无终的永恒,根本目的在于对人的超越存在进行说明。在形而下层面,《列子》运“化”为“几”自然流变于多样生物之间,成为居于有成毁的现实空间中有始有终的具体存在,突出人类学习不异生死幻化之能的可操作性。《列子》“化”区别于道家之“道”的抽象和纯粹,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自如运化,其目的在于实现《列子》超越的人生境界,这一思理路体现了中国哲学由“本”及“体”的思维特征。
《列子》;化;形而上;形而下;具象;时空;境界
中国哲学是讲究心灵的哲学,关注人的心灵存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若要讲哲学的性质,应以所研究的对象为标准。中国哲学所研究的对象为人生,而且是人的精神生活,使人达于天人合一或与道或与真如的合一,中国哲学的性质当然是一种精神性的哲学。”〔1〕“化”是《列子》以超越的生存为终极目标的哲学起点,是其论生命有无的核心概念,其对化的讨论涉及两个层面一个目标。在形而上层面,“化”兼具本体与动态化生的双重功能,以“无”为生化的根据,由无形之“气”向形质之实转化生成;在形而下层面以“自生自化”为现实的生成规律,以“几”在纷繁多样的生物之间进行自然流变。通过“化”所进行的本体和具象的双层设定,以及在可操作层面学习不异生死的幻化之能的设想,《列子》的终极目标在于为人在精神层面实现通于天地的自由营造超越的空间,企望一个界外的视点使人获得一种高超的形而上学存在。
一、“化”的形而上本体设定
“本体”不是中国传统哲学自有的概念,今天我们以“本体”概念来诠释《列子》文中的概念范畴和思想,是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西方的话语特征。但是西方的本体即实体的观念也并非中国哲学本体的意味,“故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虽以认知为起点,却常常以否定认知的终极意义为归结;本体论对先验层面的追求,也不体现为对知识的绝对性的追求,而归属于一种精神境界的追求。”〔2〕中国哲学的本体是一种本源性的存在,既关于超验的终极存在又具有体用的关系内容,它对存在的思考始终关联天道而又不离人道,关注的是人的形而上存在。
《列子》关于存在的思想以“化”的名义指向宇宙本体论,“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3〕《列子》指明纷繁复杂的现象界里万物生生不息而秩序井然,皆来自于一个源头,这个源头究其根本是万物所以化生的原由,它自身是没有具体形质的作用者,在万物始生之前和万物存在之后发挥着其化生万物的功能,在逻辑上先于现实世界、外在于有形之物而又作用于事物,成为事物存在的根据,决定着事物并超越可经验的时空。所谓“本体”,“本,乃根源,是一种动态的力量,并在动态的过程得出结果:体。体,是一种目的。本,在成为包含目的‘体’的发生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本中,我们可以发展出最原始的概念:太极。本,一动一静、一阴一阳,也就是存在的起因。”〔4〕《列子》用动态概念“化”很好地体现了所谓“本”恒动的态势和作用机制,一种非执著于某一固态的形式,一种不会停滞于物化成实的倾向,它的特性重点在于对存在事物的作用上,而不是自在地标识为某种事物。“化”在现象界动力功用的发挥直接受因于其背后那个给予它规则的东西,这个规则是“化”的主体但又不是实体。“由于本体在观中,这本体就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道,只能是渗透主体理解的本体,一种与客体相互统一的本体。”〔5〕《列子》“化”作为主体观念的产物区别于老子“道”,突显出其动态特征。“‘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他的全部思想体系都是由‘道’而展开的。而‘道’之所以能够作为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关键就在于它所独具的形而上的特性,它不属于形器世界,没有确切的形体,也没有确切的称谓,人们无法用感官来感知它,只能运用理性的力量来确知它的存在。”〔6〕“道”被老子定义为真实而绝对的存在体,“化”则被《列子》规定为运动,同时亦区别于附着于任何物质之上的运动,故有本体而非实体的意义。为更好说明“不化者能化化”,《列子》抛弃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无”之为本的命题,所谓“无”不是什么也没有的无,是与有形世界相对的那个暂时的未形世界,是实体性、对象性思维无法把握的非物存在,旨在于说明不执于实物而大全的自由境界,以其否定性的内涵来解释对经验世界的超越性,同时由此开辟出“化”生万物路径的最初始根据,彰显作为根据不受任何必然加以约束的自由本性。
“无”是一个区别于西方哲学“存有”的非实有概念,无法经验而又实有功用,它的本体性在于它是创生的源头。“‘存有’是来自希腊的概念,它是先验的而非经验的,它是西方人在追求所谓的基础而建立的,但它建立的一个逻辑的基础,它和人的生活、人的经验包括人对自身的体验和对整体的经验是有距离的。而我说的本体是我们直接感受、体验到的,它不是一般的抽象层面,而是一个动态的创生根源。所以,我们中国的本体概念具有包涵性、广大性和深刻性。”〔7〕
《列子》用古今、终始、先后、有生、不生、有化、不化等一系列的对称来推论“无”这一本体的存在,并指明它在空间上的无限性以及时间上的无始终。“殷汤问于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无物,今恶得物?后之人将谓今之无物,可乎?’殷汤曰:‘然则物无先后乎?’夏革曰:‘物之终始,初无极已。始或为终,终或为始,恶知其纪?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物之外、事之先的那个无法论始终之物,夏革以“不知”留下一个悬念,却同时肯定了“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无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内在于无极无尽的是“无无极”“无无尽”,其否定性决定了相对于他物的存在形式——非非有,它不是“有”亦不是“非有”,其内涵无限小,外延无限大,假使要它是无所不包的本根,成为一切普遍的根据,那么必然无所规定,因为任何规定都将限制它成为全有的依据。
不生不化者因其非存在性、非自身性而内在地拥有生化他物之能,决定着物自体不断运动变化的方向,“能阴能阳,能柔能刚……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列子》由始终变化逻辑上推理一个不生不化者存在,它的特征是永恒的不变性,并能以阴阳作为本体的直接呈现,以动静之功能成为万物化运的根本动力,“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阴阳尔,四时尔,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疑,固定不变。……疑独,即谓独立永存的意思,实指派生万物的本原。”〔8〕“无”作为本体既有生化的功能,又有独立永在的特性,本体在时间视域使诸事物不相同而相通。宇宙整体的内部自身既承载、沉积着过去,同时又内在地蕴含着现在和将来,现在和将来的诸多可能的事物内在成就它们的因子早已在过去潜在地存在于宇宙整体之中,这些因素经过自我酝酿、自我形成、自我发展,因为众多条件的促成而逐渐具体而微地、现实地展现在当下。“‘物之终始,初无极已。始或为终,终或为始,恶知其纪?’”事物与事件是时间的占有者,其产生与消亡占据着一定的宇宙时间,事件发生的现在是过去时间的终点,同时又是将要发生事件将来时间的起点,时间以当下为始终前后相循,依现在得以延续和划分,古今、先后、始终都是现在在时间上的积累,“化”在当下的具象成为可呈现的绝对。“谓物外事先,廓然都无,故无所指言也。”事物与事件之外只能指“无”,因为时间的无始无终正是现在所能指的,其他无物可指。在这个意义上,初始的存在以不在的否定性存在早已潜在于过去,当下的“不在”作为一种将来存在内在地存在于发展的过程当中,当下的“存在”以显见的方式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被现实的人所感受,二者在时间上的表现为过去和将来即现在的不存在,过去不能变成现在却能决定将来的存在方式,将来会变成现在又受制于过去,过去、现在、将来三者的未决与流转使时间没有起点也没有结点,成为无始无终仿佛非实有的存在,即本体的存在。在生成作用上表现为往复与循环,于是,“化”的本体作用之功在现时维度上显现出非实体的形式,它的往复性质内在于事物生灭循环和规律运动的形迹间,它的本体性因不被他物所生而独立永存,这是本体在时间上的无始末、无实体形而上思辨的注解。
“化”的运动特性最终落实在物的自生自化上。“化”由“无”为初始根据发挥作用,它的非自在性使实物自生自化处于不断地变动之中。具体可见之生、形、声、色都是与“无”逻辑上的对应者,“无”不直接作用于物而是促使物自体发挥内在的自足性去自我生成,这种自我生成是无处不在的普遍。“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列子》用“自生自化”说明万物生成与消亡的过程,亦是万物“常生常化”的依据,至于天地、圣人作为实有所见,皆无可奈何于万物,一切世间事物都以自然而然和谐的状态生存,以虚静无为的行为方式应对世间万象,才是对“无”为主体的“化”生之道的最好体认方式。
《列子》从万物的生灭论有无,构建“自生自化”的本体学说,志在个体人生命运的解脱。正如张岱年所言:“中国古代本体论的特点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时难以遍举。现在只举出三点:第一,中国古代多数哲学家不以‘实幻’谈‘体用’。第二,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表现了宇宙生成论与宇宙本体论的统一。第三,中国古代的本体论与伦理学是密切结合的。”〔9〕《列子》基于宇宙生成乃至于本体于“无”的理论综合,为其生存论哲学所服务,从“自生自化”物自体的生存方式进而议论个体对生死、对名实、对一切人生所在的看法。
二、“化”的形而下具象过程
《列子》“化”以本体层面的“无”作为生成和死亡的根据具象到目力所及之处那些事物自在的本身,演绎着生成在形而下层面各种具体感觉可经验的客观有形事物之间的流转图象,这个具象过程在《列子》这里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哲学本体宏观上的具象,由“气”这一无形的形质而至于各色有形的质料为起始。其次,现实实物微观上的具象,“机”辗转于各种生命形式之间,各种具象物和其中的隐喻在《列子》叙述的转化中成为了极具涵盖性的化生成果。《列子》具象的描述展示出生命具体形态、不同类型的生灭转化,这些有形的概括既表现出化生的具体性、彰显了生命的独特性,又在此具象过程中展露出“化”的多样性、有机性和整体性,从而为“化”的终极超越目标营造可能的广阔空间。
在“化”具象的宏观领域,《列子·天瑞》论宇宙生成的过程:“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太初”“太始”“太素”三者实际上是气、形、质三者相互关联成为一个过程,体现是从无到有,从无形到有形,从非存在到存在“化”的过程,从成物的原因到成物的质料,经由一个无个体自身属性的一个中间状态——浑沦,“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是万物未曾各自分化的状态,其形质已具体而微地存在着,是“气”之前的太始与太素的混合,这个混合终将使形质向唯一个体转化,《列子》规定“易”作为转化的中介,“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作为太初有气之前的阶段,是变化可见之前的生生不息之所在。《列子》云:“易无形埒,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穷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有学者以为:“列子对于宇宙的起源,认定‘有形生於无形。’一如老子:‘有生於无。’‘无形’之始,是‘无形埒’的‘易’,而不是老子的‘道’,更不是周易系辞传中所说的‘易之为书’之‘易’,也不是‘生生之谓易’之‘易’。它是:‘气、形、质具而未相离’的‘浑沦’。又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的本体。这个本体存在于‘天地’之先,为‘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浑然一体。这也就是宇宙起源和成立的‘无形’的境域。”〔10〕“易”乃变化、开蒙之义,通过一、七、九之运数来发挥其定性、定象的功能,通过易数的展现说明宇宙生成。事物的发展经过“一、七、九”三个阳数即事物变化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开始、盛壮和终结,之后复归于“一”。“易”以阳数的往复变化说明“气”的运行和“化”的运动本性,天地万物乃至于人则由“气”而生:“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列子》以“冲”字对气的化生给予肯定,“冲,涌摇也。”〔11〕清、浊两种不同性质的气相互涌动激荡,从而周流出不同时空所具备的不同性质,永恒运动的“气”的内动或稀散或凝聚,产生出天、地、日、月、人等客观实体存在。由“化”本体直接呈现的阴阳二气的内动流转,呈现在不同时空中的不同性能,凭借动静之功能成为万物化运的根本动力,涌动之间就能成为此物而非彼物,具备了个体自有的质料,分化成各具属性的事物。《列子》“气”是构成存在和所以能存在的中介。静态上看,“气”是无规定、无常态、无可感知、绝对的质料,抽离现象界的实际内容具有大全的性质,动态上看,“气”为实现成某种事物的过程,以无形的本然形态聚散变化,具有着物理与哲学的双重身份,既源于屈伸之气息、风气、形气、声光,又是世界万物生成之本原元素,宏大至无限,精微至无尽。
在“化”具象的微观领域,《列子》化“气”为“几”作用于各式生命存在之中。几,细微、隐微。以细微无间之“几”出入于无间之“无”,作用于有间之“有”,此“几”是“无”由非有的状态转入经验之生成者的中间者、执行者。《列子·天瑞》云:“种有几”,举凡生物界诸物种皆由此“几”运动变化而来,“若蛙为鹑,得水为畿……人久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列子》“几”与“机”有着相同的理论意味,《列子注》曰:“机者,群有之始,动之所宗,故出无入有,功有反无,靡不由之也。”“几”在“无”与“有”的逻辑空间里发挥着中介作用,“无”与“有”不是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无”不能直接作用于“有”。“有”既是万品万象又包含生命活动,生命活动本身即自然界根本的物质,其特征即是细微运动之“几”,以偶然的形式发挥出入运动变化由“无”至“有”从而化生的功用。无生命的物质演化出生命物质来,品类无限多样的物种,在外部条件细微作用下在一定的时空中自我运动变化,运动转变的方向、大小,存在的时间长短于母体而言均无所关涉,真正的“母体”是本体之“无”,决定着生成物种的性质及发展规律。现象的无限多样经由本体的作用之功以“气”为物质中介、以“几”为生变理路化生为纷繁复杂的物象。
在《列子》看来,这些宏观和微观的具象与它们的生之根由、流变之源存在着同质而相因的条件关系,万物的具象在时空中相继显示着化物之本的能动之功,生命在时空中的生灭和存在统一于“化”运动的全过程,“化”以物质为载体处于某处、具有广延性和秩序性并反映着独立于物外的虚空。《列子》由形而上之本向形而下之象进行推演,力求证明那个物外虚空的存在,为个体超越现实生存追寻境界存在打下了可资论辩的哲学基础。
三、“化”的终极境界目标
“化”的本体世界在逻辑上与时间有间隔,它是基于形而上层面的思辨,是《列子》对于宇宙在时间之维以前所进行的逻辑上的设想,假如不偏离《列子》既定的目标,它必须回归到人生存在的理路上来,也就不能不使“化”渗透了时间从而展开一个具体的历时性过程。这个历时性过程在本体意义上体现为无始无终,在抽象物展开于存在物的过程中体现为变化与始终,在人的存在、生灭上有迹可循。“中国的形而上学确实不发达,中国哲学的思维和经验世界不可分,‘形而上不离形而下’、形而上不能不受形而下者的制约,但它不仅不否定有形而上者,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形而上学。问题在于,中国哲学从‘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出发,认为形而上者不只是观念和原理,而且是存在,不仅是世界的本体存在,而且是人的本体存在。”〔12〕《列子》对于人的本体存在的思考更多地倾向于人在生存上展开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把本体世界转化到事实现象世界,也从对本体的思辨玄想回归到对事实的人及其存在意义的思索,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从形而上之“无”到形而下之“有”、本体世界到实践世界的过渡,克服生成根据之超验与生成现象之经验之间的对峙。
《列子·天瑞》基于现实人的具体生存尺度,描述了人生命形态的变迁:“人自生至终,大化有四:婴孩也,少壮也,老耄也,死亡也。”人生不同阶段的变化早已蕴藏在生命的初始的那刻,孕育于过去形变于此在,《列子》用人生大化有四旨在说明生命或者说其它的种种存在总在某一个阶段、甚或每一个瞬间必然呈现出来的不同面貌、不同的形态,这些不同内容是对宇宙大生命内在整体活动的同一性在时间阶段上的展开与说明。这个同一性即“化”,是宇宙整体自我发育、自我展开,是无所化而内蕴着变化的宇宙本体在有形层面上的表现。在这个时空统一体内部比如人生发生的事件,明显地具有不可逆性和连续性,要去识别事件与事件在连续体内部的点,实际上依然离不开相类事物重复发生而体现的周期性和特征性。时空特征在生命运动的不同阶段以特殊的表征得以暴露,转瞬即逝无法固定的时间在生命历时性的经历中以不同形态展示出周期性为人们所感知。
《列子》以为从最细微处观察,每一个事物内部在时间的连续上都充满着不断的此生彼灭的刹那结点,并无所谓稳定的、确切的、主导的东西,就此而言,世界上的事物似乎都处于无法言说的困境中。然而,在世界隐匿自身的细微时总有确定的东西呈现出来,表征着显隐的一体两面性,存在着并被理性所把握住,显出由“无”而进于“有”的全部时间历程。这里的时间是物质世界的时间,而终归它要回归到形而上之“化”那个时间之始、物质所在之前。然而,这样的回归起点依然是不离现实实践的,“由于形而上学的真理不能诉诸感性和理性而只能诉诸直觉体证,因此形而上的道的真理不能不通过实践并借助实践智慧而得到阐释……道家以体验为特征的‘知识’、超越制度范式的实践不仅基于心性境界而且也归于心性境界……”〔13〕《列子》偏于道家之一隅,以“化”为修炼的境界,经由实际操作层面的存在者在世的自我培养,渐次达至幻化于有形的境地;以出无入有的运动本体为根据,继而超越在世状态各式错综复杂的烦恼,从而实现无畏于生死的自由目标。这个目标虽不是《列子》终极的超越理想,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通过实修积累逐步提升,由“幻化之不异生死”到“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的所谓心性“化”境。
学习若神的幻化功夫。《列子·周穆王》讲述了老成子向尹文先生学幻的故事,三年而未成求退时尹文密告老成子:“有生之气,有形之状,尽幻也……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吾与汝亦幻也,奚须学哉?”生之气和形之状是有形质的东西,它们的流行表征为隐匿与显现,在时间的先后上有先天与后天的不同,在因果关系的观念里指向生命的本来之处,即阴阳,它们既不离生命现象本身,又不在生命内部的某处地方,而是悬浮于生命现象之中,因此个体生命都是幻化无实的存在。造化而成的生命在阴阳互动中往复循环地实现着稳定连续,阴阳成为学习幻化之能的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它们不仅涵容于生命本体中,而且凸现在生命单元及其生命过程的始终,因其幻化的极其巧妙和难穷其根呈现给主体无限的盲目性,学幻唯一的路径便只能在自身的结构中体验天地日月流光,体验阴阳相生的流畅和相克的恒定,放松自我与之匹配才能发挥修炼的主体能动性,从而原生出生命的冲动,实现不学乃学的幻化本领。老成子深思而有所悟,在修炼中发现先天自身内在的广延性,这是相对于向外无限扩展的张望之后向内心凝聚的发现,这种广延并非具体可感的某种空间或物体,而是一种内在的体验的广延性的扩张,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作为生命有机体的物质局限性,从而使老成子存亡自在、制控风雨、变幻季候,在本质上与宇宙的发生同化为一体两面的对应过程,然而这一幻化的提升依然带有体验的性质,还未能超越特定空间指向,无法使主体内在得到更准确的确证。
通天地应物类的化境。《列子·周穆王》塑造了一个“化人”的形象,对老成子的变化之术进行了精神的提升。化人能入水火、穿金石,千变万化无所滞碍,然而化人强调神游而形无所动,神气变化奥妙无穷转瞬即逝,只有超越常情以充满期待的想象思维内观自身,才能超越现实的特定时空指向,融自身与外物于一体、无所分别,回归到人本有的与天地消长相互感应的状态。“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这样的化境体现着修炼者逐渐显现自己本质的运动过程,而不仅是在某种时空位置上显现自己的具体存在,体现生命结构的不确定性与宇宙化生流动性的相互联通,以及本体外在向主体内在转化的流转过程。在《列子》看来一切“化”境修炼的法则、道理不过是本能浅近的避苦寻乐、学习面临死亡。“化”某种程度上是表明一种对自由境界的认识,在学习面临死亡的过程中对自由意识的自觉,发现本真的自我同时浑然于天地之大序之中,最终通天地应物类。
《列子》基于“化”的运动本性从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展开对存在本质的追寻,其思维理路一直不离从时空之内向时空之外的跃进,它从形下经验界上升到抽象和形而上追问的冲动正是源于对现象世界时空的终结与毁灭的担忧。当人们不能在瞬息万变、动荡不安的现实社会的具象世界中进行自我拯救时,便会找寻超越的非具象世界寄托精神,正所谓不能为感性所把握的存在,需要用境界去直觉感悟,因此“化”成为《列子》向审美生存的最原初的哲学解释。总之,《列子》对于“化”的两个层次一个目标的论证并非为了深度探究宇宙的本源及其终极目标,而是要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解决现世的人生问题,化具体层面为心灵层面,建构一个人人可得而合之的心灵境界,从而使精神在形而上、抽象、非具象的层面上得以无限升华,向无始无终的宇宙扩充那个完满的自我,最终获得精神上的完全自由。《列子》之“化”可看作中国精神哲学上又一个极具内涵的概念。
------------------------
注释:
〔1〕罗光:《中国哲学的展望》,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11页。
〔2〕冯达文:《中国哲学的本源——本体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3〕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7页。(以下《列子》《列子注》原文皆引自此书。)
〔4〕成中英:《论本体诠释学的四个核心范畴及其超融性》,《齐鲁学刊》2013年第5期。
〔5〕〔7〕成中英、陈望衡:《道、境界和美——关于本体诠释的对话》,潘德荣、陈望衡:《本体与诠释——美学研究与诠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4页。
〔6〕陈鼓应、白奚:《老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
〔8〕严北溟、严捷:《列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页。
〔9〕张岱年:《中国古代本体论的发展规律》,《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
〔10〕严灵峰:《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台北:文史哲学出版社,1994年,第112-113页。
〔11〕〔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29页。
〔12〕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8页。
〔13〕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26页。
〔责任编辑:流金〕
卞鲁晓(1972—),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美学研究。
〔*〕本文系淮北师范大学2012年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600849)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