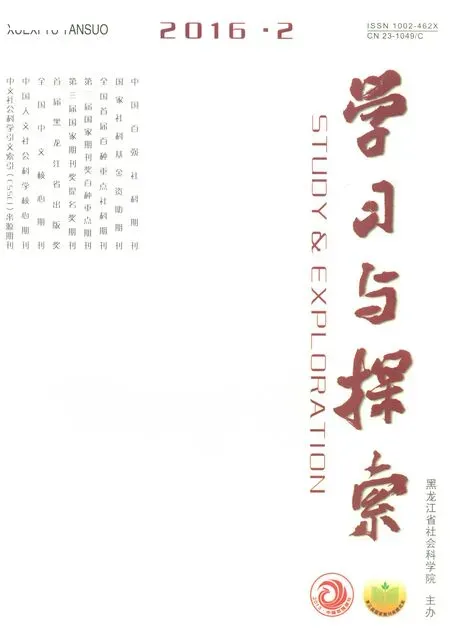发现“最后的”边疆
——1732—1932年间呼伦贝尔的地区认识史
孔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发现“最后的”边疆
——1732—1932年间呼伦贝尔的地区认识史
孔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摘要:1732—1932年间呼伦贝尔是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中文化形态相对独特的一个地区。它的行政体制和归属长期属于黑龙江,而它在地理环境方面属于蒙古高原的一部分。这种二元特征使得从清代到民国,朝廷、地方和知识分子对其的叙述策略与重点都不同。呼伦贝尔叙述中的形象经历了“防准固边前哨”“八旗驻防新城”“元兴之地”“控蒙咽喉”等转换。不同的转换,反映的则是在内外局势变化下,边疆方针的调整变化。
关键词:清代;民国;呼伦贝尔;八旗满洲;元兴之地;边疆地区认识
作为一个跨文化区域,多族群、文化和法律上的帝国,清代的“边界”( boundary)体现于各个层次上,既包含国家边疆的层面,也包含国家内部区域和族群间界限的层面。伴随着清政权的兴起、壮大和渐渐衰落,各种层级的区域和族群边界也在不断生长与重新构造。清代至民国时期“呼伦贝尔”概念的形成与其意义转换,是边界制造和划定中一个较为有趣的案例,这个过程的历史区间大体是1732年(清政府在呼伦贝尔正式设治管理)至1932年(苏炳文抗战失败,呼伦贝尔宣告沦陷)之间的二百年。在这二百年中,呼伦贝尔的范畴同今日的呼伦贝尔市并不相等,其指代的区域相当于今天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以西地区。
设置之前的呼伦贝尔曾经长期是蒙古高原游牧人群的活动场所,在此后二百年中,其经济文化形态也以游牧文化为主导。另一方面,这二百年里中央政府始终将呼伦贝尔作为黑龙江的一部分进行管理,呼伦贝尔的新、旧巴尔虎等族群在制度中也有别于“蒙古”。因此,这个地缘文化与“蒙古”相近,而长期作为“八旗满洲”的区域,在官方叙述与士人叙述、地方叙述等不同层面中呈现了不同的面貌。清代中前期,以朝廷为主导的官方文字叙述和舆图绘制始终试图建立呼伦贝尔的“八旗满洲”属性;康熙时期起流寓黑龙江的关内士人则从实际知识和自身观察出发,关注到呼伦贝尔和巴尔虎人同“蒙古”的相似。嘉庆朝边疆研究兴起后,各地知识分子逐渐关注到呼伦贝尔“元兴之地”这个重要特征,进而注意到呼伦贝尔同蒙古史地的联系。最终在清末至民初期间,以宋小濂等集官员、士人、东北本地者几个身份于一身的边官边吏,将几种话语重新整合。在这个过程中,“蒙古”同“东北”的概念边界也经历了从强化到淡化、抹平的变化。
后金—清政权的族群认知最初来自周边交往的政权和部落,其后通过向明朝与蒙古各部辖地的扩张,又将明朝和北元的地理知识也纳至自己的概念体系中。至17世纪中期时,清朝统治者已经形成了包纳中原、东北、蒙古、西域、西藏等地在内的天下框架。在这个初步定型的天下秩序中,夹在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顶角处的今日呼伦贝尔却迟迟没有进入清初人的视野。清朝认识呼伦贝尔,几乎是在完成对周边各族群与各区域的概念化之后才进行的。因此,如何将呼伦贝尔纳入既有的秩序,便成了区域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呼伦贝尔的认识史,同样也是重塑区域和族群概念的历史。
一、视域的转换与明清之际呼伦贝尔定位变化
后金—清政权对黑龙江上游地区呼伦贝尔的认识,是随着它在北方的扩张逐渐获得的。清政权早期在北方的扩张方向主要有两个:其一是三江平原至黑龙江下游的,所谓“东海窝集”区域;其二是位于大兴安岭两侧,西辽河、洮儿河等水系的嫩科尔沁、阿鲁科尔沁、内喀尔喀诸部的牧地。对于纬度更高的呼伦贝尔,后金—清政权在初期还没有接触到。清朝对呼伦贝尔邻近地区的接触和了解,大体从天聪八年( 1634)扎赉特部部分贵族在归附清朝后的逃亡事件开始。“科尔沁噶尔珠塞特尔等叛往索伦,为其族兄弟等追获被杀”①《清史稿》卷二,民国十七年清史馆本。的过程,将清朝的视线引向了嫩江流域同黑龙江中游的地带和族群。天聪九年( 1635)夏天时,生活在黑龙江中游的“索伦部落头目巴尔达齐,率二十二人来朝,贡貂狐皮等物”。②《清实录·太宗朝实录》卷二十三。崇德三年( 1638)十一月,皇太极遣人贸易貂皮时到达嫩江流域,正红、镶白、正白、正蓝、镶蓝五旗分在嫩江地区收纳貂皮408张[1]。
清朝对嫩江流域实施统治后,通过当地达斡尔人和通古斯民族同额尔古纳流域取得了联系。17世纪70年代米诺瓦洛夫和斯帕法里使华,就是由达斡尔人先导,取道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扎敦河和嫩江河谷,在齐齐哈尔嘎善同清朝官员会面的。康熙二十九年( 1690),作为“九路巡边”的一部分,清朝八旗官兵也对这段路线进行了主动的巡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索伦总管玛布岱、倍勒尔等官员在题奏巡边路线时,初步提到了莫里勒克以下至额尔古纳河口的交通情况。“ergune i angga ci,merilken de isitala,mukei wesihun wehu i yabuci,orin inenggi hamime yabumbi.”(自额尔古讷河口直至莫哩勒肯,可逆水乘威呼行走约二十日)。③《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转引自《康熙满文本九路图与清代巡边制度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满文转写见第22页,汉译见第25页。这次活动宣告了清朝政权对呼伦贝尔北部地区有了直接控制。
同年八月,同呼伦贝尔相关的另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了。这一年噶尔丹的东征造成了大量喀尔喀、巴尔虎人自喀尔喀河、克鲁伦河流域越过兴安岭进入嫩江流域,给当时的黑龙江将军辖境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这个事件使得清朝方面加强了对呼伦贝尔南部的关注和了解。“呼伦贝尔”这个概念也开始见诸史册。康熙二十九年( 1690)萨布素等人报称喀尔喀、巴尔虎人众越境原由时,就开始提到了呼伦贝尔的早期概念,“Kailar jerge bade geneci,oros gurun de gasihiyabumbi; kulun buyur jerge bade geneci,kundulen boogtu de gasihiyabumbi.”(开拉里等处为鄂罗斯侵扰,呼伦贝尔等处为昆都伦博硕克图侵扰)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二十九年户部工部理藩院等行文档,将军萨布素为查喀尔喀巴尔虎擅入索伦地方事报理藩院文。按,清代西北边陲尚有吉尔玛泰,满文名称与此相同。从咨文时间和内容判断,此jiramtai只可能是海拉尔河流域的济拉嘛泰。此时的呼伦贝尔大体还是指今日呼伦贝尔南部地区。
康熙三十二年( 1693)时,副都统哈达哈等向理藩院呈文,奏报了察看呼伦贝尔地区的情形,提出了在这一带屯田的设想。哈达哈的呈文中并没有使用“呼伦贝尔”这个集合概念,但他所提到与涉及的地区已不仅局限在呼伦、贝尔两湖周边地带了。哈达哈在行文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amban be dergi hesen be gingguleme tebufi,hailer、hulun、herelun、ur sˇun、buir、kalkai birai babe tuwaci,ergune、hailer、hulun、herelun bade,yonggan oho bime hüjiri bi,usin tarici acara ba akū; jai ur sˇun、buir、kalkai bira,ba majige yebe,usin tarici ombi sehebi.。
臣敬奉圣旨,视得开拉里、枯伦、克鲁伦、乌尔顺、布育里、喀尔喀河流等处,言其鄂尔姑纳、开拉里、枯伦、克鲁伦等处碱草丛生,不可耕种;乌尔顺、布育里、喀尔喀等处稍愈,可行耕种。⑤《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三十四年副都统、台站哈番等行文档,副都统哈达哈为奉旨视察开拉里等处报理藩院文。哈达哈文中对呼伦贝尔诸河流名称的使用,同其他同期满文文献中的常用写法并不相同,此时边疆地名的满文写法还没有完全确立。
哈达哈尝试进行统一规划的这些流域,基本上就是后来呼伦贝尔八旗主要辖地。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虽然此时“呼伦贝尔”概念没有后世那样的明确性,但呼伦贝尔这片地区已经开始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了。
乌兰布通之战后,清朝对蒙古地区的政策日益积极主动。随着清朝在蒙古高原上的扩张,清朝官员对呼伦贝尔的地缘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其重视程度进一步加强,对呼伦贝尔的实际知识掌握也更加全面。康熙三十四年( 1695)一则关于调遣官兵的奏报中,呼伦贝尔南部区域地理条件和道路状况已经有了较清晰的描述。
bayan olan ci bar hoton de,juwan duin inenggi; bar hoton ci tulkin de,juwan emu inenggi; tulkin ci hulun de,herelun birai anggai dosijiha,bade sunja inenggi isijimbi sembi…herelun i angga ci mergen hoton de isibume,futalaha emu minggan nadan tanggu nadanju sunja ba…soyolji alin i baci geneci,herelun birai siden de ememu dedun de,muke baharakū ba bi sembi…hulun buir siden i ur sˇun be dome,herelun de isiname geneci,soyolji be geneci tondo bime,jugūn sain,muke lakcarakū bahambi。
称巴彦乌兰至巴尔和屯行四日,巴尔和屯至图勒沁行事十一日,图勒沁至克鲁伦入呼伦泊至河口行五日可达……克鲁伦河口至墨尔根城,经量有一千七百七十五里……自索约尔济山至克鲁伦间数站地方,据称无水……经呼伦、布雨尔间乌尔顺河,自索约尔济山行至克鲁伦河,则道路甚好,水泉无竭。①《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三十四年各部理藩院盛京兵部刑部等处行文档,将军萨布素为克鲁伦、巴彦吴阑等处讯得噶尔丹军情事题本。
从康熙时期汉族文士方式济所著《龙沙纪略》中对呼伦贝尔地理的描述中,我们也能看到当时关于呼伦贝尔知识的完善与扩展。流寓齐齐哈尔的方式济很可能并没有去过呼伦贝尔,但是他的了解已经格外准确,“枯轮海(今称呼伦湖),周匝千里,在黑龙江之南、开拉里河(今称海拉尔河)之左。其南有乌里顺河(今称乌尔逊河)、乌兰泉及俄罗斯之克鲁伦河,皆北来汇于此,由鄂尔姑纳(今左额尔古纳河)达江……枯轮海东南八百里内,又有噶尔必海、乌兰海、布育里海(今称贝尔湖),以受南北山之水”。②[清]方式济著《龙沙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第六册。
自康熙二十九年( 1690)起,清朝政府在几年之内对呼伦贝尔的地缘政治与军事地理意义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认识的进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呼伦贝尔境内各地理概念渐渐见于史册,二是呼伦贝尔的军事地位开始被提出。呼伦贝尔军事意义上升的动因则是噶尔丹的东征威胁到清朝东北疆土。清朝对呼伦贝尔的知识,就是自东而西,因安全需要而渐渐获得的。在康熙时期,尽管作为区域的呼伦贝尔还不完全明确,清朝官方已经对其作为蒙古、兴安岭与黑龙江之间的要冲之地有了认识。
二、“呼伦贝尔”的政治规划与族群的概念化
传统中国始终有着“正名”的文化传统,“正名”标志着行政、军事与经济上的制度和设置需要“名实相配”。在雍正十年( 1732)呼伦贝尔设置之后,新近规划而成的呼伦贝尔八旗驻防之地也需要进行新的“正名”,这意味着清朝政府在叙述中就需要将其正式描述为以城塞为中心的驻防之地。这样的叙述策略首先体现在雍正十年( 1732)卓尔海请迁岭东官兵驻守呼伦贝尔的奏折中。这是史载清朝最早对呼伦贝尔进行正式开始设置的设想,它在汉文实录中是这样描述的:“呼伦贝尔附近之济拉嘛泰河口处地方辽阔,水草甚佳,树木茂盛,可以种地筑城……”有趣的是,卓尔海最初的满文叙述方式恰好略有不同“kailari de acahambi,jiramtai bira acaha anggai ba,ne sain lele,usin tarici hoton weileci gemu ombi,ongko muke sain,moo buzan labdu,gurgu nimaha elgiyen.”(济拉嘛泰合于开拉里之河口,地方辽阔,种地筑城诸事皆可;水草甚佳,树木茂盛,鸟兽鱼虾充盈”)。③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18-009,鄂尔泰议覆卓尔海奏请挑选索伦达呼尔巴尔虎等官兵于呼伦贝尔等处驻防折,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一日。汉文实录的表达以“种地筑城”为最重要的核心,水草和树木衬托的是建城处的良好条件。满文奏折则明显是两个并列描述,将屯垦者“种地筑城”和游牧游猎者“游牧打牲”,两者在语义中基本平行。显而易见,在最初上报的时候,筑城只是八旗官兵的需求,并没有成为呼伦贝尔的设置的终极目标。
相同事件在汉文实录和满文奏折中的不同表达不仅是语言上的调整,也是呼伦贝尔管理体制和经济文化的相异性的体现。不同于松嫩平原上的城池,呼伦贝尔是传统的游牧空间,未开发的自然在这里是主体。在卓尔海奏折的议覆中,关键概念nuktembi的使用颇有意味。这个概念体现了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指的是索伦人和巴尔虎人原本的非定居生活,区别于呼伦贝尔城周边定居务农的达呼尔官兵生计方式,“solon barhū nukteme taciha be dahame…dagūr se daci gemu boo arame,usin tarime banjire be dahame…”(索伦巴尔虎以习游牧为惯……达呼尔素来以造房种地生活为惯) ;一方面则对应蒙古盟旗的“游牧”概念,指代临近俄罗斯和喀尔喀的地广人稀的边疆上的管控方式“dashūwan duin gūsa be,oros hafunjire jugūn be akdulame,heen ergi be nuktebuki; jebelen duin gūsa,jecen be bitumen,kalkai bira de isitala nuktebuki”(左翼四旗扼通鄂罗斯道路,沿边界游牧;右翼四旗自分界起至喀尔喀河游牧)。①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18-009,鄂尔泰议覆卓尔海奏请挑选索伦达呼尔巴尔虎等官兵于呼伦贝尔等处驻防折,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一日。“游牧”在用词上同“种地筑城”形成了对比,而这两个概念所主要指代的区域亦有不同,前者以是筹建呼伦贝尔城的济拉嘛泰河口的核心,而后者描述的则是克鲁伦河、哈拉哈河等处。
从康熙时期向内收抚巴尔虎到雍正时期调集黑龙江兵丁驻守呼伦贝尔的过程中,官方叙述中的呼伦贝尔成为了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地区。官方书写中的呼伦贝尔不再是未归顺游牧者自由活动的荒地,而是仿效齐齐哈尔、墨尔根等处的面貌的,由屯垦和城塞组织起的八旗驻防之地。乾隆时期的地图中,呼伦贝尔首次以“地方”的面貌出现。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间(约1759—1763年),用中国传统绘图方式绘制的《国朝天下舆地全图》中《盛京兴京统图》一幅里,不仅标注除了“呼伦湖”和“布雨尔湖”,还在海拉尔的位置注出了“呼伦布雨尔”②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舆图,000820号,《国朝天下舆地全图·盛京兴京统图》。这个区域地名概念。《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绩图》中,呼伦贝尔城的位置上被明确注为“呼伦贝尔副都统衔总管驻箚处”,满文称“hulun buir meiren i janggin i jergi uher da tehe ba”。此外,图中还标注了“济尔马台台”“雅克萨台”等台站名称。③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舆图,001502号,《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四排五》。
将呼伦贝尔书写为“城塞”的叙述方式,催生了呼伦贝尔“形胜”的概念。嘉庆朝《黑龙江外纪》较早将这个概念赋予呼伦贝尔,称其“北控俄罗斯,南抚喀尔喀,山河险固,并重龙江。境内山峦盘结,以大兴安岭为正干,寻其脉络,自索岳尔济山起项,向东北行,重岩叠,起伏蜿蜒,亘六百余里,至凯河发源处,土人始名曰兴安岭。”④[清]西清著《黑龙江外纪》卷一,光绪广雅书局刻本。后世编撰《朔方备乘》的何秋涛在引述《黑龙江外纪》所言“山河险阻,并重龙江”的同时发展运用了“形胜”观念,明确称其“是呼伦贝尔城之形胜也”,⑤[清]何秋涛撰《朔方备乘》卷十一《呼伦贝尔城形胜》,清光绪刻本。这种“形胜”理论的基础建立在呼伦贝尔城的观念上。两段互文叙述所用的一组意象,“控”“抚”“山河险阻”等都是清代描述边境城塞的常用套语。在这种叙事传统之中,呼伦贝尔的意义和重要性集中在“呼伦贝尔城”,而这座城池的实际建成是较晚且缓慢的事情。《呼伦贝尔志略》如此回顾了建城历史:“定议后迄未兴筑,嗣因交易往来……始于伊敏河左岸筑土房为围……城周四里余,就商户市房为垣……道光二十七年创建南北二门……东西二门……光绪三年改修土平门。”[2]37显而易见,乾嘉时代的呼伦贝尔尚不完全具备一般意义上城池的基本形态,文献叙述中对呼伦贝尔城塞意义的强调带有愿景的意味。
官方对呼伦贝尔另一种重构办法是通过修改它的历史叙述,来强化呼伦贝尔作为“八旗满洲”的身份定义。至乾隆时期,尽管对蒙古兴起之初涉及呼伦贝尔史事叙述较多的《元朝秘史》尚未广泛流传,长期刊行的《元史》与首次被翻译为满汉文字,收入《钦定四库全书》的《蒙古源流》中仍然有相关呼伦贝尔的不少记述。《元史》中提到了也里古纳河,犍河,秃律别儿河,海刺儿等地名。清代御用史学家对其进行的解读有些是错误的,①如“秃律别尔”,按《元史》当指今天的额尔古纳河支流得尔布尔河,《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中将其当作满语”Tula bira”理解(汉译改定为图拉必喇,指今日蒙古国的图拉河)。但对弘吉剌部早期居住的“也里古纳河”,改定者还是较正确地认识到此名即是“额尔古纳”。《蒙古源流》汉译本则直接译出了“呼伦贝尔”一词。原文中“o¨ng qaγan ese itege Jˇü,olan Kereyid-iyen ab o¨u morilan ireged,Oon m o¨renü adaγ-un K o¨len Büir-e undalan”[3]一句被直接译为“翁汗不信,率克哩叶特之众兴兵前来,迎战于鄂诺河下游呼伦贝尔地方”。②《钦定蒙古源流》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乾隆朝的官方修史者还是清楚呼伦贝尔同蒙元帝国关系的。
但是在代表朝廷用意,对东北的历史地理进行官方解释的《钦定满洲源流考》中,修纂者对于呼伦贝尔境内发生的蒙元史事基本完全不引述。在有些地方还采取了刻意的回避态度。书中在对明代羁縻卫所的考证中,直接否认了元朝兴起的斡难河是明实录中的“斡难卫”所在地,称“温都卫,旧讹幹滩,今改正。明实录:永乐四年与嘉河同置。原文作斡滩,又讹斡难,乃元始兴之地,即今鄂嫩河,与嘉河远不相涉。考兴京西百五十里,有温都河出八盘岭,入浑河,音转而讹为斡滩耳”。③[清]阿桂等撰《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乾隆皇帝宁可放弃对祖先活动地域的夸大,明确否定明实录的“斡难卫”为斡难河,将其改定到今日辽宁本溪一带,这种策略初看似乎有些令人费解。究其心态,这还是出于一种将“满洲故地”同历史上东北古族建制联系起来的策略。
在《满洲源流考》之中,为建构“满洲”同历史政权之间的联系,关于东北历史与疆域的描述被总结为“若肃慎以下故城旧治,及渤海金元之所建置遺迹”④[清]阿桂等撰《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系统。实际上,这里指的“元之所建置”大多数时候只包含原属渤海辽金的地域,蒙古兴起之地和东道诸王封地完全被回避不提。有关“呼伦布裕尔”的记录被归纳到“明卫所城站”一类中。书中将扎敦河、济尔玛泰等处视为明朝并未实际控制的“明初疆圉,东尽于开原、铁岭、辽沈、海盖,其东北之境全属我朝。及国初,乌拉、哈达、叶赫、辉发、诸国,并长白山之讷殷,东海之窝集等部”⑤[清]阿桂等撰《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历史区域。为论证东北地区是清政权祖先的固有土地,就不可避免地将这个区域同元朝和蒙古人的关系尽量回避。继续沿袭这个思路,乾隆时修撰的《钦定八旗通志》《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等文献中,呼伦贝尔的居民和区域被明确定义为“八旗满洲”一部分。将呼伦贝尔作为“八旗”而非“蒙古”,除了行政体制的要求之外,也有清朝统治者重造民族历史的用意。
官修著作中将呼伦贝尔同“蒙古”切割的策略一直影响到了近代。嘉咸时期满族士人福格仍然坚持相信,“国朝未得辽沈以前,四世咸宅于此。本为辽金之地,索伦则辽人苗裔,混同江则金人苗裔俱在焉(辽之兴始于呼伦贝尔,金之兴始于伯都讷)”[4]。此类说法魏源和徐宗亮沿袭。《圣武记》称:“辽起上京,即今黑龙江北之呼伦贝尔地也。”⑥[清]魏源撰《圣武记》卷一,清道光刻本。徐宗亮在《黑龙江述略》中则进一步将有关黑龙江的历史谱系总结为“古肃慎氏遗墟……后魏时有黑水属勿吉,辽时始专其号。金元以后,部落散属,或羁縻臣之,不列版图”。⑦[清]徐宗亮撰《黑龙江述略》卷一,清光绪徐氏观自得斋刻本。在徐氏视角下,呼伦贝尔城的地域也属于这个谱系,“呼伦贝尔城,居呼伦、贝尔两湖之间。因以为名。一名海兰儿。故辽上京临潢府地”。⑧[清]徐宗亮撰《黑龙江述略》卷二,清光绪徐氏观自得斋刻本。
从雍正十年( 1732)设置到乾嘉时期,清政权完成了对“呼伦贝尔”区域和身份上的定义,这个阶段中官方声音是关于呼伦贝尔叙述的主导。官方对呼伦贝尔叙述的重构不仅是一种政治策略,也是清政权基于当时边疆局势所勾画的图景。这个时期正是清代北部边疆最稳固的阶段,中俄边界的平稳与清朝对喀尔喀蒙古的控制,使得呼伦贝尔不再像清初期一样处在危机前哨。清政权将呼伦贝尔从“牧地”改写为“城塞”,从“蒙古”改写为“八旗满洲”和“辽金故地”,某种程度上是把它从“外部”改写为“内部”的举措。
三、晚清以来边疆危机与呼伦贝尔叙述的转型
近代呼伦贝尔叙述的转变,是从元史研究的进展开始的。蒙元历史研究的深化使得知识分子重新注意到呼伦贝尔同蒙古的关系。屠寄的《黑龙江舆图说》则中将呼伦贝尔的历史渊源较之《满洲源流考》体系大为提前,称其地为“元太祖尝建兴都于巴勒渚纳海子南寻,以其地封合撒儿大王,其东北境以封宏吉剌氏。……明初元裔脱古思帖木儿驻牧于此……国初索伦部及外蒙古喀尔喀车臣汗属之巴尔呼人杂居之”[5]。这些历史学考证,成为了在“蒙古”问题框架下思考呼伦贝尔局势的基础。
晚清时期的边疆问题也使有识者对呼伦贝尔有了新的关注点。19世纪80年代时,几位内地有识之士纷纷关注到了呼伦贝尔。汤寿潜政论《防俄》指出:“额尔古纳河接俄界。呼伦城亦宜以木路达之。以为节节扼要,面面响应。”[6]清代呼伦贝尔的卡伦巡边或早期驿传,广泛利用的主要是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干流的冬季冰面,甚至俄境一侧,对于边疆危机中的中国而言这无疑是不利的情势。世人以为巩固呼伦贝尔的边疆安全,就需要呼伦贝尔内在交通与军事一体化的加强。这种视角下,呼伦贝尔不再是单纯的边境,也不是单纯的城塞,而是一个扼守边疆的有机整体,对准噶尔战争期间强调过的呼伦贝尔战略地位,此时被重新提出,且较前代重视程度更高。姚文栋在《筹边论》中尖锐地指出:“若黑龙江与俄划中流为界,此与三国时吴蜀距江为守情事相类。所谓沿江上下所在皆险,而尤以额尔古纳河通入黑龙江口一处为最要,俄若拦入额尔古纳河进踞呼伦贝尔。则江省与蒙古声息中断。俄得以纵横自如。江省既无自全之策,蒙古亦大有危机矣。”[7]葛道殷《近日北边防务轻重缓急何在论》强调了筹边论的思想,进一步指出额尔古纳河口一带“此处宜驻重兵以备之此皆边防之所重者急者”[8]。在蒙古地区局势日趋动荡之时,处于东三省、俄罗斯和喀尔喀蒙古交接点的呼伦贝尔重新成了边疆问题敏感地带。清末士人也因此开始将呼伦贝尔局势同蒙古局势联系起来统筹考量。
清末以宋小濂为代表的边官边吏的著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和话语背景下进行的。《呼伦贝尔边务报告书》中,宋小濂对呼伦贝尔形势进行了新的叙述:“呼伦贝尔为黑龙江西边门户,外蒙古尾闾,有屏蔽省城,控制喀尔喀之势。且兴安岭横绝中间,俨如瓯脱。”相较前代基于黑龙江省城的地理视角,边务报告书中的方位感已然大大本地化。“屏藩”“瓯脱”这类意象,亦采用自对蒙古历史的常见叙述方法。《边声》之中,宋小濂更是使用了文学想象去勾勒出作为“蒙古”的呼伦贝尔。呼伦贝尔的纳入中央管辖的过程被总结为“胡儿三万服威德”[9]151,根河北岸蒙元时代故城引发了“当年雄略起边陲,今日英风犹爽飒”[9]179的感慨,而对呼伦贝尔八旗官兵的嘱托则是“回头切切语我蒙,尚武无忘前代功”。关于元代的回忆和想象已经不单是史地考证,而是寄托着中华民族重新强盛的向往。这种将族群上的蒙古同地理上的元兴之地融合的思想,在宋小濂的叙述中完成了统一。同期由笔帖式恩纶于1908年所绘的一副“呼伦贝尔地图”中,除了标记山水、卡伦、台站之外,还第一次标注出了关乎呼伦贝尔八旗生计、不见主要史志的两处地名,“那罕台树林”与“墨能平野”。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舆图,001243,光绪三十四年笔帖式恩纶绘呼伦贝尔地图。沙岗之上的那罕台树林“在呼伦贝尔公署迤西……纵约四十余里,横约十数里不等”[10],是呼伦贝尔草原地区重要的木材和薪炭来源。“墨能平野”在今日新巴尔虎右旗宝格德乌拉山至乌尔逊河之间,为重要的牧场营地。此时传统官方叙述中忽略的新巴尔虎八旗牧地,已经开始得到了地方官员的重视,这种叙述方式和思维同前代相比已经大为不同了。
由于呼伦贝尔特殊的多民族驻防体制和较晚移民活动,关于呼伦贝尔的地方叙述要比东三省其他地区和内蒙古六盟相对更晚出现,其中汉文的乡土叙述更是凤毛麟角。从这个意义上讲,呼伦贝尔最早的汉文乡土叙述就是清末边官边吏的记载。乡土叙述和官方叙述的融合,也进一步说明了关于呼伦贝尔认识的成型。
进入民国初年,呼伦贝尔即经历了独立和自治风波,数年后时黑龙江省方才恢复对其管理。复治之后,宋小濂、赵春芳等清末时期就在呼伦贝尔任职的官员依然延续了将呼伦贝尔在“蒙古”问题视角下观察的思路,1922年编纂完成的《呼伦贝尔志略》沿袭了这种治边思想。其《艺文》部分中所录张家璠诗作《呼伦贝尔怀古》,仍然继续着《边声》中的主题,将呼伦贝尔边疆重振的愿望寄托在元朝的辉煌历史中。“根河阔滦考遗踪,烈祖诸子封土裂……黄种势力未可量,成吉思汗旭烈兀。土人毋忘祖业强……”[2]322-323同年印行的《黑水先民传》,也继承和发展了屠寄将蒙元之兴起纳入黑龙江地区历史的观点,更进一步提出“以江省为辽金元清四代龙兴之地”[11],将成吉思汗等元朝人物列入黑龙江省历史名人之中。
事实上,直至20世纪20年代,呼伦贝尔八旗地区有别于“蒙古”的体制也并未发生基本变化,北洋政府对蒙古盟旗的措施办法也并未施至呼伦贝尔地区。在另外的官员和士人的视角下,呼伦贝尔的政治特征仍然是迥异于蒙古的黑龙江八旗体制的。1914年,时在黑龙江省教育司任职的林传甲的《龙江旧闻录》,其中列举了汉族知识分子心中呼伦人和蒙古人的差异:“呼伦为副都统镇守旧地,异于各蒙古以盟长领之,一异也;呼伦官制为总管副管佐领,异于蒙古以台吉梅楞,二异也;呼伦种族为索伦、达呼尔、巴尔虎、额鲁特,皆非蒙古种族,三异也;呼伦各族受前清所赐之地以守边,异于蒙古世守土地,四异也;呼伦之兵官隶省城之兵司、前清之兵部,若蒙则旧属理属院,五异也;呼伦已设府厅,异于外蒙古,未尝设官,六异也;呼伦税局皆为正供,异于蒙荒大租各蒙旗各得一半,七异也……”①②《清史稿》卷一三三,民国十七年清史馆本。对于民国时代传统的史官而言,呼伦贝尔八旗也依然是八旗满洲的身份。1927年完成的《清史稿》对新巴尔虎部重要历史人物仍然是这样描述的:“杜嘎尔,哈勒斌氏,满洲正蓝旗人,黑龙江驻防。”从清中期开始形成发展的呼伦贝尔叙述,同法律意义上的“蒙古”并不属于一个话语体系。文化层面的蒙古属性和政治上的八旗身份形成了呼伦贝尔的双重体系,近代呼伦贝尔的“蒙古”叙述一方面改写了中国人对呼伦贝尔的观念,另一方面也率先在汉语文化传统中扩展了“蒙古”的概念,将清代法律意义的“蒙古”重写为更广义文化意义上的“蒙古”。
结语
呼伦贝尔八旗是在蒙古高原的一个游牧人群与文化为主的区域中,植入“八旗满洲”的体制,形成的特色区域。清朝政府为了强化这个区域的“满洲”属性,除了采用八旗满洲管理体制外,在其历史书写中亦进行了多方面重构。另外,呼伦贝尔在文化和环境上同蒙古高原的不可分性,令清朝官方建构的呼伦贝尔叙述在乾嘉时期开始被打破。晚清官纂史学的式微同边疆史地学的兴起,连同时局的变化,推动着呼伦贝尔叙述向蒙古史地方向的转型。最终,官方书写在清末民初的黑龙江发生了转变,地方志书中的呼伦贝尔重新被塑造为“蒙古”。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G].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393.
[2]程廷桓.呼伦贝尔志略[M].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1924.
[3]乌兰.蒙古源流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 585.
[4]福格.听雨丛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
[5]屠寄.黑龙江舆图说[G]/ /辽海丛书:第3集.沈阳:辽海书社,1924: 1042.
[6]防俄[G]/ /求是斋校集.皇朝经世文编五集:卷二十四.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7.
[7]筹边论三·论东北边防[G]/ /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七十九.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0.
[8]近日北边防务轻重缓急何在论[G]/ /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五十.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2.
[9]宋小濂.边声[M]/ /李澍田,主编.宋小濂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10]苏都护呼伦贝尔调查八旗风俗各事务咨部报告书[M].海拉尔:呼伦贝尔历史研究会,1986: 4.
[11]黄维翰.黑水先民传[M]/ /李兴盛,主编.黑水郭氏世系录(外十四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09.
[责任编辑:那晓波]
作者简介:孔源( 1985—),男,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清史与民族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3&ZD082)
收稿日期:2015-09-20
中图分类号:K249; K2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 2016)02-015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