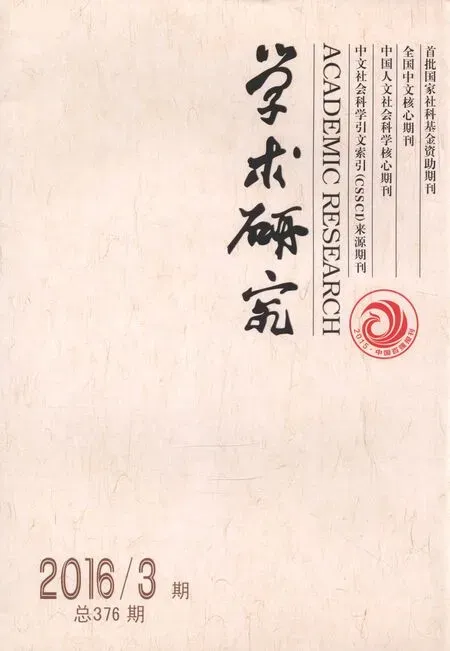当代外国文论新动态——从四部著作看外国文论四个取向的进展
周启超
当代外国文论新动态——从四部著作看外国文论四个取向的进展
周启超
[摘要]后理论时代的外国文论研究并未终结。文学理论的基础研究与前沿研究都在推进。文学学、文学地理学、文学文本分析学、理论学派与集群发育学都有新的进展。我们用德文、法文、俄文、英文撰写的四部文论著作为例证,描述出当代外国文论在这几个取向上的新收获。
[关键词]文学学文学地理学集群发育学文本分析学
一、《新德语文学学导论》与文学学
文学学(literatur wissenschaft,文学科学)发源于德国。当代德语文论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主要集中于接受美学与法兰克福学派著作,译介时间主要在20世纪80—90年代。本义或狭义的德语文论著作,在非德语专业读者的接受视野里,如果不算其身份主要是哲学家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或主要是美学家的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主要有耀斯、伊瑟尔、凯塞尔、施泰格尔的著作。以汉斯·罗伯特·耀斯与沃尔夫冈·伊瑟尔为标志的康斯坦茨学派的著作,得到了当代中国文论界积极关注。伊瑟尔的著作尤其受到当代中国译者青睐,出版界一度竞相推出其汉译本,甚至是英译本的转译。在此之前,当代中国对德语文论的引进,主要有《语言的艺术》与《诗学的基本概念》。
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沃尔夫冈·凯塞尔(W.Kayser)(1906—1960)《语言的艺术作品——文艺学引论》的汉译本,该书1948年在伯尔尼初版后多次再版,1992年,图宾根第20版;南京大学陈铨先生还在1965年就据该书1956年第4版将其译出,“文革”使得这本德语文论著作汉译本被延迟了20年,改革开放才得见天日。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埃米尔·施塔格尔(E.Staiger)(1908—1987)《诗学的基本概念》,该书1946年在苏黎世初版后重版多次;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胡其鼎据该书第5版将其译出。《语言的艺术作品——文艺学引论》与《诗学的基本概念》为其代表作,一度成为德语国家与地区大学里相关系科的必读参考书。两著提出的基本概念被不少文学术语辞典收入,成为文学学入门必读。埃米尔·施塔格尔和沃尔夫冈·凯塞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语文论界在文学学方法史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他们坚定地承续了20世纪上半叶“思想史—形式分析”流派。
然而,这两部著作的成书年代距今相隔70多年,即便是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康斯坦茨学派,距今也相隔半个世纪了。凯塞尔与施塔格尔之后,德语世界的文学学有什么新进展?耀斯与伊瑟尔的接受美学以降,当代德语文学学有什么新气象?一部优秀的德语文论教材也许就是观察德语文学学进展的一个窗口。带着这样一份希冀,我们开始了对当代德语文论教材力作的搜索。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新文学理论:西欧文学学导论》(西德出版社,1997)。该书是德国著名学者克劳斯—米歇尔·波哥达主编的《新文学理论——导论》的第2版。导论对20世纪70年代以降西欧文学学主要流派的重要学说加以评述,对德国新阐释学、文学作用与文学接受理论(狄尔泰、伽达默尔、耀斯、伊瑟尔)与法国后结构主义(福柯、拉康、巴尔特、阿尔都塞、德里达)进行概述,回顾20世纪德国文学学历程(世纪初在方法学上的多元论、50年代学院派文学学危机、60年代去神秘化等),对话语分析这一方法作了阐释。《导论》共十章,均由德国学界本领域著名学者撰文,简明而清晰地介绍和评价了当代文论十个主要流派。这部文学学导论其实是当代德国学者视野中的欧陆文论。
不久,我们发现了《今日德国哲学文学学(文选)》(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2001)。这部德语文论选,由接受美学发祥地康斯坦茨大学两位青年学者迪克·乌菲利曼(1969—)、卡罗琳·施拉姆(1967—)编选,收入当代德国人文学界最著名的学者16篇文章(其中有沃尔夫冈·伊瑟尔《论虚构行为》、曼弗雷德·弗兰克《论寓言与反讽》、莱纳塔·拉赫曼《论记忆与失忆》),对当代德语文学学的发展倾向作了相当全面的展示:对精神分析、互文性、互媒体性、女性主义文学学、解构主义、文学社会学、哲学美学等作了一一介绍,对德国文学学的历史、体裁理论、功能理论、虚构理论、系统理论以及记忆、神秘、圣像等一一加以概述。这部文选定位于高校语文系、哲学系以及所有对当代文学学感兴趣的学生和教师。从这部《今日德国哲学文学学(文选)》,可以窥见当代德国文论的风貌。可是,我们得到的是这部德国文论选的俄译本。我们多年倡导并践行国外文论著作的引进要自源语种直译的译介理念。于是,我们请北京大学主攻德语文论的王建博士出马,终于找到《新德语文学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Stuttgart & Weimar:Verlag J.B.Metzler,2007)。这部文学学导论由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德语系的两位教授联袂撰写。两位作者均为1961年出生,其专业方向又很近。贝内迪克特·耶辛(Benedikt Jeβing)主要研究歌德及其时代和20世纪德语文学及文学理论,拉尔夫·克南(Ralph Köhnen)主要研究18至20世纪德语文学及文学理论。两位德语系教授以导论的形式,深入浅出地介绍这门以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学科,介绍文学学的各种研究角度、理论方向与文学的各类体裁,介绍描述修辞学、风格学和诗学的基本理论,探讨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如造型艺术、音乐、电影、广播)的关系,阐释20世纪各种文学理论与方法。全书的分章结构再现了新德语文学学的轮廓,力求中立地展现文学学反思对象本身的全部景象。叙述系统,表述精细,使得这部文学学导论甚称当代德语文学学著作的代表。它不仅仅追求全面论述文学学的各个层面,而且追求通过字体设置、页边标题和文本框等方法,使得全书显得结构清晰,条理分明,关系明确,使用方便。作为大学文学类专业的文学学教材,此书属于同类书籍的佼佼者。
《导论》对于当代中国读者的价值,在于它是德国学者绘出的当代德语文论流变全景图,我们从中看到:当代德语文论中,与接受美学一同出场的还有其他学派;接受美学本身也还有后续发展。
经验性的接受研究关注特定的阅读方式如何产生,为什么某些读者偏爱某些文本,读者如何建构文本的意义;研究者让读者对文本进行自由联想,总结内容提要,进行改写或者词汇填空。由此出发,格勒本借用英加登的概念,提出“具体化的振幅”(Konkretisation samplituden),用这个概念来形象地展示阅读中主观要素的偏离作用。结果显示,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不仅局限于现代文本,而是作为机动要素原则上适用于“所有文学作品”。在后来的经验性—建构主义的研究框架中,格勒本指出,即使在学术领域中意义也不仅被接受,而且以意义修辞格的形式被建构,阐释的标准不是“正确性”,而是“生存力”,这就是说取决于一个阐释如何可以被接受,多大程度上有效,可带来什么样的视角,推导出来的结论是否可行。
当代德语文论的多形态性提示我们:不应把当代德语文论简化为接受美学。即便是接受美学,我们对她的接受也还有不小的空间。《导论》在论及20世纪后半叶的德语文学学结构形态时指出,自50年代起,德语文学学就不再是铁板一块。思想史、阐释学和形式分析学派是直到60年代三种最重要的趋势。随后,文学学的方法最终变得越来越多样,更迭越来越迅速,使得这一学科时至今日呈现出多层次的方法多元性。《导论》作者梳理出1965年以来的德语文学学方法丰富多彩的趋势:1965年起的接受史和接受美学,同时期开始的文学社会史;结构主义的开端;70年代下半期的心理分析文学学;80年代初话语分析完成了这一学科的根本范式转换;90年代初以尼克拉斯·卢曼为代表的系统论;最新方法论构想是最晚于90年代末发现的文化研究/文化学、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性别研究和新历史主义,它们成为文学学的主导范式。《导论》作者看出:在过去35年中,文学学的问题越来越多样化,文学学的方法和时尚变幻纷呈,文学学的范式更迭越来越快——这一切只是文学学200年来发展历史的最新阶段。《导论》归纳出当代文学学的10大范式:阐释学;形式分析学派;接受美学;心理分析文学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文学的社会史/文学社会学;话语分析;系统论;传播学;文化学。
《新德语文学学导论》对中国读者的价值,更体现于本体与反思层面:有助于推进我们对文学学这门学科的反思。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其命名应当是文艺学还是文学学?它是一门人文学科还是一门人文科学?这些问题,关乎文学研究的性质与宗旨、路径与方式、价值实现、社会使命、文化功能的定位。德语文论界对文学学有自己独特的建构,对文学学之理论问题的研究一向颇为重视。马克斯·维尔利(M.Wehrli,1909—1998)曾著有《文学学导论》(维尔茨堡,1948)、《普通文学学》(伯尔尼,1951;俄文版,1957)。后者主要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诸国的文学学现状。该书第一编“总论”逐一论及文学学地位、文学学系统、文学学历史。该书不仅提供一个关于新德语文学学基本知识的概览,“按照对象、程序、方法和术语诸方面再现了新德语文学学的轮廓”,而且还“中立地展现文学学反思对象本身的全部景象”。对文学学的起源与发展、对象与手段、方法与技术,均有清晰的论述。
文学学(literatur wissenschaft)既不是指具体的文学个案研究,也有别于文学理论(literatur theorie)和文学批评(literatur kritik),前者主要关注文学理论各种流派,后者不属于学术研究范畴,而是指出现于报刊杂志的印象式评论,主要是书评形式。文学学则是关于文学的各个方面的科学。
文学学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8世纪下半叶,最初是作为法语étude de la littérature的德语翻译,当时的表述是文学的科学(wissenschaft der litteratur),尚未形成一个复合词。要到19世纪上半叶才出现文学学一词,成为文献索引中的一个分类,包括文学史和文学学方面的著作,同时用来指专业性的文学研究。19世纪80—90年代,在文学史和语文学专业化和学科化的过程中,文学学由于文学科学这一字面含义被用来作为纲领性的口号,成为这一学科自我定位的直接反映。不过,大学的文学专业实际上还是按照语种或国别划分,文学学这一概念的真正确立要到20世纪,此后又逐渐出现普通文学学和比较文学学的专业和相应的理论体系。虽然这一概念产生较晚,尤其是作为学科很晚才得以确立,但是在内容上它表现为各个国别或者语种的文学研究,在德国主要表现为德语文学学,通常表述为“日耳曼语文学”或“德语语文学”,这一学科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逐步确立起自己的地位。
德国的文学学首先是读者文学学,它对当代世界文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德国文学学何以能在读者文学学上有如此丰厚建树?这与德国人文学术中极为丰厚的“哲学—阐释学”的涵养紧密相关。
二、《文学世界共和国》与文学地理学
一心要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作家、批评家以及理论家们,总在追问世界文学是如何形成的?总要探讨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关系。近些年,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二元对立问题获得新的话语形式:本土化与全球化。有人坚守“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这一铁律,有人则主张必须实现对民族性的超越,必须实现身份转换,才能跻身于世界文学。在各种各样对世界文学的生成方式、世界文学之发育机制的理论思考中,法国当代批评家巴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 1959—),可谓独辟蹊径。她将其对世界文学的考察转换成对文学世界的勘探。在其于2000年获法兰西人文协会奖,已被译为多种文字的力作《文学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Paris:Edition du Seuil,1999)中,她将世界文学看成是一个整一的、在时间中流变发展着的文学空间,拥有中心与边缘,首都与边疆。这些中心与边缘并不总是与世界政治版图相吻合。文学世界犹如以其自身体制与机制运作的共和国。
卡萨诺娃认为,文学与世界之间存在一个中介空间,专属于特定文学性质的争论和创新问题的讨论和斗争;在这个空间中,政治、社会、民族、性别、伦理等“各类斗争最终依照某种文学逻辑,并且通过文学形式得到折射、变形或改造。”基于这样一种新颖的世界文学观,卡萨诺娃沉潜于充满竞争、博弈的“文学共和国”,细致地勘探一些作家与流派进入世界文学的路径与模式,分析文学资本的积累过程与方式。她以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贝克特、易卜生、米肖、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等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精华的大作家创作为例,探讨一些民族文学在文学共和国里的身份认同问题,探讨民族文学与民族之外的文学语境、世界文学语境之间复杂的互动机制,建构其令人耳目一新的“民族文学的文化空间”理论:一种旨在探索“世界文学空间生成机制与运作机理”的文学地理学。
《文学世界共和国》的立意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作者看出,“直至今日,在不同的民族文学教材中,对世界文学的描述只是一个简单的并列”。作者认为,应将文学空间作为一个总体现实来理解。应该与所有幻想特殊性和岛国性的,与独一无二的民族主义习惯相分离,尤其应该终结文学民族主义造成的局限性,这就需要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本身说明事实上已出现了一个跨民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要讨论文学的跨文化性。正是文学的跨文化性在建构文学世界共和国。文学世界共和国的结构机理犹如亨利·詹姆斯的一个隐喻——飞毯上的图案。一切被写出来的、被翻译出来的、发表了的,一切理论的、评论的、出名了的书都是这种飞毯构成中的一部分。每部作品都像飞毯那样,只有从构成的整体出发才能被解码;只有与文学世界相联系,才能在其一致性中凸现出来。每部作品都是整个世界文学的庞大而复杂组合中的一个小构件。而跨民族的文学世界共和国有自己的运行模式和生成机制:
在17世纪,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最大的商业中心,但在艺术及文学上却是罗马和马德里占据统治地位;在18世纪,伦敦成为世界的中心,但占据文化霸权地位的却是巴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济上,法国在欧洲经济中排名靠后,但却不容置疑地是西方文学及绘画中心;而意大利及后来德国的音乐统治地位也不是发生在意大利或德国经济很强盛的时候;现在仍然如此,美国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并没能让美国成为文学或艺术之首。
卡萨诺瓦走向了一种对世界文学空间运行相对自主自律的机制的考察。她以动态模式挑战全球化的平静模式。这一视界,对于动辄套用经济全球化模式来考察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学之简单化做法,是一种警醒。文学资本的积累与经济资本的积累自有关联,但并不能直接划等号。卡萨诺瓦在其文学地理学的勘察中,还看出中心与边缘的互动。
所有远离中心的作家不是注定一定会落后,所有的中心地区作家也不一定必然是现代的。文学世界的特殊逻辑,忽略了普通的地理因素,建立了与政治标记完全不同的领土和边界,比如,这一种特殊逻辑可以将爱尔兰人乔伊斯和德国人阿尔诺·施密特联系在一起,让南斯拉夫人达尼洛·金斯与阿根廷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走得很近;或者相反……致力于将文学定义为统一的世界领域(或者正在走向统一的世界领域),人们就再也不能借用“影响”,也不能借用“接受”的语言来描述特殊的重大革命在世界上的流通和输出(比如自然主义,或者浪漫主义)。
卡萨诺瓦对文学世界的特殊逻辑的这种清理,对那些执着于梳理某些大国文学对小国文学、某些大作家对小作家之创作的影响轨迹的比较文学者的思维定势,也是一个挑战。身处边缘的民族文学要走向中心,自然要借助于翻译。然而,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和平行转换。翻译并不是中性的。她强调,翻译在民族文学的跨文化运作中具有工程师地位,所谓翻译的中立性是表面的。所谓美学标准的普世性其实是握有文学“祝圣”之话语权的普世性。由边缘走向中心是要讲究策略的。
在世界文学领域形成和统一的四个世纪中,各国作家为了创造和收集各自的文学资源,或多或少都是根据相同的逻辑进行斗争和采取策略的。两大策略是各民族文学中所有争斗的根基,一种是同化,通过一切原初差异的淡化或抹煞达至融合;另一种是分化或差异化,根据民族性的要求肯定各自的差异。
卡萨诺娃对同化与分化这两大策略的分析,对于我们习惯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原理,是一种超越,也是一种补充。《文学世界共和国》在其文学地理学的建构中,将世界文学的探讨转换成文学世界的勘察,力图“解决内批评——只在文本内部寻找意义要素——和外批评——只描述文本生产的历史条件——之间被认为不可解决的自相矛盾”,尝试在文学跨文化空间中定位作家和作品,提出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新说,有助于开阔观察世界文学的视野,可以作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教材。
三、《艺术话语·艺术分析》与文学文本分析学
《艺术话语·文学理论导论》(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дискурс·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ию литературы,Тверь:Твер.гос.ун-т, 2002)系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理论诗学与历史诗学教研室主任,叙事学与比较诗学研究中心主任瓦列里·秋帕教授(Валерий Тюпа,1945—)的一部讲稿,其授课对象为高校文科教师和研究生。讲稿的主题是“文学何谓?”作者在这里致力于克服文论教材中围绕这一问题而常常高头讲章的通病,选取简约而不简单的入思路径,深入浅出地阐述文学的符号性、审美性、交际性。如文学的符号性,作者说:
文学在其他的艺术样式中明显地得以突出,这是由于它采用已然现成的、完全成型而最为完备的符号系统——自然的人类语言。可是,……文学本身乃是“非直接言说”。作者诉诸于我们的并不是自然的话语语言,而是派生性的艺术语言。文学文本并不是直接地诉诸于我们的意识,就像在非艺术的言语里发生的那样,而是要经由中介——经由我们内在的视觉与内在的听觉于内在的言语形式展开的那些对文学文本的思考。这一类作用,乃是由作者的符号学活动来组织的,作者由这些或那些原初的表述——建构成派生性表述:作为“艺术印象诸因素之集合”的整一的作品。
在阅读文学文本时,艺术性表述的这一特征容易被视而不见:文本的民族语言通常是已经为我们所熟悉的。但不是艺术语言。譬如,在果戈理的中篇小说《鼻子》里,作为某个涵义况且也是基本涵义之最重要的符号而显现的,毫无疑问,乃是少校柯瓦廖夫的鼻子不翼而飞这件事本身。鼻子丢了这一情节——这自然是个符号,但这是什么东西的符号呢?并不存在同果戈理的中篇小说脱离开来的那样一种语言,在这种语言的词典里,人的面孔的该种变化会对应着一种特定的意义。每一次例行的阅读便类似于用个体化的语言进行一次例行的表述。
那么,作为“职业读者”的文学学家,究竟应该如何分析文学文本呢?《艺术分析·文学学分析导论》(Аналитик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введение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М.:Лабиринт.РГГУ, 2001)则是这位著名文学教授的一种现身说法。在这里,多年在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一线耕耘的瓦列里·秋帕力图建构了独具一格的文学文本分析学。作者以科学性为文学文本分析的旨趣,将文学看成艺术现实来具体地解读文本的意义与涵义,致力于阐明科学性与艺术性、文本与意蕴、分析与阐释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记录、体系化、同一化、解释、观念化”5个逐渐递进的分析层级,以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阿赫玛托娃的名篇《缪斯》为例,用清晰的语言详加分析,有理据地演绎自己的理论。其解读紧扣文本,其论述深入浅出,其路径令人耳目一新,深得学生和教师的欢迎。瓦列里·秋帕的力作《艺术话语·文学理论导论》与《艺术分析·文学学分析导论》,篇幅不大但内涵丰厚,既以新视界阐述文学原理,也以新维度展示文本分析,彼此有内在关联,堪称相得益彰的姊妹篇,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上具有开拓精神与创新锐气。
四、《20世纪人文学科的理论学派与集群》与理论学派或集群发育学
《20世纪人文学科的理论学派与集群——文学理论、历史及哲学》[1]是英国Routledge出版社“跨学科视界下的文学研究”系列丛书之一,2015年初版。两位主编来自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玛丽娜·格里莎科娃是塔尔图大学比较文学副教授,著有《纳博科夫小说中的空间、时间及视觉模式》(2012年第二版),并与玛丽—劳里瑞安合作出版《媒体间性与故事讲述》(2010),在《叙事》《符号系统研究》《比较文学杂志》(法语)等杂志发表论文数篇。西尔维·萨鲁皮尔在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任教,合作编辑出版了《符号系统研究》《塔尔图符号学图书馆》《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概念词典》等书刊。
理论学派和集群是20世纪学术运动的主要推动力,它们促进了学科内部和学科之间的思想交流,从而改变了学术研究的内容。该书关注一系列看似联系松散的理论学派,认为它们有非常明显的文学学、语言学和符号学内涵,同时又涉及哲学和历史学,因此从概念所属上形成了一种跨学科的联系。该书主编在前言里描述编撰目的时,鲜明地指出“本书旨在提供一种了解20世纪人文学科理论学派、集群及组织的新视界。它不仅促成概念性知识,还是一种文化与社会现象。”主编明确提出该书探讨的主要问题:“学派与集群对20世纪的学术氛围产生了何种影响?某一集群内部或集群与其学术环境之间交流的模式是什么?概念性知识如何转换为文化环境?学派或集群延续着一套什么样的解释性约定以及认识论上的偏好?学派或集群内部以及外部接受其运作方式会带来何种影响?学派与集群如何形成、怎样瓦解?缘由何在?”[2]简而言之,其主题堪称“理论学派或集群发育学”。该书共由14章组成,涉及的理论学派有: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巴赫金及其文学集群、布拉格文学集群、波兰结构主义学派、格雷马斯符号学集群、泰凯尔学派、耶鲁学派、芝加哥学派、日内瓦学派、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学派、特拉维夫诗学与符号学学派、诗学与阐释学学派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等。该著将文学理论置于人文学科大框架之中来考量其发育,具有以下特点:1.强调文学理论的跨学科性;2.关注文学理论学派或集群之间的关联性,而非仅仅逐一介绍;3.各章作者都为业内专家,因此能够提供内部观点,体现了观点的专业性。
(一)强调文学理论的跨学科性。书名的核心词之一为“人文学科”,而副标题则为“文学理论、历史及哲学”,因此有必要厘清人文学科的定义,以及人文学科与文学、哲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并分清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界限。《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人文学科”条目指出:“人文学科(humanities),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特别在美国的综合性大学。人文学科是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总和。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独特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的学科”,[3]人文学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以人文主义、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种对于鲜活灵动的人性、人的精神、人的价值与人文主义的研究,显然不同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自然与社会客观规律的研究。从人文学科的定义可以看出,哲学、历史与文学都属人文学科,而这三者之间从来都不孤立存在,因此探讨文学理论,就不能撇开其与哲学、历史的关系。因此,该书对20世纪文学理论学派或集群的论述,涉及文学理论与哲学、历史学的联系,体现出非常明显的跨学科性,将该书收入Routledge出版社“跨学科视角下的文学研究”系列丛书非常切题。前三章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学术运动的画面,这些学术运动产生了跨学科的整合,意在构建自省式的、在方法论上坚实的人文学科,以期有别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以及盲目的经验主义大潮。正如前言所述,“20世纪早期,各个学科都显示了知识整合的趋势和跨学科的转移,认为整体的、描述性的方法优于起源性探讨。心理学、哲学(以胡塞尔、布伦塔诺、蒂奇那为代表)、语言学(以索绪尔、雅各布森为代表)、文学研究、符号学(俄罗斯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以及法国结构主义为代表)、数学、生物学莫不如此。这些早期的学术团体分为阐释学、哲学和符号学等多个分支,其潜在影响以及多样性在世纪末达到顶峰。”[4]该书从跨学科的角度来观照20世纪以来的重要文学理论学派或集群,提供了新视界。
(二)关注文学理论学派或集群之间的关联性。本书所论及的各个理论学派或集群并非单孤立现象。美国普渡大学人类学及语言学教授Myrdene Anderson认为本书所论及的文学理论学派或集群之间有着繁复的联系:“进入21世纪,西方世界仍继续在理解和超越过去。20世纪,在战争与和平的交锋中,在包含英语在内的数种语言之间,学术思想往复跨越北大西洋,错综复杂,异彩纷呈。本书的作者们致力于研究这些学术运动,寻求他们独具特色、交相重叠和经久不衰的特征。”该书各章展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学术分歧与聚合、联系与传播、相似与分离。较之标准的主流历史,这部著作对20世纪的文学理论学派或集群开展了更为深入的挖掘。该书认为,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提出的一些核心概念,如陌生化、情节编织、动机等,在新批评、后结构主义及其他一些学派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5]再如,巴黎符号学派事实上是不同集群与运动的集合体;而康斯坦斯接受美学学派是以德国科学院改革运动为背景,源自一个较为宏大的诗学及阐释学集群的微小内核。全书聚焦一些看似相互之间松散关联的协会组织,但实际上它们形成了“一种从概念与亲属关系或类似的问题驱动的直觉感而产生的跨学科领域,揭示了文学理论和文学作为无主物,处于政治、美学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动荡地位”。[6]
(三)体现内部观点的专业性。本书各章作者都是该理论学派或集群的资深研究者,甚至是学派代表人物。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英语文学及叙事理论教授Luc Herman评论该书时称:“一方面,它简明易读地介绍了20世纪重要文学理论学派。另一方面,与这些学派或集群相关的文章作者们给出了内部观点。因此,本书的内容既切题又有趣。”例如,所谓耶鲁学派,指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并活跃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几个有影响的教授,包括保尔·德·曼(Paul de Man)、哈洛德·布罗姆(Harold Bloom)、杰夫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和希利斯·米勒(Joseph Hillis Miller)。曾经有人把耶鲁大学上述4位最有名气的批评家称为“阐释学黑手党”(Hermeneutical Mafia)。[7]而阐述耶鲁学派的那一章名为《(耶鲁)学派的故事》,作者即为希利斯·米勒。作为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从事欧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解构主义耶鲁批评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勒的重复理论与解构批评的实践展示了经典作品丰富多样的内涵和意义,解读文学作品的无穷可能性与潜在多样性,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开拓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由他本人来叙述耶鲁学派的故事再合适不过。再有,《芝加哥学派:从新亚里士多德诗学到修辞叙事学》一章由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写就。费伦是当今国际公认的叙事理论专家,《叙事》杂志主编,他的另一个标签则是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历经克兰(R.S.Crane)、布斯(W.Booth)、费伦,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在这三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扩大影响。从本质上看,芝加哥学派的基础理论为文学是读者与作者的交流。作为该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克兰认为,批评家应首先把握小说的情节类型,然后才能评判小说的人物、意象、措辞、视角等细节安排;布斯则将叙事看作是作者利用文本与读者进行交流的行为,他重点探讨了多种叙事技巧与叙事效果之间的关系;费伦则在布斯的理论之上,进一步阐述了叙事交流的多层次性,重点探讨叙事进程。作为布斯的学生,费伦非常清楚芝加哥学派的来龙去脉,因此他的论述足以令人信服。
该书各章的作者从专业角度出发,阐释理论学派或集群的核心概念、思想渊源、发展流变。这一梳理不仅会促进文学理论观念史、思想史研究,还会推动文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书中所论述的结构主义学派、符号学、现象学和阐释学派,对文学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该书还涉及一些多年来未得到深度开采的理论学派,譬如波兰结构主义、特拉维夫诗学与符号学学派、法国年鉴学派等,体现出理论学派或集群之深度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收获。
[参考文献]
[1][2][4][5][6] Grishakova, Marina & Silvi Salupere eds.,Theoretical Schools and Circl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umanities——Literary Theory, History,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15,p.viii,p.x,p.2,p.xi.
[3]《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760页。
[7] William H.Pritchard,“The Hermeneutical Mafiaor,After Strange Gods at Yale,”Hudson Review,28(Winter 1975-76).
责任编辑:陶原珂
作者简介周启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中图分类号〕I3/7099、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3-014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