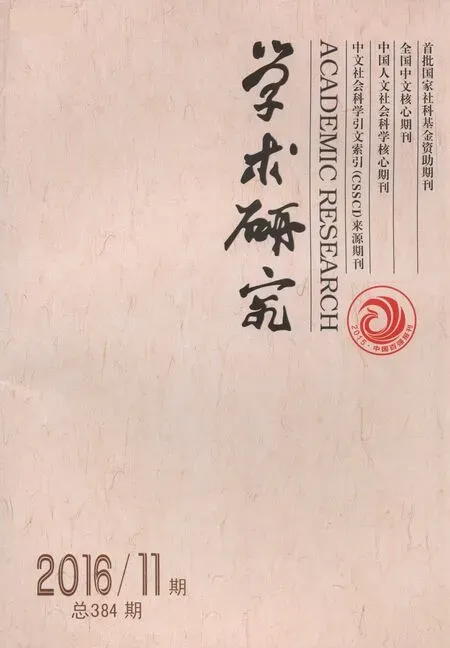人寿年班与近现代粤剧的革故鼎新*
沈有珠
人寿年班与近现代粤剧的革故鼎新*
沈有珠
“人寿年”是清末民初粤剧著名戏班,其风雨30年正是粤剧从农村走进城市、唱响上海舞台及海外唐人街的历史,粤剧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革:从岭南水乡进入城市,从班主制到公司经营管理制,从无编剧到专业编剧因人度戏及其引发的剧目、脚色行当变化,完成了从舞台官话到声腔字韵的本地化,从岭南风格到中西合璧风格的变化等等。号称省港第一班的人寿年班,积极引领了粤剧史上的革故鼎新。
粤剧 人寿年 红船班 省港班 革故鼎新
自1889年(光绪十五年)八和会馆成立以后,粤剧悄然兴旺,演出活动十分频繁,每年组建的红船班多达30—40个。“人寿年班”创建于19世纪90年代,寓意人寿年丰,太平兴旺,是晚清红船班四大名班之一,民国初年属宝昌公司旗下,有“省港第一班”的美誉。1933年因故解散,后改组为自负盈亏的兄弟班,并以“胜寿年”的班牌继续组班演出,唱响省港澳、上海及东南亚、北美各国。它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粤剧人才。“人寿年班使千里驹获得‘花旦王’、‘悲剧圣手’,白驹荣获得‘小生王’,靓荣获得‘武生王’的美誉;而薛觉先之后来成为‘万能老馆’亦是在人寿年班奠定的基础,马师曾的‘乞儿喉’更是在该班演出《苦凤莺怜》始声名鹊起。”[1]20世纪20—30年代风靡省港澳的大罗天班、太平剧团、觉先声剧团、国风剧团、胜寿年剧团、义擎天剧团、日月星剧团等省港大班,其组班人或台柱如千里驹、肖丽章、马师曾、靓少佳、白驹荣、靓少凤、薛觉先、靓新华等,均出自人寿年班,堪称粤剧人才的摇篮。
广东地处沿海,对外通商较早,粤剧受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的影响比较大,为了适应粤港澳城市演出和海内外粤籍观众的需求,与电影等新兴的娱乐形式竞争,人寿年班作为引领粤剧革故鼎新潮流的省港第一班,从演出剧目、音乐唱腔、化妆表演、舞台布景到戏班组织管理等都有了很大的变革。戏剧家麦啸霞欣喜地说:“薛觉先、白玉堂、靓少凤、靓少华诸名伶相继勃兴,均擅平喉声艺。名旦千里驹以平腔白话入子喉(旦喉,班语曰子喉,又曰奕喉),马师曾从南洋归,益以滑稽俗语入调。戏棚官话日益淘汰,二十年间字腔声韵,完全变易;由束缚进于自由,由质实进于活泼,明白通俗,平易近人,无疑已达到‘渐近自然’的境界。”[2]他也客观地指出:“粤剧之优点在于善变,而其危机亦在多变。(多变渐滥,则流弊难免。本质易漓,则基础易摇。)……除自身不断的蜕化外,通识尽量吸收外来腔调。”[3]没有粤剧兼容并收的改革与创造,就没有粤剧在20世纪20—50年代的繁荣与广泛传播,粤剧从一个岭南水乡的剧种成为海内外著名地方剧种。从人寿年(含胜寿年)在粤剧舞台上风雨沧桑50年的历史,可以窥探粤剧从农村到城市再到海外唐人街的变化历程,看到“粤剧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4]。
一、从岭南水乡到粤港澳城市舞台
晚清时期,粤剧戏班以船舶为栖息及载运工具,活跃在水网四通八达的珠江三角洲及西江、北江、东江一带的郡邑乡落,演出通常无固定戏台,农村、小城镇的祠堂、庙宇即戏台。组建初期,人寿年班的演出大都在农村小城镇,观众主要是农民,以及城市市民、小商人等。红船时代人寿年演出的剧目有《六国大封相》《天官贺寿》《八仙贺寿》《破台》《祭白虎》等传统例戏,还有酬神戏、天光戏、“江湖十八本”和“大排场十八本”,以及各老馆的首本戏。如以演周瑜著称的周瑜利,清末已有“第一小武”美誉,他的《山东响马》《周瑜归天》等叫好又叫座;还有肖丽湘的首本戏《金叶菊》《桂枝写状》;肖丽湘与小生聪合作的《游湖得美》《拉车被辱》;肖丽湘、风情杞的《再生缘》等。
宣统元年(1909),受当时蓬勃兴起的革命思潮影响,“‘人寿年’排演了一出弘扬岳飞精忠报国精神的新剧《岳飞报国仇》。新白菜饰演岳飞,豆皮梅饰李若水,梁垣三饰宋徽宗,在社会上反响很大,革命党在香港的机关报《中国日报》,特给梁垣三等赠送“石破天惊”的横幛。”[5]1911年,一些社会开明人士发起驱除嫖赌饮吹四大害的运动,人寿年班的千里驹、小生聪就演出了一套时装戏来配合宣传,剧目为《小生聪拉车被辱,千里驹演说儆夫》。赵连城回忆道:“著名小武周瑜利和武生公爷创领衔到澳门演出《说岳传》的《金兀术入寇中原》和《岳飞报国仇》两折戏,在澳门掀起一阵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高潮。”[6]新剧目顺应了清末民初的社会潮流,适应民主革命的需要,起到了粤剧改良新戏以唤起民众的社会效果,受到了广泛欢迎。
民国以前,粤剧对化妆不重视,只用乌烟按演员自己的眉眼勾画,双颊涂红粉。化妆品只有简单的胭脂纸、三凤粉,化妆效果不好还有毒,著名演员陈非侬由于长期使用三凤粉,右手中了铅毒,几个手指不能屈伸自如。人寿年班的薛觉先“开始对化妆悉心研究,陆续采用梅兰芳用的胭脂膏和芙蓉香粉,用这些化妆品比用胭脂纸和三凤粉美观,又减少了铅毒的侵害。”[7]20世纪20年代,人寿年班率先学习京剧的化妆方法,为修饰演员的面型,生脚将勒“人”字形的水纱改勒圆形,旦脚贴片子;一些较常使用的脸谱,如关公脸、包公脸等,改按京剧脸谱勾画等。
清末民初,由于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影响,粤剧戏班禁止男女合班,严禁女子上红船,认为会招致船沉人亡之灾。人寿年班为全男班,出现了花旦王俏丽康、千里驹、肖丽湘、刘家銮、玉麒麟、章仔、靓伦、千里驹、嫦娥英、冯敬文、新丽湘、靓广仔、林超群等一批著名男花旦。1933年秋,香港取消男女不得同班的禁令,出自人寿年班的大佬们闻风而动,率先改革:薛觉先组织男女临时班;马师曾的太平剧团在香港聘请了谭兰卿、麦颦卿、上海妹三个女旦正式组织男女班;白驹荣在香港组织“风雅”男女班。1936年,广州允许男女同班,白驹荣、廖侠怀、谭秀珍等人率先成立“国泰”男女剧团,粤剧进入男女合班的时代,全女班、全男班随后销声匿迹。
民国初年,粤剧戏班分化出省港班与落乡班来,一些大班常来往于广州、香港、澳门演出,称为“省港班”,不走农村小码头,观众从市民到富商、官绅均有。“人寿年拥有武生王新华、小武王周瑜利、花旦王俏丽湘、丑生王豆皮梅等‘四大天王’,当为四大名班之首,其中花旦王俏丽康是连接几年班的一代红伶。”[8]“个个唱做俱工,各擅胜场。”[9]此阶段人寿年班的剧目渐渐发生了变化,“表演上注重武生、小武生主演的正本戏,由小生、花旦串演的剧目也日益增多。”[10]人寿年班这些变化,为后来逐渐发展演变为以文武生、花旦为主戏的省港班进入城市打下了基础。而“粤剧进入城市,标志着粤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1]
二、从班主制到公司经营管理制
近代广东的商品经济发展很快,这些资本家大都兼营其他实业,实力雄厚,为民间资本投资粤戏班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因而所组织的戏班规模庞大,名角众多。从此粤剧的演出业务大多被各大戏班公司所垄断。当时比较著名的戏班公司有:怡顺公司、宝昌公司、太安公司、兴利公司、宏顺公司、汉昌公司等。[12]各大公司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纷纷罗致名角,相互竞争,推动了粤剧班业的发展。在戏行公司中,宝昌公司是其中实力最雄厚的,成为执戏班公司牛耳的王牌公司,老板是何萼楼,手下拥有“人寿年、周丰年、国中兴、华天乐”等超一流的粤剧戏班。何萼楼的宝昌公司还直接经营戏院,仅广州就有东关戏院、海珠戏院、河南戏院、乐善戏院,还租用澳门的清平戏院、香港的高升戏院。[13]而戏院的大量建造,催生了以城市平民为主要欣赏对象的大量粤剧新剧目的出现,涌现出一批新型编剧,基本上改变了粤剧的剧目体系。”[14]
宣统年间,人寿年班率先由宝昌公司经营管理,从原来的广场、庙台、草台、戏棚转移到城市华丽的剧场演出,开始步入黄金发展期。宝昌公司把吉庆公所管理时期的戏班等候四乡主会上门买戏变为公司主动上门联系卖戏,直接安排人寿年班在自己经营的各大戏院表演,解决了人寿年班难以租到其他公司经营的戏院的困难。宝昌公司在人寿年班的资金、艺人、戏院和演出等管理环节上操作有序,人寿年班占领了省港粤剧的半壁演出市场,被称为“省港第一班”。 公司经营戏班“这不但使粤戏班达至前所未有的繁荣,也使粤剧在珠三角和港澳各地进一步盛行。民国初年经历了商业竞争洗礼的粤戏班为粤剧的成熟发展刻上了商业化的烙印。”[15]特别突显的是前幕上必定刊登广告,广告上的电话号码、门牌、招牌等写在最耀眼的位置,人寿年班影响最大,承接的广告最多。
宝昌公司按照商业化的模式经营人寿年班,以重金礼聘大老倌及文化界知名人士,加强人寿年班的广告宣传和联系戏院等业务,从多种途径增加人寿年班的知名度以争取更多演戏机会。宝昌公司老板何萼楼素以眼光独到、知人善任著称,经他物色、培养而成名的演员为数不少,人寿年班早期的男花旦肖丽湘、千里驹,武生王靓荣、小生王白驹荣、小生聪,后期如万能老倌薛觉先、丑生泰斗马师曾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时千里驹只不过是东江惠州班中规模最小的戏班——龙门班(即八仙班)中的一个小学徒。在他17岁(1905年)那年,随戏班在东莞石龙镇演出时,被何萼楼赏识,以三千元将其写给师傅的“师约”买断,并将其艺名改为“千里驹”,希望他将来能驰骋千里,这是他艺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经过何萼楼的悉心栽培,千里驹技艺突飞猛进,成为粤剧界执花旦行牛耳20多年的花旦王。[16]光绪三十年(1904年),小生聪加入何萼楼的人寿年班,因其演出大受观众欢迎,班主何萼楼推出的戏目特加上小生聪之名,如《小生聪游湖得美》《小生聪拉车被辱》等,以吸引观众。
在何萼楼的引领下,人寿年班的大佬们形成了善于奖掖后进、扶持新学的班风。“小生聪乐于扶掖后辈,悉心指导千里驹,令其终成名旦。”[17]千里驹在人寿年班的“十多年间,先后在该班演出的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嫦娥英、白玉堂、靓少凤等,均受到他的扶掖。”[18]千里驹把薛觉先从一个年薪仅三百元的“拉扯”,破例提拔为年薪二千元的三帮男丑,并有意让薛觉先多担戏演主角,如《可怜女》中的巧儿、《狸猫换太子》中的宋仁宗等主角。千里驹乐于扶持新人,被粤剧界尊为“伶圣”。
三、从无编剧到专业编剧因人度戏
红船时代演出的剧目大都是传统例戏,大部分连脚本都没有,也没有开戏师爷。那时很多艺人能自己开戏,不过有些好剧目因剧本比较粗糙,不卖座,经过文人作曲加工后,卖座率大大提升。麦啸霞认为:“自文人加入编撰,词华本色兼资,韵律益趋工细,而情理交孚,华实并茂。”[19]发展到省港班时代,红船时代没有的开戏师爷即编剧家应运而生,编剧成了失意文人的一份职业,许多文人投身于粤剧编剧行业,著名粤剧编剧家有唐涤生、丁英、麦啸霞、骆锦卿、黎凤鸾、李公健、南海十三郎、黄不废等100多人,“出现了专门以编剧为业,靠出卖剧本吃饭的职业编剧组织,如:‘登龙编剧社、非非编剧社、青年编剧社’等。”[20]各班编演的新戏层出不穷,新剧目超过万个。对于这一时期的粤剧盛况,潘一帆的《粤剧全盛期》这样评价:“为了争取观众,分头搜罗编剧家,因人度戏,然后编写新剧,作业务上的竞争,各自出奇制胜,或以剧本号召,或以布景宣传,勾心斗角,这是粤剧蓬勃因素之一。”[21]
人寿年班等省港大班以新戏招徕观众,聘请开戏师爷、著名编剧来为演员量身打造剧本。“近代粤剧偏重唱工的剧目较多,要求剧本创作和音乐唱腔结合得更紧密。因此,为适应频繁更换新戏的要求,使演员容易掌握,节省排演过程,许多编剧人员照例兼任编腔撰曲,剧本写作与唱腔音乐设计由一人承包。”[22]薛觉先未曾“扎起”之前,与千里驹、白驹荣合演《可怜女》,饰“巧儿”一角,仅两场戏。“座中有许多被当时群众谑称为‘猫儿头鹰’的达官贵人的姬妾(因她们多梳一种状似猫头鹰的发髻),看到‘巧儿’死去,纷纷流泪离座而去。洛锦兴(卿)看到这种情况,便对薛觉先看好,便着人编了《三伯爵》剧目,交薛觉先演出,又大受那些‘猫儿头鹰’的欢迎。”[23]小生白驹荣初到人寿年班时寂寂无名,及至发现他演《金生挑盒》颇有观众缘,“班主马上编出了《孟丽君》这出戏来演‘风流帝王’,从此名气越来越大,还发展成独树一帜的流派。”[24]在马师曾加入后,千里驹以马薛二人戏路不同,改编曲词给马协助演《泣荆花》一剧,该剧是20世纪20—30年代粤剧的保留剧目之一。人寿年班的坐舱骆锦卿还是著名的编剧,他为马师曾编写的《苦凤莺怜》《佳偶兵戎》等都是粤剧经典剧目,使马师曾一炮走红,名闻省港,历半个世纪而不衰。人寿年班的大佬薛觉先、马师曾等均能自编自演自导。
20年代后期,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千里驹等名闻遐迩的大老倌先后离班而去之后,人寿年班陷于困窘,此阶段挺身而出的是班中另一重要人物——坐舱、编剧骆锦卿。他大胆起用了一批次等老倌担纲演出,编写新戏《龙虎渡姜公》。该剧一炮打响,班业蒸蒸日上,连年走运。后来又编出一剧《十美绕宣王》,也是连台本戏,从1928年一直演到1933年元旦被禁演为止,连演将近四年之久。人寿年班成为当时粤班不景气氛围中少数几个能连年盈利的戏班之一。“本届戏班,盈利最多者为人寿年班。盖人班所藉以为号召之三大剧本《龙虎渡姜公》《十美绕宣王》《状元贪驸马》,内容深染神怪色彩,且剧中事实,都系从旧剧改编而成者。……此种剧本,既早为观众所认识,更加以宏伟之布景,与神怪之穿插,故能处处卖座,个个欢迎,盈利实意中事耳。”[25]
红船班时代流转于各码头戏棚的剧目安排制度发生了变化,必演的例戏,偶尔在逢年过节才演出,演出剧目题材渐渐从传统例戏、历史演义转向更适合城市市民趣味的演绎男女爱情戏,许多成名生旦戏如:千里驹、小生聪的《夜送寒衣》《金叶菊》,子喉森主演的《七贤眷》,靓少凤、千里驹的《裙边蝶》《柳为卿愁》,千里驹、白驹荣的《金生挑盒》,以及薛觉先的《三伯爵》,马师曾的《苦凤莺怜》《姑缘嫂劫》等。都是在人寿年班首演而一炮打响的。新型编剧适应城市平民的审美变化,大量是以才子佳人、家庭伦理为主题的粤剧新剧目,“基本上改变了粤剧的剧目体系。”[26]
专业编剧的出现还带来了脚色表演行当的变化。人寿年班等省港大班的专业编剧编排的生旦戏,剧情更为精炼,角色人员也精简许多,其它行当的表演艺术得不到充分发挥,许多有特色的传统表演艺术如排场、南派武功日渐丢失,渐渐武生消失,生、旦并重的格局成了主流,人寿年班的当红大佬,小生白驹荣、靓少凤,花旦千里驹、林超群、靓广仔、骚韵兰、苏小伶,小武靓少佳、靓新华,男丑蛇仔利、马师曾、薛觉先、罗家权等,都不是武生行当。生旦戏的流行逐渐引起粤剧脚色行当从传统十大行当变为“六柱制”,“即以文武生、小生、正印花旦、二帮花旦、丑生、武生为台柱支撑演出。其中文武生和小生,正印花旦和二帮花旦的唱做差别不大,因而实际上只有四个行当,其它行当逐渐废弃而至失传。”[27]粤剧的一些传统行当、排场、武功遭到毁灭性打击。
四、从舞台官话到声腔字韵的本地化
同治年间,粤剧悄然在舞台官话中插入白话,清末的“志士班”大力推进白话演出,之后朱次伯、金山炳、白驹荣也努力改唱白话,但变化缓慢,直到20年代末,还停留在半官话半白话的状态。戏剧家齐如山在民国十九年以前曾看过粤剧:“还完全保存着梆子型式,话白亦系中州韵,自然夹杂了许多本地土音,但大体还未改,广东人管此叫作舞台官话,我们还能懂六七成。自从摩登的戏出来,这种旧戏就慢慢的不见了。”[28]著名粤剧艺术家红线女曾谈到她小时学艺,仍然是舞台官话。①见2009年羊城国际粤剧节座谈会上红线女的发言,当时笔者在座。新旧交替的时代变化引发了新编剧目的变化,新编剧目内容的变化又引发了唱腔的变化。
红船时代剧目分为梆子戏和二黄戏,梆子、二黄两种腔调互不混杂。粤剧进入城市后,掺杂广州官话演唱流行开来,唱腔音乐将梆子、二黄、牌子、小曲等连缀成段或成套,形成板腔体、曲牌体交融在一起的变化丰富的戏曲生腔,他们能吸收众长,融为一体,运用自如。清末,人寿年班的“名艺人肖丽湘就从昆曲、高腔、皮黄等剧种中移植改编了《六月飞雪》《牡丹亭》《仕林祭塔》《拗碎灵芝》《渔家乐》等剧目。”[29]武生王新华“就吸收了乱弹腔《陈姑赶船》的腔调到粤剧中来。”[30]粤剧专家陈卓莹回忆道:“我幼时看过著名的小生聪、名丑蛇公礼,他们的念白,时常带有顺德、台山等口音,观众不得不以为异,反而传为美谈。”[31]“不少老艺人根据现实生活的要求和本人的具体情况,也往往同编剧、乐师合作创造新的音乐唱腔。他们不仅吸收龙舟、木鱼、南音、粤讴等民间说唱文艺的腔调,还接受了电影、歌剧、流行歌曲,舞场音乐等的曲调,甚至将器乐曲填词歌唱,并且创作了许多小曲。”[32]千里驹早年习小武行当,后改学花旦,嗓子稍沙哑,但他却苦心钻研唱腔,创造出独树一帜的驹派唱腔,直接影响了嫦娥英等新一代粤剧演员。梅兰芳评价千里驹的“驹腔”:“唱曲能露字,口法极佳,又能咬线(弦)……”[33]
白驹荣是早年将传统粤剧小生由戏棚官话唱假嗓,转以广州话唱平喉(真嗓)的先驱者。在首本戏《金叶菊》中扮演周淑英,打破了当时粤剧舞台上唱和念白都用戏棚官话的惯例,大胆使用广州话结合戏棚官话,表演长篇念白“读家书”。坊间有言:“只听千里驹读家书,就值回票价。”白驹荣在剧中创造的“八字二黄慢板”经传唱后,成为粤剧常用的唱腔板式。行腔方法上突出简练干净、朴素自然的风格,注重腔与情的紧密结合,白驹荣擅长唱“木鱼、板眼、减字芙蓉”等板式,独特的唱腔被誉为“白腔”,在海内外有许多戏迷。白驹荣经常向民间艺术学习,“他演唱的《客途秋恨》,就是吸取了瞽师(失明艺人)的‘扬州腔’,形成风格独特的‘白腔平喉’。”[34]薛觉先所创的“薛腔”,擅长通过旋律和节奏的变化来抒发人物感情,唱腔精炼优美,是粤剧生脚的重要流派唱腔,海内外流传甚广。20年代,薛觉先“将京剧中的‘五音恋坛、打马过站、快三眼、原板和倒板’等多种唱法运用到粤剧的唱腔中。”[35]“善于突破曲调原来的扮演、句格而创作新腔,如与冯志芬创作[长句滚花]、[长句二黄]等。”[36]马师曾的马腔也独具特色,他在《苦凤莺怜》中创造了一段长句中板的唱段,有意模仿卖柠檬小贩的叫卖声,演唱时用力压迫喉头,创造出一种既让观众听清楚,又能贴近生活的“柠檬喉”发音方法,他在剧中饰义丐余侠魂,时人称为“乞儿喉”。
在人寿年班主领粤剧坛风云时代,粤剧“由于语音的变化,改方言后唱法由假嗓改平喉,唱腔也因而由高线改低线,板式结构从仿照皮黄体制一腔到底,改为腔调变化繁多,旋律由粗到细,由疏到密,加上吸收更多民间说唱以至中外流行歌曲等,早已移步换形,面目改观,剧种的地方特色愈益鲜明。”[37]粤剧终于完成从舞台官话到字韵声腔本地化的转变。用白话演唱,目的是使观众听懂,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精神,由此带来了唱腔、音乐的丰富多彩。此后,粤剧以其独具地方特色的唱腔、音乐而与源流相同的其它地方剧种严格区别开来。但是,除唱腔音乐之外的粤剧的“念、做、打”等艺术手段被抑制,受到粤剧专家谢彬筹如此评论:“甚至变成‘唱塞死做’,有些艺人变成只会唱不能做的‘脚画眉’,从而造成粤剧艺术的畸形状态。”[38]
五、从岭南风格到中西合璧的变化
近代以来,漂洋过海做劳工、经商的华人70%以上是广东籍,粤剧随着粤籍华工、华商的脚步飘洋过海演出,是在海外影响最大的中国地方剧种,也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剧种。马师曾、薛觉先、白驹荣等都不是最早到海外演出的粤剧演员,但他们是到海外演出影响最大的演员。薛觉先将美国电影《郡主与侍者》改编为粤剧《白金龙》,这部戏在广州、香港引起巨大轰动,在东南亚华人家喻户晓;人寿年班的台柱白驹荣在旧金山粤剧舞台改良提纲戏的表演程式,“白驹荣等人所在戏班在旧金山演出时,改变了当地戏班制度组织松散简陋、表演庸俗下流、剧目芜杂等积弊,提高了观众的欣赏水平。”[39]马师曾将美国电影中的布景、灯光等元素引入粤剧舞台;谭师曼、靓少佳和叶克明仿美国电影建立了计划置景和导演制度,粤剧戏班开始重视导演的作用及舞台美术的功能。这些粤剧大佬将西方文化引入粤剧艺术。较之其它中国地方戏,粤剧染上了浓郁的中西文化结合的现代色彩。
(一)伴奏体系从单一的民族乐器到中西合璧的乐器变革
红船时代“或与乡村旷野搭竹棚铺葵叶为戏棚,风高地迥,非有强烈乐音不能及远,故锣鼓特大,弦线特粗,轰轰烈烈,响遏行云。”[40]在城市戏院演出,有着先进的扩音设备,锣鼓等一些民族乐器已淡出粤剧舞台。30年代的“薛马争雄”是粤剧史上的辉煌时期,也是粤剧急剧变革时期,出自人寿年班的大佬们在月琴、箫笛、二弦、锣钹鼓板等岭南民间乐器基础上,还采用了西洋乐器作为伴奏乐器。千里驹最先使用喉管合乐;陈非侬始以梵哑铃和曲;薛觉先在上海结识了一个名叫尹自重的提琴家,薛在稍后组织的新景象粤剧团,就大胆启用尹自重用小提琴参加作伴奏。[41]薛觉先又将萨克斯风运用到粤剧舞台上,开西洋管乐与粤剧原有乐器结合的先河。“薛觉先是杰出的演员和革新家,……他主张‘合南北为一家,综中西剧为全体。’对粤剧的唱念做打、音乐、化妆、服装、布景以至剧场陋习都进行过改革。”[42]30年代,马师曾从美国回港组建太平剧团,只有打击乐器还保留中国乐器,将小提琴、扬琴、萨克斯风、三弦、结他、小号、椰壳胡琴等西洋乐器伴奏引入粤剧演出。“马师曾的戏路也比较宽广,被誉为‘台上霸王’。他富有改革精神,早年立志改革粤剧,从话剧、文明戏等艺术形式吸收了不少表演技艺,也采用了较多的西洋乐器来伴奏。”[43]从此省港大班群起效尤,粤剧乐器大变革,从单一的民族乐器到中西合璧乐器的伴奏,高亢噪杂的声调渐变为流利婉转柔和之节奏。
(二)风格从写意到写实的变革
粤剧进入城市后,由于粤剧剧目的表现内容、剧情发生了变化,传统虚拟程式化的表演风格为之一变,“逐渐的便将原来的格律破坏殆尽,所留的不过是极普通而在中国式舞台上所不能少的几种(如用马鞭当马骑,提腿算进门之类)。”[44]布景设计从无到有,从写意趋向写实,人寿年班等省港大班在舞台布景方面争奇斗艳。人寿年班的花旦王千里驹演出《风流天子》时,“在‘长生殿祭奠’一幕中,运用灯光变化人物形象,天幕正中起初悬挂着杨贵妃的画像,后来用电光变景,变成杨贵妃现形在天幕上演唱。”[45]给观众梦幻迷离之感。这之后,薛觉先采用立体布景并配有彩色灯光;马师曾将拍电影用的天然布景运用到了舞台上。粤剧广泛借鉴电影、舞剧、歌剧、话剧及流行歌曲的艺术技巧,将立体布景等写实性的舞台美术与舞台灯光与电光配景结合运用,形成对观众强大的视觉冲击力。红船时代在水乡码头演出,道具是传统的一桌二椅,此阶段已变成真水漫舞台,令观众目瞪口呆的当众换头术等不胜枚举。较之其它中国地方戏,粤剧现代化、科技化的进程最快。但是过分标新立异,“粤剧始终游移两可,写实又不能彻底,结果,弄成莫名其妙的不调和。”[46]欧阳予倩对此不伦不类的改革给予了批评。
著名戏剧家彼得·布鲁克说:“戏剧需要永恒的革命”。[47]有“省港第一班”美誉的人寿年班是变革粤剧的急先锋,“马师曾是粤剧艺术革新的先驱者之一,他推动完成了粤剧的两次重大变革——即完成了从‘官话’改唱‘白话’,从全男班、全女班改为男女合班的变革过程。”[48]纵观晚清民国时期的戏剧,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昆曲、京剧、闽剧、黄梅戏等中国传统戏剧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粤剧古今杂陈,中西合璧,变化最大。郭秉箴深刻地指出:“它接受了‘改良新戏’编演新戏的做法,而且进一步仿效外国电影,歌剧、话剧的艺术形式,使唱腔音乐、表演风格和舞台美术都日益洋化,而且剧本的题材内容和思想倾向,也渗透了资本主义商业化和殖民化的意识。”[49]变革集中表现在完成了粤剧的地方化、通俗化和现代化,粤剧的艺术风格与表现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粤剧获得了艺术驱动力,在粤港澳及海外粵方言区广泛流行。关于粤剧变革的得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建勋痛心疾首地批评:“这个年代粤剧最大的损失是丢失了传统。”[50]李日星却高扬:“正是在这种东西方文化交融、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大潮中,以珠江三角洲所特有的开放情怀创新精神,打破传统粤剧舞台的沉寂和格局,弘扬粤剧历史梆、黄合流,中西一体,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开创粤剧艺术的未来。”[51]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中不断革故鼎新,粤剧完成了近现代转型。人寿年班积极参与和推动了粤剧的变革,它的历史是粤剧从戏船巡演于珠三角的红船时代到省港澳城市大戏院再到非粤语区上海、海外唐人街的历史缩影。
[1][10][16][18][30][33][34][36][42][48]曾石龙主编:《粤剧大辞典》,广州:广州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748、742、866、864、264、438、876、932、264、867页。
[2][3][19][40]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粤剧研究资料选》,1983年,第45、45、48、41页。
[4][14][26]傅谨:《民国前期粤剧的转型》,《戏剧》2014年第3期。
[5]冯自由:《广东戏剧家与革命运动》,《革命逸史》(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3页。
[6]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界参加革命的回忆》,转引自谢彬等:《近代中国戏曲的民主革命色彩和广东粤剧的改良活动》,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粤剧研究资料选》,1983年,第272页。
[7]陈非侬:《粤剧的源流和历史》,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粤剧研究资料选》,1983年,第161页。
[8]谢醒伯:《话说当年红船班》,《南国红豆》1996年第3期。
[9][22][27][29][32][43][45]赖伯疆、黄雨青等:《粤剧》,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粤剧研究资料选》,1983年,第175、183、183、180、183、185、275页。
[11][38]谢彬筹:《近代中国戏曲的民主革命色彩和广东粤剧的改良活动》,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粤剧研究资料选》,1983年,第246、287页。
[12]刘国兴:《粤剧班主对艺人的剥削》,《广州文史资料》第3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31页。
[13]《粤剧艺术大师白驹荣》,广州: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1990年,第15页。
[15]李婉霞:《论清末民初公司经管的粤戏班》,《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17]赖伯疆:《粤剧“花旦王”千里驹》,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
[20]黄伟:《省港班对粤剧的变革及影响》,《文化遗产》2013年第4期。
[21]潘一帆:《粤剧全盛期》,《大公报》1977年10月4日。
[23]刘国兴:《戏班和戏院》,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粤剧研究资料选》,1983年,第348页。
[24][31]陈卓莹:《红船时代的粤班概况》,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粤剧研究资料选》,1983年,第326、323页。
[25]歌台憨者:《伍秋侬、小丁香,争主人寿年》,《伶星》1932年第36期。
[28]齐如山:《国剧艺术汇考》,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31页。
[35][49]郭秉箴:《粤剧的沿革和现状》,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粤剧研究资料选》,1983年,第396、402页。
[37]郭秉箴:《粤剧古今谈》,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粤剧研究资料选》,1983年,第213页。
[39]赖伯疆:《粤剧海外萍踪与沧桑》,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41]欧阳予倩:《试谈粤剧》,欧阳予倩编:《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140页。
[44][46]欧阳予倩:《粤剧北剧化的研究》,《戏剧》1929年第1期。
[47][英]彼得·布鲁克:《空的空间》,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105页。
[50]王建勋:《二、三十年代广州粤剧得失谈》,《南国红豆》1994年第6期。
[51]李日星:《粤剧改革的现代选择与粤剧化发展》,《南国红豆》2005年第3期。
责任编辑:陶原珂
I207.3
А
1000-7326(2016)11-0156-07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近现代粤剧海外传播研究”(14YJА760025)的阶段性成果。
沈有珠,肇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广东 肇庆,52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