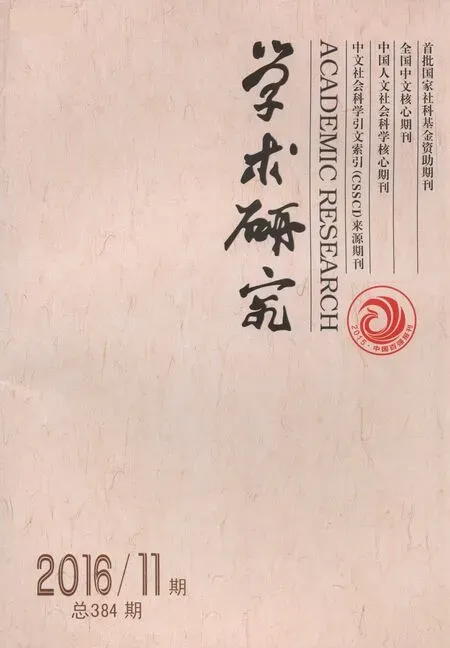略论乡土文学新传统的生成与流变
王福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教授)
略论乡土文学新传统的生成与流变
王福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教授)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几千年中国古代文学根深蒂固旧传统的新传统,而最能体现新文学传统的思潮和作品,我以为是鲁迅开创和倡导,众多新文学者仿效和承续的乡土文学——乡土小说。从题材来看,乡土小说实际上也是新文学的主要类型。这个新文学传统的基本内涵乃是思想内容上的启蒙主义和艺术方法上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一百年来,伴随和反映着世事的沧桑,乡土文学的传统也处在流变中,其创作文本呈现为乡土写实小说、乡土政治小说和乡土反思小说三种形态,时间上相应地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40年代为乡土写实小说阶段,40—70年代中期为乡土政治小说阶段,7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期为乡土反思小说阶段。我想简略地梳理这个流变的历史过程,描画出乡土文学的发展轨迹,从中找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第一阶段:乡土写实小说——乡土文学传统形成和初步呈现多样性的阶段。乡土小说的奠基人和首创者无疑是鲁迅。他的《阿Q正传》《祝福》《故乡》《风波》《离婚》等都是乡土小说的经典,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小说范式,这就是彻底摒弃宗法专制的礼教与“瞒和骗”的旧传统,用人道主义的思想和写实主义的方法,真实描摹中国近代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生活的痛苦,重点则是揭露和批判广大农民身上的国民性弱点,“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以达到启蒙主义的目的,“‘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在鲁迅的巨大影响下,一批青年作者纷纷踏上这条新型的文学之路,从自己的家乡取材,在风土民情中挖掘国民劣根性,表现出新文化者的人文意识、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在“五四”落潮之后的20年代中期卷起了一股乡土写实小说的潮流,使鲁迅创建的乡土小说范式成为新文学的重要传统,并一直延伸到30—40年代。同时影响所及,在海峡对岸产生了从20年代赖和到60年代陈映真的台湾乡土文学一脉,也证明了乡土文学与生俱来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乡土文学”的名称是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首次提出的:“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2]“乡愁”即是人文意识、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这是乡土写实小说的启蒙主义本质特征。与鲁迅相比,这些后继者更多书写故乡的风俗习惯,从古老的颓风陋习到近世的蛮风恶俗,都展示为一个个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文学形象,也使作品带上更加浓厚的地域色彩。例如,乡土小说家承接鲁迅控诉礼教“吃人”的母题,尤其着力将中国各地男人“吃”女人的野蛮习俗暴露于世,有写卖妻的《蚯蚓们》(安徽台静农)、《生人妻》(四川罗淑),有写典妻的《赌徒吉顺》(浙江许杰)、《为奴隶的母亲》(浙江柔石),还有写男人让女人用身体做生意的《丈夫》(湖南沈从文)。直到40年代,写农村妇女被家族私刑整死的惨剧仍在鲁迅弟子的作品中延续,如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萧红的《呼兰河传》。
对“五四”以来包括乡土写实小说在内的偏于暴露社会问题和人生苦难,旨在批判国民性缺点的启蒙主义文学,左翼批评家曾指责其为“只问病源,不开药方”[3],这种批评几十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科书里屡见不鲜,其实是很不适当的。一方面,启蒙文学家能诊察病源已很不简单,开药方不是文学的任务,美中不足的是病源还找得不够准不够深;另一方面,左翼批评家自以为是的药方却并非治病的良方,按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更要治死人的。然而,正是这种左翼开出的阶级斗争为主药的有毒处方,使“五四”新文学开创的乡土写实小说传统后来发生变异,衍生出一种新型而怪诞的文学形态——乡土政治小说,乡土文学的发展由此进入第二阶段。
这里必须补充一点,就是乡土文学中有一类抒情性较强的作品,较少悲剧的严酷色彩而颇含轻松愉快的情调,较少揭露国民性的弊病而多赞扬人性人情的美好,发端就是鲁迅的《社戏》,后来的废名和沈从文卓然成为此类小说的大家。许多研究者把它们命名为“乡土抒情小说”,与乡土写实小说并列,甚至把在文体上倾向散文化的萧红也归到这一类。我认为这种分类法值得商榷,它们在大类上仍然应该属于乡土写实小说,不过是其中抒情成分较多的一类,总体上并没有抛弃现实主义的写实方法,更没有背离改造国民性的基本主题。这类小说的出现和成熟,显示了乡土写实小说的丰富性多样性。
第二阶段:乡土政治小说——乡土文学传统在变异中曲折发展的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北方送来的暴力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借助外交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欺骗宣传,对中国社会主要是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使孙中山为首的一批民主革命先行者和陈独秀为首的一批新文化先驱者先后走上了以俄为师的不归路。当这种激进理论迅速付诸实践以后,一批接受了苏俄理论并参加了革命实践的新文学者,就把这种更新的力量强大的思想元素加进了乡土文学的创作,因而本来时间不长的乡土写实小说新传统便产生变异,由于外来因素强势介入的衍生物乡土政治小说便应运而生。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特征都逐渐发生质的演变,阶级斗争压倒了思想启蒙,暴力革命压倒了人道主义,消灭私有制压倒了改造国民性,为政治服务的宣传压倒了追求真实性的写实。我用“压倒”而不是“取代”来描述这个演变的状况,意思是说乡土写实小说原初的素质并没有一下子完全消失,演变有一个过程。乡土政治小说的情况相当复杂,虽然它的出现可溯源于30年代初的普罗小说,但整个30年代乡土文学的主流仍属于乡土写实小说,40年代的文学地图才变了,国统区是乡土写实小说,解放区是乡土政治小说,所以,处在转型期的40年代既是第一阶段的终结,又是第二阶段的开始。
乡土政治小说不再以乡村的风土人情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而倾力表现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作家也不再是启蒙者教育者,而是转换身份成为工农兵的学生,一起进行阶级斗争的革命同志。小说所表现和服务的政治主要是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从40年代末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到50年代赵树理的《三里湾》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60年代柳青的《创业史》和浩然的《艳阳天》,直到70年代浩然的《金光大道》,这些写于不同年代的乡土政治小说代表作,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人物的人性成分越来越稀薄直至完全泯灭,所谓“阶级性”的色彩越来越浓厚直至完全脸谱化,作品中展示的生活图景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来越大直至根本相反。总的来说,第二阶段乡土政治小说与第一阶段乡土写实小说的差别越来越明显,最后彻底抛弃了新文学的全部优良传统,堕落成反人性反现实的文学怪胎。
然而,我们必须对这个阶段的乡土政治小说进行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例如30年代初左翼作家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就不是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处理笔下的人物,典进春宝娘来生儿子的秀才地主比兼作皮贩的农民丈夫显然多保留了一点善美的人性,以致春宝娘内心希望残暴的丈夫病死后她能长久和地主一起生活。柔石之后,在左翼或革命作家中,虽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却并未完全舍弃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代有其人,不过常常被边缘化为批判对象,但正是他们艰难地延续着新文学的光荣传统,也使乡土写实小说在变异为乡土政治小说的过程中仍得以曲折地发展,薪尽火传,生生不息。
50年代赵树理的《三里湾》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是乡土政治小说中仍保持着乡土写实小说传统的范例。作为真诚信仰共产主义的老革命作家,他们理所当然地热烈歌颂并积极参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其反对资本主义和私有制,拥护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政治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可是,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面对熟悉的父老乡亲的时候,他们尚未泯灭的人性和良知使得他们不忍心把对合作社有疑虑而愿意单干的农民视为阶级敌人。这些农民存在于农村各个阶层,固然禀性自私,但渴望勤俭致富,也合情合理。两位作家带着同情和幽默批评了农民的自私落后,又用喜剧笔调把他们都送进社会主义集体大家庭。特别是,《山乡巨变》把所谓犯过“右倾”错误的乡党支部书记塑造成德高望重抵制“左倾”的正面形象,这在乡土政治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两位作家对故乡翻天覆地变革的充满人情味的描写,恰如当年鲁迅所说,“也只见隐现着乡愁”。
物极必反。“文革”中赵树理惨遭虐杀和浩然的备极殊荣,标志着乡土政治小说的两极,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也走到了尽头。生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乡土文学,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乡土反思小说——乡土文学传统回归和提升现代性的阶段。这里所谓“乡土反思小说”,是指20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来以历史反思为整体特征的农村题材小说。消灭“四人帮”的伟大壮举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人民阔步迈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而最大的历史性变化发生在农村,被打成贱民的“四类分子”恢复了公民权利,实行家庭承包和取消人民公社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私有制经济,几亿农民恢复了免于饥饿和恐惧的自由,并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大大推动了城市建设和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可见,所谓改革,实质上就是恢复由于阶级斗争而失去的自由平等的人权,虽然这是极普通的常识,然而半个世纪阶级斗争话语的权威使人们对这些常识觉得新鲜而陌生,甚至不敢理直气壮地接受。在这种旧体制僵而不死的时代背景下和国民性大倒退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基本态势也必然是久违了的乡土写实小说传统的复苏即回归。在止于1989年的新时期文学思潮中,狭义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内容上是有时间界限的,前者指揭批十年“文革”的浩劫,后者则追溯到“文革”前17年。两者出现的时间非常接近,由最初倾诉和疗救“文革”造成的伤痕,自然上溯到反思和重新评价一个时代的历史,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和思想解放运动同步发展互相促进,创造了现代文学史上空前的辉煌。虽然狭义的反思文学的高潮因政治惯性的压迫过早落幕,但“反思”已经内化为所有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作家的普遍意识,成为整个历史转型期优秀文学的共同特征。广义的反思,超越了对某一个具体政治运动的重估,扩展和上升为力求恢复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折腾史、苦难史和心灵史的真相,清理和批判外来阶级斗争和本土皇权专制合成一体的恶之源。乡土反思小说在回归乡土写实小说的启蒙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添加了厚重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提升了思想的现代性;在创作方法上则多方吸取融化古代民间文学资源和现代西方文学资源,提升了艺术的现代性,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再套用鲁迅的话,它们是“乡愁”的现代版。古华的《芙蓉镇》是乡土反思小说的第一部长篇,“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既与乡土写实小说的传统一脉相承,又突显出沧桑巨变后新的时代特色。此后,如张炜的《古船》,余华的《活着》,陈忠实的《白鹿原》,一部接一部,不绝如缕,无不是乡土反思小说的里程碑式的经典之作。而莫言从《透明的红萝卜》经《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到《生死疲劳》,终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中国的乡土反思小说达到了现代世界文学的巅峰。
回顾乡土文学的百年史,我们可以总结几点认识:第一,乡土为新文学之本,农民为乡土文学之本,人道主义是乡土文学永远的思想旗帜;第二,人类文明的进化史是曲折的,阶级斗争可以猖狂一时,但终究邪不压正;第三,必须坚持正视和批判现实的文学精神,反对瞒和骗,艺术上则必须多样化现代化。我相信,乡土文学将在百年传统的基础上开出更美丽的花朵,结出更丰硕的果实,而这是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变革互为因果的。
[1]《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6页。
[2]《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
[3]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81年,第3页。
责任编辑:陶原珂
I206.6
А
1000-7326(2016)11-015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