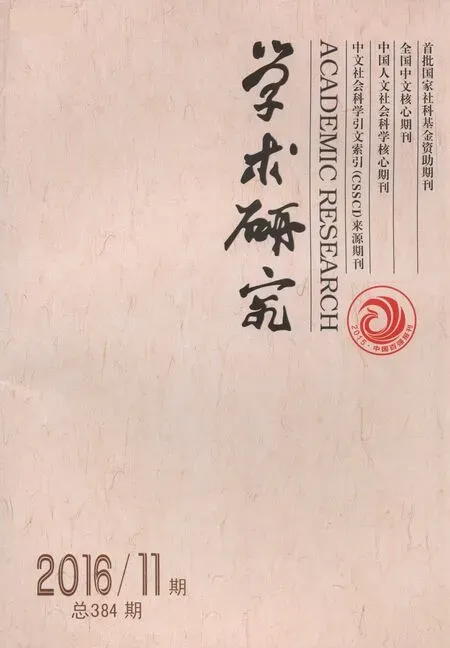古典传统是否构成现代文学的剧情主线
张 均(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古典传统是否构成现代文学的剧情主线
张 均(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最近20多年,由于美国学者柯文的“寻求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stоrуlinе)”[1]的学术观念与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的交互影响,学界有关古典传统与现代文学之关联的研究骤然增多。其中,重审“五四”激进主义、拒绝“断裂说”倡导“转型说”逐渐成为新的共识。早在1992年,陈平原即表示,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外来影响只能起刺激和促进的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变革动力应该来自这一文学传统内部。”[2]这在方法论上无疑正确,就“感时忧国”(夏志清语)或“文以载道”的文学功能观而言也比较贴切;但若推论到文学本体上,认为古典传统或千年文脉实已构成现代文学剧情主线,就要“相与细论”了。断裂说诚然有欠严谨,但转型说恐怕也只是“人心思旧”舆论氛围中研究者对文学史事实刻意筛选、叙述的结果。古典传统是否构成现代文学的剧情主线呢,可以就其雅、俗两脉分而述之。
一
近人夏曾佑(别士)曾称:“中国之小说,亦分两派:一以应学士大夫之用;一以应妇人粗人之用。”[3]此种分法于小说未必允当,但于中国古典文学整体而言,可谓抓住了要害。其中“应学士大夫之用”的文学(雅文学),主要指诗歌、散文及部分文人小说,亦是今日学界所谓“古典传统”的主要部分。那么,这种士大夫文学是否构成现代文学的剧情主线呢?
这要从士大夫文学的内在原理说起。其实魏晋诗歌也好,明小品也好,《红楼梦》也好,共享着中国文人某种集体性的生命体验与文学逻辑。斯蒂芬·欧文(宇文所安)曾用“追忆”一词概括中国古诗的特征,认为“在西方传统里,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意义和真实上,那么,在中国传统中,与它们大致相等的,是往事所起的作用和拥有的力量。”[4]这是说,相对于西方文学力求揭示“不公道的世界”的历史真实(藉此批判社会),中国士大夫文学在本质上对求取社会进步缺乏兴趣,而更多系心于灵魂的自我救渡,救渡之途则在于回忆的诗学。何谓“回忆的诗学”?因为现实社会过于黑暗令人不愿直视,也因为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令人不能承受,中国文人的内心往往被虚空缠绕。“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5]这种怀疑不但指向现实社会,也指向改造社会的文化/政治努力。故在视一切如梦幻泡影的情境下,士大夫往往将人生志趣转移到酒、药、吃、女人或古玩之上,文字世界则为其一。文字安慰内心悲哀的方法,可表现为故乡风物的绘写或方外世界的营构,但最有效者却在于往事再现,在于回忆业已逝去的生命瞬间,即用残存的(往事)碎片“设法构想失去的整体”,“把现在同过去连结起来,把我们引向已经消逝的完整的情景”,从而使“已经物故的过去像幽灵似地通过艺术回到眼前。”[6]往事涉及较广,但凡童年、青春以及一切承载着美好价值的事物,皆可纳入其中。士大夫文学藉此时间空间化的处理,以艺术再造之境承受、缓解着“大的悲哀”,多半会达成淡泊宁静的平和之美,从而不再执于现实的不堪或人世的无常。但偶而也有例外。譬如曹雪芹这样的钟于情者,很可能会从这平静边缘意外跌入更大的痛苦旋涡:回忆本身亦是梦幻泡影,以虚幻之物来抵抗无常之世事,岂不更真切地裸露了人世虚空的本相?
这是中国士大夫文学藉回忆的诗学而达成的两重境界。无论是前者所求的“破执”的宁静,还是后者“破执”不成而致更深的“大的悲哀”,都从属于“搏击在虚空中”的文学逻辑。以此种逻辑去看待现代立人/立国的文学,毌宁过于肤浅、乐观。“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这是古人对人生深切的领悟。以此为准,鲁迅孜孜于救救孩子,巴金终生诅咒人世间的不义,共产党作家的解放之求,都只能算是本该破掉的执,都可谓不明了生命的真谛。与此相对,若以启蒙或革命为准绳,士大夫文学就只能被目为颓废了。它不太关心社会,无意发掘社会现状之下的真实历史规律(无论这规律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还是阶级斗争),更谈不上藉此启发年青一代寻求社会正义。从哪一方面看,这种以“自了”为旨的士大夫文学都是无所益于当年暗黑无声的中国的。它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差异是整体性的。二者之异,几乎可说是中、西方文学之异,是记忆与真实之别,亦是消极与积极之别。可以说,走在历史乐观主义道路上、执着于启蒙/革命正义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以苍凉感、无常感为“文学最高的境界”[7]的古典士大夫文学完全不同。士大夫文学逻辑上不可能事实上也未曾构成现代文学的剧情主线。
不过,士大夫文学不是剧情主线,这并不意味着它与现代文学没有深刻关系。这表现在两个层面。一,在技术意义上,其资源仍被现代文学大量吸收,如诗歌中意象与节奏的运用,文人小说的结构艺术与白描手法等。二,在局部意义上,士大夫的虚空感及回忆的诗学亦曾支配个别作品甚至个别作家。如承鲁迅而下的萧红在心力憔悴之际也忽然掉入古文人的虚空进而写出《呼兰河传》,而六朝文之于周作人、废名,苍凉感之于张爱玲,确曾有过支配性的影响。
二
“应学士大夫之用”的古典雅文学无力充当现代文学的剧情主线,那么“应妇人粗人之用”的俗文学又如何呢?
以旧小说(含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学,其俗的关键在于“儒表奇里”的叙事结构。“儒表”指其故事大率以儒家伦理主义为想象依据,以忠、孝、节、义等概念为纷乱的社会事相和人生经验设置进入叙事的准入条件,决定其可以叙述之事和不可叙述之事。因此,旧小说的出台人物必然地“在他们行动上、言谈上、露骨地表现了忠与奸,孝友与忤逆,淫荡与贞节等等分明的道德界限。”[8]这种表层故事策略造就了旧小说明显的劝善追求。然而恰如鲁迅所言:“俗文之兴,当兴两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9]而两端之中,劝善不过是娱心之遮饰。娱心则涉及“奇里”问题。旧小说以“奇”为更内在的诉求,实为历代论者所共知。“奇”有“文奇”,如其佳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10]极为讲求变化与呼应。“奇”更体现在人奇与事奇。“人奇”指多有奇人异士,“事奇”则体现为“斗”的核心机制。斗智抑或斗勇,构成了《水浒》《三国》及无数家将小说的秘密。关羽、诸葛亮、岳飞诸辈与其说是忠义之士,不如说是非凡勇力或智力的持有者。他们与曹操、周瑜、金兀术等同样智勇非凡之辈拉开一幕一幕斗智斗勇的大戏,共同娱着读者之心。
但这种通俗文学传统与现代文学同样存在整体性、原则性的差异。以旧小说眼光观之,鲁迅、茅盾、巴金等可谓相当缺乏叙述能力,其故事沉闷甚至无趣。譬如同样写“斗”,现代文学的“斗争”就是所谓的精神冲突,“五四”文学中的人物总是在莫名其妙地思索着、痛苦着(如狂人、吕纬甫),缺乏曲折与动作。即使事涉体力较量,也不过是推推搡搡,断写不出三英战吕布、张飞斗马超那种旷世奇文,至于“死诸葛气死活仲达”一类的智斗华章更在视野之外。反过来,若以新文学为准绳,旧小说就实在不能登大雅之堂。其所谓“斗智斗勇”既不真实(低智之人才会相信李元霸、赵子龙的搏杀能力),又不严肃,完全是以锣鼓喧天的低级趣味取代对历史真理的认识。其劝善更不过是鼓励大众“做稳奴隶”的精神鸦片,无关于家国正义,甚至无关人道。如此文学,大可以“无聊、堕落”来概括。两类文学相去之远,可见一斑。
旧的通俗文学不可能构成现代文学的剧情主线是显然的。但在技术意义和个案意义上,俗文学较之雅文学还是更深地融入了现代文学。实际上,自巴金开始,现代文学就在文明与愚昧冲突的严肃故事中汲取旧小说的伦理修辞经验,人为地将思想落后/反动的人物处理为民间伦理的敌人,而把新锐人物处理为伦理楷模(实则思想新旧与道德善恶并无必然关系)。这种道德捆绑的方法曾遭到瞿秋白、茅盾等的强烈讽刺,但由于它与民族心理(即旧小说培养出的阅读趣味)高度契合,最终在新文学中渐滋渐长,并在革命文学中得到广泛使用。其中的革命英雄传奇几乎全面复活了“儒表奇里”的旧小说叙事。在样板戏中,革命信仰往往被讲述成了对党的忠,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严峻斗争被讲述成了斗智斗勇的热闹大戏。这类革命英雄传奇几乎就是披着革命外衣的旧小说。不过,此类作品即使在革命文学内部也不曾获得剧情主线位置。它们被主流评论家认为是“过分追求故事性,惊险的情节”,“多少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意义,不能使听众受到更深刻的教育。”[11]
三
由俗、雅两脉古典传统在现代时期的存在状态来看,它们都不曾构成现代文学的剧情主线。可见,古典文学传统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诚然不是“断裂”二字所能概括,但也非今天诸多“转型”论者所陈述的那般具有“内在创造性转化”的特征。二者的关系,如果要扼明述之,可概括为“断而有续”。
所谓“断”,指现代文学的想象个人、再现社会的叙事法则是从根本上撇开古典传统而另起炉灶的。这表现在三点。(1)历史对道德的取代。现代文学以西方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理解社会演变、想象人生的痛苦与欢乐,作家在营构“未庄、家、果园城”等特定社会空间和设置人物关系时,都会赋予它们不同的抽象的历史本质,如文明/愚昧,剥削/被剥削,而不再以“大的悲哀”或儒家忠孝节义等概念作为结构全篇的依据。(2)时间对空间的取代。由于历史对道德的取代,“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12]这使现代文学的人物及其环境都会在时间中经历内在性质的逐步的且不可逆的改变。“人在历史中成长”的新方法使士大夫文学“回忆的诗学”的空间化方法和旧小说的“运用无时间的故事反映不变的道德真理的较早的文学传统”方法[13]基本失效。(3)积极取代消极。由于文明/愚昧、剥削/被剥削等“区分辩证法”的使用,现代文学以新的历史价值体系启发青年投身破旧立新的社会改造事业,其积极进取之心完全是对以“自了”为旨(雅者自我安慰、俗者麻醉他人)的古典文学的否定。因此,现代文学的确突然中断了古典传统。但这种“断”又是“断而有续”的,譬如在人近中年或迭遭重创时,现代文人也可能深陷鬼气和名士气,而在考量怎样通过文艺吸引、教育民众时,共产党作家也会借取传统的善善恶恶的道德面具。但这种联系终究是技术性的、局部性的。
以“断而有续”来概括古典与现代的关系,是就文学史事实层面而言的。这可能不太符合不少学者内心涌动的民族热情与文化自信。但作为研究者,一则应尊重事实,二则更要承认事实内部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大势的力量。现代文学之所以抛弃古典而另建剧情主线,无疑是现代中国族群与个人生存处境的需要。家国破乱之际,视一切社会改革皆为“转瞬成空”必然不合时宜,无视身边的现实痴醉于斗智斗勇的热闹也不为可取。对二者之间“断”的事实其实不必遗憾。研究者既要正视现代文学业已创造新的“人的文学”的传统这一事实,更要对古典传统的当下回归有分寸恰当的判断。新世纪以来,随着家国压力的基本消失,雅、俗古典传统正在大面积重返写作,如虚空感的复活(贾平凹、格非等),如“斗”的叙述机制的再现(宫斗戏、谍战剧等)。后者在当下大众文化甚至有星火燎原之势。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古典将会从革命、启蒙倒下的地方重新夺回剧情主线的位置呢?恐亦未必。宫斗也好,虚空也好,今天的文学如果离开了现代文学开创的“人的文学”的传统,恐怕终将是无所附丽。
[1][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6页。
[2]陈平原:《新文学: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4期。
[3]别士:《小说原理》,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8页。
[4][6][美]欧文:《追忆》,郑学勤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5]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张爱玲文集》第4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11页。
[7]白先勇:《社会意识和小说艺术》,《白先勇文集》第4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
[8]巴人:《文学论稿》(下),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第468页。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0页。
[10]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
[11]依而:《小说民族形式、评书和〈烈火金钢〉》,《人民文学》1958年第12期。
[12][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0页。
[13][英]瓦特:《小说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6页。
责任编辑:陶原珂
I206.6
А
1000-7326(2016)11-0149-04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