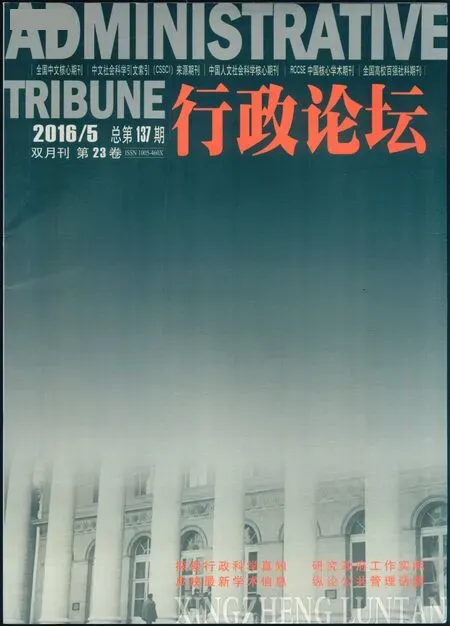政策效能缺失视域下的“垃圾围城”治理研究
◎丁建彪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政策效能缺失视域下的“垃圾围城”治理研究
◎丁建彪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垃圾围城”现象在全国范围的出现和蔓延,有其重要的缘由,垃圾治理相关政策效能缺失是重要的根源之一,具体体现为程序性、交易性、实质性和规范性效能缺失。而破解这一问题的出路就在于建构起可持续、可复制的治理结构:制度结构的构建,可为“垃圾围城”治理提供稳定和可持续的保障;关系结构的构建,可为“垃圾围城”治理提供合作共治的模式;具象结构的构建,可为“垃圾围城”治理提供有效的行动网络;联盟结构的构建,可为“垃圾围城”治理提供经验累积。在推进和实施过程中,应从多维度的视角出发,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完善垃圾治理的相关政策,创新垃圾治理方式;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垃圾市场环境,为企业盈利提供多元化渠道;通过法律法规赋予社区垃圾治理职责,探索社区垃圾治理职责的实现形式;建立和完善乡村和城市垃圾治理资金筹集机制;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强化执法力度,简化诉讼和审判流程,保证惩戒机制发挥实质性作用。
环境治理;垃圾围城;政策效能;治理结构;对策
“垃圾围城”造成的后果既威胁农产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制约城乡均衡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也对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进步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实构成严重挑战。推动“垃圾围城”的有效治理,已成为当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议题。笔者从实践性和规范性结合的视角出发,既立足实践,分析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又从规范层面提出一种稳定和可复制的治理结构,为垃圾治理提供结构性保障。
一、政策效能缺失——“垃圾围城”困境的重要根源
垃圾治理相关政策效能缺失,是造成“垃圾围城”困境的重要根源,其政策效能的缺失又具体体现为程序性、交易性、实质性和规范性效能缺失。
1.程序性效能关注政策过程应遵循的固定程序和解决政策议题所采纳的科学方法。程序性效能缺失,一方面,表现在我国并未形成统一制定垃圾治理政策的科学程序和评估流程。因此,在实践层面,政策制定大多依赖基层政府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判断和领导干部的自我认知,在这种情形下,基层政府制定的往往是一些权宜之计的政策,缺乏全局性和科学性。对垃圾治理政策的评估,也依赖政府部门自我评价,缺乏第三方和专业部门的评估,导致垃圾治理政策变迁的动力不足,严重滞后于当前复杂的现实环境。另一方面,表现为治理方法的单一性和简单性。在全国范围内,对垃圾的治理,大多是政府部门,特别是环卫部门进行自上而下的自我主导,缺乏以问题为导向的回溯勘查和由不同层次治理方法所组成的方法论体系。“目前只有城市环卫部门在管理垃圾,他们主要负责将垃圾从社区运送到垃圾处理站,在此过程中,并没有注重垃圾的资源化处理,这种处理方法不适合垃圾的分类回收”[1]。垃圾治理有其特殊性,需要从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按倒序次序来发现问题,获得有效的政策手段,评估政策的可行性,推动政策的执行,确立政策的科学目标。同样,垃圾治理需要一个多层次、多样化的治理方法构成的方法论体系。不同区域、不同地区“垃圾围城”生成的原因、解决的方法存在差异,只有当微观层面的治理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时,才可上升中观层面的治理方法。宏观层面的治理方法,则涉及根本性的问题和政策供给。只有不同层次的方法相互联动形成合力,垃圾治理才能取得明显成效。程序性效能缺乏,导致垃圾治理呈现出分散化、地方化倾向,垃圾治理方法缺乏针对性和差异性。
2.交易性效能关注资源被如何有效地利用,也即投入最少的资源成本来实现最大化的预期收益,并充分考虑其他主体参与的成本和收益优势。交易性效能缺失,一方面,表现在大量的垃圾治理资源和资金被截留、流失、浪费和无效利用。相比其他的公共项目,垃圾治理项目“黑箱作业”现象严重。政府主导建设的大型垃圾卫生填埋场,大多在环境评估、生物处理技术、防渗透和防污染保护措施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方面较差,渗滤液处理系统不达标,填埋气回收利用设施形同虚设,专用压实机设备数量有限,大多用推土机进行作业,且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在填埋的同时又造成二次污染。如在西部地区实行的“垃圾小屋工程”,每个成本都在5万—7万元之间,大都建在公路两侧,远离村民的生活区,堆放垃圾的空间极其有限,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表现在其他主体所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不能有效进入垃圾治理环节。垃圾治理项目不是公益性项目,它需要企业、社会组织、社区、民众等不同主体参与到治理过程之中,并获得不同的收益。由于我国政府主导和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束缚,垃圾市场并未向社会和企业开放,导致企业拥有的资金、研发和技术优势难以发挥。比如,机械分拣设备的投入和运行,有氧和无氧存在条件下卫生物堆肥技术的普及,垃圾处理热解气化技术的应用等。对社区组织而言,由于缺乏法制化和制度化保障,大量的社区组织不能深度参与到垃圾治理的进程中。社区组织对垃圾治理具有成本低、组织适应强、管理系统完善、人员众多,且拥有大量的固定场所和网格化的管理方法,社区组织拥有的这些自身优势也难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3.实质性效能关注政策结果取得的实际绩效,通过分析具体政策的绩效来界定政策系统的整体效能。实质性效能缺失,一方面,表现在具体政策,特别是垃圾治理过程中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垃圾分类”和“垃圾收费”政策的效能缺失。垃圾分类是世界范围内垃圾治理的通行做法,也是最有效和最可行的方法之一。在我国,垃圾分类政策的法律法规偏重于垃圾的倾倒、清扫、运输和处置的末端,作为垃圾分类的源头却无法可依。垃圾回收设施分类不规范,大多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类,而大部分居民又不清楚哪些垃圾可回收、哪些垃圾不可回收。公众垃圾分类意识不强,导致垃圾进行混杂式倾倒和丢弃。即便有部分地区、单位和家庭进行有限的垃圾分类,由于缺乏后续政策的跟进和配套,垃圾在存放、收集、处理过程中进行混杂式处理,垃圾分类政策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垃圾收费政策是治理垃圾的另一种有效手段。在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以发展落后、不增加居民经济负担为由,实行最低限度的“按户收费”政策,甚至不收费,使得垃圾治理处于真空状态,而作为控制垃圾总量、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和可持续治理的重要保障的“按量收费”政策,却迟迟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和推广。另一方面,表现在政策系统整体效能低下。政策系统的整体效能是通过系统内具体政策效能的正负总和来界定的。我国的垃圾治理存在城市、城镇和乡村的三维政策结构,不同区域的政策效能各不相同。城市垃圾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政策效能得以明显提升。但城镇却要接纳大量未经处理的人为转运的城市垃圾,加之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和自身资金、技术和处理能力的限制,导致城镇垃圾治理政策效能提升不明显。同样,城镇产出的垃圾也人为转运到乡村,加之乡村垃圾由于工业的转移和粗放型农业经营,产出大量的工业垃圾和农业垃圾,乡村垃圾治理陷入难以有效治理的恶性循环之中,造成乡村垃圾政策效能低下。治理政策的多维性又造成政策相互重叠和交叉,缺乏有效的协调和衔接,导致政策系统整体效能低下。
4.规范性效能关注政策规范性目标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对社会成员集体行动的塑造。规范性效能具体包括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理念等总的政策目标释放出的能动效能。其中,绿色发展理念对“垃圾围城”治理产生积极影响,它要求在全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理念,并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绿水青山、城乡均衡、人文与自然景观的高度融合。规范性效能缺失,一方面,表现在这些价值和理念并未真正渗透到社会领域,形成全社会自觉行动的规范,特别是治理主体的自觉行动规范。“垃圾围城”治理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往往投入多、产出少,投入和产出不对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释放缓慢,这导致作为垃圾治理最重要主体的政府,在价值理念、目标导向宣传、普及和推广中存在消极性特征,因为垃圾治理产生的效益并不像经济建设的指标那样具有杠杆撬动作用。而且,在我国的政府系统内部考评中,垃圾治理指标并未真正纳入考核体系,使政府官员缺乏晋升动机和政绩刺激。因此,部分政府官员只在形式层面予以响应,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拖延、抵制这些发展理念,部分政府部门甚至本身成为“垃圾围城”的保护者和制造者。另一方面,表现在这些规范性目标没有有效地塑造出集体行动的动机和动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的深入推进,与社会成员的生存环境和生存质量息息相关。但在行动层面,个体行为与集体行动之间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个体的行为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当他们的利益存在持续增进时,个体才根据这些共有的规范化开展集体行动。但从垃圾治理中获得的利益往往是间接性的,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物质利益。因此,规范性价值的塑造受到个体狭隘性利益的抵触,个体的行动大多是“自扫门前雪”和“搭便车”。垃圾治理政策却缺乏对社会成员进行深层次的塑造,比如,开展公民生态教育、环境保护意识培育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结果是垃圾治理集体行动动机不强和动力不足。
二、治理结构的构建——“垃圾围城”治理的关键环节
在垃圾治理相关政策效能缺失的背景下,“垃圾围城”治理要取得明显成效,需要从更为规范和科学的层面建构起可复制、可借鉴和可推广的治理结构,因为任何从局部、单一层面提出的解决政策、制度和方法已不能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难题,为“垃圾围城”治理提供新的路径选择。
1.制度结构的构建,可为“垃圾围城”治理提供稳定和可持续的保障。制度是社会成员行为过程中产生的相对稳定的规范,具有主观和客观的双重特征。作为主观的特征,它引导人们进行社会活动和社会交流,个体基于这些规范能动地行动。规范在特定的社会中又是共有的,所以制度也就变得客观、稳定和刚性,它限制人们行动的自由,影响人们采取行动的方式,为公众正确行为设定界限。正是通过制度,人们的行为才得以被控制、引导和重塑,人们的日常行为才具有稳定的特征。因此,制度结构的核心是在完善具体制度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垃圾围城”治理结构的构建,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体系。首先,要制定从源头上控制垃圾总量和减少垃圾总量的制度,这一制度涉及垃圾的成本分担、综合回收循环利用技术、约束公众自觉减少垃圾产出的习惯等不同方面。只有减少垃圾的绝对总量,解决“垃圾围城”才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其次,健全和完善垃圾治理过程中的无缝衔接制度。要严格建立起垃圾源头分类、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的无缝衔接,减少垃圾二次围城。再次,完善垃圾处理标准化的技术等级制度,这一制度涉及堆肥、生化处理、填埋、焚烧等不同的等级。只有当某一等级的技术不能处理时,才能通过另一等级的技术来处理。比如在德国,42%卫生填埋,40%焚烧制能,13%堆肥处理,5%机械生物处理。而在我国,总量70%的垃圾通过简单填埋来处理。最后,健全和完善严格的奖罚制度。对垃圾分类良好的家庭、企业和组织,通过财税和经济杠杆来激励,对高危垃圾产出主体,比如,医疗、化工废料、电子类废弃物强化监督力度,并对造成危害后果的相关主体加大处罚力度。通过优化和完善具体制度的不足和缺陷,并将具体制度中科学、有效的要素上升为全国层面统一的制度安排,才能为垃圾治理提供制度性保障。
2.关系结构的构建,可为“垃圾围城”治理提供合作共治的模式。关系结构不同于制度结构,它表现为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的状态。“社会关系不是实体事务,如果没有人类每天的介入、行动而产生和再现这种关系,它们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关系都在现实中流动和运动着,在这种运动中,它每天都在变形、改变、侵蚀、消失或变质”[2]。关系结构的核心是确立起政府、市场和社会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合作的共治模式。垃圾治理的特殊性,决定既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主导来独自解决,也不能依靠市场的自发性力量来解决,更不能交由社会自行消解,需要三方协同共治。政府应整合和清理已有的不合理的政策和法规,重新制定符合新形势下全国统一的政策法规,并将部分内容纳入法律层面强力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目标管理、工作机制、推进程序和保障手段。市场应克服垃圾市场人为分割和地方各自为政的局面,培育全国范围内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格局。透过价格机制,实现从垃圾收集、分拣、回收、储运、处理、综合利用和产品经营的完整产业链。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的地方,是社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的节点。垃圾治理作为一种纯粹性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能够实质性地承担起局部范围内监督、处理、宣传和后续的服务性工作。社会组织也能为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联系搭建起合作桥梁,有效解决政府与企业之间缺乏衔接的局面。政府应为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垃圾市场提供法治保障和制度供给,为社会组织明确权责关系和法律地位。市场充分发挥资金优势,通过技术升级和引入新的运作模式,实现垃圾资源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社会组织在既定的法律框架下,充分释放治理社会事务的优势,形成三者有机联动、合作共治的新模式。经验表明,“合作既是治理的起点和归宿,更是构建社会公平正义的必要法则”[3]。
3.具象结构的构建,可为“垃圾围城”治理提供有效的行动网络。制度和关系结构对个体的实践活动产生一定程度的强制,塑造他们垃圾处理习惯的形成。但在个体的行动网络中,不同的行动者并不完全遵守既有的制度规范和关系模式,而是分析各种资源在治理过程的分配,根据资源分配的程度,产生自我利益、自我动机和自我目标来展开行动。不同行动者的行为又彼此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形成稳定状态,这一状态被描述为具象结构。“不同的行动者在网络中打破了传统的垂直与水平关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网络中各节点互动频繁,形成一种权变式的管理”[4]。在具象结构中,个人和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单元,它们的行动直接关系垃圾治理的成效。因此,个人和家庭应自觉地进行垃圾分类和减少垃圾排放,自觉使用纸制类垃圾袋、可循环使用的布袋和可降解的生活用袋。对家用类和衣服类二手品,通过清洗和加工整理,进行社会捐赠。对电子类和电器类废弃物,主动投放到固定场所和专门的回收设备中。政府和企业作为垃圾收集和处置的主体单元,应在公共场所、商场、农贸市场提供专用的收集设备和建立固定、便利的场所,减轻垃圾收集的成本和压力。大型生活类超市,由于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应配备自动化、智能化的回收机器。对部分可循环回收的用品加入虚拟成本,当居民将这些用品放入回收机器之后,机器自动将虚拟成本以购物券的形式返还给居民,来刺激居民主动投放。村民委员会和社区组织处在垃圾治理上下联动的中枢位置。部分工作人员应走进所在辖区,对居民进行垃圾分类标准、减量化、资源处理意识的宣传和普及,纠正居民随意丢弃和倾倒垃圾的陋习。在垃圾的存放、收集和运输过程中,积极协调不同行动主体的互动行为。比如,协调居民、政府、建筑单位、企业之间临时性存放垃圾的共有场所。在垃圾收集和运输过程中协调线路的科学设置,形成互相协调和相互信任的“大环卫”体系。
4.联盟结构的构建,可为“垃圾围城”治理提供经验累积。美国学者萨巴蒂尔等人将“倡导联盟”定义为“来自不同职位的人们,他们共享一个特定的信念系统———一套基本价值观、因果假设和问题感知,并且在长时间内显示出较强的协调活动”[5]。“垃圾围城”不仅破坏环境,威胁农产品质量和安全,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对该问题的有效治理易于取得全社会的普遍共识。但由于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不均等,认识和能力不一致,造成后果的直接性和间接性不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形成垃圾治理过程中的不同联盟。在“垃圾围城”中受益或获利的联盟,缺少承担社会责任和公平分担治理成本的意愿,对垃圾治理持反对或消极态度。部分联盟由于垃圾治理缺乏和自身的直接相关性,加之观念和认识上的限制,形成中立联盟。“垃圾围城”产生后果与成员的利益和健康直接相关或者损害其既定利益的,形成垃圾治理的支持者联盟。不同联盟之间的稳定状态被描述为联盟结构。在联盟结构中,不同的联盟成员通过阐述和支持他们的政策目标来推动他们利益目标的实现,同时攻击其他联盟,导致不同的联盟之间存在对立、竞争和冲突。但由于解决共识的黏合作用,联盟结构对垃圾治理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不同联盟之间通过各种平台进行跨联盟政策学习。通过学习,提高“垃圾围城”产生后果的认识,对其生成的原因和影响垃圾治理的各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对不同的解决方案优劣进行比较,弱化不同联盟之间的分歧,增加行动共识和公平分担成本的意愿,减少搭便车行为倾向的发生,推动垃圾治理政策变迁和问题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又能更好地发挥自身汲取公共资源和相对独立地位的优势。通过对中立联盟和反对联盟的诉求、利益和目标进行了解,采取合理的资源分配进行引导和约束,并加大惩戒力度,实现中立联盟和反对联盟向支持联盟的靠拢,减少垃圾治理的阻力。对支持者联盟则进行政策引导和经济激励,充分调动他们的潜能,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推进垃圾治理目标的实现。
三、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垃圾围城”治理的根本保障
“垃圾围城”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造成这一困境根源的分析和治理结构的构建,需要从微观的层面提出更为可行和可操作的对策,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形成系统化的治理体系。
1.完善垃圾治理的相关政策,创新垃圾治理方式。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中,政府对垃圾治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应将当前普遍实行的“垃圾定额制”收费政策转变为依照“多排放多付费、少排放少付费,混合垃圾多付费、分类垃圾少付费”为原则的“动态制收费”,以此来控制垃圾总量的产出和增加垃圾治理资金。在此基础上,在有条件的城市和地区逐步推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规定居民主动将垃圾投放到专用的收集车上,对私自倾倒垃圾的行为进行教育和惩罚,减少垃圾污染面积和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同样,政府应把“垃圾分类达标”作为重要的指标。在垃圾治理的前端,对垃圾分类业绩突出的城市、城镇、组织和家庭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和一定的物业费用补贴,对垃圾分类不达标的单元,收取更加高昂的成本,建立起制度化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在垃圾治理的中端,政府应为单位和社区配备先进的垃圾收集工具,特别是多厢式垃圾分类收集车的广泛使用,并为企业和小区购置先进运输工具进行税收减免和购置补贴。在垃圾治理的末端,根据不同的垃圾类别和属性,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确保垃圾治理从源头、收集和处置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完整链条。另外,政府应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环境资源奖励”政策。随着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处在城乡结合部的大量村民,为了从拆迁中获得最大利益,私搭乱建大量的建筑物,拆除之后又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政府要对没有私搭乱建的居民,给予环境资源奖励,奖励的额度要大于私搭乱建的成本,使私搭乱建失去获利空间,同时对违章建筑进行无偿性拆除,综合利用多种措施来控制这一现象的蔓延。
2.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垃圾市场环境,为企业盈利提供多元化渠道。“垃圾围城”的解决,企业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方面,与垃圾市场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环境密切相关。据统计,我国垃圾的回收利用每年可以创造出2 500亿元以上的经济产值。但由于人为性因素的分割和地方市场的各自为政,部分沿海地区的垃圾处理企业缺乏垃圾资源,其他地区的企业由于资金、技术和政策扶持的不足,垃圾资源却堆积如山。通过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克服地区不平衡现象,实现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与垃圾处理企业能否获得盈利机会和盈利空间紧密相关。有机垃圾压氧堆肥技术的应用,是企业获得盈利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垃圾处理企业应利用专业化的技术培养和驯化微生物对有机垃圾进行快速转化,而微生物产出的粪便和微生物躯体可用来有机养殖,形成可循环的利润来源。在垃圾处理的末端,企业应通过技术升级和科技创新,实现利润增长。“作为第三代垃圾处理的热解气化技术,它可将垃圾置于1 200℃以上的高温中分解转化为汽,由此产生新的热能用于发电或供热,而处理过程很少产生二英等有害气体,其高温热解的残渣可作道路、堤坝的填充材料,按一定配比可作为生产环保水泥、砖块、下水管道等建材的原料”[6]。企业也可通过研发和推广可降解技术而获得巨大的盈利机会。可降解产业是绿色发展的关键性产业,是减少白色污染的重要举措。可降解产业应用领域广泛,既涉及居民生活塑料用袋和包装袋,也涉及农民使用的塑料地膜和塑料类产品以及工业类塑料制品。通过降低技术成本和使用成本,在全社会普遍应用,能为企业提供巨大的利润空间。
3.通过法律法规赋予社区垃圾治理职责,探索社区垃圾治理职责的实现形式。社区治理是破解“垃圾围城”的可行和有效方式。“社区能够做政府和市场不能做到的事情,因为社区拥有社区成员行为、能力和需求的信息,社区治理利用这些分散的私人信息,并根据其成员是否遵守社会规范进行奖励和惩罚”[7]。在当前,应完善部分垃圾治理的法律法规,明确赋予社区垃圾治理的权限和地位,并给予人员编制、财务、收集工具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保障。在此基础上,探索社区垃圾治理职责的实现方式。社区应积极吸纳部分社工人员、失业人员和贫困人员参与垃圾治理进程。通过专门化和专业化垃圾分类、分类回收利用等知识培训,改变当前仅仅依靠部分环卫人员被动收集垃圾的方式。在遵守相关法律和授权的前提下,社区垃圾收集人员可给本辖区内的家庭分发付费式垃圾专用分类收集袋,收集袋的价格与收集成本大体一致。规定每个家庭主动将垃圾分类投放到不同的专用垃圾袋中,社区人员在规定的时限内周期性地上门主动收集,从根本上实现“垃圾分类”和“多产出垃圾多出钱”政策落地。比如,“在台北,垃圾必须使用专用付费垃圾袋,如果不使用专用垃圾袋,清洁队可拒收,居民投放垃圾时还会有专人抽样检查居民的垃圾袋,如果发现没有按规定分类,会被罚款1 200元到6 000元新台币”[8]。另外,通过“社区+公司”形式,建立社区和公司占一定份额的混合制体制,共同实现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的全过程。社区也可通过授权或委托的形式,建立垃圾清运和处理公司,实现产业化和能源化处理,提高垃圾治理效能。
4.建立和完善乡村与城市垃圾治理资金筹集机制。多方资金共筹机制是垃圾治理可持续的保证,是破解“垃圾围城”的重要环节。在乡村治理资金筹措上,要建立起专项资金公共池。中央政府按照一定比例投入专向资金,地方政府把垃圾治理费用纳入专向财政预算,作为乡村垃圾治理的稳定源头。通过“企业+农户”的形式,充分挖掘乡村地区有机农产品种植和有机养殖的经济潜力,将利润以一定的比例投入资金公共池中,扩大资金来源。家庭通过一定的比例每月出资,来雇佣专职的人员来进行垃圾的收集和清理,剩余资金投入专项池中循环使用。比如,“广西通过筹集、管理村庄保洁费的方式向每户每月收取35元,共自筹村庄保洁费806万元,占城乡垃圾治理总投入的23.17%”[9]。在城市垃圾资金筹措上,根据不同垃圾种类,实现分类筹集的多元化模式。对生活类垃圾,要按照“动态收费制”来征收,同时扩大征收范围,将国有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营者纳入其中,扩大垃圾治理资金增量。充分利用已成熟的各种收费平台,如代扣代缴、水费和电费联合收取等方式,提高收费率,盘活垃圾治理资金存量。对工业垃圾、电子垃圾和医疗垃圾,一方面,要通过“生态税”和“环境资源税”等税收政策,补充垃圾治理资源来源;另一方面,建立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占不同股份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加强技术研发,提升垃圾处理的产业化水平,将部分利润作为治理资金。“建筑废弃物经过破碎、分选后可得到所需粒径的再生砂、石,而砂、石又是所有建筑材料中最基本的母体材料之一,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0]。市政建筑和工程,应优先采购建筑物废气循环利用的材料。废橡胶通过微波脱硫等技术生产胶粉,胶粉与其他成分混合形成橡胶水泥、橡胶沥青、铁路枕木,可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废玻璃通过粉碎、预成型、加热焙烤,可做成人造石材、人造彩砂、玻璃微珠等建筑材料。电子垃圾通过人工拆解,将有毒物质的零部件取出后,其他部件可通过电子破碎机和磁力分选分离回收技术,分离出铁、铝、铜和一些稀有贵金属。城市产出的各种不同垃圾,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化经营,能够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和利润空间,可成为城市垃圾治理资金的重要来源。另外,政府应面向城镇或城市居民发行一定数量的专用债券,按照一定比率和利息,将这部分资金作为专项资金用于城市垃圾治理。
5.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强化执法力度,简化诉讼和审判流程,保证惩戒机制发挥实质性作用。垃圾分类政策、垃圾收集过程的无缝衔接制度、垃圾收费政策以及公众垃圾分类意识的提高,都需要健全的自律和他律机制。要赋予村委会和社区垃圾治理信用记录的权限,对随意倾倒垃圾和违反垃圾分类等一系列政策的单元和个人,建立信用档案来对其不良行为发生的频率进行记录,将垃圾信用记录和社会其他的信誉记录互联互通,并通过互联网进入人民银行的信用信息数据中心,作为发放贷款、享受政府税收减免和补贴方面的重要指标,推动社会形成良好的自律机制。我国现行的垃圾治理的有关法律,只是鼓励民众实施,并未强制执行,即便执行,也缺乏可操作化的配套法律。因此,要根据现有的情况制定相关配套法律,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垃圾围城”监测和执法,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惩戒,特别是通过司法诉讼机制。法院要简化流程和改变一定的诉讼主体,支持垃圾公益诉讼。让社会成员、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对随意倾倒垃圾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对相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缩短案件审理时限和加大执法力度。对拒绝执行的企业、单位或部分公民,进一步从经济制裁、出行限制、职务晋升等方面加大执法力度,保证法院的判决得到真正落实。
[1]赵莹,等.垃圾能源化利用与管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5.
[2]杰西·洛佩兹.社会结构[M].允春喜,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95.
[3]STOKER G.Governance as Theory:Five Proposition[J].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98,50(155):17-28.
[4]王晨.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基于德国城市绿色空间治理的思考[J].理论探讨,2015,(3):163-166.
[5]保罗·A.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M].彭宇超,钟开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58.
[6]秦思昌.我国垃圾处理资源化、产业化之构想[J].中国资源综合利用,2008,(6):15-18.
[7]夏建中.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2):125-130.
[8]潭文柱.城市生活垃圾困境与制度创新——以台北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管理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1,(7):95-101.
[9]打响农村垃圾治理攻坚战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EB/OL].(2015-09-16)[2016-01-23].http://gongyi.sohu.com/20150916/n421381815.shtml.
[10]黄海.建筑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及综合利用[C].建筑废物资源产业化研讨会暨建筑废物资源化成果推广会,2010,(4):13-20.
(责任编辑:于健慧)
D630;X705
A
1005-460X(2016)05-0092-06
2016-02-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研究”(12&ZD058);吉林大学种子基金项目“‘垃圾围城’治理中的政策效能缺失及联盟治理结构研究”(2015ZZ037);“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对策研究——德国城镇化发展经验借鉴”(2014BS004)
丁建彪(1979—),男,甘肃甘谷人,讲师,从事公共政策与公共治理、垃圾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