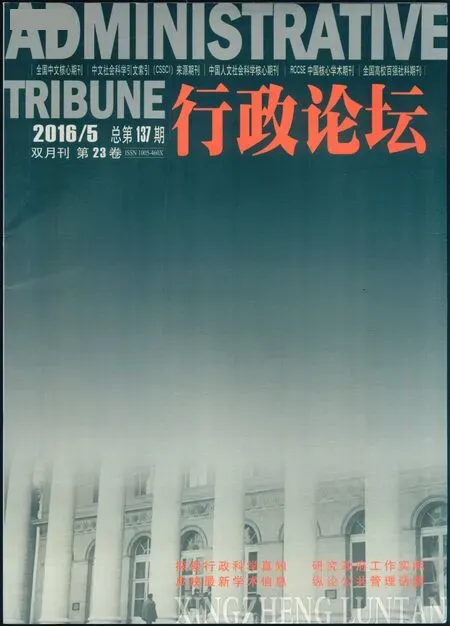论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
◎张爱军
◎孙贵勇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辽宁大连116021)
论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
◎张爱军
◎孙贵勇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辽宁大连116021)
互联网为谣言提供便捷快速的传播平台,一定社会情境下的消极社会心态是谣言产生与传播的重要诱因。网络谣言产生具有客观性和难以预测性。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网络谣言映射部分社会心态,这包括负面情绪、弱势心态和信任危机等。社会心态与网络谣言相互作用:消极社会心态下的人们更易信谣传谣,消极社会心态在网络谣言中传播扩散,在网络谣言动员中容易转化为集体行动等。网络谣言必须加以治理。基于社会心态层面的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设法治国家和提高公众的理性辨识能力。
网络谣言;群体事件;社会心态;治理策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国家;公众
一、问题的提出
谣言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但对于“什么是谣言”,时至今日依然众说纷纭。综观国内外学者对谣言的界定,大都包括以下要素:首先,谣言含有真实因子。谣言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它总是与一定的事实相关,寄生于事实之上。“人们总能在谣言背后找到孕育它诞生的细胞和温床,同时也能在现实中找到谣言信息的原型,即事实内核”[1]。其次,谣言是一种话语表达方式。在公共话语表达空间不足或可知信息匮乏的情境下,谣言就会成为人们表达、交流信息的方式和手段。“在任何一个地区,当人们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时,谣言便会甚嚣尘上”[2]9。再次,谣言可真可假。谣言是未经证实的信息,但不一定是虚假的信息,因为有大量的谣言最终被证实是“真实”的。“事实上,谣言之所以令人尴尬,就是因为它可能是真实的”[2]4。基于此,笔者认为,谣言是与一定事实相关并在社会中广泛传播的未经证实的信息。而网络谣言只是改变谣言的传播方式,互联网成为谣言的发布平台和传播渠道,使谣言传播更便捷、更快速、更广泛,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病毒式”扩散。
谣言是迄今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与人类社会共生共存。它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并因社会情境的变化,时强时弱,时密时疏。“谣言,自古有之,于今尤甚;传统社会中有之,转型社会中尤甚;现实生活中有之,虚拟网络上尤甚”[3]。观今日之中国,正处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期,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深刻变革和调整,社会矛盾积聚,社会风险增大,催生大量谣言。它们在搭上互联网的高速列车后,传播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非昔日可比。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期是深层次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期,也是谣言滋生与传播的活跃期。弗朗索瓦丝·勒莫指出:“谣言是对失衡或社会不安状况的一种反应。”[4]网络谣言在突发性、群体性事件中,推波助澜,推动事件扩大升级,成为引发公共危机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学界对谣言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作用机制、逻辑生成、防控措施等给予关注和研究,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大都把谣言的产生与传播归因于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预警系统不灵敏、政府公信力不足、法律制度不完善等方面,对谣言背后的社会心态关注不多,涉入不深,而弥漫于社会成员中的社会心理状态往往是谣言得以肆虐的重要内因。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和波斯特曼(Leo Postman)认为谣言出现应同时具备“重要性”和“模糊性”这两个基本条件,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谣言都不会产生。他们提出谣言传播公式:R=I×P(谣言传播的强度与广度=重要性×模糊性)[5]。此后,也有学者对这一公式进行完善,如罗斯诺(Rosnow)增加“anxiety”变量,即“个体的焦虑与担忧”。奥尔波特等人对谣言传播条件的研究和总结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主要是从个体层面展开研究,过于强调个体意识,而忽视谣言的社会心理属性。事实上,谣言传播的诱因是多方面的,不但来自谣言本身,而且还有谣言所处情境中的社会心态。因此,在社会转型期,深入考察社会危机背景下,谣言特别是网络谣言所映射的不良社会心态,深入分析网络谣言与社会心态的逻辑演进,对于建立更具科学性与针对性的网络谣言治理机制和策略具有积极意义。
二、网络谣言映射的主要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是对社会运行状况或社会变迁的一种反应,与特定的社会环境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密切关联,是一定时期内弥散于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普遍的、一致的社会心理状态。社会心态构成一种氛围,能够影响个体成员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在带来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结构调整、思想观念变化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也发生嬗变。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人们的社会心态附着在谣言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造谣、传谣的社会心理基础。通过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网络谣言进行考察、分析,我们发现在谣言背后所映射出的社会心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负面情绪弥漫
情绪是社会成员对现实生活的各种心理感受和态度体验,当其效价为消极性时,即为负面情绪,主要表现为愤怒、沮丧、怨恨、痛苦、焦虑等。负面情绪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能够在群体成员间传染、弥漫。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重叠。面对高涨的房价、物价、教育和医疗费用,面对食品安全隐患和环境污染,面对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社会个体中产生的不安、焦虑、不平、怨恨等负面情绪就会通过社会网络传播扩散,形成群体的负面情绪。社会负面情绪是诱发和推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往往成为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手中的利器,在转述事件的过程中,对某些情节进行不断加工、片面夸大甚至编造虚构,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扩散,激发群体的恐惧、焦虑、愤怒、不公等负面情绪。当这种负面情绪累积并突破一定阈值时,就会超出区域社会各要素结构的承受能力,使谣言受众进入非理性的宣泄状态,引发过激行为和对抗性冲突,把区域社会推至危机情境。“当他们从原子化的个人开始融入这样一个因谣言组合成的群体之中,随着群体内部谣言更加频繁、更加‘真实’的传播,他们因迷惑从而越陷越深,完全相信谣言就是‘事实’,因此,群体逐渐变得疯狂而丧失理智,最终导致冲突的发生”[6]。例如,发生在2008年的贵州瓮安“6·28”群体性事件,瓮安县初中女生李树芬溺水死亡后的几天里,大量谣言在互联网上疯传,言称“死者是被奸杀”“元凶及凶手与县委书记、县长是亲属关系”“死者叔叔被公安指使的人打死”等,矛头直指当地政府官员,加固和激发公众中存在的对“司法不公、官官相护、政治腐败”的认识和负面情绪,最终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2.弱势心态扩大
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发言时,称财大气粗的“银行是弱势群体”,引得全场哄堂大笑,也引起网络热议。但这并不是新鲜事。早在2010年,《人民论坛》就弱势群体问题做的网络调查显示,有七成的受访者将自己归为“弱势群体”,其中,在接受调查的处于社会精英阶层的党政干部、公司白领、知识分子中,也分别有接近或超过半数的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从中可以看出,“弱势”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个人自感在生存、生计、机会、权利上存在风险,得不到有效保障时,其内心就会充满焦虑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将自己归于弱势群体。从表面上看,是弱势群体在扩大,而实质上是社会上的弱势心态在蔓延。人们内心广泛存在因贫富分化、权力寻租、不正当竞争、合法权益难以保障而产生的不公平感、被剥夺感和无力感。
弱势心态在网络上会被成倍放大,使牢骚、抱怨、谩骂、宣泄等负面言论充斥于网络,成为大众常态。处于弱势社会地位的群体对自身生活环境、生存状态的认知,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体认,以及对这种弱势境遇的归因,会扩大他们的弱势心态,也容易产生强烈的心态失衡,左右他们的观念与行为。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潜伏于人们心中的弱势心态极易被刻意强调或虚构的谣言信息唤醒,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激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怨恨情绪。特别是当他们认为自己处于弱势的原因是社会不公和其他群体的不正当手段时,更容易造成其反社会情绪的宣泄和非理性行为。2013年7月12日,一条关于“神木财政亏空,免费教育和医疗废止”的谣言在微信、QQ群、贴吧、手机短信上热传,三天后,部分群众围堵县政府,引发群众聚集事件。虽然事件很快得以平息,但其背后显现的群众弱势心态发人深省。靠煤而富的神木,因煤炭价格跳水、民间借贷崩盘加剧投资者的恐慌心理;煤炭经济催生的大量富豪给普通群众以强烈的落差感;“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将被叫停的传言令底层群众本已敏感脆弱的神经又受到重重一击,广泛存在的弱势心态被谣言点燃,成为引发此次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3.信任危机蔓延
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心态和“道德资源”,是社会成员达成最大限度的“重叠共识”,实现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心理基础。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日益突显,信任危机不断深化。在吉登斯看来,信任危机是任何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必经过程,是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信任危机也正是当下中国人的切身感受,它“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社会细胞内部”[7]。
社会信任资本匮乏,信任危机弥漫,会使人们在生活中更加谨慎、相互猜忌、彼此提防,个体行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增强。一方面,人们不会轻易相信来自官方、专家、市场利益主体的所谓权威信息,甚至因为有过被“杀熟”的经历而拒绝来自“熟人”的劝告和建议;另一方面,他们又相信“小道消息”,易于轻信谣言和散播谣言,因为“当公众对一切都无法相信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相信一切”[2]84。换句话说,当一个社会弥漫着信任危机时,就会谣言四起。
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社会信任的严重缺失会导致谣言肆虐,而群众对政府及官员的不信任又是催生谣言、加快谣言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发展的重要催化因素。由于少数公共机关、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违法违纪行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可度不断下降。“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呈现一种累积性,它并没有随着对一些违规、违法的官员或政府的惩罚而消除,而是在人们的心里储存、发酵,逐渐消解人们对于作为‘整体’的政府或官员的好感和信任”[8]。政府公信力的严重缺失使其行使权力的每一个行为都容易引起人们的习惯性揣测和怀疑,甚至会陷入“塔西佗陷阱”,无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会受到公众的质疑,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如近年来发生在厦门、大连、宁波等地的反PX事件,尽管政府和专家一再声明、强调PX(对二甲苯)是一种低毒且用途极广的基础化工原料,但公众还是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对PX有剧毒、致癌、致畸、高爆炸等谣言深信不疑,并广泛传播,令公众恐慌,直至通过“集体散步”这种激烈的抗议方式驱逐该项目,谣言才消散。
可以说,如果政府发声权威,公众信服,就会及时遏制谣言,也不会出现随后的反PX事件。而在公共危机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对政府的不信任不是偶发现象,事实上,在瓮安事件、石首骚乱、抢盐风波、“7·23”温州动车事故等事件中,广大公众都选择相信和传播谣言,唯独对官方公布的真相和调查结果表达不信任,致使事态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引导和控制,反而愈演愈烈,发生公共危机。
三、社会心态与网络谣言的相互作用机制
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谣言所投射出来的主要社会心态,如消极的、负向的情绪情感和社会认知,为网络谣言的滋生提供充分的土壤环境,当遭遇公共危机时,它们附着于网络谣言进行传播、扩散、累积,一旦突破临界点,就会通过聚集抗议、冲突对抗等激烈的行为方式宣泄出来。
1.消极社会心态下的人们更易信谣传谣
人们是否相信和传播谣言与个体的情绪、情感有较大关系。受消极社会心态影响的人更容易听信谣言,他们倾向于从负向、悲观的角度对社会现象进行认知和评判,当谣言内容与个人的不满、不安、不确定性等心理相契合或一致时,就会引发其情绪情感的反应,在潜意识里认同和传播谣言,甚至根据自己的想象或道听途说的其他信息对谣言内容做进一步的删减和填充。正如桑斯坦所言:“人们是否会相信一则谣言,取决于他们在听到谣言之前已有的想法。”[9]26瓮安、石首事件中的谣言正是迎合人们的仇官、仇富等负向情绪,许多网民选择接受谣言,相信谣言内容就是事实真相,并大量转发传播相关信息。
群体归属意识使个体乐于接受和分享群体成员发布的信息。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分属于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都是一个有效的现实或虚拟的交流网络,而且群体内部联结得越紧密,信息就越容易流传。处于消极社会心态的人们会根据经历、背景等组成不同的群体,例如,同是下岗失业人员、失地农民、失独家庭等,通过QQ、微信、微博、贴吧等建立联系网络,彼此互动交流,分享信息,表达共同的利益诉求。他们是具有同样的看法、同样的价值观和同样的态度的群体,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相当数量的利益损失者为了维护其利益,必然会通过各种形式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这一过程中,把他们的声音加载在谣言上,是一种常见的手法”[10]。前文提到的神木群众聚集事件中,谣言内容由于关系民间借贷群体和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使其在这些群体之间快速扩散、动员,酿成公共危机事件。
另外,责任分散意识弱化人们传播谣言的负罪感,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来自道德和法律方面的顾虑。网络能够隐匿真实信息的特点为个人戴上面具,法不责众的心理暗示令其不必担心受到惩罚,个人淹没于群体使其摆脱道德束缚,个人的责任感下降甚至消失,并无所顾忌地散布谣言。“谣言总是被认为是从他人那儿得来的,是‘有人说’,从而消除了人们的犯罪感觉,允许人们最为自由地表达其被压抑的、迄今为止不可名言的冲动”。“谣言是一封匿名信,人皆可写而不必受到任何惩罚”[2]59。社会变革中的利益受损者大都具有较为突出的负向情绪,由于传播谣言的低成本性,加上投机心理的鼓动,一些人加入造谣传谣的大军,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环境下,妄图借此制造声势,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个人或群体通过合法途径、正当手段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无可厚非,但这种通过造谣生事、从中渔利的行为应该给予坚决抵制和打击。
2.消极社会心态在网络谣言中传播扩散
网络谣言是一种话语表达方式。网络谣言也是以“言”说“事”,“言”中不仅交代“事”,还包含“言者”的情绪情感。在消极社会心态影响下的人们在制造和传播谣言过程中,同样也会将自身的情绪情感、认知评价、价值观念等附加于谣言之上,并通过各种连接纽带在相关群体网络内传播,使得这种消极的社会心态进一步弥漫扩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生活在一个事物被说出的世界中。这些被说出的话实际上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不留痕迹的一阵风,不论它们的痕迹如何多样,都会保留下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为话语(discourse)所标记、所交织的世界中”[11]。社会心态具有传染、渗透作用,“当谣言制造了强烈的情绪,如厌恶、生气、愤怒,人们更可能传播它们”[9]98,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更多的谣言加载图片、视频等信息,增强谣言的说服力和可信度,也有效激起人们的情绪情感反应,即使后来谣言被证明是虚假的,但对该类现象的认知已经在其内心留存下来,当类似信息、场景以另一番面貌再现时,相关情绪情感就会被激活,并有可能被进一步强化。
社会流瀑效应加快消极社会心态的弥漫。“社会流瀑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们倾向于相信别人的所言和所为”[9]8。作为个体,我们每个人掌握的知识都是有限的,面对不熟悉的领域和知识,在缺乏相关可靠信息时,就容易相信别人的传言。即使传言可能是虚假的,但由于周围的大多数人都相信这则传言,我们也就趋向于选择相信它。特别是网络时代,一些人痴迷于网络大V,对他们发出的任何声音、一举一动,都不假思索地拥护支持,出现所谓的“羊群现象”。这些大V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拥有数量超百万、千万的粉丝,是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和言论的“领头羊”。一些不负责任的网络大V为提高其网络知名度和影响力,牟取非法利益,对公共事件、热点话题等恶意发表负面网络言论,策划、制造网络热点事件,煽动、点燃人们的负面情绪。如网络红人“秦火火”“立二拆四”故意编造铁道部在“7·23”动车事故中向遇难的意大利籍旅客赔偿3000万欧元的谣言,仅两个小时就被转发1.2万次,广大公众不明真相,对铁道部及政府的不满情绪非常强烈并持续扩大,政府形象及公信力受到很大影响。
3.消极社会心态在网络谣言动员中容易转化为集体行动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的长期存在和积累,使消极的社会心态不断积聚并达到较高水平,一旦出现诱发因素,遇到偶发的影响较大的社会事件,极易引起人们较为激烈的情绪反应,成为推动事件不断升级的动力因素。网络谣言在这个过程中正是发挥情绪动员的作用,谣传的“事实”激发人们内心的焦虑、恐惧、不公等消极社会心态,让旁观者对当事人产生同情和怜悯之心,并在某些事实、观点、态度方面达成共识,形成情感共鸣。在瓮安事件中,聚集在一起的既有移民拆迁中失意的流离者,也有矿权纠纷中吃亏的乡民,既有忧虑社会治安的居民,也有狂热的年轻人,他们在这起事件中产生共鸣,成为一个共同行动的临时性群体。
研究表明,作为原子化的个人与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群体中个人的有意识人格消失,无意识人格得势,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他们的思想和感情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并倾向于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即刻的行动[12]。因为作为群体,他们不善于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他们不再具备作为独立个体所具有的理性分辨能力,在谣言的围攻下越陷越深,愈发认为谣言传播的内容就是真实的,进而盲目地追随群体目标,陷入群体的无意识,个人无所不能、势不可挡的力量感无限膨胀,在打、砸、抢、烧等不理性行为中发泄不满情绪和内心积怨。
四、基于社会心态层面的网络谣言治理策略
网络谣言的产生、传播与时下人们的社会心态有着直接关系,尤其是在危机情境下,网络谣言与消极的社会心态相互作用,往往成为危机事件发展的催化剂和助推器。因此,消极的社会心态是人们制造、散布网络谣言的重要诱因,加强网络谣言的治理,必须注重对消极社会心态的疏导,大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1.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是价值观的载体,价值观是社会心态的根本要素,是个体的态度、观念的深层结构,主宰着个体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反应、情绪和最后的行为”[13]。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高度凝练和升华,从国家、社会和个人等三个层面确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各自层面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主张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所需坚持的最核心的价值观念[1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心态所应达到的“应然”高度,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引领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对于增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推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网络的空气净化、控制网络谣言的滋生繁衍具有重要意义。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心态,首先,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努力追求和实现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用好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宣传引领作用,引导公众自觉将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国家的价值目标统一起来,提高公众的价值认同和幸福感,逐步消除负面的社会情绪情感,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其次,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引导人们正确地认知社会,使其能够辩证地认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矛盾冲突等问题,看到这是大多数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增强改革发展信心,有效调整社会变革引发的偏激、狭隘的社会认知及消极的评价态度,疏解怨恨、愤懑、不公等不良情绪。最后,引导人们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个人行为的价值准则,树立正确善恶观、荣辱观、利益观、伦理观,规范道德行为,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良好的社会心态能够为人们提供宁静平和的心境,减少网民的牢骚、抱怨、谩骂等言论,提高他们科学理性认知社会的能力和辨识谣言的能力,让谣言止于理性、止于智者、止于健康稳定的社会心态。
2.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重要战略部署,这是实现现代化和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于改变人们负面、悲观的社会认知,矫正、优化社会心态,有效治理网络谣言具有关键作用。
首先,建设法治政府,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政府行政权力的运用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在法律赋予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依法惩处政府部门和官员滥用职权、懒政怠政、失职渎职等违法违规行为,树立政府的威望,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政治认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如此,政府及官员代表发布的信息和声音方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及时辟谣止谣。“扑灭一则谣言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人的问题:‘相信什么’取决于由‘谁来说’。没有一个可靠的发言人,反谣言的战斗必然导致失败”[2]271。
其次,保障公民权利。把实现公平正义作为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则,加快完善体现权利、机会、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推进司法公正,加强权利救济,加大环境污染、食品卫生、安全生产等问题的惩治力度,推进教育公平和医疗改革,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逐步消除弥漫社会的弱势心态、不确定性和焦虑感。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在公共事件发生时,官方及媒体应在第一时间公布真相、公开信息,一味地捂着盖着、封锁消息、控制舆论,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必然会引起公众的猜测和主观想象,进而臆造“事实”,导致谣言满天飞,也使事件朝着相反的方向疾步而行。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事故发生后,死亡人数、危化品危害、划分隔离带、空气污染等不实信息在网络上迅猛传播。导致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方信息公布滞后,官方的新闻发布会公信力不足,作为发言人不能解答人们心中的疑惑,甚至半遮半掩走过场,难以获得公众的信任,反而使人们更倾向于相信来自各方的小道消息。
最后,依法治理谣言。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以法治思维治理网络谣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针对网络乱象,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1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网络谣言的相关行为及适用的刑法罪责做出说明,明确造谣传谣的责任主体和责任划分,为依法治谣提供依据。谣言是一个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的复杂现象和事物,在具体的法律应用过程中,司法和执法部门还要对个人造谣传谣的心理动机、危害程度等进行细致甄别,谨慎处之,对蓄意而为、恶意造谣的人要严厉惩处,而对不明真相、非主观故意而导致谣言传播扩散的则要以批评教育为主,避免一刀切及打击面过大而走向反面,使整个社会噤若寒蝉,禁锢人们的言论自由表达权利。
3.提高公众的理性思考和辨别能力
一则网络谣言的生命力与受众的理性思考和辨别能力有较大关系,谣言接受者的理性思考与辨别能力强,谣言就容易被识别、被澄清;反之,谣言就会进入下一个传播环节。因此,提高公众的理性思考能力,使其面对谣言时能够认真辨识,不轻信,不盲从,不做谣言的“扩音器”,是控制和减少谣言的重要策略。
首先,加强国民教育,扩大公众的知识面,提高他们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在通常情况下,个人对一则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判断是以其掌握的相关知识为基础的,个人掌握的知识多一些,触及的领域广一些,就更容易判定面对的信息是否为谣言。而且,公众在受教育过程中,也会不断增强自身的逻辑推理能力和理性分析能力。事实上,每天充斥在我们周围的大多数谣言是经不起推敲的,只要我们始终保持冷静、理性的态度,大部分谣言会很轻易被识破的。此外,我们还应教授公众掌握甄别谣言的技能和基本方法,注重典型案例分析,把握谣言出现和传播的规律。网络既是传播谣言的平台,也是我们识破谣言的工具。当我们面对一条不知真假的信息时,完全可以通过网络来搜索常识知识和官方信息,以辨别真伪,还可以作为一个议题提出,由网民进行讨论,集中大家的知识和智慧来揭露谣言,让网络成为谣言的粉碎机。
其次,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提高网民的道德自律能力。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网民与网民之间的关系具有间接性、虚拟性,难以凭借直接的道德舆论进行评价,网民外在的道德约束力被弱化。因此,提高网络社会中个人的道德自律能力尤为重要,必须“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16]。通过网络伦理建设和道德教育,让网民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在独处的环境下,仍能严格自律,保持高度的道德自觉,拒绝和抵制用网络恶意造谣、恶意传谣、中伤他人、制造事端,抑制谣言的传播与扩散。
总之,谣言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现象,它与人类社会是并存的,我们不能试图消灭它,特别是到了今天的网络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策源地,成为公众对社会问题产生的观念和情绪释放的平台[17],我们只能进行有效的疏导和治理。在当前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期,我们更要注重对网络谣言的监测,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通过国家、社会和公众的合力,努力消除谣言传播的动力机制,规范和加强谣言的法律治理,最大限度地减少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1]黄毅峰.社会冲突视阈下的谣言行动逻辑探析[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12(5):29-35.
[2]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M].郑若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周玉琼.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
[4]弗朗索瓦丝·勒莫.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M].唐家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25.
[5]ALLPORT G W,POSTMAN L J.The Psychology of Rumor[M].New York:Holt,Rinehart&Winston,1947:33.
[6]黄毅峰.谣言传播与社会冲突的内在逻辑探析——从瓮安“6·28”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说起[J].理论与现代化,2010,(3):86-92.
[7]郑永年,黄彦杰.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J].文化纵横,2011,(2):18-23.
[8]赵军峰,金太军.论公共危机中谣言的生存逻辑——一个关于谣言的分析框架[J].江苏社会科学,2013,(1):130-135.
[9]卡斯·R.桑斯坦.谣言[M].张楠迪扬,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26.
[10]李若健.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1.
[11]FOUCAULT M.Death and the Labyrinth:The World of Raymond Roussel[M].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177.
[12]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8.
[13]梅萍,杨珍妮.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心态的有效引领[J].中州学刊,2015,(3):94-100.
[14]何云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主张的新诠释、新概括[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5-14.
[15]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N].人民日报,2014-02-28(1).
[16]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17(2).
[17]刘大勇,潘玲.网络舆情影响及政府应对策略[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57-63.
(责任编辑:于健慧)
D035.29;G206
A
1005-460X(2016)05-0008-06
2016-05-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微博政治引导研究”(13BZZ070)
张爱军(1962—),男,辽宁建平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网络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从事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理论、网络政治研究;孙贵勇(1979—),男,辽宁朝阳人,博士研究生,从事网络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