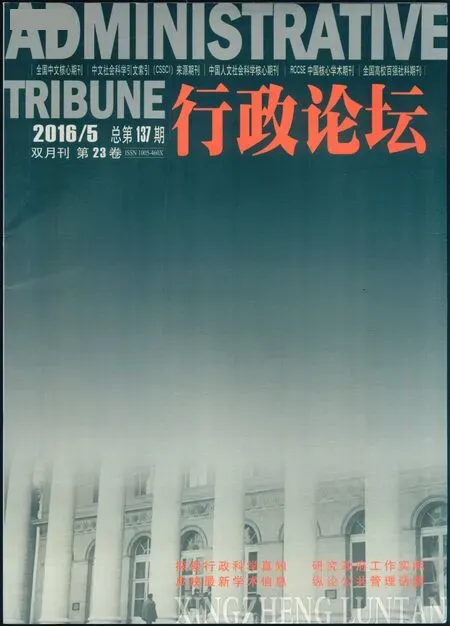协同治理生成逻辑的反思与调整
◎金太军(1.南京审计大学 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1815;2.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江苏 苏州215200)
◎鹿 斌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215021)
协同治理生成逻辑的反思与调整
◎金太军1,2(1.南京审计大学 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1815;2.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江苏 苏州215200)
◎鹿 斌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215021)
为了应对后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特征的发展,由个体失败所演绎出来的协同治理似乎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然而,基于对不确定性的重新解读、个体失败的行为指向和对协同惰性的深刻认知,协同治理的生成逻辑存在一定的推理谬误,这并非是从“应然”到“实然”的简单跳跃。因此,有必要形成一种更适合后现代社会治理的逻辑演绎。并基于协同惰性的风险,一方面要以公共权力为逻辑起点;另一方面,要以政治认同、主体条件、经济绩效、制度保障等四个要素为功能性支撑,以期达到善治的目的。
社会治理;协同治理;不确定性;集体行动;协同惰性
一、引论
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政策文本中语义的变化体现的是后现代社会对治理模式的改革诉求。但不论是社会管理还是社会治理,多元协同已然奠定在当下治理模式中的应然选择地位,成为探索治理理论的语义外延以及善治良政实践的核心主题。而这却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个疑问:为何协同治理能成为后现代社会的应然选择?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即涉及协同治理的生成逻辑。综观现有的文献资料,如胡德(Hood,2003)、卡蓝默(Pierre Calame,2005)、郑巧(2008)、沙勇忠(2010)、俞可平(2012)等,其生成逻辑的演绎大致可以概括为不确定性—个体失败—集体倾向—协同治理。
作为后现代社会的标志性特征,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和冲突成为社会治理的巨大障碍,而由此产生的个体失败似乎不可避免。这种个体失败使行动者不由得倾向于调整自身的外延关系以寻求集体性的合作,试图用集体的建构性力量弥补“单打独斗”的不足。应当说,这一逻辑演绎结合对理论要义与客观实践的运用与体悟,使社会治理内生语义与核心要旨得到彰显。
但在笔者看来,这一生成逻辑似乎陷入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ean Herskovits)的“应然—实然之谬误”,即从“是怎样”简单跳跃到“应当怎样”的天然偏见或线性推理。因为这种推理是非理性的,没有正当的依据,以至于和客观情况存在严重的脱节,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推理的谬误。具体来说,协同治理的生成逻辑看似由浅入深、步步推进,却存在诸多的漏洞,产生诸多疑问。如不确定性怎样解读?是否一定带来威胁和冲突?是否会造成个体的失败进而产生集体倾向?更重要的是,难道协同治理就不必然成功?这些疑问构成对协同治理生成逻辑的深刻反思。
二、“不确定性”的内涵解读
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中,“不确定性—确定性—新的不确定性—再确定性”的循环前进始终成为历史发展的伟大律动。如果说在近现代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和人类认知程度的限制而造成的这种律动还不甚明显的话。“随着后现代运动兴起,以‘逻辑上的非决定论’和‘历史上的进化论终结’为内核的不确定性范式却替代了现代性的确定性范式,成为确定性阐释的后现代话语”[1]。正因为是后现代社会的差异性、多元性、不稳定性、复杂性撬动确定性因素中的不确定性因子,而它们却塑造后现代精神的核心旨归。在鲍曼(Zygmunt Bauman)看来,“如果说现代性首先表现为‘确定性’以及对于‘普遍性基础’的崇拜,那么后现代性则最主要地表现为是一种不确定性和‘多元主义’,一种对现代理性的失望和反思,一种对现代理性霸权的一元论的改弦易辙”[2]。可以说,工业革命出现之后所形塑的近现代社会必然性和理性特征在后现代社会已然迷失其历史方位,而随机性、偶然性等不确定性因素却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比比皆是,成为推动历史发展和演化而不可忽视的动力。
施瓦茨(Swartz)曾言:“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3]通常来说,不确定性主要产生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由于外部环境的变迁而造成的不稳定状态,这是最为常见的、时时发生的,或潜移默化,或突如其来的“变动态”;第二,诸如权力、信息和能力等资源的不均衡配置,由此而产生行动体和行动本身的“多样态”,用博曼(James Berman)的话来说,“行动领域是开放的,而不可能如实验室环境般封闭”[4];三是由于受非理性因素(如感情波动、价值取向)的干扰,行动者的行为时常偏离正常的输出渠道,并且基于非理性因素不确定性和隐性的考量,这对行为的影响既至关重要又潜移默化。
关于不确定性的定义,理查德·福尔勒(Richard Fuerle)将不确定性解释为“在任何一瞬间个人能够创造的那些可被意识到的可能状态之数量”[5]。而米塞斯(Misses)用事例概率来表示的不确定性却是指“对于特定事件,我们知道一些决定其结果的因素,但同时也存在着我们不知道的决定因素”[6]。应当说,这种定义方式和内容都具有显著的哲学意蕴,是在一个相对抽象的语义空间内的解读。虽然不确定性的概念属于自然辩证法范畴,但在公共领域的应用就应当嵌入政治科学的话语谱系。在笔者看来,对于不确定性概念的解读应立足于后现代社会背景,侧重于内容的解构以从部分窥探整体,从而避免拘泥于本身的整体阐述而陷入抽象的逻辑陷阱。因此,不确定性的解释应当包含以下四个要素:一是复杂性。之所以复杂,是由于我们对于它的界定很难予以准确的定位,对所谓系统镶嵌的情况几无可能合理厘定。简言之,“确定性连通简单性,不确定性连通复杂性”[7]。二是多元化。这是由于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而造成的,不论是人群的自由迁徙还是科技助推,多样的利益、价值、行为的交流与碰撞已成为常态。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脱域化”[8]使人们离开祖辈生活的地域到陌生的地方去,使不同的要素在特定的空间集聚成为可能。不仅如此,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哈丁(Russell Hardin)的群体冲突逻辑中的认同差异、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困境中的利益冲突、梅莉(Sally Engle Merry)的法律多元理论,无不在说明多元化在后现代社会中所造成的挑战。三是无序性,从许多方面来说,人类是有着有序性偏好的,对有序性的追求是获得预期结果的前提,也是人的安全感的来源。但无序却始终伴随着历史的左右,并给人的有序追求造成极大的障碍。后现代社会中的结构调整、改革发展、转型升级都成为无序性扩大不言而喻的前提。四是不稳定性,普利高津(Llya Prigogine)认为,“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在所有的层次上都发现了涨落、分流和不稳定性,导致确定性的稳定系统仅仅与理想化、与近似性相对应”[9]。也许他把稳定性看成不可触摸的空中楼阁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对后现代社会不稳定性的悲观论调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人们在谈论不确定性时似乎都是与威胁、风险、危机、失败等消极性词汇相联系,这就在社会治理的逻辑演绎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不确定性导致个体失败”的假象。奈特(Frank H.Knight)并不认同这种联系,他认为风险等消极性词汇与不确定性是有着很大区别的,所谓风险是“可量度的不确定性,而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才称为‘不确定性’”[10]211。也就是说,“在风险中,一组事实中的结果分布是已知的(或是通过事先的计算,或是出自以往经验的统计),但对于不确定性来说,这一结果是未知的,这是由于所涉及的情况极为特殊,所以根本不可能形成这样一组事实”[10]211。而张康之对不确定性的悲观态度也持否定观点,他指出:“不确定性决不意味着施予组织的都是消极压力,在某种意义上,不确定性可能是组织潜在的资源,最起码,对于拥有自主性和积极行动愿望的组织成员来说,不确定性是以机遇形式出现的资源”[11]。首先,不确定性也意味着模糊性和弹性,这就为各行动者利用边界不清的机遇进行协商谈判、讨价还价预留空间,也为扩大自身能力、扩展行动领域提供便利;其次,不确定性也是一种权力来源,克罗齐耶(Michel Cozier)曾言,“一般的或特殊的不确定性因素,在任何交易中都构成最根本的资源。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在行动者看来就是权力”[12]。谁能够掌握不确定性领域,谁控制关键的不确定性领域,谁就拥有关键的权力;再次,不确定性更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力量”,不论是对制度建构还是社会结构的冲击,由此而产生的任何创新性要素,都是对旧事物的摒弃和发展。波拉克(HenryN.Pollack)指出:“不确定性,远非前进的障碍,它实际上是创造性的强烈刺激因素和重要组成部分。”[13]因此,不确定性同样遵循自然辩证法的规律。在后现代社会中,它所带来的结果并不必然与威胁、风险等消极性词汇相连,而是存在深厚的积极性价值和建构性力量。
三、不确定性场域中的个体行动选择
按照协同治理生成的一般逻辑:“不确定性—个体失败—集体倾向—协同治理。”不确定性导致个体失败,应当说这样的演绎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按照胡德的说法,“任何一个行动者,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没有解决复杂多样、不断变动的问题所需要的所有知识和信息;没有一个行动者有足够的能力有效地利用所需的工具;没有一个行动者有充分的行动潜力单独地主导一个特定的政府管理模式”[14]。的确,在后现代社会,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以复杂性的系统撬动结构、以多元化的要素助推碰撞、以无序性的流动加剧矛盾、以不稳定性的结构释放冲突,从而时时刻刻都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面对不确定性的挑战,显然增加脆弱而有限的个体行动的失败几率。政府失败、市场失灵、志愿者失灵等观点的提出,不仅是在治理理论内生语义上的反思,更是对客观实践多维外延的拷问。
不过,仅侧重于不确定性的消极影响而推导出个体失败,显然是将这种片面思维扩大化的逻辑结果。上文业已指出,不确定性也是以机遇形式出现的一种资源,是人类创造性发展的重要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必然走向失败,如果运用得当,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积极的作用,助推个体治理能力的发展。在实践中,证明此观点的例子俯拾即是,如对中国而言,从2008年开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即是一场政府自身革命。面对当代社会中民众对公共服务多元化、复杂性、个性化的要求,以管制为核心的传统政府职能已然脱离时代的步伐。在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理念的指导下,以政府结构调整为起点、以政府行为优化为抓手、以政府机制创新为选项,将公共服务职能上升为政府的核心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生语义和现实诉求。而在西方各国,在经历“企业家政府”失败的教训后,新公共服务理论试图吸收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合理内核,提出以“掌舵”角色替代“划桨”角色,使政府改革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更适合现代治理发展。但需要强调的是,不确定性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绝不是简单的哈姆雷特式预言(生存还是毁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后现代社会中,个体行为的选择和结果运用非此即彼的简单取舍难以找到正确的答案,而是应内嵌于复杂的治理过程以及深刻的关系调整之中。
可见,“不确定性导致个体失败”这一逻辑环节存在漏洞,而由此演绎出的“个体失败产生集体倾向”这一环节同样留有疑问。因为个体与集体的直线式对立仅具有抽象意义上和平面结构中的逻辑关系。严格来说,这也应当属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框架。但在社会治理中,作为一个动态、复杂、多维的行动空间,这绝非是运用简单的二元思维框架能够回应的,而将理论语义中的逻辑关系“不加修饰”地嵌入实践行为中显然是一种“想当然的无知”。面对不确定性的挑战,我们需要拓宽新的视野,创立新的关系和规范准则,进行一场“治理革命”,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村的未来提供新的精神方向和治理体制[15]。但个体行动所做出的调整,并不必然形成与他人合作的意愿,而是有五种可能的选择:一是自我优化,即通过自身改革甚至革命以实现与治理需求相匹配。这方面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如前文提到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即是一例。二是他人协助,麦圭尔(Michael McGuire)认为,知识作为社会与经济生产中的一个要素日益凸显,通过非政府的参与者将不同的知识整合为共同的任务能够创造更富有的生产力[16]。如智库在社会治理中承担信息收集、分析和知识输出的功能,成为行动者的重要智囊。三是转交给他人,即其他行动者相对自身而言更具效率和效益的事项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协定转移治权。这即是萨瓦斯(E.S.Savas)所倡导的合同外包,利用政府和企业或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来共同提供公共服务[17]。四是放弃,对公共治理而言,这并不是一种消极行为,反而是契合善治良政的有益之举。如政府权力的转移和下放,不但有利于减轻自身负担,而且对于培育社会力量、释放市场红利大有裨益。五是合作,这也就是所谓的集体行动。可见,在社会治理中,个体行为选择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仅具有完善的理论支撑,更有丰富的实践佐证。当然,集体行动的确存在巨大优势,因为个体更有可能受到外部的威胁,这种脆弱和不安全的感受,提供维系内部整合的强大动力。正如鲍曼所说:“团结在所有社会中都是确定性的庇护与保障,是信任、自信与勇气的庇护与保障,没有它们,自由的实践和尝试的意愿都是不可想象的。”[18]应当说,在后现代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调整和演变,为集体行动的建构提供必要性说明,而且公共理性的扩散和个人理性的受制也助推合作行为的凸显。
在实践中,集体行动并非是“必然的成功”,失败却往往伴随左右。从理论上分析,至少有两个因素制约这种集体行动选择,一方面,集体行动理论认为,虽然个人理性是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但这却成为“搭便车”困境的主要起源[19];另一方面,卡尼曼和特维斯基(Kahn man,D.&A.Tversky)提出的展望理论[20],是从个体行为非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认为基于人的认知局限,在不全面的信息和不完全的理性支配下,易于导致行为的扭曲,阻碍趋向合作行动的有效选择。因此,集体行动并非是个体行为选择的唯一方向,甚至其失败的风险进一步增加放弃这种选择的可能。
四、协同惰性:希望的破灭?
个体失败与集体行动之间的确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但总体倾向还是相当明显的。举例言之,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就经历三次集体行动浪潮,分别是改革开放初期以传统政治精英为代表的社会类别群体或身份共同体;21世纪初期政治精英与新兴经济主体的联合行动;2008年之后以社会力量崛起为标志的多元行动主体的共同参与。正如奥兰·扬(Oran Young)写道,“一个治理体系是一个不同集团的成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制定集体选择的特别机制”[21]。而它的最新进展即是众所周知的协同治理,我们无须再次赘述它在何种层次上运作或是处于何种文化和历史背景,仅在一个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它所促使的“所有个体的携手并进而使我们获得安全和确定性的根本保障”这一点,就足以令我们的思维逻辑产生偏向。但我们有必要担忧的是,协同治理并非想象中那样“应然”实现,诸如在目标、权力、利益、信任和成员结构上的差异足以使其困难重重。简言之,协同治理并非总是有效的,协同惰性(collaborative inertia)时常出现。依据协同优势理论的分析,协同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目标。在任何行动过程中,明确地“一致同意”是合作构成的基点。这里所谓的“一致同意”即是共同目标的达成。但该理论却强调,“由于掺杂着组织的和个人的因素,就目标达成共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2]。对任何一个协同治理过程来说,目标的冲突始终存在于个体目标与集体目标的波动与偏向之中。集体的目的在于实现集体行动,获得公共利益,而个人的目的则更为直接明了,即获取更大的自我利益。从这个角度看,漫长的协同治理过程也即是目标取得一致的过程,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耗费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时间的消磨。一方面,参与者可能会在这段时间中出现对初始目标的更改甚至背叛;另一方面,天生的竞争取向会在这种消磨中日益凸显,以加快获益的可能,从而导致各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二是权力。毫无疑问,权力是治理过程中资源分配的根本性力量,失去权力意味着失去一切。但协同优势理论认为,权力更应当是“能够对协商行为和实施方式产生一定影响的力量,因而提出‘权力点’(points of power)的概念,并认为这是构成协同权力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23]。“协同惰性的出现,往往是由于‘权力点’失去动态性,某一个参与主体始终掌握权力,占据‘权力点’,从而挤压其他参与者的权力点位,使其丧失发挥功能、突出作用的机会,从而导致协同过程的‘一家独大’,甚至陷入命令—服从模式的窠臼”[24]。这一点与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提出的协议理论论述相吻合,即“如果A比B有更强的协议力量,A通常将在协议利益中获得更大的份额”[25]。就中国来看,虽然协同治理强调多元参与,但政府主导的政治生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所谓的协同也往往表现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独特模式。因此,协同惰性不仅深深嵌入这种模式结构,甚至会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固化政府统治的新格局。
三是利益。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26]。可以说,利益既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也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源泉。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分析同目标一样,既存在公共利益,也存在个人利益,这也是与目标的二重性紧密相连的。按照协同优势理论的表述,人们之所以参与协同过程,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就在于利用集体的力量弥补个体的脆弱,通过公共利益的实现而推及个人利益的获取。但现实恰恰与此相反,协同治理成为个人利益获取的工具,公共利益反而成为副产品。在达尔(Robert A.Dahl)所提出的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中,就认为,“由于组织关注于分散的公民利益,因而许多公民共享的利益,也是潜在的,可能会被疏忽”[27]。
四是信任。信任不同于其他要素,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地构成任何一个组织的权威和能力,是维系组织成败的关键要素。值得担忧的是,信任并非是天然产生的,而是依赖于后天的培育。因此,对组织和个人在信任上的任何美好预设都存在失败的风险。一般而言,在关系复杂的治理中,不信任应是网络结构的常态。信任之所以难以建立,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由于多元主体在合作治理中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现实考量,往往采取倾向性明显的行为方式,这对相互关系中的信任感具有很强的侵蚀作用[28];二是信任与风险相伴相随,一方选择信任另一方,也就意味着必须承担失信的可能;三是信任关系的建立并非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基于长期的关系沉淀。但协同治理却往往是因特殊需要而形成,具有显著的暂时性,这种在时间上的冲突也提升了信任关系建立的难度。因此可以说,协同行为中的信任阙如,已然成为协同惰性产生的重要来源。
五是成员结构。协同优势理论认为,在协同行为中,“成员关系表现为三个特征,即模糊性、复杂性和动态性”[29]。模糊性主要是指在协同治理实践中,参与各方由于信息受限和功能受阻,难以认知其他各方的具体情况,因而造成“他是谁?我和谁?为了谁?”等一系列治理难题。而复杂性与此紧密相连,既然成员结构的模糊性造成行动中的认知困境,就由此而易于引发行为上的不协调、不统一、不均衡,形成相对无序的不利局面。动态性是强调成员结构变化的实时性、持续性特征,这就为它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又注入新的不确定性因素。应当说,成员结构的三种特性进一步加剧协同内部沟通的困难,成员关系的变动不居使本就复杂的公共事务治理难上加难,协同失败、治理失效就成为当下的常态。
总之,协同治理也并非是万能,需要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下。我们可以理解面对后现代社会不确定性风险而趋向协同治理选择的合理性,但我们更需要冷静、客观地认识一种治理模式的有限性,从而在具体的行为选择中不至于陷入固定、盲目的逻辑困境。
五、协同治理生成逻辑的调整
我们对于协同治理生成逻辑的反思并非是一种全盘否定,而是在理论深度和实践高度上的扬弃和发展。并试图吸收其合理内核,在批判继承治理理论对协同治理有效借鉴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更适合后现代社会治理的逻辑演绎。相比于“不确定性—个体失败—集体倾向—协同治理”逻辑的“应然—实然之谬误”,笔者认为,协同治理的生成逻辑可以这样调整:不确定性—确定选择标准(过程和结果)—协同治理(公共权力起点和要素支撑)。具体来说,不确定性是后现代社会标志性特征之一,逻辑演绎以此为起点,符合现阶段社会治理对现实的具体回应。而确定选择标准是指确定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标准,一是过程要具有民主性,二是结果要具有有效性。这就超越了从主体维度思考治理模式的传统范式,着眼于治理理论在社会结构变迁和政治改革实践中的运用,并通过对民主化和有效性的衡量和体悟,从而充分彰显治理理论契合后现代社会治理实践的高度和深度。依据过程和结果标准进行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不一定指向协同治理模式,如政府在纯公共物品供给、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社会组织在整合基层力量上显然更具优势。但是,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如果说需要准确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方位,具体回应民主政治发展的内生要义,契合后现代社会公共理性建构的现实诉求,那么这种逻辑演绎偏向于协同治理模式应当成为一种必要。当然,协同治理也存在惰性的风险。这就需要对其进一步地说明和完善,一方面要以公共权力为逻辑起点,而非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需要基于四个要素的功能性支撑。关于协同治理的逻辑起点,依据原有的逻辑演绎过程,从个体失败的角度思考集体行动的倾向,是基于个体力量的不足而寻求群体行动,这应是关系调整的维度。但笔者认为,协同治理是一种权力关系的纽合,“关系”固然重要,但“权力”更胜一筹。因此,“公共权力”应是其逻辑起点。众所周知,关系仅是公共权力的派生物,掌握何种权力决定拥有何种关系。在协同治理中,权力拥有者意味着拥有对重要资源的配置权,他不仅代表一种权威,更是他者依赖的基础。正是基于这种依赖关系,从而构成协同主体间的多元关系生成。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公共权力”逻辑起点的定位,直接影响协同治理研究的演绎进路,从而对延伸探究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协同治理是一个复杂的集体行动过程,它不仅涉及主体互动、机制运作、结构搭建等常规性要素,更需要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整体的架构之中。莫拉维斯克(Julius Moravcsik)曾为“共同体联系”设定四个标准,即:(1)互相尊重;(2)关注彼此福利;(3)在共同问题上互相信任;(4)互相关照[30]。可以看出,这些标准的设计意识到共同体自身运作的不足而需要进行补充,但侧重于成员关系的主观认同似乎略显单薄。因此,本文提出协同治理应基于四个要素的功能性支撑。
第一,政治认同。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认同是对共同体的依附,也就是一种“原初忠诚”。这种忠诚可以建立在语言、风俗、宗教、地域种族或认定的血缘纽带的基础上[31]。但这样的理解显然忽略政治学的内生语义,认同不仅是一种主观感受,更是一种力量。用罗斯金(Michael G.Roskin)的话来说,合法性的基础就是同意[32]。
在协同治理中,政治认同应当从两个层次上建构:一是行动者认同,哈丁认为,“个体对诸如族群这样的群体的认同是理性的,而非原生性的,亦非超理性的”[33]。从这个意义上讲,行动者的理性来源于两个方面:获益和法规。所谓获益,简单地说,即是协同治理能够为行动者带来切实的利益,不论是直接针对个人利益还是通过公共利益间接实现,只有利益才是认同的根本动力;而法规本身就是理性的文本呈现,对它的遵守,也就是对理性的运用。二是高层认同,派伊(Pye)认为,在对整个政治体系没有深刻认同的情况下,政治发展通常不能得到长远的推进[34]14。作为一个“威权主义”色彩较为浓厚的国度,高层的一言一行对社会和基层具有很大程度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协同治理仅仅获取行动者自身的认同还只是第一步,只有上升到国家的层面,进入中央政府的视野,才能具有从上至下、从局部到整体的实际的政治意义。
第二,主体条件。这里应当从两个问题去思考,一方面,协同主体的规模,是否越多元越好?斯坦纳(Rudolf Steiner)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在存在众多亚文化的情况下,若某一亚文化改善它的处境,谁受到的损失就不是非常清楚。因此,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相互合作的情景。这种观点似乎暗含一种判断,即一个社会区块越多,其合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相应的情况也就越好。但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却持反对意见,认为“比之于一个有着相对多的区块的社会,一个拥有相对少(三个或四个)的区块的社会,对协合民主构成了更加有利的基础;比之于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区块相对少的社会也大大有利于实行协合民主。其中的原因在于,随着参与协商群体数量的增加,它们之间的合作也变得更加困难”[34]48。笔者赞同后者的观点,协同治理以协商和谈判为主要行动方式,太多的主体参与,可能会降低行动的效度,造成不必要的阻碍。另一方面,主体间互动需要平等,但是否意味着是无差异行动?对这个回答显然是否定,多元主体存在差异,拥有各自独特的优势和资源配属,因而协同是一个互补长短、相辅相成的过程。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过程,就需要政府提供公共资源,而社会组织提供社会资本,以实现公共与私人的对接。
第三,经济绩效。协同治理是寻求合作共享的有效机制,因而以公正、平等为核心的价值旨归才是其内生语义。我们当然不能够否认和抹杀政治语义中公平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对经济绩效的追求和强调也是符合公共话语谱系的外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效率主义导向能够持续刺激行动者发挥自主能动性的最大化,不但激发获取常规的、存量收益的兴趣,而且在合理的范围内能够实现超常规的增量收益。
从实践的意义上看,这种发展秩序成为后发国家的一种优势。应当说,在协同治理中强调经济绩效的实现,一方面,是个人理性发挥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是对公共利益要求做出的应有回应。至于这二者关系的处理可以遵循这样的逻辑:在充分对话的基础上,将个人利益整合为公共利益,而非简单的加减运算,从而在保证公共利益实现的同时,兼顾个人利益。不过还需要强调的是,正如登哈特(Robert B.Denhardt)所言,我们不能把效率的衡量当成唯一的讨论议题,而失去以自由、正义和公平等术语为代表的一些更广泛的人类价值问题作为评判标准的重要性[35]。
第四,制度保障。从实践来看,集体行动的失败往往多于成功,究其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是缺乏应对不确定性的制度保障。马俊就指出:“制度通过对行为体预期的引导和保护,向行为体提供了应对不确定性的社会建制。”[36]应当说,制度在功能上就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控制和对确定性的一种规定。无论是奥尔森提出的“选择性的激励”,还是奥斯特罗姆(Eleanor Ostrom)提出的自主性制度,或是布东(Raymond Boudon)、贝茨(Robert H.Bates)、奈特(Jack Knight)等学者指出的制度建构的重要性,集体行动的规范性研究显然已经成为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密钥。当然,制度建构本身也存在诸多失效的可能,但这绝不意味着从根本上动摇制度保障在集体行动或是协同治理中的地位。它所具有的强制性与认同的普遍性特征,能够为政治与社会秩序提供最有力的保障,成为一种功能性需求而满足于一个群体或是社会。
总之,这里所讨论的实施协同治理的四个支撑条件,虽然有助于解释协同治理何以可为,但它们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即使当所有的条件都不利,要实行协同治理或许困难,但不应被视为不可能;相反,即使四个条件都具备甚至还存在更多的有利条件,但也不能保证协同治理的成功实践。这就符合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在研究政治科学中提出的,协同治理符合所讲的“强调机动余地、自由范围和冒险空间的政治科学文献”[37]。
参考文献:
[1]蒋红雨.论反确定性的生成逻辑[J].学术交流,2014,(9):25-29.
[2]何林军.当代社会的后现代性——鲍曼思想解读[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3):36-40.
[3]克雷纳·迪拉伍.商业万象[M].江卉,维益,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55.
[4]詹姆斯·博曼.社会科学的新哲学[M].李霞,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
[5]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94.
[6]MISESL V.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M].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55.
[7]苗东升.论复杂性[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6):87-92+96.
[8]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5.
[9]伊利亚·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M].湛敏,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43.
[10]弗兰克·H.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M].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11.
[11]张康之.论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活动[J].理论探讨,2008,(5):137-141.
[12]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M].张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导论9.
[13]亨利·N.波拉克.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M].李萍萍,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3.
[14]HOOD C.Paradoxes of Public-sect or Managerialism,Old Public Management and Public Service Bargains[J].International Pubic Management Journal,2003,3(1):1-22.
[15]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M].高凌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4.
[16]罗伯特·阿格拉诺夫,迈克尔·麦圭尔.协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战略[M].李玲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3-24.
[17]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周志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9.
[18]齐格蒙·鲍曼.寻找政治[M].洪涛,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21.
[19]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42.
[20]KAHNMAN D,TVERSKYA.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Econometrica,1979,47(2):263-292.
[21]YOUNG O.International Governance: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a Stateless Society[M].Ithaca,NY.Cornell U- niversity Press,1994:26.
[22]HUXHAM C.Theorizing collaboration practice[J].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03,5(3):401-423.
[23]HUXHAM C.AND BEECH,N.Points of Power in Interorganizational Forms:Learning from a Learning Network[Z].Best 10%Proceedings,Academy of Management Conference,2002,Denver.
[24]鹿斌,金太军.协同惰性: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新视角[J].社会科学研究,2015,(4):72-78.
[25]SMITH J M.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M].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105.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82.
[27]罗伯特·A.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M].周军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36.
[28]HUXHAM C,VANGENS.Managing to Collaborat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llaborative Advantage[M].New York:Rutledge,2005:155.
[29]HUXHAM C,VANGEN S.Ambiguity,Complexity and Dynamics in the Membership of Collaboration[J].Human Relations,2000,53(6):771-806.
[30]MORAVCSIK J.Communal Ties[Z].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September 1988),Supplement to vol.62,no.1:211-225.
[31]GEERTZ C.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c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M]//Clifford Geertz(ed.),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The Quest of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New York:Free Press,1963:109.
[32]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M].林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6.
[33]拉塞尔·哈丁.群体冲突的逻辑[M].刘春荣,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81.
[34]阿伦·利普哈特.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一项比较研究[M].刘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4.
[35]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M].扶松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17.
[36]马俊.不确定性及其后果——国际制度的认知基础[J].国际观察,2011,(1):52-59.
[37]ALMOND G A,MUNDT R J.Crisis,Choice and Change:Some Tentative Conclusions[M]//Gabriel A.Almond,Scott C.Flanagan,and Robert J.Mundt(eds.),Crisis,Choice and Change:Historical Studi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MA:Little,Brown,1973:649.
(责任编辑:温美荣)
D035
A
1005-460X(2016)05-0001-07
2016-05-30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社会和谐稳定长效机制研究”(14JZD02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研究”(13AZD018);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科研成果
金太军(1963—),男,安徽全椒人,院长;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鹿斌(1989—),男,江苏徐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