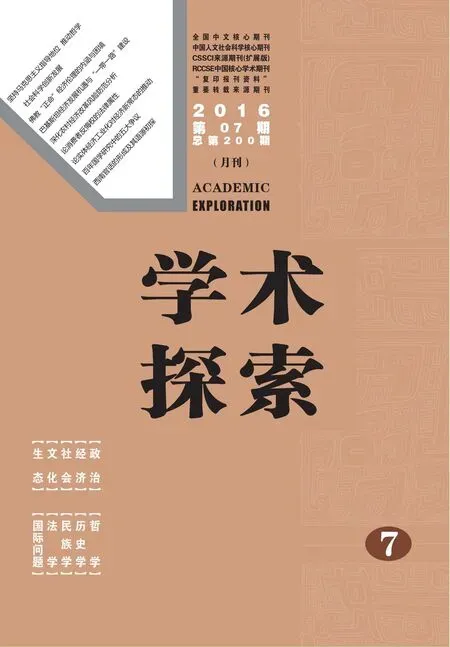佛教“正命”经济伦理的内涵与困境
周湘雁翔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佛教“正命”经济伦理的内涵与困境
周湘雁翔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韦伯认为佛教的遁世立场不会导向任何经济伦理,佛教实际蕴含经济伦理思想。在缘起论的道德原理之上,佛教提出“正命”经济伦理原则,认可物质财富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强调以合理、合法的途径获取财富,必须理性消费与合理配置等。佛教伦理曾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新形势下的诠释和建构,为经济发展提供伦理支撑、道德规范和推动力。面临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挑战,世俗化倾向与内在神圣性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张力。同时,佛教经济伦理本身的普遍性与积极性等理论困境也亟待解决。
佛教;正命;经济伦理;困境
20世纪70年代诞生的经济伦理学,对传统经济行为中的自利最大化、积累成为目的本身等做出批判与反思,将经济与伦理相结合,寻求“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发挥经世济民的思路无疑极具建设性。进而,科斯洛夫斯基在《伦理经济学原理》中说道:“伦理学是市场失灵的调整措施和补救,宗教是伦理学失灵的调整措施和补救。当经济学失灵的时候,伦理学就会出现,当伦理学失灵的时候,宗教就会出现。”[1](P33)对于经济、伦理和宗教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思路。
由于经济伦理的内涵多有分歧,[2]本文界定为经济生活、经济行为方面的伦理意识、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一向度内,新教伦理已被证明提供诸多有益资源。关于佛教,传统观点认为其追求出世,对世俗经济生活必然采取否定的态度,韦伯就曾指出“佛教的遁世立场不会导向任何经济伦理和理性社会伦理”。[3](P33)不过,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出世的独身修行,当然是佛教不变的主体之一,这是寻求宗教觉悟的向上路径。然而,佛教并没有一味排斥、贬低世俗生活,在经济生活方面也提出过许多指导思想,涵括从维持基本生存,利益大众,到趋向解脱的完整序列。显然,这些更多是指向在家的普通大众。出世与入世,一个整体的两个向度,或者说不同层次,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韦伯的观点着眼于前者,从而否定后者,难脱选择性解读之嫌。对于佛教经济伦理的探讨,于现今的意义而言,应致力于世俗大众经济生活。
一、缘起与正命的伦理原则
作为佛教的核心理论,所有教义思想均建基于缘起论上,“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4](P467)董群先生认为:“缘起论是佛教全部理论的基础,是佛教道德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佛教依此而有伦理意义上的关系性思维,建构佛教伦理的基本原则。”[5]因而,佛教经济伦理思想须置于缘起论中来加以考察。
所谓缘起,指诸法因缘和合而成。概言之,一切事物或现象的生起和存在,都依赖于各种条件和关系,一旦某一部分发生改变,整个系统就会改变。以缘起论视之,现实中的个人、社会与自然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人类活动必须为三者和谐共生的总目标而发挥作用。
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一种,对于经济行为的考察与衡量,也应以一个更宽广的视域来对待。由于近代经济发展的某些局限性,过分倚重自由市场机制的作用,以攫取物质财富为唯一目标,甚至牺牲环境换取发展,导致问题频发。究其原因,当群体规模较小时,整体和部分紧密联系,整体利益及其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被首先辨明。随着社会不断扩大,个体无法完全像关注自身利益那样,意识到社会利益的存在。因此,为扭转趋势,首先要转变思想观念,将经济活动回置到社会整体中考察,力图实现自利与利他的双重指标。由此,任何经济行为都必须拥有和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
基于第一原理之上的经济伦理原则,就是正命,即在正确的见解及清净身口意基础上,展开正当、合理的经济行为和生活。佛教虽认为人生是苦,但并不要求人人都遁世出家,而是通过正命将世俗生活与解脱连接起来。待至大乘佛教时期,进一步蜕变为“入世即出世”的菩萨精神,形成所谓的中道解脱。由此,从逻辑上确立了合理的经济生活在宗教上的合法性和神圣性。
关于正命,《中阿含经》认为,不管是当下的世俗生活,还是趋向解脱的修行,都要以理性为指导,确立合理的价值观,不应被贪欲奴役。[4](P469)《阿那律八念经》提到:“正命亦有二,求财以道不贪苟得,不诈绐心于人,是为世间正命;以离邪业,舍世占候,不犯道禁,是为道正命。”[6]
世间正命,即以合法的方式谋取财富,不贪婪,此为世俗伦理层面。出世间正命,就是要遵循佛教的戒律,远离杀生、偷盗和邪淫,杜绝各种咒术、邪伎等,此为宗教伦理层面。
《杂阿含经》又认为“正命具足”应当:“所有钱财出内称量,周圆掌护,不令多入少出也、多出少入也。如执秤者,少则增之,多则减之,知平而舍。如是,善男子称量财物,等入等出,莫令入多出少、出多入少,若善男子无有钱财而广散用,以此生活,人皆名为优昙钵果,无有种子,愚痴贪欲,不顾其后。或有善男子财物丰多,不能食用,傍人皆言是愚痴人如饿死狗。”[7](P23)相对于其上侧重谋财的职业伦理向度,正命也包含朴素的理财观念和消费伦理,既反对不量入为出的过度消费,也反对守财奴式的吝啬,提倡动态收支平衡,如是方能“现法安、现法乐”。综观正命涵盖的经济伦理,即强调以合理、合法的途径获取财富,以及理性消费与合理分配等,必然以认可财物、利益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为前提,否则无从谈起。
由此可知,正命含藏丰富的经济伦理意蕴。同时,它所指向的经济生活,不离世俗的伦理道德。特殊的一面,即符合某些特定的律法与精神,趋向解脱。因而,正命成为佛教经济伦理的基本原则。
二、正命的内在展开:财富观、职业伦理与消费伦理
正命,落实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层面,内在展开为财富观,职业伦理和消费伦理。由此,佛教经济伦理成为一个基本完整的体系。
(一)财富具有必要性与合法性
经济生活以人们对待财富的观念和态度为起点,它决定着后续经济活动的必要性和积极性。正如韦伯指出,早期天主教对待财富的态度十分消极,托马斯把追求财富的欲望,甚至符合道德正义的必要性盈利行为斥为卑贱,教会形成所谓的“利息禁令”,大量富人临终之际总是将巨额财富捐给教会,将高利贷利息返还原主,求得心安和救赎;经济行为总是不关乎道德,甚至从来就是不道德。与此相对,新教教徒表现出一种积极发展经济的特殊理性主义倾向,将对财富、盈利的追逐视为上帝的安排,对事功善行的实践,荣耀了上帝。只有对财富的占有行为,导致奢侈的享乐、人生追求的迷惑和懈怠,才成为反对的道德理由。[8](P46)财富本身并不成为罪恶的对象,而是人们持有的态度。正是这种新教伦理财富观,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与天主教相似,传统观点似乎认为佛教反对物质财富、金钱,进而反对谋求利益的行为。这种误解实则需要澄清,就佛教所释而言,财富、利益有其必要性与合法性。
人不可能离开社会,重新回到纯自然的状态,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物质财富是一切活动的基础,谋利行为必不可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说:“如一切贫穷有情,饥寒、裸露、身心不安,何能造作种种事业?若与衣食令得安乐,然后能修种种事业。”[9]如果人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基本需求都满足不了,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其余高层次行为无从谈起。甚至,倘若不能寻得合法的谋财手段,为了自身生命的存续,必定会铤而走险,以非法手段获利,贫穷极易滋生罪恶行为。《转轮王经》认为:“因穷困故,盗转滋甚;因盗滋甚故,刀杀转增;因刀杀增故,便妄言,两舌转增;因妄言、两舌增故,便嫉妒、邪淫转增。因嫉妒、邪淫增故,彼人寿转减,形色转恶。”[4](P522)
因为贫穷,引发杀人、偷盗、诈骗、抢劫、邪淫等诸多不道德,甚至犯罪行为,进而可能在社会中形成恶性循环,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风气,摧垮民众建立的勤劳致富的财富观。
从正面说,物质财富是包括生命存续在内的一切行为活动的基础;从生理满足,精神追求,到宗教看重的“解脱”“天国”,次第进阶,极少例外。从反面说,物质财富的匮乏,不仅妨碍个人的进取,而且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遑论超越世俗的意趣。
作为现代社会必需品,物质财富本身不具备善恶属性,整个经济行为都是以其为基础,佛教并未摒弃和贬低,而是将其视作必不可少的资材。从广行菩萨道,利益他人的立场出发,大乘佛教对财富持有积极和肯定的态度。财富的基础性,决定其必要性。对财富带来快乐(所有乐、受用乐、无债乐)的认同,意味着道德合法性确立。
(二)积极敬业、合法经营的职业伦理
财富的必要性与合法性,意味着财富的获取和积累必然纳入经济伦理关注的范畴。依据佛教“正命”的界定——“如法求财”,即以合法、合理的途径获得、积累财富,体现为职业伦理。
作为谋取财富的前提,职业技能尤为重要。《善生经》指出:“先当习伎艺,然后获财业”,[10](P72)也就是说,通过一定途径,掌握应有的职业技能,方能有效获得财富。
虽如上说,但佛教对世俗社会的知识和职业技能的态度存在渐变的过程。依据说一切有部的广律,释迦在世的早期佛教,出世倾向浓厚,谨慎对待天、医学等世俗知识,认为与佛教追求的终极解脱无关。部派佛教渐有转变,大乘佛教积极入世,强调自利利他,采取了更为开放、包容的态度,将世俗知识、技能整合入佛教范畴。依据《法华经》,世间法皆是佛法,“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11]换言之,世俗社会的正当劳动生产、工商贸易,佛教均认可。大乘佛教创设“五明”概念,《大乘庄严经论》认为,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都应尽量修习五明,如此才能获取足够的智慧和技能。所谓五明,包括专业佛教义理(内明),更多则是诸如声乐、算数、文学(声明),逻辑、认识论(因明),药疗技术、药理(医方明),农商、建筑、纺织、餐饮(工巧明)等。除去内明,从概数上讲,另外四明几乎可以延伸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行业。不可否认,五明有其独特的宗教考虑,但对知识和职业技能的鼓励,却又是内在于世俗社会,必然推动世俗经济发展。当这些思想落实到社会和具体个人时,呈现为一种积极的职业态度。另外,佛教六度思想中精进一项,鼓励大众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亦即敬业精神,同样具备职业伦理属性。
掌握职业技能和培养敬业精神后,对财富来源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也须予以考量,佛教认为应当通过正当的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得。此中所涉职业伦理,因佛教向下和向上的双重属性,有意兼顾世俗和教法两个层面。
就世俗层面而言,指一切的经济活动中,应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同时还应符合时代的世俗伦理道德的要求。从事任何行业,都应该积极敬业,以正当的劳动谋取财富。《优婆塞戒经》针对经营性的职业活动,专门予以规范。作为道德说教的一种,佛教自然反对杀人越货,偷扒抢劫这些违犯法律法规的行为,即使是诸如偷税漏税这类经济犯罪也在禁止范围内。同时,佛教又认为“贩卖市易教令依平,无贪小利共相中欺”,“不以斗、秤、杂、余、异、贱欺诳于人”。生产经营、工商贸易,以诚信为本,违反世俗伦理道德的短斤缺两,以次充好等不诚实行为必须禁止,否则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环境。
佛教毕竟是宗教,从中衍生出的经济伦理思想,有其区别于一般经济伦理的一面,主要指的是经济活动还应符合佛教戒律,进而有助于解脱目标的实现。据此,有些经济活动虽与世俗的法律法规不相抵触,但与教法相悖,也应尽量规避,诸如屠宰、渔猎、酤酒等职业。佛教的宗教目标在于追求觉悟解脱,这些职业容易导致恶业,使人道德堕落。这就是佛教经济伦理中不共世俗的一面。
(三)理性消费与合理配置
经济的组成要素,包括生产和消费等。吝啬金钱,致使消费不足,产能过剩,产品实现不了应有价值,资源闲置浪费。另一方面,虽说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提供经济发展动力;但过度消费不仅造成市场虚假繁荣,还导致缺乏持续投入,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生活水平难以维持。以“正命”视之,均需反对。换言之,财富消费,同样需要伦理道德去指导、规范。
根据人们对财富的态度和配置方式的不同,演道俗业经》细分为下财、中财和上财[12],呈现为消费伦理的标准。
下财,指仅将财富用来满足家人、雇工最基本的吃穿住行,不孝顺父母、给足妻儿,遑论捐助穷困,发展精神追求。这种态度和消费方式,如同守财奴般吝啬。中财,指孝顺父母,给足妻儿物资。平等地对待雇员、下属等,不令饥饿困乏。精打细算,早晚规划审计收支,谋求事业发展。因尚不信因果,对他人缺乏如理的同情心,故不会接济行善,回馈社会。这是对待财富的俭省态度。上财,指不仅用财富满足相关者的利益需求和生产活动的需要,还能广行布施,将部分财富回馈社会。尤能以之为本,向先贤学士、沙门大德学习,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在佛教看来,这种对待财富的理性态度和消费方式,更值得提倡。
与吝啬相似,佛教对奢侈和挥霍也十分抵制。物质财富的消费,目的在于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本身不具备终极属性,过度的消费行为,追求贪欲的满足,将感官享受当作唯一目的,把理性存在拉低为动物性存在,背离消费行为的初衷。奢侈消费,首先是对财富的浪费,不能得到合理配置,影响后续生活生产。其次,滋长贪欲。佛教认为欲望过多并非好事。《遗教经》指出,多欲之人,追逐利益,徒增苦恼。《善生经》告诫大众要谨防六种折损财物的行为:嗜酒,游戏赌博,放荡,沉溺歌舞,结交恶友,懈怠懒惰。与此相对,一再强调“得利与人共”“当念以利人”,布施财富,利益众生。综合所述四条,佛教消费伦理视域内,吝啬和奢侈的消费方式都是极端不适合的,节俭,进而理性消费,将个人、家庭和社会作为联系的整体考虑在内,寻求“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的统一。
理性消费固然重要,对于财富的合理配置,佛教也一直较为重视。《杂阿含经》认为:“得彼财物已,当应作四分,一分自食用,二分营生业,余一分藏密,以拟于贫乏。”[7](P353)也就是说,财富应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规划,四分之一用来支付日常生活开支,四分之二投入生产经营,余下作为贮备资金,应对不时之需。
进一步考察,《善生经》中建议将所获得的钱财分为六份:“一食知止足,二修业勿怠,三当先储积,以拟于空乏,四耕田商贾,择地而置牧,五当起塔庙,六立僧房舍。在家勤六业,善修勿失时。”[10](P72)
在生活、生产和贮备的基础上,提出一部分用于提高自身的技能和素养,以及宗教生活。其他经典中,尚有一些类似的方案。总的来说,财富配置为四大类:其一,日常生活开支,以满足世间生活的合理需求;其二,投资增值,以保证财富的可持续增长;其三,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其四,慈善事业,回馈社会,利益众生,对教徒而言,包括一定的宗教义务。
透视佛教的经济伦理思想,虽不一定完全符合现今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特点,总体而言依然具备宏观指导意义。肯定财富的必要性与合法性,为世俗大众谋利行为提供了精神层面的支撑。强调积极敬业、合法经营贸易,有利于建立健康的劳动关系和市场经济环境。理性消费,可以防范因奢侈浪费导致资源过度消耗、环境破坏等问题。合理配置,既能保证基本消费和生产,防范不时之需,还能广泛开展慈善,救济贫困弱势群体,补充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方面,无疑体现了佛教对于世俗经济生活的重视,力图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伦理支撑、道德规范和宗教动力。
三、建构佛教经济伦理的困境
自从进入商品经济社会,有了金钱,就有了对金钱的欲望。经济活动中,谋利冲动成为人的基本冲动,如何对待直接取决于人的伦理价值判断[13]。如前所述,早期天主教把为获利而获利的行为视为“鄙夷”“卑贱”。十八世纪的宾夕法尼亚,“谋利行为被视为道德行动的实质,甚至以责任的名义加以推行”。[8](P48)推动道德转向,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韦伯认为是新教伦理。新教伦理形成了所谓“天职”观念,天职源自上帝的命令,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荣耀上帝而努力工作。劳动被证明是一种苦行的技术,可以根治宗教疑惑与道德堕落。新教伦理将日常生活赋予宗教意味,取代禁欲修道作为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
关于中国宗教,韦伯指出,尽管儒家肯定财富和具备功利主义思想,但并没有像新教一样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究其原因,在于儒家缺乏一种将赚钱当作天职,或伦理上的责任的信念。[14]韦伯基本否认佛教导向任何经济伦理,但对于佛教在中国的流变和影响,承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15](P246)与之相对,余英时先生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精神与佛教息息相关;禅宗清规中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就是以超越而严肃的精神尽人世间的本分,禅门的入世苦行不弱于新教的“天职”观。[16](P104)依此逻辑,如果说佛教思想中早已蕴含对财富和世俗职业的肯定,并赋予其神圣意味,唐代禅宗则是因势利导,贯彻于具体实践中,不过多少局限在教团内部,离世俗大众尚有一段距离。待至宋代,沟壑似被破除。韦兵研究黑水城的《慈觉禅师劝化集》发现,北宋高僧宗赜已经宣称世俗生活与修行不相背离,恪尽职守的职业生活同样具有神圣性,是修行成佛的一种途径,从而构建了一套具备超越性的平民职业伦理。这种伦理思想的突破在于,沟通了神圣与世俗,将实践主体扩大至普通的世俗大众,“避免了转型中的宋代社会生活的道德真空,促进了宋代社会经济的成功”。[17]
对于韦伯曾提出的质疑,余英时等学者的回答似乎铿锵有力。然而,此中明显存在差异,即韦伯更多地侧重印度佛教论述自己的观点,后者则是基于中国佛教。中印佛教虽一脉相承,蕴含于印度佛教中的思想在中国佛教中进一步展开,但如果不对这种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习惯性地以中国佛教代表所有佛教样态,必然产生误解,无益于解决问题。构建佛教经济伦理体系,首先要明确佛教固有的出世与入世两个层面,以及不同佛教样态中的教理思想和伦理意识,并根植于现实经济发展状况、特点,杜绝含混不清。
近代以降,中国佛教开启现代化运动,如人间佛教等,基本都是取材传统佛教资源,以现代西方理性为参照,不断调整自身的叙事方式和侧重点,回应现代性问题挑战。这种策略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促使佛教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理契机”,免于被世俗社会流放。不过,理论体系的建构或者诠释,不是全无困境。宗教与现代性之间总是存在紧张关系,于佛教则是世俗化与神圣性之间不可避免的内在紧张。宋代,宗颐的佛教化平民职业伦理,就曾引发较大争议,甚至被斥责为迎合世俗,“我执”犹存。对于这种世俗化趋向,佛教界多少持保留意见。如今,这一担忧依然存在。一方面,佛教不得不重构理论,回应现代性挑战,为自身发展谋求出路,这就必然带有世俗化、去魅化的趋向;另一方面,又担心顺俗运动,可能使得人们失去高度的精神追求,演变为流俗。神圣与世俗的内在张力,致使学理上始终强调以出世为最高准则,倡导在世而出世,入世即出世。问题是,过于强调出世的诉求不仅会给人否弃世俗的印象;并且,依于经典的圆融自洽理论,究竟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多大的实践可行性,或者说能否经得起现实社会的持续考验,仍值得观望。
正如前述的“正命”伦理原则,佛教具备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供理论体系建构和诠释,以回应现代社会中经济发展提出的种种诉求和挑战。只是,这种回应始终存在着不可化解的张力。如何既能导俗,推动和规范世俗经济生活的发展,又不失去佛教看重的高度追求,将理论可行性最大化,即关于经济的伦理意识、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如何落实为伦理实践,成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构建佛教经济伦理必须面对的困境。
当然,宋代佛教职业伦理的构建所取得的实质成效,无疑证明了它绝不是空想理性主义。然而,佛教伦理没有取得如同新教一般的耀眼成就,或许与其自身对财富暧昧不清的态度相关。新教伦理视域内,受到上帝青睐的有益职业,评价标准有二:一是道德,即创造的物质财富对社会的重要性;二是私人获利情况,不应该放弃合法获利更多的途径而选择较少的途径;只有当财富引诱人懒惰、奢侈享受时,才成为邪恶的东西。[8](P131)新教伦理一方面强烈反对本能享乐,尤其是奢侈消费;另一方面又将赚钱的欲望解放出来。抑制消费和渴望赚钱,致使财富不断被投入再生产,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相较于此,佛教经济伦理对个人获利,以及攫取财富行为的态度平淡许多,缺乏明显的积极鼓励,更多地基于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或缺性,或者自利基础上的利他,“若诸菩萨求诸世间工业智处,为少功力多集珍财,为欲利益诸众生故”。[18]财富分配中,也明确一部分投入生产经营,但终究不如新教伦理般,强力推动再生产。换言之,佛教的伦理思想,可以成为市场经济行为的有力支撑与规范,然则缺乏更为积极的财富观使得推动经济发展的宗教动力稍显不足。部分佛教学者提出了所谓“佛教知足经济学”,[13]试图扬长避短,或许反证了此点。问题是,现今我国虽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人均收入相对较低,尚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这些都表明维持经济持续发展,提高人民收入仍是当务之急。如何为经济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推动,是佛教经济伦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构建佛教经济伦理的第三个困境,乃是出于佛教的宗教精神和戒律等因素,尚有一些职业被忌讳。如果说,这是因为考虑到人类的脆弱心灵,维护佛教徒的道德标准,似乎欠缺足够的考虑。以此逻辑,诸如卖酒和屠宰之类的从业者,将被排除在佛教伦理规范之外。伦理本具的普遍性得不到保障,则适用性和客观公正性将大打折扣。如何去调和这部分从业者的精神世界,需要进一步慎重处理。
综上所述,佛教经济伦理的诠释与建构,处于被动中的积极困难,不管是依据现代性理论来提取原有思想资源,还是试图扬长避短和维护传统,虽不得不为之,但不能过于急切,而应该对现代性本身展开深入的思考,充分意识到现代性的复杂。盲目展开,尽管可以实现理论上的圆融自洽,落实于实践层面则可能虚弱无力,形同虚设。
相较于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支撑,佛教在社会经济伦理方面也不乏建树,这与以往视佛教只重出世的印象不同。佛教蕴含的经济伦理思想,曾为经济发展做出过贡献,但面对新形势时,理论的诠释与建构仍面临内外困境。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财富的攫取和消费,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财富向心力不言而喻。然而,伦理道德的规范作用,并未完全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社会问题时有发生。另一方面,谋求经济持续发展,依然是不变的主题。经济、伦理和宗教的三重关系内,佛教的正命思想,的确可以展开为丰富的经济伦理体系,发挥作用。伦理道德,一旦上升到神圣性的诫命时,超验性就可以在普通概念中被表达,从而强化和补充世俗伦理。现代化过程中,佛教伦理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怎样的宗教动力和伦理规范,或者说佛教经济伦理的诠释与建构,值得探讨,也需审慎对待。
[1]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M].孙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钱广荣.经济伦理论辩[J].学术界,2011,(9).
[3]马克斯·韦伯.经济·社会·宗教[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4]中阿含经[A].大正藏(卷1).
[5]董群.缘起论对于佛教道德哲学的基础意义[J].道德与文明,2006,(1).
[6]阿那律八念经[A].大正藏(卷1).
[7]杂阿含经[A].大正藏(卷2).
[8]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9]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A].大正藏(卷8).
[10]长阿含[A].大正藏(卷1).
[11]妙法莲华经玄义[A].大正藏(卷33).
[12]演道俗业经[A].大正藏(卷17).
[13]圣凯.佛教知足经济学的建构与弘扬[J].道德与文明,2015,(3).
[14]叶仁昌.东亚经济伦理的澄清与辩思[J].独者,2003,(3).
[15]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6]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7]韦兵.佛教世俗化与宋代职业伦理建构[J].学术月刊,2008,(9).
[18]瑜伽师地论[A].大正藏(卷30).
The Connotation and Dilemma of the Buddhist Right Livelihood Economic Ethics
ZHOU Xiang-yan-xiang
(School of Philosoph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Weber thought Buddhist seclusion would not guide any economic ethics.There is economic ethics in Buddhism,hough.Based on dependent origination,Buddhism puts forward the right livelihood economic ethics which think material wealth has necessity and legitimacy.We should follow the secular and religious laws and ethics to obtain wealth,and make rational disribution and consumption.Buddhist ethics made contributions in China.Under the new situation,an interpretation and contruction of Buddhist economic ethics will provide ethical support,moral norms and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Meanwhile,it is also face the challenges coming from modernity and theoretical predicaments.
Buddhism;right livelihood;economic ethics;dilemma
〔责任编辑:李 官〕
B82-053
A
1006-723X(2016)07-0019-06
周湘雁翔(1987—),男,湖南长沙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佛教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