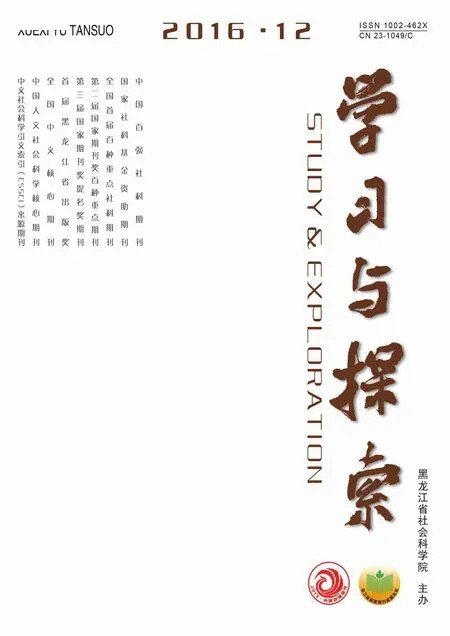唐修《周书》史论辨析
朱 露 川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唐修《周书》史论辨析
朱 露 川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唐人所修“五代史”之一的《周书》,其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周书》的史论在指陈北周历史形势、运用比较的方法评价政治得失、从“时”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关注学术发展及其社会价值等方面,多有突出的特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初史家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风貌。同时,也从历史的和个人的原因剖析,关注到《周书》史论的局限性。
《周书》史论;岑文本;历史形势;政治得失;历史人物;学术思想
唐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李渊接受起居舍人令狐德棻的建议,下诏命萧瑀等人修“六代史”,其中,侍中陈叔达与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同修“周史”。这次大规模修史因种种原因而作罢。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复诏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时任秘书郎的岑文本与令狐德棻同修“周史”,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1]2597-2598。“五代史”于贞观十年(636)正月修成进献,时任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中书侍郎岑文本等人皆因修《周书》有功受赏[2]。《周书》凡50卷,其中本纪8卷,列传42卷,当时亦称“《后周书》”[3]。史载,“其史论多出于文本”[4]2536。
唐贞观年间所修“五代史”,是在房玄龄和魏徵的监修下进行的。魏徵撰写了《隋书》的序、论,以及梁、陈、齐三史的“总论”[5],唯独没有撰写《周书》总论,这或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其一,岑文本是唐初名重一时的文章家,史载文本“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4]2535。唐太宗称赞他:“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长;而持论常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6]可见,由岑文本来撰写《周书》史论自然“不负于物”。其二,《周书》的另一位作者令狐德棻在向唐高祖进言修史时,曾着重指出撰修“周史”的急迫性,他说:“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1]2597由此,《周书》的修撰带有突出的现实意义,这就需要一位受到最高统治者信任,又擅于文辞的人来持论。岑文本堪当此任,故不复再请魏徵作《周书》总论了。当然,上述的两方面原因只是笔者依据史料所做的推论。我们还是要从彼之“文本”,回归《周书》的文本之中,来讨论其史论的特点。
《周书》中的史论有前论即篇首“序”和后论“史臣曰”两种形式。此外,《周书》作者还在叙事的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家发表论点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于序事中寓论断”。本文着重讨论前两种形式的史论。
一、以“周室定三分之业”指陈北周历史形势
对当时历史形势作全局性概括,这是《周书》史论最突出的特点。
北魏末年,统治阶层内部矛盾尖锐,六镇起义之后,国力锐减,大权逐渐旁落于权臣高欢之手。魏孝武帝于永熙三年(534)出奔长安,投靠宇文泰,后被其鸠杀。宇文泰随后扶持北魏宗室元宝炬为帝,建立西魏政权,都长安。此前一年,鲜卑化的汉人高欢在元修出奔后,立元善见为帝,建立东魏政权,都邺城。550年,高欢之子高洋篡位,建立北齐。其后七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在宇文护等人的拥护下篡位,建立北周。由此,北方先后形成了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相对峙的格局,自元修出奔至北周建德六年(577)灭齐,前后持续了44年之久。在北周受禅于西魏的同一年,陈霸先代梁,建立了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朝。于是,北周一方面与北齐交往,一方面也与南方陈朝交往,形成了东—西、南—北都有交往的格局。
如前所述,唐初《周书》的修撰有着突出的政治意义,即宣扬李唐皇朝统治集团的正统观。唐承于隋,隋由北周而来,北周则由西魏而来,因此,对宇文氏所掌控的西魏政权及其建立的北周政权的历史地位做出明确的定位,是《周书》修撰中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
首先,针对北周特殊的历史地位,《周书》提出了“周室定三分之业”的观点。《周书·赵贵等传》后论是这样分析北周所处的历史格局的:
赵贵志怀忠义,首倡大谋,爰启圣明,克复仇耻。关中全百二之险,周室定三分之业,彼此一时,足为连类。独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照邻国。侯莫陈崇以勇悍之气,当战争之利,轻骑启高平之扉,疋马得长坑之捷。并以宏材远略,附凤攀龙,绩著元勳,位居上衮。而识惭明悊,咸以凶终,惜哉[7]!
《周书》卷十六主要记载了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等人的生平事迹,他们都是西魏时期宇文泰手下的重要人物,更是辅助宇文氏建立北周的功臣。所谓“首倡大谋”,是指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杀害后,其部下士卒皆散还平凉,唯独赵贵“率部曲收岳尸还迎”,后说服众人迎宇文泰为主帅[8]。而独孤信、侯莫陈崇二人则跟随宇文泰在西魏与东魏的弘农、沙苑等重要战役中屡立战功。可以说,以他们三人为代表的一批武将,在宇文氏从西魏权臣到建立北周政权成为帝王的过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周书》作者在史论中不仅肯定赵贵等人的赫赫军功,还指出了他们在天下三分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所谓“周室定三分之业”,不仅指出了北齐、北周与南朝陈“三方鼎峙”[9]的割据形势,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北周的建立在这一历史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这正是《周书》作者对北周的历史地位及其所处时代的复杂的历史形势的准确评价。
《周书》史论提出“周室定三分之业”的观点被后世学者赞同。清人王鸣盛指出:“周之兴稍后于齐,其篡皆在梁末,亦稍后,灭齐后三四年而亡,齐与周几几乎若同起同灭者。……愚谓陈、齐、周,亦亚魏、蜀、吴。《周书·赵贵等传》史臣论曰:‘周室定三分之业。’信哉。”[10]
值得注意的是,《周书》卷十六于“史臣曰”之后,附录了西魏时期所立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名录,这里,《周书》作者似乎有意将这一制度的正式建立和推行,与北周开创的政治格局联系起来。西魏“八柱国”的设立,不仅推动了其后府兵制的创立,更促使了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形成,这其中就包括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和唐高祖李渊之祖李虎。《周书》的这一做法,与其史论中提出“周室定三分之业”的观点相结合,《周书》作者将“周室定三分之业”与赵贵等功臣在军事上的功绩相联系,即柱国大将军制度的确立和推行,推动了北周的建立和政权的巩固。
其次,《周书》史论指出了北周一朝短祚的原因。《周书》作者在高度评价宇文泰创业的功绩之后,指出他派遣赵贵追击茹茹将士,斩首数千人,又虏获梁朝百官和士民,将十余万人没为奴婢等杀戮行为,“虽事出于权道,而用乖于德教。周祚之不永,或此之由乎”[11]。这是从宇文泰失于德教的角度指出了“周祚之不永”的原因。而对于周宣帝宇文赟杀害功臣齐王宇文宪一事,《周书》作者感慨道:“齐王奇姿杰出,独牢笼于前载。以介弟之地,居上将之重,智勇冠世,攻战如神,敌国系以存亡,鼎命由其轻重。……挟震主之威,属道消之日,斯人而婴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12]这是通过宇文宪被无辜杀害的历史事实,指出了北周短祚的原因。
与此相对应的是,《周书》作者还对北周的历史命运提出了某种假设。《周书》卷三十记述了窦炽、于翼、李穆等在北周“荣映一时”的臣子。面临隋文帝篡位的情势,窦炽“自以累代受恩,遂不肯署牋”,而于翼、李穆二人则为隋所用,这为《周书》史论所谴责:
翼既功臣之子,地即姻亲;穆乃早著勳庸,深寄肺腑。并兼文武之任,荷累世之恩,理宜与存与亡,同休同戚。加以受扞城之托,总戎马之权,势力足以勤王,智能足以卫难。乃宴安宠禄,曾无释位之心;报使献诚,但务随时之义。弘名节以高贵,岂所望于二公。若舍彼天时,征诸人事,显庆(李穆)起晋阳之甲,文若(于翼)发幽蓟之兵,协契岷峨,约从漳滏,北控沙漠,西指崤函,则成败之数,未可量也[13]。
《周书》这段史论谴责于、李二人“荷累世之恩”,却“送往事居”的不忠行为。其后,《周书》作者对北周末年的历史命运做出一种假设,即认为若李穆和于翼能够发兵声援尉迟迥,则北周或许不会如此短祚。
对此,清代学者认为《周书》作者未曾深考当时形势,这条史论实是“无识之言”。在笔者看来,以令狐德棻、岑文本等人的历史视野和政治眼光,他们并非未深察北周末年的历史形势,他们发出这样一种假设,一方面是从人臣之节和忠义之道着眼的,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于、李二人的实力,否则便是空论了。
二、运用比较方法评价北周政治得失
在对历史形势做出明确评价的基础上,《周书》史论还关注北周政治得失。
比较,是中国古代史学家叙事和发论时常用的方法。“唐初史学家研究历史、评论史事和人物是很善于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的。”[14]这不仅与唐朝统治集团重视以史为鉴的传统有关,也与史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总结性和反思性相联系。唐太宗贞观年间修成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六部正史,其中,魏徵在《隋书》史论中提出了“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15]的观点,即将隋朝的历史命运与秦朝相比较,认为两者短祚的原因相近。这一观点被后世接受和传承,影响深远。《周书》史论也擅长运用比较的方法评论北周一朝的政治得失,有时明确地指出比较的对象及其特点,有时通过具体的论述或体例上的布局安排出无形的对照。
首先,《周书》将北周一朝的君主作了比较,其中尤以周武帝宇文邕和周宣帝宇文赟父子二人的对照最为鲜明。《周书》主要从君道的角度比较了周武帝、周宣帝两朝的政治得失。一是比较两者的个人德行,论者指出,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苦心焦思,克己励精,劳役为士卒之先,居处同匹夫之俭”[16]的贤君,而周宣帝宇文赟却是一位“善无小而必弃,恶无大而弗为”[17]的恶主。二是比较两者对待臣下的不同之处。周武帝知人善任,广开言路,重用了尉迟运、王轨、宇文神举等贤能之才,这些人被周武帝委以重任,心中感激,曾向周武帝谏言皇太子宇文赟的不当行为。而周宣帝亲幸小人,摈弃贤臣,滥杀忠良,致使“内外恐惧,人不自安”。对此,《周书》史论指出:“当宣帝之在东朝,凶德方兆,王轨、宇文孝伯、神举志惟无隐,尽言于父子之间。淫刑既逞,相继夷灭。”[18]三是比较两者在对待吏民方面的差异。周武帝在保定(561—565)年间宣明教化、亲视耕种、安抚百姓,而周宣帝却大兴土木、修洛阳宫、极丽穷奢。这样鲜明的对比就导致了周武帝和周宣帝两朝不同的政治形势。
从历史上看,唐贞观年间君臣是非常重视“居安思危”的,他们经常讨论历史上的政治得失,他们政论中的精彩对话被吴兢汇集成《贞观政要》一书,其中以《君道》篇为首。联系到唐太宗与魏徵等人论君道时强调的“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等思想[19]。可以说,《周书》中的君主论正反映了其成书时代统治集团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实践。而虞世南的《帝王略论》,亦可视为《周书》史论在史学上的借鉴。
其次,《周书》作者将北周与前朝的政治得失相比较。《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列传》后论着重论述了先秦分封制与北周未行分封的不同情况。作者举商周、秦汉政治体制为例,进而指出:
……由此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异术;兵权势位,盖安危之所阶乎。
太祖之定关右,日不暇给,既以人臣礼终,未遑藩屏之事。晋荡辅政,爰树其党,宗室长幼,并据势位,握兵权,虽海内谢隆平之风,而国家有盘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术,惩专朝之为患,忘维城之远图,外崇宠位,内结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潜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闻,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于公族。……是以权臣乘其机,谋士因其隙,迁龟鼎速于俯拾,歼王侯烈于燎原。悠悠邃古,未闻斯酷。岂非摧枯振朽,易为力乎。
向使宣皇采姬、刘之制,览圣哲之术,分命贤戚,布于内外,料其轻重,间以亲疏,首尾相持,远近为用。使其势位也足以扶危,其权力也不能为乱。事业既定,侥幸自息。虽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亿兆可以无患矣。何后族之地,而势能窥其神器哉[20]。
上述内容可视为《周书》作者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指出先秦实行分封制的好处在于使诸侯与朝廷“盛则与之共安,衰则与之共患”,这一制度到秦汉以后被郡县制所替代,显示出了种种弊端。论中又指出单纯地进行分封不能起到巩固统治的作用,分封制度需要配合对兵权、势位的合理调配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统治效果。论中还历数北周自文帝到宣帝历朝所行的制度,指出周文帝、周武帝、周宣帝都没有很好地推行分封制,尤其是周宣帝在位时期,对亲族大肆虐杀,最终导致了权臣杨坚篡位于朝夕之间的败局。
《周书》问世以前,历仕北齐、北周和隋三朝的卢思道曾作《后周兴亡论》,他认为隋之代周,是“天所以启大隋”的结果[21]。与之相比,《周书》作者运用比较的方法评价北周一朝的政治得失,着重指出了人事对于政治进程的关键作用,显得更为切实。
三、着重于“时”评价历史人物
强调“时”的重要,是《周书》史论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论。
“时”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一个重要范畴,它的含义很丰富,最初指四时之序,随着历史观念的发展,“时”与人事的变化产生联系。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较为明确地将“时”与历史人物的活动和功绩联系起来。司马迁的这一观念被后世史家传承,他们从治国与用人之关系,和使当时人、后人懂得做人之常理等方面评价历史人物,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22]。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和隋朝的骤兴骤亡,唐初君臣非常重视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他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关注到客观条件对人的活动的影响和作用,注意到“遇其时”的重要性。《周书》史论在这一点上有突出的反映。
首先,《周书》史论认为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是影响历史人物建立功名的重要因素。《周书》卷十七记述了梁籞等五位西魏—北周时期的骁勇将帅,他们都曾是贺拔岳的部下,并在贺拔岳被害后,与寇洛、赵贵等人一同谋划拥立宇文泰,在宇文氏政权崛起的过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周书》作者在此卷后论中写道:“梁御等负将率之材,蕴骁锐之气,遭逢丧乱,驰骛干戈,艰难险阻备尝,而功名未立。及殷忧启圣,豫奉兴王,参谋缔构之初,宣力经纶之始,遂得连衡灌、郦,方驾张、徐,可谓遇其时也。”[23]这是明确指出客观历史环境的变化,是梁籞等将帅建功立名的重要因素。
其次,《周书》史论进而从“时”的变化来看待古今人才。《周书·儒林列传》后论总结了北周一朝儒士的特点,反映出作者的人才观,即:“前世通六艺之士,莫不兼达政术,故云拾青紫如地芥。近代守一经之儒,多暗于时务,故有贫且贱之耻。”大意是说,两汉时期的儒者通晓六艺,兼能理政,而西魏北周以来的儒士则仅守一经,不通时务。两者相较,差别甚大,而其原因是由于“遭遇之时异也”:
两汉之朝,重经术而轻律令。其聪明特达者,咸励精于专门。以通贤之质,挟黼藻之美,大则必至公卿,小则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后经术。其沉默孤微者,亦笃志于章句,以先王之道,饰腐儒之姿,达则不过侍讲训胄,穷则终于弊衣箪食。由斯言之,非两汉栋梁之所育,近代薪樗之所产哉,盖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时异也[24]818-819。
《周书》作者在这里指出,两汉时期重视经术而轻用律令,西魏—北周时期则先行法令后行经术。这种时代风气的变化,使两个时期的儒士呈现出不同的行事风格和特征,即“遭遇之时异也”。
最后,《周书》作者认为历史人物想要建功立业,就要把握时机。史载,宇文泰早年是贺拔岳的部下,任夏州刺史,及至贺拔岳被害,宇文泰被寇洛、赵贵等人迎还平凉。其后,宇文泰率兵讨杀侯莫陈悦,迎魏孝武帝入关,建立西魏,是为宇文氏的崛起。对此,《周书》史论在总结贺拔胜、贺拔岳两兄弟的人物事迹时指出,正是由于贺拔岳的遇难,为宇文泰建功立业创造了时机,认为:
胜、岳昆季,以勇略之姿,当驰竞之际,并邀时投隙,展效立功。……及胜垂翅江左,忧魏室之危亡,奋翼关西,感梁朝之顾遇,有长者之风矣。终能保其荣宠,良有以焉。岳以二千之羸兵,抗三秦之勍敌,奋其智勇,克翦凶渠,杂种畏威,遐方慕义,斯亦一时之盛也。卒以勳高速祸,无备婴戮。惜哉!陈涉首事不终,有汉因而创业;贺拔元功夙殒,太祖藉以开基。“不有所废,君何以兴”,信乎其然矣[25]。
这里,《周书》作者以“陈涉首事不终,有汉因而创业;贺拔元功夙殒,太祖藉以开基”来譬喻贺拔岳与宇文氏崛起的关系。宋人叶适也指出,“高欢、宇文泰虽同于篡魏,泰,贺拔岳所奖用,岳既见杀,其下无主,扳泰而归之,则近于势之自至也”[26]。这就是说,贺拔岳的战功为宇文泰的崛起做了铺垫,而他的被害,则为宇文泰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概括说来,《周书》史论指出“时”对于人的事功的影响,而古今“时”的变化自亦影响人才的面貌,有作为的人应懂得识“时”等,这就把“时”对人和人才的几个方面都讲到了,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论上,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四、“术艺之于用,博矣”:关注学术发展
重视儒学、术艺和文学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是《周书》史论的又一个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的学术发展与南朝相较显得有些不同,而《周书》中列有标目的四篇类传中有《艺术列传》,这反映出《周书》作者非常关注学术的发展。其总体观点是:“仁义之于教,大矣,术艺之于用,博矣。”所为“大”与“博”,意思就是,思想学术有广泛的运用空间和重要的社会价值。
第一,《周书》重视将学术发展与历史进程相结合。《周书·儒林列传》序上承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序之遗风,回溯了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的历史,可视为一篇学术思想史的论纲。它在论述北周儒学时写道:
自有魏道消,海内版荡,彝伦攸斁,戎马生郊。先王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及太祖受命,雅好经术。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卢景宣学通群艺,修五礼之缺;长孙绍远才称洽闻,正六乐之坏。由是朝章渐备,学者向风。世宗纂历,敦尚学艺。内有崇文之观,外重成均之职。握素怀鈆重席解颐之士,间出于朝廷;圆冠方领执经负笈之生,著录于京邑。济济焉足以踰于向时矣。洎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诏尊太傅燕公为三老。帝于是服衮冕,乘碧辂,陈文物,备礼容,清跸而临太学。袒割以食之,奉觞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24]805-806。
论中指出了时代风气的变化是影响儒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产生了不同的时代风格。
同样,《周书·王褒庾信列传》的后论,是一篇反映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文献,《周书》作者首先论述了文学的起源及其社会价值:
两仪定位,日月扬晖,天文彰矣;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详矣。若乃坟索所纪,莫得而云,典謩以降,遗风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艺,鉴二代以正其本;阙里性与天道,修六经以维其末。故能范围天地,纲纪人伦。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至矣哉!斯固圣人之述作。
逮乎两周道丧,七十义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辩博之论蜂起;漆园、黍谷,名法兵农,宏放之词雾集。虽雅诰奥义,或未尽善,考其所长,盖贤达之源流也[27]742-743。
这里,《周书》作者认为文学起源于六经,并指出文学述作“范围天地,纲纪人伦”“穷神知化”“经邦纬俗”的教化作用,可视为一篇“文学起源论”。
接着,《周书》作者依据时代顺序,分别论述了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的代表性人物及阶段性特征。先秦两汉时期,有“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宏才艳发,有恻隐之美”;南国词人宋玉,“追逸辔而亚其迹”;“大儒荀况,赋礼智以陈其情,含章郁起,有讽论之义”;西汉才子贾谊,“继清景而奋其晖”。《周书》作者对上述四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他们“陶铸性灵,组织风雅,词赋之作,实为其冠”,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突出的地位。
降至魏晋,文学走向“著述滋繁,体制匪一”的多途发展路径。这一时期,虽然“时运推移,质文屡变”,却出现了众多杰出的文章家。十六国时期,“中州版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由于历史时局跌宕,虽然间或有鲁徽、杜广等“知名于二赵”,宋谚、封奕等“见重于燕、秦”,却都着力于“竞奏符檄”,忽略了“体物缘情”。《周书》作者认为,这并非才有优劣,而是“时运然也”,即用前文所述的“遇其时”来总结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特点。
北魏的统一北方,使文学发展出现了复兴趋势。这一时期,有许谦、崔宏、崔浩、高允、高闾、游雅等人,“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其后,又有袁翻“才称澹雅”,常景思“摽沉郁,彬彬焉”,两人皆为“一时之俊秀”。
宇文氏崛起以后,西魏—北周时有苏亮、苏绰、卢柔、唐瑾、元伟、李昶等人涉猎经史,长于属文,并以此位至显贵。北周明帝宇文毓“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他在位时期,“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28],其中,来自南朝萧梁的王褒、庾信二人享誉文坛,《周书》称此二人为当世“奇才”。
至此,《周书》作者详细地论述了上起传说时代,下迄北周的文学发展情况,在《周书》的全部史论之中篇幅最长,论述最详。这篇史论的突出特点是将文学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紧密结合,反映了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周书》史论提出了明确的文学观,即“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西魏时期,苏绰作为宇文泰推行复古改革的主要执行者,在文学上极力主张师古,推崇《尚书》文体。《周书》作者认为这种文学上的师古,“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这是批判苏绰等人一味推行复古,不因时制宜。在西魏—北周复古的背景下,王褒和庾信这两位来自南朝的词人大放异彩。然而,《周书》作者对王、庾二人华丽奔放的文风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批判:“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杨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即过于华丽淫放的文风,同过度的“师古”一样,都不能长久。
基于上述的认识,《周书》作者表达了明确的文学观: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涂,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夫然,则魏文所谓通才足以备体矣,士衡(陆机)所谓难能足以逮意矣[27]744-745。
从上述内容来看,《周书》作者着意于“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的文学观,这与《周书》记载西魏史官柳虬作《文质论》时,认为“时有古今,非文有古今”的观点一致。《周书》作者认为,诗赋、奏议、铭诔、书论等作文旨趣殊途同归,都在于“以气为主,以文传意”,因此,《周书》的史论也反映出一种文质因时的特征。
第三,《周书》史论在学术上推崇“博综”。《周书》卷三十八所记苏亮、柳虬、薛寘、李昶等人,先后参与了国史修撰和勘校经籍等事,称赞他们“学称该博,文擅雕龙”[29]。《周书》史论在评价“一代儒宗”沈重时,称其“学业赅博”:
史臣每闻故老,称沈重所学,非止六经而已。至于天官、律历、阴阳、纬候,流略所载,释、老之典,靡不博综,穷其幽赜。故能驰声海内,为一代儒宗。虽前世徐广、何承天之俦,不足过也[24]819。
上述评论,一方面指出,沈重不仅精于儒学,更是熟掌天文历法知识和佛家、道家的经典,这样一种“博综”的学术视野,与北周时期大部分儒士掌“专门”之学不同,使其“驰声海内,为一代儒宗”;另一方面,这一史论也反映出唐初儒、释、道三者之间相互交汇的学术趋势。联系到贞观年间,唐太宗曾对岑文本说:“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岑文本对曰:“《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30]贞观君臣这种“博综”的学术思想,在《周书》的史论中有深刻的阐发。
五、《周书》史论的局限
综观《周书》史论的风格,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反映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统治集团的历史观念和政治思想。这是《周书》及其同时代所修正史史论的特色,也是其局限所在。
《周书》史论没有完全脱离天人感应的思想。作为封建时代宣扬统治阶层观念的一部正史,《周书》史论虽然反映出较为重视“人事”在历史进程中之作用的历史观念,但是,它仍然未能完全摆脱天人感应的思想。《周书·异域列传》后论中指出,“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虽然“风土殊俗,嗜欲不同”,但是在“贪而无厌,狠而好乱,强则旅拒,弱则稽服”的方面是相通的。《周书》史论认为,这是“盖天之所命,使其然乎”[31]。即将所谓“荒裔”的特征归结于“天命”,这既是落后的历史观,也是落后的民族观,反映出《周书》史论的局限性。
再者,由于要突出彰显“国家二祖功业”,《周书》作者在作论时多有为李唐统治集团之祖先回护、夸饰之处。其中,《周书·萧詧传》后论中将梁主萧詧刻画成一个“任术好谋,知贤养士,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的“中兴”之主[32]。但是,萧詧本是一个争夺皇位未果而另立小朝廷的投机者。《周书》给予萧詧如此之高的评价,是源于萧詧是唐初宰相萧瑀之祖,而被萧瑀委以重任的岑善方即是《周书》持论者岑文本之祖。这样的情况,在唐初所修“五代史”中或多或少存在着,正如刘知幾所说,“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波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33]。《周书》这种回护、夸饰的做法,显得更为突出一些。
此外,《周书》史论中还有一些评价不够准确、公允的情况,是其为后人所批评的地方。
《周书》史论对北周皇朝所处的历史形势的认识,对北周皇朝政治得失的总结及其何以短祚的原因的探究,对时势之影响历史人物命运的论断等,在历史评论方面各有价值;其关于“时”的认识与运用,在古代历史理论发展上,也有一定的意义;而史论中关于学术思想史的表述,则反映了作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深厚修养,这对较晚成书的《五代史志》(即《隋志》)当有所启示和借鉴。《周书》史论的局限性,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作者个人的原因,不再赘述。
[1] 旧唐书:令狐德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王溥.唐会要:史馆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87-1288.
[3] 旧唐书:经籍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90.
[4] 旧唐书:岑文本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旧唐书:魏徵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550.
[6]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453.
[7] 周书:赵贵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271.
[8] 周书:文帝本纪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1:4-5.
[9] 周书:赵善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601.
[10]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书店,2005:554.
[11] 周书:文帝本纪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1:38.
[12] 周书:齐炀王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197.
[13] 周书:窦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530.
[14] 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56.
[15] 隋书:杨玄感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1636.
[16] 周书:武帝本纪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1:108.
[17] 周书:宣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1:126.
[18] 周书:尉迟运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725.
[19] 吴兢.贞观政要:君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2.
[20] 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208-210.
[21] 李昉,等.文苑英华:卷751[M].北京:中华书局,1966:3931.
[22] 瞿林东.评价历史人物的社会意义——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历史理论问题[J].学习与探索,2010,(2).
[23] 周书:梁禦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286.
[24] 周书:儒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
[25] 周书:贺拔胜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227.
[26]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35[M].北京:中华书局,1977:520.
[27] 周书:王褒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
[28] 周书:明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1:60.
[29] 周书:苏亮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690.
[30] 吴兢.贞观政要:崇儒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21.
[31] 周书:异域传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1:899.
[32] 周书:萧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876.
[33] 刘知幾.史通:曲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98.
[责任编辑:那晓波]
2016-06-08
朱露川(1991—),女,博士研究生,从事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
K0
A
1002-462X(2016)12-016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