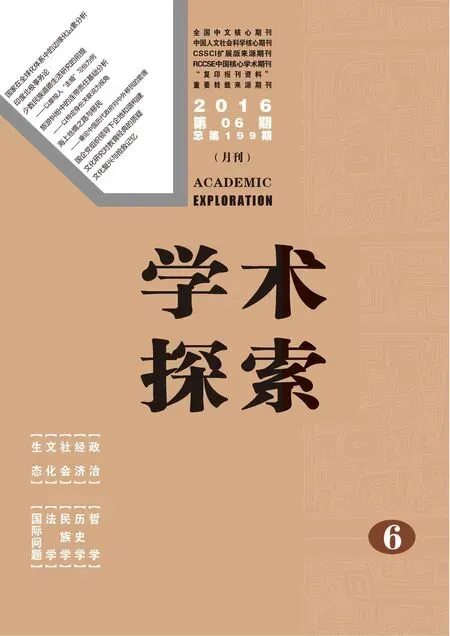忧患意识与乡土情怀
——略论陈荣昌的辞赋及骈文创作
王 准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忧患意识与乡土情怀
——略论陈荣昌的辞赋及骈文创作
王准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清末云南学者陈荣昌的辞赋及骈文创作,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忧患意识与乡土情怀。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既与新旧交替时代的中国清代、近代文学一脉相承,又反映了滇人辞赋、骈文创作的繁荣。在云南晚清、近代文坛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忧患意识;乡土情怀;辞赋与骈文
清代文学具有集历代文学之大成的发展趋势,辞赋、骈文等古代文体亦呈现复兴之势。就云南而言,清代是云南本土文学继明代后的又一繁荣期。涌现出众多著名作家和优秀作品。陈荣昌的辞赋、骈文创作就反映了这种繁荣局面以及中国晚清、近代文学的某种发展趋势。而陈氏辞赋、骈文中忧患意识与乡土情怀的统一,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彰显出其作为“儒家人文主义者”[1](P140)的人格魅力与精神境界。
一、陈荣昌辞赋、骈文中的忧患意识
陈荣昌(1860~1935),云南昆明人,祖籍江苏南京。字小圃,号虚斋,又号铁人。晚年自号困叟、遯农。光绪癸未(1883年)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和贵州、山东二省提学使等。[2][3](P757)著有《虚斋诗稿》《虚斋文集》等多种著述。作为云南近代乡贤中的杰出人物,陈荣昌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仰者和积极践行者。有学者指出:“陈荣昌是虔诚的爱国爱乡者,为国家救亡图存、变革图强而竭忠尽智,为救滇强滇而披肝沥胆,奔走呼号,奋斗不息。”[1](P202)这一评价高度概括了其卓尔不群的君子人格。
陈荣昌的辞赋共21篇,其中《虚斋文集·卷一》收录《翠湖赋》等16篇,《桐村骈文》收有《谷花鱼赋》《吊古赋》《续离骚》《续九歌》《七解》5篇。其骈文收入《桐村骈文》中,共43篇。这些作品均已收入《云南丛书》。而儒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4](P276)的忧患意识则是陈氏辞赋、骈文的重要内容,陈荣昌或托古讽今,发为忧国之叹;或针砭时弊,表达救世之心;或以身作则,呼唤人间正气,凸显了其人品修养与担当精神。
首先,陈荣昌往往借古讽今,在辞赋和骈文中抒发忧国忧民之叹。借用楚骚汉赋的形式以表达忧思,是其创作手法之一。比如收入《桐村骈文》中的《七解》,就借用了汉代流行的“七体”,陈荣昌将同属楚人的庄子与屈原并列,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处世之道。庄子“诱子以生民之欲,进子以方外之游”先后用“天下之至味”“天下之妙乐”“人生之快事”[5](P26135)等七事启发屈原,望其摆脱烦忧。而屈原对家国之事始终难以释怀,常常“抱忧愁之疾”。[5]赋的末尾以庄子为屈原论述“生死之义”屈原“作《怀沙》之赋,自沉汨罗而死”作结。在《七解》中,两种处世态度既反映了儒、道思想的不同,亦是国家危亡之际明哲保身与心怀天下两种人生境界的对立。从情感上来说,富于忧患意识的陈荣昌显然对屈原更为赞同,《七解》显然是借屈原表达忧国之思,抒愤懑之情。
而《续离骚》,则是陈荣昌拟骚体作品中的鸿篇巨制,该赋仿《离骚》之体,既叙写自己的坎坷经历,又饱含着对国家之事的无限忧愁,融身世之感与家国之念于一体:
余颍川之遐胄兮,自明季而南迁;历七世逮于先考兮,凡儒业之四传。值回纥之煽乱兮,飞昆明之劫灰;毁先庐于一炬兮,致尽室之离披。时予方在母兮,从父之官乎会泽;及半途而余降兮,戒征车于七日。肇赐名于始孩兮,实取意于梧桐;华虽朝荣而夕悴兮,干直耸于苍穹……阅甲午与乙未兮,迭襄校于文衡;忽蝮蛇之东来兮,激横波于沧澥。仗鶺鸰之急难兮,侍板舆以归里;身孑孑而独居兮,志更专乎报主。苟上国荐食于封豕兮,吾又何辞乎荼苦;皇忧民之涂炭兮,宁弃地而成行……余岂不倍悲国之无人兮,奈春晖其将晚也……忽惊寤寐以环顾兮,闻画角之哀音;问麻姑以消息兮,谓桑田其已变。隔天门之九重兮,望少康而不见;叫重华于苍梧兮,闻虞宾之尚在。况暴秦其犹未帝兮,何忍为鲁连之蹈海。[5]
《续离骚》一文,是陈氏辞赋中的鸿篇巨制、亦是云南古代辞赋中为数不多的骚体赋。该赋写到自己身逢乱世的不幸,对国家危亡的忧虑和自己欲挺身而出,救国家于水火的大无畏气概。又述及甲午战败后清王朝的一系列危机,如台湾被割让等(准按:“皇忧民之涂炭兮,宁弃地而成行”即暗指清廷割让台湾,与日本议和之事)。通过个人经历与国家急难的对比不难发现,陈荣昌对当时发生的一切始终给予强烈关注,随时做好为国赴难的准备。将个人困难置之度外,以国家之事为己任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十分突出。同时,受儒家忠君思想的影响,《续离骚》里也蕴含着对清王朝国祚终结的惋惜之情(准按:“问麻姑以消息兮,谓桑田其已变”等暗示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之事)。和《离骚》一样,《续离骚》也属于“明己遭忧作辞”[6](P45)之作,反映了陈荣昌历经磨难、自强自励又忧国忧民、系念家国的心路历程。
其次,陈荣昌辞赋、骈文创作中忧患意识的另一表现,就是针砭时弊,表达救世之心,《虚斋文集》中的《斩马剑赋》《扑鼠赋》和《虎伥赋》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面对沉重的忧患,陈荣昌并非一味哀叹,而是不断寻求解决办法,以期为国分忧、为君解难。比如《斩马剑赋》,以西汉朱云上书汉成帝“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以厉其余”[7](P2915)的典故加以发挥,痛陈时弊。陈荣昌借大司马之口“状其五罪”,直言“马之饕餮者”“马之下劣者”“马之喑哑者”“马之桀骜者”和“马之畏缩者”[8](P25723~25724)的种种丑态及其危害。既借古讽今,又以马喻人。赋中所谈到的五种劣马,无一不是晚清官场中那些尸位素餐、贪得无厌而又昏庸无能的官吏的生动写照。而联系陈荣昌所处年代,以及他在任时弹劾贪婪媚外的贵州巡抚兴禄,推举梁启超、袁嘉谷等贤才的壮举,我们不难看出陈荣昌对时局的担忧、对贪得无厌之徒的深恶痛绝,以及消除弊害、为国求贤的决心与信心。
而陈荣昌的《扑鼠赋》与《虎伥赋》,也表现了针砭时弊、积极救世的思想,饱含忧患之情。《扑鼠赋》,有对贪婪之徒的辛辣嘲讽,同时借鼠之口,揭露有权势者的聚敛无度,进而凸显了晚清社会的种种黑暗与不公,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表。而《虎伥赋》则通过愤世子和离诟先生的对答,对为虎作伥者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画,直言其危害,最后借愤世子之口,抒发“缚以终君系虏之缨,而斩以豫让报仇之剑”[8]的除害之愿,与《斩马剑赋》有异曲同工之妙,将忧患意识和兴利除弊之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与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的忧患意识、救世思想相呼应,陈荣昌辞赋及骈文中的忧患意识还表现在以身作则,呼唤人间正气。他有《自策》诗曰:“撑起脊梁立定脚,好还正气与苍穹。”[9](P25932)儒家思想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修身之道对陈荣昌为人与创作有很大影响。故而陈荣昌的一些辞赋和骈文创作感情充沛,行文中激荡着浩然之气。比如《虚斋文集》中的《大节赋》:
节之时义大矣哉!白铁青铜,黄琮苍璧。炼而弥坚,挫而不屈者,金石之精也;沅芷澧兰,崃松甫柏,焚而益香,冻而乃活者,草木之情也。鸟,则王雎挚而有别,黄鹄寡而自贞。兽,则騶吾信而后应,羔羊杀而不鸣。矧夫圆颅方趾,受中以生,居三才之列,为万物之灵乎?[8](P25722)
陈荣昌选取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节操为题,指出其重要性。他认为,自然万物尚有节操可言,而人亦不可失之。他继而以“出处之节”“取与之节”和“死生之节”为论点,历数各种表里不一的失节之态,由此凸显自己对气节的推重。在《大节赋》的末尾,陈荣昌列举周文王、鲁仲连、诸葛亮等“生不虚生,死非徒死”[8]的历史人物,赞美其节操并以之为榜样。最后以“沧海可变,泰山可颓;卓然大节,亘古崔嵬”[8]的论述作结,再次点明主旨。由此可见身处忧患之中的陈荣昌推己及人,希望以传统士人之“大节”,砥砺品格、树立正气的强烈愿望。而在清末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这种于无限忧患中展现节操的做法更有惊世、警世、救世的感召力,具有一种动人的精神力量。
二、乡土情怀与陈荣昌的辞赋、骈文创作
除了深重的忧患意识,陈荣昌的辞赋、骈文创作也流露出了浓郁的乡土情怀。他对家乡人物、风土始终满怀热爱、眷念之情。乡土情怀充实了其辞赋和骈文创作,且与其报国之念有高度的一致性。成为云南地方文学中的佳篇。在陈荣昌的辞赋、骈文中,乡土情怀集中表现为对隐居生活的喜爱、对同乡之人的思念和对家乡风物细致入微的刻画,乡土之美与生活气息融为一体。
辛亥革命后,陈荣昌淡出官场,并于1913年返回云南,携家眷及好友王仲瑜等卜居鸣矣河畔凤村(今昆明安宁县街道办事处镇鸣矣河村)。陈荣昌隐居鸣矣河后,生活清贫,以诗词书法自娱,笃信佛教。《桐村骈文》中的骈文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隐居生活,很多作品都表现出了甘于淡泊、摒弃尘俗、悠然自得的心境。比如在《明夷河解》一文中,陈荣昌详述自己将“鸣矣河”改为“明夷河”的缘由。他指出:“河之畔有村曰凤村,村之上有山曰凤山。《诗》不云乎:‘凤凰鸣矣'河之旧名,盖取诸此。”[10](P26117)而他觉得:“自惭弗类,乃更今名。”[10]有人认为:“凤之鸣,其声归昌,归昌则吉,明夷则凶。先生之号,无乃不祥?”[10]并援引《周易》中“明夷”之卦加以解释。对此,陈荣昌不以为然,他认为:“今之更名,取其音、非取其义也。……鸣与明,两音大同;夷与矣,一声相啭……文字各别,语言自通。”[10]该文围绕“鸣矣河”改为“明夷河”一事,突出了旁人的烦琐和自己的简约。《周易·明夷》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坚贞,晦其明也,内难能而正其志,箕子以之。”[11](P194)故“明夷”有丧失其明,藏其明,晦其明之意。[12](P196)陈荣昌生逢乱世,又历经宦海沉浮,江山易代等事件,因而在隐居鸣矣河后对《易》之“明夷”似乎有了更深的理解。鸣矣河改名一事,反映的正是“固穷以保真,韬晦以终老”[10](P26117)的隐逸思想,表现了一个不慕名利、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突出其阅尽沧桑之后甘于清贫、淡泊自守的心理状态。
而《吾爱吾庐记》,则记叙了素有“陶癖”的好友王仲瑜的隐居生活:
卷诗书而还故乡,佩牛犊而归农圃。访三南之居士,石淙不远;作五柳之先生,松径犹存。喟然曰:“此非先人之蔽庐欤,今吾居之,非故吾欤!”移旧匾而悬之。日手陶诗一卷,吟咏其间:“翠屏九叠,南山见也;薰风一曲,北窗凉也。青鸟翩翩,感王母也;攀龙无路,怅三良也。离筑荆剑,其人安往也;问今何世,远莫逮乎黄唐也。”长吁短唏,万感交集。傲霜有花,惟黄菊之知我;排闷无酒,迟白衣而不来……是以易悲作乐,转啸为歌。逍遥林下之风,跌荡山间之月。仲举芜秽,洁于万户侯家;稚圭草莱,荣于六街甲第。枕石高卧,人境自幽;望云危坐,天宇顿阔,盖骎骎乎羲皇上人矣。虽秦之阿房;汉之长乐;魏之铜台,晋之金谷。尔为尔,我为我。各适其适,岂以彼易此哉
“陶癖”即突出主人对陶渊明的仰慕与喜爱,室名“吾爱吾庐”亦出自陶渊明《读山海经》中“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13](P133)除陶渊明外,作者还提及被誉为“三南居士”的明代云南安宁名士杨一清。足见陶渊明等人对好友王仲瑜的影响,自然之美景与淡泊心境完美融合,古今人物、事物在不同的时空中交错呈现是此文最大的特点。陈荣昌借描写好友“陶癖”的同时突出了自己对隐逸生活的无比留恋,和权势富贵如浮云的感慨。而那种含不尽之意于言中,近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13](P89)的自得之感在此文中亦有体现。
而对同乡之人的思念之情,是陈荣昌辞赋、骈文创作中乡土情怀的又一表现。陈荣昌出仕在外时,常常惦念家乡云南,对于和自己一样宦游在外的同乡也充满了厚爱,在深挚的友谊中洋溢着浓浓的乡情。比如怀念同乡,会泽人张莹的《招鹤赋》:
鹤兮归来,东方不可以往些。万怪惶惑,山有夔魈,水有罔象些。龙伯佻人,其长难以计些;铁镞六尺,射天蜚响些;王亥获禽,生啖以自饢些;归来归来,无惝恍些。鹤兮归来,西方不可以处些。赤犬天飞,傅翼如虎些;张吻呀呀,茹血不吐些;有鸟人面披发,鬤不可以为伍些;归来归来,久恐罹苦兮。鹤兮归来,南有羽民,飞而攫肉些;啮汝皮骨,葬之于腹些;幸而获全,神火炎炎,燎毛如鶖秃些;无水无草,奚以饮啄些;三身之国,以鸟充使,不堪其辱些;归来归来,恐遗毒些。鹤兮归来,北沙莽莽,号曰寒门些;无冬无夏,积雪连天些;冰海千里,跕跕以堕其间些;氋氃冻冱,永不得蹁跹些;归来归来,无自含冤些……鹤兮归来,返滇疆些。金江洱海,环点苍些;玉龙千仞,茎天阊些;鸡足名山,仙所乡些;太华昆池,波汪汪些;夷然清皓,浴生光些;金钟石鼓,家在中央些;翠屏歆渌,澡肺肠些;彩云五色,勿迷方些。[8](P25724)
《招鹤赋》前的小序交代了作赋缘由:“会泽张莹,字鹤君,余之同学友也。光绪甲午八月,疾殒于京师。时余分校入闱。梦鹤君来语余曰:‘莹之叔后夫曾客死,莹又将不得生还,奈何?'余惊寤,及出闱,鹤君果死矣。”[8]此赋为悼念客死北京的云南同乡而作,对于友人不幸离世,陈荣昌不胜悲戚。他把友人比作高洁的白鹤,想象其游历四方时的艰难遭遇,并用家乡的各种秀美山川,招徕其亡魂永归故里。该赋仿《招魂》之体,突出了外界的艰险与故乡的美好,东西南北各处的险境象征着亡友生前经历的坎坷人生和险恶官场,而美丽的故乡云南才是他最后的归宿。这种写法与《楚辞章句》中“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14](P175)的构思是一致的,只不过《招鹤赋》多了对云南山水景物的描写,让友情与乡情互为表里,取得了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
此外,陈荣昌辞赋、骈文中集中反映其乡土情怀的还是那些描绘云南风俗、物产和风景的佳作。比如《续九歌》,就借用屈原的《九歌》之体,叙写云南本土信仰的九种神明,这些神祇包括观世音、城隍、龙神、金马碧鸡等。反映了云南巫风的浓厚和陈荣昌对民间生活的热爱。《续九歌》以骚赋之体,在生动直观地展示清代云南民间信仰的同时也为今人研究云南民俗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而《谷花鱼赋》则是陈荣昌为数不多的描摹家乡物产的作品。在昆明方言里“谷花鱼”意指“稻田或田边水沟里生长的小鱼,水稻扬花时捕捞”[15](P213)其名由此而来。《谷花鱼赋》,描写其由来、产地以及食鱼之乐,全篇洋溢着乡土生活气息:
朱门弹铗苦垂涎,何似村翁得自然。无数小鱼新上市,安排一醉稻花天。时则珠露良宵,金风爽昼;树何阴而不清,山何色而不秀,莲萼红凋,菊苞绿皱。高岭则丹桂难攀,遥汀则白蘋罕遘。爰有谷花,体清香美;取以名鱼,质不伤俚。界禾亩而作池,开筚门而临水。小则一寸二寸,多则千尾万尾。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岂其食鱼,必河之鲤。风人所咏,今得之矣。钓不用丝,撮之以箕;拾芥尤易,盈篮自携。置门内而馈亲故,呼桶中而遗山妻。小玉烹鲜出,长须贳媪来。于是命家儿、召邻叟、据石床、偎瓮牖。润焦唇而鲸吸,战骈拇而牛吼。击缶敲壶,倾觥覆斗。何心更嚼屠门肉,此味足下宾筵酒。客于是乐甚,为醉中之歌。歌曰:“斋堂一盂粥,敲鱼响空木;长生先辟谷,腹无半粒粟。学佛不饱学仙饥,不仙不佛酣且嬉。”主人亦和而歌曰:“万头羊,千头牛。朝食暮食怀百忧,肠回腹痛哽其喉。我家鱼尽谷正熟,两餐饭饱万事休,仰天大笑轻王 侯 。”[10](P26122)
全赋短小精炼,生动而富有概括力。四六相对,属于典型的骈赋。风格亦雅亦俗、亦庄亦谐。既显示出陈荣昌对骈赋文体驾轻就熟的运用,又表现出其对民间口语的大胆借鉴。透露出陈荣昌隐居鸣矣河时既学佛求仙,又留恋世俗。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复杂心态。情、景、物自然天成、浑然一体。赋中人物不为物所役,只追求精神上的自足自适,这就使原本微不足道的谷花鱼饱含着朴素而深刻的人生哲理,引人遐想、发人深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陈荣昌在以巧妙的构思和精美的笔墨描摹家乡云南的山水风物时,并没有忘却家国之事。忧患意识没有就此磨灭,反而更加突出。比如创作于光绪辛丑年(1901年)的《翠湖赋》:
苴兰城堞之间,有翠湖焉。蛇岭枕其后,华山抱其前。地近市而能雅,人侪俗而欲仙。北地寒多,万象忽焉变态;南天暖甚,九龙各自安眠。我归乡里,五年于此,羌夺席而抗颜,非沉渊而洗耳。出门一笑,指倦眼以看花;一日三餐,寄生涯而在水……有月色风色,有云光水光;有燕语莺语,有书香酒香。朝朝暮暮,洒洒洋洋。白社人来,尽入敲诗之座,紫衣客在,同归安砚之乡……将军谁是,苍茫细柳之营;举子空忙,寂寞皇华之馆。岂不以遥望长安,心悲骨酸。车上之铃声乍起,舟中之指血难干。如此风波,孰挽滇池之倒;感言地气,绝无易水之寒。况千古楸枰,几场傀儡。汉唐之日月都湮,蒙段之山川易改。料梁王之画舫,曾来此游;问沐氏之名园,而今安在?风习习兮雨潇潇;水澹澹兮烟飘飘。寄迹则浮萍一片,抽丝则乱絮千条。安所得红藕香中,涤尘襟之懊恼;碧漪亭畔,终身世以逍遥。[8](P25733)
《翠湖赋》创作之时,正值八国联军侵华之际,腐朽的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中,已是风雨飘摇。对于以天下事为己任的陈荣昌来说,这既是国家的不幸,亦是个人之不幸。故在赋末发出了“举目有山河之感”的沉重叹息。正如王夫之所云:“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16](P140)《翠湖赋》便属于“以乐景写哀”之作。赋的上片是读书赏景、飘飘欲仙之“乐”,下片是江山易改、国破家亡之“哀”。翠湖的一泓春水,承载的是昆明山水之美、生活之乐;更是山河犹在、物是人非的感怀和国家将亡又无力回天的深重苦闷。《翠湖赋》于模山范水之中将哀乐之情一并抒之,凸显了陈荣昌内心深处的情感波动,更容易引起人们心灵上的强烈共鸣。
三、陈荣昌辞赋、骈文的文学史价值简论
陈荣昌的辞赋和骈文创作饱含忧患意识与乡土情怀,又兼备众体、博采众长。在云南晚清、近代文学史上取得了较高成就。袁嘉谷《清山东提学使小圃陈文贞公神道碑铭》云:“以为诗文,渊懿古茂,兼杜诗韩笔而一之……发为文章,其书满家,又不肯与世俗所谓文学家、诗词家、书画家较短长、立异同,盖自有千秋,非一时一地之人也。”[3](P757~758)又云:“以余力为六朝骈文,赅徐、庾之长。”[3](P757)对陈荣昌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足以说明陈荣昌包括辞赋、骈文在内的文学作品的重要的文学史价值。我们认为,陈荣昌的辞赋、骈文反映了云南辞赋、骈文创作的繁荣。既突出地域特征,也反映了清代文学的某些特色。
就辞赋创作而言,陈荣昌的辞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云南清代辞赋创作的繁荣局面。有学者指出:
明清是云南辞赋的极盛时代,这个时期作家众多,赋制纷繁。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在中原早已衰落而走向末路的辞赋在滇南呈现了再生的新气象,作家们在这一文学样式上较好地展示了自己的才华,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出现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固然来自多方面,但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滇南沃土的文化发掘来得太迟,惟其来得太迟,作家才有那样强烈的文化冲动,必欲把这一块土地所蕴藏的美作广泛地文化发掘……近古云南作家的辞赋比起散文来更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赋中所体现的,是从来没有人注意过的壮丽河山,丰富物产,民情民俗,充满了神奇和遐想。[17](P447)
陈荣昌的辞赋创作亦是如此。他的辞赋对云南的山川、物产等多个方面都做了曲尽其妙的描写,既展现了其才华的丰富,又熔铸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乡土情怀,呈现出一幅幅多姿多彩的云南本土风物画卷。同时,陈荣昌对赋史上的各种赋体均能熟练运用,比如《续离骚》《续九歌》全用骚体,《劳谦赋》运用散体,《谷花鱼赋》运用骈体,它们无论在表情达意还是描写物态上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效果,云南本土文人对这些赋体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可见一斑。受到清代文字狱等因素的影响,清赋虽存世量大,但发展相对处于低潮,内容和形式趋于平庸,而以陈荣昌为代表的一批云南本土作家恰好以多样的赋体和丰富的内容弥补了这些不足,使清代辞赋在整体平庸的特征下也拥有独特的一面。
而陈荣昌的骈文创作,则体现了清代骈文的复兴之势。受到清代“社会环境的压抑,文化学术思潮的复古……汉学兴盛的学风”[18](P206)影响,发源于魏晋六朝的骈文在清代再度繁荣,以徐陵、庾信为代表的六朝骈文成为清人的学习对象,文坛上出现了以袁枚等“骈文八家”为代表的作家群。清代骈文既师法魏晋六朝又自成一体,成为清代古体文学再度繁荣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作为陈荣昌骈文代表的《桐村骈文》,便与清代骈文创作的发展一脉相承,云南近代学者方树梅指出:“清季滇人以骈散文著者,先生为一大手笔”,[12](P326)这是对陈荣昌骈文较为中肯的评价。与清代众多骈文家一样,陈氏骈文既有六朝风韵,又有清代骈文文体齐备和以博学见长的特色,兼及本土风格,在清末骈文领域独树一帜。足以表明清代文学集历代之大成的发展趋势一直延及近代,对文学史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就作家主体言之,陈荣昌出生在世习儒学的书香之家,他曾有诗云:“我家世为儒,巾箱守旧学。”[19](P25977)儒家思想影响着陈荣昌的一言一行。特别是在国家危难之际,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忧患意识在陈荣昌的辞赋和骈文创作中尤其突出,体现了其作为一个正直的士大夫内心流荡的浩然之气。从这一方面来说,陈荣昌与屈原、杜甫等前代文人多有相似之处。但必须注意到的是,在经历了出仕为官、兴办教育、考察日本以及辛亥革命等一系列人生和国家大事之后,陈荣昌辞赋和骈文创作中的忧患意识往往表现为国家前途的忧虑和思考,传统文学中的忠君恋阙之思反而退居其次。这就足以说明陈荣昌并非是守旧不变的迂腐儒生,而是懂得与时俱进,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做出正确选择的“粹然儒者”。[3](P757)(袁嘉谷语)这与众多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晚清、近代文人也是一致的,在继承儒家传统的基础上蕴含着某种新变。而陈荣昌辞赋和骈文中的乡土情怀,是其心系家国的另一种表现,也有其晚年隐居乡里、信奉佛教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陈荣昌在思想上又与陶渊明、王维等有许多共同之处。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的完美人格在陈荣昌身上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使其成为云南晚清近代士人中的杰出人物。
总之,陈荣昌的辞赋和骈文,突出了忧患意识与乡土情怀两大主旨,又通过它们体现了其君子人格;既顺承了清代、近代文学的发展趋势,又丰富了云南本土文学创作,堪称晚清近代云南文坛的一代宗师。
[1]陈友康.一代文宗陈荣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
[2]方树梅.陈虚斋先生年谱[C].谢本书.清代云南稿本史料[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3]袁嘉谷.清山东提学使小圃陈文贞公神道碑铭[C].方树梅.滇南碑传集[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4]孟子.告子下[C].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陈荣昌.桐村骈文·卷下[C].赵藩,陈荣昌,袁嘉谷.云南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班固.离骚赞序[C].洪兴祖.楚辞补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7]汉书·朱云传[C].班固.汉书(第67卷)[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8]陈荣昌.虚斋文集·卷一[C].云南丛书(第49册).
[9]陈荣昌.虚斋诗稿·卷四[C].云南丛书(第49册).
[10]陈荣昌.桐村骈文.卷上[C].云南丛书(第49册).
[11]周易·明夷[C].王弼撰,楼宇烈,校释.周易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2]王弼.周易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洪兴祖.楚辞补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5]张华文,毛玉玲.昆明方言词典[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16]王夫之.姜斋诗话[M].舒芜,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7]张福三.云南地方文学史(古代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18]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4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9]陈荣昌.诒书生日以诗勖之[C].虚斋诗稿.卷九[M].云南丛书(第9卷).
〔责任编辑:黎玫〕
Sense of Suffering and Local Feelings—On Chen Rongchang's Cifu and Parallel Prose Creation
WANG Zhun
(College of Humanities&Sciences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650091,Yunnan,China)
The Cifu and parallel prose creations of Chen Rongchang,a scholar in the lateQing Dynasty,showed senseof suffering and local feelings from differentangles.Diverse in genre and rich in content,these workswere consistent in style with the literature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reflecting the prosperity of Yunnan people in poetry and parallel prose creation.Thanks to Chen,a glorious page was lef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well as in modern literary circle of Yunnan.
sense of suffering;local feelings;Cifu and parallel prose
I207.23
A
1006-723X(2016)06-0129-06
王准(1990—),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诗经》《楚辞》、古代辞赋、云南地方文学、民俗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