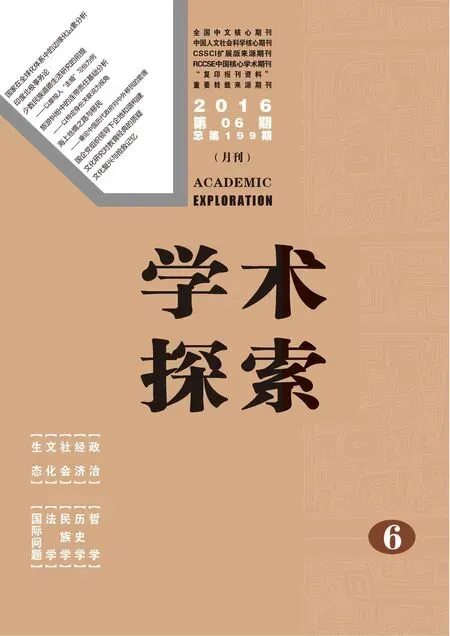张爱玲小说的叙事空间
杨 春
(中华女子学院 学报编辑部,北京 100101)
张爱玲小说的叙事空间
杨春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北京100101)
张爱玲故事空间通常发生在上海和香港,而话语空间通常发生在上海或美国。小说中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的分离,造成价值观的双重审视。故事空间叙述视角的不同,空间表达的价值观和立场的不同,不同人物的空间视角不同,空间含义也不同。故事空间的塑造,既有力地表现了作品主题,又丰富了空间叙事。小说的物理空间主要关于上海和香港的城市空间,心理空间充分地利用隐喻和象征等表现手段,表达内心的感受,社会空间叙述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的生存空间的艰难。
张爱玲;叙事空间;叙事策略
张爱玲的空间形式、空间维度、空间视角、空间功能、空间层次以及空间美学等文本特征的挖掘和研究,对于重新审视经典叙事学理论,完善女性主义叙事学,多维度建构叙事空间理论,挖掘张爱玲的叙事学特征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小说理论中,虽然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并存,但是长期以来理论研究重视时间维度而忽略了空间维度。[1](P54~60)张爱玲对于叙事空间的创作和利用是登峰造极的,她的空间不但描写生动、具体、形象而又真实,而且记录、见证和保存古老的上海和摩登的香港城市的空间图景。她是丰富多彩的家庭日常空间的塑造者和生产者,也是社会空间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展现者。同时从叙述交流的研究角度还会发现,不同空间的读者、不同的创作空间、不同的空间叙述视角对于重新阐释和解读张爱玲作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空间理论是目前学术界非常热的话题,因为空间对哲学、社会学、地理学、史学和文学等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很多理论学家也为空间理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约瑟夫·弗兰克《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巴赫金《小说中的时间和时空体形式》、巴什拉《空间诗学》、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德塞《日常生活的实践》、福柯《规训与惩罚》、戴维·哈维《后现代状况》、鲍德里亚《幻象》、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等著作都为空间理论建立了理论体系。[2](P25~35)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理论来进一步展现张爱玲作品的叙事空间。
一、张爱玲的叙事交流空间
对于空间理论具有开天辟地作用的是查特曼,他根据文本的故事层面和话语层面将空间分成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故事空间”指行为或故事发生的场所、地点或环境,“话语空间”指叙述者的空间,包括叙述者的讲述或写作的空间。在张爱玲作品中,故事空间叙述的是人物与事件的背景,对人物、情节和主题具有推动作用;话语空间则反映的是作品采用叙述视角,描述故事空间的方式,小说中人物的空间感受、认识和态度,以及彰显的人物形象、心灵、价值以及审美趣味等。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的划分,实际上使张爱玲文本发生的内容空间和形式空间剥离和对立起来。查特曼区分了“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奠定了空间理论的基础,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和价值。在对张爱玲的小说进行全面研究后发现,只对空间进行这样的二维的划分是远远不够的。罗宾·沃霍尔将叙述交流的过程划分为六个角色:有血有肉的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有血有肉的读者。[3]实际上这六个角色所处的空间对于张爱玲的小说都可以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根据交流角色所处的空间,可以分为实际作者空间、隐含作者空间、叙述者空间、受述者空间、隐含读者空间、实际读者空间等。真实作者空间指的是创作者所处的空间,真实作者指的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构思和运用自己的技巧与方法,直接从事文学和艺术创作活动,并产生出体现创作者个人特性的作品的自然人。隐含作者空间指的是处于创作状态下的作者的空间。隐含作者是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概念,用来指称一种人格或意识,这种人格或意识在叙事文本的最终形态中体现出来。换句话说,某一个叙事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形态,正是隐含作者有意地或无意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审美趣味等注入其中的结果。叙述者空间指的是小说中叙述者所处的空间。叙述者指直接以语言为观众提供讯息或发表评论的人。受述者空间指的是受述者所处的空间,受述者指的是故事的接受者。读者所处的空间对小说的创作也有影响。而且故事中的人物对于空间的视角不同,产生的空间的价值观和判断也不同。
(一)张爱玲的故事空间
张爱玲所创造的故事空间显示了她惊人的才华。故事空间反映了她对空间本质认知的自然把握,小说的故事空间表现出鲜明地域特色和深刻的社会内涵,其细腻笔法描写了当时时空下的都市和乡村的空间状况,在张爱玲的故事空间中,空间意象色彩斑斓、空间形象饱满丰富、空间地域特征明显。自然风貌的地理空间、家居的“堂寝”空间、民间的习俗空间和社会性别等级空间之间相互交融,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转换相得益彰。构建了常与非常、平凡与传奇、世情与人性的二元对立性的空间组合。反映了张爱玲在空间上的关于历史、民族和现代性的思考和反思,展现了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状况,呈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故事空间上的深刻冲突,具有非常鲜明的张爱玲式的空间个性特点。
发挥故事空间在小说中的功能是张爱玲自觉追求的结果,也是她的小说具有了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因为对故事空间功能的关注标志着现代文学对于城市空间的叙事元素的关注的投射。张爱玲的故事空间多发生在“上海”和“香港”之间,张爱玲将人物放在双城之间进行实践和探索,观察城市空间感和空间文化对于个人特别是女性的生存状态的影响,这种自觉空间意识和空间文化观念在当下叙事学的时空观念非常盛行之际,重新绽放了异彩的光芒。《倾城之恋》就交代了故事的素材来源于香港:“珍珠港那年夏天,港大放暑假,我经常去浅水湾饭店去看我的母亲,她在上海跟牌友结伴同来香港小住……有两个留在香港就此同居了。香港陷落后,我每隔十几天去看他们,打听有没有船回上海。他们俩本人予我印象不深。写《倾城之恋》的动机,至少大致是他们的故事,我想是因为他们是熟人之间受港战影响最大的。”在张爱玲的故事空间中,香港是灯红酒绿,男欢女爱的,同时也是悲哀和无奈的(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白流苏);香港是传奇的故事的诞生地,也是演绎着平凡人的生活的场所(如《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罗杰);香港是上海人的无限憧憬和想象地,也是流落的他乡甚至堕落之所(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在张爱玲的香港空间中,呈现的是香港的情与爱,上海人在香港的努力和挣扎,以及香港的漂泊与无奈。而张爱玲故事中的上海也呈现出不同的风味,张爱玲是上海的书写着,弄堂与洋房,楼梯与电梯,公寓与老宅,呈现出颓废与繁华、苦闷与挣扎、欲望与无望的上海都市空间。张爱玲的上海和香港的双城故事,产生的是双重城市视角,古老与文明、传统与现代、他者和自我审视等视角,使得张爱玲叙事空间呈现出独特的光芒。同时故事空间无论发生在上海还是香港,在这两个城市空间中,张爱玲关注的共同主题是对女性生命力的表现和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个体生命的思索和怀疑。
(二)张爱玲的话语空间
张爱玲的话语空间或者说创作空间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她的生平足迹令世界瞩目,呈现了中国文学女作家走向世界文学的历程。其空间跨越了上海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新中国、英国殖民地香港、异域美国不同环境的巨大变化,[4]创作空间的变化,呈现出张爱玲文学创作地域上的流变轨迹,使得作者的创作背景、创作风格、创作动机、创作情怀、创作态度、创作个性、创作观念、创作心理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话语空间是文本话语发生地点,可以是讲述故事的场地,也可以是写作的地点。《创奇》的话语空间是上海,话语空间反映的是作者受到所处的创作空间历史文化的影响,所以小说所持的观点、态度和评价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创作的话语空间的伦理和价值观等。张爱玲话语空间与故事空间处于分离状态,这样的叙事策略是为了便于从一个空间来观察另一个空间。
后来移居到美国的张爱玲,创作地发生了改变,她的创作观念也有了变化,美国的环境使她对于女性以及对于人性的感悟更加彻底。《色戒》就是一个例证,她在《惘然记》卷首语上说:“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的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30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晚年在美国的张爱玲把自己的感情和对人生的感悟投射到了小说中去,表现了生命个体的悲哀与苍凉,她渴望救赎女主人公,也是试图解救自己。张爱玲在美国创作时,“人性关注”“家族情结”和“故国情怀”依然没有忘怀,但是背井离乡的创作空间和环境使得张爱玲的创作又多了一份漂泊、无奈、怀旧和伤感。
相同的故事,由于作者张爱玲创作空间不同,政治、文化、社会、风俗以及阶级观点等不同,使作品的观点可能不同。张爱玲《十八春》与《半生缘》实际上讲述的是一个故事,男女主角沈世钧与顾曼桢的悲欢离合经历了十八个春天,小说中沈世钧软弱,顾曼桢不幸,顾曼璐自私,祝鸿才无耻。但是因为话语空间的不同而成了两部作品,因而关注点不同。《十八春》是张爱玲在大陆时的作品,故事具有鲜明的共产主义倾向,男女主人公在大时代的感召下奔赴到了东北。《半生缘》是张爱玲到美国进行的改写,张爱玲更强调了对人性的关注。
(三)张爱玲的读者空间
张爱玲的读者群以及读者群所处的空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道非常奇异的景象,研究张爱玲的读者空间实际上就是一部关于张爱玲接受的地域史。多地域的读者,产生了多层面的接受视角和研究视角。多层面的阅读喜好、价值观念、文化取向以及民族特征对于张爱玲作品本身的解读和感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爱玲最初的读者空间是上海。张爱玲的读者意识非常强,她在创作时说《传奇》读者是上海人。“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眼光来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才能看懂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但是后来张爱玲的读者空间变得越来越大。而且随着张爱玲热潮的一浪接着一浪,读者空间并非那么狭小,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以及南洋等都呈现出不同的读者空间,这些读者因所处的空间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例如关锦鹏在改编《红玫瑰与白玫瑰》成电影的过程中,就对小说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将佟振保、王娇蕊和孟烟鹏进行了改造:佟振保成为情爱中挣扎的平庸者,王娇蕊成为挑战常规的叛逆者,孟烟鹏成为反抗男权主义的觉醒者。再比如作品《色戒》伴随着电影改编的成功,由于读者解读空间的不同对作品的解读视角不同,使得对于小说的评价产生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有人认为《色戒》存在严重问题,触犯了民族的价值底线,颠覆历史,玷污人性,践踏道德,涉嫌违法。[5](P77~84)有人从人学的角度,根据张爱玲的人生经历,认为这部作品对理解张爱玲丰富的情感世界以及张爱玲所塑造的灰色人物非常有帮助。[6](P119~121)
(四)张爱玲的叙述者空间
张爱玲有时在作品中为叙述者设立一个空间,将叙述者空间与故事空间分离,处于孤岛时期的女性作家身份的焦虑和自发肩负的对于人性关怀思考的责任和使命,使张爱玲自觉地为叙述者确立了一个独立的空间,通过叙述者将作家的理性与人物的经验性和个体性分离开,从而将生命的体验性和人生的哲理性有机地结合。因为叙述者的空间对于作品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叙述者的空间决定着叙述者的地位、身份、人格以及价值观等,叙述者的空间还决定着叙述者与作者、叙述者与作品、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等,叙事者的功能具体说表现在叙述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以及距离调控、叙述者对于作品的参与与干预、叙述者对于故事的态度和评价等等。如《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篇“请您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很显然这里讲故事的人和故事中的主人公处于两个不同的空间,叙述者的空间在上海,故事中的女主角葛薇龙的生活空间在香港的姑母家,将两个空间进行分离,是作者潜在的叙事策略,目的是为了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小说对香港的姑母家的花园空间描写可以窥见一斑,“园子里也有一排修剪得齐齐整整的长青树,疏疏落落两个花床,种着艳丽的英国玫瑰,都是布置谨严,一丝不乱,就像漆盘上淡淡的工笔彩绘”。这里叙述者首先采用的观察视角是上海人的视角,香港相对于上海来说是开放的。接着小说又叙述到“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的面上”。叙述者又采用了外国人的叙述视角,香港这片神奇的土地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印象是“荒诞、精巧、滑稽”。也就是说在西方人的视角中,香港是古老的东方文化的象征,是中西文化混杂具有东方情调的英国殖民地。《沉香屑第一炉香》这篇小说的空间叙述视角是值得在文学史上写一笔的,因为作者既用全知叙述者视角客观地全面地叙述了关于香港的观察,同时还注重视角多重性,有来自英国殖民者的,也有来自中国上海人的,多重视角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了作品的主题。
张爱玲有时还将叙述者和受述者的空间分开,这实际上是将叙述的主体和接受体之间分开。如《沉香屑第二炉香》文章开头说“克荔门婷兴奋地告诉我这一段故事”,很显然故事的来源是克荔门婷,克荔门婷是故事的最直接的叙述者,并且作为叙事者的她对此故事评价是:“我真吓了一跳!你觉得么?一个人有了这种知识之后,根本不能够谈恋爱。一切美的幻想全毁了!现实是这么污秽!”“我”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直接叙述者,而是受述者,同时也是转述者,主体克荔门婷和受述者“我”之间就“性”的问题的认识和评价是不同的。小说在叙述的过程中采用这种分离形式的叙事策略,其目的是多重的:为故事营造荒谬和可悲的故事气氛,便于故事的发展和暗示故事的结局;形成叙述视角和观点的转换,便于叙述者从不同的空间对故事的内容进行不同价值观的评价,深入地揭示主题;提供一个叙述的场所,使得小说的叙述更逼真,叙述者更具有权威性。
(五)张爱玲的故事人物空间
张爱玲的作品具有永恒魅力的另一个根源,来源于她对故事空间的塑造。故事空间呈现出家庭空间、城市空间与民族空间对人的塑造力和影响力,张爱玲还通过塑造人物空间,拉开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而她建构故事人物的空间,常常采用建立历史空间、异化空间和隔离空间的手段和方式。
历史的空间。历史空间实际上是利用历史造成的空间距离,重新为人物树立塑造历史的故事和场景,从而揭示空间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霸王别姬》中运用历史的空间,塑造了美丽、聪慧、爱情至上的虞姬。虞姬深陷在男性父权的语境下,而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与男性意识也在小说中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体现被屏蔽的女性主义意识浮出历史水面的艰难性。女性主义的价值观和思维意识在历史文本和英雄美人的佳话中进行理性的思考,小说微妙之处在于将虞姬的死放到了男权社会的话语暴力中进行书写,通过描写美丽善良多情的虞姬在楚汉战争中自刎的故事,表面上看虞姬自刎是为了爱情和战争所迫,但是深层上则是对深深刻在女性灵魂深处潜藏的男权话语的社会伦理、社会价值和社会意识所形成的隐含暴力,从精神、肉体对女性的禁锢与规训,这种隐含的暴力使女性无处可藏身,只有自杀才是最好的解脱。张爱玲颠覆了男权话语霸权和宣泄了女性的绝望与反叛,历史空间成为张爱玲的护身符。
异化的空间。异化的空间实际上是采用塑造异于常规的空间,张爱玲为人物建构了一个异化的陌生化空间。在《金锁记》的金钱异化空间中,物质上的极度膨胀和精神上的极度空虚,曹七巧被异化成失去情感能力的疯子。她身上存在着情感、伦理和道德上被异化后的缺陷,这种缺陷在异化空间中被放大后,引起读者认知上的震撼是新鲜的和强烈的。叙述者以远视和客观的视角,叙述陌生化的异化生活场景空间对曹七巧的影响。张爱玲采用异化空间拉长了叙述者和读者的距离,使作者重新进行思考和认识,同时感同身受的体验以及寓言似的故事又使得读者对故事人物的处境产生认同,又拉近与隐含作者的距离。
隔离的空间。隔离的空间实际上是塑造一个与世界隔离的空间。张爱玲塑造的《封锁》,是时间停顿的空间、隔离的空间、狂欢的空间和乌托邦的空间。张爱玲关注的是女性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的生存问题,她一直苦苦追问和思索着女性生存艰难的根源以及女性的出路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问题是紧紧相连的。张爱玲制造了一个封锁性隔离的空间《封锁》,在这个空间中进行尝试性的实验和思索,以极小的空间,折射出人的生存问题,从而进一步寻找解决现代文明痼疾的良方,最后到关注整个人类社会问题,使得张爱玲走出了国土,成为世界性的作家。张爱玲一直在寻找完美的乌托邦的空间,而她《封锁》中的电车就是她所寻找的世外桃源的一个映射。在与世间暂时隔离的空间中,不仅是解决婚姻问题的空间,也是寻求灵魂上的解救,张爱玲希望通过空间的隔离来进行虚拟的空间的描摹,希冀能够解决关于人类命运的问题。列斐弗尔《空间的生产》指出:“某个空间崩溃了。”列斐弗尔所指的空间崩溃是指基于历史、父权、道德观等等方面的传统观念构筑的社会空间消失了,以往传统空间造成的破碎感、杂乱感和无奈感被释放,在新的空间中随着时空观的变化及引起新的身体体验与情感体验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发生着变化,性别观、婚姻观、价值观以及信仰等都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在浓缩的封闭的空间中得以展现,从而展现了空间的社会生产性、社会工具性、社会意识形态性。
(六)张爱玲的故事人物视角空间
对于故事空间来说,叙述视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故事空间由于采取的叙述视角不同,从而能使表达的价值观和立场不同。张爱玲的小说在叙述的过程中,对于空间的感知、认识和评价,往往采用全知叙述视角和人物视角交错的方式来进行。全知叙述者对“故事空间”进行全景描述,从而使文本建立的空间展现在读者的面前,由于全知视角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又是从故事外视角叙述,因而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深思熟虑展示故事的空间和评价故事的空间。作品有时换成人物视角来观察空间,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性别身份对空间的感受。人物视角指的是故事中的人物的视角,故事的人物视角可以展示人物的感知和评价,反映的是人物对某个事件或某个空间的态度和看法,构成整个故事空间评价的一部分。不同的人物对同一个故事空间进行评价,可以形成人物之间的对话。
张爱玲充分地运用故事空间对不同人物的评价不同,使空间产生丰富的含义。《倾城之恋》的白公馆就因为人物的视角不同,使叙述作品中的空间被填充成不同的含义,承受了丰富的内涵。在《倾城之恋》中作者先用全知叙述者的视角将白公馆描述为一个落伍的时代的象征,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白公馆是一个可以逃避现实的神仙似的地方,这里可以逃避现实,过了千年似乎只是一天。白公馆也是一个耗费生命的地方,有的是青春,有的是生命,孩子会一批一批地出生,也会一批一批地被浪费掉了生命。接着又将对白公馆的评价换成人物的视角,以女主人公流苏的视角看,白公馆是拥挤的没有私人空间的。很显然全知叙述者的视角和女主人公白流苏的评价视角是不同的,白公馆不是白流苏的世外桃源,是她必需逃脱的苦海。这样小说因全知叙述者视角和人物视角的不同,造成了叙述眼光和叙述声音的分离,两者视角的对立,为评判空间的价值标准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二、张爱玲的空间叙事功能
故事空间对情节的发展起着促进关系。巴赫金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认为空间和时间同样重要,在文学的时空体里,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
张爱玲故事空间的叙事功能,表现在促进了作品的主题的发展。张爱玲小说中的空间对于表现人物的社会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故事空间的对立为小说的故事冲突创造条件。很多现代小说家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且还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和安排小说的结构以及推动整个叙事进程。[7](P15~22)例如《金锁记》分别以“麻油店”“姜家”构成情节结构的故事空间,使得故事空间成为与曹七巧人性变态密切相关的空间场所。“麻油店”和“姜家”代表了女主人公曹七巧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情感历程,“麻油店”是曹七巧的出生地,七巧穿着“蓝夏布衫裤”,过着卖麻油的朴素乡村生活,有肉铺里的朝禄的爱,而在姜家曹七巧生活环境却是十分恶劣的,周边人对曹七巧的恶评,形成了一张铺天盖地的网,将曹七巧淹没在口水中,甚至丫鬟小双和凤箫也瞧不起她,生存空间极其恶劣。曹七巧赢得了二奶奶的头衔,但是残疾丈夫的肉体是没有生命的肉体,她的空间是被压抑被歧视的。这样的空间造成了七巧的人性被扭曲和行为的乖戾。空间的不同,造成人物的性格、阶级、立场、观点不同。爱德华·苏贾指出,当叙事的时间被中止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有限时间下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充塞着诸种联系,它们交互作用。该场景的全部意味是由各个意义单位之间的反应联系所赋予的。
张爱玲的故事空间有力地丰富了空间的叙事。《倾城之恋》叙述的是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历经磨难而最后结婚的故事,故事空间在香港和上海之间徘徊,使得故事的空间维度得到很大的跨越,故事空间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也会发生改变,有时还会也随着故事空间的变化而变得传奇。白流苏在上海白公馆中,家里的环境非常压抑。经历了失败的婚姻的流苏,身无分文,前途渺茫。当她来到香港,命运发生了改变。香港是一个充满着诱惑的城市,人的欲望在香港这个开放的城市中尽情宣泄。在这个城市里,有电影院、广东戏院、赌场、格罗士打饭店、思豪酒店、青鸟咖啡馆、印度绸缎庄,人们可以享受着阳光、浪漫、潇洒和风流,范柳原和白流苏可以穿着泳装并排坐在海滩上。故事空间的多样性增加了文本的丰满性和充实性,
故事空间有时候会成为某事发展的阻力。《花凋》的故事空间是没有亲情与爱情的。张爱玲把郑川嫦禁闭在封建老宅中,封闭的空间成为川嫦寻找爱情和幸福的阻力,使川嫦经受着精神折磨,爱的各种权利一点点被剥夺,最后她失去了生存下去的能力。在《花凋》中人们刻骨地冷漠,女性的地位是从属、压抑和窘困。郑川嫦的家是个狭小的空间,“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郑川嫦一生只认识一位男士章云藩,“可是她没有比较的机会,她始终没来得及接近第二个人”。这也是个经济上非常吝啬的空间。“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这样禁闭的没有温暖的空间使得川嫦感到窒息,她开始反思,并逐渐有了自我观的认识。这是个无望、腐烂的即将死去的空间,这种空间感受与温暖的、安全、有爱的家的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爱德华·苏贾说,空间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空间是社会动力和社会意识的镜子,空间的组织和意义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它是实际上充溢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物质空间的极度闭塞,造成内心世界的狭隘和精神世界的空洞,张爱玲通过郑川嫦在封闭的性别空间中的遭遇,实际上隐含地表达了深刻的渴望——逃离。
三、空间的叙事层次
叙事空间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成不同的空间类型。叙事空间理论开创者约瑟夫·弗兰克在《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将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分成了语言的空间形式、故事的物理空间和读者的心理空间。[8]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将空间分为物理空间(自然)、心理空间(空间的话语建构)和社会空间(体验的、生活的空间)。[9]爱德华·苏贾在《后现代地理学》关注空间建构中的权力关系以及社会生活中的阶级、性别、种族等方面的压迫形式。张爱玲的小说的空间情况可以分化为物理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等三种形式。
(一)物理空间
张爱玲的物理空间主要是关于上海和香港的城市空间。张爱玲的作品表现出空间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地域性物理空间主要是关于地域空间的研究以及关于对地域的外部特征的描绘。在张爱玲小说中电影院、公园、饭馆、酒吧、公馆、公寓、弄堂等这些成为城市标志的空间,往往是张爱玲叙述的主要空间。她所创造的这些典型空间,既是故事发生的空间,也是城市的精神和文化的象征。小说《色戒》发生的地点是香港和上海,小说重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旧上海的繁荣,小说中呈现出诸多的上海的空间,有平安电影院、凯司令咖啡馆、西比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等,还有电车、人力车等等,还有南京西路,具有民俗和风俗画的特征。张爱玲在《半生缘》里描绘的南京的楼下开铺楼上住人的老房子特色,至今在南京还是一道风景线。
民族性物理空间,张爱玲的作品体现了民族文学记忆功能。在民族空间的叙述中将民族流逝的空间追溯和记录下来,从而作者和读者之间在民族感上获得最大的认同。张爱玲《茉莉香片》中:“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通过民族化和传统化的屏风的叙述,展示了聂传庆对死去母亲的生命的思考,通过民族化意象的建构,将民族历史文化中人们的生存状况、伦理和意识形态等进行建构。物质上中产阶层的构建。《沉香屑·第一炉香》对梁太太的住所进行了叙述,长方形的草坪、白石子栏杆、栏杆外的荒山、齐齐整整的长青树、疏疏落落的花床和艳丽的英国玫瑰,不调和、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空间呈现出色彩斑斓却又与文化杂糅的生活画卷,构筑了一幅上流社会繁华而衰颓的缩影,深刻地记忆和储存了在文化入侵过程中的种种同化与异化、拒绝与接收、渴望与躲避的矛盾的心理,折射出文化传统在面临侵入时的种种窘境。
(二)心理空间
《沉香屑第二炉香》叙述的是因为新娘在新婚之夜缺少性知识而造成精神崩溃的故事。小说在叙述丈夫罗杰被不了解事情真相的人误以为是色情狂而丢失工作时,罗杰的心情的表达是通过厨房的描写来完成的。叙述者采用故事人物罗杰的视角,使得读者随着他的视角环顾他的房间,“厨房里的灯泡子不知为什么,被仆人摘了下去”,厨房暗淡一片,暗示罗杰的生命之灯无形之间被人给摘走了,他的人生就像他的厨房一样昏暗一片,没有希望。烧水的呜呜声音,仿佛是哭的声音,揭示了罗杰内心的哭泣。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工作,火光“只剩下一圈齐整的小蓝牙齿”,“化为乌有”,暗示了罗杰的生命即将消逝。这些都与罗杰往常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现出生活的异常和变化,使读者很容易就意识到了故事的结局。采用人物视角可以利用空间很好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得故事空间和人物内心空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对于表现人物的感受,揭示人物的命运,以及暗示故事的结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张爱玲的小说充分地利用隐喻和象征等表现手段,对物理空间进行叙述和阐释,用空间来表达内心的感受,从而形成心理空间。《半生缘》中沈世钧在守旧的家庭里长大,父亲沈啸桐长年住在姨太太家,身为大太太的母亲则守寡般住在南京的老祖宅中。在父亲的强权之下沈世钧优柔寡断,渴望逃离旧家庭。在沈世钧逃离旧家庭时,小说叙述了一段火车的空间感受,“一上火车,世钧陡然觉得轻松起来”。因为火车从相对封建落后的南京驶向相对开放的上海,“火车的行驶的确像是轰轰烈烈通过一个时代”。反映了世钧对新生活的渴望,对“家里那种旧时代的空气、那些悲剧性的人物、那些恨海难填的事情”的痛苦,他渴望丢下沉重的包袱像火车似的冲破黑暗,驶向光明。
(三)社会空间
张爱玲的小说中的社会空间充分地叙述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的生存空间的艰难。民族、文化、政治、性别、身份等多种因素在空间中会有折射,各种因素、各种关系在空间中聚合,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形成社会空间,社会空间理论提供了空间的社会评价视角,这个视角更有利于对空间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分析。张爱玲通过特定的社会空间有力地刻画了男性霸权社会空间对于女性的摧残和压迫。《半生缘》中对以沈啸桐为中心的社会空间进行了刻画,小说中旧式商人沈啸桐娶了两房太太,他住在哪个公馆,哪个公馆就要比其他的公馆奢侈和浮华一些,住在姨太太那儿时,就多用两个男当差;住大太太那儿,就悬挂起字画,铺上红地毯,新做上窗帘。他在哪儿,家中最值钱的财物,即装着股票、存折和账单的铁箱就搁在哪儿;他住在哪儿,姨太太也会被当成正太太,“可见在他父亲来往的这一个圈子里面,人家都拿他这位姨太太当太太看待了”。而且啸桐是生意人,只认钱和儿子,因为生病他可以丢下十几年的姨太太和孩子而不管。在这个黑暗与腐朽的环境下,女性的财力、物力、人力和精神完全由男性控制着,其生存状态完全取决于男性。
[1]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2]程锡麟.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叙事空间理论概述[J].江西社会科学,2007,(11).
[3]Robyn R.Warhol-Down.“Chapter fourteen.Gender.”Optionsfor Teaching Narrative Theory.Ed.David Herman et al.MLA,forthcoming.
[4]黄万华.“三级跳”:战后至1950年代初期张爱玲的创作变化[J].社会科学辑刊,2009,(5).
[5]刘建平.颠覆历史,玷污人性,践踏道德,涉嫌违法——电影《色戒》批判[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8,(2).
[6]杨璇.寻找女性主义的声音——解读《色·戒》中王佳芝形象[J].凯里学院学报,2013,(4).
[7]龙迪勇.论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J].江西社会科学,2003,(10).
[8]lrena R.Makaryk,gen.ed.,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3.I 2
[9]Philip E.Wagner“Spanal Criticism:Critical Geography,Space,Place and Textuality,”in,lulianWolfreys,ed.Introducing Critici -sm at the21st Century.Edinbourgh University Press,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2006.
〔责任编辑:黎玫〕
Narrative Space in Eileen Chang's Novels
YANG Chu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Journal,ChinaWomen's University,Beijing,100101,China)
Eileen Chang's narrative space and dimension are worth studying.The story in her novels usually occurs in Shanghai or Hongkong,while discourse space in Shanghaior the United States,the separation of which causes double examination of the values.Different narrative perspectives in the story space result in different values and positions of the space expression,and different spatialperspectives of the characters different spatialmeanings.The narrative function of Eileen Chang's story space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irreplaceable role itpl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the story space has notonly expressed effectively the theme of thework,butalso enriched the space narrative.Space in Chang's novels can be analyzed in three dimensions:physical space,psychological space and social space.The physical space refersmainly to the urban space in Shanghaiand Hongkong;the mental space conveys inner feelings by making full use ofmetaphor and symbolism;the social space narrates the difficult living space ofwomen under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Eileen Chang;narrative space;narrative strategy
I207.4
A
1006-723X(2016)06-0135-07
杨春(1970—),女,辽宁人,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