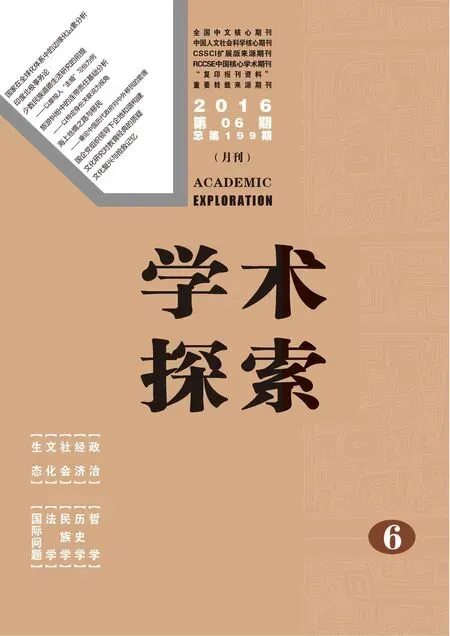文化研究对教育经典的质疑
金志远
(内蒙古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文化研究对教育经典的质疑
金志远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教育经典的永恒价值、权威性和代表性,人们一直是不容质疑的。在已有研究中也很少有人质疑它的永恒价值和权威性。在文化研究看来,教育经典尽管有它的历史价值和教育价值,但是它的神圣地位、确立过程的主观性、价值性和时代性以及其精英文化基础是可以质疑的,教育经典有人为夸张、主观偏好、价值有涉、时代限制、文化偏狭等局限性。泰勒所著的《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文化研究;教育经典;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
文化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但选择哪一种文化进入研究视野,标识出了研究主体的文化立场。“文化”在文化研究中以两种主要的相互交叉的形式出现。一方面是文本、修辞、话语等象征性方式出现;另一方面,文化以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整体的生活方式出现,囊括观念、态度、语言、实践、制度和权力结构,又包括一系列文化实践——艺术形式、文本、经典、建筑、大众商品等等。[1](P48)文化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对教育研究的冲击也是全面而深刻的,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已具有了一定的积淀。
古今中外有许多教育经典名著,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卢梭的《爱弥儿》、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以及中国的《论语》和《学记》等,在课程领域以美国课程论专家泰勒所著《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为代表。那么,教育著作如何成为经典之作,它的神圣地位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的基础是什么?本文试图从文化研究的视角结合泰勒所著《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一书予以讨论和回答。
该书自1949年首版以来,已重印30多次,并翻译成多种文字。1981年,泰勒《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曾被评为1906年以来对学校课程领域影响最大的两本著作之一,它是经典的现代课程理论著作,是理解课程领域后继著作的必读书。[2](P5)对泰勒《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中提出的确定教育目标等四个基本问题,有的人说:“在所有课程论方面的著作中都显性或隐含地探讨泰勒的这四个基本问题。”又有人说“课程的一般理论和概念体系在这些年中没有什么进展,讨论的问题就是泰勒在1950年提出的课程编制的那些问题。”还有人认为,它“至今还在课程学者中广为讨论,并占据课程领域的中心地位”。[3](P454)可见,该书是教育领域,尤其是课程与教学领域的经典之作。
一、文化研究对教育经典的神圣地位表示质疑
教育经典在人们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在时间上生命力持久,可以跨越不同的时代,历经上百年甚至上千年不衰,在功能上,发挥着价值引导的功能。有论者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辞源》归纳分析认为:“‘经典'是‘传统的权威性作品',是‘一定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是‘作为典范的经书'。”[4](P173)这里讲的权威性、重要性、指导性和典范性正是经典的神圣地位的具体表现。如对《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的影响,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课程研究的“圣经”。瑞典学者胡森等人评论指出:“这本书被看作是课程研究的范式,看作是达到了课程编制纪元的顶点。如果人们不了解泰勒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就不可能全面地了解课程问题。”[2](P2)那么,该书果真有如此的价值吗?它的这种神圣地位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一方面,教育经典的神圣地位的确立和产生不是客观的,具有人为夸张的偏颇,其标准很难令人信服。一是由于教育专家们对教育经典的价值和意义非常充分地挖掘和整理,甚至较高地放置到教育及教育史中,夸大其历史作用,缩小其不足和局限性,让普通读者和学习者自然而然地承认了教育经典的所谓的经典价值和影响力。二是由于教育专家们把自己的意图,尤其是把统治阶级的政治教育意图和目的非常巧妙和隐蔽地渗透在教育经典的评述中,这样让普通读者和学习者不经意间、自然而然就接受了教育中体现或渗透的统治阶级的文化、政治意图。有论者指出:“不管在什么语言背景中,经典是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它不但具有规范、法则的意义,而且也具有或明或隐规范、制约人们思维、行为和情感的文化、道德和政治力量。”[5]正因为如此,人们对经典作品的理解、评价都站在特定时代、特定民族和群体的特定态度和立场上。这就导致把教育经典局限在经典的狭小的范围内,不切实际地夸大了教育经典的教育价值,拔高了教育经典在教育及其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剥夺或限制了普通读者和学习者对教育及教育著作进行评价的话语权,促使他们跟随教育专家选定的教育经典而走的被动的局面。
另一方面,教育经典的神圣地位也是一种假象,因为不仅没有任何一种教育经典能够经过所谓的“神圣性”的证实,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教育经典经过了所谓的“神圣性”的证实。所谓教育经典的神圣性是一种主观推测、主观愿望而非一种事实。比如说,我们无法证明泰勒所著的《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达到了课程编制纪元的顶点,也很难证明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课程研究的“圣经”的观点,这些只是有些西方学者的主观判断和认定。
那么,文化研究就是消除教育经典唯我独尊的神圣地位,给非教育经典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实现对教育及教育史的全面评价。有论者指出:“经典作家的声望不是来自他或她的作品的内在优良品质,而是更多地来自复杂的环境与情势,这种环境与情势使文本最初能被人发现,然后使它们能够保持在一个优越的位置上。”[6]这样,本来具有内在优良品质的教育著作和成果,常常由于内在品质无关的其他原因而被排斥在教育经典之外不被人们认识和重视。
在文化研究看来,人类教育及教育史实际上也是广阔的社会史、文化史,所以遴选和挖掘少数教育经典不能反映全部的社会史、文化史,也不能反映全部的人类教育及教育史。要反映人类教育及教育史应对各民族在各时代的教育所体现的全部教育价值进行全面把握和评估。非教育经典也和教育经典一样,往往具有不可轻视的教育价值。那些被排斥在教育经典门外的所谓的非教育经典著作,也许在某些方面逊色于所谓的教育经典,但它们之所以诞生并流传很久,除了反映作者独到的教育发现、教育才华和主张之外,还反映了社会的需要,甚至在某些方面具有所谓教育经典所缺乏的教育价值和意义。因此,教育研究对教育经典的偏爱,甚至拔高其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客观上造成对非教育经典的贬低和拒斥,这对非教育经典来说是不公平的,使它远离读者和学习者的视野,削弱或遮蔽了其应有的教育价值和意义。
当然,文化研究对非教育经典的关注和重视,决非是对教育经典在教育及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彻底推翻和否定,更不是对所有非教育经典的平反和认可,也绝不是对历史上所有的教育著作进行重新的认定。文化研究的目的是要为教育研究提供一种比较客观、理性的视角和态度,人类教育是一个庞大的教育文化系统,教育经典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它不可能代表人类教育及教育史这一庞大教育文化系统的全貌,因而要对人类教育及教育史这一教育文化系统进行全面观照,非教育经典著作就应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占有一定的位置和分量。这有助于消除普通读者和学习者对所谓教育经典的盲目推崇和迷信,也会消除他们对教育经典的偏颇理解的误区,重新构建他们评说教育经典的话语权。
二、文化研究对教育经典的确立过程表示质疑
美国课程论专家泰勒所著《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被人们美誉为课程与教学研究的“圣经”,在西方课程理论发展的历程中,“泰勒原理”的诞生是现代课程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甚至到今天有论者认为,“泰勒原理”就是了解课程研究的最基础的课程理论,是当之无愧的“敲门砖”,是中小学教师学习课程知识、进而登堂入室的必由之路。[7](P2)为什么得到如此高的评价?事实确实如此吗?我们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予以分析。
一般说来,教育经典是在中外浩如烟海的教育著作中经过大浪淘沙而洗练出来的精品,是中外教育历史长河中公认的具有深度的、有影响的优秀理论著作和作品。尽管如此,在文化研究看来,教育经典的确立和认可过程是由代表特定国家、民族和群体的少数学术权威和教育家独断完成的,普通读者和学习者缺少确立和认可的话语权,很难参与其中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导致教育经典确立过程和程序的不科学性。虽然这些少数学术权威和教育专家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学术积累,对某些教育经典的确定和评价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教育经典的如此确立过程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价值性和时代性特点,缺乏客观性、中立性和永恒性。
主观性是与客观性相对的,具体指教育专家们以自己的价值取向、个人的主观偏好确立和评价教育经典的过程。教育经典的确立过程不是客观中立、价值无涉的过程,而是以一定的标准进行价值介入的过程,它把教育经典置于被扩展了的话语、文化、意识形态、种族、性别等诸领域。他们对某些经典与非经典的归纳常常招致非议。由此导致什么是教育经典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究竟哪些著作真正属于教育经典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标准。譬如,不同的学者对什么是经典和名著的看法各有不同。大英百科全书董事会主席提出了衡量“名著”的六条标准:一是名著是经久不衰的畅销书,而非畅销于一时;二是面向大众,通俗易懂,而不是为少数专业人士写的书;三是名著不因时代变迁和政治、思想、原则的变更而失去价值;四是名著言近旨远,隽永深刻,一页书的内容多于成本的其他著作;五是名著有独到的见解,能言前人之所未言,言他人之所不敢言;六是名著探讨了人类长期困惑、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在某一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8](P前言)有论者认为,一本可以称为名著的教育哲学著作至少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它的思想具有原创性;第二,它应该有着完整的、新的哲学基础;第三,它应该对一定范围内的教育实践产生深刻的和长远的影响。[9](P53~54)可见,连对何谓是教育经典的看法和观点也不一致,还谈哪些是教育经典的著作呢?
价值性是指教育经典都是受价值引导的,而且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要求,它反映出主体和社会的价值趣味与文化偏好。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指出:“一个社会如何选择、分配、传递和评价它所认为的具有公共性的知识,与这个社会的权力分配和社会控制有关联。”[10](P61)教育经典对文化的选择具有鲜明的社会控制意图。事实上,对泰勒“目标模式”,我们只是认为它是科学的、严格设计与评价的,我们却不了解“目标模式”的真正的价值内涵。“目标模式”的课程研究认为,课程的编制和设计不是价值问题而是技术问题,[11]他们自称不讨论谁应该选择目标,更不讨论选择哪一种目标。也就是只关心目标的操作性,而不管目标的价值性。而事实上,教育和课程是由有价值的活动构成的,包含着价值的选择,而必须牵涉课程中目标、内容和活动的价值。就“目标模式”来说,课程内容和知识的选择是为达成目标服务的,而事实上对目标的分析和确定都是依据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非凭空做出的。学校通过课程、目标以及评价实现社会人员的选拔和流动,并且牵涉到利益和阶层,因此,“社会中的价值判断影响着课程、教材内容的选择,课程知识与权力、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学校课程知识受到社会的价值取向、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并在权力、利益的分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课程的选择与评价就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目标模式'预先设立特定的学习目标,暗含着成人社会的价值、思想和意识形态。‘目标模式'的设计和评价正是扮演了社会控制的角色,表面上看只追求技术和价值中立,但实际上包含着社会价值意识形态社会习惯的灌输”。[12](P148~149)
时代性是指教育经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不同的价值标准和社会、政治要求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甚至人们对教育经典的价值和作用的认识、理解和认定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时代性是与经典性相对存在的一个概念,所有的经典都曾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性特点,这表明在某一时期的教育经典在另一时期未必是经典,甚至出现被打入另册的现象。
文化研究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人文学者对所谓的经典作品研究的不满。高高在上的象牙塔式的精英作品研究越来越成为少数人把玩的古董,与社会严重脱离。文化研究关心的不是文本的内容,而是文本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生产出来。教育经典的确立过程,实际上就是回答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来,泰勒所著《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得到如比高的评价,也是这一学科的西方—欧洲中心论的产物,实际上没有这么悬乎。甚至可以说,泰勒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也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继承了杜威、桑代克、贾德和波特等人的学说以及现代课程理论先驱博比特和查特斯的理论研究成果的有用部分,另一方面,也和现实的课程实践有关联,是课程实践的产物,具体表现在“八年研究”。所以,泰勒的这本书有它的理论和实践的时代背景。甚至泰勒本人也说:“这两条原理都是作为特定环境条件下的产物而形成的。”[12](P152)因此,该书带有当时时代的印记。既然有时代性就免不了时代的局限性。针对教育经典确立和评价过程的时代性特点,文化研究向教育经典发难,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揭露教育经典确立过程中被掩盖、歪曲和遮蔽的本来面目和真相的时代局限,也就是说,“文化研究的批判性眼光要揭露的是经典确立过程中被歪曲或遮蔽了的真相”。[13]这个本来面目和真相就是,教育经典既有可能是所有教育著作中的优秀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教育真实的情况,也有可能是某个时代某个教育家的一己之见、一家之言,更有可能带有某个阶级、民族和群体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文化倾向和价值偏好的特殊目的。
当然,文化研究并不因为教育经典的主观性、价值性和时代性而否定教育经典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它反对的是教育经典所谓的客观性、中立性、永恒性以及它的强制性。
三、文化研究对教育经典的精英文化基础表示质疑
美国课程论专家泰勒所著《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在西方课程理论谱系中,“泰勒原理”既是现代课程理论的基石,又是学校课程实践的最得力的指导手册。在世界当代课程研究领域,“泰勒原理”是课程理论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的理论话题。[7](P2)为什么获此殊荣,原因有很多种,但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它诞生于西方,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承载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精英文化。
一般地说,教育经典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选择的是最有价值的文化,要选择人类文化中的精华。经典研究所重视的教育经典,就是属于人类的精英文化,精英文化是由一个社会的知识阶层所创造、传播、分享的文化。[14](P77)教育经典所选择的文化,总要反映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或主流文化。翻开中外教育史,可以说,它是一部精英文化教育史。精英文化在教育经典中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并成为一种教育范式。所以,经典研究对教育经典的重视,就是对精英文化的重视。古今中外的教育经典始终不改精英文化的本色。在文化研究看来,所谓的经典在本质上是精英主义的,是对非经典的、亚文化和边缘文化的排斥。这样实际上构成了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的霸权、压迫及不平等。教育经典的选择从来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与政治、经济等其他人类活动有着纠缠难解的关系。可以说,在教育经典的选择上存在着利益争夺的问题,它主要是被精英文化和主导文化携手垄断的。
一般而言,文化研究并非指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指当代非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研究。它是一种具有非边缘化、解地域化和消解中心等特征的学术话语和理论思潮。譬如,它非常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弱势群体和亚文化,关注文化中蕴涵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保持与社会密切的互动关系。[1](P47~48)具体到教育领域,它关注边缘性的研究领域,如妇女和少数族裔的教育等。文化研究以全新的视角和路径,向精英文化提出了挑战,认为代表精英文化的教育经典忽视了社会文化的异质性和多样性。
首先,文化研究拓宽教育研究的视野,将具有教育特征和内涵的社会多元文化现象纳入教育研究的范畴,动摇了教育经典的精英文化基础,消解了精英文化的主导地位,以前居于亚文化、边缘文化之列的女性教育、殖民地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及其著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教育经典的精英文化基础,会导致现有的亚文化、边缘文化为低一等、次一级的文化。其中,女性教育、殖民地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及多元文化教育在教育及教育史上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很难与男性教育、殖民宗主国教育、主体民族和主流文化的教育相匹敌。如对《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这本书的顶礼膜拜和无限推崇,就明显地表现出重欧美教育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这实际上就是在世界教育史、课程论史上人为地建构起了中心和边缘、西方和东方的二元对立。在文化研究看来,人为地把文化财富缩小为精英文化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它实际上是把未来的一代代人与文化财富中心的庞大的部分切断了,我们再没有机会去发现它们的教育价值了。在文化研究视野下,长期未受重视的女性教育、课程得到重新评价,消解了教育研究中的男权主义。这种状况、这种地位,是女性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另外,文化研究消解了中心和边缘、西方和东方的二元对立,特别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为这种消解提供了理论支持。文化研究宣告:“在各民族文化之间不存在优劣,只存在交流和互补,更没有一种文化永远处于先进地位。”[15](P429)不同文化背景的课程与教学论并无“经典”和“非经典”、“先进”和“落后”、“科学”和“非科学”、“现代”和“原始”之分,有的只是在文化的限域内课程理论与它为之服务的课程实践之间的适应性问题。在文化研究的影响、倡导和推动下,处于边缘的亚文化地位的殖民地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和女性教育正逐渐从依附的、从属的地位中解脱出来,成为与宗主国教育、主流文化教育和男性教育共生与对话的教育文化样类,正在逐步消解着自身的亚文化、边缘文化身份和地位,向主流文化、中心文化方向发展。
其次,文化研究拓展教育研究的理论资源,从而实现教育研究的转变,对以精英文化压制大众文化的观点进行了猛烈批判,冲击了教育经典推崇的精英文化价值体系,开拓了现代教育文化民主的空间,以前属于边缘文化、亚文化的大众文化成为教育研究的文化基础,并获得应有的地位。如果把精英文化作为教育经典的唯一基础,并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取向加以强调和突出,那就会产生排斥其他文化进入教育系统,从而使得这些文化失去传播和保留价值,会导致以俯视的态度对待大众文化。与传统教育经典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在文化研究看来,教育研究应注重大众文化,研究教育经典著作的大众文化基础,教育经典应包括被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和主流文化排除在外的教育著作和作者。在此影响下,以前不受重视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被逐步引入到学校开设的课程中来,还有如民间教育、乡土教育、民俗教育等,也越来越受到教育研究者的青睐。在文化研究的视野里自然就没有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低俗与高雅之分,它不会立足于精英文化的立场格外垂青于高雅文化,也不会对大众文化持居高临下的贬损态度。从这一点上说,文化研究就是使教育研究拉近与大众文化教育的距离,放下研究教育经典高高在上的架子,体现教育研究对大众文化教育的学术关怀。
总之,文化研究对教育经典研究提出了诸多质疑,但这些质疑不是否定教育经典的存在价值以及文化研究和教育经典研究之间的对话和互动的关系。同时,教育经典和非经典二者之间应该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应充分认识和肯定二者各自的价值,特别是非教育经典应有的教育价值和意义。文化研究拓展了二者的视野和领域,广大教师和教育研究者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1]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拉尔夫·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M].施良方,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3]张人杰,等.20世纪教育学名家名著[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陈月茹.中小学教科书改革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5]陶东风.“大话文化”与文学经典的命运[J].中州学刊,2005,(7).
[6]张红兵.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冲击[J].思想战线,2003,(9).
[7]杨明全.泰勒[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8]刘新科等.中外教育名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麦克·F.D.杨.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M].谢维和,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1]胡东方.课程政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1.
[12]金生鈜.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
[13]周宪.文化研究:学科抑或策略?[J].文艺研究,2002,(4).
[14]安桂清等.时尚文化·课程开发[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15]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李官〕
The Questioning of Cultural Studies on Educational Classics
JIN Zhi-yuan
(Education Science College,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Hohhot,010022,Inner Mongolia,China)
The eternal value,authoritativeness and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educational classic have always been beyond the doubt of people.Few have questioned its eternal value and authority in the existing studies.In the view of cultural studies,however,its divine status,subjectivity of the establishing process,value,times and the elite cultural foundation can be queried despite its historical and educational value.For they may involve such lim itations as artificial exaggeration,illusion,subjective preference,value interference,times limit,and cultural parochialism.A case in point is Taylor's book“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cultural studies;educational classics;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G05
A
1006-723X(2016)06-0142-05
国家哲社项目(14XMZ107)
金志远(1965—),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