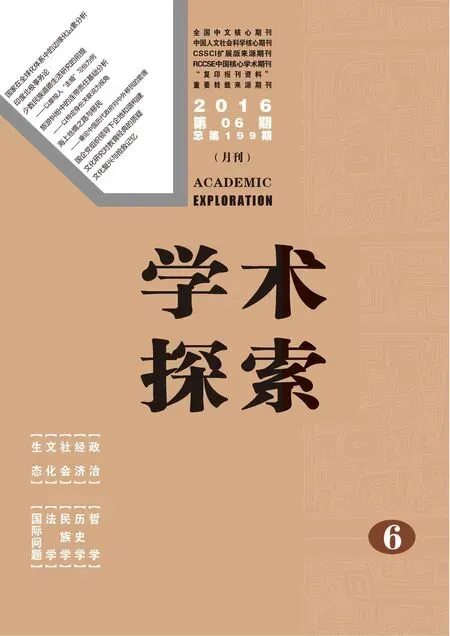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研究的前提
——以摩梭人“走婚”习俗为例
李 兵
(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研究的前提
——以摩梭人“走婚”习俗为例
李兵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开展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研究,必须澄清一些前提性问题:为什么要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道德生活,其内涵究竟如何?应当怎样开展此类研究?抽象地议论,容易流于空泛,结合实例更能体现这种思考的真实意义和价值。以摩梭人“走婚”习俗为个案,展现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研究的意义,揭示其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内涵及其实际功能,讨论此类研究在方法论上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利于提升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研究的学术水准和实践价值。
少数民族道德生活;“走婚”;前提思考
为什么要从哲学的视域研究少数民族的道德生活?换言之,研究的意义何在?什么是少数民族的道德生活,其内涵究竟如何?应当怎样研究这种道德生活,也就是如何对其道德生活做出既符合其生活的本来面目,又具有某种现实价值的理解和诠释?澄清这些问题——当然不止这些问题,但至少需要首先弄清这些问题——是今天开展类似课题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如果没有进行这样的前提思考,那么,研究就可能是盲目的,除了制造一些看似热闹的学术幻象外,对相关理论发展和现实生活都少有裨益,甚至还会造成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误读和对他们自身文化自觉的误导,以及在应对现实生活挑战时的错觉和迷惘。本文拟结合对摩梭人“走婚”习俗的道德解读,谈谈我对开展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
不妨从我个人对摩梭人“走婚”现象的认识过程说起。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在川滇交界的泸沽湖畔,住着一个被分别识别为纳西族和蒙古族的同一个族群——摩梭人。由于在这里的大部分摩梭人,还保留着一种“男不婚女不嫁”,男女双方过着暮合晨离的“走婚”生活,以及与这种婚姻形式相适应的“母系大家庭”结构,而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好奇和关注,特别是随着被誉为“摩梭女杰”的杨二车娜姆的《走出女儿国》等作品的问世,更是激起了各方人士对这片神秘土地的无限遐思和想象。带着不同的主观意象褒扬者有之,从不同的思想背景出发贬抑者也不乏其人。我几十年前初接触到这种婚俗,也是感到非常的惊异,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将其视为母系氏族社会婚姻形态的遗迹观念。但随着了解的增多,一个深深的疑问开始萦绕在自己的脑海,那就是,母系氏族社会作为原始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从考古发现中显示,距今早则四五万年,晚则六七千年,为什么可能保留至今?即便“女儿国”的生产力水平再低下,生产方式再落后,也不至于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停滞不前、原封不动。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或原因,导致那里的人们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执着,坚守着被同时代的其他人们视为原始、野蛮的婚姻习俗和家庭结构?据说,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一个“世界级的未解之谜”。
伴随疑问产生的同时,我开始关注这种婚姻习俗和家庭结构的内涵,在现代主流婚姻家庭模式的参照下,无须更多的思考便会发现,摩梭人的“走婚”习俗的确有着其他婚姻形式无可比拟的优点:在两性关系上,它超越了一切非情感的因素,诸如一夫一妻制形成以来人们摆脱不了的经济、政治、文化、信仰、门第等因素的影响;在家庭关系上,避免了父系大家庭永远解决不了的,诸如翁婿、婆媳、姑嫂、妯娌等错综复杂的家庭矛盾,以及核心家庭以“契约”为纽带的夫妻关系的脆弱性和家庭抗风险能力的微弱性。近期,民政部发布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称,2014年全国共依法办理离婚登记363.7万对。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已连续12年呈递增状态。北京市离婚登记办理数量也连续12年递增,2014年以5万5千余对“领跑”全国各大城市。80后成为离婚队伍的“主力”。有的离婚甚至仅仅是将其当作“合理避税”的便捷途径。可见,较之摩梭人的婚姻家庭关系,“文明社会”人们的婚姻家庭关系是多么的脆弱和“庸俗”。如此看来,摩梭人的“走婚”习俗及其家庭结构,不仅不是落后的、原始的,而且,若以“爱情”作为考量两性关系的最高标准和以和谐作为评价家庭关系的终极尺度,那么,摩梭人的婚俗和家庭关系或许还代表了人类两性关系和家庭结构的未来发展趋势。于是,我看到不少人开始为这种婚姻习俗和家庭结构大唱赞歌,将家庭道德的许多美好的词汇,诸如“两情相悦”“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家庭和睦”“尊老爱幼”等,贴在了摩梭人的走婚习俗和家庭关系上。果真如此吗?这种婚姻习俗和家庭结构在其他人群中有借鉴和效仿价值吗?为什么这样好的婚姻家庭模式即便在当地也不是呈增长的势头,而是出现衰落的趋势?
带着这些问题,我进一步搜集了近年来研究摩梭人婚姻习俗和家庭结构的资料,并重新阅读了此类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走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摩梭人的婚姻家庭结构,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现象,在本质上它是合乎人类家庭演进规律的一个特例,亦即人类曾经普遍存在的婚姻家庭结构在当代社会的遗存,正像必然性总是寓于偶然性,普遍性总是根植于个别性一样,在无限多样的人类生活样态中,在一个数十年前还几乎与世隔绝的偏僻之地,保留这样一种与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相适应的婚姻家庭形式,并不断在其文化(特别是婚姻家庭观念)的强化下得到巩固,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不能理解反而是不可理喻的,因为任何理论的建构,都是以其不能涵摄大量的“例外”存在为条件的。理论的价值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它并不承诺对一切现象负责。
在经过这番心路历程之后,问题终于凸显了出来。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少数民族的道德生活?研究的意义究竟何在?毫无疑问,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绝不仅仅只是为了猎奇,也不只是为了向人们呈现一种“别样”的生活样式,而是为了在深度理解某种道德生活的基础上,开掘其中蕴含的思想启示和实践价值。那么,这些启示和价值到底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实现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我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由于不同民族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不同,历史演进各异,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因为某种历史机缘,民族文化发展水平比较高,形成了自己民族自成一体的文化系统,因而,具有较强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如彝族、藏族、白族、蒙古族等;有的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形成自己民族(族群)的理论形态的民族文化,文化更多的是以直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呈现出来。相对于已经达成某种理论自觉的文化来说,这种文化比较弱势和无力,很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侵蚀,以至于秉承这种文化的“人们共同体”,由于缺乏对自己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在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和外来文化的内外冲击下,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文化,从而导致民族特性的淡漠与丧失。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成其为一个民族的内在根据。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1](P37)可见,它对于一个民族实现自我认同是必不可少的。婚姻家庭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是最重要的社会制度。诚如恩格斯指出:“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呼,并不是单纯的荣誉称号,而是代表着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2](P37)因此,婚姻家庭生活及其所形成的道德观念,就成为这些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开展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研究,有利于少数民族实现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进而了解自己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自身特色和演变趋势,使他们的道德生活由自发变为自觉。
其次,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中华民族文化是56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同创造的,犹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华民族正是在“分分合合”的历程中,“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1](P268)当前,我国正面临树立文化自觉、培养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不仅是文化界的任务,也是全社会的任务。少数民族道德生活,是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它们或多或少带有某些传统社会和过去时代的特征,但唯其因为它们受到西方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相对较小,更能在本真的意义上显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精神特质。开展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研究,无疑可以从一些独特的维度或层面帮助国人实现对自己文化来龙去脉的理解,从中发现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质和发展轨迹,让一些曾经被忽略或边缘化的文化鲜明地凸显出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提供更加丰富的道德文化资源。
再次,实现我国各民族文化的“各美其美”与“美人之美”。文化的互渗与融合是一个民族(国族)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中国由于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在这个“地理单元”中生活着个性鲜明、差异显著的56个民族。各民族在文化上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开展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研究,深入解读和阐释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道德文化,开掘其中仍然具有时代性和人类性价值的思想内涵,在增强各民族文化自觉自信的同时,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理解,对于构建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当代中华民族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二
如何理解少数民族的道德生活,它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这也是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研究必须澄清的问题。让我们再回到摩梭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中。
大致而言,摩梭人的“走婚”可以分为三种形式,即“暗访”“明访”和“共居”,前两种为“走婚”的主要形式,后一种情况相对较少。与这种走婚习俗相适应,形成了摩梭人特有的婚姻家庭道德。如果我们撇开孕育这种婚姻家庭道德的社会经济基础和自然、历史原因不谈,单就这种道德生活直接的表现形式来说,的确具有许多当代人类普遍认同的道德价值。如,两性交往主要取决于“两情相悦”、男女在交往关系中地位平等、分合自由不受情感之外的因素限制、两性关系没有独占和欺骗;建立在母系大家庭基础上的家庭关系十分和睦、尊老爱幼、相敬如宾,家庭成员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因此,在这些地方见不到鳏、寡、孤、独、离婚、财产分割等现象;由于每一个孩子都是在这样的家庭(社会)环境中成长,从小被和谐的家庭氛围和人际关系所熏陶,养成了摩梭人敦厚善良、温和友好、循规蹈矩的民族性格,以至于10多年前有媒体报道,泸沽湖上下的自然村,从新中国成立到如今,只有1个人被劳动教养过3年,在这50年里,全行政村近千人中,犯轻罪的只有1人,没有犯重罪的。除了在两性关系的乱伦禁忌上,由于只是注重对母系血缘的限制,而对父系血缘两性交往缺乏严密的约束,是一个重大缺憾外,几乎就是一幅当代婚姻家庭“世外桃源”的景象。
然而,从哲学的视域,应当如何看待这些道德现象呢?是不是像有的研究者那样,以当代主流社会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关系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弊端为参照,而无限拔高这种婚姻家庭结构的伦理合理性,甚至将其标榜为某种道德典范和人类两性关系的未来趋势,希望其他人去学习和效仿;或者像另外一些研究者一样,将其贴上母系氏族社会“活化石”的标签,而无视其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和重要的文化价值。我以为,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可取的。它们共同的失误在于,没有把这种道德现象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加以认识,都存在把复杂的人类道德生活现象简单化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倾向,也是此类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针对第一种倾向,我认为,首先,必须看到,摩梭人的婚姻家庭结构,确实具有母系氏族家庭的主要特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道,“她们全体有一个共同的女始祖;由于世系出自同一个女始祖,后代的所有女性每一代都是姊妹。……一切兄弟和姊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的性关系的禁规一经确立,上述的集团便转化为氏族了,换言之,即组成一个确定的、彼此不能结婚的女系血缘亲属集团;从这时起,这种集团就由于其他共同的社会的和宗教的设施而日益巩固起来。”[2](P50)他还认为,“在氏族制度可得到证实的一切民族中,即差不多在一切野蛮人和一切文明民族中,几乎毫无疑问地都曾经存在过这种家庭形式。”[2](P50~51)摩梭人的婚姻家庭结构在本质上与上述论述是高度一致的。正像这种婚姻家庭结构也曾在世界许多地方延续到至少19世纪中后叶一样,作为人类曾经普遍存在的家庭形式,在其消亡的条件尚不具备的时候继续存在,尤其是它一经形成之后,还要受到基于这种家庭形式的社会和宗教设施的巩固。因此,在一个东方大国的某一特殊地域,还保留着这样的婚俗,是完全可能的,并不是什么难解之谜。
其次,它一定是这一“人们共同体”根据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婚姻家庭形式上所做出的最合理的选择。人们无论选择哪种婚姻家庭形式,本质上都与他们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有关。在这里,恩格斯的经典论断,依然是我们理解各种历史现象,包括摩梭人“走婚”这一所谓“世界级之谜”的不二锁钥。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族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的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越少,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2](P13)这是对这种婚姻家庭形式何等合理清晰的解释!或许因为我们曾经教条主义地套用这些思想,并不加区别地付诸现实的政治操作,导致了许多严重的政治和政策错误(在对待摩梭人婚姻习俗上就是如此),从而极大损害了这些重要思想的理论威信。但这不是理论本身的错误,因而,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让本来已经得到合理解释的问题重新变得混沌和模糊。
再次,我们在充分肯定摩梭人的婚姻家庭道德之于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合理性的同时,切忌不要超时空地发表一些毫无根据和意义的空泛议论,更不要夸大这些道德观念和规范的适用范围。事实上,无论就摩梭人本身来说,还是就“走婚”对于其他人群的影响来讲,其值得珍视的程度远不及人们附加在其之上的想象。当年青一代摩梭人“走出女儿国”,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之后,往往会主动放弃“走婚”习俗,而更愿意选择主流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形式。这说明体现在这种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道德,只有在纯粹或者严格的摩梭母系社会中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功能,彰显其美好。一旦脱离了那种“社会制度”和环境,这些道德的生命力将会完全丧失,或者变形为与一夫一妻制相伴而生的名曰“走婚”的嫖娼与卖淫。随着旅游业的开发,在泸沽湖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伤风败俗的现象。
最后,还有人将这种婚姻形式看成是人类两性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甚至还引用国外的一些调查资料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离婚率不断增高,许多人愿意选择不受约束的两性关系,一些女性因为可以得到社会保障的支持,不在乎做单亲家庭母亲,自己抚养孩子,无须男性的帮助。由此得出,摩梭人的“走婚”实际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这无疑是极为荒唐的。西方的高离婚率和大量的单亲家庭,是现代财产关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与摩梭人“走婚”没有任何联系;而至于说到未来的两性关系,即恩格斯所说的“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必须是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创造的财产关系后才可能出现。摩梭人选择“走婚”与其说与他们的财产关系无关,毋宁说就是他们财产关系的产物,只是经济的考量隐藏在了其基本的“社会制度”中。
对于第二种倾向,我以为是一种轻率和无知的表现。首先,一种古老的婚姻家庭形式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极高的人类学和文化学价值,在高速现代化的当代中国,甚至可以视为稀世文化珍宝。它既是人类了解自己过去、理解自己文化、认知人性生成的重要途径,又是人类探索未来走向、预测文化前景、把握自身命运的重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高度重视人类学研究的成果,马克思曾留下包括《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在内的一系列人类学、历史学笔记,并试图在摩尔根等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重新阐发业已成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恩格斯撰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是为了“补偿我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并在马克思写在摩尔根一书的详细摘要和批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对摩尔根等重要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性阐释,以“实证”的方式检验和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他本人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列宁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介,认为该书“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6](P677)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如何从哲学的视域看待和研究历史文化现象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确立了直到今天为止无人可以超越的研究人类发展史的思想原则和方法。循着他们的理路,我们可以从包括少数民族道德生活在内的文化现象中,获得更多具有更高价值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其进行简单的描述和轻率的价值判断上。
其次,尽管像摩梭人“走婚”这样的婚姻家庭道德生活,没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但不妨碍它能对当代人类生活形成了富有启迪和参考价值的参照。“在当代,功利主义的价值体系、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使人总是要借助某种‘中介'才能与世界联结、照面,而‘中介'后的世界已不再是人们真实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它往往表现为可以计量的‘价值'(商品、货币、资本)、被定义了的概念和仿佛游离于世界之外的‘原子式'的个人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关注一下依然具有某种异质性特征,带有更多原生态痕迹的少数民族文化,无疑会使我们在浮躁中感受一种沉稳,在喧嚣中获得一份宁静,在狂乱中领悟生命的孱弱,在荒诞中觉解人生的真谛。”[3]少数民族道德文化,包括这里作为案例的摩梭人婚姻家庭道德,正如前文所论,它所能给予当代人类的当然不是摆脱“现代性”困境的现成答案,也不可能成为这些族群以外的人们可以直接效仿的生活样态,但是,它们对于今天人们的思想启迪和参考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告诉我们,今天的生活不过是从过去的生活嬗变而来的,同样,今天的生活也会向着未来的可能性开放,婚姻家庭关系也不例外。诚如摩尔根所说:“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低级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反之,亲属关系制度却是被动的;它只是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马克思接着批注道:“同样……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学的体系,一般也 是 如此。”[2](P37~38)
三
基于上述分析和我个人关于摩梭人“走婚”习俗的认识过程,最后想谈谈我对怎样研究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的看法。在伦理道德研究中,目前出现了一种所谓研究的方法论转向。这里所说的“转向”,就是认为应当将伦理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引入到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研究中。总体上讲,我不反对将其他学科的方法引入到伦理学,包括少数民族伦理问题的研究中,尤其是在把伦理学定位为某种“科学”的情况下。一定意义上讲,少数民族伦理研究因缺少可供哲学“反思”的思想材料,其道德生活更多地表现为直接的生产和生活形式,的确不能缺少了田野调查这个环节,否则容易落入空洞的概念演绎的窠臼。但是,又必须看到,伦理学也好、道德哲学也罢,它终究是一门哲学学科,哲学是思想的事业,它自有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理路,自有其他学科和研究方式不可取代的功能和价值,即便是借鉴和运用诸如“民族志”等方法,也应将哲学的存在论追问、认识论探究、价值论考察等融入实证研究或田野调查之中,否则,哲学注定将在学科林立的当代学术话语体系中扮演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即既无实证研究的细致、深入与具体,又无哲学研究的高度、深刻与普适,既没有耕好别人的田,还荒了自己的地。在我国,且不要说从哲学切入少数民族伦理研究很难真正做到田野调查所要求的“融入”,即便纯粹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也多是蜻蜓点水式的做点问卷调查,极少有像摩尔根那样,整整用40多年的时间追踪研究北美印第安人,最后凝结出《古代社会》这样的划时代作品。我在搜集摩梭人“走婚”资料的时候发现,多数研究者也就是到泸沽湖畔的某个村寨做了一个短期的调查,进行了简单的数据统计和个案访谈。可见,真正的“民族志”方法是很难做到的,况且它还不是哲学研究的正道。我作为一个客串研究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的热心者,自然提不出什么具体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在此,不揣冒昧提两点建议,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首先,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黑格尔认为,“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4](P43)哲学研究决不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也不是对事物做出某种似是而非的判断,或是“盲人摸象”般的片面议论,总之,它不能停留于事物的“表象”,而是要达到对事物的概念把握,也就是他所说的“自觉的理性”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从事哲学研究必须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做到像孙正聿教授所说的那样,“一是必须‘寻找理论资源',‘通晓理论思维的历史和成就',以概念作为专业性研究的‘阶梯'和‘支撑点';二是必须把握本学科关于对象世界的规定性以及本学科已有的对‘全部生活'的理解。”也许,有人会认为,概念或理论不仅不是认识事物的“阶梯”和“支撑点”,而且还可能成为遮蔽事物的观念障碍。这是对人的认识缺乏反思的表现。“人们对文本的阅读和对现实的观察,必须并且只能以已有的概念、范畴、知识和理论构成基本的主观条件。用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说法就是:观察渗透理论,观察负载理论,没有中性的观察,观察总是被理论‘污染'的。借用黑格尔的说法就是:没有概念把握的对象,对象只能是‘有之非有'、‘存在着的无'——对象存在着,但对认识的主体来说并不存在。”[5]总之,没有必要的理论准备,不占有与研究对象大致相匹配的概念工具,即便事物或现象就在你的面前,除了得到一些感官接触到的“杂多”和“表象”,事物对你根本就不存在。实际的情形是,我们的许多研究者,不是不使用现成的概念,而是不加反思地将现成的概念套在其观察对象之上。由于理论准备不足,特别是没有“通晓理论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概念缺乏有机性、历史性和系统性,致使对现象的描述或解释,总是流于肤浅和随意,尤其是未达到“自觉的理性”与“事物中的理性”的统一。
其次,要保持一定的间距。这个观点可能容易引起反感。我们不是一贯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对事物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吗?不错!问题是我们是在什么层面上研究事物,是以什么学科为背景研究事物。如果是从以反思为基本特征的哲学的视域研究事物,就应当有这样的反思自觉,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不以某种概念为中介,我们很难获得对事物的真正把握和理解,同样,如果不以某种已经“构成思想”的关于“对象世界的规定性”为研究对象,就很难谈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大家知道并不是建立在某种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但并不妨碍他在对人类历史的理解上,做出了不低于摩尔根实证研究的贡献,相反,摩尔根的研究不过是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关于早期人类生活的例证。马克思在总结其《资本论》研究方法时说道:“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的”。[6](P92)这可以理解为时间上的“间距”,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须用还原论的思维去追溯事物的始源状态,当下存在的形态才是哲学研究的最佳对象。当代解释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揭示了时间“间距”不仅不是理解事物的障碍,而且还是理解事物的条件。因此,从哲学上研究少数民族道德生活,无须去猎奇般地发现某些与现实具有巨大反差的道德现象,而是应当认认真真地解读少数民族“实际生活过程”这部打开了的“心理学”大书。此外,还要注意空间“间距”,没有与各种事物的必要的“间距”,就没有真正的哲学。如果说科学研究要尽可能贴近事物的话,那么哲学研究恰恰要自觉地与事物保持一定距离,这是哲学反思的基础和条件。“正是由于这种‘间距',哲学才能使人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才能全面地反映现实,深层地透视现实,理性地解释现实,理想地引导现实,理智地反观现实,才能实现‘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7](P226)
[1]费孝通论文化自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李兵.作为生存意识和超越意识的少数民族文化[J].学术探索,2012,(12).
[4]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孙正聿.做学问[J].哲学动态,2009,(8).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孙正聿.简明哲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左安嵩〕
The Prem ise of Research on the M oral Life of M inority Nationalities—Taking the“Walking M arriage”Custom of the Mosuo People'as an Exam ple
LIBing
(School of Marxism,Yunnan University,Kunming,650091,Yunnan,China)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themoral lif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wemust clarify such premises as“why should we study?”,“What is the connotation ofmoral life?”,and“How should we carry out such research?”.Case-based study instead of abstract talk,can better reflect the truemeaning and value of this kind of thinking.By examining the“walkingmarriage”custom of the Mosuo people,this paper explores themeaning of research on themoral life ofminorities,the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function ofmoral concepts and norms,aswell as issues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methodology of such studies.This paper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cademic level and practical value of ethnicmoral life research.
minoritymoral life;“walkingmarriage”;thinking of the premise
C955
A
1006-723X(2016)06-0036-06
李兵(1963—),男,重庆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基础理论、政治哲学、民族文化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