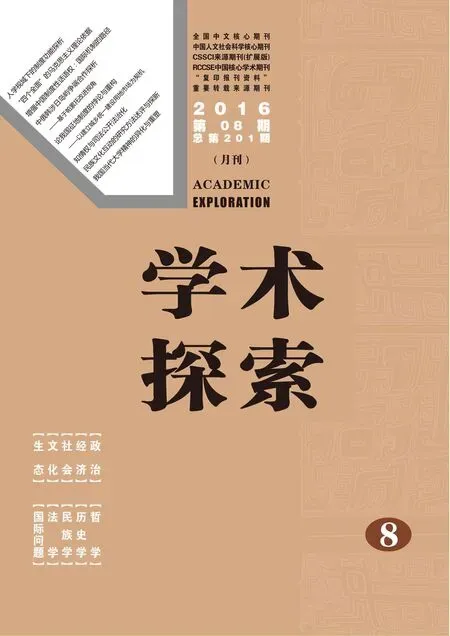另一种写实传统:论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对中国画的影响
刘连杰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另一种写实传统:论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对中国画的影响
刘连杰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由于巫术思维的影响,远古绘画并不取悦感官,追求视觉真实,而是追求与事物本身的同一性,注重对事物构成要件的完整性呈现。它决不会同意为了视觉需要而对事物进行它们本身所没有的透视变形,更不会因为视觉前后遮挡的局限而破坏事物本身的完整性,这是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的基本内涵。这种写实观不只是存在于早已消逝的远古时代,它对中国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中国绘画史上形成了一个鲜活的传统。认真梳理这一传统,可以破除近代以来对视觉写实的迷信,澄清历史的真相,恢复绘画写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为绘画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思考方向。
巫术思维;写实观;中国画;影响
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是绘画写实观的一个基本类型,它不仅仅存在于遥远的早已消逝的远古时代,而且也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绘画观念,并在绘画史上形成了一个鲜活的传统。认真梳理这一传统,可以破除近代以来对视觉写实的迷信,澄清历史的真相,恢复绘画写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为绘画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思考方向。
一、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的内涵
人类最为古老的绘画并不是为视觉服务的,它们或者画于隐蔽幽深的洞穴之中,或者画于不打算重见天日的墓穴之内,其动机都不在于取悦感官,而是试图通过巫术作用直指事物本身。在原始人类看来,绘画不是为那些观看它们的人而存在的,而是为画中事物本身而存在的。他们几乎分不清楚事物和事物的图像之间的区别,或者说无意做出这样的区分,事物的图像直接就被等同于事物本身,对图像的操作可以等同于对事物的操作,用长矛和石块攻击壁画上的动物可以有助于实际的狩猎,对人的图像进行破坏就会给这个人带来厄运。这是原始巫术思维在绘画中的体现。如果回到“写实”一词的本义,抛开视觉迷信,从力求与事物同一的意志来看,我想没有绘画能够比远古绘画更加写实了。首先,远古绘画的目的在于实现对事物的操纵,描绘事物就是呈现事物本身,使事物在绘画中直接到场,而不是表达个人的观点,也不是表达群体的观点,至少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如此。因此,它比今天已属于人文学科并被“趣味”弥漫的任何绘画都要更少主观性。其次,远古绘画与事物的关系更为直接,它无意取悦观者并使观者从中获得满足,而是试图以某种方式直接介入事物本身,当某幅作品被完成时,它总要对事物发生一些实际的作用。这尽管神秘,但远古人类却相信它是绘画的真实功能。
人们往往会认为,远古绘画比较朴拙,还处于绘画的不成熟状态,并将之类比于儿童画。但实际上,远古绘画从目前已发现最早的“绘画图案”算起,到原始社会解体,经历了十几万年的传承与发展,凝结了一代又一代远古艺术家的智慧与技艺,这是儿童画所难以企及的。如果我们愿意看一看距今15000年的法国拉斯科洞穴壁画中的约百种动物画像,其简洁流畅的线条,丰富细致的颜色,准确的比例,传神的动作,栩栩如生的神态,绝不亚于今天的绘画技巧。正如贡布里希所言:“与我们不同之处不是他们的技艺水平,而是他们的思想观念。”[1](P21)那么,他们的思想观念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呢?这就是巫术思维。根据弗雷泽的研究,巫术思维的第一原则是“相似律”,即“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个东西”。[2](P26)就绘画而言,就是把事物的图像和事物本身看成同一个东西,用对事物的图像的操纵代替对事物本身的操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事物的图像必须与事物本身具有同样的构成部分,他们要击打动物的头部,动物的图像必须画出头部,要击打动物的腿部,动物的图像必须画出腿部,为了对事物进行全面的巫术操纵,事物的图像必须在构成要件上与事物本身一一对应。远古人类不是把视觉作为绘画的基础,而是把他们对于事物的知识作为绘画的基础。因此,贡布里希在考察古埃及绘画时指出:“当时最关紧要的不是好看不好看,而是完整不完整。艺术家的任务是要尽可能清楚、尽可能持久地把一切事物都保留下来,所以他们并不打算把自然描绘成从偶然碰上的角度看到的样子。”[1](P30)
完整性是远古绘画的创作法则,这已被大量的远古绘画作品所证明,并在不同的对象那里形成了不同的创作模式。首先,在对单个事物的处理上,它绝不会同意为了视觉需要而对事物进行它们本身所没有的透视变形,而是从它们最容易看完整的角度去呈现。例如约2700年前古埃及墓穴壁画赫亚尔肖像所示,一只正面的眼睛被放在侧面的脸上(在古埃及人看来,只有从侧面,才能将包括后脑勺在内的头部完整地呈现出来),上半身正面呈现(以便看到胳膊与躯体的接合),而胳膊和下半身则侧面呈现(这样可以看清胳膊和腿的运动),两只脚都表现出从大脚趾向上去的清晰轮廓,像是有两只左脚似的。整个画面看起来极其扭曲,但千万不要以为古埃及人不知道一个人看上去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只是在遵循着某种规则作画,以便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都包括在其中。
更有甚者,为了呈现出事物的完整面貌,有些原始艺术甚至在一幅画中呈现出同一个动物的两个侧面形象。例如博厄斯在《原始艺术》一书中所考察的北美洲北太平洋沿岸的印第安人装饰艺术,他们将动物切成两半,并相互对称地排列在一起,共用一个头部,甚至将头部也切开,平铺在画面上。整个画面就像是事物在几何学中的平面展开图,完全没有立体感,彻底取消了视觉透视。据作者说,“之所以有这些变形和切开的做法,是由于制造者认为必须把动物的所有象征纹样画全的缘故。”[3](P216~217)
其次,在表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时,远古绘画不会因为视觉前后遮挡的局限而破坏事物本身的完整性,因为事物图像的不完整往往意味着巫术功能的不完整。例如我国阴山岩画中的车马图,两匹马背靠背卧在马车的两侧,它们的头、腿和尾巴则分别指向左右两个方向。在古埃及绘画中,被前面的碗所遮挡住的壶的那部分也要画出来,被毯子盖住的人的身体也可以完整地呈现出来。博厄斯指出:“这些绘画绝不能说明作者不会用透视方法去观察和创作,而只能说明作者的兴趣集中于充分表现一切特点。”[3](P68)
再次,当多个事物同处于一个画面,这些事物被呈现的角度并不需要一致,而是各自选择自身的呈现角度,以保证所有的事物都能得到完整地呈现。例如出自底比斯墓室的古埃及壁画《贵族庭院图》,图中画着一个有池塘的花园,它把池塘画成从上面看到的样子,把池塘周围的树画成向不同方向伸展的样子,而把池塘里的鱼画成侧面看到的样子,这样,它们就既不会彼此遮挡,也不会显得不完整,从而让死者能够巫术性地享用这个花园。再如我国云南的沧源岩画,人、牛、猴子、房屋众多,场面宏大,但其中的人皆为正面呈现,而牛和猴子均为侧面呈现,这是因为直立的人从正面看最完整,而身体向后延伸的牛和猴子则从侧面看最完整。
最后,正如博厄斯所说,“一般情况下,作者是希望表现动物全貌的,但在条件不允许时,就表现其主要特征而略去次要部位。”[3](P206)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些主要部位和次要部位的区分标准不是随意的,而是服务于巫术功能,即,那些在巫术活动中需要针对的部位就是主要部位,而在这一巫术活动中暂时不需要针对的部位就是次要部位。它并不依据视觉原则,而是依据人们的知识水平。同样,除了主次,远古绘画中的大小也不是根据视觉透视确定的,而是根据人们对事物意义的知识,例如贡布里希曾指出,“埃及人所画的老板就比他的仆役大,甚至也比他的妻子大。”[1](P31)在远古人类那里,知识显然也是事物的一个组成部分。
总之,远古绘画“是不能用缺乏技术或尚欠成熟的概括能力来加以解释的”,[4](P177)它有着自身严格的创作法则,这一法则与巫术思维紧相联系,要求事物的图像与事物本身在构成要件上一一对应,以便于巫术操纵。美国艺术史论家霍华德·加德纳认为,远古绘画“只要求图式的简单等同——要求创作出能够象代码一样被‘解读’为人、物或景色的各种形式”,[5](P16)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远古绘画不只是用来解读的代码,它更是使事物直接到场的神圣仪式,而能否成功地使事物到场,关键在于事物构成要件的完整性。解读是从观者的角度而言的,标准是模糊的,只要有蛛丝马迹,人们就能认出它是何种事物,而完整性是从事物的角度而言的,在巫术思维看来,它是事物“真实”的存在方式,也是远古绘画巫术写实的基本要求。在中国绘画中,它形成了绘画写实的另一种传统,对中国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对中国人物画的影响
据叶青的考证,中国画从战国晚期就已经开始了视觉写实的探索,并在之后的绘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6](P40)但这并不意味着视觉写实最终能在中国画中大获全胜,直到近代,中国画都没有完全走上纯粹视觉写实的道路。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中国画偏向写意,也不仅是因为中国画缺乏科学的视觉写实技法,最主要是因为在视觉写实之外,中国画依然重视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就人物画而论,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对造型方式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在那些具有神圣性应该严肃对待的人物画中,构图往往采用正面形象,正如明周履靖云:“惟画神佛,欲其威仪庄严尊重矜敬之理,故多用正像,盖取其端严之意故也。”[7](P495)其实,不仅是神佛,中国历代的帝王像,以及其他人的遗像,几乎清一色都是正面像。这与西方不同,为了表现出脸部的生动轮廓,凸显人的精神气质,西方绘画往往喜欢表现人物的侧面。从画面效果而言,正面像往往会显得呆板、没有生气,但中国画却将之用在最需要重视的场合。帝王像也好、遗像也好,都是供后人瞻仰的,本应将自己最具风采的面貌呈现出来,可中国画却偏偏选择了正面像。实际上,帝王像、遗像在中国并不仅仅只是一幅画像,它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表现活人的风采,而是具有一种神圣的仪式性,使人死后能够在画中继续存在。这是一种带有原始巫术性质的思想,因而它的首要追求是完整,特别是脸部的完整,而不是视觉上的生动。这种完整性要求脸部该有的部位都必须得到充分的、清楚的呈现,不能有任何遮挡,因此,当郎世宁在人物面部画上阴影时,自然引起了雍、乾二帝的反感,认为这至少是一种不吉祥的表现。因为阴影只是由光线暂时造成的视觉因素,并非人脸的构成部分,不能以之遮蔽人的本来面目。
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影响中国人物画的另一体现在于,即使是那些表现侧面的画像,也应把重要部位呈现出来,即使这种呈现并不符合视觉形象。受到西方视觉写实观念影响的清代画家丁皋在其《写真秘诀》中写道:“至于五分相是各得其半。吾见向有写半面而只眼画全者,此法差矣。当取五官之半,染拖出来,而后面始得圆,若用全眼,成扁片矣。”[7](P560)五分相即侧面像,理应只画出半只眼,据此,丁皋对传统画法提出了批评。这一批评透露出了中国人物画五分相也多有画全眼者,同时也透露出丁皋对中国人物画中的巫术写实传统并不了解。在巫术写实观看来,眼睛是人脸的重要部位,必须在画面中完整地呈现出来,不能因为视觉的局限就贸然将之遮挡起来。其实,这种侧面全眼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画中,在古埃及绘画中更是普遍存在,古埃及人物画遵循一种叫正面律的造型原则,几乎所有的人物都被画成侧面正眼的形象,据说这是为了让死者的灵魂能够准确地找到属于自己的形象。有学者认为这种呈现方式甚至还影响了西方的立体主义绘画。对于中国和古埃及的这种侧面全眼的构图依据,人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均忽略了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的影响。
与古埃及相似,中国民间至今都还存在着这样的观念,认为遗像是死者灵魂的依附之所。既然遗像并不是为观者而画,而是为死者而画,那么它所要遵循的原则当然就不是观者角度的视觉原则,而必须遵循一种与死者具有同一性的造型原则。这种同一性原则要比视觉原则全面得多,也稳定得多,它不会因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动不居。它有时甚至还要考虑伦理、社会地位、身份、职业等种种因素,例如很多画中的主要人物比其他人物要大得多,甚至有时同一人物的头部也要比身体其它部分大得多,以至于不成比例,这些就不是人体的物理形象了,而是人物的社会形象,正如佛像的脑后有一轮佛光一样。也许我们今天会认为这不是写实,而是加入了人们的想象,但当时的人却没有把它当作想象,而是当作人物本身的构成部分。至少加入这些因素,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想象力,而是为了人物能够更加完整。
此外,《历代名画记·张僧繇》中有关动物画的记载也可以佐证人物画中完整性原则的重要性。其云:“金陵安乐寺四白龙,不点眼睛,每云点睛即飞去。人以为妄诞,固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两龙乘云腾去上天,二龙未点眼者见在。”[8](P162)这虽是南朝时人的传说,但也是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念的遗留,它告诉我们,龙不点睛,尚不完整,就不是真龙,一旦点了眼睛,龙就能飞走。可见,绘画能否发挥巫术功能,就在于它的完整性。
总之,中国的人物画除了视觉写实之外,受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的影响,很多时候还要考虑人物构成要件的完整性,这一完整性追求是为了让画像与人物之间更加具有同一性。也就是说,它不是画家为了一己的主观创造力,也不是为了观者的主观艺术情趣,而是为了画像能够更加真实地成为人物本身。这同样是另一种绘画写实的追求,不能轻易地用视觉写实一概否定。
三、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
与人物画一样,中国山水画同样也受到了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人物画更加明显。不同于西方风景画,中国山水画从其诞生之初就喜欢画大山大水的全景,将山水的整体面貌呈现出来,不仅如此,它甚至还要画出山中景致的细节。这在视觉中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要看到全景,则必须远视,但远视就不可能看到细节。山水画对整体和细节的同时呈现就如同人物画中的侧面全眼一样,并不是画家无意中所犯的错误,而恰恰是有意追求的效果。南朝王微《叙画》云:“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7](P585)“太虚之体”即宇宙全景,“寸眸之明”乃细节呈现,因而,在他看来,绘画正是对视觉局限的有意克服,从而追求一种视觉不可能达到的完整性。这一观念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山水画史。从具体作品来看,山水画并不遵守统一的透视法则,为了表现山水整体,往往当缩小时缩小,当放大时放大。有时为了使近处在透视法看来过大的景物不至于遮挡后面的景物,可以采取将近景推远的方法,使观者仿佛悬在半空中似的。有时为了使远处在透视法看来本应很小的景物,但为了呈现它,又可以将之放大,如很多画中远处的瀑布、路桥、房屋就并不比近处的瀑布、路桥、房屋小。甚至在景物的大小明显不合透视法而使画面显得不协调时,画家就直接用一片水、一片云或一片空白来缓解这一矛盾。为此,在宋代的李成和沈括之间还发生过一段公案:李成主张视觉写实,认为绘画只应画其视觉所见,人在山下,只能看见山上之亭馆及塔楼的榱桷,因而当仰画飞檐。沈括则对李成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一视觉写实的画法“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又如屋舍,亦不应见中庭及后巷中事。”[9](P121)这种追求“重重悉见”的绘画观念正是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追求完整性的体现,在沈括看来,这才是山水画的正统。
在中国画家看来,山水画就应该画山水本身,而不是画人对山水主观的视觉感受,不能因视觉局限而破坏山水本身的完整性。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中国画家没有透视法的观念。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早在南朝时宗炳就提出了“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7](P583)的现象,宗白华认为这就是透视法了,但“中国山水画却始终没有实行运用这种透视法,并且始终躲避它,取消它,反对它。”[10](P143)个中缘由,值得我们深思。退一步讲,即使宗炳所说还不是科学的透视法,但远景短缩的简单道理还是懂的,不至于在画中把远景放大。另外,山水画“画松树,近处的松针一根一根地画,远处的松针也一根一根地画。”[11](P88)远处的松树不可能看见一根根的松针,这是基本的视觉现象,中国人没有透视法,总不会连起码的视觉经验都没有吧。因此,中国山水画法必另有原因,这就是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对完整性的追求。
山水画与远古巫术绘画的相通还体现在它的巫术功能上,对山水画巫术功能的表述早在其诞生之初就有非常明显的体现。王微云:“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7](P585)美国艺术史家方闻也认为:“在古代中国人眼里,绘画就好比《易经》中的象,具有造物的魔力。画家的目标在于把握活力与造物的变化,而不仅仅限于模仿自然。绘画应当包孕并且掌握现实。”[12](P3)通过绘画来“掌握现实”正是远古的巫术思维,在这一思维看来,山水画不只是山水的图像,而是与山水本身具有同一性的存在,或者说它就是山水本身。有了它,人们就无需再寻求山水实体,对它的操作就等同于对山水实体的操作。与王微同时的宗炳就认为山水画具有“卧以游之”[8](P153)的巫术功能,有了山水画,“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7](P583)以至于石守谦认为宗炳的《画山水序》“隐隐展露出艺术在宗教仪式上所具有的神秘意义”。[13](P16)正如上文所说,山水画追求与山水实体的直接同一性,它并不注重与观者的联系,而是注重与其所绘之物的直接联系,这是一种更为原本的写实。尽管这种写实观随着原始思维的解体而逐渐褪色,但却慢慢化入人类的潜意识而继续对后来的绘画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不管后来的中国山水画如何发展,这种写实观都一直伴随其左右,理解这一点,建立现代山水画的中国品格就有了更多的思考方向。
四、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对中国画“观物”方式的影响
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不仅影响了中国画的造型方式,更是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画的“观物”方式。不同于西方的焦点透视,中国画并不囿于视觉角度,不强制事物接受视觉角度的剪裁,而注重对事物的整体观照。宋代郭熙认为,山之大物,观之则“每远每异”“每看每异”,且随四季、朝暮、阴晴而变化不定,不可蔽于一端,因而提出了“面面看”的原则,强调“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7](P635-636)这是对中国传统绘画“观物”方式全面系统的总结。这一“观物”方式不囿于视觉之所“见”,而更强调事物本身之所“有”。只要是事物本身所“有”的,即使暂时不能在某个单一的视觉角度中所“见”,也应“罗列于胸中”。可见,这种“观物”方式不是从观者出发的,而是从事物出发的,完整性高于视觉性。郭熙认为:“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鱼钓为精神”。[7](P638)这一比喻与视觉无关,而与山水的完整性相关,这些事物是山水的有机组成部分。就视觉而言,没有草木和烟云的山、没有亭榭和鱼钓的水顶多不适于观赏,但于山水本身而言,没有它们,就显得不完整了,犹如残疾的人。也就是说,如此比喻并不指向可否观赏,而是指向事物本身是否完整。略小于郭熙的沈括也同样指出了单一的视觉角度对于表现山水大物的无力,“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景;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景,似此如何成画?”如果人站在东边,那么西边就是远景,应当缩小,但如果站在西边,那么东边又是远景,应当缩小,这对于无法在一个视角角度中穷尽的山水大物来说,透视画法就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认为“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7](P625)然而,真山毕竟是真山,在那个没有飞行器的时代,人又如何能够像观假山一样地去观真山呢?只能“面面看”“饱游饫看”,通过身体的游走克服单一视觉角度的局限,获得山水本身的完整性,刘继潮教授称之为“游观”。郭熙所谓“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7](P634)南朝宗炳所谓“身所盘桓,目所绸缪”,[7](P583)正是对“游观”的表述。过去我们倾向于比附西方的焦点透视,将“游观”称之为“散点透视”,然而,“散点透视”不能仅仅停留于“散”,还必须具有能够使自身组织起来的方式,这一方式无疑就是事物本身的完整性。
这种追求事物本身的完整性,不限于单一视觉角度的“游观”自然无法像西方焦点透视画法那样可以写生,它只能在对山水进行多方面的整体观照之后再通过艺术手法组合成画面。《唐朝名画录》载玄宗命吴道子往写嘉陵江水,空手而归,帝问其状,奏曰“臣无粉本,并记在心”,且于一日之内就画出了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14](第一册P164)这一记载并非是为了表现吴道子的记忆力超强,而是意在说明中国画独特的“观物”方式,它不急于将单一视觉角度之所见记于粉本,而是要待整体观照之后表现出事物本身的完整性。这是中国画“目识心记”的独特的“观物”方式,不同于西方绘画的“目识笔记”,也是“目识笔记”所难以承载的。
当然,中国画对事物的整体性观照不仅仅体现于山水大物,它已经成为中国画基本的“观物”方式。郭熙云:“学画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临其上而瞰之,则花之四面得矣。”[7](P634)“花之四面得矣”正是花的完整性呈现,这里视觉角度的选择须服从于事物完整性的要求。唐王维《山水论》云:“石看三面,路看两头”,[7](P596)明董其昌《画诀》云:“山行时见奇树,须四面取之,[14](第五册P141)皆是基于整体性原则。依此而画出的事物,荆浩称之为“物象之源”。[7](P607)荆浩认为,整体性原则不仅仅指单个事物的整体呈现,而且还包括事物间的整体秩序,不可因单一的视觉之所见而破坏事物间的整体秩序。据此,他批评了那些“屋小人大”“树高于山”的画法,这种画法尽管可能符合一时的视觉透视,但却违反了事物间的整体秩序,是不可取的。
总之,中国画的“观物”方式强调完整性,而不是视觉性,从它极力走向事物本身的角度而言,它也是写实的,但却不是视觉写实,而是受到远古绘画影响的巫术写实。
结语
总而言之,追求与事物本身的同一性,注重对事物构成要件的完整性呈现是远古绘画巫术写实观的基本内涵,也是中国绘画写实的一个重要传统,而且是最为古老悠久的传统,对中国绘画的整体面貌具有深远的影响。今天的人们喜欢视觉写实,并以此作为绘画写实的衡量标准。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有问题的观念,视觉写实并不能达到绝对的真实,这还不是指因视觉诠释的差异而对画面的影响,例如不同的人对同一片风景的真实描绘可能截然不同。仅仅就视觉写实的追求本身而言,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视觉逼真只对那些喜欢通过视觉和自然打交道的人来说才是真实的,而对于那些从未见过照片的民族,他们甚至不能认出照片上的人就是自己。这种现象也同样发生在明末西方绘画刚刚传入中国时的人们身上,他们对透视画法所表现出来的更多是惊愕,而不是赞叹。正如利玛窦所言:“他们出于好奇心,是来看其中供奉的美丽的圣像。”[15](P405)人们认为,绘画怎么能这样呈现事物?按透视法则和光影原理进行的视觉写实并不完全符合中国人的写实观念,它把很多本不该属于事物本身的人为因素强加给了事物,这乃是对事物极大的不忠实。因此,宗白华说,西画“貌似客观实颇主观”,而中国画“似乎主观而实为一片客观”[10](P133)。可见中西方绘画写实观的差异之大。
其实,西方绘画对视觉写实的极端追求,只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情*参见拙作《西方绘画写实观及其对中国画的误读》,《学术交流》2015年第6期。,在此之前,绘画甚至没有被特意强调为视觉艺术,也容许其他写实观念存在。就中国画而言,写实标准其实也是多样的,除了巫术写实、视觉写实之外,还有更具原创性的身体写实,当然这就需要另文撰述了。这里仅想说明,写实标准并非视觉写实一种,这使绘画能够从更多的角度丰富自身,也为绘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1]贡布里希. 艺术的故事[M]. 范景中,译. 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
[2]弗雷泽. 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M]. 汪培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博厄斯. 原始艺术[M]. 金辉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4]阿恩海姆. 艺术与视知觉[M]. 滕守尧,朱疆源,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5]霍华德·加德纳. 贡布里希:艺术为什么具有历史[J]. 美术译丛,1988,(3).
[6]叶青. 应物传神——中国画写实传统研究[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7]俞剑华. 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修订本)[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8]王伯敏,任道斌. 画学集成(六朝—元)[M].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
[9]沈括. 梦溪笔谈[M]. 侯真平校点. 长沙:岳麓书社,2004.
[10]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1]刘继潮. 游观:中国古典绘画空间本体诠释[M]. 北京:三联书店,2011.
[12]方闻. 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M]. 李维琨译. 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13]石守谦. 赋彩制形——传统美学思想与艺术批评[A]. 美感与造型[C]. 北京:三联书店,1992.
[14]卢辅圣. 中国书画全书[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
[15]利玛窦全集(第四册)[M]. 罗渔译. 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1986.
〔责任编辑:李官〕
Another Tradition of Realism: Impact of Magic Realism on Chinese painting
LIU Lian-ji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Due to magic thinking, primitive painting is not made for eyes, but for things themselves. although it looks not real, everything is here. It cannot accept perspective distortion, because that does not belong to things themselves; it also cannot accept incomplete things, although they do so in the visual. This is the basic meaning of magic realism in primitive paintings. The magic realism exists not only in primitive paintings, but also in Chinese ancient paintings, and forms a living tradition. Knowing this can remove the misunderstanding for realism, restore the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it, and provide more directions for thinking future development of painting.
magic thinking; realism; Chinese painting; impact
云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2014Z040)
刘连杰(1980— ),男,安徽天长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
J232.9
A
1006-723X(2016)08-012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