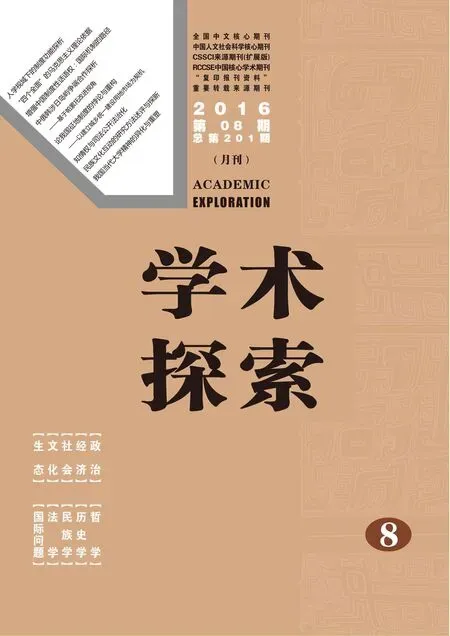论我国征地制度的悖论与重构
——以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为契机
张保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所,北京 100720)
论我国征地制度的悖论与重构
——以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为契机
张保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北京100720)
我国当前的征地制度偏离了公共利益的本质,存在着公益征收和规划征收、垄断谋利之间的悖论,其根源在于二元体制和产权模糊。重构我国征地制度,应当完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明晰农村土地产权边界;应当以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为契机,改土地所有权征收土地使用权征收,并回归公益征收和市价征收。
征地制度;规划征收;公益征收;悖论;重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要求“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从而拉开了征地制度改革的序幕。但《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论述仅指出了改革的基本方向,如何改革还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此,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这些改革建议主要是限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以及提高征收补偿等问题的阐述上,并未深入探究我国征地制度的深层次矛盾。①相关文章非常多,这里仅列举几篇:唐健.征地制度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中国土地科学,2011,(11). 窦祥铭.征地制度改革与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研究[J].石河子大学学报,2012,(8). 李中.我国征地制度:问题、成因及改革路径[J].理论探索,2013,(2).李红娟.我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改革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征地制度改革试点的分析[J].管理现代化,2014,(1).笔者认为,限制公共利益的范围和提高征收补偿等建议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阐明现行征地制度的深层次矛盾,征地制度改革无疑如同水中之月不切实际。
一、现行征地制度的内在悖论
目前,我国征地实践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一方面,征地范围大,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土地征收已成为中国城市规模扩张的唯一选择。1981年,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共计7438平方公里,到2008年,建设用地面积已达36295.2平方公里。[1](P26)不到30年,我国城区面积扩大了近5倍。相应的,我国城区人员却并没有扩展五倍。据报道,一些地方在2004年已经把2010年的用地指标用尽;[2](P69)另一方面,征地补偿低,失地农民很不满意。据17省的调查显示,1995年以后43.26%的行政村经历过至少一次征地。[3]土地征收成为对农民土地权益最主要最直接的威胁。据统计,中国目前的群体性事件和群众上访事件,超过80%都与土地买卖和房屋拆迁有关。[4](92)现行征地制度还制造了大量腐败,推高了城市房价。高企的房价扭曲了房产的本来价值,绑架大量的财富,既影响公众的幸福感,也不利于经济发展。
现行无节制的征地诱因是土地财政和发展经济的冲动。如前所述,学者一般将这一诱因转换为现实归因于征地制度中公共利益范围的模糊以及补偿较低。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原因,征地制度本身所存在的严重悖论也给了征地机关以可乘之机。
(一)公益征收与规划征收的悖论
《宪法》第10条第3款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收并给予补偿。”《物权法》第42条、《土地管理法》第2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征地机关对集体土地的征收本应当限制在公益征收范围之内。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实践中,地方政府基本无视上述条款的规定,而是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9条的规定对集体土地进行征收。该条规定,“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第9条根本没有提到“公共利益”这一标准,征地只要满足土地在城市规划区这一条件即可(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房地产管理》仅规定对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的征收要符合公共利益的条件。参见该法第6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直言之,如果该块集体土地处于城市规划区内,其最终的命运是将必然被征收。
在这里,“公共利益”和“城市规划”产生了冲突。如果坚持《城市房地产管理》第9条,那么显然就不可能坚持“公共利益”。在二者只能选择其一的情况,作为征收主体的地方政府显然更愿意选择“规划征收”这一征收方式。此时,“公共利益”要求形同虚置。数据显示,“全国征地用途中仅有20%的土地是出于绿化等公共利益需要,80%的农用地被征收后则转做房地产开发等建设用地”[5]
(二)公益征收与垄断谋利的悖论
如果政府是基于“公共利益”征收,那么政府应当是以相当于市价的对价征收集体土地,再以直接划拨或以征收所付出的代价为对价交与用地人。直言之,政府在征收土地过程中不得谋利。这也是世界各国惯例。征地机关不能一边说是基于公共利益对集体土地进行征收,而另一边又赚取征收与出让之间的巨额差价。但是,我国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这意味着集体土地被征收后,所有人与使用人(主要是农民)只能得到种植价值的补偿,至于土地的建筑价值以及交换价值丝毫得不到补偿。众所周知,土地的种植价值相对于土地的建筑价值以及交换价值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即使是按种植价值,标准也非常低。无论种植何种作物,补偿标准一般仅参照普通农作物的种植收入进行补偿。基于17省的调查数据也显示,目前政府出让土地的平均价格为778000元/亩,与支付给村集体的单位补偿额均值为24980元/亩补偿款相比,溢价高出30倍以上。[3]另外,以武汉市为例,该地到村集体的征地补偿款一般为3万~5万元,而土地出让最高可以到达360万元。[6]显然,征地制度成为征地机关营利的工具。征地制度“用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低价购买,用市场经济的办法高价出让土地。”[7]在这里,地方政府显然把自己当成专营土地的经济主体。地方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集征收权和规则制定权于一身。制定征收标准和补偿标准不以公平为标准,而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为标准。
征地机关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具有正当性。政府应当是市场的服务者而不能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之中去。现行制度以“公共利益”为由征收土地,再转手谋利的做法显然存在悖论。正是这种悖论,征地机关实现了以“公共利益”之名行垄断谋利之实。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悖论的出现有着深层次的根源。只有认识到导致现有体制问题的背后根源,方能找到征地制度重构的路径和具体措施。
二、现行征地制度形成原因与重构障碍的排除
(一)现行征地制度形成原因探究
1.城乡二元土地制度
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是规划征收的根源。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是由《宪法》确立的。《宪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也做了相应的规定。其中,《物权法》第47条更进一步,不但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且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在城市市区的范围不扩大的情况下,强行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为国有或许是现实的静态反映。但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城市的范围在近几十年内扩张了将近五倍,[2](P69)原来的郊区和农村现在变成了城市市区。此时,只有通过征收将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才能满足“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值得说明的是,《宪法》第10条第1款的规定与第3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的规定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规定城市的土地必须属于国家所有,另一方面又要求征收必须符合公共利益,显然是不可能的。
2.农村土地产权模糊
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则是征收机关能够以较小阻力实现低价征收的另一根源。产权模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集体所有,名不符实。这又主要体现在主体虚位和权能空置上。集体自身模糊无比,而集体所拥有的权利也是模糊无比。[8]现实中,集体往往为村干部所控制,而村干部往往又为地方政府所控制。于是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村干部对集体土地予取予求。第二,农民权益边界模糊。尽管目前物权法确立了土地承包经营和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的物权性,但这些权利权能并不完全。这些权利被限制处分,限制使用范围,实行用途和规划管制。包括农民在内所有人并不认为农民的权益比以前有多大的变化。权益的模糊削弱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性和动力。
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导致了农民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或许是有意为之,为地方政府主导土地产权并方便征收提供条件。一方面,产权模糊可以减少征地阻力。由于城市房屋的所有权是清晰的,因此,目前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大体是公正并得到了多数人的接受。这一事实可以反面印证产权模糊对于集体土地征收的影响。另一方面,产权模糊影响产权价格,降低征地补偿标准。美国学者阿尔钦有“所有定价问题都是产权问题”的论断。该论认为,所有产权残缺都会影响定价以及价格机制发挥作用。[9]
(二)现有征地制度重构障碍的排除
显然,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农村土地产权模糊既是形成现行征地制度的原因,也是征地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重大障碍。只有排除上述障碍,才有可能重构我国的征地制度。
1.废除城乡二元土地制度
笔者认为,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应当废除,理由如下:第一,强行将城市市区的土地规定为国家所有,不具有任何的正当性。根据物权法法理,所有权的取得方式中也没有一种通过法律直接规定取得的方式。第二,强行将城市市区的土地规定为国家所有是现有无限制征地的根源。同样地,这样的做法也毫无正当性。凭什么城市土地一定是国有的,而不能是集体所有?同为所有权,二者应当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第三,正如《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所指出的那样,“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为此,该决定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既然要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城市和乡村土地就应当同地同权、同地同价,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延续过去的二元土地制度。
为了彻底解决二元制度所带来的弊端,笔者建议修订《宪法》第10条第1款“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以及其他法律与此相应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将《宪法》第10条第1款、《物权法》第47条第1款和《土地管理法》第8条第1款修订为“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原来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如此,城市规划区的农村土地不必经过征收,不必变成国有土地方即可成为城市建设用地并进入建设用地市场。
2.明晰农村土地产权边界
目前,由于现行制度中的种种悖论,尽管法律规定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但名不符实。各地的调查也显示,多数农民也认为农村土地为国家所有。[10]那么既然如此,何不干脆肯认这种现实,直接或默认农村土地为国家所有?这种观点是对不合理现状的妥协,笔者并不认为不值得提倡。另外,还有理论认为,现有体制的形成是“农民从政府那里无代价获得土地权利,又无偿地归还了集体”。[11](P27)既然当初免费授予,现在理所当然可以免费拿回。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历史上,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农民的土地都是无偿获得的。农民中的富农和中农的土地即不是无偿获得的;另一方面,所谓的无偿也并不是真正无偿的。无地农民所分配的土地,是其参加革命以及付出政治支持的代价。第二,集体化,也只是从个体所有的形式变成集体所有的形式。共有,从其本质上,是所有的一种形式。因此,土地集体所有是农民拥有土地的一种形式,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农民的土地主人的地位。
消弭目前争议并欲在征地过程中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需要明晰农村土地产权边界。明确赋予集体国有所有权与国有土地所有权同样地位和同样的权利内容。二者不同仅权利主体的名称不同。此正如一件物品究竟是属于张三还是李四的差别一样。这也体现了《物权法》不同主体一体保护的精神(参见《物权法》第3条)。明晰农村土地产权边界,具体地说:第一,明确集体所有权不得因征收而改变。既然法律规定土地所有权不得转让,那么通过征收改变集体所有权的做法就不具有合理性。堵住转让之口在先,而开强行征收之口在后。人们有理由质疑:国家需要土地为什么不先在市场上购买而非要强行征之呢?第二,明确土地使用权人的主体身份,明确土地使用权可以自由出让和转让。按现行制度,征收土地时,土地补偿费给村集体,安置补助费则给安置单位,农民个人则只能得到少量的青苗补助费。之所以如此,在于未承认土地使用权人的权利主体地位,即使《物权法》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地位也是如此。有鉴于此,有必要明确土地使用权人的主体身份。除此之外,正如上述,只有明确的产权,才可能有真实的产权价值,提高补偿标准。目前,农民被排斥于建设用地市场的主体之外,农民的土地权益只能任由他人主宰。
三、重构我国征地制度的建议
不堵住肆无忌惮的对集体土地的征收,没有土地可供交易,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最终将是空话。因此,征地制度改革不但是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需要,也是建立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前提。
(一)从规划征收回归到公益征收
重构征地制度有两种模式:一是继续现行的征收补偿模式,继续对规划区内的土地实行无条件征收,但提高征收补偿(规划征收在国外并无先例。不过,英国1947年《城乡规划法》规定,政府可以通过向城市零星土地权人支付补偿的方式将其土地开发权(不是占有权)收归国有);[12](P63)二是公益征收的模式,政府只能以公共利益为由征收集体土地。不涉及公共利益的土地权利则由集体或相关权益人以交易主体的地位直接入市。笔者认为,目前的征收补偿模式补偿太低,如提高补偿,政府无利可图,其将不会进行征收。所以征收补偿模式面临着要么不征,要么以损害被征地人的利益模式进行征收。显然,上述模式不能解决用地需求,也不能保障农民的土地利益。同时,指望征收机关在征收时考虑农民的利益,显然也是与虎谋皮,不切实际。因此,今后征地制度应当采取公益征收的模式,此符合《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缩小征地范围”的精神。需要说明的是,公益征收才是征收的本质。被称为征收权之父的格劳秀斯曾经论述道:“国王能够通过征收权……从国民处取得财产。通过征收的方式取得财产,第一,必须满足公共福利(公共福祉),其次,必须对损失予以补偿……”[4](P119)另外,征收的公益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识。[13]
公益征收需要做到:第一,废除《城市房地产管理》第9条。第9条是目前导致集体土地非公益征收的罪魁祸首,理所应当被废除。如前所述,应当将《宪法》第10条第1款和《土地管理法》第8条第1款修订为“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原来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第二,立法机关应当制定公益性征收名录。符合名录的,可以征收。名录应当包括道路、公园、基础设施建设等,低收入者的住宅建设以及旧城改造(应当取得当地居民的大多数的同意)等。不在名录,以公共利益主张征收的,必须由法院进行判定。值得说明的是,司法判定应当采取异地管辖原则。否则基于中国现在的司法环境,难以保证裁判的公正性。
公共利益本身即是一种价值判断,一定程度上应从动态上综合考虑到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因素进行决断。但这决不意味公共利益的范围是可以任意设定的,无论到何时,其基本范围还是大致确定的。因此,制定一个名录大致还是可以实现的。名录的制定应当是各地的人大常委会而不应当是各地政府。为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可以考虑在一定期间内对名录进行修改,但也不宜变动过快。
(二)从低价征收回归到市价征收
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标准是非常低的。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土地管理法》第47条)。”地方政府仅以不超过三十年的总产值换取耕地的所有权,显然是不公正的。另外,即便是这些过低的补偿费用,农民也只能得到其中的一小部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1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安置补偿费名为专款专用,实际上也主要为集体经济组织所得。[14]据对中国17省1956位农民的调查显示,目前失地农民得到的单位补偿额均值为17256元/亩(村集体所得的单位补偿额均值为24980元/亩)。值得说明的是,调查还显示,有9.87%的现金补偿尚未落实,12.95%的被访农户则声称没有得到任何补偿。[3]这使得农民获得的土地补偿不仅无法保障农民未来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有时甚至难以维持现有生活水准。[4](P92)
征收制度性质上属于强制购买,但强制性仅体现在剥夺权利人的出卖决定权,而不在剥夺其得到等价补偿的权利。关于补偿,主要有两种理论,一种为既得权说,该说基于自然法,认为个人的财产既然是合法取得,那么就应当得到绝对的保障,即使基于公共利益被强制征收,也应当给予等价的补偿。另一种是土地效用说,该说认为,土地不是一般的财产,而是最重要的生产及生活资料,既具有产生经济效益的功能,也具有社会保障、保持社会稳定的功能。因此,不仅要补偿其土地的自身价值,还要补偿失地人的安置等费用。[12](P41-42)无疑土地效用说对失地人保护更为有力,但即便是既得权说,我国征收制度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增加农民土地收益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是,不得不说,完全按照土地效应说甚至既得权说进行在我国将会遇到地方政府的强大障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千呼万唤始终不出即是这种现实的反映。但是,笔者认为完全赔偿是必要的。这不但是公正的需要,也是可行的。第一,坚持公益征收,缩小征地范围。如果以目前征地规模计算完全补偿总额,那自然是地方财政不能负担的。但是,如果把征地范围局限于公益征收范围之内,征地范围将大幅度缩小,如此也将大幅度地减少地方财政的征地支出。第二,仅征收土地使用权,不征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具有永久性,而土地使用权则具有期限。因此,购买土地所有权显然要比购买土地使用价格要高。如果仅征收土地使用权,显然可以减少征地支出。征地之前,政府应当预估公益用地的使用年限,然后根据年限进行征收。为减少支出,可以规定征收使用权的年限不得超过三十年。三十年到期后,如果续用,政府可以继续征收该土地使用权。同时,政府还可以采取分期付款方式支付征地款,这样也可以起到减少当期支出的作用。公益项目,本来要用很多年,如果一次性支付,压力自然大。分期支付也符合会计上的权责发生制原则。第三,诚实地说,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即便完全是以公益征收,完全补偿也将给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困难。对此,国内有一种理论认为,目前土地之所以增值是政府规划和前期准备的原因。依此理论,政府为土地增值做出了贡献,理所当然应当拿走土地的增值收益。[14]贡献论在英国实践中有类似的做法。1947年英国《城乡规划法》规定,凡被开发土地因规划而提高了地价,开发者应当向政府支付开发费;相反,如果规划导致土地贬值或土地不能开发,政府也应当给予补偿。[12](P63)贡献论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认为土地的全部增值收益属于国家所有显然也不合理。因为,土地增值的因素非常复杂,例如经济发展形势、地理位置等,不能简单归因政府规划。正如《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所指出的那样“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需要指出的是,土地增值收益依所有权理论,无疑还是归所有权人的,只是由于政府规划为土地增值带来了贡献,因此可以通过税收从所有权人那儿分享一部分土地收益。[15](P258)
在具体制度建构方面,笔者认为,第一,可以制定征收补偿标准。但是,该标准应当是最低标准,不影响双方自由协商。第二,价格必须参考当地相同品质、区位的土地价格。必须强调的是,征收的本义是强制改变权利归属,但改变的前提必须是等价补偿。否则,这种征收与抢劫无异。实行等价征收,使得征收后无利可图,也可以遏制地方政府肆意征收集体土地的冲动。正是由于可以赚取低价征收与高价出让之间的巨额土地增值收入刺激地方政府不断掀起征地的狂潮。[7]第三,国家可以对补偿收入征收一定的税收,建议税收最高不得超过20%。正如前述,税收的正当性在于国家规划带来土地升值。
(三)从征收土地所有权到征收土地使用权
目前,对于集体土地,一律采取征收所有权的方式。这样做是很不公平的。法律一方面禁止土地所有权转让,另一方面却又通过征收改变土地所有权归属,这种做法不正当。这是一种变相低价购买土地所有权的制度,与禁止土地所有权转让的法律规定相悖。给人一种集体所有权不是不能转让,而是只能转让给国家的印象。另外,土地具有永久性和稀缺性的特点,因为其未来价值是很难估定的。估价过低,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而估价过高,则政府负担过重,也不利于发展公益事业。在此情况下,如果仅征收集体土地使用权,则可以做到两全。一方面,政府以较低价格征得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得以发展公益事业;另一方面,农民和集体也得以保留土地所有权,从而不致丧失未来增值收益。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征收制度的框架虽然是由法律规定的,但具体的征收办法却是行政机关制定的。例如,2011年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试行)》(粤府办〔2009〕41号)则由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制定。拟定中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则由国土资源部制定,国务院批准。这种既是征收主体又是规则制定者的做法违背了制衡的基本原理。笔者认为,征地法律应当由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定。非但如此,立法草案也应当由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委员会拟定,而不能由主管部门制定好草案由人大进行批准。
结语
土地征收制度的正当基础是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正如路易斯·亨金指出:“从来没有哪个制度否认过宪法的征收权,重要的是对征收的法律限制。”[16](P755)这个限制主要就是“公共利益”。征地改革实际上是要改变目前土地收益的分配格局。对此,政府作为利益相关者应当主动退出利益分配。这既是因为政府本身应当成为公益的代表,而且还是因为打破不合理的城乡二元格局,“保障社会成员公平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并促成贫弱者自强,使每一个公民体面地生活”是“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17]
[1]王旭东.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研究[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2]章彦英.土地征收救济机制研究——以美国为参照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3]叶剑平,田晨光.中国农村土地权利状况:合约结构、制度变迁与政策优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
[4]骆祖春.中国土地财政问题研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5]赵蕾.土地法律修改将提速保障农民权益[N].南方周末,2008-10-16.
[6]胡静,苏楠.城市化中非自愿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初探——以湖北武汉为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7,(6).
[7]崔艺红.新农村建设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J].经济师,2008,(5).
[8]张保红.论农村双层土地权利制度的重构[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9]周其仁.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J].经济学,2004,(1).
[10]陈小君.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J].中国法学,2012,(1).
[11]汪军民.土地权利配置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2]卢展元.土地换保障:扩大推动发展民众基础的政策选择[M]. 北京:群众出版社,2012.
[13]陈江龙,曲福田.土地征收的理论分析及中国征地制度改革[J].江苏社会科学,2002,(2).
[14]刘勇.涨价归公的理论依据与政策评析――兼论我国农地增值税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与对策[J].当代财经,2003,(2).
[15]李慧中,张期陈.征地利益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6]路易斯·亨金.宪政与权利[M].郑戈,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17]刘同战,张益刚.完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的若干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13,(10).
〔责任编辑:左安嵩〕
On the Paradox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Land Expropriation System in China—Ta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as an Opportunity
ZHANG Bao-hong
(Institute of law,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20, China)
China’s current land expropriation system has deviated from the essence of public interest. The paradox between commonweal collection, planning collection and monopoly profit is rooted in the binary system and the vagueness of property rights. To reconstruct China’s land expropriation syste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urban-rural dual land system and define the property right of rural land boundary;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establishing a unified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to change land ownership levy into levy of land use right; to return to public welfare levy and price levy.
land expropriation system; planning collection; levy for public interest; paradox; reconstruction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资助(2015M570203);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资助项目(Yq2013148)
张保红(1978— ),男,河南固始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广东韶关学院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法、土地法研究。
C912.82
A
1006-723X(2016)08-005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