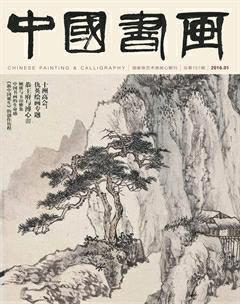中国书画的生命感
樊波
在我看来,与西方(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绘画相比,中国画更富有一种生命感。这种生命感集中地体现在中国画的笔墨形态上。西方绘画自文艺复兴以来,画家笔下的物象渐渐变得美妙生动起来。直至19世纪,以人物为主体形象的西方绘画在刻画真实生命的艺术水准上已达到极其完美的程度。有的人说,西方的静物画不如中国花鸟画那样洋溢出一种自然的活力,但是当你看到德拉克罗瓦所描绘的奔腾神勇的狮、虎和马的形象,恐怕就要对这种孤陋的判断作出修订了。但我仍想说,中国画所透发出来的生命意味的确还是要比西方绘画更为显著、浓烈。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画所描绘的对象是一个充满生机、神采斐然、气象万千的世界,而且是因为中国画描绘这一世界所采用的语言媒介——笔墨形态本身就构成了具有相对独立的生命单元。中国画笔墨在表现客观世界的同时并没有牺牲和泯灭自身的生命价值,相反倒是越是深入世界就越发彰显出自身的生命涵量。或者说,它越是更加自然、精妙地展示世界就越发对自身的生命形态提出更高、更独立的要求。这一点,起初似乎在书法领域比绘画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书法在肇于自然的同时更具有一种超越自然的倾向,因此更注重超越自然而诉诸于自身笔墨形态的建构。我们看到,六朝以来的书论一方面以从体察自然意态中来阐发用笔的规则和变化,所谓“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竖如万岁枯藤”“乙如崩浪雷奔”,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又从体贴人的生命内涵和形态中获取建构自身笔法语言的审美根据——这就是“骨”“筋”“肉”“气”这四个相关概念的提出。大约是传为卫铄所撰的《笔阵图》最早出现了这些概念——这里我们不必追溯这些概念产生的更深远的思想渊源和文化背景(比如人物品藻),而只需指出,在书法实践的基础上,六朝后来诸多书法家和批评家相继都运用这些概念进行书法品评,南朝谢赫亦在著名的绘画“六法”论中提出了“骨法用笔”的命题。这都表明,一个不再以外在自然比喻为体例,而是以人的内在生命结构为主干,标志着中国书画笔墨形态相对独立、完整而系统的品评话语已然形成。到了唐代。书画理论中这样的概念品评更是比比皆是,五代画家荆浩对这四个概念作了更为深入明晰的理论阐发和总结——这是中国书画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思想事件,是中国书画家应当获得大大品赞的一个理论创举。
这几个概念凝结了中国书画的生命感,并从笔墨形态的角度揭示了中国书画的内在品质。从生理学意义上讲,“骨”是中国书画笔墨的结构支撑。从美学上讲,“骨”意味着笔的力度,意味着一种阳刚风范:“筋”是中国书画笔墨运行的枢纽机制,笔墨合筋就具有一种韧性,就流回出一脉阴柔韵致:而“肉”则将“骨”和“筋”综合起来、统一起来,使笔墨语言拥有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形态。如果说,“骨”“筋”“肉”对于笔墨而言还只是一种技艺规定的话,那么“气”则属于一种玄妙的形上要求。好像当年陈独秀曾批评说: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气”,不知“垛为何物”。其实中国的“气”论,不能以科学之理考,而应以文化之途解,更当以美学之义释——如此来讲,“气”就不能当作氧气或二氧化碳来看待,不能当作某种“物”来看待,而应作为人的生理与心理相合而成的精神状态来感知。尽管这种生理和心理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深究,但由此而形成的精神状态——“气”却必须从文化和美学的角度统而观之。先秦哲学家管子所说的“精气”,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都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对于中国画的笔墨而言,仅仅有“骨”、有“筋”、有“肉”还是不够的,只有当“气”统摄、渗透了“骨”“筋”“肉”才会焕发出真正的生命光辉,才会拥有真正活的灵魂主宰。管子曾说:“有气则生,无气则死。”我们也可以说,笔墨有“骨”、有“筋”、有“肉”而无“气”还是形同死物,而一旦有“气”则顿然改观,顿然获得新生,笔墨形态就会顿然透发出一种蓬勃的生命感。
如果说,中国书画的笔墨表现为一种具有生命内涵的语言形态,那么西画的语言媒介则往往只是再现物象的纯粹工具。记得意大利大画家达·芬奇说过,绘画要高于雕塑。因为雕塑的语言媒介只包含了形式、形体、方位、动、静五大因素,而绘画的语言则包含了明暗、色彩、形体、形式、方位、远近、动静十大因素。然而无论西方雕塑和绘画包含了多少因素,具备多少表现功能,但其语言媒介并没有相对独立的生命形态,它作为一种工具在履行功能后往往沉没于客观物象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西方绘画的语言媒介越是彻底地沉没,客观物象才会越发如真如幻地显露出来。中国书画则不然,中国书画的语言形态是与自然物象同时协和出场的。中国书画的语言形态越是见出自身的生命魅力,自然物象才会越发呈现出一片生机,两者相摩相荡,相得益彰。另据西方学者沃尔夫林概括,西方古典绘画有“图绘”和“线描”两种手法。这里就其“线描”而言,却仍是沉没于物象结构所规定的轮廓格式。我在卢浮宫曾见过一尊浮雕人物坐像,衣纹表现一改体块方式,而以精美的线条刻镂而成、披身而下,初观疑同中国永乐宫壁画。细而察之,方知人物的身体结构仍然严谨地支配着线条的转折趋向。所以宗白华说:“西画线条是抚摩着肉体,显露着凹凸,体贴轮廓以把握坚固的实体感觉。”“其结果是隐没在主体的境相里。”而中国画“每一线有种独立的意义与表现”。宗白华还说,西方“后期印象派重视线条的构图,颇有中国画的意味,然他们线条画的运笔法终不及中国的流动变化、意义丰富”。这是因为中国历代书画家都极为自觉地追求笔墨线条相对独立的生命感,也都极为自觉地认识到只有这种聚集了丰富、浓烈生命意味的语言形态才能与蕴含着无限生机的自然万象相匹配、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