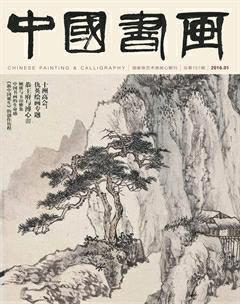玉山雅集之外的顾瑛
罗中峰
元人顾瑛(1310-1369),生于昆山界溪之累世豪族。“曾大父宗恺,宋武翼郎。大父闻传,元卫辉怀孟路总管”,是以“大父洎其诸从父,皆纡金拖紫,贵显赫赫”。然而顾瑛本人却无意仕途,年十六废学从商,三十岁“复读旧书,日与文人儒士为诗酒友,又颇鉴古好玩”。年约四十岁。则专志营造“玉山佳处”,并创造玉山雅集的文化盛事。年四十七,剃发为金粟道人。年四十九,自撰《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洪武元年(1368),谪居临濠,翌年病逝于斯。
顾瑛以举办“玉山雅集”而名垂青史,以至于曾有论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顾瑛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主持玉山雅集。成为玉山雅集的东道主、首席诗人”。本文却认为顾瑛一生其实颇见曲折。除了世人熟知的雅集志业之外,他曾在政治与文化场域之间穿梭,也曾徘徊于诗文倡和与宗教修行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再者,顾瑛晚年甚至从玉山雅集的活动场域,转移到湖海漂泊的生活世界里,并逐渐从社会生活舞台上隐退,企图超越凡俗、隐逸避世。
一、政治参与
至正十年(1350)顾瑛独资赞助昆山州重建城隍庙的义举,成就了一桩由热心公益的乡绅响应官府感召而捐资修庙的善行美事。一方面,此举被诠释为:“瑛也独任,不烦公私,而成之速、工之美若此。盖上以善劝下、下以善应上,感孚之理固自有不可遏也。”另一种诠释,则又归诸于顾瑛个人的宗教经验:“盖十年前。瑛曾梦与神接。神语之曰:‘岁在摄提龙御于斗,必有良牧,式康式阜,吾宫当大,汝其左右。”亦即,由于庙事兴废与城隍之神所示梦境相符,顾瑛遂“忻然以庙事为己任”。又或许,顾瑛之所以慨然承担修庙之举。乃是其济贫周急、豪侠好义性格的表现。如同殷奎评述顾瑛所言:“方其年壮气盛。觊慕布衣任侠之权。至以原巨先、杜季良自许。请致宾客。将希踪郑庄,一何快也!”于是乎“忧人之忧、乐人之乐”,遂慷慨捐输、义无反顾,正如他因“重义急水火”、爰慨制柟木棺以赠郑元佑的义举一般。
顾瑛与官府的关系究竟是否异常密切?曾经响应城隍庙重建工程的举动,是否意谓他刻意经营政治人脉以保障私家利益?其实或许不然。顾瑛曾自述其“不学干禄,欲谢尘事、投老于林泉而未能果”,抱怨其衷心向往林泉高致,却每受官府干扰:
先是浙东帅府以茂异辟为会稽儒学教谕,趣官者至,则趋而避之。至正九年,江浙省以海寓不宁,又辟贰昆山事。辞不获已,乃以侄良佐氏任焉。
可见顾瑛逃避任官之犹恐不及,又以侄代己出任昆山武职,争取隐逸自由之身,然而官威所迫,自有其无所逋逃之强势。随着元末战乱四起,顾瑛更难以置身事外:
又五年(案:至正14年),水军都府以布衣起佐治军务,受知董侯抟霄。……又一年,都万户纳麟哈剌公复俾督守西关,继委审赈民饥。公嘉予有方,即举知是州事。朝廷使者衔宣见迫,且欲入粟,泛舟钓于吴淞上。
至正十四年(1354),顾瑛以布衣佐治水军军务、平定海寇。来年,督守西关、审赈民饥,甚至从军幕中,奉命选领水军、协力剿捕昆山贼党。可见元官府强制顾瑛所为劳役,除了征辟儒学教谕之类文职外,另有军事武职若干。其中督守西闾关、筑城守备之役,颇令顾瑛苦不堪言,随后“入粟补官”的胁迫,更逼使其舟遁避祸。然而,至正十六年(1356)当张士诚据吴之后。他却依然迫于时人交相荐举之厄。顾瑛欲谢世缘而无策,于是“祝发庐墓”、削发做在家僧,并且“营别业于嘉兴之合溪”,“阅大藏经以报母恩”。同时更“渔钓五湖三泖间”,希能谢绝尘事,与世相忘——其所以矢志拒绝出仕的决心可见一斑。
基于前述,至正十五年(1355)被迫镇守西关的顾瑛,显然是百般不愿的——既感慨“腐儒不愿黄金印,旧业犹存负郭田”,更因隐居无门,只得聊以“名惭征士起,职愧守关忙”而解嘲。无奈“守关三月不得去”的他,除了“朝骑生马驱公府,暮阅阴符校武书”之外,还得苦于修城之难“二月修城五月过,修城不了奈城何?只因一夜斜风雨,到晓都坍一半多”,乃至于必须面临“赈饥岂意属儒冠”、“又俾审理民间饥”的沉重负担,岂料极度难堪之境,更属“补官使者招入粟,一纸白麻三万斛”!盖因元廷政府为了导引民间力量协助官方赈济灾荒的工作,出台了“入粟补官”政策,并于元文宗时期予以制度化。该政策鼓励(强迫)富民“依例出米”或“折纳价钞”。此所以顾瑛被迫审赈民饥,以至于“频年官籴廪为空,数月举家朝食粥”:直到面对元廷“到处都添滥设官”的强制入粟之令如大难临头时,顾瑛只好重施故技,走为上策——不得不泛舟吴淞江上,逃匿江湖以远避风头。值此之际,顾瑛只能发出“肯将身事逐飘蓬,鬻爵何缘到野翁”的感叹,同时心生“老去滔滔嗟逝水。愁来咄咄作书空”的牢骚,以及“殷勤寄语娄东友,归日草堂重赋诗”的期盼。
但事实上,顾瑛并非昧于民间疾苦、对社会现实无感的人,是以在诸多诗作中,表达其社会观察与批判的观点。例如,有关发行新钞之弊,他发现“新行交钞愈涩滞,米价十千酬四升”、“二斤十贯新交钞,只直仓黄米四升”,战乱频年,民生凋敝之惨境:“海贼初退山贼连。姑胥细民如倒悬”、“街衢寂寂无车马。风景凄凄似禁烟”。然而官府籴粮征役的苛政,更使民生疾苦雪上加霜:“长淮千里连烽火,浙西三年运米薪”、“官支烂钞难行使,强买盐粮更打人”、“口传催办军需事,一日能无一百回”、“官府征求苦到骨,村落饿殍寒无裳”:但人祸之外更逢天灾交迫,百姓生计更是难以为继:“梅雨今年多去年。青秧白水漫平田”、“饥农仰天哭无食,今秋无成将奈何?……皇天流毒虐下土,自此天下何由安”……但即使目睹此等社会苦难,“寸心忧国惭无补”的顾瑛又能有何作为?是否于诗歌作品中表达对于大有为政府的期待?抑或是为理想权力典范讴歌赞颂?的确。前述行动正是顾瑛向政治权力祈祷、为政治权力欢呼礼赞的策略,其例女吓所列:
1.至正十年(1350),顾瑛设宴于玉山草堂。邀于立、良琦、石载、殷子义、瞿荣智、顾权、秦约等人同为涮东副元帅(索珠)饯送,歌颂其镇驱海寇、护送漕粮抵京之伟功,及其兵不扰民之军纪,更推崇其效忠王室奋不顾家的精神,足为士大夫之楷模。席中致赠画家从叙所作《云帆驾海图》,并由于立写序言道:“国有人焉,所以重为天下贺也。吾党能言之士为歌诗以美之。”其余宾客均赋诗于卷后,合力完成《送涮东副元帅巡海归镇诗并序》以赠。
2.至正十二年(1352)。昆山通守郜肃。“以军食民命为急,跋履川原,冲冒风雨”,致力于堤防修缮工作。因其尽心尽力。“能恤民之劳,故民乐于趋事。堤既成。田亦增垦,潦不为灾”。故其所为政绩“较之常岁修围之夕卜其增垦露田若干亩、计赋若千万”。堪令“食人之椽、玩岁而愒日者”心惭而效法。顾瑛遂与一批“大夫士嘉其政绩,咸为歌诗美之”。作筑围辞、筑围妇、筑围谣等诗歌。
3.至正十四年(1354)。江西行省检校官赵伯坚“来浙右籴米十万石赈饥”。不同于以往籴粮侍郎“输钱索物要酒浆,磨牙吮血如虎狼”的恶形恶状,赵氏在过程中,不扰民、不劳官,“微服民间身作商,指廪发粟酬其偿”。故吴民难得不因官籴粮而受苦伤。顾瑛感念万允遂“效白居易体”作《官籴粮》歌谣一首,“使吴民歌以饯其行”,并祝愿后来者能“以公籴粮为典常东吾之民始安康”。
4.至正十五年(1355),枢密院断事官脱因本主漕政海运,适逢贼寇进犯苏州,竟揽为己任,率众杀贼以全吴城。顾瑛于感激之余,深盼脱因能蒙召诛乱、平定天下,因而“谨葺长短句引其意,使吴民歌之以报公”。爰赋《君臣同庆乐》一曲上呈以示感恩,“欲希公之听,庶知娄东野人亦知公之万一”。
以上事例。可说是文人透过歌诗文字为政治权力欢呼礼赞、以实践其社会参与的卑微努力,但这犹如寄托渺茫悲愿于祈祷政治权力之能有效作为——既然认定“吾辈无与于世”且不求闻达,遂只能盼望“今四郊多垒,膺厚禄者则当致身报効”。倘治世难期、生命艰危。则终须安排足以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生活策略。
二、宗教修行生活
吴宽观看顾瑛《补释典》《写道经》两张小像后,评其“游心虚寂之地,其气已衰”,并认为另一幅老年像所绘“方床曲几。与一老翁对语,癯然病状,宛若维摩诘,又何其惫也”!但吴宽以为顾瑛之所以修行释道。乃因“是时玉山方避征辟,为全身远害之计”,故认定其游心方外乃是逃避入仕以求自保的策略。诚然,当至正十六年(1356)两度兵入草堂,顾瑛历险流亡商溪避难,甚至母丧旅次。却仍无法“以斩然衰绖”为由拒辞授官。遂索性“祝发家居,日诵大乘经以荐母”,显示其“屏却世缘,以游心于清净觉海”之决心。借以杜绝逼官之厄。但顾瑛断发为僧,未必只是伪装姿态,实则当顾瑛于至正十六年(1356)正月开始使用“金粟道人”一称号时,追求某种超越世俗、了脱生死的生命观,可能才是更深层的动机——他所逃避的不只是官场,还包括死生大限的实存忧惧。
至正十八年(1358)。顾瑛自题《金粟道人小像》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标榜三教合一且勘破生死的达观态度。同年,顾瑛自撰墓志铭,则特别陈述一段三生奇缘——“人传前身是慧聚寺比丘延福。又梦中知向一世为黄冠师,姚兴孙者是也,金粟道人由是而名”——由道士姚兴孙、经比丘延福、再转至今生既僧且道的金粟道人,似乎是一条延续三世的宿命轨迹,规定了他47岁以后的人生道路。其实道释兼修之法门,系其家学传统。据载。顾瑛的祖父顾闻传“好道家清净之说,尝以所居为真馆”。父亲玉山高士顾伯寿不屑于用世,不仅嗣葺该宫观,更“取黄帝老庄之书读之,而奉释氏不杀生之戒惟谨。每遇生辰,辄不茹荤、不饮酒:杜门却扫,焚香清坐,岁以为常”,其长子元臣则是道士于立的高第弟子。修道与学佛,似为顾氏家族传统之一。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顾瑛晚年的生活方式。
顾瑛之父玉山高士拜于立的父亲于中岳为师,修习丹药长生之术,而他似于十岁时由萧元泰真人启蒙(“我识丈人甫十岁,示我琅函启神秘。饱读山中石室书,碧玉丹章尽奇字”)。萧元泰对顾瑛期许甚高(“谓我身中有仙骨,晚岁相期供服事”),但他虽幽居丘壑却一直无法摆脱尘世之累,对于宴游之乐的兴趣也似乎高过于服食养生(“我尚笑谈浮大白,君能服食事中黄”)。至正十六年(1356)自号金粟道人之举,固然是其人生转折点,但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四日夜,顾瑛寓居吴江法喜寺时,玉山中芝云堂、读书舍、可诗斋发生火灾之意外,可能才是更重要的启示。次年顾瑛为《写道经》小像所题志文字。值得引述如下:
予去年春正寓吴江法喜寺,是月四日夜,玉山中芝云堂、读书舍、可诗斋,有郁攸毕方之灾,平日所藏书几二万卷皆为煨烬,独《云笈七签》不毁。因有三生之悟,即芝云堂北创小殿若干楹,像释迦、老君、孔圣于庄中,标其颜曰“三静殿之皆结不二室”。
顾瑛本人逃过火灾劫厄。而道经《云笈七签》竟能焚而不毁,遂使他萌发“三生石上旧因缘。也是山僧也是仙”的“三生之悟”。顾瑛更因《云笈七签》这部北宋道教类书所引导。搜集了《大洞玉经》正文、释义并相关诀图文章与存修法,钞写为《大洞隐文》,以精进内修存真之功:
阅《七签》,向有<大洞三十九章释义>,味其旨,皆内修之奥。适汝易袁君子英自昆山携范阳卢君公武手钞赵松雪书道经一部,内有《大洞玉经》三十九章,即其正文也。又得双凤普福室道藏内思真之诀、存真之图、郁仪之文、结磷之章,并其存修之法,考之《八素真经》中所谓大洞一法,尽合二契于敬矣。因手类为《大洞隐文》。……
于是出现了更多画像,如《读道书小像》《玉山勘书图》等。录其修道探玄、焚诵服食的参道生活。
反观袁华所题《顾仲瑛栖禅小像》,谓其“中岁慕道,阅经律论。员颅方袍,指心见性”,使我们看到另一个学佛顾瑛的形象。基本上。顾瑛与佛门文士(如良琦)往来唱和的历史既早且长,但他认真学佛的机缘,可能是与商溪母丧之劫有关。至正十七年(1357),他曾自述学佛动机:“用以脱尘垢,全我浊世身,荐我生身母。”前一年,母亲归瘗祖莹后,他“庐草屋三间于葬侧”,名为“北山兰若”,于其中“披阅释氏大藏经典,手书补其阙漏者三百若于卷”,并写像纪其“补释典”的孝行:至正十九年(1359),顾瑛更有亲赴法喜寺“楼居日钞佛书,至午而止”的行程。钞写经书似乎是他的重要修行法门。至正二十一年(1961)。顾瑛题朱琏所藏吴孟思书三体心经。写下“斩钉截铁画虚空,三体分明一体同。读得正中无一事。莲花开在海当中”“当心一画到如今画画皆心不可寻。尽说朱珪精字法。看他那画上求心”二偈,提示其观于书作笔画上求心、即心悟空的体会。洪武元年(1368),当顾瑛发配临濠前重登虎丘,因无缘再遇居中禅师,遂发愿‘弛日南归,却来座下作有发侍者”——面对此行之还乡未卜,祸福难料,似唯有求佛方能安心。但或许更重要的是,佛法使他了悟空幻,“视世等尘垢”:佛法为他提供了一种面对死生大限的达观态度,以及如何斩断生离死别、宿业嗔爱之苦的不二法门。
事实上,在连年战争威胁生命、财产安危的处境中,顾瑛系同时诉诸佛、道以证成超脱生死的旷达胸怀。年四十九,有感于“当今兵革四起,白骨成丘,家无余粮,野有饿莩。虽欲保首领以殁,未知天定如何耳”?“且有鹏鸟入室。恐倾逝仓卒中,则泯灭无闻。”故鉴于生命无常、死期难料,因此他效法东汉赵岐在生前立碑、预营寿藏、并敕子以遇死即埋掩的故事,预为寿藏名“金粟冢”。并先撰墓志铭自志平生、立遗嘱告戒子孙以“苎衣、桐帽、椶鞋、布袜,缠裹入金粟冢中,慎勿加饰金宝,致为身累”,更基于“三生已悟身如寄”的态度,发抒其看破生死无常无伤、殁吾宁也的安息观:“大生之有归。犹会之有离。譬彼朝露,日出则唏。予生也于生弗光:予死也于予何伤?愿言兹宅,永矣其藏。”不仅如此,顾瑛甚至模仿唐司空图之“豫为蒙棺,遇胜日,引客坐圹中赋诗、酌酒裴回”以证其“生死一致观”的行径一般,“遇胜日,率亲戚故旧,至其处(案:金粟冢)饮酒赋诗为嬉”,游他郡时,则“图寿藏规制,并录志文以自随”,借此以证其为“一死生、解外皎者”。
然而,顾瑛表现其旷达超世之道家襟怀的极致姿态,该算是至正二十年(1360)中秋夜举行的“金粟冢燕集”。他函邀陆麒、秦约、谢应芳、殷奎、袁华、翟份、于立等挚友十二人赴宴,席设墓垄之上,众人“环坐冢上,前列短几,陈列觞豆,各真笔札于左方。兴至而咏、情畅而饮。不以礼法束也”。顾瑛畅言其达生委命视死犹归、宁与友人于墓冢上欢饮赋咏的心志:“齐物我、一死生,先生玄门之道也,予虽不敏:岂以死生动其心哉?以其殁而吾故人哭于斯、祭享于斯:曷若生而与吾故人饮于斯、赋咏于斯也。”充分表现出玩世之士不以死生而动其心、忘世且忘身的生命姿态。
三、晚年舟游生涯
顾瑛于《金粟冢中秋燕集》诗中写道“战血溅野草,饿莩填荒沟。我时挈妻孥,夜泛苕霅舟”,表明其经常乘舟逃难的处境。其实移家上船、舟游四方,似逐渐成为顾瑛生活的常态。至正十五年(1355),倪瓒因不堪忍受兵匪骚扰与差科逼辱,被迫散财弃家,逃向晚年流浪漂泊的生涯。同年。顾瑛也因入粟补官的压力而“泛舟钓于吴淞上”。三年之后,倪瓒题写《金粟道人小像赞》复云顾瑛“忽自逸于尘氛之外,驾扁舟于五湖。性印朗月,身同太虚。非欲会玄觉于一致,而贯通于儒者耶”?显然倪瓒的说法,并非只是推崇其三教合一境界的美饰修辞。却可能也是顾瑛浪游江湖的事实报导,因为,友人邾经是以“半生落魄江海上”来形容顾瑛:“脱略富贵如浮云,往年避名不肯作州尹,比年分财尽付与子孙。半生落魄江海上,芒鞋竹杖乌角巾。”然而,殷奎确实是用一种瞻仰的视角来颂扬顾瑛晚年的舟游生活:“及乎晚节,逃名自放,汗漫江湖,欲招陶岘、揖鲁望而与之游,又何卓也!”鉴于唐开元中家于昆山的陶岘,“富有田业,择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则汛艚江湖、遍游烟水,往往数岁不归”。他曾“自制三舟,备极坚巧。一舟自载,一舟致宾,一舟贮饮馔”,“吴越之士号为‘水仙”。陶岘向往谢灵运但殉所好、莫知其他、“终当乐死山水间”的生活态度,故而舟游烟水江湖,“栖迟于逆旅之中,载于大块之上:居布素之贱,擅贵游之欢。浪迹怡情,垂三十年,固其分也”!至于陆龟蒙则自许为“涪翁、渔父、江上丈人之流”,喜欢乘小舟、随兴漫游。船上“设篷席、赍一束书、茶灶、笔床、钓具、棹船郎而巳。所诣小不会意,径还不留。虽水禽戛起、山鹿骇走之不若也。人谓之江湖散人”。殷奎将顾瑛的泛舟浪游生活,推崇至陶岘与陆龟蒙之逍遥舟游典范的文化高度,并非偶然,因为顾瑛之逃名自放,不仅是高谢荐辟的隐逸姿态,更是从文人社群之中心焦点(玉山雅集)隐退遁迹、摆脱繁华雅集而归于平淡逍遥的壮举,其旷怀自逸之境,非一般人所能到。
从玉山主人变身为金粟道人之后,顾瑛的生活场域逐渐从“雅集”转移到“江湖”。但不同于倪瓒之弃家漂泊,至正十六年(1356)之后,玉山雅集虽仍然偶有举办。但次数渐减,俟顾瑛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迁居合溪别业后。与文友聚会雅集就更不容易了。其中。包括因友人来访慰问而举办雅集者。例如至正十六年(1356)底。因缪叔正前来慰问而有可诗斋雅集之会于烽火隔江、近在百里之际,顾瑛虽已落发为僧,尚与诸公觞咏,共忘此身于干戈之世。至正十七年(1357)二月,良琦、葛天民于戎马交驰之际远道来慰故人之隋,并问讯仲瑛之祝发,遂有柳堂春雅集。至正二十年(1364)四月,于玉山火灾之后,岳榆等人前来访慰人事惟艰之境,因集春晖楼上,饮酒赋诗共赏芍药。同年秋九月,愚隐师携祺上人等过访顾瑛,语道相契,并于书画舫欢饮倡和,一居数日方别。其次,系由顾瑛邀集的聚会,如至正十七年(1357),春晖楼前共赏牡丹之会,袁华犹戏云“虎头学佛宗三车,饮酒食肉谈空华。了知何必假外相,始悟在家真出家”。同年九月,顾瑛置酒会友朋于可诗斋,贺长子顾元臣以功升水军都府副都万户而归。是年冬,于芝云堂与六客分饷黄柑之会。次年四月,邀王蒙等人同集玉山于艰难之际、以慰交游之情,因“置酒梧竹间,饮散于芝云堂前,复坐池上书画舫中,玩月啜茶”。九月,则置酒于书画舫邀友同集,为谢应芳移家泗川里而饯别。至于至正二十年(1360)中秋那场惊世骇俗的金粟冢燕集,则仿佛是道别俗世的隐退之宴,预示其即将淡出世界舞台的姿态。
约略在玉山雅集次数减少的同时,顾瑛开展了“千里乡关路,十年湖海心”之所谓汗漫舟游的生活。根据他在诗作中的自述,例如:“渺渺长江飞白鸥,衔鱼逐我水仙舟。渔童能舞樵青唱,如此十年如梦游”、“十年一个水仙舟,只拣溪山好处留。茅屋已于临水卜,桃源不必问津求”、“故乡元不在并州,碌碌真成汗漫游。十载家山蝴蝶梦,一春风雨海棠愁”等诗,吾人可知顾瑛援引唐人陶岘水仙舟的典范(“谢安别有围暮墅,陶岘宁无载酒船”)。多年之间自放江湖而恍如梦游。这个决定,除了躲避征书的目的外(“知君有禄堪娱老,顾我无方可疗穷。欲借官舟从此去。布衣乌帽隐辽东”),更是出于逃名避世的抉择——因此,他以“达人悟物变,名不欲世闻”以及“十年名利不挂口,布帆满引三江风”等语,强调此一觉悟的意义,甚至举家移居。以求彻底避世。
“亲友散如雪,云树空悠悠。独尔数君子,艰棘见何由。”顾瑛远举避世之举,不免逐渐淡出社交圈子。其原因一方面自与战乱导致亲友离散的局势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出于他个人的主观拒离因素。顾瑛隐居玉山时,为了坚拒征辟,故“达官贵人未尝一见其面,征车之来,则逾垣闭门,甚于段泄。不知者或讥以迂怪”,自不意外。但亲朋旧雨也渐有拒绝往来者,如至正十九年(1359)春,顾瑛赴“同里法喜寺楼居,日钞佛书至午而止。余暇则吟咏不辍,虽亲旧来访亦不往苔焉”,似仅少数友人(如袁华、谢应芳等)例外得见。至正二十三年(1363)。为了更有效地辟世遯迹,也因为“王山中亭馆拆毁殆尽,仅留一草堂耳”,顾瑛势须择地卜筑新居,从而发现嘉兴合溪一带,“水多野阔,非舟楫不可到,实幽栖之地”。因此,顾瑛考虑其“地幽水秀,风俗朴俭,遂营别业,为焚诵计”,归为焚香诵经之新居。且由于该地萧然幽寂、屏绝世氛,故不拟俗人打扰(“是中多雅趣,难许俗人分”)。此一辟地而隐的策略,透过空间距离的隔绝,期使“门无胥吏催租至”。但并未全然断绝人际往来的联系。仍然是“座有诗人对酒吟”。
据悉顾瑛流寓异乡、隐居合溪时,“守道度日”、思索“四大安稳之问”,因此日常生活除了“一闲之外。无以为故人道”。然而,合溪虽地僻幽远,却仍不乏友人过访的纪录。如金贡诗云“此日孥舟却重过”、“莫雨放舟溪路远”。知其似曾远道拜访顾瑛,观其“合浦溪头景趣多,草堂结构倚沧波”,或如沈允到访(“合溪溪头放棹过”),依然是诗酒风流一场(“新诗酹倡似羊何”、“重感开尊留笑语”)。高叔彬携松陵谢氏《巫峡云涛石屏卷》来访求题。故为制长诗一篇寄题。然而,更多的情形则可能像是“怅望劳清梦”的达止善,虽“扁舟期独往”,但因“风雪恨侵寻”所阻。是以空间距离终究缓减了人际互动的频率——面对面互动的机会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书信问答的形式。从下引书信中,我们知道顾瑛隐居合溪时,仍不忘孜孜吟咏,且与诗友保持唱和关系:
承寄诸诗,读之不忍释手,随即和复。适往禾兴,失于写上。昨日又辱见和八诗,《合溪行卷》始不寂寞矣。鄙作附呈,并求窜改。阿瑛载拜博文先生馆下。
更重要的是,逃名远逐江湖之上的顾瑛,依然保持着友情连系的互动需要,于是舟游访友即成为玉山雅集的替代方案。参阅诸多诗句,可为例证:“遥知别后多相忆,早晚当期汗漫游”、“思君隔湖水。便欲放舟寻”、“放船问友或过剡”、“道人系缆夫容湾。飘然又移秋雨间”、“合浦堂成未得过,远承契阔到岩阿”、“王猷性僻径相过,三日扁舟泊涧河”、“夫容湾似星子湾,秋日放舡游其间”。在这段漫游期间。顾瑛访友对象或许是有选择性的,但他与张士诚政权守官谢节雪坡的交游则显得格外频繁。至正十八年(1358),顾瑛受谢节之邀,分赴吴江与嘉禾两地参与“水西清兴”雅集:翌年年底十一月,谢节转任杭州太守,顾瑛更受邀(携袁华同行)远赴“西湖梅约”。往返行程将近两个月——行程首赴甫里白莲池访元鼎师而有桂轩雅集之会,次赴西湖赏梅之约,唯因兵乱骤至,故循水路泛海转进。先至璜溪宿吕氏铁砚斋。再入华亭马庸小竹楼雅集,继而乘漕舟至云间会杨维桢、谢伯理等人。从而联句分韵。酣酒宴集。此后顾瑛多有舟访谢节之行,遂有“渺渺烟波一叶舟,年来多为谢公留”的记载。
但如果,远遁合溪之后,空间距离将不可避免地冲淡了友朋之间人情往来的密度(“莫讶年来不相见,只缘衰懒罢逢迎”),其所造成的隔绝效应,也往往会使书信往来的困难度相对增加(“数月诗邮雨不通,草堂坐对鲤鱼风”)。故大体而言,在某个时期后,顾瑛与朋友的书问交通的确是大幅减少,如以下书函所示顾瑛迁居合溪三年之后(“三载移家在秀州”)与外界连系的困难处:
仆蒙贤守怜流寓甚切,故三归草堂。前日蒙良贵季子下访,适在楠李,甚缺一见。而吾斓家书舟欲来又值雨阻,信艰时之难见如此。临楮悬悬,其情可知,幸亲照。
以至于谢应芳感慨道:“客来常问信,书去半沈浮。”虽然顾瑛仍间或孥舟出游访友。如以下致卢熊函所示,知其思友心切而有太仓、昆山、吴江(平望)之行,但因时局纷扰,朋友星散,似乎只能与特定友人相见,出入行踪更趋低调:
阿瑛启:遁迹异乡,甘与草木同腐。远领斯文,大芘眠食粗安。但于友朋,多不奉书问为缺。实以路远便艰,谅知我者必毋见诮。今年目昏手勘,老态顿加。因思太仓诸友,际此多故,不知再能相见不?因陪雪坡舟中数日,得入城一见。然风景非前,诸公放落,独与学古、彦文周旋两日,不胜慨然。回昆山途中,邂逅令弟,曾附意,亮达听司。近始知致身重戛喜慰无已。然未获为贺,负罪!负罪!傥至平望,毋惜枉驾。辰下暑隆,唯冀善加调摄,以膺大用,不具。五月三日顾阿瑛手书拜公武交契。
然而,即便此行消息得在朋友圈中流传,但顾瑛之行踪飘忽,也未必能够轻易相逢。谢应芳即曾有扑空的经验(“传书元有误,飞鸟竟无还”),惆怅失望之情,显然在所难免。
“玉山隐者久不见,闻道移居合浦东”。面对顾瑛迁徙远游、难得一面的遗憾,友人们表达思念的方式颇为多元。譬如有人因朋友久别而辄感思念,遂往往想象他在远方“吟诗云半席”,接着不免“遥想与谁分”。进而遗憾自己未在合溪雅集现场。或是虽知顾瑛已经远离,仍然往游玉山春晖楼,欣赏牡丹并赋诗遥寄,向缺席的主人报导赏花心得,借此表现出另一种思念方式,可见顾瑛未曾远离其心中。又或如部分友人仍企图游说返乡,例如谢应芳写寄<合浦还珠词>之举:
余以玉山隐君避地居梢李,犹合浦之珠徙而去焉。今谢杭州当路于吴,而州县更化,犹合浦之有孟尝也。人而珠者,可不还乎?因作合浦还珠词,寄君以致招要之意。
甚至某些友人似并不赞成顾瑛长期退隐,以至于颇有招隐意图。例如释克新曾认为顾瑛并非丘壑人,尚且“圣主征贤图治急,未容便作哜桑民”,言下之意似在劝说顾瑛考虑出仕。但顾瑛既已选择浪游江湖的生活方式,即坚定无悔。期间虽有若干次探视玉山草堂之举,然已再无可能重回玉山雅集的世界了。
正因如此,缅怀玉山草堂之风华殒丧的不舍情绪,自然成为玉山友人的共同心声。于是,我们听到谢节《过玉山草堂有怀》的哀愁是“玉山草堂湖水东,望之不见心忡忡”。在诸多倡和中,蔡宗礼的和诗所感慨的是“草堂人去无来客,鸳渚云深有钓翁”,而回首往日题诗处,只在荒烟落照中。章明则低吟“繁华已随化蝶梦尘土空嗟失马翁。画舫疏帘久相忆,草堂清尊惟与同”以为呼应。回应友人的感慨惆怅,顾瑛不禁兴发“却忆故人悬望久,草堂清兴此时穷”之叹,从而表达了幽隔野水、音书断绝、乱离漂蓬而身心不得宁处的生活境况,遂遥寄寂寥与朋友共慰远念:
草堂还只在娄东,身未宁处心烦忡。青海久无青鸟使,白头今似白凫翁。江湖千里舟楫渺,关塞十年戎马同。天上故人多远念,作诗同寄寂寥中。
其实,咀嚼顾瑛在诗作中所透露的美丽与哀愁。不难发现其虽优游而未必忘世。仿佛旷怀自逸却又不免惊愁哀伤,是以“十载闲身若转篷”的生活中,忧喜参半、爱憎交融的心境似乎才是真实写照。顾瑛曾因“惊心世事乱于丝”,因此“客中长拟四愁诗”,亦曾自比“杜陵忧国鬓成丝”,于是乎“伤时频赋七哀诗”。另一方面也心忧漂蓬,以至于“布帆六幅西风里,坐看青山叹白头”。他曾在雪后放舟探梅途中。目睹“亲友如星皆散落。唯闻野哭与荒鸡”的兵后萧条景况,却也自许“不是道人闲不得,西风落日起兵尘”。至于幽居合溪别业的心情。则有时“自怜如庾信,萧瑟住江城”,有时候却又自豪其“五株杨柳绕川斜,绝似渊明处士家”。此外既曾有过“三径不荒松菊在,白头且觅醉生涯”的轻安自得,也不免在历经“丘尘惨淡十年春”之后,兴发“心悟三生总一身”之感而亟求觉空解脱。虽然某些友人较能体会顾瑛隐居生涯的寂寞孤远,如叶懋所云:“秋雨江湖孤梦远,春风庭馆一尊同。遥知旧隐非前日,多在荒原寂寞中”,然而。在众多友人的心目中——姑不论是否出于善意安慰。抑或是基于迢遥远隔所衍生的蒙咙美感——透过某种理想典范的想象投射。以美化顾瑛生活图像的结果,则塑造出一幅逍遥高士的浪漫形象。
这个形象乃是经过一番筛汰建构的文化修辞过程所造就的成果——一方面是将顾瑛的愤懑郁结的情绪过滤掉。使其超脱日常生活的所有忧患愁苦:另一方面则将钓翁的文人理想投射其身,想象其渔钓于五湖三泖之间、逍遥野航乎兵尘俗世之外。既能悠然忘机而与鸥鹭相亲,亦想必陶泳于吟诗乐读的闲情生活中。于是乎,即便不强调钓翁形象,也必然彰显相关的人生价值观,遂能与其舟游生活方式异曲同归。于是有所谓“高士潜身入埜航,平生与世澹相忘……寂寂闲身书帙畔。悠悠清梦钓丝傍”之作,推崇其闲身忘世、垂钓耽书的隐逸高情,或如“风波不作泛槎客,烟渚长思垂钓翁。闲身自与鸥鹭集,浩兴或比渔樵同”之作,远怀一名身闲忘机、能与鸥鹭同集的避世钓翁,以及“故人天上皆知己,此老槎头独钓翁。尘土十年双鬓改,江湖万里一鸥同”之作,则刻画出沧桑十年、漂泊江湖的孤独钓翁形象。除此之外,另有“归哜且结忘机友,避世空为祝发翁”、“忘机海上鸥相得。采药山中鹤不惊”之说,强调其避世方外、交友忘机的隐逸情怀。至于“爱君溪上新居好,物物撩人总要诗”、“爱君合浦新居好,想见临流日赋诗”等语,则凸显出赋诗咏物作为顾瑛隐居生活之核心价值的重要性。当殷奎以“及乎晚节,逃名自放,汗漫江湖,欲招陶岘、揖鲁望而与之游,又何卓也”等语来颂扬顾瑛晚年的舟游生活,正是延续此一形象建构工程的努力方向:他将顾瑛的泛舟浪游生活。追配陶岘与陆龟蒙的传奇风姿,标举出一种令所有文人欣羡向往的文化典范,亦即金粟道人遥驾水仙之舟以浪游江海的逍遥自逸形象!然而,当顾瑛晚年浮沉于茫茫烟水之间,仿佛也带走了玉山雅集繁华的艺术世界,一并隐入寂天寞地之中,渐行渐远。
责任编辑:欧阳逸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