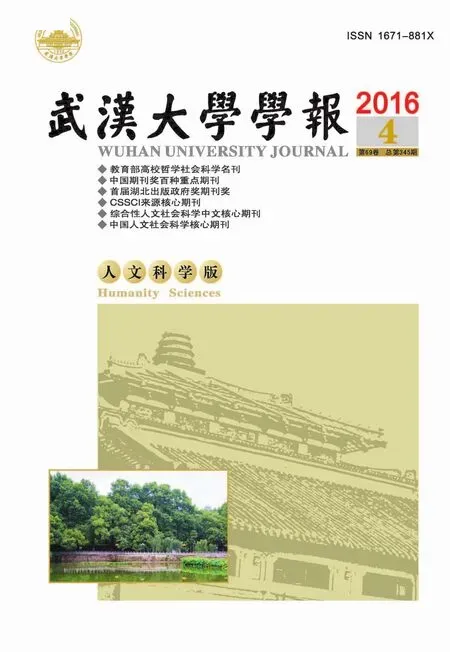列维纳斯后期反现象学的再次探险
陶渝苏
列维纳斯后期反现象学的再次探险
陶渝苏
摘要:列维纳斯认为,存在论与现象学相互纠缠,存在是在场的,它必须显现出来。存在论与现象学必然导致压制“他者”的总体性和同一性。他受德里达批评的启发,在后期思想中提出“别于存在”以反对存在论,提出历时性的时间以反对本质化的共时性时间,提出“言说”以反对将一切变为陈述对象的“所说”,从而开始了逃离现象学的再度探险。
关键词:历时性; 列维纳斯; 现象学; 存在论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是最早将现象学译介到法国的哲学家之一,现象学也由此成为当代法国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毫无疑问,列维纳斯本人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受益良多。然而,他后来发现存在论与现象学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压制他者,形成一种极权主义的总体性和同一性,因而它们是造成占有性的自我中心主义,甚至最终导致战争的罪魁祸首。于是,他踏上了反对存在论与现象学的道路。但是,由于他深受现象学的滋养,在其前期的思想表述中不自觉地使用了存在论与现象学的诸多词语和方法,所以遭到了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哲学家批评。正是这些批评,促使列维纳斯后期思想发生了明显转折,他再次开始了逃离现象学的探险历程。这一探险在当代法国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深刻影响了当代法国哲学的研究旨趣和基本特征。
一、 别于存在VS存在论
列维纳斯后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德里达对之进行的深刻批评具有密切关系。正如戴维斯在《列维纳斯》一书中所言:“列维纳斯后期文本特别是《别于存在抑或超乎本质》中所包含的根本性思考,乃是接纳德里达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尝试。”*柯林·戴维斯:《列维纳斯》,李瑞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德里达提出,列维纳斯前期思想中存在着诸多自相矛盾。一方面,列维纳斯认为,传统哲学对同一性和总体性的追求与一种关于“光”的话语密不可分。光是知识的隐喻,是可理解性本身。在光照之地,绝无真正的“他者”*陶渝苏:《列维纳斯“他者”之思》,载《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63页。。因此,超越存在论和现象学的“他者”必须是逃离光的、非现象性的,是不可主题化、不能显现、不可言说的。列维纳斯宣称自己是“为了克服现象学而去研究现象学”*汪堂家:《同名异释:德里达与列维纳斯的互动》,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14页。。在《时间与他者》中,列维纳斯提出,对于“他者”,不能使用“外在性”概念,因为“外在性”是空间属性,而空间则是以光为条件的*Emmanuel Levinas.TimeandtheOther.trans.Richard A.Cohen.Pittsburgh: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87.p.76.。然而,另一方面,在《整体与无限》中,列维纳斯不仅以“外在性”为副标题表明了这本书的主旨,而且还大量使用了“外在性”概念。德里达认为,这种自相矛盾只能说明要彻底摒弃
“外在的”和“内在的”等词汇是枉费心机,因为“人们恐怕无法找到一种无空间断裂的语言”*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三联书店2001年,第194页。。德里达还指出,要建立一种“对抗光的哲学话语”几乎是不可能的,“语言本身就是‘光’的一种坠落”*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三联书店2008年,第181页。。尽管列维纳斯在使用“面容”(visage)来隐喻“他者”时再三强调它的非现象性,然而“面容”的“神显”(épiphanie)却恰恰表明它无论如何也逃避不了某种“光照”,这就关涉到“现象学的暴力”*德里达:《书写与差异》,第139~140页。。
列维纳斯的回应是谦虚而谨慎的,同时他也坚守了原有的立场,并在其反对存在论与现象学的哲学话语方式上进行了一番新的艰难探索。他指出,在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看来,存在是必须显现出来的,它必须在意识中在场。这就是说,“存在是表现,存在=表现”*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145页。。因此,存在论与现象学根本不可分割。列维纳斯认为,意识中的在场意味着世界的安宁。安宁是一切运动和静止的支撑者,唯其如此,所有被思想者及其思想才能在不动者这里找到各自的位置,并由此形成一个同一性的世界。世界才是可以被人们所理解的。因此,“世界,就是位置,就是地点”*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150页。。换言之,在场与安宁标志着意识是一个港湾和出发地即不动者,被思想者及其思想从这里出发,然后又返回这里;世界在其中被认识与被表达。在场既表现了事物的运动,又保证了世界的同一性,还体现了光的照耀——事物的显现及其可描述性和可理解性。因此,在列维纳斯眼里,在场、显现、可描述性、可理解性等修辞隐含着一个前提性假设,即存在着一个稳固可知的现实,人们能够解释这一现实。这就是他千方百计想要逃避的存在论假设。“现象性,存在本质在实在中的展示,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永久前提”*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trans.Alphonso Lingis.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81,p.132.。要从存在论与现象学中突围出来而解放“他者”,就必须破坏这种安宁、在场与显现。列维纳斯强调一种永不停息的“零度场所”(null-site),其缘由正在于此。
虽然列维纳斯反对存在论和现象学的立场是一贯的,但是由于德里达的批评,列维纳斯也意识到自己早期不自觉地使用了存在论和现象学的术语来阐述其观点,因此后期的他不再或者很少再使用如同“绝对外在性”(absolute exteriority)和“绝对相异性”(absolute alterity)这样的词语,而是代之以“别于存在”(otherwise than being)、“亲近”(proximity)、“邻人”(neighbor)、“他性”(illeity)、“踪迹”(trace)等词语。同时他反复强调,由于突破现象学与存在论的最大困难就体现在哲学话语的使用上——一旦陈述,就意味着陈述对象的在场性和自身显现性,因而要揭示非现象性“他者”的意义,就只能言说那种“模棱两可的话语”(equivocation)。他说,在关于“邻人”、“踪迹”等表述中,“模棱两可的话从未被驱散”*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94.。
列维纳斯指出,“别于存在”并不是“另外的存在”,也不是“不存在”,而是有别于存在。“另外的存在”和“不存在”仍属于存在论的范畴。另外的存在仍然是存在,是另一个“他我”;“不存在”是对存在的否定,也只能由存在来加以解释。所以,列维纳斯说,“存在与非存在彼此说明”*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3.。这显然不符合他反对存在论的初衷。他指出,“别于存在”诚然是要在存在中被理解的,但是,它绝对不同于本质,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生存论意义上的存在,并且它只有在宣称“超越”的时候才会被说出。“超越存在中的‘他性’是这样一个事实,它对于我是一种离开,这种离开使我完成了朝向邻人的运动”*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13.。换言之,“他性”不是那个同一性的“我”,而是从“我”处“离开”;离开孤独的、内在性的“我”去向别处。于是,“别于存在”或“超越存在的‘他性’”不是一个当下在场者,它并不在意识中显现自身;它离开自身而朝向邻人,因而它不能被主题化。笔者以为这一表述已经很接近德里达所说的“在场而又不在场”的那种言说方式。
列维纳斯再次运用笛卡尔式的“无限”来揭示这种“别于存在”。“无限”与思想当然有联系,“无限”的概念就存在于思想之中,但是这种关系绝不是包含的关系,思想决不能包含“无限”;这一“在……之中”“既是作为另一个对同一个的插入(incidence),又作为二者的非重合(non-coincidence)或时间的历时性”*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171页。。这就是说,思想与“无限”的关系就是一种与“更多者”和“无法包容者”之间的关系,即无限对有限的溢出。列维纳斯指出:这种关系应该被想成是在“作为‘增’扰得‘减’不安的方式”*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171页。,作为“另一个摇撼着同一个一直到它内核的分裂”*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248页。来理解。在列维纳斯看来,存在论总是与整体性与同一性相关联,无论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概念化体系,还是海德格尔式的以此在的生存为起点而以其死亡为终点的封闭式生存论,都是这种整体性与同一性的体现。因此,若要想从这种整体性与同一性中突围,就必须使其“内核”发生内爆,寻求有限中的增补和溢出。无论“干扰”还是“摇撼”,列维纳斯的目的都是要破坏体现同一性的整体性,使之断裂、分解。
列维纳斯还使用“踪迹”这个词来表述“别于存在”。在他的语境中,既然“别于存在”是非现象性的,它就不能在场,不能是当下显现的。它只能以“踪迹”和“被抹去的踪迹”的形式存在。他说:“历时性通过把踪迹转变成离场的迹象来隐藏陈述和主题化”*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93.。这就是说,“别于存在”要逃避被主题化的危险,就不能把自己固定为在场,固定在当下,成为被陈述的对象。它必须是永不停息的流动(历时性),准备离场的行为。然而这种离场又不是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是留下了自己模糊不清的踪迹。“在踪迹中丢失的踪迹”,总是那么“模糊不清”,甚至几乎“一无所有”*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93.。
使列维纳斯花费笔墨最多的还是“亲近”与“邻人”。在他看来,“亲近”是首要的人性,是“为他人的自我”(the-one-for-the-other),它发生在任何主题化之前,应该在存在论范畴之外被设想。根据朱刚的解释,“亲近”与自我的“前史”有关:“亲近”不是“我”自由意志的结果;在“我”还没有来得及主动地作出决断和采取行动之前,就已经被邻人所纠缠、所指控,“无端”地成为他人的人质(hostage),“处于宾格之中”,完全臣属于他人,承担一个非我所愿的责任。如果说存在论关涉一个内在性和同一性的自我,关涉中介性的意识的话,那么,“为他人的自我”则是存在论的史前史*朱刚:《替代:勒维纳斯为何以及如何走出存在》,载《哲学研究》2011年第11期,第89页。。列维纳斯指出,“亲近”与对“他人”的责任具有直接性,一旦有第三方进入,它就又会成为一个意识问题。他认为,在“亲近”“言说”和“责任”中没有问题,它就是人性使然;同时,它也是非对称、非互惠性的。列维纳斯还指出,“亲近”不是一种静止状态,而是永远的躁动不安,它既外在于自身,又不在他人之中,而是在对他人的替代之中*朱刚:《替代:勒维纳斯为何以及如何走出存在》,第91页。,因而处于“零度场所”,对它而言,没有场所反而是适宜的。“亲近”“不是融合,而是与他人的联系。这种联系既不会包含他人以废除其相异性,也不会在他人中抑制我自己”*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86.。这就是说,“亲近”是非-位置(non-place)的,它永远流动,不能在场,不能显现;它一旦固定在某处,就会成为意识的对象,被人们所理解和陈述。它也不能被融合,既不会以占有的方式去除他人的相异性,也不会使自己的独特性消融在他人之中。换言之,“亲近”不是任何主题的联结,不是被叠加而成的结构;所有的综合和同时性都被它拒绝,“亲近,仿佛是一个深渊,阻隔了存在的不可分裂的本质”*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89.。列维纳斯对“邻人”的表述也具有同样的特点。他说,“邻人”拒绝将自己放入探求他的思想中,“邻人”是一个具体而现实的人,不是一个思想的对象,“邻人”的积极意义之一就在于打破了“我”此前的孤立状态,“我”暴露在他的面前,从而消解了“我”的内在同一性。“邻人”“逃避陈述,甚至是现象性的瓦解”*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88.。它“先于所有自我意识”*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92.。
二、 历时性的时间VS本质化的共时性时间
存在与时间一向相互规定,无论阐明还是逃离存在论都要对时间作一番深入考察。列维纳斯要想超越存在论,也必须克服现象学的时间观。与列维纳斯在《时间与他者》中强调要从“未来”入手去理解时间*陶渝苏:《瞬间、时间与他者》,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不同,他在《别于存在抑或超乎本质》中对现象学的内在时间观与存在论之间关系的认识更为清晰,因此他提出真正的“时间”是不可追忆的“过去”(the past)和无法显现的“历时性”(diachrony)。
我们知道,开现代时间观之先河的是奥古斯丁。他对此前以物理运动来度量时间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因为他认为,这种自在时间观不仅与上帝创世的观念难以相容,而且在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其说。奥古斯丁指出,实际上时间是一种思想(即心灵自身)的延伸。过去、现在和将来只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中,并且是以延伸的方式存在于我们当下的意识中。因此,比较确当的说法是,时间分为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这三类;过去事物的现在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是注意,将来事物的现在是期待。整体时间就是在当下意识(注意)中联系起来的记忆与期望。“谁否定将来尚未存在?但对将来的期望已经存在心中。谁否定过去已不存在?但过去的记忆还存在心中。谁否定现在没有长度,只是疾驰而去的点滴?但注意能持续下去,将来通过注意走向过去。”*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53页。由此,奥古斯丁打开了主张时间内在化的新维度。
胡塞尔深受奥古斯丁内在化时间观的影响。胡塞尔认为,若要对时间意识进行现象学分析,就必须“悬搁”客观时间即时间客体。当我们不再关注时间客体(如一段旋律),而是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意识本身是如何构造时间客体这个方面,我们就把握了时间本身。与奥古斯丁一样,他发现,时间不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依次交替的点,时间有一种延展性,因为感知有一种延展性。以声音为例:我们以意识到的声音绵延中的第一个时间点作为现在,它是原制作物,具有自发性的特点,不是被生产出来的,因而它是起源,是严格意义上的感知,胡塞尔称之为“原印象”。然而,这个“切身的声音现在”不断地变化为一个“过去”,另外又一“有新的声音-现在来接替那个过渡到变异之中的声音”*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85页。。这就是说,任何现在都要走向过去,都会被新的原印象所替代。但是,在被延展了的声音感知中,人可以觉察到从现在到现在之延续的客体,觉察到过去之物作为曾在之物被给予。这就是“滞留”。可见,在胡塞尔这里,感知既是当下的,又是可以被延展到过去的,而且还可以延伸至将来。时间亦是如此,现在既是当下,同时又可以向过去与将来两个方向延续。在时间视域中,除了滞留所保持的连续性之外,人对尚未到来的将来还有某种期待,就如同我们在听一段音乐旋律时,对未听完的部分有着某种期待一样。在胡塞尔那里,这叫做“前摄”。于是,由于感知的延展性,任何一个现在时间都体现为一种滞留、现在、前摄的三重时间视域,一个时间晕。
如果说海德格尔早期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论述的时间还是一种此在的时间性和有限性的话,那么,后期他在题为“时间与存在”的演讲中所阐释的就是存在自身的时间。海德格尔指出:在西方-欧洲传统思想中,存在从来指的都是诸如在场这样的东西,而在场就是现在。但是在海德格尔这里,存在不是存在者的基础与根据;凡物都有其时间,但存在不是物,也不在时间中。只不过它通过时间性的东西而被规定为在场,规定为当前。海德格尔说:“当时间一直在流逝的时候,时间就作为时间而留存(Bleiben),留存意味着:不消逝,也就是说在场。”*《海德格尔选集》上, 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664页。换言之,时间的流逝就表明了时间的持续在场。于是,存在、在场的涵义被改变了,存在就是让在场(Anwesenlassen),它始终作为“解蔽的赠礼”被保存于“给出”中。鉴于此,海德格尔指出,“当前”不同于“现在”。在场有“在那里”的意思,它将时-空联系起来,因而在场既有持续,也有“逗留”(das Weilen)和栖留(Verweilen)的意思。只有一个维度的“现在”与“客人在场”意义上的“当前”完全不是一回事。在当前中,不再现在的东西即曾在还存在并活动着,在场在曾在中被达到;尚未现在的将来也会以某种方式在场。所以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有三态:曾在、当在、将在,所谓在场就意味着这三态之间的“相互达到”,即此三态嬉戏着、活动着、统一着,在“相互传送”中达到。所以时间是四维的,在第四维的时间中,曾在、当在、将在既“澄明着分开”,同时又在“切近处相互接近”、相互通达、相互统一。然而,无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如何不同于经典现象学,即便这里的“在场”已经不再是意识哲学意义上的在场——他强调人不是时间的制作品,相反,人是时间的接受者,而是“本有”(存在)自身的一种运作,一种“给出”,但它终究仍然是一种在场,一种“自行显现”。既然是显现,就不可能不暴露在光之中。因此,王恒犀利地指出:“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最终竟又是其现象学了。”*王恒:《时间与存在——海德格尔后期的时间性疏论》,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15页。
列维纳斯的使命就在于超越存在论与现象学,因此他必然要反对这种在场时间观。
列维纳斯将时间区分为可回忆的共时性本质时间和不可回忆的历时性时间。在列维纳斯看来,真正的时间是已经流逝而一去不复返的,即不可回收、不可恢复的。被意识之指漏掉的那些时间片段不可能以某种方式得到恢复;时间之不可回收就好比无限之不能够被思想所包含,“时间将是无限之加在减中的爆发”,“时间相等于无限的‘存在’之方式”*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132页。。
但是,在存在论者和现象学家的眼中,时间是在场的、可理解的、可显现的——既然它在场并自行显现,就无论如何都与回忆有关。列维纳斯指出,时间通过滞留、回忆和历史编纂学恢复了所有的事物,在回忆中,没有任何事物会失去,每一件事物都在场或再现,成为一种在意识中的共时性聚集。于是,时间的历时性被损坏殆尽。因此,列维纳斯批评胡塞尔说,他把内在的时间性描绘成一种流动,在其中时刻一一经过。它们流动,但是它们被扣留。换句话说,在胡塞尔看来,时间在意识中流动,然而这种流动性却被滞留在回忆之中。犹如我们欣赏一段旋律,正因为声音的流动被扣留在记忆里,我们才能够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即一段旋律来欣赏。列维纳斯指出,胡塞尔将时间置入时限与在场的关系中,这样一来,“任何变化都可以在由保留(rétention)与前保留(protention)所支配的这一共同在场中重新找到同一性”*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123页。。通过滞留和前摄,“时间被聚集在现时之中,那些似乎要消失的被留下了”*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174页。。也就是说,由于回忆与期待,在时间中流动的事物统统都可以被唤回到意识的在场中来,成为共时性的展示。这里面只有同一性,而完全没有他者的容身之地。同时,列维纳斯也批评海德格尔。他指出,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意义体现在非人类的沉默言语中,这一“寂静之声”只有诗人才能听见,诗人将它转变成人类的语言。这样一来,任何涵义和可理解性在表现与在场中都可以实现了。从此,任何历时性都被排斥在外。“意义被想成揭示,想成为存在的表现。主体的心理现象从此包括了它的同时化、它的再现,而全靠这些,就没有什么东西还在外面了”*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180页。。换句话说,尽管海德格尔早已超越了意识哲学,而将时间看成是存在自身的运作过程,但是,一旦想要去领会与揭示存在的意义,想要把时间变成为一种在场与再现,就逃离不了共时性与同一性,在此情况下,他者同样无法藏身。列维纳斯说:“存在的显现属于存在的运动,其现象性是基本的,没有意识不能做到,对于意识而言,表现是被构造的。”*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131.
概而言之,在列维纳斯看来,从自身出发又返回自身的意识活动势必会形成一个有限的同一性整体,其中所有事物都是在场的、可显现的即处于“光照”之中的,因而是可理解的。无限则是思想所不能包含者,是有限中的溢出。如果时间一旦被纳入内在性的意识之中,通过“滞留”与“前摄”恢复为在场的,那么时间的历时性便不复存在,而变为同步化的共时性时间。“对于意识,过去总是一种现时之改变:如不到场,任何东西都不能发生”。“在意识中,现时之进程就理所当然地展现在一种同时性之中”*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258页。。进一步说,即便时间不被纳入意识中,但只要时间是在场的、可显现的,那么实际上它就仍然处于“光照”之中,就不可能不与意识和回忆相关联。
如果说现象学强调“起源”、“在场”和“现在”的话,那么,列维纳斯则提出,对他人的责任发生在“一个比任何可描述的起源都更加古老的过去”*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9.,“一个比任何现在都更古老的过去,一个从未出现的过去”*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24.。他之所以看重“前起源”的“过去”,其目的就是为了把“起源”推至一个不可企及之处,使之无从追溯,无法纳入意识之中,以此来抗拒现象学的“起源”和“在场”。列维纳斯指出:时间的流逝是不可回收的,它以不可表象、无法追忆的前历史的事情来抗拒现在的同时性。无法追忆并不是缺乏记忆的结果,似乎它没有能力去跨越大尺度的时间间隔,恢复过于久远的过去,而是因为它不能与现在通约。就是说,它无法将分散的时间聚集到现在,无法对付历时的时间*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38.。他说“历时性拒绝连接,它是不可整体化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无限”*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11.。
三、 言说VS将一切变为陈述对象的所说
列维纳斯发现,将一切事物及其变化聚集到意识中来,将历时性的时间同步化为共时性的力量就是语言。存在一旦被陈述,就会成为一种主题对象,成为意识中的在场被同一化,一切相异性就被暴力所剥夺。当然,这种立场遭到了德里达的批评。德里达说,当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就是言语的可能性时,是不是意味着话语本身就是暴力呢?根据列维纳斯的观点,“述谓作用乃是第一暴力。既然动词/存在和述谓行为在其它任何一个动词及任何一个普通名词中都被牵连,那么非暴力语言最多应当只是一种纯祈祷、纯膜拜语言,它只为了呼唤远处的他者而说出些专有名词”*德里达:《书写与差异》,第263页。。但是,德里达指出,这种所谓的语言对他者什么也不能提供,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意义。何况事实上,列维纳斯自己也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无论在《时间与他者》还是在《整体与无限》中,他都花了相当多的笔墨来描述他者,并且“面貌也是言语”*德里达:《书写与差异》,第263页。。
后期列维纳斯仍旧坚持了早期的基本立场,只不过他不再直接去描述他者,而是使用“别于存在”这样的词语来谨慎地避开存在论陷阱。不仅如此,列维纳斯后期花了很大篇幅来直接研究和讨论语言问题。他虽然没有明说,但从他后期所作的调整来推测,他应该也承认,德里达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如果继续使用存在论语言去陈述他者,就意味着用彼同一性去反对此同一性;但是,如果不使用某种言语,“别于存在”的意义又将如何被揭示出来?
列维纳斯在《别于存在抑或超乎本质》一书中区分了“所说”(the said)和“言说”(the saying)这两个术语,并深刻分析了“所说”在存在论与现象学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列维纳斯指出,“存在论的发源地就是所说”*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42.。他认为,本质(essence)是在主题中作为一个实体(an entity)而被命名的。提及本质与实体的关系,不得不关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众所周知,柏拉图对于经验世界的流变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只有永恒不变的“相”才是真正的存在。然而他却不能解释本质界(存在)与现象界(非存在)之间的关系。与此不同,亚里士多德则肯定变动不居的现象界的实在性。为了解释复杂多变的经验世界,他尝试建构一个逻辑性的框架,来包容存在作为存在的多种形态。他发现了逻辑和语法与存在论的关联性,发现了以实体为核心的十对范畴的存在论意义——通过这十对范畴,人们就能够陈述一个实体运动、数量、场所等多种形态。自此,人们开始把对事物及其变化的认知与陈述纳入严整的逻辑结构之中,事物的差异性和时间的历时性被武断地裁剪掉,西方哲学逻辑化概念化的特征正式达成。“在海德格尔之后,essence已经回复到了其原本‘存在之真理’的涵义,莱维纳斯也是在‘存在’的意义上来使用‘essence’这个词。”*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第193页。存在是动词,是行动;存在物建立在存在自身的运作过程中。但是,在列维纳斯看来,“这已经是存在的某种阐释,已经是一种遮蔽”*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137页。。“海德格尔的论说关键在于,它提出了存在是任何意义的本源。这立即就导致了以下一点,即人们不能超越存在而思想”*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143页。。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列维纳斯对语言和存在论与现象学之间的必然联系作了进一步分析。他指出,在本质与实体之间有一种模糊微妙的联系,以至于两者可以混用。在一个陈述中,实体可以作动词性理解。比如,“使变红”(redden)这个动词表达的是一个东西由不红变红、由浅红变为深红的变化过程。通过动词,我们就可以描述事件、行动和变化,于是,一切都成为可讨论和可陈述的了。在此,本质不仅可以被传达,而且能够在谓词性陈述中被时间化。列维纳斯指出,动词to be 是将历时性同步化和时间化的领域,也即是回忆和历史编纂学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本质成为一种在叙述中被聚集、被同时化、被呈现的现象。他洞察到,进入存在和真理其实就是进入所说,存在及其意义不可分割,它们是被说出来的。“这种所说的还原在陈述句中呈现”,“它重新统一成结构;它将已经运作起来的东西重新结构。还原将再次使别于存在如同永世”*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44.。这就是说,即便不是逻辑化、概念化的论述,而是诗意的叙事,只要进入“所说”,进入谓词性的陈述中,一切都变成了主题和论说对象,被描述,被共时化,被凝固化“如同永世”。
既然存在论与“所说”纠缠在一起,那么,逃离存在论与现象学是否就意味着切断语言?“别于存在”的意义将如何揭示?在此,列维纳斯直面德里达的批评,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建立先于存在论的表达和意义。”*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46.
列维纳斯认为,“言说”是一种先于语言的前语言,它存在于语言符号和语言系统出现之前。“言说”甚至不在意识之中,它在一切对象化的认知之前。它是不可回收、不可表象的前存在论的“过去”。这种原始或者说前原始的语言无需长篇累牍的阐述,漂亮辞藻的装饰,利害得失的算计,直接就是一种对邻人的责任,对他人的回应,就是被扣为人质的状况。因此,他说:“与他人的责任关系的涵义如同言说。所谓言说,在载荷着信息、内容的任何言语之前,在作为所言的言语之前。”*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193页。“别于存在在言说中被陈述,而这个言说必须是未用语言表达出来的”*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7.。他还指出,“言说”固然是交流,但它更是所有交流和暴露的前提,因为沟通的开启是在“言说”中实现的。它不是铭刻在“所说”里,传递至解释并被他人解码的内容。它是在对于自己的危险展示中,在真诚中,在解除其内在性和抛弃一切遮蔽中,将自己裸露于创伤和脆弱性之前。但是,这种前原始的“言说”后来被移植进了“所说”之中,从此“言说”从属于主题。由于主题化,能够说出一切的“所说”被传输到我们面前,存在的本质、理论和思想的共时性被转达至我们,“言说”被背叛了。现代语言引导着我们脱离别于存在或主题之外的他者。然而,列维纳斯指出,“陈述并没有耗尽言说中的‘有’”*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6.,从“所说”中挽救抽取出“言说”仍然是有希望的。
“我”对他人的责任心为什么会成为“言说”,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给予”中呢?究竟它比“给予”多了些什么?单纯的“给予”是一种结果,无关乎真诚,它可以是毫无保留地“给予”,也可以是有所保留地“给予”。“言说”则不同,它是不断地自我开放,完全彻底地将自己交付于他人,随时准备被传唤到庭(comparution)。在列维纳斯看来,这就是真诚性,正是这种真诚性使“给予”变得毫无保留。他说,在此“言说”不是对话,而是“见证”:“向我为之无限打开自身的人的无限之见证。”*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232页。“言说”是一种宣称,一种不断自我开放的开口,一种“被围困的引渡”。“言说”就是面对他人,暴露自己,从众人中走出宣称“我在此”。这是作为被告被传讯到庭,是我对他人责任的无可躲避。列维纳斯指出:“言说完成了应该和给予结合在一起的真诚性。它和给予是不可分离的,因为是它打开了保留之库。”*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236页。就是说,“言说”表明了一种毫无保留的开放与暴露,唯其如此,“给予”才是可能的。真诚的“给予”不仅是没有自我,而且还是不由自主地自我舍弃。舍弃享受中的自我满足,从自己嘴里将面包夺走给予他人。这种开放的态度不只是掏出钱包,而且是打开家门,“让饥饿的人分享你的面包”,“将可怜的人迎接到你的房间”。在列维纳斯看来,在对待他人的真诚性方面,“所说”要虚伪得多。在“所说”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美丽动人的词语,其中“信息在交换,祝愿在传播”,唯独“责任心在逃逸”。真诚性则是一种没有所说的言说,一种“为了什么都不说的说”,“一种债务,一种自我之揭露的承认”*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236~237页。。
另外,“言说”还表明了一种极端的被动性。列维纳斯说,言说行为从暴露给他人的至高被动性中被引进,而这种暴露就是对他人的自由精神负责。在传统哲学中,这种自由精神属于主体,主体是自己及其宇宙的主人和宰制者。这种关于主体的定义在列维纳斯这里被彻底颠覆和颠倒了。他指出,“言说”意味着对主体的废黜或去位。善并不是主体的自由意志。其实,并没有谁生来就偏爱行善。主体此前一直在自己的内在性和同一性中活动,突然,他人烦扰“我”,把“我”从孤独中唤醒。他似乎“一下子没有了保护,成了赤贫的悲惨者,好像就这样一下子被托付给了我”*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159页。。于是,“我”必须回应他,“我”无法逃避对于他的责任。在这一责任中,“我”的整个主观性都为他人而构建,自我的港湾就是“为他人”,这就是所谓“为他人的自我”。此时,传统意义上的“自我”已经不能确立,相反,自我被流亡和被放逐。“‘我在此’意味着我以上帝之名,服务于那些凝视着我的人,没有任何自我认同”*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ThanBingorBeyondEssence,p.149.。“我处于作为被告的宾格(accusatif)地位”“我确立不起来,而是要被废黜,要被代替,要为他人、为他人的过错而受苦、而遭罪,甚至去赎罪”*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193页。。唯其如此,列维纳斯指出,这里面表现了一种“他律”,一种“非异化”、“非奴役”、非“独特性之丧失”的他律。至此,列维纳斯借助“言说”,使“他者伦理学”最终达成。
四、 结语
列维纳斯的哲学目标就是要摆脱存在论与现象学的束缚,以建构面向他者的伦理学。他强调,“别于存在”的他者只能与有限中的溢出和过剩——无限,逃离同时性的真正历时性,没有“所说”内容而只有一种废黜主体地位、彻底开放自我的伦理宣称——“言说”相关联。
无论列维纳斯反对存在论与现象学的再度探险是否完全成功*一些学者并不认为列维纳斯已经成功超越了现象学,相反,他们认为列维纳斯思想不过是对海德格尔现象学存在论的另类解释,“亲近”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意向性。然而笔者却认为,不仅列维纳斯明确将克服现象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为此付出毕生心力,而且就其后期思想来看,已经远离了现象学的本来含义。如果仍然将其哲学视为现象学中的另类,不免显得牵强。,它都深刻地影响了法国乃至整个欧陆后现代哲学的研究旨趣和基本特征。后现代主义批判同一性哲学,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理论资源无疑来源于列维纳斯。德里达关于意义“延异”和解构的伦理面向的思想,及其对海德格尔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明显受到了列维纳斯哲学的启发。利奥塔的差异理论及其对所谓“元叙事”的怀疑,鲍曼的爱抚伦理学及其对回归“为了他者”道德的呼吁,均受到了列维纳斯思想的深刻影响。甚至最近20年来声名鹊起的几乎所有激进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列维纳斯的名字相联系。毋庸置疑的是,列维纳斯已成为当代法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作者地址:陶渝苏,贵州大学哲学系;贵州 贵阳 550025。Email:taoyusu@163.com。
Anti-phenomenology and the Re-exploration:Levinas’s Latter Thought
TaoYusu(Guizhou University)
Abstract:Levinas holds that ontology and phenomenology are intertwined,for that being is present and must be appearing.Ontology and phenomenology inevitably lead to totality and identity,which suppress “the other”.Inspired by Derrida’s criticism,Levinas in his latter thought proposes “otherwise than being” against ontology,diachronic time against the essentialized synchronic time,“saying” against “the said” that turns everything into objects of representation,thus begins to flee from phenomenology and explore again.
Key words:diachrony; Levinas; phenomenology; ontology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4.010
基金项目:●贵州大学科研成果奖励基金(2014);贵州大学重点建设哲学学科群项目(2016)
●责任编辑:涂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