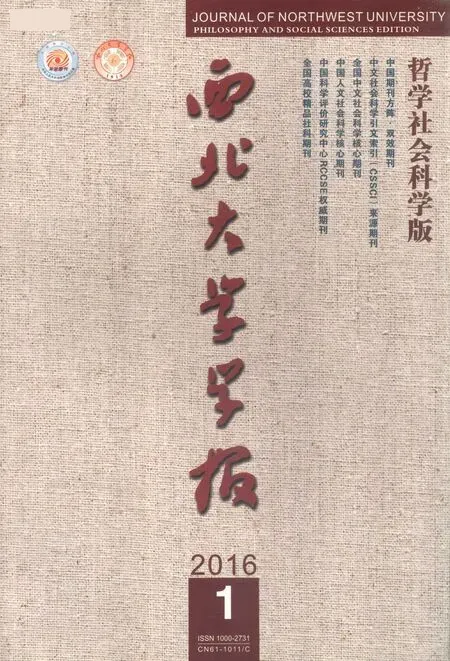论现代性语境下人类时间意识的倒转、断裂与重构
赵立敏
(1.衡阳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2.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
论现代性语境下人类时间意识的倒转、断裂与重构
赵立敏1,2
(1.衡阳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衡阳421002;2.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100872)
时间不仅是一种尺度,还是一种意义的源泉。不同时代的人们总是从时间观念中构建他们看待世界和生活的不同方式。本论文指出不同时代的时间意识导致了这三种时间总是处于一种微妙的、相互争夺的张力关系之中,也造成了意义与真理、延续与变迁、传承与更替、静滞与发展的不同时代导向。传统社会以“过去”为中心,强调回归和经验,现代社会以“未来”为中心,以进步主义理念为旗帜,强调发展与规划。但是现代时间意识过度地从“未来”中攫取意义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何重构新时间意识,仍是人类发展的重要议题。
时间意识;现代性;规划、意义
在西方社会理论和哲学语境中,现代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一般来说,现代性是指16世纪以来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事实和观念事实”[1](P10),这个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凸显近现代社会是一个与传统社会迥然有异的社会,它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观念上与过去断裂,从目前关于现代性的种种讨论来看,对现代性的看法十分不一,对它的后果评价有好有坏,现代性既意味着理性化、世俗化、主体性崛起,也意味着无序、短暂、流动和共同体的没落。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后现代性作为与现代性相对的一个范畴被提出来,按照利奥塔的观点,后现代性的特征表现为碎片化,小叙事取代了现代社会中的宏大叙事。而本文将尝试从时间的维度来阐述过去、现代与后现代的境况。
与传统社会的时间意识不同,现代的时间观也是现代性的一个表现,而且它还是推动其他现代性进程的一种内在动力。过去的时间总是与空间联系在一起,时间是以发生在某一空间的具体事件来规定的,正如传统社会描述时间的语句“一炷香的功夫”“一顿饭的时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等,过去的时间总是伴随着一种生命体验,是一种生物时间和相对时间,康德(Immanuel Kant)、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为代表的学者主张这种时间观。随着机械钟的发明,机械化的时间把过程分割成精确描述的一个个点(时、分和秒),时间从具体的空间和事件中抽离出来,成为了虚化的时间,它是一种没有生命体验的抽象时间,是一种物理时间和绝对时间,这种时间观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力学为依托,成为现代社会主导人们生活和工作的主要时间观。在现代社会,时空的抽离和虚化被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视为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他认为时间从空间的抽离导致空间的进一步虚化,即“不在场”的空间大规模诞生[2](P14)。吉登斯关于现代性时空的描述为现代性研究增添了新的面向,但是他的现代时间观主要是从客体而非主体的角度描述,他考察的是时间而不是时间观。笔者把时间观和历史观联系起来,提出人类的“时间意识”概念。所谓的“时间意识”是指一种看待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时间观念,它处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不同的“时间意识”决定了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向和方式不同,也决定了不同时间所蕴含的资源和能量各不一样,所以“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心中的位置和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尽管时间总是不断向前流逝,但是人们对时间的欲念和意义索求却并不一定与时间的流向同一,甚至完全可能与时间反向。在传统社会,人们习惯于回归“过去”,未来则是“上帝的时间”。在启蒙时代,人们习惯于面向“未来”,“未来”是人可以控制的时间。当过去和未来都从人们的手中逃逸时,人们又开始关注“当下”。
一、倒转:传统和现代的时间意识
现代时间的诞生与进步观念密不可分。自进入19世纪以来,以英美等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崛起为标志,人类迎来了一个所谓的“进步时代”,“进步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广泛接受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进步主义学者总是这样宣称:社会过程总是沿着一条有迹可循的进步路线向前发展。事实上,自古希腊思辨哲学的萌芽到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再到文艺复兴以及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的爆发,都闪烁着进步观念的思想火花。但是只有在工业革命时代伴随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现代进步观念才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意义,而这一不同意义又主要体现在人们的时间意识上。
梳理进步理念发展的脉络可知,现代进步观念的诞生源自传统时间与现代时间的分离。传统的时间主要是以“过去”为重心的时间,人们总是不停地从“过去”时间中索取意义,并以“过去”决定看待世界与生活的方式。正是基于“向后看”这一特性,这就决定了传统社会是一个“仪式社会”或“文化社会”。而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则正好相反,人们更多地是从“未来”时间中去获取意义,去构建人类的体验,这就决定了现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社会”或者“规划性社会”。
与“向后看”的“回归性取向”不同,现代性时间主要是一种“向前看”的“前瞻性取向”。在传统社会,“过去”“现在”“未来”一定程度上是分离的。而到了现代社会,“过去”“现在”“未来”被打通,并一以贯之地指向了“未来”。当现代人回顾过去时,他们把历史过程中发生的那些看似随机、偶然、零散的事件串联起来,从中发现这些事件可以通过因果关系编织在一条向前发展的线条之中。从一个总体的历史时间维度来看,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或者文明和文化都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机械到有机不断进化的时序。“现代时间意识”还认为:既然社会和历史是沿着一定的轨迹向前发展,自然这种发展也会从“过去”一以贯之地延伸向“未来”的空间,所以“未来”也同样遵循进步的路线可以被探寻和预测,未来可以由过去推导而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事实证明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测和控制能力确实大大增强。大部分人都憧憬着未来是美好的,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会把人类引向一个物质越来越丰盛的阶段,还会迎来一个文化繁荣、精神自由、人类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
自从科学的强劲发展加强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测能力后,人们就由“向后看”更多地转向了“向前看”。这种朝着现代性转向的背后其实质是“过去”与“未来”关系的倒转,即“未来”已经变成了一个比“过去”更加重要的时间,人们从对“过去”的回归性要求转向一种不断对“未来”的规划性要求,“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借助知识环境的反思性组织,未来被持续不断地拖入现实之中。”[3]概而言之,以工业革命为转折,如果说工业革命之前的人们的生活还主要依赖过去,那么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人则更加注重对自身和社会未来发展的预测和控制,未来开始在现代人生活中占据了比过去更加重要的位置。
从“对未来的预测”开始转为 “对未来的全面规划”则是科学发展的又一次极度膨胀。从17世纪科学开始兴盛后的两百年时间里,科学对未来的控制是基于客观预测的基础上,也是基于历史和相信一套贯穿于过去与未来的客观规律在无形中发挥支配作用的基础之上,这至少说明人类在一定程度上还无法完全摆脱客观环境及历史的支配。但是进入20世纪后,人们对未来的规划和控制几乎已经到了完全自主的地步,甚至已经到了无须基于历史和规律的地步。例如“原子物理学最重要的新成果是认识到可以将完全不同类的自然规律应用在同一物理事件上,而不会引起矛盾。这是由于以下事实:在一个建立在某些基本理念之上的规律系统中,只有某些特定问问题的方式才是有意义的,从而,这样一个系统就有别于允许提出不同问题的系统。”[4](P33)这说明了 “科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套有效的假言命题系统,它随着产生的结果而变化,其有效性不取决于它‘显露’了什么,而在于它‘是否有用’。”[4](P34)换言之,科学的使命已不再关注“是什么”,而关注“为何”,从对真理的揭示转向对过程的揭示,从过去对意义的强调转向现在对目的和功能的强调,科学理论得以成立的基础已不在于它真的揭示了什么永恒的真理,而在于它对于解决和维护社会问题及秩序的成效,这就是现代科学的转向,这一转向使得人们变得越来越从功能和行动的方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事物本身的内在价值和规律去考虑问题,基于此,“未来”便被纳入到对人类社会的功能性建构之中。
现代科学对未来的控制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今天一个人自诞生之后甚至从还未诞生之时就开始了或被开始了对自己的教育规划、职业规划、婚姻规划、养老规划等人生计划。我们不仅规划自身,还规划我们的后代。各种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金融保险体系、教育服务体系、卫生防疫体系等都是建立在对“未来”的预测和掌控能力大大增强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未来”的风险计算、评估和有计划的规避措施从而使未来符合人们预计中的期望。在古代情况则恰好相反,人们难以预知“未来”,“未来”也被等同为“未知”,被认为是不确定的、充满风险的。人们赖以生存的依据在于“过去”或传统,所以来自祖先的权威和世代相传的经验是他们看待世界的主要方式。然而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对未知命运试图加以掌控的企图始终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冲动,也是面对周围环境自我保存的最基本要求。面对这种生存意识和未知的风险与人本身的渺小无知带来的无力感的内在张力,于是人们把预知未来的力量交付给了上帝或神灵,通过古代巫师、先贤圣人或宗教领袖与自然或上帝的神秘交流以及在他们的沉思冥想中,人们获得了关于未来的种种征兆,然而这些上帝或神灵的代理人只能“预知”而无法“改变”这种宿命论式的未来,未来的真正掌控者是神或上帝的意志。尽管古人也曾尝试改变命运,但是无论他们怎样行动都会有一疏漏,都终究无法改变这种命定的未来。相反,现代社会中“未来”的真正掌控者已不是上帝或神灵,而是人类自己。“未来”完全由人类所操控,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塑造未来。然而根据卡尔·波普尔(Sir Karl Raimund Popper)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的见解,由于人们能够预测未来,所以就会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未来,从而改变未来发展的方向使之符合人类自身的期望,这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未来最终的样子并不像人们当初的预测那样,结果造成了物理学所说的“测不准”问题,在波普尔看来这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5](P78)。
与古代通过巫祝和神启的方式预测未来不同,现代人通过科学对自然及社会规律的掌握来预测“未来”被证明是更加精准有效的方法。不仅是过去,连现在和未来都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严格监测体系中被加以规整和控制。人们总是满怀一种对未来的期待视野,而且这种期待视野通过占有过去加以实现。
二、断裂:两种时间意识的后果
当人们凭借科学的发展加强了对自然和社会的控制、规划和改造的同时,人们也遭到了自然和社会的反制。而这种反制的原因恰恰来自推动科学发展本身的逻辑——理性反思。理性反思的前提是必须把反思之物对象化、客观化,通过与反思之物保持一定距离,人们才能够看清所谓的“实在”。现代性反思的特性在于它既是一种回溯性的检视,又是一种前瞻性的计划。理性反思把“过去、现在、未来”连接起来,“现在”由“过去”发展而来,同时又指向“未来”。在理性反思的要求下,“过去”本身的现时性或本真性意义就此遁隐了,“过去”的价值就只剩下作为“未来”的需要而成为被未来不断索求的“材料”。在对“过去”与“未来”的省思中,古人总是把历史与自然统一起来,认为历史是对自然之永恒的投射,是人类渴望像自然一样不朽的替代物,从而人类也通过历史获得了一种类似自然的永恒性[4](P25)。古人在历史中获得的真理其本质是自然这一伟大存在的启示和流露。真理也就是自身显露的东西,“无论是神圣真理和理性真理的揭示,都不言自明地被理解为遵从人与世界关系的令人敬畏的简单性。”[4](P27)人只要感受和顺应自然显现出来的那些现象和变化就被认为是顺应了真理。在中国的朴素哲学中,真理即 “天道”就说明了真理对古人的显露是极其自然、简单和诚恳的,真理就是如其所是的东西。然而随着理性的胜利,理性开始对人们所见和所听等一切感官不再信任了。在现代人看来真理往往隐藏在感官背后,把感官或经验视为“对真理的直观”这种古老哲学显然不再适宜现代科学探索的要求。现代人认为那种多变的、瞬间飘渺的感官或经验恰是对永恒真理的扭曲。“自然科学的崛起,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都似乎是由我们的感官自身不能发现真理这一发现所释放出来。自此之后,由于确信感觉不可靠和随之相信纯粹观察不足以发现真相,自然科学转向了实验。”[4](P54)也正是基于对感官直观不信任这一前提,理性反思才变得如此迫切。“人如果要追求真理与知识,就不能相信感官所给予的证据,也不能相信精神的‘天赋真理’,也不能相信‘理性的内在之光……’”[10]一切都必须通过反思以及对反思本身的反思的拷问。总之,真理获得的途径从古代的“直观”和“启示”已经转向了现代科学的“理性”和“实验”。如果说古人对自然的永恒性保持了一种油然而生的敬畏和融入,那么现代人对自然的态度则是一种凌驾和抽离,自然不再被视为那个具有永恒性的真理性显示,而是被视作对真理的遮蔽故需要被置入反思的框架之中加以把握和改造。自从古人对“过去”的“看”被以“未来”为指向的理性反思的“看”取代后,这种新的时间意识确实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化,然而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却说道:“进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进步。”[6](P98)因为现代的“时间观”在带来更加精确地预测和控制的同时,也带来了极为负面的东西,即古人在以“过去为中心”的时间意识中获得的祥和与宁静已经被无节制的对未来的征服冲动所取代了。在古代和现代的两种“时间意识”背后其实质是“意义”与“真理”的殊途,如果说古代对过去的富于直观性和启示性的“看”主要产生了“意义”,那么近现代反思性的“看”则是为了“真理”,而后者之于前者的“看”的方式的转变其实质是“真理”对“意义”的过分压制和侵夺。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曾认为现代社会中理性作为一种总体性力量已经开始侵入并统治人类的三个基本领域——认知领域、规范领域和审美领域。这三种领域分别对应着真、善、美三种价值体系,且这三种价值体系本应根据各自的运行逻辑发展,例如认知领域遵循的是理性逻辑,规范领域遵循的是价值逻辑,审美领域遵循的是趣味逻辑[7](P10)。如果说“求真”追求客观的“真理”,那么“求善”和“求美”则追求的是“意义”。自从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理性逻辑作为唯一的运行逻辑统治了人类的三大领域之后,历史本身的自足性就被掏空了,意义就不可避免地衰落和丧失,代之以一切根据都被一种工具理性计算的目的论来衡量。在科学时代兴起之前,我们发现古人常把宇宙的真理和意义统一起来,“真理”在自行显露的那一刻,“意义”也获得了圆满。而在科学时代“真理”则完全替代或取消了“意义”,进而又取消了“真理”,因为现代科学所标榜的“真理”已经蜕变成一种追求功能和目的的纯粹“有用性”。
意义的丧失,也就意味着信仰和传统等价值的失落。正如吉登斯指出的那样:“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9](P9)人类在滥用工具理性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和政治利益的同时,已经忘却了对“人”本身这一根本性的关切,这就是现代科学产生的本质性危机。这一危机带来的后果是人自我实现的各种可能性被取消。自从“未来”被人类严密地控制和规划之后,未来开启的那种无限可能的空间就此封闭。本雅明曾强调社会过程中事件的偶然性和现时性,认为 “一切过去都有一种无法实现的期待视野”[8](P268)。然而在现代社会一切过去的可能空间和期待也在人类面前封闭,所有的过去都被单一的未来所占有。在对未来的规划体系中,人也成为了工具理性的对象而被规定了。正如前文所述人自诞生之后甚至从还未诞生之时就开始了或被开始了对自己的教育规划、职业规划、婚姻规划、养老规划等计划,然而这些规划最终变成了规训,完全忽视了每一个的具体性和个人自身的内在需求。更有甚者,人的欲望、冲动、个性等多样化的人性都必须整合进社会的角色期待和结构之中,这样社会才能以更加有效的方式运行,经济才能更加快速地发展。人变成了社会结构中的一个个原子和生产环节中的一个个要素,“顺从主义”成为了这个社会编织成的一张泯灭人性的大网。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的“异化”、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单向度的人”、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的“文化工业”、福柯(Michel Falcault)的“全景式监狱”、默顿(R.K.Robert King Merton)的 “训练有素的无能”等都是对规训的描述。以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马克思、弗洛伊德(Sigmunol Freud)、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人为主,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其跨越的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让我们意识到科学的本质性危机给人类带来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很多社会理论家和现代艺术家希望重新回归人性,要么以先锋主义为代表主张用审美来取代理性,要么以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为代表主张用信仰取代怀疑和虚无,要么以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尼采和心理学派为代表主张回归到人类本能冲动和原始欲望的感性来取代超感性,不管这些理论家主张的方式如何,其目的都是希望重新寻回失落的“意义”用以对抗日益被工具—目的论所扭曲的“真理”。
三、追寻:重构人类的时间意识
显然,科学发展的逻辑在“真理”与“意义”之间制造了无法缝合的巨大鸿沟,它产生了这样的悖论:科学既带来了人类的解放又把人类放入囚笼之中,既带来了物质的丰盛又带来了精神的匮乏,既带来了最大限度的创造又带来了全球性的破坏。近代以来,“未来”被认为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之下终于可喜地处于人类的全面掌握之中,但恰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未来”反而越来越远离人们的规划,整个社会变成了“失控的世界”[9](P25),各种形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成为了现代社会的痼疾,生态环境的破坏、贫富差距的扩大、地区冲突的频发、经济的衰退等似乎意味着“未来”甚至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容易逃离人们的计划。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中乌托邦的力量已经穷竭,“未来”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否定的东西,已经由一种鼓舞人心的事物变成了一种令人丧气的事物。“生产力变为破坏力,计划的能力变为潜在的干扰的能力……近代曾经从中获得自己的自我意识和自己乌托邦期望的那些增强影响的力量,事实上,却可以使自主性转变为依从性,使解放转变为压迫,使合理性转变为非理性。”[10](P52)
在经典进步理论中,传统被归入前现代而被贴上落后、愚昧的标签,古人以直观感悟真理的方式在今人的科学观看来似乎浅薄而幼稚,来自祖先的权威和世代相传的经验对于那些正致力于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而言经常被视作应被清除、推倒的障碍。然而,社会具有不可化约的历史维度,必须强调传统的特征,尊重传统,因为传统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它的进步性。如果说科学总有一种面向“未来”的预测和控制冲动,那么传统则有一种面向“过去”的回归冲动,这种回归让人类的精神有所依赖和归宿,不至于陷入虚无。总之,“面向未来”和“回归过去”是人类自我保存和升华的两种基本方式。
未来与历史传统正是现代和传统的两种时间意识的对应之物,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困境就在于他们的时间意识总是无法很好地调和“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三种时间总是处于一种微妙的、相互争夺的张力关系之中,而人类立足于某个时间的一端,从而制造了时间的断裂和鸿沟。传统的时间意识立足于“过去”,既带来传承与延续,也带来了静滞与落后。现代的时间意识立足于“未来”,则带来了扩张、变迁与破坏。在现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程序原则已经脱离了人们对道德原则的需求,以至于启蒙时代那个被人们所牢牢把握的“未来”也从人类的手中逃逸了。面对“未来”和“过去”的双重失落,现代人或者要求重新回归传统和历史,或者要求回到“当下”或“现在”,然而对“当下”的过分强调则可能导致“历史”和“乌托邦”两种力量之源的枯竭,一味地沉浸在当前的感官体验之中,失去了“回归历史”和“面向未来”的冲动,也将是一种充满危险的偏颇之举。总之,如何重构新的时间意识,如何在“过去、现在、未来”上获得一种平衡,从这三种时间中吸取力量,重塑人类的生活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并进一步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这仍是人类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议题。
[1] 汪民安.现代性[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0.
[4] 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M].王寅丽,张立立,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11.
[5] 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杜汝楫,邱仁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6] 斐迪兰·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远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 哈贝马斯.西方理性主义[M]∥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 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M]∥汉娜·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9]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0] 哈贝马斯.新的非了然性——福利国家的危机与乌托邦力量的穷竭[M]∥苏国勋,刘小枫.社会理论的政治分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责任编辑陈萍]
The Reversing and Breaking and Re-constructing of Modern Time Consciousness in Modernity Discourse
ZHAO Li-min1,2
(1.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HengyangNormalUniversity,Hengyang421002,China; 2SchoolofJournalism,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Time is not only a kind of standard but also a resource of meaning. Different people from different times always treat their world and lif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ime sense, and attempt to get existing value and developing power. Different time sense resultin a kind of subtle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which includes: significance and truth, continuity and change, static and developing. In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past lies in the center, and tends to pursue history and experience. In contrast, modern society is based on progressive idea, and emphasizes the future, developing and regulation. However, over emphasis on the future also leads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Therefore, we should consider how to re-construct time sense.
time sense; modernity; regulation; value
2015-04-11
赵立敏,男,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从事文化和政治传播研究。
【哲学研究】
B821
A
10.16152/j.cnki.xdxbsk.2016-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