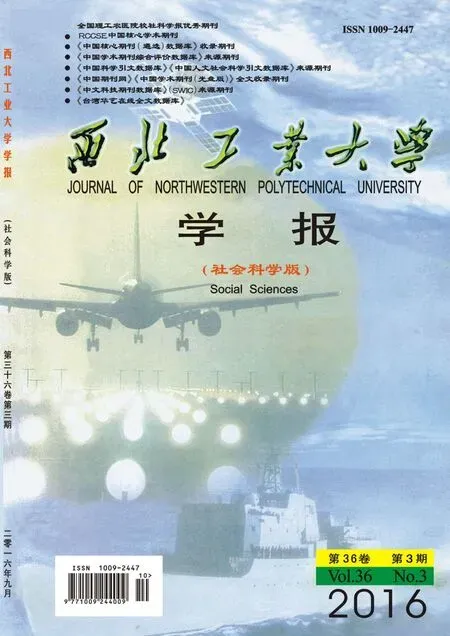儒家信仰的合理性及其当代价值
孙长虹,徐朝旭
(1.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05;2.闽江学院思政部,福建福州350121)
儒家信仰的合理性及其当代价值
孙长虹1,2,徐朝旭1
(1.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05;2.闽江学院思政部,福建福州350121)
儒家信仰从“天人合一”的本体出发,认为个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促进文化生命、民族生命乃至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它相信个人可以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得到不朽。在儒家信仰中,生命与精神、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精神性是人类生命永恒的需要,道德是人类生命的存在方式。儒家信仰面向人的理性开放,面向科学、社会发展的方向开放,具有合理性的内核,能够与其它文化进行对话交流,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其价值和意义。
儒家信仰;生命;精神;道德
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着信仰缺失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统信仰的解构,使得现代社会中信仰的确立缺少了文化和心理上的“根”。信仰对于个人和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而且在终极层面上关系到人们的价值观和意义追求。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出现了问题,把很多本应该继承发扬的东西都给随意地否定了。无论什么样的背景下,斩断自己民族的文化根源,既无可能,更无必要。可喜的是,近些年来,我国开始日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发掘传统儒家信仰资源,为当代的信仰建设提供有益的资源是非常有意义的。儒家信仰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信仰?为什么在任何时代背景下其都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和践履者?千百年来其怎样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了传统社会的精神气质和面貌?在现代社会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何在?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问题。本文试图在现代学术视野中,阐释儒家信仰的合理性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价值。
一、儒家信仰之生命性
儒家信仰具有宗教性,实质上是一种天地信仰、生命信仰。祭祀是人类信仰的最早的表现形态之一。儒家有“三祭”,包括天地、祖宗和圣贤,与一神教相比,儒家信仰中拜祭的对象比较杂多,并且处于不断地增加之中,虽然如此,它有贯穿其中的核心内容,这个核心是生命。天地是普遍生命的创生者,祖先是个人特殊生命的血脉来源,圣贤为我们指明了生命存在的方式。对天地的祭拜,表明对精神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对圣贤的祭拜,显示对文化生命的注重;对祖先的祭拜,展现了对自然生命的尊重。“三祭”说明儒家既有天地信仰、又有祖先崇拜、道德崇拜的痕迹,这三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即对生命的注重。因而,儒家信仰实质上是一种深刻的生命信仰,不仅体现为对个人生命、人类生命的尊重,也体现为超越个人生命甚至人类生命的一种广阔的生命观。
在生命观上,儒家信仰与世界上其它宗教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儒家是重视生命、重视现世的信仰,它认为人的不朽可以通过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在现世实现。这与世界上一般宗教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费尔巴哈认为,宗教体现了人类的恐惧感的需要,诸如对死亡的恐惧。的确,世界上各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重视对死后生命的安置问题,而死亡几乎从来不是儒家关注的重点,“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在儒家看来,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立德、立功、立言,实现对死亡的超越,达到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德性、功绩和言论而影响他人、后世,达到不朽,实现从有限向无限的转换。所以孔子评价自己为:“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在儒家看来,人之价值和意义在于发奋努力实现自己的生命使命,因而其自始至终蕴涵着昂扬的乐观主义和进取精神。
生命的不朽不仅体现在个人通过立德、立言、立功来得以实现,而且也体现在生命的繁衍生息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集·西铭篇》)在儒家看来,生命并不仅指个人的自然生命,而且指文化生命、民族生命、人类生命以及宇宙生命。“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其实强调的是个人对传承文化生命所担负的责任。虽然个人的自然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文化生命、民族生命、人类生命是与天地同在的无限的存在者。这种思想体现了非常广大的、深刻的、超越特定时空的生命观。在空间上,生命不是狭隘的自我生命,而是开放的,是面向他人、社会、文化、人类以及自然宇宙开放的;在时间上,生命是流动不息的,整个人类生命乃至宇宙生命薪火相传,个人生命处于整个生命之流之中并在其中获得意义和价值。
在儒家看来,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需要人自身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开放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保存和发展,也要促进其他生命的保存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意义和价值。有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精辟表达了儒家的文化、政治、道德理想。这种理想说明儒家的个人实现绝不局限于狭隘的范围,而是扩展到社会乃至宇宙。唐君毅认为,在儒家思想中,“吾人生命之扩大,心之性情之流行等,要不能安于此限制之内,而终必将洋溢出于其外,且进而洋溢出于特定的自然物,如禽兽草木等之处。因此儒家之心情,即达于另一种形而上的及宗教性之境界。此即对天地、祖宗及历史人物或圣贤之祭祀崇敬的心情。”[1]儒家精神不仅包括对人类生命的关切,也有对文化生命、自然生命和宇宙生命的关切,这种宗教精神无疑具有最宽广的情怀。就如施韦泽所说的:“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识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识。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对他来说,善就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2]儒家信仰对生命的态度与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存在内在的相通之处,都体现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和保存、发展生命的积极意识。这说明儒家的观点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思想的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
并且,在对待人类生命和自然界中其他生命的关系问题上,儒家既看到了人与万物的联系,又看到了二者的区别。人与万物都是天地的创生物,但是,人与天合一,天的创生性是由人来体现和实现的。人类应该在宇宙自然中承担起创生的责任,这种责任绝对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建立在尊重自然秩序基础上、促使其良好运行的一种责任观。这样,与其他宗教相比,儒家信仰在对待生命问题上的态度更趋理性。在儒家信仰中,绝对不会出现佛教中的舍身饲虎、割肉饲鹰,也不会出现基督教中杀子献祭,因为这违背了对生命的尊重以及自然秩序。因而,儒家信仰中的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在生态保护、动物保护上究竟应该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当代的学术争端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困境。而在儒家看来,既要尊重其他生命,又要发挥人在保持和维护自然秩序方面的能动作用,而不能陷入究竟是人类中心还是非人类中心的二元对立中,这种综合思维方式深刻影响到价值观,将会为现代社会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一条可供借鉴的路径。
二、儒家信仰之精神性
儒家信仰注重生命的精神性,即重视精神追求、精神境界。孟子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其实就是强调的精神性,强调涵摄天地,超越个人、与天地齐的宽广境界。儒家精神强调尽心知性,身体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不止于此,还要与天地参。“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儒家精神性追求的集中表现。芬格莱特认为儒家“生活中至高的价值和尊严,以及生命的神圣性,都取决于实现卓越的人生之道的全心全意的精神和技艺。”[3]这样看来,儒家注重实现生命的精神性,这种精神性有着独特的蕴涵,主要体现为生命的创造性。
儒家所强调的创造性精神具有本体上的依据,即“天人合一”。在儒家信仰中,天地具有创生万物的本性,人与天地合一,也应该具有创造性。当然,这种创造性并不在于创生万物,而更多的在于顺从天意、协助天意而致力于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从这层意思上看,儒家的创造性的确不在科学创造上,而更多的是在顺从自然规律上,不过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当代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新一代儒家学者已经开始注重儒家思想与科学的契合问题。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了儒家创造精神在生态意识方面天然地与发展中的科学精神的一致性,说明了其可贵的人文价值。
儒家信仰的精神性与现代西方对宗教形式的超越具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大卫·艾尔金斯提出了在传统宗教之外构建个人生活的主张,他认为:“精神性是所有滋养自己的灵魂、发展自身的精神生活的人们都可以接近的,无论他们是在传统宗教的围墙之内还是之外。”[4]儒学的精神性注重个人与天地的直接交流而无需借助特殊的形式,比如特殊的僧侣集团等,从而使得其精神性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形式的束缚和偏执的可能性,具有了超前性,为其在现代社会发挥价值和作用提供了基础。
儒家信仰中的精神性并不排斥神秘性,而是主张去体悟天人合一的本体所带来的人的生命的精神价值和深刻意蕴。这种观点与西方近年来出现的对宗教的超越的观点相类。艾尔金斯认为:“精神性的本质特征是神秘性,这一事实在科学和物质的时代容易被忽视。精神性植根于灵魂,由对神圣的体验所培育,并助长了尖锐、惊奇和敬畏之感。其性质正表达了生命的神秘性和我们自身存在之深不可测。”[5]儒家在人与天的本性上,其实带有先天的神秘主义色彩,只不过,在天人合德中,这种神秘性越来越多地转向神圣性,即道德性方面,但是从本源的角度追溯,仍然不免带有神秘性,就如康德所说:“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6]这与儒家信仰中对天的信仰、对道德的信仰是一致的。
精神性需要是人类的普遍、深刻、永恒的需要,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日益需要精神的支撑。西方的一些神学家甚至认为:“人们永远需要诸神,需要只有诸神才可能提供的一般性补偿物。除非科学把人变成神,或使人灭绝了人性,否则,人们将继续过着受到种种有限性所限制的生活。”[7]虽然事实已经证明:无神论者一样有精神支撑,不过,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认宗教对人的吸引力。“宗教之所以存在的人性基础与其历史性根源之所在:解救科学与道德不能明显解决的精神支撑问题,为人生的杠杆提供了一个用力的支点,来担负其生命发展的重量。”[8]不过,在当今社会,不管是西方还是我国,都存在着邪教的问题,美国的人民圣殿教、我国的法轮功、全能神这样的邪教甚至都能吸引到一定数量的信徒,这从一个侧面恰恰说明人们需要精神的东西,而传统宗教则面临着吸引力不够的问题,因而迫切需要发展完善,才能够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精神支撑。西方神学家柯林斯指出,今天的宗教必须要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刘述先认为:“当代美国宗教哲学的探索无疑可以给予我们一些重要的启发,激励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改造中国哲学,给予它创造性的诠释,来迎接以及面对我们的现在以及未来的世界。”[9]儒家信仰一方面具有宗教性,在精神方面具有深厚的蕴涵;另一方面,它没有宗教偏执的缺陷,具有开放包容的精神,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契合性,在现代社会应该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儒家信仰之道德性
道德在儒家信仰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整个儒家思想史,可以说是一部道德进化和完善的历史。从“天人合一”出发,在起点上,儒家认为天人之间最重要的同质性在于道德,“天人合一”的核心是“天人合德”,道德是人的存在方式。关汉卿的《窦娥冤》中有句脍炙人口的唱词:“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充分说明了关于天地的道德本性的观念是多么深入人心,对一些罪大恶极的事件和人物,人们往往描述为天理难容、人神共愤。简言之,儒家信仰就是道德的信仰。唐君毅说过:“儒家信各种道德实践之道,如仁义礼智;信人有能为仁义礼智之善性;信仁义礼智之悦我心;信人之自尽其此性此心,即能为贤为圣;信贤圣之可学而成;……信贤圣之德泽流行,与天德之流行,无二无别”[10],这样看来,与一些功利性的信仰相比,儒家信仰本质上是一种优质的信仰。这种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对外在神圣者的依赖,把神从高高的天上拉回人间,强调相信规律、相信人性,相信自己。因而,在儒家信仰中往往不会出现基督教世界中“假如没有上帝,道德如何可能”的难题。儒家信仰是人文信仰,自觉的信仰,它相信秩序、相信人性、相信道德,并且,这些内容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因而,儒家信仰具有不断发展完善的可能性。
儒家信仰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决定论”,认为道德能够改变命运、决定命运。在儒家思想中,由于道德的本体性地位,因果报应实质是道德报应。虽然儒家信仰中没有形成人格神,但是它仍然潜在地认为宇宙、天地不仅为道德秩序提供了本体依据,而且也是秩序的不出场的、最终的维护者,正如俗话所说“举头三尺有神明”、“神目如电”、“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等,其实都是强调存在着神秘的力量对善恶报应进行着监督和管理。冯梦龙的小说《三言》中的很多故事都在说明和论证这个道理,进而影响和引导人们的行为,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道德决定论”的实质是由人自己的思想行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世界各大宗教信仰与道德也是密切相关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有丰富道德蕴涵的教规教律,儒家信仰与之相比区别在于其他宗教往往是以道德为工具,而儒家是以道德为目的。唐君毅认为,基督教与儒教相比,“前者是以道德建基于宗教,后者是融宗教与道德。前者着重信历代传来之天启,后者贵戒慎乎不睹不闻不己所独知之地,此是二种精神之大界限。”[11]这样,儒教更注重的是人的理性,而不是完全寄托在启示上,从而使得其宗教性上少了偏执,多了理性。正是由于充分相信人类理性,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依靠神圣者上帝、真主的救赎不同,儒家依靠自觉自力。唐君毅认为,儒家“即自信吾人之能发出或承担此信仰之当下的本心本性,即具备,或同一于、或通于此信仰中所信之超越的存在或境界,此信仰中之一切庄严神圣之价值之根源所在者。”[12]钱穆也认为儒家是“一种现实人生的新宗教,他已具有宗教教义中最普遍最重要的‘慈悲性’与‘平等性’,他亦具有宗教家救世救人的志愿与能力。他与宗教之不同处:一则:宗教理论建立在外面‘上帝’与‘神’之信仰,而儒家则信仰‘自心’。”[13]儒教信仰相信人性,对人性抱有先天而来的乐观态度,不像有些宗教信仰完全依赖外在的启示,难免走向偏执和极端。儒家信仰力求在人类理性与外在神秘力量之间寻求平衡,因而,其不会因此而滑向反面,即自我中心主义或寡头人文主义。
儒家信仰强调人通过体悟去认识“天人合一”,体认到天的意图,做到安身立命。从“天人合一”的本体出发,道德具有了本体性地位。儒家相信人的神性,如孔子在儒家文化中就已经被提升到即凡而圣的高度,“不仅‘天’是人格化了的,人也是神化了的。”[14]这种神性是通过人的德行来实现的。在儒家信仰中,“只有通过一生的自我修养才能保持人和神之间的适当关系,这种自我修养包括奉行礼仪以及多做个人贡献。”[15]民间的造神运动是这种思想的表现。民间造神是基于对象的道德品行和功绩,典型的如关公,因义成神,被尊奉为关帝,并且得到官方的认可,关帝庙因而遍布各地。官方和民间祭祀的一大目的是崇德报功,这都体现了对人本身及其行为的尊重。史书记载,如果民间崇拜一些奇怪的有违天道的东西,地方官员就会出手干预,把这些淫祠淫祀拆除毁掉。冯梦龙的小说《三言》中对此也有形象的描述。韦伯认为,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对于包括巫术在内的奇怪的信奉都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他说:“儒教也认为巫术在面对德行(Tugend)时,是无计可施的。凡是以古典的生活方式过活的人,就不必畏惧鬼神;只有踞高位而不德者,才会使鬼神有施力之处。”[16]在儒家看来,神必须是具有道德性的,是厚德载物的,而不可能没有道德性,只有神秘性;否则只能是妖魔鬼怪,邪不压正,妖魔鬼怪害怕正义的有德性的人。在儒家思想中,甚至可以承认万物有灵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灵”都值得崇拜的,起码的标准是德行或功绩。
儒家信仰与我国民间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影响。与民间信仰相比,儒家信仰具有超功利的特质,它超越了功利的层面,历来注重精神层面。民间信仰则存在着鬼神观念,信仰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趋利避害。儒教信仰则已经超越了回报,旨在实现作为人的价值和意义,它注重超越自然生命的文化生命的传承、精神生命的实现,这不是世俗化的民间信仰所能望其项背的。
儒家信仰与民间信仰虽然在层次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但是在对伦理秩序的追求方面则存在着共性。儒家推崇生生不息的宇宙秩序,希望能够实现赏善罚恶的永恒的正义秩序;民间信仰中同样存在着报应的观念。虽然,关于赏善罚恶的目的性上儒家信仰与民间信仰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儒家是不求回报的,而民间信仰则往往怀着得到神鬼回报的直接目的,但是在表现形态上则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唐君毅认为:“在中国,则神意乃人力所可转,人修德以自求多福,神未有不助人者。神意可由人转移,则专司祭神,测知神意之巫觋之重要性,亦自然减少,不易成一特殊阶级,宗教亦不易有超越而独立之文化地位矣。”[17]这种态度反映了“天”的人格化的一面,认为人在神面前是有能动性的,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得到相应的报偿。这种观念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公正的伦理秩序的尊重和追求,另一方面有助于善恶报应观念的形成和确立,符合人们理性和情感的需要。
四、儒家信仰之开放性
“天人合一”的本体蕴涵了儒家信仰的开放性。儒家承认人的神性,这事实上为依靠人的理性提供了理论前提。在儒家学者看来,圣人是做人所追求的目标。圣人体现了天的意志,但是,圣人与天并不是等同的,人需要不断地反省努力去接近天的旨意,因而,这客观上蕴涵着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理念。
儒家信仰面向人的理性开放。儒家历来强调尊重和实现人的能动性。在人神关系上,一方面,人是实践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体现了对人的理性能力的尊重,克服了在天人关系上的蒙昧主义,具有理性主义的内涵。另一方面,虽然尊重人的能动性,儒教并没有把“天”排除掉。在儒教中,“天”好像是牛顿的“第一推动力”,它制定了规则,并且促使万物按照规则开始运行,当然其后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在人们的行为严重违反天意的情况下,给予灾异的告诫,就如董仲舒所认为:“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天通过灾异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干预、引导和惩罚,这种观念既为“天”保留了神秘性,又引导人们进行自我思考和反省,避免滑向过度倚仗自我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窠臼。就如刘述先所说:“儒家的思想富有高度的辩证性,然必须依赖善巧的思虑与解释才能掌握其微意。它的思想富于开放性,生生而不容已”[18]。
儒家信仰面向科学开放,面向未来开放。儒家推崇生生不息的发展精神,强调天人共同创造的精神,这些客观上具有与现代科学精神相通之处,从而使得其作为一种宗教性精神,在一定意义上说具有前瞻性。并且,儒家信仰并不固执不化,而是面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开放。事实上,儒家信仰与现代西方神学发展有相通之处,这不仅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及对话的可能性,而且说明了儒家文化具有面向未来开放的资质。随着科技和社会的日益发展,现代神学进入多元发展的新纪元,除了传统神学的发展以外,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神学派别,其中,过程神学是最有创造性的。过程神学力图重构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以期更符合现代发展所带来的对世界的认识。“过程神学家深信,需要一种新的哲学,帮助现代基督教思想摆脱过时的形上学所讲究的‘一成不变就是完美’,并且重构神学,切合这个将‘变更’置于‘存有’之上的现代世界。”[19]而在儒家中恰恰一直就存在着“变动”的思想,“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其历来把存在与变动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与过程神学存在着共通之处。就如白诗朗所认为的,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可以对话和交流:“我们也能够为对话找到一个根据,这种根据植根于哈特桑恩双向超越性学说所强调:‘神——人相互性’(divine-human reciprocity)以及对于信赖社群的服膺。对于人类的完善和德性,儒家和过程神学家均坚持一种经得起检验的希望。”[20]这说明儒家信仰具有本质上的合理性和开放性,能够与其它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其价值和作用。
五、结语
儒家思想蕴涵着深刻的人类智慧,其在历史上和现代社会都不乏忠实的践履者和传播者。当然,我们也不会否认其存在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约束力和信仰者数量的问题。与其他宗教相比,儒家并不强调人格神的存在、末日审判等等,它对人们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指引和依靠,强调自觉,与其他宗教的神律相比,它对人们的约束力就有所不足。唐君毅认为,儒家中之宗教意识,“似较缺乏宗教性之坚执与迫切感,乃由超世间与世间之对峙而生之超越感。然此毕竟为得为失,则未为易言。”[21]不过,约束之强度不够,从另一个方面说,则不易走向偏执。此外,儒家义理往往是精英知识分子才能掌握,而对普通民众,则强调“百姓日用而不知”,这样其难免陷入难题,精英分子能够培养起精神,而普通百姓则比较困难,这就制约了其影响力;并且,“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则自觉无从谈起,这样,其精神中难免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这是今后其理论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总体看来,儒家信仰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它具有强烈的人文关切,强调对自然生命、文化生命以及宇宙生命的尊重和发展,体现了非常开阔的胸怀。它注重道德价值和精神追求,在终极意义上为人们提供着行为方式和价值意义的规范和引导,并且,它面向人类理性、科学开放,符合人类理性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现实性。在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很少有盲目排外之偏激,而是在兼包并蓄中不断发展。就如钱穆所说:“在中国史上,我们可以说,他既没有不可泯灭的民族界线,同时亦没有不相容忍的宗教战争。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新分子之羼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在中国文化史里,只见有‘吸收、融和、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22]当今的儒家信仰仍然应该发挥这种有容乃大的胸怀。我们相信,只要不断发展完善,儒家信仰一定能够为更多的人所认同甚至信仰,在现代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1][12][21]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3][美]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4][5][美]大卫·艾尔金斯.超越宗教——在传统宗教之外构建个人精神生活[M].顾肃,杨晓明,王文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五卷)[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美]罗德尼·斯达克,[美]威廉姆·希姆斯·本布里奇.宗教的未来[M].高师宁,张晓梅,刘殿利,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成中英,麻桑.新新儒学启思录——成中英先生的本体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9]刘述先.理想与现实的纠结[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10]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1]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3][2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4][15][美]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M].蒋弋为,李志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16][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7]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8]刘述先.文化与哲学的探索[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2.
[19][美]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M].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0][美]白诗朗.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M].彭国翔,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B82
:A
:1009-2447(2016)03-0070-05
2016-06-14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3AZJ001);2016年福建省中青年社科类科研项目(JAS160416)
孙长虹(1973-),女,山东淄博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闽江学院思政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