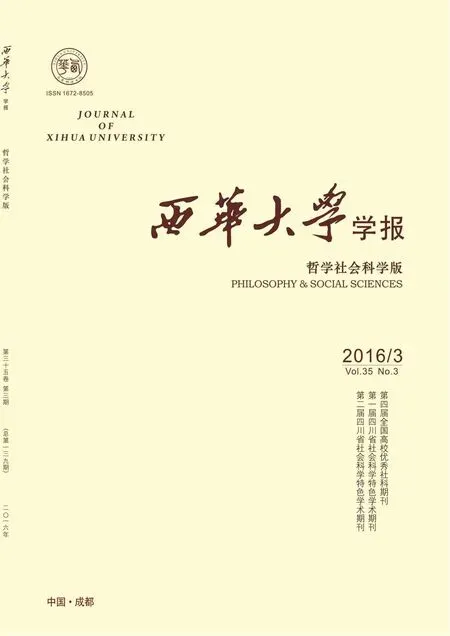副文本与翻译研究
——从序跋角度窥探小说翻译
邵 霞
(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 陕西商洛 726000)
副文本与翻译研究
——从序跋角度窥探小说翻译
邵霞
(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摘要:学界从各个方面对小说的成功译介进行了探讨,但是鲜有学者从副文本翻译角度探讨其对小说译介的推动作用。本文从序跋角度探讨副文本在小说翻译中的阐释性功能,运用描述性研究方法,说明序跋在小说翻译中的作用。诸多例证表明,译者对原作中副文本的翻译为读者提供了了解作者、作品、译者翻译目的和翻译思想的捷径。
关键词:副文本;正文本;序;跋
一、副文本及其价值
副文本(法语为paratexte, 英文为paratext)这一概念,由法国文论家热拉尔·热奈特1979年在《广义文本之导论》中首次提出[1]。他在1982年出版的《隐迹文稿》中指出副文本包含标题、副标题、前言、跋、告读者、插图、插页及其它附属标志。
1997年在《副文本:阐释的门槛》中热奈特又将副文本细化为十三个类型,包括出版社的内文本、作者名、标题、插页、献词、题记、序言交流情景、原序、其他序言、内部标题、公众外文本、提示和私人内文本。对于作者来说,副文本是他们经营文本的特殊策略;对于读者来说,副文本是进入正文本的必经之路;对于文论批评家来说,副文本是解构作品的切入点。正如热奈特所比喻的:“没有副文本的文本就像没有赶象人的大象,失去了力量。”
金宏宇指出在汉代,序又称叙、前言和引子等。跋,包括后记、后叙和跋尾等别称[2]。序跋可以反映作者、译者的生平经历尤其是与作品相关的写作、翻译动机、生成过程、出版、传播和译作在原语和译入语的接受情况,经常还会涉及到作品的修改、版本变化等方面的信息。鲁迅和郭沫若就经常在序跋中涉及以上内容。与正文本所具有的想象性、虚构性和抒情性等文学本体特征相比,副文本具有纪实性和真实性的特点,它偏重于吐露历史本质,因此具有文学史料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副文本既是文本的构成要素,又是文学史料的重要来源,更是译者和读者进入正文本阐述的门槛,因此它具有阐释学的价值,是关于一部作品内部与外部最完整的阐释。严复正是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深谙汉语但不懂英语的林纾在《<黑奴吁天录>序言》中透露了他的翻译动机和翻译思想。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这就是傅雷从文艺学和美学角度提出的翻译标准“神似说”。这些副文本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翻译文献和研究资料。
二、译作序跋与内部阐述
中国文学的成功外译与汉学家及诸多译者的共同努力分不开,以下将从不同译家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成功译介说明序跋翻译的重要阐释性作用。内部阐述主要包括作品标题、主要内容、结构、版本和文类等重要信息。
1.作品标题
Venuti 认为译者前言是译者对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隐身”的一种形式,他认为当源语言与译语间有较大的差异时,译者应当通过前言的形式“显身”,在前言中作辅助性阐释以帮助读者跨越差异,使读者更好地接受和阅读译文[3]。葛浩文在SandalwoodDeath的前言译者注中,对莫言《檀香刑》这部作品的命名进行了解释,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用Sandal-wood-death 这三个单词来表达莫言的 “Tan-xiang-xing”。[4]同时,葛浩文在前言中指出故事的发生背景是一百年前的义和团运动,讲述刽子手如何用骇人听闻的手段将犯人折磨致死。
2.作品主要内容
葛浩文在翻译姜戎的《狼图腾》前言中[5],讲述了该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向目的语读者讲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一位知青在内蒙古草原插队时与草原狼和游牧民族相处的故事。葛浩文同时说明了该部小说发生于毛主席号召城里人上山下乡时期,讲述了牧民与强悍的草原狼之间的斗争和依赖关系。读者可以从前言中了解到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激发读者的读书欲望。
3.作品文类
葛浩文在BigBreasts&WideHips(《丰乳肥臀》)的前言介绍中[6],指明这部作品是小说,从历史角度描写一个女人和她的九个孩子(八女一男)以及女儿们的丈夫的故事,从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写到新中国改革开放后,描绘了该阶段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在《酒国》(TheRepublicofWine)的前言中[7],葛浩文指出这是中国文学中少见的力作,与斯特恩(Laurence Sterne)《项迪传》(TristramShandy)在文类上最相近,这是一部复杂的寓言,写的不仅仅是国民性,还涉及到如何定义真理、理想、想象和创造力等更大的话题。
4.作品版本
对于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在《红楼梦》翻译过程中所参照的版本,学界曾有“有正本、程乙本”之争,而杨宪益在出版说明中对他们翻译过程中所参照的版本有如下一段文字进行说明:
Our first eighty chapters have been translated from the photostat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Peking, in September 1973 according to a lighographic edition printed by the Yu-cheng Press, Shanghai, in about 1911. This Yu-cheng edition had been made from a manuscript copy kept by Chi Liao-sheng of the Chienlung era. The last forty chapters are based on the 120-chapter edition reprinted by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Peking, in 1959 from the movable-type edition of 1792.[8]
以上文字说明他们译本的前八十回是采用“有正戚序本”进行翻译,后四十回是以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的版本进行翻译。在大中华文库《红楼梦》汉英对照本的前言中可以找到类似的文字:
本译本为一百二十回,其中前八十回以“戚蓼生序本”有正大字本为底本,后四十回则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印行的“程乙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版本对个别地方做了校改或补正。[9]
前言中的这些阐述证明杨宪益夫妇翻译过程中前80回所参照的中文版本是“有正本”,而后40回是参照人民文学出版社校勘重印的“程乙本”。译者前言中的这些信息为厘清《红楼梦》版本之谜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三、译作序跋与外部阐述
译作中的外部阐述包括阐明译者的翻译方法、译者翻译观、翻译动机和社会文化语境等,以及交代原作的原型(如贾平凹在长篇小说《高兴》的后记中透露高兴的原型就来自于自己的儿时玩伴刘书祯)等。
1.翻译方法
重“形合”的英语和重“意合”的汉语造成了英汉语在语法方面的巨大差异,译者的翻译方法体现在对汉英差异的翻译中。作为古代文学史上的丰碑,《水浒传》凭借其悲壮的英雄故事和质朴的语言赢得读者好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对译本在目的语中的接受起到了关键作用。沙博理(Sideny Shapiro)的译本是目前学界广泛接受的全译本。他的译文以直译为主,读起来通俗易懂,将施耐庵正文本中所塑造的草莽英雄形象和农民起义军与官府力量作战的场景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沙博理的五本译作中,每本的后记中都有对相应章节的注释,如第五本中对第九十四章进行了解释[10]:
Xi Zi, or Xi Shi——famous beauty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5 B.C)
Bianzhou, or Bianlinag——present-day Kaifeng
——where the Eastern Capital was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960—1127 A.D.)
沙博理在后记中对西施和汴州的翻译采用拼音加解释的翻译方法,可以帮助读者迅速定位历史人物以及历史地点,从而更加有效地理解故事发生的背景。
美国译者葛浩文为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SandalwoodDeath(《檀香刑》)的前言中指出韵律在汉语中运用的广泛程度远远大于英语,因此他对作品中的韵律、尤其在对猫腔翻译时更是绞尽脑汁。他坦白在译作中由于不可译性或文化空缺,他对部分词和术语进行省略,对于这些省略的词汇他在后记中专门罗列出来进行阐述,以弥补译文中的零翻译损失。如:
dan 旦:a female role in Chinese opera
Gandieh 干爹:a benefactor, surrogate father, “sugar daddy”
Ganerzi 干儿子:the “son” of a gandieh
Gongdieh 公爹: father-in-law
葛浩文在后记中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专有项词汇的翻译主张,他认为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可以采取音译加注释的方法,音译可以帮助目的语读者了解中国对相应称呼的发音,而后面的注释则有益于读者对相应拼音所代表的亲属称谓的理解。葛浩文在TheGarlicBallads(《天堂蒜薹之歌》)的后记中用拼音加注释的翻译方法对主要人物谱系表和中国命名方式进行阐述,方便英语读者了解中国命名的语言文化,如[11]:
GAO YANG (“Sheep” Gao): a garlic farmer高羊大蒜种植户
GAO MA (“Horse ” Gao): a garlic farmer高马 大蒜种植户
FANG JINJU(Golden Chrysanthemum): his daughter方四叔之女
FANG YUNQIU (Fourth Uncle): head of the household方家家长
葛浩文在后记中对人名采取的是音译加注释的形式进行解释,说明小说中各个角色在源语言中的发音、字面含义以及人物谱系间的关系,利于读者对故事脉络的把握。同时,葛浩文还附表说明单元音、双元音以及 “c”、“q”、“x”、“z”、“zh” 在现代汉语中的发音,使读者能够对源语言中的语言特色有更直接的感知。
2.译者翻译观
对于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原则,除了从译者的译著中找出答案,还可以在译者的译序跋里所表达的翻译观中窥探一二。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和闵福德(John Minford)在《红楼梦》的英译本TheStoryoftheStone的第一卷序言中对于他们的翻译观的阐述有益于研究者了解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体系。如下所示:
This translation, though occasionally following the text of one or other of the manuscripts in the first eighty chapters, will nevertheless be a translation of the whole 120 chapters of the Gao E edition. —— My one abiding principle has been to translate everything- even puns[12].
从序言中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霍克斯不仅指出了他的译本是参照众多资料后重构的版本,更重要的是他透露了他的翻译思想就是尽可能翻译出原作中的一切思想内容和艺术,包括让译者们棘手的双关语他也尽力为之。
3.翻译动机
翻译作为跨文化的话语实践,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不同历史时期的译者翻译活动总是在明确的翻译动机的推动下进行的。
如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中对他当初翻译《域外小说集》的翻译目的进行了说明:“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要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这结果便是印译《域外小说集》。”[13]
由此可见,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而国人依然愚昧无知的历史背景下,鲁迅的翻译目的是希冀通过翻译国外先进的文化思想和与中国一样的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来唤醒民族的“国民性”。又如他在《<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中谈到:“这剧本也很可以医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章回体小说开山之作《三国演义》的两个主要英译版本。最早的译本是1925年由英国汉学家泰勒(C.H.Brewitt-Taylors)翻译的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泰勒的读者群主要为旅居中国的外国人,他们迫切希望通过译本了解中国、消遣生活和消解乡愁。泰勒的翻译动机是使译本在目的语读者中得到广泛传播。对于中英差异较大的文化,他倾向于利用简洁的译文“去陌生化”使读者可以流畅地完成阅读。第二个英译本是1992年由美国汉学家罗慕士(Moss Roberts)翻译的ThreeKingdoms,他的英译本是目前传播最广泛的全译本。全景式地呈现和传递中国文化是罗慕士的翻译动机[14],对于汉英文化差异较大的内容,他不惜牺牲译文在目的语的“接受性”而坚持保持翻译的“充分性”,意在使目的语读者以中国人的方式理解中国文化。此译本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将正文部分(共1457页)进行了忠实地译介,此外,该译本最大的特色是,译者用了共计231页(累计数万单词)的序言、后记、注释等分章节(共120章)介绍和解释《三国演义》中涉及到的主要人物、重大历史事件时间、三国时期头衔和职务列表、三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图和重大战役路线图。为了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要求——娱乐消遣或学术研究,罗慕士在后记中引入了清代编者毛宗冈对《三国演义》(1660)所作的注释,为了保证援引材料的权威性和全面性,罗慕士还补充了《通俗演义》中的部分内容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罗译本的百科全书特性正是它在英语世界流行的主要原因。
4.社会文化语境
同一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由此就会催生不同的译本。 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的小说DavidCopperfield的三个译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初民族文学处于新旧转型时期,包括林纾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立场,面对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他们没有弱势和自卑心理,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应对西方的文化观念。林纾的译本《块肉余生述》采用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了大量的改写。而20世纪末张谷若的译本《大卫·考坡菲》和庄绎传的译本《大卫·科波菲尔 》多采用异化策略。20世纪初的社会有“开启民智”的风气,具有吸收和接受外来文化的意识,但是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还很有限。文学翻译的选择取向受制于民族文学系统的诗学规范,因此林纾在《块肉余生述》序言的最后写道:“不必心醉西风,为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为不负矣。”[15]这段序言说明林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和坚持,因此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译观。
源于话本的《西游记》的原始功能是取悦听众,对它的翻译始于1895年。在《西游记》的众多译本中,1942年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的英译单行本产生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伦敦。被纳粹炮火轰炸下的英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迫切需要英雄主义的作品鼓励广大民众。韦利在前言中指出他的《猴》不是全译本,而是基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天国之行,一首伟大的中国讽喻史诗》和海斯(Helen M. Hayes)的节译本,鉴于当时的社会语境中简短的节译故事更受欢迎,因此他在译文中采用删减和节略的方式,删减原文中的独立情节和对话,将一百回的《西游记》缩减为只有三十回的紧密衔接的节译本。由此可见译者为了迎合当时社会的主流诗学和满足读者期待所作的努力。[16]
综上,从以上小说的成功译介可以看出副文本是关于正文本的最完整的导读性叙述,它是关于正文本本义和写作意图、翻译意图的阐释。著名符号学研究学者艾柯认为:“在‘作者意图’和‘阐释者意图’之间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即‘本文的意图’。”将艾柯的理论套用到带有序跋的译作中,如果说作品正文本表现的是“文本意图”,作者的自序跋则表示“作者意图”,译作序跋则是“阐释者意图”。总之,副文本参与正文本意义的构建,是正文本意义构建过程中活跃的介入性因素,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构建起积极的生成作用。
结语
世界文论发展的趋势是由作者中心到作品中心再到读者中心,而对于作品和作者以外的副文本甚少关注。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理论更多地是关注作品或文本(text),伴随作品产生的副文本未曾真正地进入
研究视野。副文本作为环绕和穿插在正文本周围的辅助性文本,其功能主要是对正文本及作者和译者意图进行阐述和交代,属于爆料性文本。译作的序跋翻译和正文本翻译共同构建了完整的译文。
本文通过对四大名著和莫言、姜戎等作家作品中的序跋翻译进行了描述性研究,对小说的成功译介作了有效探索,为中国现当代小说翻译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和案例。对副文本翻译的探索有助于剖析汉学家对中国文学英译的特点,从中汲取教训,为中国的小说翻译提供行之有效的指导。
参考文献:
[1]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M]. 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71-72.
[2]金宏宇. 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30.
[3]Lawrence Venuti.Translationandtheformationofculturalidentities[M].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5:10.
[4]Howard Goldblatt.SandalwoodDeath[M].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2012:IX-X.
[5]姜戎. 狼图腾[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1-2.
[6]Howard Goldblatt.BigBreasts&WideHips[M].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12: VI-XIV.
[7]Howard Goldblatt.TheRepublicofWine[M].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12:V.
[8]陈宏薇,江帆. 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C]// 刘士聪. 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57.
[9]Cao Xueqin & Gao E.ADreamofRedMansions(汉英对照) [M]. Trans.,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3: 30.
[10]Sideny Shapiro.OutlawsoftheMarchV[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6: 3077.
[11]Howard Goldblatt.TheGarlicBallads[M].New York:Academic Publishing, 2012:289-290.
[12]David Hawkes.TheStoryoftheStone[M].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3: 11.
[13]刘运峰.鲁迅序跋集(上卷)[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202.
[14]Roberts Moss.ThreeKingdom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11:1459-1690.
[15]块肉余生述[M]. 林纾,魏易,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
[16]Arthur Waley.Monkey[M].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61:7-8.
[责任编辑刘瑜]
On Paratext and Translation Studies—Study on Translation of Novels from Preface and Postscript
SHAO Xia
(SchoolofLanguageandCulturalCommunication,ShangluoUniversity,Shangluo,Shanxi, 726000,China)
Abstract:Many studies have been prob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novels, but few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translation of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text translation. Based on descriptive approach, the significance of paratext translation is demonstrated from the illustrative function of paratext in novel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paratext is the royal road to know the author, the works, the translation purpose and theory of a translator.
Key words:paratext; text; preface; postscript
收稿日期:2016-01-05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联基金项目(2015Z080)“陕西文学作品中地方民俗文化的翻译——基于贾平凹英译作品的研究”;商洛学院科研项目(14SKY024)“陕西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从贾平凹、陈忠实等作品外译谈起”;陕西省社科联基金项目(2016Z134)“贾平凹小说后记注译研究”;陕西省教育厅基金项目“贾平凹作品序跋翻译与研究”。
作者简介:邵霞(1983—),女,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16)03-0085-04
·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