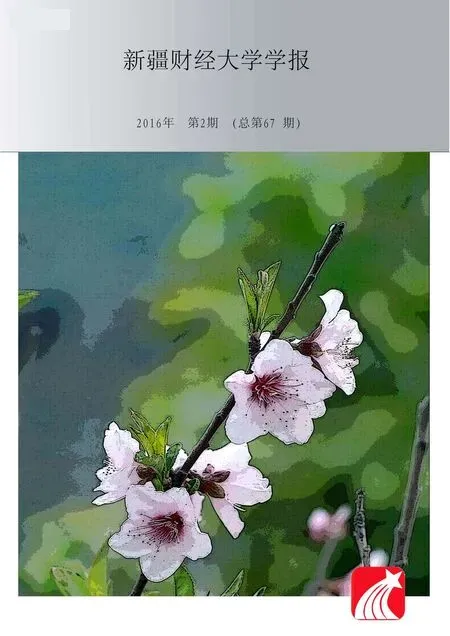令状及其悖反:逮捕的制度进路分析
——以保障人权为逻辑起点
王 东
(新疆财经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令状及其悖反:逮捕的制度进路分析
——以保障人权为逻辑起点
王东
(新疆财经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摘要:令状制度是西方法治国家逮捕制度的基础制度,其设计是出于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的理念。无状逮捕在立法上虽然限于紧急情况下实施,但在实践中却呈逐渐扩大的趋势。通过分析影响令状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保障公民不受不合理羁押的功能是其逻辑起点,应寻求对于当前中国刑事司法改革中逮捕制度所涉及的不同诉讼价值相互融合的路径,以建立一种“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价值均衡的制度模式。
关键词:逮捕;制度进路分析;令状制度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时隔16年来对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修正。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集中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这是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件大事,且如何更好地推进司法制度的改革进程也是每年全国两会讨论与关注的焦点[1]。其中,在刑事侦查阶段如何加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是讨论最多的热点问题。
为防止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对逮捕结果价值的过度追求,从而发生任意压制甚而随意剥夺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司法违法行为,现代法治国家均在刑事诉讼法中细致规定了逮捕程序。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强制措施的适用折射出国家公权力对犯罪嫌疑人私权利的压制。其中,对犯罪嫌疑人的个体权利压制程度最为严重的当属逮捕措施及捕后羁押。逮捕通过一定时期内拘束犯罪嫌疑人之自由,目的或在于保全被告,或在于搜集、保全证据,以利于刑事程序的进行。令状制度是西方法治国家逮捕制度的基础制度,其设计是出于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的理念。无状逮捕在立法上虽然限于紧急情况下实施,但在实践中却呈逐渐扩大的趋势。本文以保障人权为逻辑起点,通过分析影响令状制度的制度因素,着重于其保障公民不受不合理羁押的功能,寻求逮捕制度所涉及的不同诉讼价值相互融合的路径,进而分析我国逮捕制度在刑事司法中的实践,把逮捕制度放在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宏大体系中加以考察,提出保证逮捕制度所涉及的诉讼价值相互融合的分析路径。
一、逮捕措施分析的两种进路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在刑事程序中加强保护被追诉人个体权利日益成为主流话语。法学界对直接牵涉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逮捕程序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批判或反思。批评针对的主要方面包括:我国逮捕条件规定得较为模糊宽泛[2],逮捕程序缺乏司法审查[3],被逮捕人人身自由权利没有有效保障措施[4],逮捕后的不当羁押缺乏救济措施[5]。这些批评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关键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以及该如何解决。
目前学者大多认为问题主要存在于立法技术有缺陷和实践操作不当两方面,并提出针对性意见,如完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逮捕的规定,加强逮捕审查,保障被逮捕人的人权等。对于这些解决之道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技术进路”。这一进路的出发点是,当前我国逮捕措施实施过程中的种种弊端主要是立法技术和操作技术出现了问题,即可以通过改变法律规定以及严格遵守逮捕程序的操作要求加以解决。
以这种“技术进路”分析问题并努力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尤其对当下我国刑事司法人员专业能力普遍较低的状况确有针对性——明确细致的程序设置便于理解也便于执行。但是,如果我们把研究视野拓开就会发现,在逮捕实施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仅仅是一种结果,是整个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运行的一种结果。1996年刑事诉讼法虽经修订却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技术的种种不足[6],这些不足表明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必须而且也只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制度性调整或改革,而不能满足于个别程序技术的改进或者部分法律条款的增加。由此,只对逮捕程序本身进行技术性的整改,虽能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效果,但却无法真正找到“病因”,从而无法治愈“病体”。
因而,尽管中国的逮捕措施确实需要改进,但是本文的中心论题并不是要对其进行反思或者提出具体的改革建议,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逮捕的制度基础以及影响该基础的制度性因素,来揭示导致我国刑事侦查中逮捕措施的不当采用成为一种畸形“合理现象”的制度原因。所以,本文的主要分析视角为一种“制度进路”。制度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起作用的多种制约性因素的组合,影响制度的有效运行既有制度内的各种条件,也包括制度外的种种因素。
二、西方令状制度与逮捕权的分配
考察西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逮捕程序的启动阶段,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的基础性制度——令状制度。令状是“法院发出的要求接受者做所命令的事情的一项书面命令,它们大多是有关诉讼的开始或继续事宜的,或者是要求做出某一特定行为的”[7]。在令状制度下,追诉机关无权自行剥夺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此项剥夺或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决定权多由独立于追诉机关的中立裁判者享有。如学者所言:“当负责法律执行的官员意图进行逮捕时,获得逮捕令状决非‘走过去,拿过来’那么简单。相反,向签署令状——该令状表明已发现的事实足以担保具备法律要求的合理根据——的法官提出足够的证据资料是该法律执行官员的责任。由于是由法官决定合理根据存在与否,法律官员必须极力表明案件已经具备合理根据。进一步,也并不是每一个法官都乐意签发令状。因此,该法律执行官员可能被指令回去补充更多的证据材料或者被告知以现在的事实情况不可能签发令状。”[8]
由于拘束人身自由的逮捕必须经过特定机关的审查决定几乎已经成为现代各法治国家宪法中的要求,所以令状制度中的逮捕权客观上就被分割为逮捕申请权和逮捕决定权两部分。[9]将特定的强制处分权的决定权限委由法官来行使的立法例可以被称之为法官决定模式,其他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国家机关——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仅仅具有申请权。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要将逮捕权进行分割且又作出这样的权力分配形式呢?通过考察关于逮捕等强制措施行为性质的理论变迁,我们可以发现,此种逮捕权力的配置模式是贯穿西方司法程序的价值理念和政治组织原则所共同决定的结果。
(一)程序性与实体性:逮捕的双重行为性质
逮捕是在刑事侦查过程中所实施的强制行为,故传统刑事诉讼理论将其定位于一种单纯的刑事诉讼中的程序行为(刑事诉讼行为)。诉讼行为,是开启、进行、终结诉讼的各个行为,即在不同诉讼阶段进行并为完成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而开展的行为[10]。就此而言,无论是出于保全被告还是搜集或保全证据之目的,逮捕确实属于程序行为。一般而言,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要经历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其间要发生数以百计的程序行为。除有法律专门规定外,并非每个程序行为都必须受专门机关的审查。因为,如果对每个当事人或者司法机关认为不妥的程序行为都授以申请审查或救济的权利,则必将导致法院疲于应对而难免致使诉讼进程拖延。甚而,如果无论进行到哪一个阶段,无论是何种内容的程序行为都可以被独立提起审查以至作出改变,则极易产生前后冲突的裁决结果,亦会使诉讼资源在审查诉讼行为的反复折冲中白白消耗。为避免此类恶果,学理与立法都细致分辨了须申请审查以及可申请救济的程序行为的特例种类。
上述传统理论将逮捕等刑事诉讼强制行为定位于一种单纯的程序行为而忽略了其对被强制人实体权利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Niese对此传统学说进行了整体检讨,并且提出了双重性质(功能)说,即某些程序行为可以兼具程序与实体的性质,尤其是强制处分行为[10]。逮捕当然是保障侦查程序顺利进行的程序行为,但是逮捕措施的施用无论如何都会造成被逮捕人人身自由权利的受限制甚至是被侵害,也就是说,逮捕行为干预了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基于逮捕的强制行为的这种特性,德国学者Amelung曾更进一步地指出,刑事诉讼法应该根本放弃“强制处分”的传统用语,改以“刑事诉讼上基本权之干预”替代,如此才能精确描述这种公法行为的特性[10]。应该说,“刑事诉讼上基本权之干预”理论强调对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的重视,因而特别注重在刑事诉讼中强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而不仅仅是注重对被追诉人罪责与刑罚的审查与判断。由此,只要是违法造成被追诉人权利受侵害的强制行为,就应该获得特别的审查程序来限制或救济的机会。
(二)令状制度: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伞
由于将逮捕等强制处分行为定位于干预公民基本权利的公法行为,这就与宪法所设置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基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优于国家权力的宪政理念,在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中,逮捕制度的设计更多注重对逮捕权力的限制,从而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任意侵犯。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宪法中大多规定逮捕的程序来规制公权力。例如英国宪法性文件《人身保护法》规定,没有法庭所发的附理由的逮捕令不得逮捕人,被捕人或其代表有权请求法庭发出命令将被捕人在一定期限内解送法庭,以审查其监禁理由,如认为无正当理由可立即释放(此规定被称为“人身保护令制度”)[11]。《美国联邦宪法》第1条第9款也规定了人身保护令制度,并在宪法第4修正案中进一步明确了逮捕令的签发程序[12]。在法国,《人权宣言》作为宪法的序言被写入1791年宪法之中,直至今日仍是法国《刑事诉讼法》的指导原则[13]。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宪法中也大多有类似的规定。
由上,逮捕行为指向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逮捕程序理应通过令状制度的严格审查机制来尽可能保护公民的权利。令状制度下通过将逮捕权分割为申请权和决定权并交由不同的诉讼机关行使,这就抑制了追诉机关因过分追求诉讼结果而滥用逮捕措施的可能性。同时,逮捕权的分割与配置亦是西方制度中的权力组织原则指导下的结果形式。西方分权与制衡的权力组织原则为根深蒂固的一项基本制度原则,运用在司法制度中就是体现为各项司法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的态势。在逮捕程序中,申请权与决定权的分属尽管在某些情势下会影响逮捕的效率,但是权力的相互制约却能使逮捕维持在一个合法的范围内而不致公民的权利轻易受损。
(三)保留与比例:令状制度的制度基础
将逮捕等强制处分行为定位于干预公民基本权利的公法行为,就要求令状制度受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约束。这两项原则构成了令状制度的制度基础。
1.法律保留原则。依照法律保留原则,国家机关要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必须有法律授权的依据,并且应该遵守法律设定的限制性条件,否则就属于违法侵害人民基本权利的行为,意即对于刑事诉讼上基本权之干预的行为由法律规定为行动依据,严禁任意为之。法律保留原则与无罪推定具有内在联系。按照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推定其无罪。既然犯罪嫌疑人在未经宣判有罪前为无罪之身,那么应该尽可能使其人身自由处于不受限制的状态。因此,对于逮捕的施用需要通过审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再颁发令状方可进行的制度设计,直接反映了对追求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两种不同刑事诉讼价值在程序中的平衡,是对司法权力的抑制和对人权保障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具体体现。
2.比例原则。依照比例原则,国家机关对被追诉人实施逮捕(以致干预基本人权)这一诉讼“手段”与其所欲达成的“目的”之间,必须合乎比例,亦即具备相当性的关系,其具体内涵包括适合性原则和必要性原则[14]。适合性原则要求实施逮捕时必须适合或有助于相关目的的达成;而必要性原则就是要求在审查实施逮捕时,只有当不能选择其他同样有效且对基本权利限制更少的措施时,逮捕措施才可认为是必要的。例如,为防止犯罪嫌疑人毁灭证据或逃匿,虽然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等手段都可施用以获此目的,但除非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无法有效达到此项目的,否则逮捕就不应被施用——因为逮捕对基本权利限制更严厉。此外,即使采取逮捕能实现所欲达到的目的,但如果限制被逮捕人基本权利的强度超出了所需的范围,则仍不能采用。因而,比例原则反映在令状审查时,逮捕决定权之享有者对所涉法益的权衡考量,即因实施逮捕而限制被捕人的权利所造成的不利益,不得超过采用逮捕所欲维护的利益。
综上所述,令状逮捕的制度因素至少包括两个:一是在刑事诉讼中对国家权力限制的需要和对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视,即价值平衡的结果;二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原则——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在司法领域具体运用的结果。令状制度的确立正是出于防止国家公权力可能被滥用的目的,将逮捕的实施设计为一个严格的权力制衡的制度形式,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构成了令状制度的基础。逮捕的申请权和决定权的分属配置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设计的原则在司法领域的延伸,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权力在逮捕令状制度下相互制约平衡。但是,令状申请是否就是绝对不可逆的制度,令状制度与诉讼效率价值又该如何实现平衡呢?
三、令状制度的悖反:影响令状制度的其他制度性因素
在令状制度下,侦查机关虽然在客观上存在实施逮捕的需要,但其本身却无权决定逮捕,而只能向独立的审查机关提出逮捕申请。但是,假设是现行犯或情况紧急的严重犯罪,如果还一味要求先由逮捕决定机关进行审查再签发令状,那么就会与刑事诉讼之效率原则相悖,亦无法有效实现打击犯罪之目的。因而,在大多数国家里,为适应侦查实践要求快速决断的情形,规定了令状制度的例外情形——与令状逮捕相对应的“无状逮捕”。
无状逮捕在各国立法中大多针对两种情形:一是现行犯,二是符合法定条件的严重犯罪,情况紧急以至于来不及请求法官签发令状时。在这些紧急情况下,警察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及时控制犯罪嫌疑人。不过,这种逮捕与令状逮捕在效力上具有显著区别。无状逮捕仅仅是暂时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手段,而不具有羁押的法律效力。因此,在警察实施逮捕后,只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时间届满,警察或者释放犯罪嫌疑人,或者根据需要向法院申请捕后的羁押。
无状逮捕在立法上虽然限于紧急情况下实施,但在实践中却呈逐渐扩大的趋势。例如在英国,进入20世纪以来,议会通过制定法不断扩大警察无状逮捕的权力,“到20世纪70年代,规定有无状逮捕权的制定法已经有近70部”[13]。《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不仅将普通法上的严重犯罪纳入可捕罪的范围,从而间接扩大了警察的无状逮捕权,而且警察无状逮捕权还从可捕罪进一步泛延到可捕罪以外的一般犯罪,从而将所有的犯罪都纳入了无状逮捕权的视野。在美国,197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美国诉瓦特森”一案确立了无状逮捕的基本原则:“如果逮捕是根据合理依据进行的,那么,即使存在足够的时间申请逮捕令状,在公共场所实施的无状逮捕仍然是有效的。”[15]依此,在美国刑事诉讼中,警察在两种情形下有权无状逮捕:一是对于警察在场时实施的任何犯罪可以直接逮捕;二是对于重罪,如果警察具有合理根据也可以进行逮捕。此外,在大陆法系国家,虽然令状制度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为了适应实践中快速侦查和紧急扣留的需要,也赋予了警察享有暂时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权力。这些控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虽然没有冠以逮捕之名,其实质却与英美法系国家扩大无状逮捕适用范围之本意一致,即在于将暂时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手段从令状制度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以强化侦查的效率[16]。
无状逮捕的此种扩大趋势,虽然可以用“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理由加以解说,但是对于无状逮捕这一本是令状逮捕制度的例外情形,在实践中却突然成为侦查机关的“更爱”而尽夺令状制度的“风采”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使得我们颇感疑惑:为什么以限制公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为基础的令状制度却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遭遇如此悖反呢?难道侦查机关为追求效率而宁弃犯罪嫌疑人权利于不顾?对此,可以从影响令状逮捕的其他制度因素进行分析。
首先,侦查机关“偏爱”无状逮捕是由其职业倾向与工作方式所决定的。侦查机关的主要任务就是侦查犯罪、调查收集证据以追诉犯罪人。在刑事诉讼中,逮捕被追诉人不仅可以防止被追诉人阻碍、扰乱追诉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且还可以通过直接控制被追诉人而获得许多其他侦查的意外收获。如对被逮捕的人,警察可以通过拍照、提取指纹等方式获取平时较难获得的重要信息;再如通过讯问、交谈获得与犯罪活动有关的信息,甚至是归罪性证据。由于实施逮捕是控制犯罪人、获取证据最为便利的方法,因而若能摆脱审查令状的束手束脚,侦查机关自然是乐意为之。所以,只要存在可能性,侦查机关当然会选择实施无状逮捕来尽早控制犯罪嫌疑人以获取更多的侦查线索。
其次,无状逮捕的扩大与传唤制度的功能萎缩紧密关联。传唤犯罪嫌疑人于特定时间到特定地点应讯也是一种强制处分行为,因为如果犯罪嫌疑人届时拒绝到场,则司法机关便可对其采取拘提或逮捕之强制行为。但是,随着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以及传唤制度对犯罪人心理强制力的逐渐衰减,虽然送达了传唤令,但拒不到场或逃匿的事例时常发生。为弥补传唤制度功能缺位,对于一些传唤不足以保证犯罪人到场应讯或受审的轻微犯罪,可直接由追诉机关实施无状逮捕,而无需法官审查后签发令状。
最后,无状逮捕的扩大也与法官人员编制相对较少有关。由于令状逮捕需要法官的谨慎审查并签发令状,所以从收到申请至签发必然间隔一段时间。但是,在侦查阶段,被告之保全或证据搜集与保全,时机往往稍纵即逝,申请与决定分离的结果,容易使侦查坐失良机。此外,侦查犯罪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必须发动强制处分的时点常常不分昼夜,且在犯罪率呈升高趋势之际,如果逮捕都采取令状制度,则法官的人员编制必须相当庞大才可勉强应对,或许还得全天候待命以接收侦查机关的申请。可是法官人数大量增加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所以扩大无状逮捕范围成为刑事司法的最优选择。
影响欧陆及英美令状逮捕制度的制度因素当然还不止上述这些。除了这些具体的制度因素之外,还有更大的司法制度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在发挥作用,例如犯罪率的攀升,民众安全感的减弱,司法制度中侦查部门权力的扩张,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等。这些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令状制度悄然发生着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设立令状制度的基础。当前,令状逮捕制度虽然逐渐减弱了其暂时剥夺公民人身权的功能,但依然是着重于保障公民不受不合理羁押的一种重要手段。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令状逮捕及其悖反(无状逮捕)是上述这一系列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
四、中国逮捕制度问题再分析
通过上述对两大法系国家令状逮捕制度的分析,回过头再看看我国的逮捕制度。“在我国,逮捕具有‘绑架’起诉、审判的效果。即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往往不得不尽量作出起诉的决定,法院则要尽量宣告被告人有罪,并根据羁押期限决定判处的刑罚。”[17]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逮捕采取“侦查中——检察院批准或决定,审判中——法院决定”的模式。那么依照此模式,公安机关并不能自由实施逮捕措施,其需经检察机关或法院的审查决定后签发逮捕令再进行逮捕。这种逮捕模式的设计理念是出于抑制逮捕权的滥用,是符合现代刑事诉讼的民主化潮流的。但是,实践中的情况却非想象中那样美好。对于我国当前的刑事侦查阶段逮捕的施用,大致可以用“有罪必捕,以捕代侦”来描绘。据《中国法律年鉴(2011)》的相关数据,2011年批准、决定逮捕的人数为923510人,除以提起公诉的人数1238861人,可以得到逮捕率为75%。有学者研究发现:“在2005 年以前,我国逮捕率一直高达90%以上;近年来,在法学界的强烈抨击下,逮捕率有所降低,但除最近两年,逮捕率都高达80%以上。根据收集的资料,这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18]如此高的逮捕率至少可以说明公安机关逮捕措施的申请是很容易得到逮捕决定机关的批准的。可是,为什么逮捕决定机关如此轻易就批准申请,为什么在以刑事程序中加强保护被追诉人个体权利为重点的司法改革的背景下侦查机关依然倾向“有罪必捕”,这种逮捕审查与西方令状逮捕制度在实质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正如前文所述,令状逮捕制度是西方国家司法制度中种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也由于这些因素的不断整合与博弈进而产生了对令状制度的悖反。同样的道理,我国当前逮捕制度的异化也是由我国司法制度中的种种制度性因素所共同造成的,主要涉及刑事司法权的配置方式、逮捕审查的行政化操作方式和捕后羁押的制度断层。
1.刑事司法权的配置方式。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将侦查权、公诉权和审判权分别交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行使。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的初衷大约是力图维持一种制衡与协作的关系。但是,检察院行使逮捕的审查批准权时,其国家公诉机关的身份使其能否保持客观中立显得令人怀疑。国家公诉职能与侦查职能之间的工作内容的连接性,使得检察机关处于一种角色的循环变换之中。具体表现为:在某一个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提出对犯罪嫌疑人的逮捕申请,由检察机关进行逮捕审查,此时检察机关行使的是侦查(监督)职能;而在该案件进入到公诉阶段,由侦查机关进行案件移送,由检察机关进行审查并提出国家公诉,此时检察机关行使的是国家公诉职能。
检察机关这两种权力的交叉变换使得逮捕审查权与公诉权无法兼容,反而造成检察机关为保障国家公诉权的顺利行使而无意识地支持甚至配合侦查机关的行动。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如此轻易就批准逮捕申请——批准逮捕对检察机关日后行使公诉权显然更加方便。因此,由并非独立第三方的检察机关作出的审查批捕,与由独立于追诉机关的中立裁判者进行审查的令状制度之间“形似而神非”。
2.逮捕审查的行政化操作方式。在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逮捕申请的审批,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行政化的程序。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提请逮捕书和案卷材料、证据进行审查。对于一般案件,是否批准由检察长作出决定,重大案件则要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察机关经过审查,批准逮捕申请的,发布批准逮捕决定书。由于在审查时基本上是由审查人员依据公安机关的书面材料来作出决定,且虽然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若干情形,“对于司法人员正确把握逮捕必要性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但囿于司法规范内容的有限性与案件事实无限性之间的张力,办案人员在自由裁量范围内形成了自身的司法经验”[19],使得这种文案审阅的方式必然将审查重点落于逮捕条件是否具备,所以,侦查机关对提请逮捕书内容合理的取舍安排会使申请较易得到批准。
3.捕后羁押的制度断层。在我国,逮捕后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限制效力处于一种持续延长的状态。这种对犯罪嫌疑人的审前羁押当属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但在我国却缺乏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除非原来的逮捕理由已不再具备,否则,捕后羁押的延长注定是与诉讼办案期限同期。由于没有专门的羁押制度,审前羁押依附于逮捕及其他刑事追诉活动,服务于侦查、审查起诉等办案活动的实际需要。这种不设限的逮捕羁押,容易产生一种制度性诱导——追求通过逮捕来控制犯罪嫌疑人以获取侦查信息的公安机关更会“放心”地“有罪必捕,以捕代侦”。
除了上述直接影响我国逮捕的制度性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制度原因。例如我国刑事司法中政法传统犹存,使得逮捕等强制措施依然是控制犯罪、维护秩序的重要社会治理手段;再如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逮捕替代措施形同虚设,诸如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在实践中缺乏操作的具体标准而难以发挥效果;还有对于被逮捕人在羁押期间的人身权利的受损缺乏程序性救济措施。上述种种,有学者总结了逮捕中心化的三大“死结”,包括制度环境死结、制度心理死结和制度效用死结[20]。这些制度性因素的“合谋”致使我国刑事侦查中逮捕措施的不当采用成为了一种畸形“合理现象”。
五、结语
就今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大方向来看,笔者赞同逮捕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是建立法院审查模式的观点。“法官比检察官更能通过逮捕审查发挥保障人权的功能,而那些关于检察机关行使逮捕批准与决定权具有正当性的论证,都是罔顾基本法理和诉讼规律的。在积极推进人权保障事业和刑事诉讼程序法治化的背景下,我国推行由法官统一审查逮捕的改革,可谓科学、合理、务实、可行。”[21]
通过对西方令状逮捕制度和我国逮捕制度的比较分析,笔者想要说明的是,影响逮捕制度的种种制度性因素同样也影响着司法制度的各个方面,因此,除了对不合理的司法制度进行技术进路上的分析外,我们更应该深入制度的内部去探究。所以,改革逮捕制度甚至整个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起点应该是对整个司法制度的审慎而又全面的考察。只有把逮捕制度放在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宏大体系中加以考察,才能把握保证逮捕制度所涉及的诉讼价值相互融合的路径,即一种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价值均衡的制度模式,这也是对逮捕制度进行“制度进路”分析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刑诉法修改,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EB/OL].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_article/content/2012-03/17/content_3437743.htm?node=6148,2016-03-08.
[2]刘根菊,杨立新.逮捕的实质性条件新探[J].法学,2003(9):49.
[3]高景峰.审查逮捕若干问题研究[J].人民检察,2001(7):39.
[4]孙谦.论逮捕与人权保障[J].政法论坛,2000(4):64.
[5]陈瑞华.审前羁押的法律控制——比较法角度的分析[J].政法论坛,2001(4):4.
[6]陈瑞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技术问题[J].法学,2005(3):16-27.
[7]彼得·G·伦斯特洛姆.美国法律词典[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41.
[8]J.Scott.Harr,Karen M.Hess.Constitutional Law for Criminai Justice Professional Woodsworth[M].Woodsworth Ltd,2005:161.
[9]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96-199.
[10]林钰雄.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25,226,233.
[11]约翰·斯普莱克.英国刑事诉讼程序[M].徐美君,杨立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5.
[12]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C·迈克尔斯.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M].吴宏耀,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25.
[13]贝尔纳·布洛克. 法国刑事诉讼法[M]. 罗结珍,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380-391.
[14]Steve Uglow.Criminal Justice[M].Sweet & Maxwell Ltd,1995:71.
[15]United States v.Watson,423 U.S. 411,96S. Ct.820,46L[Z].ED.2d,1976:59-89.
[16]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95.
[17]李昌林.审查逮捕程序改革的进路——以提高逮捕案件质量为核心[J].现代法学,2011(1):116.
[18]陈永生.逮捕的中国问题与制度应对——以2012 年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制度的修改为中心[J].政法论坛,2013(4):17-35.
[19]杨秀莉,关振海.逮捕条件中社会危险性评估模式之构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1):63-70.
[20]梁玉霞.逮捕中心化的危机与解困出路[J].法学评论,2011(4):145.
[21]刘计划.逮捕审查制度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J].法学研究,2012(2):142.
【责任编辑:甘海燕】
An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Approach of Arrest——With Assurance of Human Rights as the Logic Start Point
WANG Dong
(Xinjia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Urumqi830012,China)
Abstract:The writ system is basic in arrest system in western countries government by law, whose design is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ion to guarantee citizens’basic constitutional rights. Legislatively, arrest with the writ can only be carried out under emergency circumstances; however, it tends to be exercised more and more in practice. By analyzing the inner logic influenc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writ system,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function to guarantee the citizens not to be taken into custody unreasonably lies in its logic start point. It is of necessity to find a path integrating different appeals and values arrest system involved to establish a system mode keeping the value equilibrium of assuring the human rights and striking crimes.
Key words:arrest; an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approach; writ system
收稿日期:2016-03-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民族自治地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项目编号:09XJC820017)
作者简介:王东(1976—),男,经济学博士,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司法制度、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40(2016)02-0059-08
DOI:10.16713/j.cnki.65-1269/c.2016.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