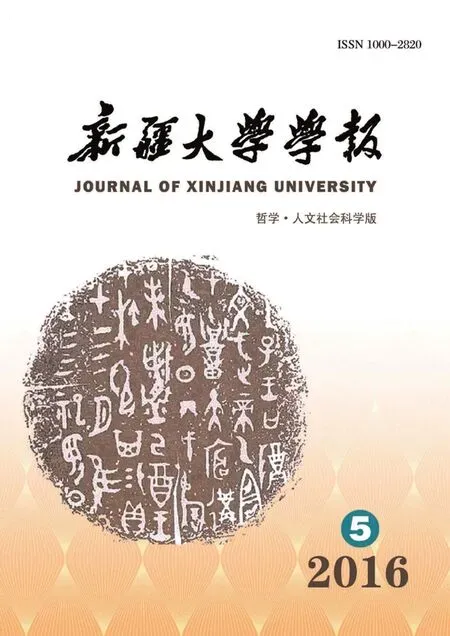唐前关中文化嬗替与本土文学创作之阶段性*
王 伟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自西周以迄隋唐,关中为文化奥区,其间本土文学灿然蔚兴,对汉唐文学走势与体式产生重要影响。然学界究治唐前学术与文化者多称道于山东,而言文学者则必以江左为善。自《后汉书》以至《隋书》,此类言说模式陈陈相因,关中遂仅以用兵盛地而为世所知,文化与文学则少人辞及。其实,自周秦取霸关中以来,其地文化长期为主流文化核心,并与本土文学互涵同构,推展时代文学体势之演进。
故本文以关中文化在唐前之嬗替为观测点,着力探究关中本土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及其成因,以期有助于还原与再现文学发展的历史场景,并藉此推深学界对唐前文学发展的研究。
一、秦汉时期关中文学的肇端
关中为姬周发祥地,及殷灭,沣、镐(今陕西西安西南一带)迭为周都,现存《诗经》中《周颂》《大雅》《小雅》及《尚书·周书》中的多数篇章,均创制于关中①丁宴《毛诗谱考证》、王应麟《诗地理考》、朱右曾《诗地理考》等均对《诗经》创作地域有细致推证。。平王东迁洛邑,关中文化与学术之优势地位渐次衰退,但文学活动却并未终止,《诗经·秦风》《尚书·秦誓》即是明证。此外,关中士人又东向入鲁,汲取思想养料,孔门七十二贤者中有三名来自凤翔(今陕西凤翔)[1],可见其守正进取的精神依然存在。
在战国前期,诸侯卑秦。秦孝公以商鞅为相,“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2],振衰起敝,但囿于保守的文化主张而使赢秦缺席于百家思想舞台。现存秦文以奏议与石刻为主,其中李斯《谏逐客书》风格雄肆,颇类孟轲。《韩非子》末附李斯与韩非驳难一则,犀利峭刻。传世之碑刻文字,文风典雅,内容质实,关中文风之质直朴素于此初现端倪。另《汉书·艺文志》载“秦时杂赋”9篇、《左冯诩秦歌诗》3篇和《京兆尹秦歌诗》5篇,虽今难睹全貌,但仍可由题目感知关中文化精神之余温。先秦是关中文学的滥觞时期,此期关中文学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官方作品屡遭兵火而毁坏殆尽,而民间歌诗却赖口耳相传,故体现出群体性和层累性特点;二为文学个体意识尚未觉醒,故创作既无署名意识,亦无保存意识,从而表现为零散而乏系统之特点。
汉兴而定霸长安,关中复为文学重地。《汉书》《后汉书》正传与附传共有传主717人,其中籍属京兆、冯翊、扶风三郡者有110位,占总数的15%。而据《汉书·艺文志》、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和《后汉书·艺文志》载两汉有作者籍贯可考之书籍共822种,其中出自三辅士人之手者139种,居总数之17%。文化兴盛与文学繁荣常具互涵同构之关系。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共收两汉文学家204人,其中籍贯可考者191人,其中关中籍者有韦孟、韦玄成、司马谈、司马迁、王隆、李固、杨恽、杨修、张超、苏顺、谷永、杜笃、冯衍、苏武、肖望之、班彪、班固、班昭、曹众、韦彪、赵岐、赵壹、窦卓、贾逵、李寻、梁鸿、苏竟、朱渤、杜邺、傅毅、马融、马芝、士孙瑞、张敞、傅簨及刘氏宗室文人54人。关中郡县占天下郡国比例之5%,然文学家数量却占全国总数的28%,关中诚为天下文学家最为集中的区域。细而论之,汉代关中文学又呈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创作呈现出文重诗轻之趋势。严可均《全汉文》共收文章1 490篇,其中关中作家作品有1 050篇,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于此相对应,诗歌创作则是汉代关中文学创作的短板,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为粗选对象,可看出关中存世作家仅有15位,共50余首诗歌。这既与时代文学大势相关,又表现出汉代关中浓郁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和重实用与内容、轻审美与形式的文学思想。
其次,文学创作的区域化特点。汉代关中共分3个州际行政区,即京兆、扶风和冯翊,下辖不到60县。其中近30余位作家相对集中在畿辅地区,尤以长安及郊区陵县最为显著。另外司马迁、杨敞等虽籍非京郊,然却早居长安,长久濡染于京师文化圈。《后汉书》三辅列传士人共60人,其中有47人出自于京郊陵县。伴随士人中央化趋势的加强,徙居三辅者多环陵伺居,从而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以陵县为外围的文学发展圈,相形之下,关中其它区域则成为文学的寂寥之地。
最后,文学发展的族群化特点。汉代关中文学家大多身负深厚的家族背景,如京兆韦孟、韦玄成、韦彪,韩城司马谈、司马迁,扶风班固、班彪、班昭,弘农杨恽、杨修,京兆杜笃、杜邺,武功苏武、苏顺、苏竟,扶风马融、马芝等。家族化已经成为文学发展的鲜明特点。如弘农杨氏自杨敞在昭帝朝为御史大夫、丞相始,就屡见史册。至东汉,杨震一系四世三公,祖孙父子相继掌朝六十余年,为家族之文化活动、文学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又扶风“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3]。这种累世公卿的局面不仅为文学创作或文学家族化的趋向提供动力,更对家族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风格特征及美学旨趣产生重要影响。
汉代关中文学上述特点的形成自有渊源。首先,与关中地区良好的文化积淀和雄厚的政治基础紧密相连。西汉立国后多次迁徙诸侯、功臣后裔及富贾、豪杰于诸陵邑,朝廷对陵县的政治关照和高素质人群的迁居,使得京郊陵县无疑成为当时政治与文化资源的“富矿”,从而对天下士子形成强大的向心力,进而使其成为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势区域,为关中文学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其次,也与关中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密切相关。作为政权核心,关中成为全国游学与仕宦者的首选之地。天下英才汇聚关中,极大地促进了关中士人的文化水准和文学修养。班彪幼年,“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其文学修养的涵育与培植,与远道而来的好古之人不可分割。马融早年不仅亲炙挚恂教诲,还与张衡、窦章、崔瑗、王符等相互往来,交往频繁。关中士人或因姻缘、或因地缘、或因血缘、或因学缘、或因业缘,遍交当世人杰,在文学创作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同促进了关中文学的繁荣。
另外,两汉关中文化世家多经学明敏,且累代相传,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化好尚和系统成熟的家学。如冯奉世诸子中,冯野王通《诗》,冯逡以《易》见长,冯立以《春秋》为世所知,冯参习《尚书》,皆各通一经。其子冯衍通《诗》,衍子冯豹亦善《诗》《春秋》。扶风冯氏世业儒学、以《诗》传家的家族文化在贾逵、班固、韦玄成等家族亦有鲜明体现。
总之,关中因地利之便而促成其对本土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之功,地域性文化甲族的涌起、肇基和家法家学系统的完善建构,为两汉关中文士成长创造了优越的外部环境,并导致两汉业文之士的聚居。
二、魏晋时期关中文学的继兴
宕至魏晋,关中饱受羌氐之乱与董卓之叛的影响,人口流亡而经济凋敝,已难有西汉武帝至东汉和帝、安帝时期的郁勃文气,文学创作明显衰落。出于保族全宗抑或前途名利的考量,此期关中士人多起身行伍,并至官显要。如武功苏则,少以学行闻,后以宗族部曲力量起家,为酒泉太守,转安定(今宁夏固原)、武都(今甘肃徽县一带),后随曹操南征张鲁、西平麹演,得拜护羌校尉(《三国志》卷一六《魏书·苏则传》)。京兆杜畿避乱荆州,以荀彧荐,后拜护羌校尉、西平太守,以军功显于时。时局纷扰,关中部分士人家族由儒质而武化的趋势逐渐明显。
曹魏后期,颜斐为京兆太守,他“起文学,听吏民欲读书者,复其小徭……又课民当输租时,牛车各因便致薪两束,为冬寒冰炙笔砚”[4]。由于关中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底蕴,且大族余势尚在,故至西晋,关中经济、文化逐渐摆脱汉末颓势而走向恢复。元康初,雍州刺史唐彬谓:“此州名都,士人林薮,处士黄甫申叔、严舒龙、姜茂时、粱子远等,并志节清妙,履行高洁。”[5]1219本土文化重现生机,从而带动了士人阶层的蔚兴。魏晋时期,关中文化与文学最为明显的特点莫过于家族化。“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6]20,陈寅恪先生于此洞见世家大族与地域乃魏晋及其以降学术文化转移升降之关键,甚合时代学术变迁之实情,堪为不易之论。其实,经学家族化背景下的文学家族化趋势早在西汉就已出现,此于前文已有叙及。魏晋由于分裂与战乱,学术文化发展呈现出区域性特点。在文化最为发达的洛阳,玄学清谈成为一时显学。而青徐一带儒学厚重,且又受到玄学浸染,故有玄学、经学并重之势。关中由于学风保守,故仍延持两汉经学传统与教育形式,而阻拒清谈玄风于关外,故大族仍以儒学、文赋见长。这是关中守正质实精神之体现。
曹丕于延康二年(220年)采陈群之言,颁布九品中正制,“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7]。受其影响,关中文学家族普遍呈现出士族化特点。以京兆韦氏为例,该家族在东汉至曹魏时期,于名、位、势等方面皆有出色表现,故最迟至曹魏时期其就已跨入士族行列[8],“自汉丞相贤以后,世为三辅著姓”[9],“世为三辅冠族”[10]1012。华阴杨氏“自震至凖七世有名”[5]2200,京兆杜氏亦为“中华高族”[11],扶风窦氏亦转型为地方豪酋,并渐次与胡族改姓者融合。可见,魏晋关中本土文学群体大都出现了士族化倾向。
三辅大族多累世儒学,故虽屡遭战火,但仍能维持文化区位优势。如京兆杜氏自杜畿以降,杜恕、杜预父子俱以文史称胜。杜预尤为甚,自称有“左传癖”,尝“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会盟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5]1031。曹魏时期“高视于上京”(曹操《与杨祖德书》)的杨修亦为其中代表。京兆韦端与大儒孔融交好,孔融在寄韦端的信中曰:“前日元将来,渊才高茂,雅量弘毅,伟世之器也。昨日仲将又来,懿性贞实,文敏笃诚,保家之主也。”而有“关西孔子”之称的弘农杨彪亦评韦康“年虽少,有老成之风,昂昂如千里之驹”[12]69,以孔融、杨彪所言,韦康、韦诞皆堪为栋梁。魏晋关辅文学成就最著者为挚虞,其“才学博通,著述不倦”,“尝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6]1427。其在文坛的优异表现,说明关中文学已重回文坛中心了。
值得关注的是,泥阳傅氏在西晋成为关中文学的新生力量。泥阳(今陕西耀州区东南)终汉一世仅有两位士人,即傅宽、傅毅。北地泥阳魏晋时始属雍州,文化大为改观,仅傅氏一族就先后出现了傅玄、傅咸、傅祗等数位文学家,并有十二部著述流传后世。北地傅氏在西晋文坛的崛起源于其地兴学倡教的扎实推进和临近州县的文化带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使其成为魏晋时期关中最具潜力的文学地区。
三、北朝杨隋时期关中文学的蔚兴
自隋之后,史家或学者言及北朝文学,率多以东魏、北齐为重镇,而对西魏、北周多刻意漠视。这当然与隋唐之际的南朝化审美倾向及其该倾向下对前代文学作品选择性保留与编选的思想休戚相关,也与西魏、北周及杨隋统治者虽娴于弓马,却在文化上主动接受南朝文学思想影响的文化同化趋势关系密切。其实,北朝关陇文学亦并非乏善可陈,据对《北史》《魏书》《周书》、严可均《全后魏文》《全后周文》《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等典籍记载进行爬梳搜辑,可知现今存名的有北朝关中文学家51人,其诗赋创作虽乏文质焕然之佼佼者,但风骨与气力俱健者亦不在少数。后世文学批评者对其所以褒奖远低于贬损,实拜隋唐文学批评话语系统之单一与典籍保存之非中立性立场所赐。
从作家结构看,十六国及北魏、西魏、北周、隋初的关中文学群体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即皇室文人群体和地方士人文学群体。
皇室文学群体是关中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其中以苻融、苻朗为代表的前秦皇室文人群体和以杨广为代表的周隋皇室文学群体声名最著。苻融“尝著《浮图赋》,壮丽清赡,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赋,临表不诔,朱彤、赵整等推奇妙速”[5]2934,“推其妙速”说明其文学创作既快且好。符朗著《苻子》,以寓言体表达淡薄世事的退让观念,文笔浅淡并具哲理色彩。北周、杨隋两代,定鼎长安,关中文学遂迎来较大发展,并呈现出迥异前代的属性。自苻坚始,关中士人或险仕胡朝,或率族依违各股势力之间,均体现出鲜明的武质色彩。符融自幼“旅力雄勇,骑射击刺,百夫之敌也”。王猛卒后,融代其位,淝水之战中率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亦以力称。而北周隋初之杨坚、杨素等皆为关陇军事集团的核心,其尚武用力之色彩也极为鲜明。可见北朝关中上层文人群体大都具有鲜明的武质色彩。
北朝时期活跃在关中文坛的还有地方士人群体,如京兆韦氏、杜氏,弘农杨氏,扶风窦氏和武功苏氏等。韦氏成员于北朝在军事、政治领域多有建树,于文化文学也颇留意。如北周名将韦孝宽“虽在军中,笃意文史,政事之余,每自披阅。末年患眼,犹令学士读而听之”[12]536。其兄韦夐“少爱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录数十万言”[12]544-546。京兆杜氏也有多人善属文,留意经传。“杜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符坚平凉州,父祖始还关中。兄坦,颇涉史传。”[10]1722“杜杲字子晖,京兆杜陵人也……杲学涉经史,有当世干略”[13]1017。武功苏氏也是关中望族,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苏湛“少有器行,颇涉群书”[10]1017,苏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13]381,宇文泰所颁示的“六诏”皆出其手,其模仿《尚书》,意在改变华丽的文风。从兄苏亮“少通敏,博学,好属文,善奏章……亮少与弟绰俱知名。然绰文章少不逮亮,至于经画进趣,亮又减之。故世称二苏焉”,“所著文笔数十篇,颇行于世”[13]678。此外苏绰、苏椿、苏亮、苏湛、苏让俱留名正史,可见武功苏氏文化素养之高。此外,安定梁盺、安定皇甫蟠、陇西辛庆之、京兆王子直等并具才名,“韦、辛、皇甫之徒,并关右之旧族也。或纡组登朝,获当官之誉;或张旗出境,有专对之才。既茂国猷,克隆家业,美矣夫”[13]704,实非虚誉。
南北朝时期关中文学活动具有独特的时代文化背景。
首先,关中文学文化活动对于都关中之政权而言,具有别正朔、示正统的积极文化意义,对于政权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比如公元545年,宇文泰欲革易时政,然鉴于“自有晋之际,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乃命绰为大诰”,文章模仿《尚书》,“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13]391。此举就历史潮流而言,明显属于逆势上扬,但对文坛主流而言,确属新鲜风气的重启,亦见出关中文化之独特性。虽然北周文学创作残余者无卓著实绩,但其所依循的文化革新之新路实为诗歌走向盛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其次,关中文学创作在北朝之所以不及山东,与外部文化环境与内部政治环境实具重要关联。十六国以降,关中战乱较河朔尤多,加之北魏都洛阳,遂使关中文化丧失地利之便。在文化建设方面,特别是书籍整理方面,东部的学术文化人才实远多于关中。在政治方面,北高欢和宇文泰皆出身北魏之代北“六镇”军人,对汉化持有复杂心态。但情况不同者在于,高欢统辖之山东地区,为汉族士人密集区。颜之推由南入北,久仕北齐,恐与他在文化与文学上挟南人之偏见不无关系。西魏君臣多为六镇旧卒,久染鲜卑胡风,对北魏汉化本就心存抵触。苏绰虽在《六条诏书》中言“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治民”[13]385,但实际上宇文泰在关中并无“求材艺者”之打算,其选人轻阀阅而贵实才,于文学与学术心存保守之见。况且西魏立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内忧与外患始终如影随形,确使其难以虑及或腾出手来进行文化更新。故《隋书》《北史》之《儒林》《文学(苑)传》言及北周,则曰:
周氏创业,运属陵夷,纂遗文于既丧,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苏亮、苏绰、卢柔、唐瑾、元伟、李昶之徒,奋其鳞翼,自致青紫[14]。
可见关陇文化不及山东,既与关中本土文化基础相关,又与施政者的主张紧密相联。
四、结 语
关中本土文学创作自先秦以降,历经两汉、魏晋、北朝和隋唐,其文学变化既受制于外部文化环境,也受到本土文化精神的影响,同时自身的文化文学传统也对其走向和嬗变轨迹具有内在的制约。在断续发展中,其自身文学精神既有与世沉浮之“变”的一面,也有持望传统之“守”的一面。这种文学面貌最终在唐代,随着政治一统和文化融合而最终汇入唐代文学发展的洪流之中。关中不仅为盛唐之音提供了空间环境,也为其提供了充足的思想文化养料,进而成为唐代文化与文学板块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