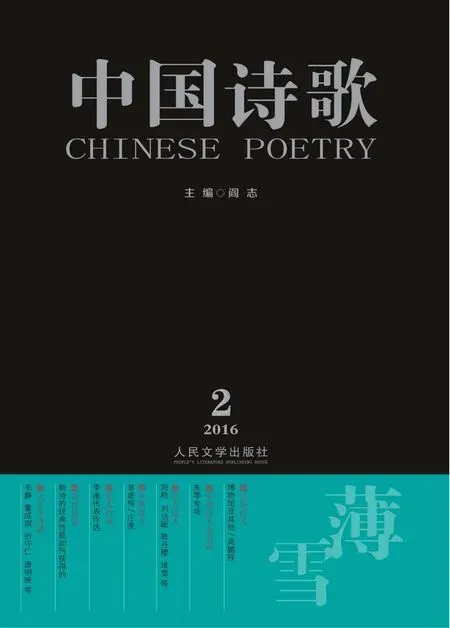何进的诗
何进的诗
光芒
戴上近视镜
朝旧月亮出没的地方张望
远方如碎了一地的叹息
近处浮动的光晕
像是太阳脸上的黑斑
摘下眼镜,眯起一条缝
影子模糊地弯着腰
阳光像服了兴奋剂
亢奋得如同极昼
这时,我只能看清一米以内的
事物。一米以外的世界
在渊面行走
如一条河流,流向另一条河流
光芒太强了
灼伤许多袒露的事物
那些哑巴一样隐忍的事物
还有些事物渐渐老去
这时,世界离我很近
那些光芒,是我前世留下的遗产
关于光
夜里,一束光躺在藤椅上
醒来,恍见一株青稞被收割的情节
情节里有命运的镰刀
有秋天盘桓的影子
地上的金黄落叶
宛如瘦削的灵魂
有一种辽阔的悲伤
透过这一道道光柱
我发现,世界裹在云与雾之中
漏下一些发黄的光斑
光有时像柔软的植物
又如一条通往梦境的河流
退守到时间裂缝的背面
黑夜便姗姗离去了
光劫走了一段段逆袭的光阴
在雨水打湿的地方
今夜有光落在我房中的藤椅上
它像主人似的安详
惊醒了我这个不速之客
壮阔
柔软的阳光,吹起了口哨
像娇嗔的外孙女踩响了大地的风琴
从燕晗山那边探出了头
星儿漏下的秘密也渐渐隐去了
初春,从木棉树顶端滑了下来
这时,整座城市像个偌大的花瓶
盛满了火一般的红杜鹃
燃遍所有的公园、街角、山坳和郊野
在湿漉漉的墓碑旁也嫣然而笑
一群燕子飞过,细雨浸润的清气
连同那淡然的箫音,都被燕子羽毛带走了
呵,啼血的勒杜鹃
有如上帝在伊甸园孕育的种子
绽放在爱人的玫瑰时光里
我忽然看见一只破蛹的蝴蝶
飞过勒杜鹃的一片片红
它是在渡过丰腴的大地前世或来世
尚未做母亲前的一次初潮
不是向上,而是向下
我喜欢在灵动的春天里
听夜雨歌,看夜雨舞
有时它像一个逗号,伸着懒腰
雏菊般端庄,欢快盛开
有时它像一串破折号,撒欢地
直奔荷塘,踩碎月色
有时它像一个句号,一头扎在
黄昏的蛹中,孵化一地阳光
夜雨,落在杨树的枝头上
渗入骨骼,生出满树新叶
从此,世界不再寂寞。有时
又如深醉的琴声,让我在湿漉漉的远方
体验动与静。在山坳里
变成落日与岩石的呼吸,让那些
孤独一路瘦削下去,留下微弱的叹息
成为写意画中,落墨最轻最深的一笔
有时我还喜欢闭上眼睛,遐想
伴随着夜雨,四处翻检着
史书中的破旧。香气氤氲
希望从被抛弃的事物中,找回
干草的味道,还有突然而致的喜悦
每听一次夜雨,就知道
生命又走了一程
不是向上,而是向下
向下,是大地亘古的不朽
白鹭
风化老了的礁石
被阳光削成了酒壶
酒壶顶端立着一只白鹭
头朝南面的海滩
像一个思想者
不远处,深圳湾的红树林
任性地飘拂起来
鸟群蜂拥地向南飘移
这是人类的朋友呵
我的匆匆过客
留下了深情温润的眷恋
它们要远行,相忘于江湖
要去寻找生命的密码
每年它们都要途经这里
与陌生的同伴相遇
我知道,它们当中有些生命
是在红树林中诞生的
这就是它们的故乡呵
它们与朦胧的雾岚一起飞走
并以梦的方式繁衍乡愁
而飞翔是必须的
有翅膀的生物,必定会
给自己画出一个远方
三月的还魂草
南方未走出阴冷的黄昏
阳光便修补起草木的天空
古榕的骨头
有如时间的画像
遂泛起新绿
三月的背影
让轻烟隔一层幻象
如穿过冬天游戏的过客
拴住新事物的魂灵
木棉花、勒杜鹃如期而约
手挽手啼血,热烈绽放
成为暮色中燃烧的诗句
呵,雪在三月融化了
融化成云的眼泪
那些凌空的藤蔓中有痴鸟驻足
生长起烟岚与欲望
这是莺飞草长的季节
连胚芽也在飞翔呵
三月是一年一度的还魂草
它不止一次地
让我在困倦的光阴中死里逃生
迷幻的暗冷
白天,很久没有阳光了
黑云暗恋一些浑浊的句子
我的身体颠簸起来,像一团梦境
思绪弯曲成西边的冷脸和愁眉
野草在空中梦游,宛如一堆忧伤的纸灰
哦,白天和夜晚一样的迷幻
从窗口望出去,教堂也已漆黑
涌动的雾霾潦草地打起哈欠
这时,世界的子夜只剩下祷告和钟声
暗冷如一条蛇袭来
这生命中正在承受之轻
使我弓起了背,如一只决斗的猫
木棉花
农历乙未年的春天
一些新的叙事
已渗透到
那五片拥有曲线的花瓣里去了
一朵朵的
朝孕育过寓言的地下蔓延
如落日的臀部
盛开出母性的火焰
不知道它诞生在
什么地方,藏于体内的灵魂
要飞到哪里去
它的身影,已成为南方的活化石
它有浑圆的
身姿,背负起优美的灵魂之重
花冠上的胎痣和纹路
就是真实的见证
坠落了,抖掉前生的
灰尘,成为地上饱满的忧伤
夕阳的苍茫
傍晚,大围山有些虚静
几声发皱的虫鸣,飘过了
山的那边脊背,嵌入了
深谷的挽歌。这时,我托着
夕阳,像托起亘古的
残梦。凉风吹来,第四纪冰期
脱去的外衣,留下潮汐腥味
那是夕光的味道。夕阳
西下,顷刻在我的手掌,晃动起来
于是,天地万物,也随着晃动了起来
人类和夕阳一样,升起又落下
老了,跌跌撞撞,如黄昏
归隐。这里的夕阳,由氧吧供养着
它游离尘世。人的心,常会高于
庙堂、炊烟,高于雷声滚滚的
天庭,但它永远也
高不过,亘古不变的苍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