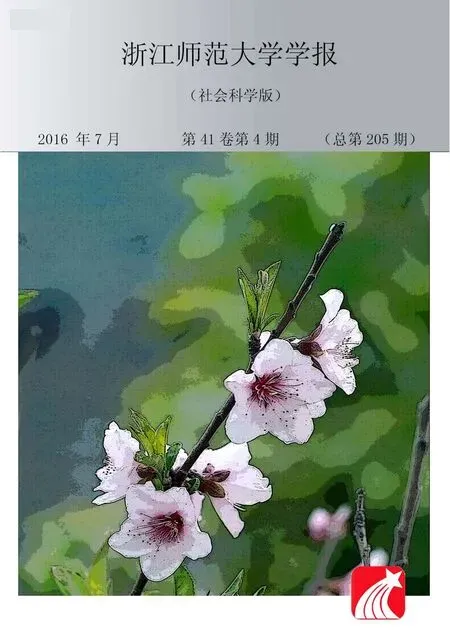梭罗自然思想研究补遗
刘略昌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上海 200083;上海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306)
梭罗自然思想研究补遗
刘略昌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上海 200083;上海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梭罗不仅著有大量自然文学作品,而且还对19世纪中期美国的科学发展、教育体制及印第安人的刻板塑造等诸多问题给予了深入思考,这些现实思考与其自然思想息息相关。梭罗主张进行超验的科学研究,他对美国自然史、生物学等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梭罗“以大自然为课堂”和“从做中学”的理念与后来进步教育运动的理念不谋而合。梭罗理想的人类是能与自然完美感应的印第安人。无论是对自然观的阐发,还是对教育观、科学观和印第安人观的论述,梭罗最终的目标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希望摆脱当时大多数人所过的静静的绝望生活,而去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精神生活。
关键词:梭罗;自然思想;补遗
梭罗是一位伟大的自然文学作家,其代表作《瓦尔登湖》《缅因森林》《科德角》等都充满了对自然景物大量的细腻描写。梭罗是自然散文之父,“在书写自然方面,美国文学史上没有其他作家能比梭罗和卡森写得更加动人深刻”[1]。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曾经指出,梭罗今天之所以能被人们铭记,是因为在其一生中他必须努力尝试着去深刻地理解自然。[2]布伊尔的言辞虽然多少有些夸大的成分,但却也道出了梭罗在阐释自然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近十几年来,随着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和生态批评的逐渐崛起,梭罗的自然思想在我国受到了普遍关注。中国梭罗批评是世界梭罗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深受美国梭罗研究潮流的启发,如它侧重于剖析梭罗自然观的形成原因,挖掘《瓦尔登湖》中蕴含的自然思想,对梭罗自然观进行整体审视,或辨析梭罗与爱默生及其他美国作家自然观的异同。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秉持强烈的批评自觉,尝试着开展梭罗与道家思想或陶渊明等中国作家自然观的比较研究。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成果丰富了世界梭罗研究,如程爱民(1998)[3]、苏贤贵(2002)[4]、陈茂林(2009)[5]、陈凯(2004)[6]、杨靖(2015)[7]等人的研究都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是,梭罗的思想丰富驳杂,他的自然观并不局限于《瓦尔登湖》中的文字表述。他也不像一般评论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消极遁世的自然作家,而是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现实的积极应对人。[8]对于当时美国的科学研究、教育体制及印第安人的形象塑造等诸多问题,梭罗都予以了密切关注。梭罗的这些现实思考与其自然理念息息相关,对之加以检视有助于拓宽既有的思路,从而为学界更全面地理解梭罗和梭罗的自然思想提供一个思考的视角。
一、梭罗超验式的自然科学研究
关于梭罗的科学理念,国内学人关注甚少,仅有高璐对梭罗科学发展观的统筹关系进行了一定勾勒。[9]国外学界则倾向于从生态的、人文的和象征的角度切入予以细析,[10]上述三种方法固然触及了梭罗科学观的某一方面,但梭罗的科学思想却比这其中的某种见解要复杂得多。梭罗的自然史写作及其科学观念与他对自然的反应密切相关。尽管梭罗用科学的眼光研究自然,并将其发现详细记录于笔端,但梭罗对那些只知积累自然知识的人却心怀疑虑:“科学的描述与诗意的生动描述不同,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看腻了的照相。科学的描述也不同于绘画和素描,尽管这种比较对科学过于不利。”在写于1860年的同一篇文章中,梭罗继续宣称:“所有的科学都是权宜之计,都只是通向绝不可能实现目标的手段而已。毕竟最为真实的描述,那种可以最为方便地辨识花朵的描述,就是目睹此物时人们内心激起的一种无法衡量而又生动感人的描述。尽管可以计算、测量并分析组成花朵的每个原子,但科学描述却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1]117梭罗更感兴趣的是感知自然而不是照相般机械地记录自然。不过与其他超验主义者相比,梭罗对大自然的兴趣更为浓厚,因为藉此他可以更加全面地把握真理。
梭罗对当时的科学发展持负面看法,其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科学强调对物种进行分类。梭罗生活在一个解剖学家和分类学家的极盛时期行将结束的时代,那时的自然史既不研究习性和生命史,更不试图把人类看作是自然的组成部分。美国批评家兼自然主义者约瑟夫·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曾经指出:“梭罗了解的唯一正规的科学是那些最不能激起哲学思想的内容。”[12]127-128梭罗从来不会为了解剖需要而急于杀死动物,因为他认为这不是获取真正知识的方法:“这样匆忙地杀死禽鸟或兽类,使活物变成骨骼……让我想起了杀鸡取卵的寓言。这个案例与杀鸡取卵毫无二致。”[11]109
由于梭罗更倾向于主观而非客观,因此梭罗观察结果的精确性和价值经常受到人们的质疑。1906年版《梭罗日记》的编辑布拉德福德·托里(Bradford Torrey)就认为:“令当今读者感到不解的是,这么激情洋溢的一位学者(梭罗)为何花了这么多年时间,却只学到了相对来说这么少的知识。”[13]xiii梭罗本人也意识到,很少有人能洞察自己科学观察的目的。受邀加入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时,梭罗在日记中写道:他拒绝了这一邀请,因为“事实上我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一名超验主义者,此外还是一个自然哲学家”;“我本应马上告诉他们,我是一名超验主义者。这就能立刻让他们明白:他们不会理解我作出的种种解释。”[14]
梭罗在进行自然观察时偶尔也出现了一些纰漏,个中原因不难理解。首先,梭罗缺乏足够的科学设备。直到1854年,梭罗才拥有了观鸟镜,接着他配备了望远镜而非更加高效的双目镜,他还把帽子当作采集植物标本的盒子。如有必要,显然他必须向别人借用显微镜,但梭罗有意不借助这些科学设备进行观察,因为梭罗认为它们会造成自然景象的扭曲变形。其次,当时也没有足够的参考书籍,图书馆里能找到的自然史大部分都出自英国人之手,因为美国缺乏能与之相媲美的同行。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的美国科学正处于起步阶段。
假如能读到当今的生态学研究成果,梭罗很可能会对当时科学视野的狭隘少些抱怨。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现在有些科学家对梭罗的开阔视野和研究方法流露出欣赏之意。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梭罗的研究方法固然不够复杂,但他却对整体环境的复杂关系表现出了敏感性。梭罗曾被1972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OxfordEnglishDictionary)认为最早使用了“生态学”(“ecology”)这一词汇。虽然进一步的研究证明这只是一场误会,但梭罗为未来的读者记下了自己对自然的敏感反应,这自然有助于促进“生态学”一词的广泛使用。
梭罗还被认为对科学研究的几个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梭罗曾独立完成一篇论文《森林的演替》(“The Succession of Forest Trees”),迄今为止它依然是关于这一主题的佳篇力作。此外,梭罗在日记中还对康科德周边的动植物作了巨细无遗的记录。对研究美国自然史的学者来说,这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对湖泊学家、生物学家、气象学家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家来说,梭罗的观察记录也极为重要,因为这些科学家发现,在从事相关科学研究时,梭罗做的这些田野笔记值得一再引用。
二、梭罗以大自然为课堂的教育理念
梭罗并非专门的教育理论家,但他开办过学校,从事过具体的教学改革工作。梭罗对教育问题虽然没有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但其教育思想却散见于《野果》《瓦尔登湖》等自然写作和《约翰·布朗最后的日子》等政论文中。只要细读梭罗的这些著作,我们就会发现梭罗在其中时不时地对当时的教育体制发表感慨。例如,在晚期创作的《野果》中,梭罗经常提及自然这座大课堂蕴含的教育价值:“我从未为这些演练预习(指采越橘)交过半文钱,也没置过装,但我从中学到的反而比在任何学校学得还要实在,而且获得回报”[15]82;“长浆果的地方本身就是一所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不用听斯托里、沃伦和韦尔耳提面命,你也能学到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学、医学和神学知识,田野比这些哈佛教授不知强多少”[15]83;“那一天我的疯狂‘拓展’(指采越橘)经历无论用什么好学问来换,我也不换。所有的文化都必然通往自由和发展,我顿悟到的远胜过我在书中学到的。那里对我就像一间教室,所有值得听取、值得见习的我都能听到、见到,而且我无法不好好上课,因为身边一切都在给我上课。正是这种经历,最鼓舞人奋进,终于促使人去深造,好生研究。”[15]85除了认识到自然的教育作用和意义,梭罗还宣称自然是最佳、最健全的教育体制,教育不应该只局限于学校教育:“我们总洋洋得意地自夸自己的教育体系如何高明,但为什么把教育局限在学校和教师职责之内呢?我们人人都是教师,而广袤天地就是学校。只关注研读书本或上学上课,却没想到眼前的万千风光就是一本内容丰富的教科书,这岂不是很可笑吗?”[15]352
在《约翰·布朗最后的日子》中,梭罗将当时的教育斥责为“奴性教育”(“servile education”):“我们似乎已经忘了:‘博雅教育’这个术语在罗马人那里最初指的是培养自由人;而纯粹为谋生而学习贸易和专业却被认为只是培养奴隶。明白了‘liberal’这个词的意思之后,我会更进一步宣称:虽然致力于艺术、科学或文学,但却完全不是有钱人和有闲暇的人,而只有那些诚挚自由的人才会在真正意义上接受到博雅教育。诸如美国这样的蓄奴制国家绝不可能容忍博雅教育这样的事物。”[16]167-168梭罗还斥责大学教师没能对学生求学起到思想引路人的作用:“教育的顺序已经颠倒过来了……在布道之后,一位颇有影响的大学教师觉得有必要告诉那些已经成年的学生:起初他也像那位牧师当时的想法一样,不过现在他觉得布朗是对的。但人们却认为,学生的想法远远超前于这位教师,正如他的观念领先于那位牧师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教师只是似懂非懂地意识到:他们没有起到引导作用,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力量的损耗,他们被拖曳着前行。”[16]164
梭罗对教育的论述涉及到许多层面,仅从教育类型来看,梭罗在不同著作中论及了中小学教育,批判了大学教育,主张进行社区教育和社会教育。梭罗的许多教育主张与后来的进步教育运动(progressive education movement)的理念不谋而合。梭罗强调“从做中学”而不是被动地在室内接受知识,梭罗主张学习当地的历史,研读自然而不是死记硬背那些与当地当下无关的教材内容。后来,杜威阐述的“从做中学”的教育主张风靡全球,传入我国后对陶行知、蒋梦麟等一批现代著名教育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实在此多年之前梭罗就已经用实际行动阐明了这一理念。在教学方法上,梭罗同样颇有进步教育运动论者的味道。梭罗采用的主要教学方法是理解法和诉诸儿童的道德感:“我想使教育成为一件对教师和学者来说都令人愉悦的事情。这种教学,我们希望持续到老,不应该时而在课堂,时而在大街上。如果能对学生更有帮助的话,我们应该力求成为学生的同伴,和学生一起学习。”[12]148-149在教育理论方面,梭罗认为:儿童本性为善,学校应该有助于促进儿童的内部发展,使其趋向完美。梭罗深信,通过实现人的全部潜能,可以建立一个人间乐园,梭罗的教育哲学就以此为目标。
梭罗还对当时的大学教育和大学师资提出了严厉批评。他在给爱默生的信中声称:哈佛大学教授各种学科知识,但却没有触及知识的本源,太多的教学时间花在了研究理论而不是实际应用上。实际上,梭罗主张的教育是博雅教育和功利教育的合二为一。梭罗批评当时的大学教师“只是哲学教授,而不是哲学家”,[17]他们对寻求真理不感兴趣,相反却生活在业已确立的制度的阴影之下,他们把光阴都用来捍卫现状了。在梭罗看来,真正的教育家应该致力于不断开拓学生的视野,应该鼓励和引导学生从大自然中获取真正的知识。
三、梭罗理想中能与自然完美感应的印第安人
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白人大量移居北美,美国文学中对印第安人的描写就从来不曾中断过。梭罗对印第安人也曾给予密切的关注,并在许多作品中有所记录。陈乐福[18]认为“梭罗却形成了与之(当时的美国史书)截然不同的印第安人观”这样的论断有些过于简单化,不足以揭示梭罗对印第安人持有的复杂态度,也未能指出梭罗印第安人观与其自然理念的关联。其实,从孩提时代起,梭罗就对与印第安人有关的一切怀有浓厚兴趣。在乡间散步时,梭罗很早就开始注意搜集印第安人遗留下来的物品。1848年后,梭罗开始大量阅读涉及印第安人的书籍资料。在生命最后的14年中,他至少阅读了与之有关的两百本图书,作了大约三千页的笔记。这超过50万字的笔记主要选自相关图书、小册子及部分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它们清楚地揭示了梭罗对印第安人的理解。
梭罗毕生都在寻求一种理想的生活,这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他也在寻找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人类,就是那种能与自然完美感应的人:“正是灵魂与自然的融合才使智力富有成效,才催生了想象。”[19]梭罗之所以迷恋印第安人,这与他对荒野的兴趣直接相关:“对我而言,印第安人的魅力在于他们在自然中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们是自然的居民而不是客人,他们在自然中能够从容优雅地过日子。”[13]253为了了解“印第安人是什么类型的人,他们在那里如何生活,他们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艺术和风俗,他们的想象和迷信”[20],梭罗花了大量时间来阅读有关印第安人的书籍。梭罗明白印第安人的生活具有一种有机完整性,这种理解有助于促使当代的文明获得新生。印第安人的生活体现了一种自然标准,它与人类文明的通用标准形成了抗衡。梭罗主要关注的是历史上而不是现实中的印第安人:“在美国的白人文化里,安息日沉闷无趣,人们顺从于毫无乐趣的工作和昂贵的舒适品。‘印第安的”一直是批判美国白人文化的一个基点。‘印第安的’意味着悠闲和健康。如果无知落后的野蛮人注定要毁灭,那么正如印第安斗士吃掉敌人的心脏一样,获得重生的野蛮白人或超验的印第安人也能汲取野蛮人的种种优点。”[21]213
梭罗把现实中的印第安人看成是历史上印第安人的影子。现实中的印第安人受到白人文明的腐蚀,但却无法吸纳白人文明的益处。梭罗受到了当时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印第安人许多陈规看法的影响。虽然通过大量阅读及1857年与缅因印第安导游波利斯的相遇,梭罗获悉了不少有关印第安人真实生活的情况,但他却从没完全摆脱对印第安人的思想偏见。在《为约翰·布朗请命》中,梭罗还把印第安人说成是口是心非的小人:“他们设想的是一个有着信仰和宗教原则的人,而不是一个政客或印第安人。”[16]147梭罗把印第安人和自己蔑视的政客归为一类,这清楚地表明他的见解难以脱离当时的美国主流社会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偏见,即认为印第安人缺乏精神追求。梭罗珍视印第安人的许多价值理念,然而“人们可能会暗自忖度:像他这样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独立的人,怎么会受到这些文化偏见的影响呢”[21]194?由此可见,梭罗接受的关于印第安人的教育并不完整。
梭罗赞美诸如海因斯、默尔温和古德温这样的康科德猎人,因为他们与自然保持着亲密接触,但在大多数康科德人的眼中,这些人不过是些流浪者。有两次,梭罗声称海因斯使他想起了印第安人。[22];[23]290梭罗曾经断言:“伐木人及其伐木经历更应受到注意。或许与任何其他人相比,伐木人的行为更应该在冬天标志着新的纪元。既然印第安人已经消失了,那么伐木人就是最接近自然的人了。”[23]244但正如印第安人一样,伐木人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他们缺乏精神自觉和审美意识。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梭罗在现实中都无法找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人。因此,他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希望将来能够涌现这样一种理想的人物。
在当今中国,梭罗作为生态批评的先驱被广大评论者所熟知,但他们对梭罗自然思想的理解过多依赖《瓦尔登湖》,未能充分揭示梭罗自然理念的动态演变。梭罗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其伟大在于他是一位圆形而非扁平人物,在于他所展现出来的复杂的多面性。不是一味寄情山水,超然于人世,相反梭罗积极介入现实,对19世纪中期美国的科学研究理念、教育机制以及对印第安人的认知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均建基于梭罗自然观的底色之上,但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延伸。其实,无论是对自然观的阐发,还是对教育观、科学观和印第安人观的论述,梭罗最终的目标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就是摆脱当时大多数人所过的静静的绝望生活,而去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精神生活。
参考文献:
[1]BROOKS P. Speaking for Nature: How Literary Naturalists from Henry Thoreau to Rachel Garson Shaped America[M].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80: ix, xii.
[2]BUELL L. Thoreau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M]//MYERSON J.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David Thoreau.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5:171.
[3]程爱民. 论梭罗的自然观[D].南京: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998.
[4]苏贤贵. 梭罗的自然思想及其生态伦理意蕴[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2):58-66.
[5]陈茂林. 诗意栖居:亨利·大卫·梭罗·的生态批评[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6]陈凯. 绿色的视野——谈梭罗的自然观[J].外国文学研究,2004(4):129-134.
[7]杨靖. “疾病的隐喻”:梭罗论健康与自然[J].外国文学评论,2015(1):44-57.
[8]杨金才. 梭罗的遁世与入世情怀[J].南京社会科学,2004(12):71-76.
[9]高璐. 梭罗自然观视阈下科学发展观的统筹关系[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4):90-94.
[10]BAYM N. Thoreau’s View of Science[J].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63(26):221-234.
[11]THOREAU H D.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Journal XIV[M].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906.
[12]HARDING W, MEYER M. The New Thoreau Handbook[M].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P, 1980.
[13]THOREAU H D.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Journal I[M].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906.
[14]THOREAU H D.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Journal V[M].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906:4-5.
[15]梭罗. 野果[M].石定乐,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16]ROSENBLUM N L. Political Writings: Henry David Thoreau[M].Beijing: th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03.
[17]THOREAU H D. Walden[M]. Princeton: Princeton UP,1971:14.
[18]陈乐福. 梭罗:一个后殖民作家[J].外语研究, 2005(2):75-78.
[19]THOREAU H D.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Journal II[M].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 Mifflin and Company, 1906:413.
[20]THOREAU H D.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Journal XI[M].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906:437.
[21]SAYRE R F. Thoreau and American Indians[M].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77.
[22]THOREAU H D.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Journal VI[M].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906:233.
[23]THOREAU H D.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Journal III[M].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906.
(责任编辑周芷汀)
Research on Henry David Thoreau’s Outlook of Nature: A Supplement
LIU Luechang
(CenterforPost-doctoralStudies,Shanghai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Shanghai200083,China;SchoolofForeignLanguages,ShanghaiOceanUniversity,Shanghai201306,China)
Abstract:Henry David Thoreau not only produced a large quantity of nature writings, but also actively pondered on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stereotyping of American Indian image in the mid-19th century, all of which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his outlook of nature. Thoreau conducte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a transcendental way, which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iology. Thoreau’s notion of making nature the classroom and learning by doing coincided with the idea of the later progressive education movement. Thoreau held that the ideal human being was the American Indian who could perfectly correspond with nature. When illustrating the notion of nature, education system, science development and American Indian image, Thoreau actually betrayed the same concern: people should lead a meaningful spiritual life rather than a life of quiet desperation.
Key words:Henry David Thoreau; outlook of nature; supplement
收稿日期:2016-05-06
作者简介:刘略昌(1978-),男,山东潍坊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6)04-007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