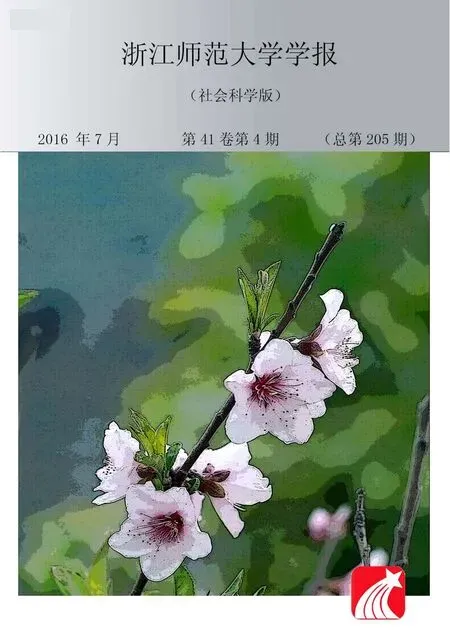清乾嘉年间西方“技艺之人”驻广州十三行商馆经理人
伍玉西
(韩山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 潮州 521041)
清乾嘉年间西方“技艺之人”驻广州十三行商馆经理人
伍玉西
(韩山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 潮州 521041)
摘要:清乾隆、嘉庆年间,在北京为清政府服务的西方“技艺之人”在广州十三行商馆设立了经理人,其职责是为他们转递来往于欧洲与北京间的书信、物品,并向中国政府推荐新的技艺人才。这种代理人最初是在清政府禁传天主教、广州一口通商以及澳葡当局取缔耶稣会的背景下,由乾隆帝批准设立的,在嘉庆朝早中期延续了下来。共有8位这样的经理人入驻过十三行商馆,各人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其中5位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由于来自法国的“技艺之人”受到澳门葡萄牙人的打压,对在广州设立自己的代表有着最为迫切的需要,因此广州经理人制度的建立与人员的变更主要与他们有关。广州经理人的设立表明,广州十三行不仅是1757-1842年清代一口通商时期中外经济往来最主要的场所,而且也是那一时期中西文化交往链条上最为重要的环节。
关键词:乾嘉年间;“技艺之人”;广州十三行;经理人;传教士
清乾隆、嘉庆年间,在北京为清政府服务的“技艺之人”向广州十三行商馆派驻了自己的代表——经理人(procurator),并且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procurator”或译为管区代表、司库、帐房、经理员等,①本是大航海时代天主教各修会因传教需要而在一些重要站点设立的代办机构,主要职责是筹措和管理传教经费,为传教士提供后勤服务,转递书信和物品等。[1]348-349乾隆、嘉庆两朝本是清政府厉禁天主教传播的时期,为什么还要批准那些有着传教士背景的“技艺之人”在广州设立经理人呢?有哪些人担任过这一角色?他们的命运如何?对这些问题的考察,②有助于厘清乾嘉年间清政府对外政策变化的脉络,还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广州十三行在那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技艺之人”进京与驻广州十三行经理人的设立
明崇祯年间,汤若望等一批具有一技之长的西方传教士受聘为明政府修历和督造火炮,开西方“技艺之人”为明清两朝政府服务的先河。入清后,汤若望出任顺治朝钦天监掌印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虽然对天主教态度各有不同,但在延揽西洋技艺人才这一点上是共同的。除个别人之外,应召为清廷服务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传教士而言,为中国朝廷效力当然只是一种手段,他们是想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来博得中国皇帝的欢心和上层官员的支持,进而为传教创造条件。尤其是雍正禁教后,他们能以合法身份居留京师,管理京中四堂教务,并乘机秘密发展中国信徒。双方各有所需,因此在康雍乾三朝,大批怀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受聘为清政府服务,从事天文历算、翻译、医药、机械制造(主要是钟表制造)、绘画、雕刻、音乐、测绘、建筑等方面的工作。
从康熙朝开始,西方“技艺之人”进京服务形成了一整套程序,包括申请、推荐、批准、考察、伴送等环节,因此在进京前他们必须在登陆口岸停留一段时间。笔者发现,除了康熙朝进京的白晋和张诚这两位法国人于1687年7月在宁波登岸外,[2]8其他技艺之人都是在澳门和广州上岸的。康熙朝时,在广州停留者或住怀远驿,或入住天主教各修会在广州的会院。③进入雍正朝,清政府的天主教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先是1724年雍正禁教,各地的传教士除留京效力者外,余被遣送至广州安插。接着是1732年署理广东总督印务、广东巡抚鄂弥达驱逐广州传教士到澳门,并拍卖了各修会在广州的住所和教堂。[3]1221732年驱逐事件发生后,担任钦天监监正的戴进贤曾上奏雍正,“恳乞留二三西洋人在省城居住,以通澳门音信”。[4]173他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④雍正虽然厌恶天主教,但在利用传教士为清廷服务这一点上与康熙倒是一致的。进入乾隆朝,乾隆帝一方面继承了雍正的禁教政策,另一方面又招揽了大批西洋技师。在1732年至1762年这30年间,批准进京服务的西洋人要在澳门接受广东官府的核查,情况属实后再来广州办理进京的相关手续。从法籍耶稣会士钱德明1752年10月的一封信中可知,他们在广州等待期间是不能下船的,必须呆在船舱内,日用所需及进京的文件概由中国差官代为办理。[3]372-373
在雍正朝和乾隆朝早期,推荐技艺人才的途径只有两条,一条是葡萄牙贡使推荐,另一条是已在京服务的传教士上奏,尤以后者推荐的为多。然而,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后,清政府对“外夷”管束日益严格起来。这年十月,两广总督李侍尧上《粤东地方防范外夷条规》,经军机处议奏后旨准颁行。其中规定:禁止“夷商在省住冬”;禁止“外夷”雇人传递信息;“外夷一切事务,似宜由地方官查办,庶为慎重”;“至澳门寄住之西洋人,如有公务转达钦天监臣,应令该夷目呈明海防同知,转详臣衙门酌其情事重轻,分别咨奏办理。”[4]337-340也就是说,以后在粤西洋人如有公务呈报,必须由澳门议事会理事官向设在前山寨的海防同知禀报。与此同时,在钦天监等机构任职的西洋人也不能再直接上奏言事,有事只能呈文军机处,再由军机大臣等转奏。这种规定的出台,受影响最大的是法国人。原来,在1773年耶稣会解散前,进京服务的西洋技师来自三个传教组织,即葡萄牙系统的耶稣会、法国系统的耶稣会和罗马教廷传信部。这三个传教组织在中国是有矛盾的,尤以葡、法争斗为烈。葡萄牙享有远东“保教权”,⑤受其“保护”的耶稣会士早在明嘉靖年间即已进入中国传教,并于1623年建立了独立的中国副会省。进入17世纪后,随着葡萄牙帝国的衰落,他们独占的远东“保教权”受到其他势力的严重挑战。受法国国王“保护”的耶稣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17世纪80年代强行闯入中国传教区。在1732年鄂弥达驱逐广州传教士时,法国耶稣会被迫把活动基地从广州迁到了澳门。葡萄牙人为维护其在远东的独占利益,极力排斥来自法国的耶稣会士。事实上,自“防夷条规”出台后,澳门议事会从来就没有向广东官府推荐过一位来自法国的“技艺之人”。
不久后,在华法国耶稣会又遭受重大打击。从18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葡萄牙、西班牙、那不勒斯、帕尔玛、拉丁美洲、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着手驱逐耶稣会士,或者取缔耶稣会组织。[5]85-861762年7月5日,葡萄牙澳门总督奉印度总督之令,拘捕了所有在澳门的耶稣会士共24人。无论是葡萄牙系统的,还是法国系统的,统统送回葡萄牙本土监禁,耶稣会在澳门的产业也被变卖一空。[6]725-727在葡萄牙本土和海外“属地”上,耶稣会成了非法组织,会士不能再以合法身份进入和居留澳门。这样,他们在广东境内唯一可以作短暂停留的地方就只剩下广州西南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区了。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陆续有法籍耶稣会士来到这里,混居在西方商人中间。他们想以“技艺之人”的身份进京,却又申报无门,因例禁西洋人在广州过冬,所以贸易季节一结束他们就得离开,到法属殖民地印度洋西部的毛里求斯岛暂住一段时间,到第二年乘信风船再来。
1765年,一位具有医疗特长的法国耶稣会士巴新来到广州,想进京服务,却又申报无门。适逢乾隆第五子腿患肿疡,求西医诊治。[6]1026在京的法国耶稣会士得讯后抓住了机会,请宫廷画师意大利人郎世宁出面,向乾隆推荐了巴新。乾隆谕令署两广总督杨廷璋派员查实,由驿护送来京。[7]254借此机会,他们向清政府请求解决他们信息传递困难的问题。乾隆三十一年(1766),法国技艺人蒋友仁等呈文军机处,声称在京法国人的乡信不能及时递接,因为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以来,葡萄牙人不允许法国人到澳门寄居,“是以京广两地信不易通”。他们希望中国政府能“施一善法”,使他们的“乡信易通”,“天文、医科、丹青、钟表等伎陆续来京效力,稍伸蚁悃”。为加重份量,他们还声称:为感谢皇恩,他们愿进土物,“今闻乡国来人,带有丝绒织就花草人物单子六张,亦因乏人料理,无能发送来京”。[4]377杨廷璋于三十一年(1766年)七月二十日奉旨回奏,答复了蒋友仁等人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请求。他一方面完善了在粤洋人公务呈报制度,规定在澳门的仍按原方案执行,住在广州十三行商馆的洋人如有公务禀报,则先告知中国行商,由行商禀南海县,南海县报两广总督,两广总督再上奏请旨。但另一方面,他借口蒋友仁等人反映的情况不属实,主张西洋人事务“应请仍照成例办理”,甚而建议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来限制京粤洋人间的书信传递。[4]378-380
蒋友仁等见目的没有达到,遂于三十二年(1767年)再次呈文军机处,明确提出,请求同意留下一二位法国人长住广州十三行商馆,让其为在京法籍“技艺之人”转递书信、物品。他们的理由是:从欧洲寄往北京洋人的土物家信,“由各国洋船带至广东省城洋行交卸,俱要收付回帖,并讨水脚船费,又查收在京堂内修士西洋人家信及一切所要单帐寄回故里,以便备办,转年寄来等事”,必须得有“本国一二人在广东省城洋行居住办理方妥”。他们还宣称,向年原留有法国人邓类斯在广东洋行居住,代他们管理此类事务。广东官府例禁外国人在广州过冬,看守余货的人也得到澳门居住,因澳门的葡萄牙人独不准法国修士洋人存留,所以只得随商船来往于广州与法国之间。但本年内邓类斯“偶得头晕之症,不能乘船过洋”,所以请求同意让“邓类斯一人常在广省洋行内居住,免其往来涉海之苦”。[7]275
邓类斯是法国耶稣会士,冯承钧在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时将其取名为费若瑟。[6]768他于1737年来华,在江西、江南一带秘密传教多年,后转往广东,1764年任法国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兼司库。[8]787适逢葡萄牙政府逮捕澳门耶稣会士,他在广东无法容身,曾有一年时间躲在珠江上的小船里。经过一番磨难后,“终密入广州,寓某商长家”。[6]768-770“某商长家”,译为“某行商首领商号内”更为合适。1765年左右,由潘振承出任公行商总,因此邓类斯极有可能租住在潘振承的同文行内。蒋友仁等闻知其遭遇后,想为他谋一合法身份,因他年过六旬,不能以“技艺之人”的身份荐于朝,遂以需在广州为在京法籍技艺人设一转信人呈请。军机处接到蒋友仁等人的呈文后,转奏道:
伏思洋人往来广省至冬底洋船南去,如果需看守余货,仅留本国一二人在行内居住,其事似属可行。但查阅禀内情节,前任督抚既不许其在省过冬,俱令在澳门居住,俟来年夏令再行随船到省,其防范约束自必有故。且各处洋人俱住澳门,独拂郎济亚国(即法国——作者注)并不准一体存留,此中有无违碍情形,亦难悬揣。[7]275-276
军机大臣们因此建议敕下两广总督李侍尧查实,并评估让法国人邓类斯一人在“省城洋行常住”的可行性。李侍尧奉旨派员核查。香山知县张德洄奉命要求澳门议事会对葡萄牙人捉拿“大小三巴寺僧”(即圣保禄书院和圣若瑟书院的耶稣会士)之事和法国人邓类斯的情况作出说明。[9]514李侍尧据调查结果回奏称,澳门葡萄牙人曾逮捕“三巴寺僧”,而邓类斯与“三巴寺僧”素有交往,因此不敢往澳门。他认为“粤东省会为五方杂处、人烟辏集之区”,禁止洋人在此过冬的大方针不能变,但既然澳门葡人与法国人邓类斯之间“彼此既有猜疑之事,恐致将来别生衅端”,“且邓类斯为在京效力蒋友仁等托寄书信之人,亦与贸易夷商往来,不一者有间,似应准其在于省城洋行居住。责令寓居行商保领约束,毋许纵令与汉奸往来勾结,及任听番厮出入滋事。其余各国夷商,仍照定例遵行,不得援以为例,藉口逗留省会过冬。”[7]278
李侍尧首开此例,实是奉旨而行。乾隆的御旨虽然比较模糊,但善于揣摩皇帝心理的地方官员一下就能明白其中的玄机。乾隆对西洋科学和宗教没什么兴趣,但他偏爱西洋奇器、西洋艺术,需要有一批精通其道的西洋人在身边当差,以满足他变化不居的西洋爱好。耶稣会士在明中叶即已来华,积累了与中国皇帝和上层官员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加之他们在欧洲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技能操练,有扎实的人文功底和很好的科学素养,能满足乾隆各种怪异的要求。有这样一批西洋人在身边当差,乾隆何乐而不为?乾隆对他们也很关照,即使在禁教条件下,对他们有限的秘密传教活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受“防夷条规”的限制和澳葡当局取缔耶稣会的影响,传教士在广东没有了立足之处,乾隆破例同意他们在广州设立代表,寓居十三行商馆,为他们提供传递书信、物品方面的服务。
二、乾隆朝中期的广州经理人
从邓类斯开始,在乾嘉年间形成了京城技艺洋人派驻广州十三行商馆经理人的制度。邓类斯的公开身份是“在京效力蒋友仁等托寄书信之人”,因此得到了清政府官员的安全承诺,下澳门时不会受到葡萄牙人的迫害。[6]770实际上,他还扮演了法国耶稣会与广东官府联络人的角色。邓类斯在中国内地秘密传教多年,知道非法入境的危险,所以当有新来的法国耶稣会士时,他就设法把他们作为“技艺之人”推荐给中国政府,不能荐于朝的则劝他们回国或去毛里求斯岛,不主张他们非法潜藏。据笔者统计,在邓类斯得到特批居留十三行商馆后的短短6年时间里,有8位法国耶稣会士打着有各种技艺的幌子顺利进入北京。他们是金济时、晁俊秀、梁栋材(即甘若翰)、严守志、齐类斯、贺清泰、李俊贤和潘廷璋。这是与邓类斯长驻十三行,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广州的官员和行商,向他们作鼎力推荐分不开的。
或许是受到法国耶稣会的启发,在京葡萄牙系统的技艺传教士也于1770年在广州设立了经理人,任职者为中国籍神父艾若翰。艾若翰,又写作艾若望,费赖之说其人生于广西,长于澳门,1743年进入修院,1754年晋铎。从1770年开始至1784年乾隆朝大教案爆发,住在十三行商馆区,为葡萄牙系统的耶稣会士办理书信、物件转递事宜。[6]846因他是中国人,居留十三行地区也就免于报批了。费赖之可能把他的籍贯弄错了,据广东巡抚孙士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八月二十一日的奏报,艾若翰是江西临川人,本名球三,“住在广东省城西关外,办理西洋人寄信事务”。[7]359“广东省城西关外”即十三行商馆区内。
然而好景不长,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被迫宣布解散耶稣会。消息于第二年传到中国,原来在华的耶稣会士统统成为在俗修士,失去了自己的组织。在这样的形势下,教廷传信部试图借机全面接管中国传教事务。教廷传信部成立于1622年,从欧洲各修会招募传教士派往中国。在耶稣会解散后,传信部一面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进行大规模的潜藏活动,一面与葡萄牙、法国争夺对华传教事权,广州经理人的人选问题即是其中之一。法国不愿放弃经营多年的对华传教事业,路易十六任命前法国耶稣会北京负责人晁俊秀为法国传教会会长及北京教区产业代管人,曾留学法国的中国籍神父杨德望为驻广州司库,嘉类思为国王与传教士之间的联络人。[10]28-29但在路易十六的指令到达中国之前,在京法籍传教士已向清廷推荐了新的广州经理人,理由是邓类斯年事已高,必须有新的人手接替他。⑦乾隆四十一年(1776),原法国耶稣会士汪达洪、贺清泰等人呈文军机处,称居广州“料理本国新来听用之人并一切事务”的邓类斯病老回国,现有西洋人席道明在广东居住,请允许让他“长住省城”,“接管一切”。[7]306虽然一些葡籍传教士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军机处还是要求两广总督李侍尧派员核实席道明的情况,如果没有问题,就让他接替邓类斯驻省管事。广州知府督同香山知县传唤了席道明,调查结果是:
席道明系拂郎济亚国人,乾隆三十八年搭夷商啵吐洋船到澳门,住居小三巴寺。因前驻广东省城办理往来书信之邓类斯老病回国,该国有信令其赴省按办。于乾隆四十一年七月来省,现寓陈广顺行内,平日并无过犯,亦非潜逃至省。[7]307
行商陈广顺和“澳门夷目唩嚟哆”(即澳门议事会理事官)各出具了甘结。席道明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士,西文名读音为哂摩咧地,[7]326即Nicola Simonetti,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到达澳门,任教廷传信部澳门司库,[10]20乾隆四十一年(1776)七月移驻广州,寓居广顺行,已事实上接替了邓类斯。李侍尧得到下属的报告后,同意了汪达洪等人的请求,同时强调:“仍责令寓居行商保领约束,毋许纵令与汉奸往来勾结,及任听番厮出入滋事。”[7]311
传信部在中国设立代办机构始于1705年。那一年,教廷特使铎罗在广州停留期间,设立了传信部广州办事处,其主要职责是“经管分发传信部的津贴,同时代表传信部向该部所派的教士转达命令”。[11]101因管理传教经费是办事处主任的主要职责,所以也称其为司库。作为教廷派驻中国的代表,传信部司库“是欧洲传教士、中国教士及圣廷之间的媒介”,[12]87他们“虽然不参与直接传教,但在派送经费、解决问题和差派新来的传教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3]3541732年,传信部司库被驱往澳门。经汪达洪等人的推荐,传信部司库席道明在耶稣会解散后得以移驻广州,成为京城技艺传教士驻广州经理人,主要为原法国耶稣会士和传信部传教士服务。
但席道明任事不到两年就死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七月初四日,两广总督桂林在给内务府的咨文中称,席道明在该年闰六月死于“省夷馆”内,葬于黄埔马鞍山。他还提出,席道明是汪达洪等人保举接办邓类斯事务的人,现在他死了,“如汪大洪等另行保举,接办有人,再行照例办理。”[7]327“汪大洪”即汪达洪,他与贺清泰在乾隆四十七年果然又推荐了新的广州经理人,他们呈文军机处称:
乾隆四十一年,蒙皇上天恩,准令西洋人席道明住居广东省城,料理本国新来听用之人并一切事务,达洪等得以在京专心效力。今席道明病故,无人接管。现有西洋人多罗、马记诺二人在广东居住,若令多罗、马记诺长住省城,接管一切,实为妥便。[7]339
两广总督巴延三奉旨派员对哆啰、马记诺二人进行调查,结果是:
兹据洋行商人潘文严(岩)、蔡世文、陈文扩、石梦鲸、蔡昭复禀称,商等遵查西洋国夷商多罗、马记诺二人,于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内附搭西洋澳船来粤,现在省城外晋元夷馆居住。查该夷自到广以来,因席道明病故,该夷接替代办一切事务,均属妥协。[7]339-340
巴延三于是同意让他们二人住驻十三行商馆,接替席道明的位置。
哆啰、马记诺都是意大利人,圣约翰布道会士,[12]103乾隆四十六年(1781)八月来到广州,住在“晋元夷馆”,时人称为“哆啰夷馆”,[7]359,380或“哆啰馆”。[7]409哆啰是传信部的广州司库,已事实上行使了之前席道明的职责,四十七年(1782)又获清廷的批准。马记诺是哆啰的助手。汪达洪是前法国耶稣会士,与另外两位法籍传教士贺清泰、梁栋材一起反对由路易十六指定的中国传教区负责人晁俊秀。[6]966路易十六本已指定由中国籍神父杨德望任广州司库,但汪达洪等人先是推荐了席道明,接着推荐了哆啰,杨德望实际上没有到任。席、哆二人都为传信部系统的传教士,哆啰还是意大利人,法国人的内部矛盾以及汪达洪等人的“基督教国际主义”终酿成巨祸。
在耶稣会解散前后,一大批服务中国多年的耶稣会士或因年老,或因修会解散过于忧伤而相继过世,京城的技艺洋人越来越少,乾隆为此两次发布招揽西洋人才上谕。而此时的欧洲出现了中国皇帝准备驰禁天主教的传闻,认为“使中国人皈依天主的时候到了”,从1782年开始,欧洲各国纷纷派遣传教士来华。他们为进入内地,大多聚集在“哆啰夷馆”。[12]28哆啰除了推荐一些传教士作为“技艺之人”进京外,还安排了本系统的一批传教士非法进入内地潜伏。据哆啰本人供认,从1783年至1784年,在中国信徒的要求和接引下,由他经手向山东、湖广、江西、陕西派潜的传教士共有4批9人。[14]608-609这些人在出发前,住“哆啰馆”一至二天不等,“研究和分析向导——教士、讲授教理的中国人和专门从事这方面冒险活动的行家——为他们指出的路线”。[12]28-29中国教徒采取逐站护送的方式,把传教士送往目的地。乾隆四十九年(1784)四月,福建人蔡伯多禄从“哆啰馆”接走4位传教士,准备把他们送往西安,当行至湖北襄阳时,被当地驻军抓获。湖广总督特成额为此奏请“逐细跟究”各地“有无开堂惑众不法情事”,同时飞咨陕西、湖南、广东三省,查获与此案有关的人员,特别要求广东方面追查“发派西洋人之广东人罗玛当”的下落。[7]345乾隆下令各省进行搜查,并调查此事是否与西北回民起义有关,由此爆发了1784-1785年乾隆朝大教案。这个教案“涉及到全国十几个省份,共有18名外国传教士和数百名中国教民被捕入狱”。[15]215由于广东是此案的源发地,乾隆除申饬两广总督舒常、广东巡抚孙士毅外,还谕令他们对哆啰进行斥责,把他发交澳门,令其回国受惩处。至此,中国政府对哆啰的处罚还不是很严厉。但这年十一月,陕西在查案过程中获知罗玛当在本年内往山陕、湖广、山东、直隶等省派遣了10人,清廷对他的处罚顿时严厉起来,哆啰以及为他服务的一批中国信徒被逮捕,送往刑部受审。他不久后死于北京狱中。
在此案的处理过程中,广东巡抚孙士毅曾奏请裁撤北京“技艺之人”设在广州的经理人。他的理由是“内地民人传习天主教,皆由夷人常住洋行,与附近民人往来熟悉,致起勾引弊端”,因此“无庸另设专管洋人久住省城”。[4]454为达此目的,他说服了粤海关监督穆腾额,与他就同一个问题分别上奏。但乾隆不仅没有同意,而且把他们训斥了一番。广东督、抚只得按乾隆旨意办理,继续保留广州经理人。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让京城的“技艺之人”推荐,而是饬令澳门“头目”选择诚实之人作为“管理之洋人”,住省照旧办理。[4]470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二月,哆啰的助手马记诺在广东督抚的指定下,成为北京技艺洋人驻广州的经理人。[14]611
三、乾隆朝后期至嘉庆朝的广州经理人
“哆啰案”后,在华法国传教会日益陷入困境。虽然法国遣使会在路易十六的一再劝说下同意接管原法国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并有三位该会传教士于1785年顺利进入北京,但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接着是拿破仑战争,受此影响,来华传教士人数大为减少。他们即使到了中国,也难以进入北京。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推荐这一环节。广东巡抚孙士毅在处理“哆啰案”的过程中,以行商“失于防范,任由蔡伯多禄来往勾通”为由,令潘振承等行商“自罚”银12万两。[7]391受此打击,行商们对转荐西洋人才采取了消极抵制态度。据笔者统计,从案后的1786年到嘉庆开始驱逐传教士的1805年,广东督、抚奏报的技艺洋人共有4批7人,但没有一批一人来自行商的推荐,都是由澳门议事会推荐的。行商们的不合作态度由此可见一斑。葡萄牙本来就想遏制法国在远东的势力,加之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葡法成为战争敌手,葡萄牙女王诏令澳门总督禁止保护法国传教士,澳门议事会拒绝向广东官府推荐来自法国的技艺人才。[16]535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传教士要想以技艺之人进京就变得非常困难。
在广州经理人方面,法国人更为棘手。虽然广东督、抚指派由马记诺接替哆啰出任,但法国人被哆啰弄怕了,不再信任传信部的传教士。大约从1786年开始,前法国耶稣会士梁栋材获乾隆批准到广州休养。此时在北京甚有影响的法国遣使会士罗广祥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选定为法国传教士驻广州的经理人,并游说乾隆皇帝接受。但行商们“想方设法把该司铎召至北京”,[16]536梁栋材不得不于1790年12月离粤北上,仍回钦天监任事。[6]1020-1021此后,法国人又指派了在澳门的遣使会士韩纳庆任法国传教会的正式代表,负责推荐法国传教士进京。韩纳庆和另一位遣使会士南弥德费尽周折才成为“技艺之人”,1794年6月来到北京。[16]536也就是在这一年,法国人金德担任了本国传教士在广东的经理人,但他上省居住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只能呆在澳门“管理该国乡信等事”。[9]596
嘉庆六年(1801),法籍“技艺之人”罗广祥、巴茂真、贺清泰向管理西洋四堂事务大臣苏楞额呈文,称原来广东“料理京内北堂一切事务”的法国人金德回国,“现有西洋人魏腊尔一人,居住广省,接办一切,实为妥便。”[9]596当时北京有四座教堂,北堂是前法国耶稣会的教堂,后由法国遣使会接管。所谓“料理北堂事务”就是办理北京法籍传教士往来广东的书信、物品等事务。罗广祥等人呈文中提到的魏腊尔即意大利人维拉,是葡萄牙系统的遣使会士,1784年抵澳门,任教于澳门圣若瑟修院,1803年卒于澳门。[9]596“刘注”魏腊尔本是葡萄牙人,长期在澳门居住,1802年时已病重,担任经理人的时间不长,事实上没有上省居住。
在魏腊尔病重时,贺清泰、南弥德又推荐了新的经理人。据嘉庆七年(1802)八月初三管理西洋四堂事务大臣苏楞额给两广总督倭什布的咨文,苏楞额曾为贺清泰等人的请求转奏:
据天主堂西洋人贺清泰、南弥德呈请,前因承办北堂事务无人,曾经呈恳安置魏腊尔承办。今准两广总督咨覆,魏腊尔现已患病,不能到广接办。窃思清泰等北堂虽有六人:贺清泰、梁栋材、潘廷璋、巴茂正年俱衰迈,吉德明发疾,惟南弥德现年三十五岁,后继乏人。若广省无人接办,有情愿进京效力者无人呈报,乡信土物无人接收,不得不续恳天恩,现有西洋人明诺,与巴类斯德罗在吕宋行居住,二人俱可以接办本堂事务。为此泣求转奏,行知两广总督,于二人中安置一人接替,则清泰等继续有人,永沐皇恩于无既矣。等情。据情具奏。[9]599
贺清泰、南弥德的请求得到了嘉庆批准。两广总督倭什布在接到上谕后,檄行广州府,转饬南海县,详细查明。从嘉庆九年(1804)六月二十四日两广总督倭什布给内务府的咨文可知,南海县的调查结果是:“住广西洋人明诺,年力精明诚实,并无过犯,堪以接办北堂事务。”因此清廷决定:“嗣后凡有京内北堂寄交洋信等项事件,以及西洋人有情愿进京效力当差者,即饬令住广西洋人明诺接办一切。”[14]825明诺,又译为明坚,法国遣使会士,1793年到澳门,任教于圣若瑟修院。[16]556-557他于嘉庆五年(1800)潜至广州,“企图赴京不遂”,[9]599“刘注”但已经混居在商人中间,住所是十三行商馆区内的吕宋行,即西班牙馆。大约是在1803年,他居住十三行商馆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
牟泽雄:真正良性的评奖,就应该针对做出成绩以后(成果出版物)再进行,甚至都不需要自己申报填表之类的程序。我们还是接着刚才书法创作中的“新帖学”话题吧!
然而到了1805年,形势又发生了新变化。嘉庆虽然在临朝初期延续了乾隆的海外人才政策,引进过少量洋技师,但自乾隆死后(1799年),不喜爱西洋技艺的嘉庆对京城洋人的管束严格起来,设立了专管西洋人事务的四堂事务大臣,由内务府总管兼任,又规定京粤洋人之间的书信必须通过驿传,建立了一整套类似于现在邮政挂号信式的签领程序,所有“印领状”交内务府存档。1804年底,来自教廷传信部的“技艺之人”德天赐违禁雇人往澳门传递书信,信使在江西境内被抓获。[14]830清廷又兴大狱,查获的潜藏传教士或关或杀,中国信徒或遭流放或受杖责,是为“德天赐案”。案后,嘉庆对西洋人更加不信任,开始借各种名目有计划地遣返技艺洋人。嘉庆十六年(1811)时京城尚有11位洋技师,其中4位“学艺不精”的传信部传教士在这年即被遣送澳门,剩下的7人中又有2人被遣返,其他5人先后在北京去世。道光十八年(1838),毕学源在北京去世,天主教传教士作为清廷“技艺之人”的历史结束了。
“德天赐案”后,传教士已不可能再以“技艺之人”的身份进京,京城的洋人也逐渐减少,需广州经理人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少。嘉庆十一年(1806)四月十六日,澳门同知王衷通知澳门议事会:
照得办理西洋堂信件夷人明诺,寓居省城荷兰夷馆。现奉督部堂批行,饬令该夷下澳居住,以后北堂信件即令在澳照料,毋庸寓在省门洋行会馆。[9]600
四月十六日,王衷把寓居在十三行荷兰馆的明诺驱逐,“由省亲押下澳”,“交该夷目收管照料”。但澳门的葡萄牙人并不欢迎明诺,他遂于这年离开了中国。[9]604
明诺走后,法国人书信转递等事务由苏振生接办。苏振生,又译为李士奈,法国遣使会士,1801年到澳门。[16]5591805年,他与另一位法国遣使会士马秉乾获得进京许可,[17]14但当他们行至山东德州境内时,遭奉命而来的德州知府拦截。原来,在“德天赐案”审理完结后,协办大学士禄康等人奏请“将西洋外夷苏振生、马秉乾二人仍令回国”,嘉庆饬令沿途省份截住已在进京路上的苏、马二人。[14]891他们又返回了广东。苏振生出任广州经理人,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复,但明确规定他只能住在澳门,不得居留广州。[9]568-569不过他还是设法在那里寄居了一段时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在书信和日记中多次提到他,如1807年12月9日的信中这样写道:
罗马天主教会值得警惕,他们在北京的影响似乎有所复兴。有一个人获准居留广州,他的身份是内地传教士的“经理人”(Procureur)。[18]186-187
1808年1月5日的信中又说:
苏振生是一位天主教传教士,两年前中国政府勒令他离开中国,现在得到皇帝任命,作为北京传教士的“经理人”(Procureur)留在广州。几天前,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餐桌上我们相识了。他是一位法国人,很活跃,也很健谈。他跟查玛斯先生一起,住在瑞行里。[18]214
四、结论
在中国官方文献中,对本文所论经理人的称谓有:“寄托书信之人”“办理往来书信”之人、“料理本国新来听用之人并一切事务”之人、“代办一切事务”之人、“管理之洋人”“专管洋人”“管理该国乡信等事”之人、“料理京内北堂一切事务”之人、“办理西洋堂信件夷人”“承办北堂事务”之人、“办理北堂事务”之人等,不一而足,其职责是为在京西方“技艺之人”转递书信、物品,并向清政府推荐新的技艺人才。他们是在清朝禁传天主教和对外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制度的背景下,受1762年澳葡当局关闭耶稣会澳门通道的影响而出现的,存续时间为乾隆中叶至嘉庆中叶。有8位这样的经理人入住过广州十三行商馆,停留时间长短不一,其中有5位得到了正式批准。经理人的设立本是自乾隆中叶以来清政府对外实行有限交往政策的产物,而个别经理人的非法行为加剧了清朝君臣对“外夷”的不信任感,使这种有限的交往政策变得更加有限。由于在华法国势力受到澳门葡萄牙人的打压,对在广州设立自己的代理人有着最为迫切的需要,因此经理人的设立与变更主要与法籍人士有关。因1757-1842年间清政府只开广州一口通商,十三行商馆区成为了那时中外经济交往最主要的场所,本文所论经理人入住此地的事实表明:广州十三行也是那一时期中西文化交往链条上最为重要的环节。
注释:
①就本文的研究对象来说,中文文献中对他们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称谓,译为司库或帐房不能概括他们的职责,译为管区代表不太合适,因为他们跟传教没有直接的关系,译为经理人或经理员较为妥当,即经手管理相关事务的人。
②关于天主教会在中国设立经理人的相关研究有:戚印平著有《关于耶稣会驻澳门管区代表及其商业活动的若干问题》一文(载戚印平著《远东耶稣会史研究》第348-404页),浙江大学孔梦寻2013年的硕士学位论文《耶稣会商业活动中的管区代表研究 ——基于三份相关文书》,刘小珊、陈曦子、陈访泽合著有《明中后期中日葡外交使者陆若汉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澳门经理人;康志杰的《中国天主教财务管理制度——“帐房”为核心的考察》(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的“天主教传华及中西文化交流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2015年9月)以及吴伯娅的《澳门与乾隆朝大教案》(载“16-18世纪中西关系与澳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11月,澳门)都提及广州的经理人,但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
③据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的报告,1704年时广州有七座教堂。参[法]杜赫德编,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页。
④费赖之(Louis Pfister)在《戴进贤传》中说,雍正派人对天主教书籍进行审查后,发现“毫无可以降罪之处”,“由是遣发澳门之传教士三人得复返广州”(参[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56页)。他们复返广州干什么?如果是定居,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1735年10月写于北京的一封信中说,为答复戴进贤的请求,雍正两次召见担任宫廷技师的传教士。雍正除了明确表示要把传教士逐出中国外,再没有其它的态度(参阅[法] 杜赫德编,耿昇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Ⅳ],第92-100页)。汤开建先生的《雍正教难期间驱逐传教士至广州事件始末考》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考察,认为“雍正驱广州传教士至澳门,其意已决,在京西教士亦无可奈何”(参汤开建:《雍正教难期间驱逐传教士至广州事件始末考》,载《清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31页)。
⑤“保教权”实为一种传教独占权。新航路开辟后,伊比利亚人与罗马教廷在海外扩张上合拍,教皇授予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在新征服的土地上享有“保教权”。两国国王全权负责各自势力范围内的传教活动,享有传教士入境的审批权,但得给他们提供免费舱位、传教经费和安全保护。
⑥1685年粤海关设立后,一些来粤贸易的西方商业公司陆续在广州西南城外租用中国行商提供的房子建立商馆,逐渐形成了外商集中的商业街区,中国行商也在附近建有行栈。“其地理位置集中在广州城西南郊西濠西岸临珠江之地,即今十三行路以南至江边一带。”到18世纪六七十年代,商馆区“已基本成型”。参赵春晨、陈享冬:《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兴起》,载《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25-33页。
⑦邓类斯何时离开中国,难以确定准确时间。费赖之说邓类斯1779年尚在广州,1780年才回到法国(参[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770页),中文文献反映他在1776年即已回国。但至晚到1776年,他不再履行广州经理人的职事(参[法]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787页)。
参考文献:
[1]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伊夫斯·德·托玛斯·德·博西耶尔夫人.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M].辛岩,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3]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Ⅳ)[M].耿昇,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耶稣会简史[M].谷裕,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6]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一册)[G].北京:中华书局,2003.
[8]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M].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9]刘芳.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G].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
[10]张先清.传教士、民族主义、经济利益——1774-1784年北京天主教团体的权力交替[M]//吴义雄.地方社会文化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1]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12]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M].黄庆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3]NICOlAS S.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1:635-1800[M]. Leiden:Brill,2001.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二册)[G].北京:中华书局,2003.
[15]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16]荣振华.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M].耿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7]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三卷)[M].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18]EILZA M. Memori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Vol.1[M]. Lo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 and Longmans,1839.
(责任编辑廖向东)
Procurators in the Guangzhou Thirteen Hongs Dispatched by Western Technicians and Artists During the Reigns of Qianlong and Jiaqing of the Qing Dynasty
WU Yuxi
(CollegeofHistoryandCulture,HanshanNormalUniversity,Chaozhou521041,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reigns of Qianlong and Jiaqing of the Qing Dynasty,procurators were dispatched to the Guangzhou Thirteen Hongs by western technicians and artists who served the imperial court of the Qing in Beijing,responsible for delivering their letters and articles between Europe and Beijing, and recommending new technicians and artists to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The policy of appointing procurators was first ratified by the Emperor Qianlong, when the Qing Government prohibited Christianity and Guangzhou alone was open to foreign trade, and the Portuguese authorities in Macao outlawed the Society of Jesus at same time. It was then still applied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 of Jiaqing Dynasty. Eight procurators, five of whom having obtained permission from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once resided at the Guangzhou Thirteen Hongs and each remained there for a varying length of time. The establishing of procurator system and personnel changes was mostly related to the technicians and artists who came from France, for they were suppressed by the Portuguese colonists in Macao and cried for agents of their own in Guangzhou. Procurator system of Guangzhou manifested that,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anton System(1757-1842),the Guangzhou Thirteen Hongs were not only the leading site of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but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link in the chains of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Key words:the reigns of Qianlong and Jiaqing of the Qing Dynasty; western technician and artist; the Guangzhou Thirteen Hongs; procurator; missionary
收稿日期:2016-05-30
作者简介:伍玉西(1965-),男,湖南新化人,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江南城镇通史”(15FZS007)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6)04-0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