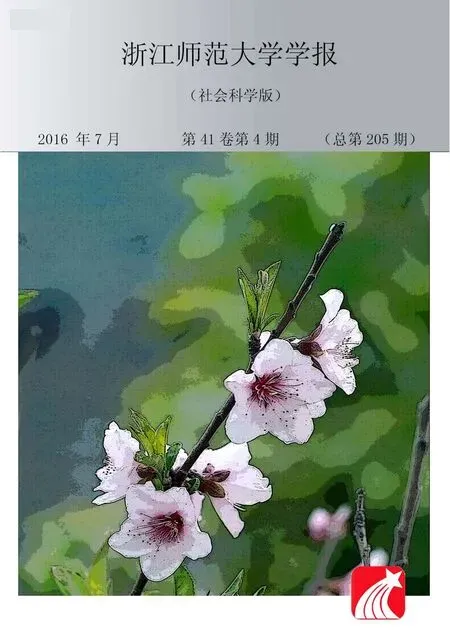“同形异构”的聚合
——《水浒传》与《儒林外史》的另一种文化阐释
葛永海, 孔德顺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同形异构”的聚合
——《水浒传》与《儒林外史》的另一种文化阐释
葛永海,孔德顺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从特定角度来看,《水浒传》是好汉聚义,《儒林外史》是文人雅集。两书的聚合描写富有张力,所谓“同形异构”,乃指两书人员流动的方式主要都是由散而聚,发展轨迹同中有异,生动展现了封建时代的游侠与游士以仪式化的方式各自在江湖与庙堂之间演绎文化身份上的进退与转换。尽管两书终极理想内涵相类,都体现出对“义”与“礼”的呼唤和重建,但小说相近的幻灭结局折射出重建文化秩序而不可得的悲悯,正是这种深刻的文化反思使得两书成为中国武者小说与文人小说的典范之作。
关键词:《水浒传》;《儒林外史》;聚合仪式;同形异构
《水浒传》和《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长篇章回体小说的杰出代表,描写对象上前者是英雄好汉,后者是知识分子。内容上前者是通过好汉起义,讴歌反抗精神,后者是通过文人百态,讽刺儒林众生。两书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实则不然,从特定角度来看,两书无论是情节结构、小说主题还是文化意蕴层面都有着某种特殊的相似性。语言学中的“同形异构”是指词形和词序相同,而内部构造不同的一种句法现象,这里我们不妨引用此概念,把两书中这种类似的现象叫做小说中的“同形异构”。“同形”包括外同与内同,外同即结构相似,内同即主题趋同,“异构”则是路径不同。通过对这两部小说“同形异构”的梳理,我们可以较充分理解明清小说经典在思想主题探索和文化人性反思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与深度。
《水浒传》和《儒林外史》,或描写好汉起义,或描写文人轶事,一个尚武,一个崇文,前者是流落的武者,后者是游走的文人,虽然表面上看来描写对象是不同的,但实际上他们都属于同一个群体——游民。王学泰认为游民主要指“一切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特点就在于‘游’”,并且指出他们的特点是“缺乏稳定的谋生手段,居处也不固定,出卖劳动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财务的,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1]游民在宋以后大量出现,并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群体。在《水浒传》和《儒林外史》中这类人群尤为突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手段和方式,表现多种多样。有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靠出卖劳动力的,如《水浒传》中街头卖狗皮膏药的打虎将李忠、《儒林外史》中靠吹嘘和杂耍为生的张铁臂;有经历过艰辛的冒险或者游荡四方的,如《水浒传》中豹子头林冲、《儒林外史》中的马纯上;有科举失意谋求他路的,如《水浒传》中的吴用、《儒林外史》中的牛布衣;有通过非法手段谋取财物甚至性命的,这在《水浒传》中颇为常见,《儒林外史》中也不乏其人,如骗取船家钱财的严贡生。
因此大体上,我们可以将《水浒传》中的游民视为游侠,而将《儒林外史》中的游民视为游士。他们的共同点是脱离主流秩序,并且生活在庙堂与乡土社会之间的间隙中,正是因为脱离,反而为他们的聚合提供动力,《水浒传》中好汉结盟与《儒林外史》中的文人雅集正是这群游民在失序与回归中表现出来的极具特色的人生运行轨迹。
一、两种“由散而聚”的仪式叙述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之称和所谓“制礼作乐”之说,礼仪已成为华夏文明之文化秩序的一种象征,其具体表现形式即为各种典礼仪式。仪式由传统习惯发展而来,是一种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行为方式,其基本作用是使人们之间互相理解。[2]仪式一直处于人类文化学研究的中心位置,因为它作为行为表述与符号表述最能体现人类的本质。《水浒传》中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排座次与《儒林外史》中以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杜(少卿)为主的文人大祭泰伯祠都堪称聚合仪式的典范,且两书中分别出现的好汉结盟与文人雅集实际也都是聚合仪式的具体表现形式。
《水浒传》相应描写了聚合的三种仪式,即入伙、拜盟、排位,都体现了游侠重义的价值立场。
1.入伙
入伙保证了梁山泊人员稳定维持在一百零八之数,入伙有两种方式即投名状和引荐。投名状可以表明自己投靠组织的强烈愿望和忠诚决心,是江湖上接纳新人常常履行的一种仪式。《水浒传》第十一回中林冲带着柴进的推荐书投靠梁山,梁山头领王伦则要林冲交出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3]149这种手段的意思是用他人的性命来验证自己弃绝退路的忠诚,防止日后变卦,这实质上是保障山寨安全的一种措施。小说自晁盖在梁山泊当头领之后,就不再需要投名状了,而是换成了由原来山寨头目引荐。《水浒传》第四十四回石秀叹气:“小人便要去(梁山),也无门路可进。”戴宗则说:“壮士若肯去时,小可当以相荐。”[3]1618第六十七回李逵看焦挺有本事,便推荐他投奔宋公明。焦挺说他“投奔大寨入伙,却没条门路”。[3]931可见因为有熟人引荐,被引荐的新人也是值得信任了,故不需要投名状再去表示忠心。
2.拜盟
在古代便有歃血为盟,它原是原始部落的遗俗,到了先秦时已经雅化为诸侯间盟会的仪式,特别从宋代开始,拜盟的风气开始在民间社会,尤其是草莽江湖中普及开来,因此“结义为兄,誓有灾厄,各相救援”则成为“水浒时代”绿林好汉效法的通例。[4]根据拜盟规模的大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结拜和聚义。
书中真正意义上的结拜首先开始于第七回,鲁智深说他“年幼时也曾到过东京,认得令尊林提辖”,[3]99林冲大喜,即结义拜智深为兄。再如第二十七回武松在十字坡遇到张青夫妻,论年齿张青却长武松五年,因此武松拜张青为兄;第三十八回黑旋风李逵见到宋江后“扑翻身躯便拜”,而后道“结拜得这位哥哥,也不枉了”;[3]518第四十四回锦豹子杨林小径偶遇神行太保戴宗,大喜,邀住戴宗结拜为兄。聚义相比结拜来说,规模更大,形式更加庄重。《水浒传》第二回少华山朱武、杨春、陈达三人是聚义的开端,他们“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虽不及关、张、刘备的义气,其心则同”。[3]33接下来还有桃花山周通、李忠的“聚义”,有梁山泊王伦、杜迁、宋万、朱贵、林冲“聚义”以及第十五回的“七星聚义”等。
3.排位
入伙和拜盟的目的则使得英雄好汉汇集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江湖组织极力渲染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兄弟”之情,强调彼此之间“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但实际上这个整体里特别讲究尊卑有序,[5]梁山好汉们先后总共进行了七次座次的排位。通过确立交椅的次序,进而反映尊卑有序,保证了山寨内部的团结和稳定。
第一次以林冲上梁山为肇端,开启了好汉们首次排位,接下来是智取生辰纲之前“七星聚义”,作者较为详尽地描绘了整个排位场景,从 “列了金钱纸马,摆了夜来煮的猪羊”到“发誓、烧纸”,以排位步骤的有序性和严谨性,标明了排位仪式在诸位好汉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后好汉人员迅速增加,梁山队伍不断壮大,像火并王伦、大闹清风寨、劫法场、破无为军等这些重大事件后都进行了排位。施耐庵在整部小说中对最后一次排座次的描写最为浓墨重彩,如挑选吉日良时、焚一炉香、对天盟誓、歃血为盟,这些仪式行为在好汉中具有独特的意义,都暗示着江湖法则,其中的行为规范对后世帮会的结拜都有深远的影响。
《儒林外史》中着墨较多的聚合包括三次文人雅集和三次祭礼。通过文人聚会集中描绘了儒林百态,体现文人重礼的价值立场。
1.雅集
文人雅集是一个古老传统的仪式,最早要追溯至《诗经·小雅》里记载的宴饮集会的诗歌。文人雅集的内容通常以宴饮、游赏、赋咏为基本活动方式。《儒林外史》中的集会仪式总共出现了三次,展现了形形色色的儒林面貌。
第一次是以娄家公子为首的湖州莺脰湖集会。参加的人包括“娄玉亭三公子、娄瑟亭四公子……共合九人之数”。[6]163在这次聚会上文人侠客汇聚一堂,吟诗、击剑、奏乐、酒食,堪当“一时之盛”,“望若神仙,谁人不羡”。实际上,作为相门公子的娄家公子,欲学信陵君“礼贤下士”,而请来的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三人空有虚名,最后以“人头会”的闹剧草草收场。
第二次是杭州西湖斗方诗人集会。参加的人包括赵雪斋、景兰江、浦墨卿、支剑锋、胡三公子、匡超人。这次集会由浦墨卿提出一个问题让众人讨论:“一个中了进士,却是孤身一人;一个却是子孙满堂,不中进士。这两个人,还是那一个好?我们还是愿做那一个?”[6]226这次集会的地点在酒店,大家吃着酒食,然后拈韵作诗。虽然最后得出了“诗名也是一种功名”的结论,似乎聊以自慰,但他们内心深处对于功名利禄的艳羡却无法完全遮盖。
第三次是南京莫愁湖湖亭集会。参加的人包括杜慎卿、季苇萧等十三人。这次的集会由杜慎卿发起,集会的目的是评判优伶,并且吸引了“城里那些做衙门的、开行的、开字号店的有钱的人”,引得众人“齐声喝彩”。[6]329杜慎卿等人游览名胜,品评梨园,看似名士风流,实则与名士风度相悖,这种在公共文化空间中的炫耀性展示和标榜,充满世俗化的格调。
2.祭礼
“祭”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祭祀之礼,就是以礼物向神灵祈祷、致敬和献礼,以求消灾增福得其庇佑。
第一次是出现在小说第三十三回中南京大祭泰伯祠,这是全书最隆重的一次祭祀。迟衡山首次和杜少卿商量建泰伯祠的事,“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却并不曾有个专祠。那文昌殿、关帝庙,到处都有。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6]418此后,惜墨如金的吴敬梓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叙述祭礼的细枝末节,写出祭礼的全部过程,描绘了一个极为“乏味枯燥”的祭祀场面,如写参加祭祀的士人,或捧尊,或捧玉,或捧帛,或捧馔,按主赞者的号令,一次又一次地跪、献、拜、兴;又如细写祭礼各种规则,包括每个人的站位、祭拜的顺序、跪拜的次数,这些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再如写十二种乐器与三十六人的佾舞队都是按照古代的形式,或制作,或编排,“司祝、司麾、司尊、司玉、司帛、司稷、司馔……佾舞一个步骤也不能少、不能乱”这样繁琐的句子比比皆是。
这次祭祀引得“两边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动”,因为“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听见这样的吹打”。从周围百姓的态度看,这次祭祀是热闹堂皇的,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严肃而繁缛的祭祀仪式正是对礼乐学习的一次具体实践,此次祭祀特别突出了古代儒家注重实践与重视礼乐仪式的传统,俨然与空谈八股时文的世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除了礼乐实践外,祭祀泰伯祠还蕴含着礼让精神,小说第六回严贡生诈骗钱财与三十三回泰伯祠大祭迟、杜二人推辞主祭,这正反映了“礼让”截然不同的两面。这一行文人进行隆重的祭祀,实质是将古代礼乐视为矫世变俗的良方,这不仅是大祭泰伯祠的文化内涵,也暗含着吴敬梓本人的夙愿。
相比而言,后面两次祭祀活动要简略许多。第二次是五河县祭节孝祠。对于这次仪式描写,吴敬梓主要运用了对比的手法,通过余虞两家的叔祖母入祠与方家老太太入祠场面的鲜明对比,一边冷冷清清,一边热闹非凡,讽刺之情溢于言表。第三次是徽州祭烈女祠。王家三姑娘因为丈夫死了,不愿意连累父亲养活她,执意为丈夫殉节,在父亲王玉辉“青史留名”的回应下,绝食八日而死,三姑娘的死换来了隆重的祭典。吴敬梓用极其客观的笔调写出了王家三姑娘的可怜和王玉辉的可悲。通过学人,说他“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6]600反映出封建礼教下以烈女为荣的悲哀。
DG-SHGR路由将雷区FAR定义为凸包H的扩展区域,区域中心点位于H内,再依比例因子(scale factor)扩展。
石昌渝先生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把《水浒传》归为“联缀式”结构,又认为“联缀并不意味着结构散漫,《水浒传》的各个单元部分都有一种张力,它们都趋向梁山,逼上梁山的主题把它们聚合成一个艺术整体。形虽不连而意相连,各个自成单元的人物传奇故事总起来是一个脉络贯通的有机构成。”[7]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儒林外史》:“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8]两书中的聚合形式不仅是一种社会行为实践,实际上它还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象征着秩序、规范和信仰,《水浒传》与《儒林外史》以大大小小的聚合仪式建构情节框架,不断推进整个故事的演进,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聚合代表的文化信仰也不断发生转化。
《水浒传》因“义”而聚,《儒林外史》以“雅”而集,两部小说人物都是在聚合仪式中一个个出场,又接续退场,描写的中心人物接力似的不断转换,逐步形成汇聚之势,犹如千支万流同归于大海,这是两部小说在形式上的共通之处。通观此类结构,汇集到“大海”之前的每一条“小溪流”,不是孤立存在的,都互相有联系,汇集后也不是机械地作叠加运算,而是成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值得一提的是,《水浒传》在排座次后无论是对抗朝廷还是被招安剿匪都属于集体活动,完全符合聚合结构的模式;而《儒林外史》在祭泰伯祠后又陆续写了若干的人物传记,聚合后又再分成不同的“支流”,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水浒传》的聚合结构比起《儒林外史》更加典型。
二、发展路径之异构与终极理想之趋同
《水浒传》和《儒林外史》两部小说分别展现了好汉结盟重义与文人雅集重礼,这些游民通过不同方式形成聚合正是为了重建“义”与“礼”,但是因为游侠与游士的身份不同,他们重建“义”与“礼”的路径也不同。
《水浒传》中的游侠一开始或为吏、或务农、或从商,然后这些人因为各种因素或主动或被动地脱离了社会秩序,成为游民,并且把“义”作为是游民江湖的核心规则。其中史进与少华山绿林人物的结义,成为以后各个山头的结义和梁山泊聚义的彩排或预演,成为全书结构由小聚义到大聚合的开端。[9]之后从七星小聚义再到白龙庙聚义等等,“义”不断以聚合的形式演绎壮大,《水浒传》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不仅成为整部小说意义最重大的一次聚合,游民江湖的“义”更是达到了顶峰。小说在整体结构上由散到聚,好汉们也是完成了“由散到合”这一过程,彻底疏离了主流社会而走向江湖。
然而当招安成功时,梁山好汉身份骤然发生变化,由乱臣贼子转变为忠臣良将,原来江湖中遵循的秩序规范也从兄弟之“义”转化为对朝廷的“忠义”,完成了从主流秩序疏离到回归主流社会的转变,好汉们从民间重新回归到庙堂。但是这种秩序的回归注定是一种悲剧,国家之“忠义”是“忠”大于“义”,这与江湖之“义字当先”显然矛盾,这就为梁山好汉最后的结局埋下伏笔,当征完方腊班师回朝时,一百零八将只剩二十七人,梁山好汉名存实亡,“由合到散”暗示着重建新秩序的彻底失败。
《儒林外史》的一群游士虽大都生活在主流秩序中,然而因为礼崩乐坏,士人蝇营狗苟,与社会道德背道而驰。三次文人雅集以及两次祭祀集中展现了一群假名士之真面目,他们抛弃了儒家德行规范,转而追名逐利,儒家伦理道德已被破坏得体无完肤。三次“热闹”非凡的聚会、五河县节孝祠祭祀的闹剧以及徽州烈女祠祭祀的荒唐,都反衬出儒家规范中“礼”的失落。另一方面在世人轻看“礼”的时代,杜少卿等人大祭有“至德让礼”的泰伯,正强力表达对儒家之“礼”的呼唤,并且想以此重建儒家道德规范,强化“礼”在士人精神秩序中的作用。事实证明,依靠个人力量显然不够,纵然大祭泰伯祠当天盛况空前,完成了形式层面的礼乐重续,此后却是风流云散,最终结局萧瑟。卧闲草堂本第三十七回总评说:“本书至此卷,是一大结束”,[10]“大结束”表明“泰伯祠盛典”之后礼依然衰微不振,全书结局也印证了泰伯祠从筹划到大祭,从衰落到倒塌,到头来只是一番无用功。小说最后倒是让我们看到萧云仙拓边、劝农,全年践行礼乐,以及市井四大奇人有“真儒”之风,仿佛礼乐在市井得以复苏,儒家“礼”的规范从主流文人群体转向民间,这些自命不凡的名士费尽心思呼唤的“礼”竟然在市井平民体现,啼笑皆非后发人深省。然而市井四大奇人身份微贱,对儒家规范的建立毕竟意义有限,“礼”由合而散也暗示着士人精神秩序重建最终惨淡收场。
聚合是因“义”而聚,因“礼”而合,发展路径则是展示了游侠与游士为了“义”或者“礼”而做的不同努力,因此无论是聚合还是发展路径,两部小说分别都指向各自的终极理想。
从上一段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水浒传》的游民有两个方面的理想。其一是追求物资的丰富与平等。“论秤分金银、成瓮吃酒、大块吃肉”,游民身处社会底层,本身谋生手段相对匮乏,所以追求衣食之欲对他们特别有吸引力,这个口号甚至屡屡出现在劝降的环节中,并且成效不俗,反映了游民对衣食无忧的生活的向往。其二就是构筑以“义”为核心的梁山王朝,这也是《水浒传》中的最终理想,实质就是重建新秩序。书中第七十一回排座次后有篇韵文,“单道梁山泊的好处”,开头就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在这个理想国中,好汉们在这里不仅消灭了等级差别,消除了隔阂,还享受着自由的狂欢。在这个国度,“义”是好汉们理想的人际关系和行为准则。美国人赛珍珠早在20世纪30年代把《水浒传》翻译为AllMenAreBrothers,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亦是从另一个方面表明梁山好汉的理想。由此看来,好汉们的终极理想不仅涵盖了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囊括了秩序和精神上的认同。
《儒林外史》并没有像阮小五和李逵那样直接把理想说出来的人物,而是通过描写正面人物委婉透露出对“礼”的向往。作者一开始就借理想人物王冕来“借名流隐括全文”,之后描写了装病不去朝廷做官的杜少卿,他以隐士的身份逍遥自在地游于庙堂之外;世人认为儒家理想只能做修饰文章的辞藻时,迟衡山却坚持以制作礼乐为己任;世人对征辟趋之若鹜时,庄绍光则谢圣辞官;礼乐式微,求功名的文昌殿和求利禄的关帝庙泛滥时,这些秉承儒家核心价值的真儒真名士要建立泰伯祠,呼吁大家学习礼乐,由此他们成为儒家道德规范的真正践行者,且一度闪耀在历史的时空中,但时代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回应,于是,他们很快淹没在岁月的风尘中,成为历史遗迹。
泰伯是西周太王的长子,他主动把王位让给了姬昌,因此被尊称为“让王”,孔子赞美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11]孔子特别强调他的“让德”,在孔子看来只要大家都能让,就能够克己复礼,礼也就能回归。礼不仅包括社会政治制度,而且还包括社会道德规范。《儒林外史》中的这一行文人正是继承了孔子的意志,可惜的是孔子在他的时代都没有成功,到后世封建社会,这种超阶级的“让德”只是美好的空想,他们信仰得越虔诚,折射出现实社会越是丑陋。他们的行为对黑暗社会批判得越是尖锐,最终理想不仅没有靠近,反而越是遥不可及。
文人的礼乐教化与武人的替天行道最终都未能实现,“忠义”瓦解了“义”,“功利”腐蚀了“礼”,上流抑或下层,只是死水微澜而已,最终主流文化秩序取得了胜利。在这两次带有浓烈时代色彩的精神突围表演中,我们感受到游民群体重建社会秩序不可得的悲哀。
三、“同形异构”的文化启示
从《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的聚合仪式出发,以“同形异构”为切入点,探讨两大游民群体如何在庙堂与民间之间进退转换,又是如何由散而聚,由聚而散。我们可以品味小说聚合仪式描写所包含的一些文化意蕴。
其一,仪式叙述的实质是以文化秩序为内核的。通过上文关于仪式形态的分析,不难看出,仪式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内在力量,是因为它作为一种规范和传统对社会起调控作用。仪式不仅确定了组织的有序性和等级分层,如《水浒传》排位的尊卑有序、《儒林外史》中按照儒家规范次序进行的大祭泰伯祠,还成为一个巨大的象征符号,将现实与信仰连接,两书通过对各自江湖文化秩序的掌控,把分散的游民和游士凝聚在一起。这些力量归根到底还是文化秩序在起作用。
纵观六大明清小说,除了本文讨论的两书外,《三国演义》通过“桃园结义”的结拜仪式展现了“忠义”;《西游记》通过九九八十一难的“取经、除妖”仪式展现了自由叛逆与社会秩序的冲突;《红楼梦》通过君臣、生日、祭祀等多种仪式展现了儒家“忠、孝”等伦理冲突;《金瓶梅》通过结拜仪式、祭祀仪式颠覆了传统文化的信仰,透露出对秩序丧失的悲哀。这些小说中的仪式叙述都展现出对文化秩序思考与反省。通过这几部经典小说的烘托及运用,可见仪式叙述发展到明清阶段,整体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叙事模式。而《水浒传》的“好汉聚义”和《儒林外史》的“文人聚合”在充分继承前人仪式描写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了游民游士两大江湖,其中的仪式描写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反映出两书的聚合仪式相比其他小说诸多仪式所反映的内容更加深刻和典型,在表达的主题上更加凝聚,更具代表性。
其二,“庙堂”和“江湖”的斗争始终穿插在中国古代小说,《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的创新之处在于写出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某些规律,也就是“官方与民间相互转化”或是“主流秩序与江湖规矩相互博弈”。 一方面在“转化”中,我们能看到官方和民间不是孤立相对的,甚至某些条件下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转化,如一道圣旨就可以让梁山好汉转为“正规军”,让庄绍光直接踏入天子殿前。另一方面在“博弈”中,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不可替代作用的两大基石“义”和“礼”,一直处在扭曲的状态,而在秩序之外的游民不断地试图去改造和复原它,只是这呼唤和重建“礼义”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上一刻拜将封侯,下一刻毒酒赐身,上一刻祭典场面万人空巷,下一刻则一片废墟无人问津。
两个场域,两种秩序,彼此交织往复。伴随着复杂和深刻的斗争,在凸显“游民群体在主流与民间相互转换中力图重建礼义新秩序”文化主题的同时,也展示了中国传统文人探索思考文化人性的终极心灵图式。此外,庙堂与江湖的斗争往往以江湖游民的失败告终,但是作为此类小说承担的终极理想——“义”与“礼”已经被表达得最为深刻。“义”和“礼”两方面的展示与投射之典型,使得《水浒传》与《儒林外史》成为中国武者小说与文人小说彰显文化理想的代表。
其三,《水浒传》与《儒林外史》中游侠游士的终极理想是突破主流秩序去重建礼义,但是前者夹杂着“义的伪形”,后者包含“礼的原形”。
原形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原质原味文化,即其民族的本真本然文化;伪形文化则指丧失本真本然的已经变形变质的文化。[12]10刘再复在《双典批判》中认为无论是《水浒传》的“聚义”“忠义”,还是《三国演义》的结义,都是“义”文化的伪形。[12]20笔者不否认如李逵劫法场时排头杀人,实质就是披着一层“义”的外衣,实有滥杀无辜之嫌。再如智取生辰纲时晁盖等人认为“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以抢劫的方式“劫富济贫”,实质就是“以暴制暴”,目的为了自己“图个一时快活”。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水浒传》中游民的组成成分复杂,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因子也在所难免,而他们不满主流秩序敢于重建新秩序已经是游民对文化理想的一次伟大尝试了。
相对于伪形,笔者认为《儒林外史》反映了“礼的原形”,例如书中虞博士有两件事容易引发争议:其一,虞博士的表侄借他的房屋住,把屋拆了变卖掉,还要再跑来向他借银子租屋住。对此,他非但不动气,反而点头借钱。其二,一秀才考试作弊,不小心把夹带的经文放在试卷里一起缴给监考官虞博士。虞博士非但不处罚他,反而替他遮掩。考毕,那秀才来道谢,虞博士佯推不认得他,说并无此事。小说对此两事的描述似乎有些讽刺意味,因“礼”而“让”,虞博士的行为看似是非不分,但是这种“礼让”本身是纯正的,李汉秋认为这“就存在着因矫枉过正而近于可笑的成分”,正像天目山樵所评:“仁而近愚”。[13]而太过于纯正的“让德之礼”在那个时代里只是个美好愿望,因其迂阔,固无法实现,其悲剧之结局也就是注定的。
参考文献:
[1]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16.[2]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4.
[3]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4]宁稼雨.水浒别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49-150.
[5]王同舟.地煞天罡:《水浒传》与民俗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78.
[6]吴敬梓.儒林外史汇校汇评[M].李汉秋,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78.
[7]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4:340.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174.
[9]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
[10]朱一玄,刘毓忱.儒林外史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273.
[11]朱熹. 四书集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1957:45.
[12]刘再复.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0.
[13]李汉秋.《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蕴[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44.
(责任编辑张丽珍)
The Aggregation of Isomeric Homomorphism:A Different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WaterMarginandTheScholars
GE Yonghai,KONG Deshun
(CollegeofHumanities,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Abstract:From a specific point of view, Water Margin is about heroes who get together and uprise, while The Scholars is a refined gathering of scholars. Their depictions of aggregation are full of tension. The so-called “isomeric homomorphism” means that mobility of people in these two books is from states of dispersing to gathering, and their development tracks are not only similar but also different in some ways, vividly displaying how wandering cavaliers and roaming scholars in the feudal age advance and retreat and transform their cultural identities in the imperial court and underworld in a ritual way. Although these two books have similar ultimate ideals and implications, they both embody a call for and reconstruction of “justice” and “etiquette”, and their similar vanishing endings reflect their pity on the lost cause of rebuilding the cultural order. It is such profound cultural reflection that makes these two books become paradigms of Chinese novels about martial heroes and scholars.
Key words:Water Margin; The Scholars; rite of aggregation; isomeric homomorphism
收稿日期:2015-10-08
作者简介:葛永海(1975-),男,浙江嵊州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孔德顺(1990-),男,安徽合肥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城市叙事的古典传统及其现代变革研究”(10CZW038)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6)04-002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