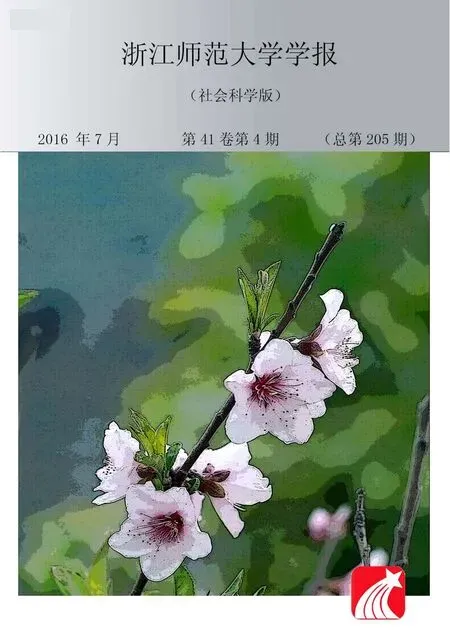在社会变迁中重构公共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与保护路径的再思考
——基于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案例观照
张青仁
(中央民族大学 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在社会变迁中重构公共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与保护路径的再思考
——基于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案例观照
张青仁
(中央民族大学 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仅是传统社会的遗留物,而是区域社会民众共享的公共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立足于其公共文化的属性,通过契合当下社会的保护措施,恢复其公共文化的属性,在社会运行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文化属性的恢复必须突破遗留物思维下的遗产观和商业化时代文化资本论的局限,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立场出发,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维系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推动全球社会发展中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文化;社会运行;遗留物
为了确保全球一体化进程不会对地方性的文化实践造成破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2003年起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我国亦迅速地加入了这一行列中。在10多年的发展中,我国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不少地方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着与民众生活脱节和措施不当等弊端。[1]在工具理性的侵袭下,围绕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价值,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措施纷纷上马,不少地方甚至陷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权的争论中,保护本身流于形式。[2]
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困境产生的根源在于国内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认识不清,以及在此基础上没有形成契合遗产属性和社会发展的保护措施。因此,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已过10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与属性,对我国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策略进行反思。
一、从遗留物到公共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的再认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初兴起于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第三世界。一方面,全球一体化加强了拉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联系,但在商业资本的侵蚀下,拉美国家的文化资源成为发达国家竞相追逐的对象,以玻利维亚为首的拉美国家开始对本国文化的所有权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全球化、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渗透使得诸多非西方国家对本国文化的处境产生了担忧,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诸多发达国家开始对本国传统文化进行保护。[3]在这两种思潮的交融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世界各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而确保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不会对地方社会的文化造成破坏,确保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如下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和传统手工艺等五类,这一内容体系与民俗学研究的范畴基本一致。此外,在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基础上诞生的民俗学致力于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构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研究内容与研究旨趣的双重一致性,使民俗学者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最为重要的参与主体。
然而,诞生于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俗学研究很长一段时间秉持着遗留物的理念看待民俗。尤其是以芬兰、德国为代表的欧洲民俗学者将民俗视为是历史遗留的产物,他们希望通过对本国民俗传统的搜集与抢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构建本国的民族文化之根。虽然遗留物的理念在当下民俗学研究中已是日渐式微,但在传统和现代二元对立基础上诞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却激活了民俗研究中的遗留物理念,并使其成为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的基本原则。
在遗留物理念的影响下,对遗产真与假的判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首要问题。对于能够进入保护名录中的项目,秉持遗留物理念的保护主体将其视为人类文明的集大成者与终极形态,诸多保护措施的确立旨在在社会变迁的情境下对人类文明终极形态本真性的维持;此外,传统社会遗留至今的、具备着本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因此成为价值属性的代表。在商业资本的参与下,各地生产性保护措施纷纷上马,成为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手段,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权归属更是导致了诸多纷争的产生。
围绕着遗产真与假的争论、生产性保护的大行其道与遗产保护的本真性之间的张力使得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与实践处于撕裂状态,而脱离社会语境的保护策略及其保护效果的差强人意亦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要性的质疑。在理论层面上,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类学民族志书写已经注意到遗留物理念影响下的本真性并非是真实存在的实体,而是不同主体合谋建构的产物。而在当下,对于本真性的研究已经转移到“了解在个人和群体的话语中,本真性的功能和意义究竟是什么”。[5]这意味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并不在于挖掘遗产本身作为传统的属性特征,而是应该对遗产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与价值进行关注。事实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兴起的拉丁美洲,在多元族群社会中具备的社会生产能力正是评判与确立遗产的重要指标。[6]
基于这一思考,高丙中提出了“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这一命题。他认为,在传统社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日常生活的形态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与团体中,并作为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而为群体成员共享和传承。进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定区域的民众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凝聚着世界观与认知观的地方性知识,并以生活文化的形态存在于特征场域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软性社会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区域社会民众共享的公共文化的形式,在规范民众行为、实践共同体认同和维系社会运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赋予其价值的来源并不在于遗产本身作为碎片化的遗留物的本真性特征,而在于遗产作为地方社会民众共享的公共文化具有的意义生产的价值。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在社会变迁中恢复公共文化的意义生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遭遇危机的实质是共同体内公共文化的传承断裂。原因在于现代化进程导致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突出表现为当下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由此导致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场域的破裂。此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危机的出现亦与包括民俗学在内的现代学科对传统社会公共文化的定性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起源于五四时期,但从那时起,作为民众日常生活共享的民俗文化被定义为由“传统性的(落后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所代表的观念”,[7]进而被标签为落后、愚昧的象征,由此导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成为去传统和去民俗的过程。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西方文化的影响与渗透更加剧了这一过程。文化自觉的缺失与现代化影响的双重作用直接导致了当下中国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危机的出现。
在传统社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体共享的公共文化,并在群体共享过程中实现其意义生产,维系着社会的正常运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传承场域与意义生产的当下,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不应该只局限于项目本身,而是应该建立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共同体公共文化属性认知的基础上,在社会变迁中恢复其公共文化的属性。在实现遗产保护的同时,实现其在培育民众自我认知、实现社会创造性发展的意义。这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扎根于现在,是对过去的重建、选择和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非仅是对静止的过去表达敬意,而是立足于社会延续性对其进行后续的创造”。[8]这也正是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作用的基本要求。
恢复遗产作为群体共享的公共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其意义生产的前提是立足遗产本身的特征,为其在当下社会寻找新的社会定位和生存空间。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类别区分,但这一区分是基于学科范畴基础上的产物,缺乏从民众的立场出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定位的准确认知。
重新审视民众日常生活,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众日常生活的存在形态主要包括处理人与自然的物质生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生活、满足人类自身诉求的、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组成的艺术生活和人类自身所处的文化空间四种类型。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文化的属性,就必须立足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形态,依据不同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生活的融入程度,在变迁的社会结构中为其寻求新的社会定位,恢复其公共文化的属性。
具体而言,对于能够融入当下社会的物质生活实践,可通过政策性支持、大众传媒宣传等多种手段,培育民众对非物质生活实践的需求与传承自觉,并以此为基础对其传承与发展进行保护;对于与当代社会完全脱节的物质生活实践,可通过活态博物馆的形式,发掘其作为文化象征、社会记忆的价值,服务于当下社会的发展与建设。社会生活是民众日常交往的重要维度,是规范民众日常生活的基础与框架。即便在社会变迁的当下,集体参与的社会生活亦能起到文化之根的作用。对于此类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采用政府引导、群众动员的方式,通过将其转变为当代社会的公共文化活动,重构其在当代社会的传承场域,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形态与精神内涵的双重传承。艺术生活作为人类精神层次的追求,具有一定的审美属性与价值,因而具备产业开发的价值。对于此类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要培育民众的审美需求与市场需要,通过切实可行的生产性保护措施,从技艺传承的层面进行保护。需要注意的是,在生产性保护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协调好艺术生活的精神内核与当前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在不违背艺术生活精神诉求的前提下对其进行适度的创新,这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公共文化传承与创新并举诉求的回应。对于文化空间的保护,首先需要对文化空间本身及其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勘定与归类,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文化空间保护的范围。在保护措施上应以人为核心,通过民众的生活实践将文化空间的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融合,赋予文化空间的造血功能,从而实现文化空间整体性保护的目标。
三、个案观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宁波经验
作为我国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地带,浙江省宁波市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截止2013年,宁波市共有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0项。改革开放后,宁波市较早开始了对辖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宁波模式”。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紧扣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文化的特征,依据不同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融入程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传承营造相应的社会空间,并通过传承群体的实践恢复其作为当代社会的公共文化,盘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中的运作,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双向结合。具体而言,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主要包括博物馆建设、生产性保护、校园传承基地建设、公共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等多种路径。
(一)博物馆建设
博物馆保护是指利用博物馆这一空间,通过图像、视频等媒介手段,以融合实物的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收藏、保护、研究与展示的过程。采用博物馆方式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是在地方社会中有着重要价值,却与当下社会完全脱节的物质生活和艺术生活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从1997年宁波慈溪兴起的第一家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开始,在经历了慈溪发轫,宁海、象山等地民间非遗博物馆的纷纷兴建,再到鄞州区20余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群的发展后,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目前已经发展到了40余家,其中宁海县十里红妆博物馆、象山县德和根雕艺术馆、鄞州区朱金漆木雕博物馆等尤具典型代表性。
以现代科技展览与社会生活完全脱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方面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直接保护,另一方面,这一途径亦使民众可以直观、生动的形式,获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直观感受,并能以参与体验的方式,传承作为文化记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为重要的是,博物馆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现代社会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宁波市文化部门在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建设的同时,亦通过在博物馆举办多样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将与社会生活完全脱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公共文化的形式嵌入当下社会生活。在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培育民众文化自觉的同时,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当前,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参观博物馆非遗展览已成为宁波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内容。在群众热情的推动下,宁波市民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已如春笋之势遍地开花。
(二)生产性保护
生产性保护,是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产业开发,将其转变为当代社会的消费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主要运用在当前仍然表现出强烈市场需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上,尤其是在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与传统医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上。
宁波市文化部门通过资金支持、项目补贴、政府重点采购和后期奖励等多样化的方式,对不少非遗项目、服务和项目的生产性保护进行资助。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政府资金支持下,走上了市场化运作的轨道,取得了经济效益与文化传承的双赢,宁波江北慈城冯恒大食品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年糕制作技艺是宁波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年糕制作技术的进步,传统年糕制作技艺逐渐面临着传承危机。在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年糕制作艺人冯恒大成立了宁波江北慈城冯恒大食品有限公司。在继承传统手工技艺的同时,冯恒大食品有限公司利用现代科技大力开发新产品。如今,冯恒大食品公司已成为宁波年糕生产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大的专业企业之一。在实现年糕传统技艺传承的同时,亦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生产性保护亦应该突破遗留物理念,在传承中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技艺。这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取得成效的关键,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公共消费文化具有的传承性与变异性特征的体现。宁波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创新性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以骨木镶嵌为例,宁波本地传统的骨木镶嵌技艺多用于家具陈设。随着西式家具的普及,传统骨木镶嵌技艺日渐失去了生存空间。在创意礼品兴起的当下,不少企业将骨木镶嵌技艺应用于书签制作、钢笔装饰等创意性礼品中,取得了不俗的经济效益,骨木镶嵌技艺亦以新的形态得以传承与应用。
(三)校园传承基地建设
作为民众生活文化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艺术生活中的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具有的教育意义成为传统社会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内容。随着村落、家庭结构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依存的传承场域发生变化,不少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正面临着传承土壤缺失带来的传承危机。在当代社会,学校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是现代文明的传承空间。由于传承内容、传承旨趣的重合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危机的当下,学校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传承的重要依托。
基于这一认知,结合本地文化传统与教育发展水平,宁波市文化部门选择在本地区有着悠久文化底蕴的、契合社会发展且在儿童社会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通过将其纳入学校课程等多样化的方式,大力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传承。
从2007年开始,宁波市文化部门就开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基地的建设。目前,宁波市已经建立起了多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基地,形成了包括奉化市尚田镇中心小学“奉化布龙”传承基地、奉化市萧王庙街道中心小学“奉化吹打”传承基地、镇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蛟川走书”传承基地、余姚市泗门镇中心小学“犴舞”传承基地、北仑柴桥实验小学“造趺”传承基地、北仑区梅山学校“水浒名拳”传承基地、余姚市肖东第一小学“姚剧”传承基地、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宁海狮舞”传承基地、奉化市高级中学“奉化布龙”传承基地在内的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基地。除了将传承人请进课堂,在校园内传授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宁波市文化部门还通过让学生走出校园,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等多样性的活动,实现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在技艺与内在蕴含的双重传承。
校园传承基地建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有着重要意义。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危机的根源在于社会巨变带来传承空间的消解,学校作为制度性的文化传承场所,能够作为新的传承场域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空间缺失的困境。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社会的公共文化。由于遗产本身具有的象征意义,传统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往往局限于血缘、地缘等共同体内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危机的当下,对传承群体的限制不仅加剧了遗产本身的传承危机,亦无益于恢复其作为公共文化的属性,因而也限制了社会大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体验与参与。校园传承打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边界的限制,通过将所有学生纳入传承对象,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范围。最后,学校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学校教育是儿童文化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学校教育,能够培养学生对民间文化的兴趣以及接受、感知多元文化的能力,促进学生开放、包容的文化观的形成。
(四)公共文化建设
公共文化建设是政府部门采用行政手段,通过举办文化活动、文化展览等多样化的方式,向民众提供普及的、大众文化产品服务的过程。作为相沿成习的民俗生活,传统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即是共同体内的公共文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纳入城市公共文化建设,亦是满足现代社会民众多元文化诉求的基本要求。宁波市文化部门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城市公共文化的建设体系,并使之成为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亮点。从2007年至今,宁波市已连续多年举办广场展览、非物质文化遗产讲座、公益培训和公共庆典,形成了诸如“阿拉非遗汇”“我们的节日”等一系列公共文化建设的典型项目。
“阿拉非遗汇”是宁波市文化馆和市非遗保护中心联合举办的大型群众性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从2013年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届。“阿拉非遗汇”选择在宁波市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宁波广场举办,以“亲近、共享、传承”为宗旨,精选宁波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广场上集中展演,通过文化表演、邀请观众参与、举办非遗讲座等多样化的形式与参与民众互动。在深化宁波市民对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受的基础上,通过群众参与的方式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传承,引导民众多元文化观的形成。“我们的节日”则立足于宁波本地丰富的节日文化,通过举办以群众为主体的公共庆典,展演并传承宁波本地的传统节俗。仅2010年,宁波市文化部门就组织了“我们的节日·清明放风筝”“我们的节日——‘瑞虎纳吉’端午女红技艺展”等多项民俗节庆活动。此外,连续多年举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龙舟竞渡”等更成为全市民众乐于参与的民俗庆典。
以公益性、参与性为主要诉求的公共文化建设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传承营造了新的场域,恢复并实践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意义生产。与传统社会局限于共同体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实践不同,宁波市文化部门推动的公共文化建设跨越了共同体的边界,为不同层级、不同地域的文化构建了一个交融的平台。这一举措不仅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传承,而且也是当代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蕴含着文化启蒙的社会意义。
(五)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划定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区域,为达到保护目标而指定或实行管制和管理的地区。在文化生态区中,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历史街区、乡镇、传统民居、历史古遗迹等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艺等相依相存,并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和谐相处”。[9]构建生态文化保护区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保护,对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空间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存在的民俗生活保护的结合,构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之间良好的、互动的关系。
靠海而居的环境使宁波东部形成了深厚的海洋文化,其中以象山文化最具代表性。三面环海的自然环境、靠海而居的生产方式形塑了象山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形成了包括徐福东渡传说、晒盐技艺、渔民开洋谢洋节和象山—富岗如意信俗在内的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象山本地更是有着包括石浦渔港古镇、王将军庙、妈祖庙和城隍庙等多个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从整体层面而言,以海洋文化为中心,象山本地已经形成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互相依存,人类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文化生态系统。
在对象山渔文化普查的基础上,在专家学者、地方文化精英与当地民众共同参与下,宁波市文化部门制定了《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确立了象山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以人为核心,活态传承的思想。近年来,象山县先后恢复了诸如三月三踏沙滩、渔民开洋谢洋节、妈祖信俗、如意信俗、渔师信俗等传统民俗,创新发展了渔歌、渔曲、渔戏、渔鼓、渔灯等渔文化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此外,象山文化生态保护区还以诸多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为主体,通过传授、培训以及宣传等多样性的手段,激发传承人对于本土文化的热情,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带动下,使得文化保护成为象山民众的文化自觉。
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形成是建立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文化属性认知的基础上的。这一认知自觉使得宁波市文化部门能够较为精准地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危机的根源,通过契合遗产属性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措施,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社会的机制,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活态传承。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形成亦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迅速发展的经济使宁波民众较早地产生了文化自觉,同时亦减轻了非物质文化保护过程中的经济诉求,使得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能够突破文化资本论的局限,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多样传承机制。
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一举措不仅盘活了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激发了宁波民众对于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而且促成了宁波民众文化自觉的形成,形成了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民参与的社会氛围。在社会结构变迁、人口流动性急剧增加的当下,对于外来人口众多的宁波而言,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转变为全民参与的公共文化建设,其实质是引导外来人口建立文化认同,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运行中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在传统社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共同体内的公共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面临的传承危机,其实质是作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公共文化在社会转型期遭遇的困境。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共同体的公共文化,实现其在当代社会意义生产的过程。就此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文化本身的问题,更是关乎社会发展的问题。
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当代社会的公共文化,首先需要打破遗留物思维的局限,紧扣当下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变迁的社会结构,从民众的生活世界入手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在变迁的社会结构中重新定位遗产属性,进而通过多样化的手段与保护措施,恢复其作为当代社会的公共文化,实现其在当代社会的意义生产。对遗产公共文化属性特征的恢复亦须突破文化资本论的局限,在超越遗产保护工具理性论的前提下,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视域出发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维系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推动全球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作为一项政府主导的文化实践行为,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文化的特质有赖于政府部门的角色转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政府部门必须转变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在立足文化规律的基础上,动员社会力量,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特征与当代社会的现状,建立与文化本身相适应的传承机制。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传承及其作为公共文化具有的意义生产价值。
参考文献:
[1]吕俊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去主体化倾向及原因探析[J].民族艺术,2009(2):6-11.
[2]刘爱华.工具理性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困境探析[J].民族艺术,2014(5):123-127.
[3]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者的两难选择[J].河南社会科学,2008(1):14-20.
[4]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J].民族艺术,2008(1):6-17.
[5]瑞吉娜·本迪克丝.本真性[J].李扬,译.民间文化论坛,2006(4):103.
[6]CARABALLO P C. El Patrimonio Cultural y los NuevosCriterios de Intervención. La Participación de los Actores Sociales[J].Palapa,2008,1(3):41-49.El Patrimonio Cultural y los NuevosCriterios de Intervención. La Participación de los Actores Sociales
[7]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J].文艺研究,2008(2):77-83
[8]ROSAS M A. Presentación[J].Alteridades,1998,16(8):3-10
[9]黄小驹.陈至立:加强文化生态保护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水平[EB/OL].[2015-12-07].http://www.zjwh.gov.cn/dtxx/whrd/2007-05-31/57615.htm.
(责任编辑傅新忠)
Reconstructing Public Culture in the Changed Society: Reflection on the Property and Protection Pathways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Ningbo
ZHANG Qingren
(InstituteofGlobalEthnologyandAnthropology,Minzu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not a remnant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but is the public culture shared by the local society.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be grounded in its public cultural property through suitable measures that fit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to restore its public cultural property so as to gene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social operati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ublic cultural propert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he heritage concept under remnants thinking and the cultural capital of this commercial era so as to grasp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maintaining the diversity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global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uman social community.
Key words:prote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ublic culture; social operation; remnant
收稿日期:2016-04-03
作者简介:张青仁(1987-),男,湖南麻阳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民俗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保护及县域实践研究”(13CMZ046);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课题“宁波市现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体系建设研究”(201401)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6)04-007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