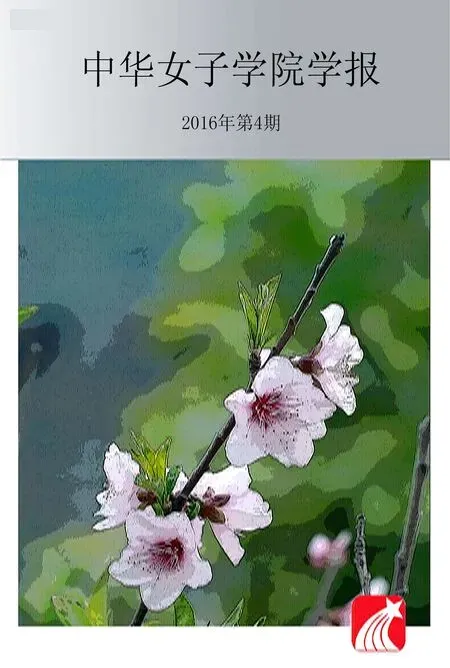以社会众生灵魂相探究“人类精神”生态嬗变
——荷兰华裔女作家林湄长篇小说《天望》《天外》的世界性价值
王红旗
以社会众生灵魂相探究“人类精神”生态嬗变
——荷兰华裔女作家林湄长篇小说《天望》《天外》的世界性价值
王红旗
《天望》《天外》是荷兰华裔女作家林湄,运用俯仰天地的特殊“边缘”视角,超越时空与文化的跨国界、跨宗教、跨文体的写作方式,以隐喻的诗哲性语言、博爱的性别关怀伦理,书写曾经领跑世界现代文明的欧洲这一片人文沃土,华丽表层之下弥漫着自然与精神的重重雾霾,导致生存与此的人类患上极度的恐惧焦虑症。在这两部作品里,林湄关于灵魂与人性、时空与存在、家国与宗教、钱权与欲望、有限与无限等等哲学问题的沉思,以东西方人性的情感世界内核、婚姻家庭物象的文学叙事,走进了社会众生的一个个灵魂的秘境深处。并以一代代人的灵魂镜像群,寻找人类之爱的心性同构,探究“人类精神”生态之嬗变的世界性意义。
林湄;人类精神;世界性价值;《天望》;《天外》
林湄是世界华裔文坛的重要代表性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视野宏阔,观照深远,富有俯仰天地的睿智境界和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其巧妙多变的叙事方式,往往以纵横开阖的画卷式、开放式结构,把诗歌、散文、美学、史论、哲学、宗教等等,如数家珍般地融入她的小说里。牵动读者不可释怀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其思想与精神的流向,以及对人物灵魂隐秘世界的复杂性探索。评论家常说她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她不仅是“能够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运用个体化的语言把感受编织成故事叙述出来的叙事艺术家”,而且是“能够在其中思想,用寓意的语言把感觉的思想表达出来的叙事思想家”。[1]234她既是擅长选择超越时空与文化的跨国界、跨宗教、跨文体的作家,又是运用隐喻与诗性语言,描写个体人的灵魂存在状态的哲人。她以博爱、宽容的关怀伦理,在精神雾霾弥漫的世俗社会里,透过表层华丽发现陷入多重苦难中的精神焦虑症。以超性别的人类意识,认为“‘立人’已成为时代的要务和当下的一种呐喊和虔诚的厚望。”[2]
林湄十年磨一剑,2004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望》,该小说问世后曾在《欧洲时报》全文连载,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Charles Willemen曾撰文称赞:“在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天望》是一部坐云看世景的优秀小说。”法国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韦遨宇也赞誉《天望》是这场新千年、新时代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一只报春之燕。2014年,她再次十年磨一剑,在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天望》的姊妹篇《天外》。这两部作品的写作要旨,与卡尔维诺的“我在每一讲中都为自己提出一个任务,要向未来一千年推荐我倍感亲切的一种特殊价值”[3]有着相似的目的性。林湄的小说同样承载着她自己的“一种特殊价值”,就是通过“我愿与生活一起燃烧,和文学同甘共苦,将不同社会阶层的移民在新语境里的生存遭际展现,并探讨他们的‘困惑之理想’与‘精神之象征’”[4]557,来探究“人类精神”生态之嬗变,寻找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与国家的人性“根性同构”。
一、以俯仰天地的特殊“边缘”视角揭示现代人类的生存困境
林湄的《天望》与《天外》,运用多重叙事方式,构成“别样”的人类生存图景。如果说《天望》是“天人相望”,是超越世俗社会的边缘视角,《天外》则是“天外之际”,把自我置于浩渺宇宙的空虚之中,仍是另一种“边缘”视角。其共同点均在于,以俯仰天地的特殊视角,洞察科技与物质文明发展的极端欲望所引发的全球性的“人类精神”生态病症,寻求多元文化平等交流的通道与救赎策略。《天望》《天外》两部作品以“边缘”检视“中心”所产生的距离感,不仅使叙事者“第二自我”处于崭新的宁静时空之中,以大自由、大自在的境界形而上之求索,并且,随着视角游动展现出更多层级的视野与澄明的画卷,从而获得历时性与整体感的全息世情世景。
当然,林湄选择多重“边缘”视角叙事,与其传奇经历、存在身份、性别观念与宗教情怀有着密切关系。当青梅竹马的爱情婚姻遭遇刻骨铭心的分离,携两幼子生活历尽艰苦而永不放弃,磨炼出其独立的精神、坚忍的意志与文学的创造力,集单亲母亲、记者、作家于一身的生存境况,其对社会民族、性别人生、人性真谛、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有着切身的独特体验。青春时代,她在中国的农村插队落户,由大红大紫跌落到大难大悲,无奈之下独自移居香港,在殖民地社会里生活18年之久。中年时期,她从香港移居欧洲荷兰,带着希望重新开始生活,遇见爱情并走进了跨国婚姻,在不断经历多样人生遭际里重新发现自己,升华自己的生命之境。其阅历与思考对其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在对东西方文化数十年如一日的探索中发现:“肉体可以漂泊,文化乃是人的灵魂、精髓,不但不能漂泊,反而跟随着您的一生。”[5]1她在不同制度社会之间漂泊迁徙的经验是,将现实、理想与未来的思索分离开来,在自己的精神王国里寻找美好和渴望的一切。可以说她创作的原动力来自于灵魂的内在召唤,来自于对人的个体灵魂及生命意义一步步地深入探寻。她崇尚真善美,憎恶假恶丑,甘于清寂,淡泊名利,拒绝一切诱惑,相信宗教信仰是没有国界的,能够如水般潜移默化地塑造人的灵魂,更信奉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然而,目睹社会现世对权力的无限崇拜、对金钱物质匍匐爬行之悲剧后,她以文学创作来支撑自我的脆弱灵魂,践行其担当的意愿。
林湄在《天望》序言里写道:“《天望》,义即‘天人相望’;天在哪里?对于欧洲文明来说,天在上帝的脚下。天就是上帝,是神学构筑的辉煌宫殿,是人的初始的归属。”开篇就点明其宗教救赎的宗旨。她“从边缘的特殊视角,将人文精神、书卷经验、生存感观、生命意识以及对于灵魂、肉体的哲学和美学思考,编织成串串的问号,然后抽离自己的位置,坐在飒飒的白杨树顶上,望天兴问,沉思默想”。[5]2“坐在飒飒的白杨树顶上”对天发问,看起来是一个超越尘世的自由时空,但是飞翔坠落,命运却掌握在“飒飒”的风里。意象的飘忽感与不确定性,不仅是作者、叙事者生存现实的心境自喻,而且是小说中的两位核心人物形象,从中国南海边上的小渔村漂流到欧洲大陆的微云姑娘,与西方混血儿男人弗来得成婚之前,夹杂忧虑的喜悦心情与命运未知的隐喻,更暗示其情感生活与基督传道之路的前途未卜,埋下其救世理想与现实艰难的伏笔。
《天外》的叙事者是凭“天外”视角,在“天地人宇”之间的时空延伸,可以远近、内外收放自如,寻找到“第二自我”明察秋毫的精确维度与特定视域。此时关注的已不仅仅是其外部世界的大宇宙,更是直达内心深层的小宇宙。也就是说,当自我置身于无限时空的漂泊之野,人类的生命之岛地球就变成一粒尘埃,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个体,只不过犹如放大镜之下整日忙碌的一只只蚂蚁,就不禁会引人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哲学问题。林湄认为,选择“天人相望”、“天外之际”是她探测自然与社会、众生灵魂之相的最恰当视角。《天望》的篇章“金”、“木”、“水”、“火”、“土”,正是由人类外部社会生活世界进入,即从华人女子微云“东女西嫁”的婚礼“初夜”拉开序幕。《天外》的篇章“欲”、“缘”、“执”、“怨”、“幻”是直接进入人类的内心世界,即从中年华人夫妇郝忻与吴一念婚姻生活几十年发生情感危机的心灵距离与隔膜开始。但是,从某种哲学意义上讲,“天外”视角更容易接近一个个人的灵魂,更能够体察由欲生缘,因缘而执,由执生怨,因怨而幻的内在情感变迁。因为,中国先哲老子在两千年前就早已洞明,宇宙间只有自然中的人类,并无人类中的自然,而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101
当然,其中隐含着林湄的宇宙观,即从人类与自然的本原关系,阐释其生命存在的价值真谛。因为,人类的生命诞生于无极之河,家园“悬泊”在浩瀚之空,与“万物为一”。法国学者于连·弗朗索瓦曾强调:“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7]笔者认为,林湄小说特殊视角的选择,与此具有异曲同工之理。在林湄看来,“我活在被悬于空虚里无数星球中的一个地球上,除了对虚空的神秘感到好奇费解外,因天性对生命、精神、物象喜寻恩爱叩问,自然对这宇宙奇特奥秘的杰作——人,深感兴趣与探究。”[4]1那么,“天外”对林湄观测“地球村”人的灵魂、情感世界,更是一个超越“只因身在此山中”的清醒。尤其是“21世纪的欲望、性爱和无常,比起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复杂和多元化”。“我笔下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既不同于传统观念的东方式,也不同于西方作家笔下的情感和生存方式,然而,他们却是人的‘共性’和‘个性’的彰显者。在理性与感性、存在与虚无、完整和欠缺的跨时空实践中,除了离不开人类悠久的、切身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还受到时代发展和变化中的各式各样思潮影响,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4]3-5因此,林湄借“天外”的视角,将人的奇特奥秘和记忆,以个体人的生命、性爱、死亡,人对爱情、婚姻、家庭的自我迷失,写出正在继续漫延的“人类精神”之灾难。
林湄的作品以多重边缘视角,对人的个体灵魂、人类命运的追问,体现出其寻根与反思的精神及自觉的人类意识。因为文化离不开民族性,民族性离不开血缘、教育、习惯养成,甚至还有不同地域与自然生态环境等生成的“根性”,这种根性是生命最初的形体和原本,割切就是死,而移植后的生存形态和质量与过去的样子不同。这是一道特殊的景观:有的入乡随俗,有的不适应被淘汰,有入俗而变异的,有通过生存感悟而产生一种超形体的新状态。“我是谁?是一棵树吗?那么,离开了本土,移植在天涯海角的另一片土壤里,叶子和果实自然与原生有所不同。……我去问谁呢?没有人回答我。我走啊,飘啊,寻索啊,充满彷徨、矛盾和惆怅,甚至为此感到不幸和悲伤。可是,漂泊已不是新鲜的话题了,它已成为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并且还在继续与发展。”[5]1也就是说,林湄自我放逐的肉体漂泊,目的是为伴随其灵魂审视人类的现世。
因为,林湄眼中的欧洲古典圣景已不复存在,宗教信仰已渐渐式微,人的灵魂孤独无依、饥饿漂泊。残酷的战争连绵不断,科技与物质的极度开发在激发人类创造力的同时,更使其贪婪之心膨胀,膨胀到甚至可以完全毁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冷漠。人类在现代性文明进程中,丧失了原初的自然崇拜和万物相依共生的远古记忆,其信仰变异为对金钱权力的崇拜和对人的力量的崇拜,而无视人类力量的有限性。《天望》以宗教传道者弗来得的受难,证明主宰人类命运的神在人们心中的死亡,大自然的破败萧条、地震海啸警示诞生于“自然之母”的人类,对自然母亲的背叛。尤其如今面对科技信息“云时代”的人类力量全新“质变”,人类是在创造中毁灭还是在其中重生,只有自己拯救自己。如果《天望》呈现的是宗教救赎的失败,而《天外》揭示的却是人类自我救赎在绝望中的希望。
林湄《天望》《天外》两部小说里自然与社会生态的特写画面,呈现出一幕幕令人触目惊心的悲惨场景。A镇原本世外桃源似的诗意栖息地,充满魔力与魅力的自然交响乐已经消逝,正在发生这样的奇人奇事:“那里三面依山,满山均是葡萄,南面对着幽幽河道,风景宜人,如世外桃源,原有千多户口,以种植葡萄为生,人民丰衣足食,自从河畔开发成旅游区后,各地商人便注重起这块休闲地了,房屋、汽车、废气废物日益增多,A镇丛此命运多舛,先是不停地出现交通意外,接着出现各种早已灭绝的病毒,地方政府决定进行空气消毒,这下可怪了,病毒没了,满山遍野的葡萄则变成条条枯藤,像僵死的干杆。居民的身体和生活也渐渐地起了变化,全部患上胆量病,胆小的不愿出门,怕光怕见到人,怕电视、电话、收音机、音响、汽车、电脑……胆大的性欲超凡,见异性就想做爱,而不愿用避孕套。”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视眼里,世界像一座大殿堂,外表装潢得华丽辉煌,里面已经破烂不堪,又像一座古老的大屋,经过历代浩劫、蹂躏、破坏、以血和龌龊污染,已成一片废墟……或像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的预见一样,地在浮动、旋转,空气在变异,所有支撑房舍和殿堂的柱子均将被灾难和病毒所冲击,不是倒塌,就是毁灭。”[5]381-382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A镇,“古典时代依附上帝的拯救而产生的魅力已失去,世界性的战争已将西方科学带来的精神文明粉碎。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却失去了心灵归属。……威胁着人类精神走进坟墓的不是温饱问题,而是战争、贪婪和物欲,和随之而来的冷漠、空虚和恐怖感。”[5]2这可以说就是全球自然生态环境危机的缩影,验证了细菌学家罗伯特·柯赫在1905年提出的警语:“人类终有一天必须极力对抗噪音,如同对抗霍乱与瘟疫一样。”[8]1“噪音”当然隐喻人类创造性的破坏力。如果说此前描述的是欧洲因自然生态的破败而危机四伏,那么下面展现的却是人文生态破坏之惨重。
尤其是患“胆大症”女人骂“胆大症”男人的对话,“笨猪,废话太多!”“大汉,我要赶回家写稿,报社若不采用,我就到电台投诉,电台不受理,我就自己发传单,谁说女人不能干男人的事,什么传统妇德,统统靠边,我们不能再受男人统辖,必须颠覆男性,解构,父权,大胆探寻,迫寻自我,提高意识,改变待遇,唤醒感觉,发挥作用,彰显性别意义,摧毁男权主义,扫除男权威风,必要的时候,剪掉男性特产。”[5]385性别战争导致男女伦理生态的混乱不堪。
历史上欧洲这一片令人类仰慕的人文沃土,如今无论社会、自然与人文生态,都恶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天外》里的中国官商勾结的宴席,“桌面早已摆好杯碟,法国红酒、国产茅台、杏仁露、奇果汁等饮料也已就位,不一会儿,菜式陆续上桌,日本鱼翅、石斑鱼,美国龙虾、花枝,荷兰芦笋、刀豆,江浙乳猪、乳鸽,广东蛇肉、山鸡野味等,将大圆桌面摆得满满的。”在觥筹交错的欢愉氛围里,透露出一种钱权交易、阿谀奉承的腐败之气,在被奢靡掩饰的太平盛世里人类的精神生态颓败之极,反映出人类在钱权驱使之下变得鼠目寸光,灵魂在多种欲望里无奈无望地挣扎。然而东方人还视其为实现生命价值的乐土,蜂拥而至。那么,在一片精神的荒原之上,物质财富究竟还会存在多久?
尤其《天外》对男主角郝忻“出轨”之后,个人深层心理“小世界”的开掘极为缜密,并富有多重隐喻。他的性意识的觉醒,诞生出两个灵魂的博弈,竟质问自己在情欲沉浮的世俗生活与高雅诗意的精神生活之间,“我怎么不可能在其选一呢?”“为何人到中年会干出如此不堪的事情呢?”“我在中国工作时身强力壮,每逢肉体和灵魂冲突时,就用‘政治’来恐吓自己达到逃避真我的目的,出国后,也碰到过肉体对意识的挑战,却被固有的观念死死地束缚或卡住,常用‘败坏’、‘缺德’字眼鞭挞自己,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病愈后才意识到我的灵魂原来已留下许多影子……如‘生存’、‘欲望’、‘青春’、‘美貌’、‘时间’、‘享乐’等,有时它们会一起联合起来拉着我,让我陷在死亡的边缘……所以,我一面渴望一面害怕……于是,越陷越深。”[4]190尽管林湄点化浮士德的灵魂复活,指点其“囚住恐惧和希望,不让她们向社会靠近”。但此时他的回应:“我虽从美的理想中走出来追求真,但‘真’更令我凌乱不堪,而更多的人总是处在迷惑里,没有感觉和意识。”也就是说,当其美好理想降落到现实之地,发现真实世界如此残缺凌乱,而人类竟然对此集体无意识的生活于其间。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强大的诱惑使然,实则是人类性解放之后心理的食性百态之相。以此隐喻在以男性价值为核心的父权体制中,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对男性的压抑。虽然,他在情欲中战胜与化解自己的“恐惧”,仍不放弃撰写《傻性与奴性》的传世之作,“知行合一”去接近、拥抱“希望”。从而引出当代世界不仅女性需要解放,男性同样也需要解放的命题。
林湄在《天外》的结尾,描绘出一种性别的和谐之境。郝忻与吴一念夫妇在经历灵魂“无常”磨难之后所看见的:“这时,两人的目光同时被窗外奇特的晨曦景象所吸引,一束绿光像一把大伞从天悬下,不一会儿,云丝如羽毛般散开,闪烁着绿红紫黄的色彩,云彩里突然呈现一洞天,一道彩虹跨越洞顶,郝忻刚才看到的景象可不是这样啊,不由叹道:‘你进书房前,我在天花板上看到蓝天白云上有—双眼睛,它充满着无限怜悯的神情。’”“一缕金色的晨光正好投进这平凡的不大的书房,在两人身上微微荡漾,仿佛在笑、在说话、在歌唱……”[4]554-555这样一个夫妻诗意栖居之所——家的存在,郝忻在妻子怀抱里的灵魂相拥场景,一方面,证明人的神性在于自我灵魂的内在信仰,对自我灵魂病症的自我疗愈,两性可以共同创造平等和谐的婚姻日常生活;另一方面,预示神性是人类流淌了亿万年的血脉心海之爱,历尽劫难仍然携光明与希望而永恒存在。如果从“家国同构”更宏观层面而言,人类精神的疾病源自于国之失序。但是,人类有自我疗救愈化灵魂的神性。“按理,社会是永远不会患上一种不治之症的。”[9]85
林湄的《天望》《天外》正是运用边缘视角的勘探发现,曾经领跑世界集文化、艺术与政经于一身的欧洲正在走向没落的原因,以人类理智、意志与创造力膨胀的灵魂镜像,揭破为什么科学与财富不能够拯救人类于危机之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被终极悖论所困?无论是“胆大症”和“胆小症”,均是“恐惧症”的一体双面,是人类生存迷失的“大世界”缩影。“若个人迷失还有望于整体精神环保的医治,最遗憾的是集体的迷失。当迷失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病态时,就出现有人麻木,有人随俗,有人感到失望和不安。不安容易引发失心症,人一旦失了心,心理病、精神病随之而至。”[4]2因为,当人类发现自己生活在一片废墟的虚无黑暗里,没有太阳、月亮与星星,没有光明与希望,就像失去母亲与家园的流浪儿,陷入一种极端的孤独恐惧之中。人类必须唤醒存活于潜意识深处自然崇拜的原始信仰,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万物为一”的互依共存关系,反思人类自身的善恶良心问题。林湄坚信,人的最高特性是神性,而神性是人类灵魂“原乡”永恒的精神力量,是超越东西方具体宗教形式的文化互补共生,是人类对平等博爱信念的坚守,人类个体灵魂真善美的内在完成。这丰富多变的边缘视野,恰恰是林湄以特殊的审美距离推开“大世界”、“大宇宙”之门,以家族、家庭日常生活“小世界”、灵魂“小宇宙”,参透人性的奇特与奥秘,寻找人类得以拯救之锁钥,更是林湄以“内视角”的心理解剖,使其文学创作走向哲学深度的艺术实践。
二、从生活“日常”与“无常”探秘人的个体灵魂生态
《天望》与《天外》两部小说的叙事主题是心脉相通的。林湄横贯东西、穿越古今,运用人类精华思想的“互证”,表现出对宇宙自然生态与人类精神生态的深切忧虑。作品穿越后现代世界极端的物质文明,展现出东方人如朝拜般涌向欧洲而陷入漂泊“无常”的生存状态。《天望》以欧洲多样人种混血儿弗来得跨国婚姻的夫妻情感的冲突、痛苦、误解与和好,解释多元文化互识、互证、互补之构境。弗来得四处奔走传播“圣爱”,不被家人与世人理解,屡屡遭遇侮辱打骂,仍然为获“天国的大奖”执着重新上路,就如同塞万提斯笔下本性正直善良、富有无畏精神的堂吉诃德一样不合时宜。《天外》从移居西欧大陆的一对华人夫妇的“婚姻危机”为轴线,牵涉出五个不同样式的家庭,构成西欧社会华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呈现社会众生的灵魂镜像。表达“人类精神”在物质与欲望的致命诱惑里,灵魂如何冲破道德的界堤,化为恐惧焦虑的漂浮能指。书斋知识分子郝忻耐不住魔鬼的诱惑“解禁”之后,在物质与精神、生与死、性与爱,肉体与灵魂、婚姻与家庭的焦虑与交锋中,自我生命被两个相悖的灵魂撕扯着、分裂着、生成着……郝忻酷似歌德笔下“一体二魂”、性格自相矛盾的浮士德。林湄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时而会邀请堂吉诃德与浮士德的灵魂出场,魔鬼出来诱惑,并且以显形或隐形的超时空对话,创造出“比真实更真实”的特设语境,显示出更深刻的讽刺与批判意义。
《天望》里的弗来得,是来自欧洲大陆乡村的一位农场主,他的“太爷有西班牙血统,太奶有英国人血统,母亲有印尼人血统”。用他的话说:“我不像爷爷是一个虔诚而古板的清教徒。我的血液,有着多样人种的基因、欲望与性情。”[5]6他本性诚实,天真纯洁,渴望真理,一方面有着坚定的基督教信仰,有获得“天国的大奖”的理想;一方面又质疑神性与人性、神权与人权的对立,以及古板的基督教观念。但是,爷爷的突然死亡,孪生兄弟依理克的被金钱的异化,成为其放弃巨额财产、舒适生活,为宗教奉献终身“传道”的生命转折点。弗来得带着新婚妻子到处传播圣经,到难民区做善事,救助弱势群体,却被审查惩罚。但是,四海为家的漂泊生活,却使这对各自“逃离”家园的夫妻更加相依为命。虽然微云是为实现自己与父母的“金凤凰”之梦、为物质生存而“逃离”家园,弗来得是为实现宗教理想、传播“圣爱”而“逃离”,是纯粹精神的目标。然而,夫妻凭借本真的善良,在传道的艰辛磨难中成为知心伴侣。尤其是雪天里小鸟衔枯枝筑巢对微云的启示:“家园?鸟儿也有回归感?微云深感惊奇!然而,怎样性质的回归呢?灵魂?肉体?还是情感?它既然不能适应这儿的冬天,为什么不去接受新的环境?……原来,它飞翔的翅膀不仅具有求生愿望的功能,还有随同灵魂呼唤的感应。……本能地毫无保留地选择最安全、最适合自己生存的枝头筑巢,当春天的步伐到来的时候,无论刮风下雨,都无法阻挡它的回归。这交织着时间和自然情感、根和枯枝的巢,似乎流露着远古以来生命的奥秘和无言神明的具象。”[5]240林湄以“内观”来表现微云的内心独白与自我叩问,难道为了改变命运而“逃离”家园的漂流,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许人类在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近关系里,更能发现其灵魂深处相同根性。
弗来得知道了撒母耳不是自己的儿子,是微云与华人知识分子老陆偶发“一夜情”所生。但是,在夫妻分居后,当微云遭遇牢狱之灾时他仍能托人送钱并竭力帮助,在思念微云的痛苦中能够重新认识自我、爱情、婚姻的关系问题,并且反思自己把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看成是生命的唯一意义,是否会制约自我的灵魂?其实,他并不理解上帝的绝对权威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被物质财富所颠覆,甚至已经变成遮蔽当代人攫取财富的虚伪谎言。他的胞兄依理克不仅要拆掉小教堂来开发房地产,而且还要卖掉祖传的圣水壶,他因为对现实的绝望而生命垂危,奄奄一息,连医学专家在太空站研制的最新医药对他都无济于事。
然而,弗来得却是反思之后的“众人皆醉我独醒”。他认为,“现在,信仰没落了,人们转而追求金钱、高科技、美女和性事……结果,离婚率冒升,未婚妈妈数字增加,性病数目急升,毒品、枪杀,无奇不有……道德、家庭、伦理观日渐丧亡。政府要花费无数的人力、财力、物质去解决艾滋病、毒品、枪械等等问题,却没有一个执政者考虑到医治人的灵魂比医治人的肉体更为重要……欧洲比美国还糟糕,是吃美国的垃圾虫……败坏的风气比美国有增无减。”[5]242虽然,弗来得家族相传数代的宗教信仰,已深入他的骨髓或者说潜意识。他认为,人的最高特性是神性,当这个依附对象失去了,生命如同死”[5]444但是,在微云归来的亲吻、呼唤和热泪的怀抱里,他的生命复活了。弗来得宽容了微云,接纳了儿子。弗来得的肉眼失明却开启了“心眼”的反视,继续向灵魂深处去探寻生命的真谛。如果相比起来,堂吉诃德精神的死亡留下了那个时代的悲剧,而弗来得作为西方文化的代码,在与“他者”文化的互动里中获得了灵魂“新生”。从人类学的层面,生动表现出人类精神生态的互助变化,指出最先进的科学与某一种宗教都拯救不了人类,而只有真爱对人类“地球村”的精神生态疗愈,更显示出其世界性意义。
《天外》里的郝忻是一位书斋知识分子——文呆呆,出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从小就患有爆炸声恐惧症,常备耳塞以防巨响刺激。其中的隐喻暂且不论。他和妻子吴一念同是插过队的知青,恢复高考后又一同成为大龄的大学生。毕业后,郝忻被分配到A城当中学语文老师,吴一念在B城做企业单位的经贸员,夫妻之间在那段“大我”的“非常”年代,能够相敬和睦。移民至西欧之后,在艰难的日常生活中仍然能够“水乘鱼,鱼乘水”地同甘共苦。郝忻常常以“尊妻、敬妻、顺妻”自训,默认妻子给自己的“两边不到岸的边缘文化人”身份定位,为改变家庭生活状况,听命妻子办“翰林院”挣钱,却不甘心放弃为事业奋斗的理想。他和妻子在更高的精神层面如同两股道上跑的车,孤独的灵魂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庸常里挣扎。然而,一场雷雨声的惊吓,昏迷中灵魂进入阴界的“会亲厅”,与父母对话,受魔鬼黑猪、梅菲斯特诱惑,唤醒了他对生命死亡、存活、时空、理想等等的欲望想象。
而且,郝忻对浮士德着魔般的痴迷起来,“一有时间就往图书馆找资料、做笔记,还抽空到浮士德原居地参观、走访和拍照片。假日和几位朋友游览德国时,趁最后一下午,他独往参观魏玛区的浮士德生前居所和他平日喜欢去的咖啡馆和酒窖等地”。“一有时间就到各地旧书店采购有关浮士德的生平传记,周六特地到跳蚤市场寻找旧物上的浮士德塑像,拍摄浮士德穿戴的服装、领带等式样,并关注其“长大胡子,颈围绉领,穿戴大和线帽……的音容笑貌与走路行态。”背着妻儿跟随两个洋人学者再次考察“传说中的浮士德博士陵园”。他越了解浮士德就越喜欢他的傻气、单纯和认真,情不自禁地暗自模仿起浮士德的言行举止,已经从内心把浮士德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可以说,魏玛之行,真正激活了郝忻深埋在心底的精神理想,他决意研究浮士德和阿Q精神,比较“傻性”、“纯性”、“奴性”与“民族性”的有什么不同,完成《傻性和奴性》的传世巨著。但是,他的理想在想象时空里飞奔,却总是在妻子的埋怨嘲弄中坠入现实日常生活之河。
郝忻再次站在浮士德雕像前请求指点,浮士德含笑娓娓而谈:“我说自己蠢货是因为我尽管是位满腹满腹经纶的博士,但一牵着学生的鼻子四处驰骋时,就什么也不懂……所以,应当到俗世闯一闯,承担和体验人间的祸福,或与暴风雨奋战一番。”从地域而言,“我是在自己的国土上逃闯,而你,敢大胆出国?”在家庭与事业方面,“既然肉体的翅膀不容易同精神的翅膀结伴而飞,那就各自飞翔吧,像在我的胸中,住着两个灵魂”。[4]98-99郝忻对浮士德“两个灵魂”共存有一种升华性的体悟。因为,在西欧世俗社会,性是随处可见的,性自由、性开放、红灯区、性博物馆,性用具商店、性表演……比比皆是,“性事干脆走到使用价值生产的阳光下面,并且洪水般的泛滥和被生产制造出来”。[10]22尤其是,郝忻与心理医生彼得谈话的关键词只有性压抑、性解放,无意发现独身男人大卫睡房里的小秘密:排放着几十个胖瘦不一、高矮不等的拟真美女。这些黄色的“性拟真”,“因为这是性行为的即时生产,是快感那生猛的现实性。在这些被目光整体穿越的身体中没有任何诱惑,因为这个目光到处被透明的虚无吸引着。”[10]32就是这种标志着人类性爱死亡、充满诱惑的死亡的性幻觉化膨胀,在转换中变成了一种骇人听闻的欲望文化,成为一种无可救药的诲淫,激活了郝忻被长期压抑的性意识、性欲望,情不自禁地与自己的女学生芾芾发生性关系,感觉到自己人到中年才真正体味到性爱之乐趣。
郝忻认为,一方面性能够激化生命活力,对肉体之乐抑制不住而想入非非;一方面唯恐妻子知晓,为自己愧对妻儿内疚痛苦;一方面在注视女性肉体时,会不由自主产生意淫的念头,甚至去摸女学生粉嫩的手;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行为深感焦虑不安却难以遏制。两个相悖的灵魂引发的精神分裂症,在原我、旧我与新我之间恐惧徘徊,战战兢兢不堪终日。如同浮士德“两个灵魂居于我的胸膛/它们希望彼此分割,摆脱对方/一个执着于粗鄙的情欲,留恋这尘世的感官欲望/—个向往着崇高的性灵,攀登那彼岸的精神殿堂!”[11]96郝忻被两个同栖一身的灵魂纠缠、困惑,不知如何处置自己身体。当然,作为一个理性的知识分子,虽然他懂得人之性在情中为之爱,于婚内为之伦,于欲中为之本能。但是,这个“被解放”的男性身体,在欲望诱惑的失序现实里,仍然无法主宰自己灵魂对肉体的背叛。
相比较而言,郝忻比浮士德晚出生两百多年。浮士德是厌倦了枯燥无味的书斋生活,才不得不到俗世闯荡。他“先为饱学之士,再为权势高官,最后成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本拥有者”[11]97,才可以成就那个时代的浮士德精神的悲剧。郝忻经历复杂坎坷,他在集体主义“大我”的意识狂潮里长大,如今又生活在缺失尊严与信仰的西欧。但是,此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强制性地把原本秘密与诱惑的性,物化为消费的商品,变为国民生产总值。郝忻岂能耐得住这铺天盖地的象征世界里的性诱惑与性控制,他在肉身的色彩与形体图画之前神魂颠倒,把生活、婚姻家庭弄得一团糟,总是“一个灵魂多次批评我,另一个灵魂却不听话”。
与浮士德一次次的超验对话,表达出其在人生事业上“目标已有、道路却无”的精神痛苦。浮士德的人生理想是“从‘小我’,成为‘大我’,最终这个‘大我’一样一败涂地。”[4]180浮士德在“小我”理想的“知识幻灭”之后,追求“获得权力和产业”的“大我”理想,但是“填海造田”事业的失败,酿成其生命无可挽回的大悲剧。郝忻与浮士德的生命悲剧很相似,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即是从‘大我’成为‘小我’的“一败涂地”。郝忻从弗洛伊德“一个人处在某个集体中会丧失自己原来的性格和特点”的观念受到启发,他说:“我就是在集体中生活了几十年的人,难怪没有了性格和特点,不敢拒绝,不善分析真相,只知适应或随从,甘愿被左右、照别人意愿行事,到了快成尘土的时候还不了解自己。”[4]192当然也就未能撰写出《傻性与奴性》的传世巨著。林湄从个体灵魂的不同矛盾性,人性欲望与生存现实的纠结与不甘,勾画出人性本然的真实生态,原来生与死、性与爱、善与恶、美与丑种种复杂,都共存于人的灵魂深处,也许这就是人性“主体互补”的常态,也许正是在对立与和谐、互补与矛盾中更体现出内在灵魂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排挤性,个体的人需要在生命两极之间寻找平衡支点,面对欲望、理想、现实与未来时,生活才有升腾的可能性。
三、路漫漫兮之求索——如何建构“人类精神”的理想家园
《天望》《天外》两部小说以弗来得与郝忻为核心人物形象,弗来得的传道为获得“天国大奖”,郝忻撰写《傻性与奴性》为实现人生理想。其实是林湄以此构成的“人类精神”生命和灵魂欲望的实验场。崇高理想之语给人以慰藉与力量。但是,高远的理想非但迟迟不能实现,“无常”的灾难却时时不期而至。美好理想一旦降落世俗现实,就面临生命的疼痛与死亡,但是,人类在一次次失望与绝望的灾难中前行,在一次次带着希望再出发的磨砺中获得新生,世代传承精神文明的薪火,人类理想从未泯灭。这应该是林湄为寻找人类的心性同构而阐明的深邃之理。
如果说,弗来得生命的复活,隐喻真爱可以征服最先进的科技与最邪恶的暴力。那么,郝忻始终被“一体二魂”撕裂折磨得痛苦不堪,也许是对东西方传统经典、文化伦理的质疑性隐喻。两部作品的结尾,《天望》的“救火”、“救人”场景,《天外》出现的蓝色“天眼”意象,仿佛暗示现代人类只有付出真爱才有希望。因为,真爱与自由是人类天然的本性,乃自然所赐予,“傻性”与“奴性”、“小我”与“大我”,均为社会集团伦理所规定,为后天之品质。无论是“食性”本能的形而下,“性爱”情感的形而中,还是“审美”升华的形而上,或如林湄“认同的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4]556人类如能从中悟其道而行,方能游刃有余。林湄曾说人类只有一种语言战无不胜,那就是——爱。即爱的信仰。因为,社会集团的制度伦理道德因时而变,人性本质追求真善美之爱却自然绵长。那么,“人类精神”生态之嬗变,就是一个不断解放个体人性、升华人性、不断创造爱的社会伦理过程,尽管有时会走向其反面。当前,要拯救全球化之下人性伦理、灵魂冲突、精神病态,唯有以东西方互补共生的文化之合力,构成“和而不同”的“美美与共”之境。
林湄在《天望》《天外》这两部作品里,对海外华人女性的灵魂与精神之群像的探察,同样独到而深入骨髓。尤其是从性别关怀伦理视角,以爱情婚姻的日常生活细节,展现出其内心的精神之维、灵魂之变。《天望》里的女主角微云,与弗来得结婚后从“自我”与“他者”互识的痛苦中自醒,逐步建立起夫妻的互敬互爱,与丈夫一起四处奔波传播圣爱。但是,异国处境的心理孤独却需要乡情的慰藉,没料到与华人老陆偶发的“一夜情”,成为她婚姻“无常”的开始。虽然丈夫最终接纳了他和老陆的儿子为儿子,她的忏悔与真爱唤醒濒临死亡的丈夫弗来得。《天外》里的女主角吴一念与微云相比完全不同,她撺掇知识分子的丈夫郝忻弃文赚钱,下海经商,尽快改变家庭物质生活。她对于丈夫的“出轨”怨恨至极,却意识到离婚后“最难的是女人”而维护着家庭。但是,她在与舒棋的比较中改变了自己的性别观,认为“男女的区别只是肉身方面,欲望和感觉还是一样的,痛是痛,乐是乐,苦是苦,甜是甜……既然如此,男人可做的,女人也可行。”[4]164尤其是“乐身”与“乐心”性与爱的分离观念,使她自如游走在与子乐的“婚外情”之间。然而,林湄借诗人梅如雪的性观念:“‘人性’和‘性爱’如同树干和树叶相依存。‘人性’失去‘性’乏味无趣,‘性爱’失去‘人性’得不到持久。它们互生互存,相濡以沫,令存活丰富多彩、惟妙惟肖。人类不愿公开流露对其体验的真实感受是因为害怕被人讥笑或视为卑劣之徒。弗洛伊德之前,有哪位心理医生看病时会意识到有种被隐藏几世纪的‘现实’,深刻顽固地潜伏在人类的血液里却为人所不知。”[4]191以不动声色的讥讽,揭开了现代人只是“乐身”的“婚外情”面纱。那么,吴一念宣言式的、主动的“出轨”,是效仿与报复丈夫,还是寻找个人情感的幸福,也真假难辨。这两个女主角、包括郝忻最终均回归婚姻,仿佛拖着一个长长的中国尾巴,但有谁能说在现实面前“家”不是一个较好的归宿!当下的欧洲,如德国就是“传统婚姻家庭占百分之三十,同性恋家庭占百分之三十,独身生活的占百分之三十”[12],也许这才是林湄之所以呼喊“保住家就好”的深意。
林湄以不同阶层的华人女性群体的生命体验,解读男女不同的性爱心理,女人以为有爱未必有性,男人认为有性未必有爱。性与爱的意识错位困扰着人类的情感世界。然而,只因男女之间性与爱、灵与肉统一的最高境界古今难全,爱情才成为文学永恒之母题。《天望》里的虹、阿彩、海伦与翠芯,为获得身份权和生活资源而对爱情、婚姻与性的功利态度,《天外》里亚裔华人舒棋的因多次遭遇婚变的悲惨,蔺嫂经常遭遇家庭暴力的无奈,吴一靳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婚姻触礁女人侃侃而谈的家庭观,梅如雪诗性的生存智慧,老祖祖的上善若水,每一位女性形象不仅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其朴实善良的灵魂底色令人印象深刻。林湄关于灵魂与人性、时空与存在、家国与宗教、钱权与欲望、有限与无限等哲学问题的沉思,运用特殊视角的文学叙事,情感世界内核与婚姻家庭物象的伦理探秘,走进了社会众生相的一个个灵魂的秘境深处,“让无法复原的焦虑与伤痛、生存本相的恐惧与无奈,在慈爱的悲悯里得以修补与安慰。”[4]557但是,如何构筑“人类精神”的理想家园?相信林湄路漫漫兮将会继续地求索。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Z].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2]林湄.卷首语[A].王红旗.中国女性文化(18)[C].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2.
[3](意)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M].杨德友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4]林湄.天外[Z].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
[5]林湄.天望[Z].北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6]辛战军.老子译注[Z].北京:中华书局,2012.
[7](法)于连·弗朗索瓦.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M].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美)戈登·汉普顿,约翰·葛洛斯曼.一平方英寸的寂静[M].陈雅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9](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10](法)让·波德里亚.论诱惑[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1]叶隽.歌德思想之形成——经典文本体现的古典和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12]王红旗,谢妮.中德两国“女性和职业生涯”的现状[EB/OL].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node_7064072/content_35795971. htm.
责任编辑:杨春
Changes on Human Spirits Discussion on World Values of Novels Looking at the Sky and Beyond the Sky by Chinese Dutch Female Writer Lin Mei
WANGHongqi
Looking at the Sky and Beyond the Sky are two novels that is written by Chinese Dutch female writer Lin Mei.With a trans-border,interfaith and across-genre writingmethod,the author,froma special marginal perspective, tries to show us a real Europe,which once led to the world’s modern civilization,is filled with natural and spiritual degradation under its gorgeous surface,leaving the citizens suffering from the extreme fear and anxiety.In these two books,Lin ponders over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the soul and humanity,time,space and existence,home and religion,and money,rights and desire,as well as the finite and infinite.With the literary narration of emotional world, marriage and family of humanity in western and eastern world,Lin also delves into the deep inside of human beings. At the same time,she also tries to find the heart isomorphism for the love from human mirror groups,so as to explore the world values ofchanges on human spirits..
Lin Mei;human spirits;world values;Looking at the Sky;Beyond the Sky
10.13277/j.cnki.jcwu.2016.04.009
2016-05-10
I106
A
1007-3698(2016)04-0051-09
王红旗,女,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研究。10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