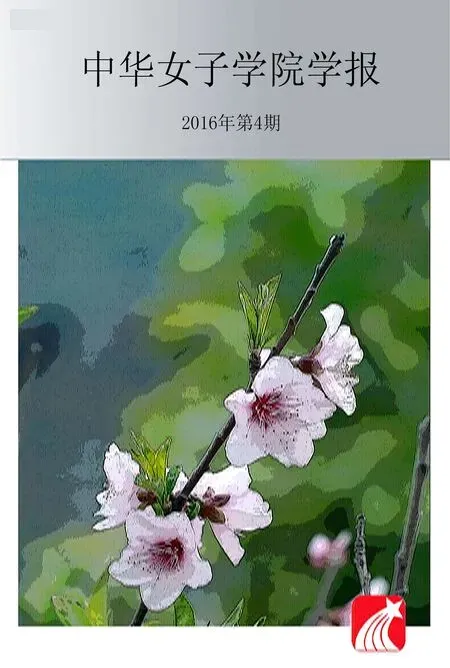关于强制猥亵、侮辱罪的认定
党日红
关于强制猥亵、侮辱罪的认定
党日红
强制猥亵、侮辱罪历经从流氓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到强制猥亵、侮辱罪的演变过程,罪名的演变引发犯罪构成要件的变化,正确理解使用暴力、胁迫手段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这一客观要件的内容,对于本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修正案九”调整本罪的行为对象不仅顺应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且是发挥刑法保障功能的需要。厘清本罪与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侮辱罪的界限,其一看双方的关系,其二看是否带有公然性,其三看侮辱行为是否带有淫秽内容。
猥亵;侮辱;强制
强制猥亵、侮辱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修正案九”)新修订的罪名。该罪名最早源于1979年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的流氓罪,即对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其中的侮辱妇女就是现行刑法强制猥亵、侮辱罪的雏形。1997年修订刑法,鉴于流氓罪这一口袋罪的弊端,将其分解为几个具体罪名,其中之一就是现行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这里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指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方法,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行为,该罪属于选择性罪名,猥亵与侮辱的对象均是妇女,以体现对妇女人格尊严权益的保护。刑法是社会生活的调节器,为了更大地发挥其保障功能,2015年8月29号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进行了修订,即将原来的猥亵妇女改成猥亵他人,同时第二款增加了“有其他恶劣情节的”提高法定刑的条款。随即,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六)》,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更名为强制猥亵、侮辱罪。刑法保护范围的扩大不仅引发罪名、犯罪构成的变化,而且导致了刑事犯罪认定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出现。
一、对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与侮辱妇女的理解问题
首先,现行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以叙明罪状的形式规制了本罪的成立必须使用强制手段,即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由于本罪是轻于故意杀人、强奸罪等其他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且基本犯的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决定了这里的暴力程度应当是比较轻微的,不包括杀死与伤害这些严重的暴力范畴,否则犯罪性质会发生变化。
其次,使用强制手段的目的是为了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上述手段的强制性体现了本罪的违背被害人意志性,这种违背正是对被害人人格尊严的侵害,从而使人格尊严权利成为本罪的直接客体。笼统说来,猥亵或者侮辱,均是犯罪嫌疑人性行为以外的、但与性行为有关的一种性刺激或者满足的下流行为,其主观动机是荣辱倒错的无聊心理作祟,这是猥亵与侮辱的共性特征。但是,刑事立法既然区分猥亵与侮辱,将两者并行列出,毫无疑问,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笔者认为,从实践中发生的案件来看,猥亵是指满足变态欲望的、有伤风化的、侵犯他人人格尊严的下流行为,具体表现为与他人强行拥抱、接吻,抚摸敏感部位,强行抚摸身体等。猥亵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对被害人实施猥亵行为,另一种是强迫被害人自己实施猥亵行为。二者均属于违背被害人情感,引发被害人厌恶感或者羞辱感的强制性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现实中发生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奸男性的范例,应当纳入强制猥亵他人的范畴,而不能认定为强奸罪。尽管有人提出扩大强奸罪的犯罪对象,但目前尚未被刑事立法所采纳,而猥亵对象范围的调整,也适当解决了上述问题。而所谓侮辱,虽然也是基于流氓动机,但略带有挑衅性质的有损妇女人格尊严的行为,一般说来是不接触被害人的身体的,即非身体接触或者非私密部位接触,如对被害人露阴、面对被害人手淫、强拉被害人的衣服、多次偷剪被害人的发辫、向被害人身上涂抹污物或者泼洒腐蚀性物品、不怀好意地对被害人围追堵截、调戏取乐等等。立法者之所以将猥亵行为与侮辱行为规范在一起,是因为这两种行为本身存在密切联系,不好区分。但是比较而言,猥亵行为是直接接触被害人身体的,而侮辱行为似乎与被害人有一定的空间感,二者的微弱差别仅在此。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猥亵与侮辱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具有同一性,不宜做区分。[1]主要理由为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以后,本罪侵害的法益由妇女的“性决定权”变成了“他人的性决定权”,更无区分猥亵行为与侮辱行为之必要。从文法上讲,猥亵行为包含了侵犯他人性决定权的一切行为,而侮辱行为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一旦超出则可能侵犯另一法益,可能触犯其他罪名规范。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这里的法益,事实上就是强制猥亵、侮辱罪的犯罪客体,无论最初的妇女还是现在的他人,其“性决定权”与性自由权均无实质差别。而所谓性自由权,是指权利主体在自由意志支配下自由选择或者拒绝性伴侣的权利,是现行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强奸罪的犯罪客体,这种表述无疑造成本罪与强奸罪犯罪客体的混淆。刑法分则同一章节犯罪的排序本着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由重到轻排列,强奸罪位于本罪之前,显而易见其社会危害性重于本罪,主要是两种犯罪客体的差异。如果两种具体犯罪的直接客体完全相同,行为方式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又都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范畴,那么有必要在罪名设置上规制两种不同的犯罪吗?直接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作为强奸罪的预备行为处理,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刑事立法之所以将本罪与强奸罪规制成两种不同的罪名,其根本原因是由这两种犯罪构成的要件差异性所决定的,而在诸犯罪构成要件中,犯罪客体决定犯罪性质,一种危害社会行为侵犯法益的社会政治意义越大,则社会危害性越大,分则中罪名的排列恰恰说明了这一点。显然,这两种犯罪的直接客体(侵犯法益)是有区别的,毋庸置疑,强奸罪侵害了妇女的性自由权,而本罪的客体则为他人的人格尊严权,即民事主体作为一个“人”所享有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并且受到他人和社会的最基本尊重的权利,是民事主体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与其在社会上享有的最起码尊重的结合。两种犯罪虽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其直接客体的这种差别也是很明显的。因此,本罪犯罪对象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本罪直接客体的变化,而将本罪与它罪客体混淆来论述强制猥亵与侮辱两种行为是否具有包容关系或是否具有同一性,也是不科学的。况且就“修正案九”而言,侮辱与猥亵就行为方式和行为对象而言,依然有区别,并非一个概念,多数学者也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2]
再次,如上所述,强制猥亵妇女在很多情况下与强奸罪的实行着手行为比较接近,如对象都是妇女,其法益侵害具有相似性,同属于性犯罪等等。由此带来这两种犯罪认定上的困难,如某女士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书,某男突然从后面将其抱住,强行接吻、抚摸等,某女士高呼“抓流氓”,该男子落荒而逃。对于这种行为应当如何定性?是构成强制猥亵罪还是强奸罪(未遂)?笔者认为: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性行为,则应认定为强制猥亵罪。强奸罪毕竟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中的性质较为严重的犯罪,而且这两种犯罪的主观目的、犯罪客体也各不相同,前者是基于满足自己取乐、无聊、变态等下流目的,后者是出于强行奸淫的目的。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毕竟是根植于内心的想法,最终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方式加以判断,而行为模式的相近性则给这两种犯罪的区分带来一定的困惑,对于这种情况,在认定时坚持疑罪从轻的刑事诉讼原则是非常必要的。
二、关于本罪猥亵对象由“妇女”到“他人”的变化问题
所谓犯罪对象,是指犯罪行为直接指向的人和物。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即是“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行为。显然,猥亵的对象由妇女变为他人。“他人”泛指年满14周岁的一切自然人,已无性别之分。为何扩大猥亵的对象?笔者认为理由如下:一是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猥亵的行为对象已不仅是妇女,男子遭受猥亵侵害的案件也不容忽视。据2013年《广东省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报告》显示,男生被迫发生性行为是女生的2.2倍至2.3倍。而且,男性被猥亵在我国有不断增加的趋势。[3]如河南发生的一起妇女猥亵中学生案件:甲与乙经常在一起玩耍,一日乙去甲家,甲母有意在柜子上放了一些钱,乙偷拿了一部分,甲母发觉后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和向学校告发相威胁,迫使乙多次与其发生性关系,使乙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乙母发现遂报案,甲母被抓获。[4]131该案是一起典型的妇女猥亵14周岁以上男子案件。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即使为男女异性间性交行为,若系女性强制男性,如妇女诱惑少男成奸者,均可认为是猥亵行为。“修正案九”扩大本罪的对象范围,乃是提高刑法同犯罪做斗争的适应性的需要,也是充分发挥刑法调控功能的体现。二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要求。在“修正案九”出台以前,本罪的对象仅限于妇女,是鉴于妇女身心方面的特殊性,有必要予以特别保护,以体现党和国家一贯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原则,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把猥亵年满14周岁以上的男子排除在犯罪之外。“修正案九”将男性公民人身尊严的权利保护也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同样的权利刑法不分性别地予以保护。三是更好发挥刑法作为保障法的作用。刑法虽属部门法,但与其他部门法比较而言,具有保障法的功能,为其他部门法律的贯彻实施保驾护航。当一种危害社会行为达到犯罪的程度,已经超越其他部门法的调整范围,刑法将其规定为犯罪,使用刑罚的方法制裁这种犯罪,既是刑法任务的要求,又符合刑法的谦抑性精神[5],同时也是时代发展、法治完善的标志。四是国外先进的立法案例可为借鉴,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32条规定:“对男或女受害人,或其他人适用暴力或者以使用暴力相威胁,或利用男或女受害人孤立无援的状态而与之进行同性性交或者其他性行为的,处三年以上六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又如《法国刑法典》第222—27条至第222—32条也对强奸之外的性侵行为,规定了构成犯罪的几种情况,也无对象限制。上述域外刑事立法例的合理之处,值得我们借鉴。由于此前不能惩治强制猥亵男子的行为,已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这种情况下我国刑法及时予以完善,弥补了刑事立法的不足。此处的“他人”,应当无性别、身份、心智成熟程度、精神状态之限制。
“修正案九”只是将猥亵的对象扩大为他人,由此引起本罪罪名的变化,但是,侮辱的行为对象依然保留为“妇女”,为何不将猥亵与侮辱的对象都统一为“他人”呢?这是立法的疏漏还是另有其因?笔者认为,现行刑法于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了普通的侮辱罪,其适用对象无性别限制,可以是男子,也可以是妇女。这种侮辱是基于贬低他人人格与名誉的主观目的而公然侮辱他人,相对于普通的侮辱罪的规定而言,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属于刑事特别法,其侮辱的对象只能是妇女,而且一般带有流氓动机。刑法之所以在普通的侮辱罪之外另行规制强制侮辱(妇女)罪,其立法意图是突出对妇女合法权利的特殊保护,当然,这两种侮辱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修订后的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中这种下流的猥亵他人形式,在我国以前的刑事普通法里面没有规定,猥亵年满14周岁以上男子不为罪,如果出于侵犯他人名誉的目的,公然侮辱的构成第二百四十六条的侮辱罪,估计这就是“修正案九”扩大猥亵的适用对象而将侮辱的对象依然控制为妇女的主要原因吧。刑事立法的诸条文之间讲究内在联系与衔接,如果在刑事普通法里面可以解决的问题,再以刑事特别法加以规制,显然是有画蛇添足、浪费立法资源之虞。
三、关于强制猥亵、侮辱罪(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与侮辱罪(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界限问题
现行刑法在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罪一章中,既设置了侮辱罪(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又设置了强制猥亵、侮辱罪,前者是指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败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这两种犯罪虽同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但是,由于立法意图与出发点不同,保护的法益也不同,侮辱罪的客体是他人的名誉。名誉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是外部名誉(社会的名誉),指社会对人的价值评判;第二种是内部名誉,指客观存在的人的内部价值;第三种是主观名誉(名誉感情),指本人对自己所具有的价值意识、感情。而作为侮辱罪客体要件的名誉应当仅指外部名誉。[6]80-82而强制猥亵、侮辱罪的客体则是人格尊严,侵害的法益应当是被害人的自我感受。这种犯罪的客体的差别引发其他犯罪成立要件上的差别,虽在实践中有时难解难分,不好判定,但是若细加分析,其差异性也是有的。下面分几种情况认定。
1.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基于满足自己或者第三人的性刺激、性满足欲望,猥亵他人(男子)的定性问题——依法认定为强制猥亵罪(第二百三十七条)。如2016年2月江苏宣判一起男子猥亵同性入刑案件:新华社杭州2月3日专电(记者陈晓波):浙江一邓姓男子在网吧趁另一名男子睡熟之际,对其进行猥亵。对此,浙江温岭市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一审宣判,以强制猥亵罪判处邓某有期徒刑8个月。[7]
由于“修正案九”的出台,猥亵对象的扩大,笔者认为,可以将男性强奸同性的行为认定为强制猥亵罪,这样2015年初发生在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海会镇年丰果园的守园大爷深夜遭一名男子强暴案件、2009年3月18日河北石家庄两名男子抢劫“强奸”一位打工仔案件[3]的定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基于损害他人(男子)名誉的目的,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的定性问题——应认定为侮辱罪。如张某是某单位的领导,因公干得罪了一批人,某日,张某正在接待外宾,一群工人用事先准备好的臭鸡蛋、烂西红柿等污物向张某身上抛洒,致使张某身体散发难闻的气味,接待外宾工作被迫停止。此事影响很大,给张某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几度抑郁。[4]145领头工人使用向被害人身上喷洒污物的暴力手段,公然贬低张某人格,侵犯其名誉权,造成张某人格的减等,其目的就是让张某难看,其行为就属于第二百四十六条的普通侮辱罪。
3.使用言辞或者文字的形式,公然侮辱他人(男子、妇女)的定性问题——应认定为侮辱罪。侮辱罪与强制猥亵、侮辱罪的客观行为方式是有区别的,强制猥亵、侮辱罪只能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排除其他方法的适用,前面已有论述。而侮辱罪除了使用暴力侮辱外(如胯下之辱),还包括言词侮辱和文字侮辱。前者是指使用言词对被害人进行戏弄、诋毁、谩骂,使其当众出丑,如被告人秦某与被害人张某是姑嫂关系,因家庭琐事结怨,某日张某夫妇在家邀请一些朋友聚会,惹得秦某不快,后因小孩子淘气引发大人的口角,秦某一气之下把其嫂子张某婚前与人恋爱并私自堕胎等婚前不贞的事实公布于众并大肆辱骂,当时就令其兄大为震惊,张某羞得无地自容,客人们不欢而散。[4]146当晚,张某便跳河自杀。秦某的行为属于言词侮辱,依法构成侮辱罪。后者是指使用书写、张贴、传阅有损他人名誉的大字报、小字报漫画、标语等形式达到公然贬损他人名誉的目的。如果排除暴力方法,使用言词或者文字的形式侮辱他人的,依法构成普通法意义上的侮辱罪。
4.使用暴力、胁迫等方法猥亵、侮辱妇女的定性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上面第一、二种情况侵犯对象均为男子,在现实生活中虽有发生,但是毕竟没有妇女受到侵害的情况多,而第三种情况行为方式容易评价行为的性质。因此我们还是把探讨的重点放在女性遭受暴力侵害情况下二罪的区分上来,试比较如下:
案例1:女职工谢某因家人住院,上班后神情恍惚地走进男更衣室,恰好遇到男职工赵某更衣,谢某便马上退出。这时,旁边的几个男职工开始起哄:“别人看了你,你也要看别人啊!”在大家的煽动下赵某一把抓住跑开的谢某,将谢某的两只手反拧过来,用另一只手强行剥开谢某的上衣,谢某挣扎,赵某又拉下了谢某的长裤,并且用手在谢某身上摸来摸去,直到单位领导赶来后才制止了这一闹剧。[4]132
案例2:女村民宋某生性活泼,被告人容某(男)误认为宋某是轻浮之人,某日,容某用下流语言调戏宋某,宋某大怒,狠狠地打了容某一个耳光,并大声斥责他,围观的人也认为容某不对。容某顿时恼羞成怒,一拳将宋某打倒在地,顺势骑在宋某的身上,抓起路边的牛粪、烂泥往宋某的嘴里、脸上、身上乱抹,还说着:“你们看啊,她吃屎呢!”宋某的嘴里、耳朵里、全身都被粪便涂抹,恶臭难忍。[4]147这次侮辱事件,由于当时围观的群众特别多,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致使宋某精神失常。
上述两个案件就行为方式而言,均使用了暴力手段,对象都是妇女,而且都呈现公然性的特点,但是,案件性质不同,案例1是强制猥亵、侮辱罪,案例2则构成侮辱罪,以此为例分析如下:
(1)从案件起因来看,侮辱罪往往是为了宣泄某种不满或者积怨,即事出有因,如容某侮辱宋某的目的是为了泄愤;而强制猥亵、侮辱罪一般与积怨无关,往往临时起意,带有突发性的特征,如男职工由于报复、破坏名誉等主观目的,强行剥光女职工的衣服的行为之所以构成强制猥亵、侮辱罪,恰恰是出于刺激、满足性欲的主观倾向。[8]
(2)从行为方式来看,案例1中的侮辱属于淫秽性的侮辱行为,而案例2中的侮辱与淫秽性行为无关,只要是使用诋毁他人人格或者名誉的手段均可。而且强制猥亵、侮辱罪尽管不排除公然进行的情况,但不以“公然性”为成立要件,多数带有私密性特征;而侮辱罪其客观方面要求必须“公然侮辱他人”,才能构成犯罪,公然性是侮辱罪成立的法定要件。再者,案例1中男职工侵害谢某构成强制猥亵、侮辱罪没有“情节严重”的要求,而案例2中,容某构成犯罪必须“情节严重”,即强制猥亵、侮辱罪不是情节犯,而侮辱罪是情节犯。
(3)从侵害法益的性质来看,案例1强制猥亵、侮辱罪侵害的是他人的人格尊严权,以及现行宪法第三十八条和妇女权益保障法有关妇女人格尊严与名誉权的规定。我们认为他人的人格尊严是强制猥亵、侮辱罪的主要客体。而案例2的侮辱罪如上所述,法律明确规定以“公然性”作为其犯罪成立要件,公然性要求犯罪必须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下,采用使不特定多数人看到或者听到的形式侮辱他人[9]727,折损被害人面子,改变他人或者公众对被害人的看法,造成其人格减等,影响被害人生活等不良后果,这和写一封信寄给被害人对其进行辱骂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因此,公然性特征决定了侮辱罪侵害的法益是他人名誉,或者称之为公众名誉。
[1]孙红涛.修改后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罪名如何确定[N].人民法院报,2015-10-21.
[2]韩轶.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几个问题[J].河南公安高等学校学报,2002,(2).
[3]我有话说.男性被性侵法律存空白专家称受害者可以是男性[N].法制日报,2015-08-06.
[4]韩玉胜.刑法各论案例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陈兴良.刑法歉抑的价值蕴含[J].现代法学,1996,(3).
[6](日)早稻田司法考试教研室.刑法各论[M].早稻田:经营出版社,1990.
[7]法制新闻.浙江宣判一例男子猥亵同性入刑一案[EB/OL].央视网,2016-02-03.
[8]彭新林.关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两个问题[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3).
[9]张明楷.刑法学(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蔡锋
Identification of Crime of Forcible Obscenity and Insult
DANGRihong
The crime of Forcible Obscenity and Insult relates to women in particular and is seen in the same light as hooliganism.In this regard,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use of violence,coercion and insult.Adjustment to criminal behavior information in“Nine Amendments”ofthe Criminal Lawplays an added securityfunction.There are three aspects that maydivide the boundaries ofthis crime and that pure insult accordingtoArticle 246 ofthe Criminal Law:bilateral relations,public nature,and insult via obscene behavior.
obscene;insult;enforcement
10.13277/j.cnki.jcwu.2016.04.001
2016-04-16
D923.9
A
1007-3698(2016)04-0005-05
党日红,女,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教授,刑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10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