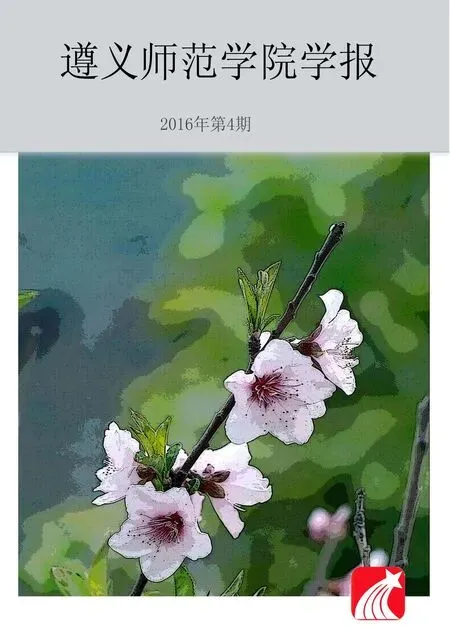共产国际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决策关系研究
汪学平
(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共产国际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决策关系研究
汪学平
(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共产国际及其军事代表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执行错误的军事战略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在请示共产国际同意后才执行的战略转移,期间工农红军关于战略转移必要的理论、物质和舆论准备也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
长征;共产国际;党的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组织人事、军事策略以及财政经济等方面都深受苏联主导下的共产国际的控制和影响,这种局面直至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决定“予以解散”时为止。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此种关系的影响,正如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党在这个时期犯了那么多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了那么大的损失,我们中国人当然要负责,但与共产国际有很大的关系”[1],这种指导错误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的战略转移。
一、共产国际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关系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第三路军第八纵队周浑元部偷袭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的最主要通道——黎川,中央苏区和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拉开序幕。此次“围剿”,蒋介石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反共方针,动员64个师7个旅6个团,另加航空队11个,飞机105架,兵力合计约80万人[2],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的统一指挥下,采用以碉堡和封锁线为中心的新式战术,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对中央苏区封锁围攻。
历经前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中央苏区范围扩展至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60个县[3],核心区域人口达200万以上[4],工农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
增至约10万余人[2],红色革命政权日益巩固。1933年初,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央苏区的危害日益严重,红军的军事战略、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则由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李德实施。虽然李德在《中国纪事》里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自辩时表示:“我对政治领导不进行完全任何干涉”[5],但是他承认“博古以及后来的周恩来,总是习惯地把一切军事问题事先同我讨论一下,然后在军事委员会上代表我的意见”[5],而他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命令行事,“他(指曼·弗雷德)要我负责在中央苏区严格执行他的一切指示,其根据是,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5],这些表明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决策者是李德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远东局负责人阿瑟·尤尔特。
“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6],中共中央充分估计到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战斗地动员群众在‘粉碎敌人新的五次围剿’,‘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口号的周围……保卫苏维埃”[6]。李德完全照搬苏联军事学院教科书的教条和苏联军事条令,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为口号、实施“两个拳头打人”战略,企图以“短促突击”战术应对国民党“围剿”军的堡垒战术。所谓“短促突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1933年9月12日给中央苏区的电报指示:“我们应该让敌第一梯队部队向前推进几里。在这时我们将迅速在两翼运动,以便出人意料地迎击敌主力部队。在先歼灭敌第二梯队之后,再以小股部队击溃其第一梯队”[7],初步表述“短促突击”理论雏形,而李德在1934年4月《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和《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里集中阐述这一战术原则,即工农红军以防御支撑点诱引敌人远离堡垒,以主力部队对被吸引来的敌人进行突然、集中地打击,以便于在己方堡垒前歼灭敌人。
至1934年4月,国民党军在江西省构筑碉堡5300个[4],修筑链接碉堡的公路6000余里[2],蒋介石严格要求贯彻稳扎稳打战略,“匪区纵横不过五百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8],此战略战术致使红军传统运动战受到遏制。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理论针对第五次反“围剿”国民党军“堡垒主义”的战术变化,同时表面上看符合工农红军此前创造的游击战、运动战战略战术关于“迅速”、“突然”、“机动”、“集中兵力”基本原则的总结,起初得到朱德、项英、林彪、彭德怀和聂荣臻等军事将领的支持,成为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运用的战术。但是在国民党军“稳扎稳打”、“以静制动”、“注重工事”、“集中优势兵力”背景下难以达到歼灭战的目的。聂荣臻在1934年2月16日与林彪向朱德总结经验教训时表示“短促突击”战术“结果仍变成堡垒战”[9],而指挥体系、战术训练和武器装备方面的严重问题致使工农红军在堡垒阵地战中存在着攻坚能力不足的致命缺陷。1934年4月28日,在博古、李德和朱德亲自督战且调集红军精锐第一、三、五军团9个主力师参战的情况下,中央苏区北部门户——广昌保卫战失利,国民党军伤亡2600余人,红军主力伤亡5000余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急转直下。
二、共产国际与“湖南计划”
日益严峻的军事形势导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始考虑撤离中央苏区问题。其实溯及到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曾建议中央苏区红军在保卫中央苏区时,应该特别参考前四次反“围剿”运动战和游击战关于红军“机动性”的成功经验原则,同时:“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7]。同年7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负责人埃韦特给上级皮亚特尼茨基报告中表示:“尽管我们竭尽全力,最终还是未能摆脱僵局。而敌人的工事和数量反而有了增加。……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但是我认为,近期我们摆脱中央苏区所处困境的希望不大”[7]。可见,第五次反“围剿”尚未开始,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就已经在考虑是否放弃中央苏区根据地问题。
同年11月2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上海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曼·弗雷德提出“湖南计划”[10],要求中央苏区红军主力跳出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分别向赣北和湖南西北部地区突破,打击北面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侧翼和后方。“湖南计划”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绝和共产国际执委员会的否定。李德1933年12月23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复电表示:“尽管计划被否定了……总计划的原则被采纳了。在(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强调(有必要)指出,我们将来的策略也应该是
把西面作为进攻的方向”[7]。共产国际执委会1934年1月2日致电中共中央表示中央苏区军事行动根本上应该由中共中央来决定,而且“我们认为,在目前形势下,11月27日的计划是不利的”[10]。
1934年4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屡战失利,中央苏区南线门户筠门岭、北线门户广昌等战略要地相继失守,虽然博古在《红色中华》社论坚称:“我们要保卫土地、自由、苏维埃,直至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最后一口气”[11],但是撤离中央苏区的计划已经成为中共中央高层的理性选择。1934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瑞金会议决定实施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博古文选·年谱》记述:“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12],并将这一会议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埃韦特(即李德《中国纪事》中的阿瑟·尤尔特)1943年6月2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说中共中央“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10],他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考虑在中央苏区反“围剿”各种可能性穷尽的情况下:“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才应使用”[10]。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反复研究讨论后做出决定,并复电中共中央和埃韦特:“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10],这是中央红军此后进行战略转移行动的决策根据。
三、共产国际与长征的准备
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4年6月16日电报及此后的指示,中共中央立即采取一系列战略转移的准备措施,包括扩红运动、粮食储备、福建战役、舆论宣传、转移侦察和探路这些准备措施都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部署指示下进行的。
1934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公开指示信,指出“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了五六七三个月扩大红军五万的计划”[13],为长征进行兵员的补充,要求各级动员机关无论如何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该计划。根据红星报报道,工农红军1934年5月扩大23025人,6月扩大29688人,7月(至15日止)扩大2457人[14],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之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10多个新兵团、140万发子弹、7.6万多枚手榴弹和大批物资补充到红军各主力军团[15]。
为配合红军的战略行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4年6月17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建议“发动福建战役,将其作为预防和吸引敌人”的措施[10]。1934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以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人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途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分成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关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意图,朱德后来表示:“是准备退却,先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16]
193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把全中国变成他的殖民地,把全中国的民众变为亡国奴”的野心,抨击国民党政府不仅“出卖了东三省,出卖了热河内蒙”,而且向“全中国唯一反日反帝的工农的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进行不断的‘围剿’”[6]。《宣言》在日本帝国主义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并不断向华北蚕食,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情况下,既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向日本宣战,又起到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作用。
1934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举行秋收六十万担借谷运功,并决定立即征收今年的土地税,随着武装保护秋收的运动迅速切实的完成,以供给各个战线上红军部队的需要”、而且“这一任务,一般的要在九月十五日前完成”[6],从时间节点来看,此举目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保证红军粮食供给,而是为工农红军进行长征准备粮食必需品,而是对共产国际关于“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的应对措施[10]。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任弼时等组建红六军团后“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其目的在于与活动在贵州、湖南和四川范围内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取得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6],此训令拉开红军长征的序幕。时任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回忆指出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17]。
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后,1934年9月17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确定此前“湖南计划”既定的湖南西部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目标,“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
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10]。9月26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为即将实施的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进行政治动员。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共五个主力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组成的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共约8.6万人,分别自瑞金、雩都地区出发,实施战略转移向预定的湖南西部出发,自此开始漫长艰苦的“长征”历程。尽管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周密的筹划和准备,但是基于李德“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的考虑,因而关于工农红军战略转移部署仅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知情,“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分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5]。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博古、李德为首的最高“三人团”“没有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干部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而且“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即李德)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6],导致工农红军在长征初期一味退却逃跑消极避战,携带大量辎重和甬道式行军严重削弱红军机动性能,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包围线,尤其是湘江战役时遭遇严重的损失。
[1]周恩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M](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熊尚厚.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准备之考察[J].民国档案,1992,(1):101-105.
[3]凌步机.中央苏区区域范围考察[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2,(3):50.
[4]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5]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第9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8]王多年.反共戡乱(上篇第四卷)[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
[9]周均伦.聂荣臻年谱(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11]博古.我们的位置在那边,在前线上,站在战线的最前面[A].李志英.秦邦宪(博古)文集(下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12]吴葆朴,李志英,朱昱鹏.博古文选·年谱[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1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1934-193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4]一年来扩大红军的统计[N].红星报,1934-07-22.
[1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16]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A].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史料[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17]萧克.开路先锋:红六军团的先遣西征[J].军事历史,2006,(6):8.
(责任编辑:娄 刚)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intern and the decision of Long March by Chinese Workers'and Peasants'Red Army
WANG Xue-pi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Zunyi Normal College,Zunyi 563002,China)
Long March made by Chinese Workers'and Peasants'Red Army resulted from the wrong military strategies carried out by Comintern and its military advisor in the counterattack on the“fifth encirclement and extermination campaign”;it was also a kind of strategic shift implemented by CCP after it was agreed on by Comintern;and the necessary theory,materials and preparations for public opinion about strategic shift were conducted under the guide of Comintern as well.
Long March;Comtern;Party’s construction
D231
A
1009-3583(2016)-0009-04
2016-03-16
2013年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长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系研究(13SZK004)”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2015年项目“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期间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15KRIZY10)的阶段性成果
汪学平,男,河南洛阳人,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党史研究。